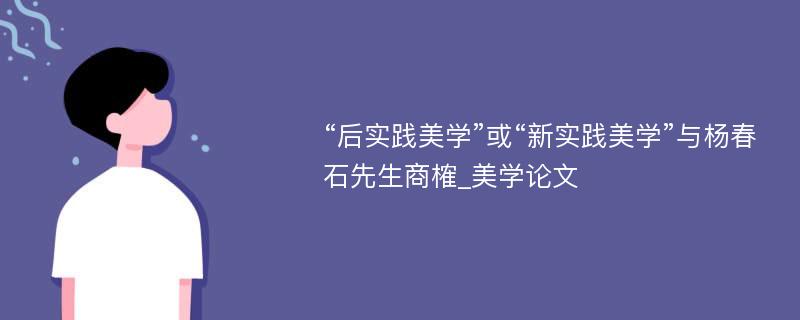
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与杨春时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走向论文,杨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所在
杨春时先生对实践美学(准确地说应称之为“旧实践美学”)的批评,应该说是相当有力的 。较之以“反映论”为代表的“前实践美学”,旧实践美学虽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却仍陷 于客观论和决定论的桎梏不能自拔,以至于有诸如“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之类于情 不合、于理不通的说法。依逻辑,一个东西,要么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要么是个体性 与社会性的统一,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社会性和客观性并非一个逻辑层面 上的东西,怎么能统一,又如何统一?究其所以,无非既不愿意放弃客观论和决定论的立场 ,又不愿意像彻底的客观派美学那样,干脆主张美是客观世界的自然属性。正是这种理论上 的不彻底,造成了旧实践美学在逻辑上的混乱和在论争中的尴尬。只要不转变这个立场,引 进再多的新范畴(无论是实践范畴还是其他什么范畴)都无济于事。即使没有后实践美学的批 判,旧实践美学也终将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并不仅仅因为旧实践美学 在成为主流学派以后“无所建树,停止发展”,更因为它在理论上“先天不足”,具有无法 克服的自身矛盾。
然而,后实践美学虽然对旧实践美学攻势凌厉频频得手,其自身理论建设的基础却也相当 脆弱,无法真正取代旧实践美学。杨春时先生批评实践美学关于审美起源的说法——原始人 在自己劳动创造的产品中看到自己的本质力量,因而产生喜悦的心情“只是一种臆测”(注:本文所引杨春时先生观点,均见《走向“后实践美学”》一文,《学术月刊》1994年第5 期。), 但他提出“审美发源于非理性(无意识)领域”,难道就不是臆测?至于审美“突破理性控制
,进入到超理性领域”,就更是问题多多。什么叫“超理性领域”?杨春时先生说是“终极 追求”。我不知道他说的“终极追求”又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它真是超理性的,是类似 于道、禅、般若、真如一类的东西,那它就不能为理性所把握,只能诉诸体验甚至超感体验 ,也用不着什么美学。如果说对超感经验或超感体验之类的描述也是美学的话,那也不是什 么“后实践美学”的事,因为老庄、禅宗等等早就说得很多而且很透彻了。
就算超理性是所谓“终极追求”,审美是“超越现实的自由生存方式和超越理性的解释方 式”吧,那么,人的这种超越精神、自由追求和解释方式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吗?是上帝赋予的吗?是人一生下来就有的吗?要不然就是杨春时先生自己想出来的。事实 上,超越也好,自由也好,种种生存方式也好,都不是人的天赋、本能或自然属性。它们只 能来源于实践并指向实践。尤其是杨春时先生最为看重的“自由生存方式”,就更是指向实 践的。的确,艺术和审美能够创造一个超现实的美好境界,它可以在现实领域中并不存在。 问题是,人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现实领域中并不存在的美好境界呢?难道只是为了满足自 己的想像力和好奇心吗?也许,杨春时先生会说,是为了“终极追求”。那么,人又为什么 要有“终极追求”呢?难道不正是为了让现实的人生活得更幸福吗?这就要诉诸实践,否则就 没有意义。人不能没有想象,但也不能只生活在想象中。同样,人不能只有实践,但也不能 没有实践。当然,实践并不万能,也并不理想。它并不像旧实践美学设想的那样,可以造就 一个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杨春时先生说得对:“生 存的意义问题不是现实努力所能解决的”,但它又是不能不诉诸现实努力的。努力尚且不能 最终解决,不努力那可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实践解决不了的问题(生存的意义),艺术和审美同样解决不了。以为艺术和审美就能解决 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这只是杨春时先生和某些现代哲学的一厢情愿。杨春时先生在批判旧 实践美学把现实审美化的同时,显然也把审美理想化了,正如他在批判旧实践美学理性主义 倾向的同时也陷入了神秘主义一样。
何况我们别无出路别无选择。自从人通过劳动使自己成为人,从而告别了动物的存活方式(
顺便说一句,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生存方式”)以后,他就踏上了一条永无止境的不归之路,那就是:他必须通过不断的实践斗争,使自己越来越成其为人。
也许,这才是人的“宿命”,而实践也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旧实践美学的确没能很好 地解决许多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实践就不能成为美学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我们不能因 为旧实践美学的失误,就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新的美学来取代旧实 践美学,但不是用“后实践美学”,而是用“新实践美学”。
二、逻辑起点
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至少和杨春时先生是有对话基础的,因为我们都同意,创造具 有权威性的现代美学体系,其关键是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可靠的逻辑起点。整个美学的范 畴体系应该也只能从这个逻辑起点中推演出来。但我还想强调三点。第一,从逻辑起点进行 推演,一直推演到艺术和审美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有不少中间环 节 ,不可能要求一步到位。第二,重要的是推演出美学的“第一原理”,即关于美和艺术的本 质的定义,然后再逻辑地顺次推演出一切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其中,不能有任何一 个规律是从另外的原则引入或外加进来的。第三,这个逻辑起点必须是在人文学科范围内不 可再还原的。不可再还原,才具有可靠性。如果杨春时先生同意这三点意见或这三个前提, 那我们就可以展开讨论了。
杨春时先生认为,“应该确认社会存在即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为了剔除其中的古典主 义和形而下的因素,杨春时先生把它改造为“生存”。人的社会存在即生存,万事万物都包 括在生存之中。生存是第一性的存在,是哲学唯一能够肯定的东西,当然也能作为美学的逻 辑起点。更重要的是,生存以实践为基础,却又超出实践水平,做“后实践美学”的逻辑起 点就更为合适。何况,在杨春时先生看来,人的生存有三种方式,其中“自由生存方式”明 显 地具有超越性,很自然地就能得出“审美的本质就是超越”的结论,也符合他的方法论思想 (美和审美包含在作为逻辑起点的那个概念或范畴中)。
这似乎无可挑剔。但可惜,这即使从逻辑推演上讲,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杨春时先生既然 以“生存”为逻辑起点,那他的美学就该叫做“生存美学”。然而杨先生却宁愿叫做“超越 美 学”,因为他的“第一原理”是“审美的本质就是超越”。从这一点上讲,他把他的美学称 之为“超越美学”也并无不妥之处。问题是,生存并不等于超越。比如所谓“自然生存方式 ”似乎就不具备超越性,“现实生存方式”看来也成问题。从生存到超越,显然缺少中间环 节。杨春时先生何以能够从生存推演出超越来,我们不得要领。
何况,他的那个逻辑起点(即所谓“生存”)本身就十分可疑。什么叫“生存”?它的内在规 定性是什么?人的生存和动物的存活又有什么区别?人是怎样从动物也有的“存活”一变而为 “人的生存”的?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有了自由和超越的精神和可能?不把这 些问题都一一解决,指望着从“生存”两字就能直接地推演出美的本质,也不过一厢情愿。
显然,所谓“生存”,也是可以再还原的。即使如此,我们和杨春时先生也仍有对话的可 能。因为我们(包括旧实践美学)都同意:“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既然如此,我们便只 要问一个问题就行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成为人?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获得了“ 人的本质”?
答案也只有一个:是劳动。只要“劳动使猿变成人”这一结论不被新的科学研究所推翻, 这个答案也就勿庸置疑。既然是劳动使人成为人,是劳动使人获得了“人的本质”,而我们 又都同意“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那么,我们就该都同意,是劳动使美获得了“美的本 质”(其实同时也使艺术获得了“艺术的本质”)。因此,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就不能也不该 是别的,只能是劳动。劳动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也最一般的实践。以劳动为逻辑起点, 也就是以实践为逻辑起点。这正是我们虽然和旧实践美学多有分歧,却仍然要把自己的美学 称之为“实践美学”的原因。
以劳动作为艺术和审美一般原理的逻辑起点,首先意味着以劳动作为艺术和审美最初表现 的历史起点。但与旧实践美学不同,新实践美学更关心的不是或不仅仅是人类的劳动如何产 生出艺术和审美,而是它为什么必然会产生出艺术和审美来。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艺术 起 源和审美起源并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学、人种学、文化学或心理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 新实践美学的艺术发生学和审美发生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的任务,是要从生产劳动的实 践原则中逻辑地推演出艺术和审美的本质规定性。因此,在这种探索中,既不能把艺术审美 和生产劳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我们和“后实践美学”的不同),又不能把它们等同起 来(这是我们和“旧实践美学”的不同)。对于我们来说,劳动只是研究艺术和审美起源的一 个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开始,我们不会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始劳动对原始艺术有什么影 响”、“射箭的弓怎样变成了拉琴的弓”诸如此类的一般描述上。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从 发生学的角度去打开人的感性心理学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巨大书卷,并从哲学的高度揭示艺术 和审美必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这个观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邓晓芒撰写《艺术发生学 的哲学原理》,以及邓晓芒和我合作撰写《走出美学的迷惘》(注:该书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
时就提出了,可惜至今仍未 能引起美学界足够的重视和注意。
三、内在规定
劳动能够成为美学的逻辑起点吗?这恐怕是杨春时先生要怀疑的。按照杨春时先生的方法论 思想,美学的逻辑起点中应该包含着美,而劳动似乎没有。如果劳动即是审美,劳动产品即 是艺术作品,则山货店就会变成美术馆,工地也会变成歌舞厅了。我们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地 把劳动和艺术、审美混为一谈,但如果不揭示劳动的内在规定性,则上述误解仍不能消除。
无疑,劳动不是艺术,也不是审美。原始劳动就更不是。借用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它最初 不过是人类在死亡线的边缘所作的一次“获生的跳跃”。在这种水平极其低下的活动中,人 类随时都可能走向死亡或者重新沦为动物。因此,除了实用功利的考虑,他不可能还有什么 别的考虑。
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最原始、最简单、最粗糙、水平最低的生命活动中,也已经蕴含着(而 且必然地蕴含着)艺术和审美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还十分微弱,并不起眼,甚至还不能为 原始人所自觉意识,也不即是艺术和审美,但有些萌芽,已经十分可贵了,因为如果连这么 一丁点因素都没有,我们实在不知道艺术和审美将何由发生。
蕴含在原始生产劳动中的艺术审美因素就是劳动的情感性以及这种情感的可传达性和必须 传达性。原始劳动,即便再简单,再粗糙,水平再低下,也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生存方 式而不是动物的存活方式。人与动物有什么本质区别?区别就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 ,而动物的生命活动则是无意识的。正是意识,使动物也有的“表象”上升为“概念”,“ 欲 望”上升为“意志”,“情绪”上升为“情感”。人的劳动与动物的觅食之最本质的区别也 正在于此。动物在自己的觅食过程中只会产生情绪。这些情绪会随着过程的终止而消亡(一 匹猫不会因为一想到自己曾经成功地捕捉了一只老鼠就笑起来)。人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却 会产生情感。他会因此而爱上自己的劳动产品。我们说“会”,不是说每次劳动都会这样, 或每个劳动者都会这样,只是说有这种可能,而动物是没有这种可能的。猫不会把吃过的老 鼠尾巴挂满一身,人却会欣赏和炫耀自己的劳动产品。也就是说,人的劳动具有情感性,它 是一种“有情感的生命活动”。
人不但会在劳动中产生情感,他还会以劳动产品为传情的媒介,把情感传达出去。正如马 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你使用我的产品而加以欣赏,这也会直接使我 欣赏。在这种相互欣赏中,情感就借助劳动产品这个中介而得到了传达。唯其如此,工匠之 间相互赠送工具,战士之间相互赠送武器,才会是一种相当之重的情分。杨春时先生难道从 来就没有过一点点这方面的体验吗?如果当真没有,那实在是太不幸了。要知道,即便是一 个猎手或一个农妇也是会有这种体验的。当他们打到一只硕大的猎物或种出一种稀罕的菜蔬 时,也会请左邻右舍乡里乡亲一同分享。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这样做,并不一定出自某种功利 目的(比如睦邻友好)。基于功利目的的考虑是有可能的。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只因为他们 在劳动中产生的喜悦需要传达,这才有了炫耀,有了不计功利的分享。
蕴含在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中的这种艺术性因素和审美性因素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恰 恰相反,缺失了这一环节,劳动就不成其为本来意义上的劳动,就会变成“异化劳动”了。 由于异化日久,很多人已体验不到劳动的情感性,甚至怀疑劳动是否当真具有情感性。这并 不奇怪。但这丝毫也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逻辑和经验两方面证明这一点。劳动,尤其是原始 劳动,常常是一种集体的行为。它需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功 利目的的吸引是远远不够的。仅靠功利维系的团队是酒肉朋友乌合之众。树一倒,猢狲就散 。这就同时还需要情感的维系。只有功利需要再加情感维系,同步的、相互协作的社会性劳 动才有可能。即便奴隶,在一起抬石头时也会喊上一声“哥儿们,一起来吧”。这份情感, 我自己在强迫性劳动中就曾体验过。至于本来意义上的劳动,就更不可能没有情感了。我们 甚至还可以说,情感不但是劳动的产物,它还是劳动的前提。
勿庸置疑,劳动,尤其是原始劳动,从根本上讲只是人的一种功利活动。因此,在原始生 产劳动中,艺术性因素和审美性因素归根结底还是处于附属性地位。它们随时随地都要以生 产 劳动的实际效益为转移,否则原始人类就无法生存。在这时,艺术和审美的本质还是潜伏着 的。它们还只是具有艺术性和审美性的“因素”,远不是艺术和审美。
四、第一原理
从蕴含在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中的艺术性因素和审美性因素,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和审美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有诸多中间环节,比如巫术与图腾,本文无暇论及(注:如有兴趣请参看拙著《艺术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这里 要回答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原因,最终使艺术和审美必然地要从生产劳动中诞生出来。也 就是说,艺术和审美发生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
还是要从劳动说起。正是劳动而不是别的,使人建立起两种学术界都承认的关系,即人与 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还有第三种关系,却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人与劳动的关系 。劳动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也是使人从猿变成人的根本原因。能够使人 成为人的,也能够证明人是人;而原本不是人的,也必须证明自己是人。因此劳动与人的关 系就是一种确证关系:劳动以其过程和产品证明人是人,人则以某种形式证明劳动是人的劳 动 。
证明劳动是“人的劳动”的形式是一种心理形式,它就是确证感。这种证明之所以要通过 一 种心理形式来实现,是因为“人的确证”归根结底是人的自我确证。因此,它必须能为每个 人所意识到,也就只能诉诸人的内心体验。事实上,正如人只有在感到自由时才自由,在 感到幸福时才幸福,他也只有在感到被确证时才被确证。也就是说,人的确证是要由确证感 来证明的。母亲疼爱婴儿,猎人炫耀猎物,小男孩因水面的圆圈而惊喜,艺术家因遇到知音 而激动,这些都是确证感。正是靠着它们,人确证了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而那些不能使人 体验到确证感的劳动,则是“异化劳动”。
人的劳动确证人是人,确证感则确证劳动是人的劳动。可见,确证感,既是人确证劳动的 心理形式,也是人确证自己得到了确证的心理形式,是“确证的确证”。因此,从理论上讲 ,任何人都不能体验不到确证感,无论他用什么方式。事实上,人类体验确证感的方式是很 多的。小男孩把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小女孩在纸上画出圆圈,都是。他们是那样的幼小, 有此一举,也就够了。但人类不能满足于此。人类必须创造一种普遍可靠行之有效的方式, 确保(至少在理论上确保)人人都能体验到确证感,并能传达这种确证感。这个方式,就是艺 术和审美。
艺术和审美起源于劳动。因为人最早是在劳动中,在自己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体验到确 证感的。正是“确证”两字,把人的“喜悦”和动物也有的“兴奋”区别开来。也就是说, 他喜悦,不仅因为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他生存的需要,还因为它能满足他确证的需要。他能在 他的产品那里体验到确证感。唯其如此,他才会爱上他的某些(不是所有)产品(比如工具)。 他会觉得他的这些产品不但是“好的”(合目的),而且是“美的”(有感情),因而爱不释手 ,甚至到处炫耀,并希望别人欣赏,因为这是他证明自己是人的“物证”。炫耀,就是“出 示”证据;欣赏,就是“认可”证据。
无疑,人的这种意识(如果它可以叫做审美意识或艺术观念的话)最初是十分朦胧甚至不自 觉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炫耀,为什么要请别人欣赏,所以它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无 意识”。原始人甚至会把那些原本确证自我的“物证”看作神的恩赐,把自身本质力量的内 在闪光当作外在对象来崇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这些“神秘的圣物”体验和传达确证感 ,因为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神灵。人所崇拜的一切,归根结底都只属于人自己。至于“不自觉 ”和“无意识”,则无非证明它们在理论上已“不可再还原”。从这个意义上讲,确证自己 是人,体验并传达确证感,就是人性的普遍共同原则。
总之,人在劳动中获得了一种心理能力,即通过确证感的体验,在一个属人的对象上确证 自己的属人本质。审美就是这样一个心理能力和心理过程。换句话说,审美,就是人在一个 属人的对象上体验确证感的心理能力和心理过程。这个对象,最初是劳动产品(主要是劳动 工具),后来则主要是艺术品和自然界(这一发展演变过程另文讨论)。但不管它是什么,只 要能使人体验到确证感,它就是审美对象。确证一个东西是不是审美对象的唯一标准是确证 感。由于美是要靠美感来确证的,因此美感就是确证感;而为美感所确证的美,也就是能够 确 证人是人的东西。正因为“美是能够确证人是人的东西”,所以美是肯定性的(丑则是不能 确证人是人的东西,所以丑是否定性的)。又因为确证自己是人,乃是人的“第一需要”, 是艺术和审美发生的“第一推动力”,因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观点,就叫做“ 审美本质确证说”。这也是“新实践美学”区别于“旧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关键 之一。
当然,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其间尚有许多中间环节和逻辑过程,但已非短短一篇论文所能 尽说。这里不过把最基本的问题提出来,并以此引玉之砖求教于杨春时先生及诸大方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