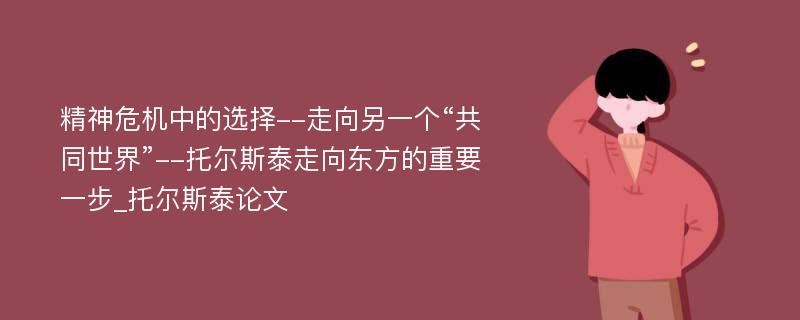
精神危机中的抉择——走入另一个“共同世界”——托尔斯泰走向东方的重要一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走向论文,危机论文,精神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到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和激变,人们总会提到著名的阿尔扎马斯之夜。那是1869年9月,托尔斯泰去平扎省置买田产, 夜宿在阿尔扎马斯这个小镇的旅馆里。“我突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念头,夜里两点钟,我痛苦,害怕,恐惧起来,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我坐起来,吩咐套车……”这段给妻子信中谈到的情节,后来被写入一篇没有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里:我曾试想,是什么东西占据了我的心灵:是买到的东西,还是妻子。没有什么值得快活的,这一切都是虚无。怕死盖住了一切。……刚一躺下,突然由于惊骇又坐了起来。苦恼,就象呕吐前常有的苦恼一样,不过只是精神上的苦恼。不得了,真可怕。看来,死是可怕的。如果你想起生,那么快要死的生是可怕的。不知怎么,生和死溶为了一体。不知是什么把我的心要撕得粉碎,可又不能撕碎。……
存在主义的先驱,俄国著名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把托尔斯泰的这一心理危象视为人们从平常生活的“共同世界”落入“个人世界”的例证。人们为了混迹在“共同世界”,不能也不敢看到一切有违这个“共同世界”的理性视为常识和公理的东西。但是,死亡却不顾忌这一点,它有自己的真理。它能够把人驱除出那个“共同世界”,使人在“个人世界”之中,用自己独特的非理性的眼光,面对先前不敢正视的一切,认识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当然,还有“特殊的人”,能“在精神极度兴奋的罕见时刻”,“会听见和理解神秘的死亡语言。”而托尔斯泰就“获得了这种机会”,这就是以“死亡的疯狂”,“把人们从生活的恶梦中唤醒”的阿尔扎马斯之夜。
舍斯托夫特别看重阿尔扎马斯之夜,他指出,描写这一夜的“《狂人日记》可以被看作托尔斯泰50岁以后所写的全部东西的总标题。”这“‘疯狂’就在于,从前以为是真实的东西,现在看来是虚幻的东西,从前以为是虚幻的东西,现在则以为是唯一真实的东西。”
这里,舍斯托夫指的是托尔斯泰的精神激变。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的这一精神激变是非理性的产物。在这里,他再三强调这阿尔扎马斯之夜降临的突然性:托尔斯泰“没有任何明显的外在原因,突然被可怕的难忍的苦恼所惊扰”,“周围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切照旧”,而“托尔斯泰突然无缘无故地焦虑不安”……同时,舍斯托夫也指出“托尔斯泰一生在心灵中都觉察到那个把自己逐出‘共同世界’的东西”。他列举的是发生在托尔斯泰幼年时的一次次精神刺激和精神发作。不过,“娱乐,游玩,关心生活,一切充满人生的‘事情’,诱使托尔斯泰长期离开他的异常梦幻,”因为他“本能地害怕不在共同世界中而在个人世界中生活”。(注:以上引文均见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99—107页。)
那么,阿尔扎马斯之夜为什么会突然地降临在斯时斯地?为什么它就决定了托尔斯泰后半生的创作主题和精神探索呢?
必须指出的是,舍斯托夫也许忽略了一点:阿尔扎马斯之夜发生在托尔斯泰40岁(1869年)距一般认为的托尔斯泰发生精神激变的时期(通常以托尔斯泰在50岁后写的《忏悔录》(1879—1881)作为托尔斯泰思想发生激变的标志,以此来划分其创作时期)还有10年。如果说,阿尔扎马斯之夜标志着精神激变,那么,为什么在40岁至50岁之间,托尔斯泰还创作了显然属于精神激变前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而且舍斯托夫也说,托尔斯泰这时期还是那个“共同世界”的“高尚的欺骗的献身者”,他正一面“教导人们夸耀正面生活和扼杀真理”,一面“从傻瓜手里极便易地买到庄园,无情地欺负无地的农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阿尔扎马斯之夜之后。
如果非理性的解释毕竟不能告诉我们答案,那么我们只有诉诸理性的解答。
实际上,阿尔扎马斯之夜在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中很难视为一个动因性的事件,它只是托尔斯泰精神危机的一个表征。我们在考察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的时候提及它,只是想说明,托尔斯泰将自己逐出那个越来越认识到“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的“共同世界”,不是“突然”的,不是非理性的觉语,而是他长期精神探索的结果,如果把阿尔扎马斯之夜视为获得觉悟之机,那么它只是长期求索而偶然得之的。
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把自己逐出那个“共同世界”,不是为了象安娜·卡列尼娜那样,要“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走入舍斯托夫所谓的“个人世界”,而是要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共同世界”。可以说,这正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的重要特征。
阿尔扎马斯之夜的象征性意义在于,人从“共同世界”恍忽间抽身出来,藉着生和死的观照,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实际上,阿尔扎马斯之夜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与皮埃尔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种精神的危机和震颤。
要把自己逐出这个看上去是唯一的现实的“共同世界”,是多么不容易,从《哥萨克》到《阿尔贝特》,实际上都隐藏着托尔斯泰想要摆脱这个“共同世界”的梦。但是同时,托尔斯泰又在这个“共同世界”上卖劲儿地活着:就是在他创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期,“他管理产业十分忙碌,对牛羊的饲养繁殖大有兴趣,照顾他的财产,总之什么都干。”
正如托尔斯泰后来在《忏悔录》(1879)里说的,这不过是在“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不过我们起码可以由此看到,托尔斯泰的思想是面向现世生活的,而同时,他也从未停止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他1876年4月28 日在给费特的信中抄引了贝朗瑞的四句诗:
死神自己会来,
何用我们关怀。
好好生活——这个课题
却须就地解开。(注:《托尔斯泰文学书简》,488页。)
我们可以从70年代托尔斯泰的书信中听到他孤独、怀疑、消沉的怨言,看到他的精神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他几乎把自己完全闭锁起来。从交往和通信中,我们看出他对俄国内外的一切时事兴味索然,(注:《托尔斯泰在70年代》,207—208页。)从大量笔记来看,他醉心于阅读一系列西方哲学著作:从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当然,看来最有感触的大抵还是叔本华。(注:《托尔斯泰传记材料》,3卷,18页。)
在《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后期,托尔斯泰醉心于叔本华,他认真地讨论“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法则”,苦苦地求索“天人关系”,求索人生的意义。阿尔扎马斯之夜发生的前五天(1869年8月30日), 即托尔斯泰赴平扎省买地的头一天,他给费特写去了那封狂热推崇叔本华的信。(注:《托尔斯泰文学书简》,421页。)因为在《战争与和平》中, 天道的大势粉碎了一切人为臆造的“进步”和“历史科学”,粉碎了一切西方理性和科学的高傲,它甚至使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感到一种完全不可抗拒的宿命力量,连探索主人公皮埃尔也相信没有上帝的意志,一根头发都不会从头上掉下来。那么,人生的探索,乃至人类生存本身,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许果真象叔本华断言的,生命毫无意义?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面临了新的危机。这大抵就是阿尔扎马斯之夜的心境,也是这一时期精神孤独中哲学思考的心境。
我在人类知识之林中,在数学和试验科学的光照下,在思辨科学的昏暗中彷徨……出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因为,看来,“严格合乎理性的认识——象笛卡尔所作的那样,从怀疑开始,抛弃任何一种让人相信的认识,并把一切重新建立在理性和经验规律之上”,只能“提供一个肯定的答案,叔本华的答案,即生命没有意义,它是恶。”托尔斯泰分明看到,理性不能给生命以答案。
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该做些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是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象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注:《托尔斯泰文集》,15卷,41页。)
这种周期性的精神抑郁,实质上就是一次次大大小小的阿尔扎马斯之夜,一次次将自己逐出“共同世界”,在“个人世界”里进行着一次次向死的追问:
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拥有6000俄亩土地,300匹马, 那又怎么样呢?
好吧,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呢?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缘,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注:《托尔斯泰文集》,15卷,14—16页。)
“生活中除了死,前面再没有什么了……”1876年2 月他给哥哥也这样写道。
在这一个个阿尔扎马斯之夜的面死而生中,在托尔斯泰面前或许也闪现过舍斯托夫引以为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舍斯托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拯救自己灵魂的圣者一样,一向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要敢想敢干,要走向沙漠,走向孤独生活。”“‘一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敌人”,因为“灵魂越分离越孤独,它就越能找到和碰到自己的创造者和上帝。”(注:以上引文均见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35页。)
这种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思想模式认为,人只有在被逐出“共同世界”之后,成为一个否定了“共同世界”之理性的个人,才能清晰地,“本真”地“发现自我”。
而令舍斯托夫不满的正是,托尔斯泰违背了他所认定的真理之路:走出人们的“共同世界”、走入“个人世界”而觉悟人生的真谛。对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最终不是走入“个人世界”去觉悟人生,而竟是走入另一个“共同世界”:走向人间,去向一个村妇帕申卡寻求真理,“在菜园子里做工,教孩子们读书,还照料病人”这些“对古典主义的赏光”的描写,舍斯托夫大加揶揄。(注:以上引文均见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123页。 )然而正是在这条令这位西方化哲人大惑不解的道路上,托尔斯泰走近了中国古典文化思想。
在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中,个人只有在上配天道、下张人伦的整个社会伦理系统之中,在“共同世界”中有了自己的定位,才能理解自己的真实存在。人的本质是仁。仁者人也。仁,《说文》注云读如人相偶之人。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词。中国的个人不仅是生活在家族、国家之中的,只有把个人的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发现自我的存在和价值,而且中国人认为自己和天地万物为一体,自我完成——“成人”是和成物——使天地万物达到完善,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相统一的。
的确,在阿尔扎马斯之夜的死的观照下,托尔斯泰的面前摆着两条路,或是象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借着那支理性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在死的观照下,看透并决心摆脱那个“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的“共同世界”,“摆脱所有的人和自己”;(注:《安娜·卡列尼娜》第7部31章。 )或是象列文那样,抛弃这个“共同世界”公认的理性答案,而全身心地投入另一个“共同世界”,去向“挖出了铁、传授了伐木、驯养了牛马、传授了播种、传授了如何共同生活、安排好了我们的生活”(《忏悔录》)的人们的那个“共同世界”,寻求关于生命意义的信仰和知识。
也许,在一次次阿尔扎马斯之夜的向死的追问下,托尔斯泰也曾产生过“摆脱所有人和自己”的念头:列文这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正是“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但是,人应该走向联合这一一贯信念使托尔斯泰扭转了方向。在将自己逐出那个使生命成为罪恶的“共同世界”之后,他却转向了另一个“共同世界”。因为他从根本上就不相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个人世界”存在,自然也就不相信这个“个人的世界”可能有到达真理的力量。
1870年7月21日, 托尔斯泰在笔记上谈到从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家的缺点,认为即在于他们仅承认“个体(即所谓主体)的自我意识”,他认为,人既可以意识其自身是“一个人,一个个体”,但也可以“非个体性地”意识到自身是整个世界。他写道,“一个人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是‘一切’,还是‘我’,依年龄不同而使然。”托尔斯泰认为,人之出生,便是一种个体化,即“获得个体性地看待一切的能力”。他认为,这出生是“从总的生命转向个体性的迷误”。而在生命的过程中,人不断地“涤除自己的个体性,渐渐地不再作为单一的人,而是和整体相融合。”而死,有时是缓慢的(表现为衰老的)死,就是停止个体性的生存,摆脱“以个体性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迷误”。当然,人到中年,当他感到自己“正值生命旺盛之时”,他“也能够看到自己个体性的迷误,而意识到总体生命的真理。”(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48卷,126—128页。)
既然不承认脱离总体的个体性,那么,托尔斯泰也就自然不承认个体性的认识能力:
“无数的人和其它生物大概构成着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就象一个细胞不能理解整个机体的生命一样。”1876年4月14日,托尔斯泰在给A.A.托尔斯塔娅的信中写道。 (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62卷,266页。)
“我是什么?是永恒的一部分。”(注:《托尔斯泰文集》,15卷,44页。)只有把自己融于人群,走入“共同世界”,生命才有意义,也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人们只有在整个人类的心中见到自己,才能把握自己的生命。”(注:《生之道》第3章。)
而对于个人的修养和完善,也是如此:独自一个人或是一些人是无法达到洁净的。要洁净就得大家一起洁净。把自己隔离开来不染污泥,这是最严重的不净。(注:《托尔斯泰文集》,17卷,144页。)
这些都是托尔斯泰坚持至终的观点。相反,从“个人世界”托尔斯泰没有看到生命的真实意义:“‘我的生命是什么?’——‘是罪恶。’——完全正确。错误仅仅在于,我以只适用于我个人的答案去看待一切生命。”是的,“谁也不会妨碍我们和叔本华一起去否定生命”。(注:《托尔斯泰文集》,15卷,49页。)可是,——
“可是农民们是怎么死去的?”(注:《父亲》下卷,455页。 )托尔斯泰这一直到临死还在追问的话,竟把他带向越来越远的东方,他正是在农耕的、古老东方的“共同世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的。
这样,托尔斯泰就不但和舍斯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道扬镳,而且也和整个西方的思维方式背道而驰了。面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危机,托尔斯泰没有走向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之路,而是回首瞩目东方,特别是将向中国的古典文化思想投以挚诚的目光。
在《忏悔录》和《安娜·卡列尼娜》里,托尔斯泰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在抛弃了西方理性思维之后,探索认识生活真谛的历程。
首先是宗教的非理性救托尔斯泰于理性宣判的一死(象皮埃尔一样,解救其理性危机的是共济会的信仰):“合乎理性的认识否定生命的意义,而大众,整个人类以不合理性的认识承认这种意义。这种不合理性的认识就是宗教,”“我之所以接受宗教信仰是因为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大概别无出路,只有死亡”。
于是,他必须先承认“世界的生存是依据某个人(自然是指上帝)的意志进行的。为了理解这种意志的意义,首先要服从它,做要求我们做的一切。”这里,托尔斯泰所行的不是中国人的知行合一,而是基督教的信行合一。不过,“理解这种意志”的探索一步步地破坏这种合一的信行:
但是我从承认上帝的存在又转向对他的关系的探索,我又想起那个上帝,我们那位派来了圣子,即救主的三位一体的造物主。于是,这个与世隔绝,与我无关的上帝就象冰块一样在我眼前溶化了……我陷入绝望中……
然而这种对于虚妄的绝望,正促使托尔斯泰走向新的认知的微明。那个“三位一体的造物主”的化解终于给托尔斯泰带来一个类似中国人的“德性之天”的,活在人心中的上帝。
如果说,在《战争与和平》中,恢宏的天道还是完全外在于人,只是偶或间给无可作为的人们以一线宿命般的天启——人在上帝面前是卑微的;那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已经开始了从“天在外”向“天在内”的转变。对于不是执迷于理性的人,天的启示便显现在人的心中。
推究把他引入疑惑,但是当他不用思想,只就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时时感觉到他的心灵中有一个毫无错失的审判官……
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藉着启示而向人们显示的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
不能不注意到,在彻底否定过去的那个“共同世界”的理性的时候,托尔斯泰受着叔本华的非理性思想的影响,继续走着心脑对立、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的西方思维的路子。当列文不再象《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们无为以待天命,而重新开始人生价值的探索的时候,托尔斯泰特别强调非理性的“一点即透”的灵感和生而知之的本能:
为了上帝而活着,他略一暗示我我就领悟了……
他们对我说的是已经在我心灵中存在的东西……
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不过是发现了我所知道的东西。(注:《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19章。)
这虽然表面上颇似中国传统的体悟认识,实际上它还只是一种强调非理性的直觉顿悟,而与中国传统的被称为实践理性认识论的心脑合一,理性与非理性合一,知行合一,主客体合一的中国古典的认识论还处于貌合神离的形似关系。走向非理性,这是许多人对托尔斯泰后期思想的判定。然而,我认为,托尔斯泰没有走向非理性,而这大抵恰恰是他得益于后期直接接触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
因为,既然托尔斯泰已经领悟到“天”,领悟到人是天(或叫“永恒”、“上帝”)的一部分,并且从天在外走向天在内,那么,便有了领悟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主客体合一的认识方式的可能性。托尔斯泰把这个“天”—上帝视为“人体及其智慧之源”,它“和生命是一回事”。因此,对这个上帝的信仰便转化为对人自身的信心,(而不是基督教式的人在上帝面前的罪孽感。)成为“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的传说的信仰”——应当“成为更好一些的人,即生活得和这种意志更相一致些,”(注:《托尔斯泰文集》,15卷,50—61页。)即所谓以德配天。
这样,认识上帝——认识天和认识生命——认识人自身,便有可能终于统一起来。至此,托尔斯泰的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便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初步接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