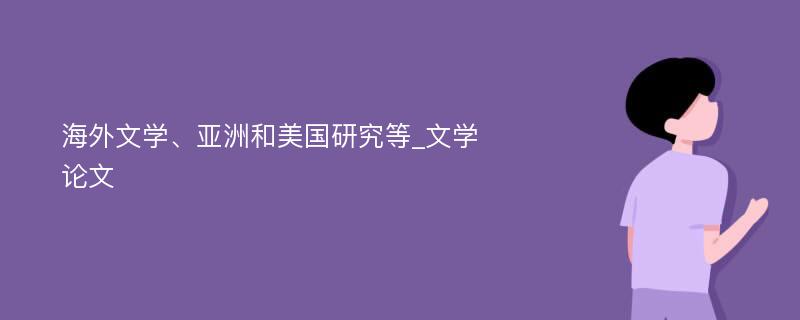
海外文学,亚美研究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他论文,亚美论文,海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王德威教授最近在一篇题为《贾宝玉也是留学生》的文章中提醒大家,“留学文学”绝对不仅限于众所周知的几位台湾作家的作品:白先勇的《纽约客》、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其实,晚清的“留学生狂想曲”——代表作如《苦学生》、《新石头记》——中,像贾宝玉这样的公子哥都轻而易举地被作家请到西洋游览了一番。如果我们把“留学”的主题扩大到“留洋”,那么晚清还有其它作品可以归到这一范畴之内。学者阿英在五六十年代编过一本六百多页的《反美禁约文学集》,其中收入散文、诗歌、小说多种,全部是为了呼应在美华工反抗移民政策而作的。虽为“政治文学”,有几部作品如《苦社会》、《黄金世界》,很能体现晚清社会风云变幻、前途不测的整体风貌,文体上则能代表由章回小说向现代小说演变时期的特色。如果继续把留洋文学中的“文学”扩大到文化的范畴,那么近一百年来对于留洋的想象和叙述则多得数不胜数。80年代岳麓书社出版的由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厚厚的几大本,收入的作品大多是如容闳这样的外交官出使西欧、美国所作的旅行札记。而同样的80年代,大洋彼岸,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欧梵和David Arkush两位学者编辑的一本华裔作家的美国印象记,从编辑形式到选目都与《走向世界丛书》完全不同。这些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比任何一个单一的文本更能体现东西方文化精神、文化体制上的差异。
对于西洋、美国的想象,清晰地反映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自我界定。李欧梵、David Arkush主编的文集,题目引用了费孝通1943年对于美国文化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评断——美国是一个“没有鬼魂的地方”(land without ghosts)。 费孝通说:“在一个没有鬼魂的世界里,人可以活得自由而且轻松。美国人的眼睛是向前看的。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们的生活里缺少了一点什么,我不羡慕他们的生活。”“鬼魂”在文化心理学上的意义是“被压抑的历史的回归”(return
oftherepressed)。美国文化的历史记忆中有不少精神压抑、 心理创伤的案例。因此费孝通的论断不可简单地作“客观”之解。相反,虽然不能笼统地断论费语“代表”了某种“中国意识”,其中的“中国情结”是很明显的。只是在这里,“中国”二字应该作何解释?
“国家”在政体、民族、种族以及语言地理上的意义在“留洋文学”及与其相关的“海外文学”中是极其混乱的。这在用外文写作的作品中尤其明显。比如在亚美文学的文集时常榜上有名、却很少有人过问的欧亚裔混血作家Diana Chang,她有一部小说《爱的前沿》(Frontiers of Love)记叙的是抗战晚期居住上海的三位从事写作的混血青年的故事。我认为这本书不只对于亚美研究者,对于中国研究者也是极有意义的。Chang描绘的上海是一个特殊的世界, 是“一个欧亚混血的世界”。“严格地说,它不能算作一个中国城市。虽然大部分居民是中国人,但这些人都是有钱人、西化派、基督徒。”租界里的生活并不是理想的生活,Chang对此充满了自嘲。小说的女主人公Sylvia 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殖民制度下的苟活者,而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竟然变得像古董一样值得玩味了。”她和她的朋友没有能力冲破种族、阶级的界限,投身到中国人的抗战中,但是他们也不同程度地为自己憧憬的“新世界”付出了代价。Chang的文字洗练、冷峻,有现代主义之风, 套的却是女作家喜欢用的言情小说的路数。把Chang 的英文现代派作品与张爱玲的中文现代派小说放在一起读,“上海”这个读本陡然变得更为复杂、多元化了。令人深思的是这幅多面体的历史画面,偏偏需要读者深入通常所界定的“外国文学”的领域去寻找。Chang的自我定位与种族、 血统联系很紧,这是她被塑造成为一位亚美作家的原因。但是一个作家的自我定位可以是多方面的,除了种族、血统之外,地理、世系、传统未尝不能成为自我定位的方式。“海外文学”中的“海外”是个地理的概念。Chang虽然并不涉及世系与传统,地理对她的人物却影响极大。 Sylvia在北平长大的,北平代表她浪漫化的纯真的童年,是复杂的上海促使她女性意识、种族意识、政治意识的萌发。
如果非要用“中国”、 “美国”来定位一个作家, 那么DianaChang 的例子证明,所谓“国家/民族”在海外作家里是很难界说的。“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的二元对立,很难概括表与实、内与外、疏与离等等复杂情况。况且,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根”的意义,不是通过文学读本本身就可以了解的,文学的阐释常常受到某一学科,以及学科背后的理论体系所左右。留学生文学、留洋文学、海外文学在中国研究的殿堂里只是个“小领域”、“小传统”。其实,“大”、“小”之分多半是文评家所确定的,作家未必有同样的体会。如果我们站在作家的角度来观察“传统”、“历史”这样的理论先设,也许反而衬出理论的狭隘!
二
那么上述的留洋文学、海外文学在美国是在什么样的学科背景下探讨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亚美研究”的学术背景等复杂情况。国内报刊对于亚美文学的解读,多半套用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模式,这个模式起码在一个意义上是有所欠缺的,那就是把文学读得太实, 把文学仅仅看成是某一种文化/ethnicity(其实culture和ethnicity也有不同)的载体。其实, 在美国历史上,虽然ethnicity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题目,
但是大部分批评家认为ethnicity 的内容、功能却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在亚美文学中,有许多作家关注ethnicity,却很难用某一种确定的“ 亚美性”来概括。亚美文学的地域性、阶层性都有很大的差异,尤其这十几年来随着女性研究与亚美文学的融合,ethnicity更无法抽象地、单一地、 笼统地讨论。
ethnicity的复杂性使得亚美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 恰恰因此,有关亚美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至今历史学家众说不一。历史学家Ronald Takaki的专著《来自大洋彼岸的陌生者》(Strangers from aDifferent Shore)其实是一本移民劳工史, 只是最后一章里简单涉及亚裔移民从自我意识到自觉意识的过程。Takaki所勾勒的历史是由一条从被排斥到主动反抗的主线构成的,虽然很有连贯性,却很难解释社会历史和文化意识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另一位历史学家William Wei 所著《亚裔在美洲》(Asian American Movement )集中在六七十年代,试图从政治、文化、学院、社会等各个领域去寻找亚美裔的足迹,看似社会运动史,文中涉及到种族与性别之争、学院与社区的分歧、文化与政治的距离时,每每承认每场争论必然使得“亚美意识”重新定义,使人感到亚美裔运动似乎并不是一个有头有尾的社会运动,而更多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社会思潮。
亚美文学史至今只有Elaine Kim十多年前所著的唯一一本。文化史、文学史虽有不少社会理论所不能涵盖的复杂性,Kim 的文学史却极受六七十年代左派社会思潮的左右。“亚美文化”背后有一系列理论的假设,比如它代表的是受压迫的、第三世界的、劳工阶层的文化,再如“亚美文化”是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的文化等等。写文学史免不了要寻“根”,亚美文化的“根”于是便寻到了亚裔的社区,寻到了唐人街。本世纪初被拘留在天使岛木屋里的华工写下的广东方言“木鱼歌”成了经典;40年代菲律宾裔移民作家Carlos Bulosan受左派思潮的影响写下的America is in the Heart成了代表作,相反,非英文作品, 对亚美的自我界定不能产生直接的正面意义的多半被排斥在研究范畴之外。
从受六七十年代亚美政治思潮较大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自我定位是一个重要主题。Maxine Hong Kingston80 年代的长篇小说Tripmaster Monkey的主人公Wittman Ah Sing可以看成是对六七十年代典型的亚美人物性格(Asian American subject)一个略带调侃的总结。Wittman是一个文化叛逆。这种叛逆精神不只是一种政治姿态, 几乎可以说是他人格的全部。把中文中一个普通的名字“阿兴”翻译成英文,再把它当成姓来使用,这种做法本身就意味着Wittman Ah Sing 的自我起源于一种误读。这种误读(misrepresentation )注定了他的边缘人的位置。所以,我把Wittman Ah Sing 理解为一个有亚美特色的叛逆精神的寓言。它与西方主流现代派文学中所塑造的叛逆形象的主要区别就是,Wittman少了几分严肃,多了点幽默感和戏剧性,所以, 最近有的学者认为亚美主体(Asian American subject)基本上可以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解释。Kingston把这个人物比作猴戏里面的孙悟空形象,既有大闹天宫的勇气, 又不失为一个机灵鬼、 一个讨人喜欢的捣蛋鬼(trickster)。这种写法当然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与其说是一种文本的翻译,不如说是一个原型的移植。翻译有时还不得不顾及忠实于原文,而忠实原文不是Kingston为文的出发点,孙猴儿这个形象,主要在于强调Wittman的聪明, 而这种聪明又多少带有点类似王朔小说里的“玩主”的市俗气(street smartness),令人想起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Wittman不“像”在大陆、台湾、 香港受中文教育长大的年轻人,但是有谁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呢?中国文学里的“中国”人物不也是多彩多姿的吗?
借用孙猴儿的原型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把Wittman Ah Sing这个人物放在戏剧的框架里,强调他的语言、性格的表演性。这就有点和哈克·贝利·费恩不一样了,哈克·贝利·费恩的叛逆性格有本可查,基本是一个线性的发展。Wittman 的叛逆性格却有点将错就错的果断劲,其反面也就是一种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宿命感。他这样的性格很难为观众、读者所接受,Kingston想到了这点,于是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向读者提示,引导读者对其“恶行劣迹”采取宽容、 温和地调侃的态度。Kingston不只塑造了小说的主角,而且塑造了小说的读者。亚美种族在她的笔下是一个宽容、活跃的“阐释团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这种写法是不是可以看作是Kingston从80年代的角度对于60年代盛行于加州大学校园的反文化( counter- c- ulture )的敬礼之作呢?Kingston及其同时代作家Frank Chin都主张“亚美人”和传统意义的“亚洲人”不一样。可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大环境下,应该看到“是”和“非”都是一种姿态,与跨文化的复杂性并不能等同。
随着种种文化理论引入亚美研究,更因为从60年代至今美国社会大环境的风云变幻,亚美文化研究的主旋律有不少发展。虽然现当代西方文学的写作、阐释脱离不开自我(self)和定位(identity)核心问题,亚美文化批评家对于文化、历史的大叙事也多有关注。最近,本来不受重视的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留学生文学有几部著作相当走红。但是,对于六七十年代以前的亚裔作家,例如Diana Chang, 却仍然很少有人注意。
我认为亚美研究虽然对美国语境的认识日益深化,对于“中国”这个文本的解读却远远不够深刻、复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各种后殖民主义为理解东西文化交通提供了一个蓝本,但是这个蓝本是否适用于每一个案例却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亚美文学借用了不少中国文学中的原型,偶而也涉及一些“中国”事件,如文化大革命等。所缺乏的恰恰是“中国”观点、“中国”视角。中文名词形式没有复数,其实观点、视角不应只是一种。此外,“中国”的意义也不清楚,我更倾向于比较广泛的地理性的理解。“海外文学”,这个字眼本身就包含了人文与地理、想象与写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觉得亚美研究者对于用中文写作,受传统中国文化美学影响,或是积极地参与亚洲文化建设的作家注意不够,而在与亚美文化相交叉的“海外文学”之中,采取这样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的大有人在!
香港作家董桥在一篇散文中引用了英人的一句话:“We travelledto discover the past.”这本是针对返乡的游子而言的。 实际上,很多有旅行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异地他乡寻找到先人的足迹,那种感觉同样令人欣喜。对于海外文学、亚美文学的研究,多少年来一直徘徊在几个貌似单纯,实际上意义复杂的字眼之间:“本土”与“异域”、“主体”与“客观”、“我者”与“他者”。然而文学本身所提供的历史上的连续性,却往往在概念的缝隙之间。旅行的意义绝不止于猎奇,拘泥于概念反而会限制我们创造的想象力。我想,在今天文化资本转眼之间就被带上了“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的销售商标之际,重新考虑一下“中国”、“美国”、“自我”、“真实”的问题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海外文学为这种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