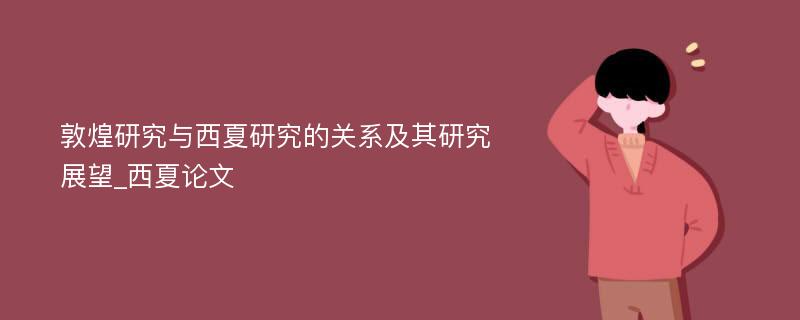
敦煌学和西夏学的关系及其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关系论文,敦煌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0.6;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052-07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西夏学是利用过去的历史资料、近代出土的西夏文和其他文字文献以及文物资料,研究西夏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学科。除西夏时期外,还上及西夏建国前主体民族党项族的历史,下至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的历史。
敦煌学和西夏学都是新兴学科,两学科的建立都与近代大量文献的发现有直接关系,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推动了相应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敦煌学和西夏学文献的发现都在20世纪初,但敦煌学起步较早,西夏学较为滞后。两个学科关系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属于交叉学科。
一 敦煌学中包含有部分西夏学的内容
(一)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有大量西夏洞窟
敦煌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敦煌及其附近的大量石窟群。西夏统治敦煌近两个世纪,皇室笃信佛教并在民众中大力推行。然而敦煌石窟群中究竟有多少西夏洞窟,过去并无文献记载,也缺乏系统的科学考察。
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石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系统考察,由常书鸿所长、王静如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宿白教授担任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甘肃省博物馆的陈炳应参加。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原来认为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八十多个西夏洞窟,大大改变了对两窟群洞窟布局的认识。这次的调查结果分别发表于20世纪70—80年代[1-2]。此后一些专家对东千佛洞、文殊山万佛洞等石窟进行考察,又发现了一些西夏时期的洞窟[3-4]。河西地区总共约有近百座西夏洞窟。
西夏洞窟在敦煌莫高窟中占有很大比重。《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附录《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中,计开凿和重修的西夏洞窟约占莫高窟全部近492个有壁画、塑像洞窟的六分之一[5]。在管辖敦煌莫高窟的王朝中,西夏属于开凿和重修洞窟较多的一代。
敦煌石窟自前秦以后至元代历经11个历史时代约一千年,西夏王朝占据敦煌约190年,西夏洞窟在敦煌莫高窟中占据一个历史时代①。西夏洞窟的认定和分期是以洞窟题记结合洞窟壁画、塑像的艺术特点并与宋、回鹘以及元代洞窟比较为依据的。西夏洞窟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对于西夏洞窟的数量以及对一些洞窟是否属于西夏,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6-8]。
莫高窟和和榆林窟有近百处西夏文题记。莫高窟有题记45处,分布于21个洞窟。其中第65窟题记称此为“圣宫”,第285窟称为“山寺庙”。榆林窟有题记47处,分布于16个洞窟。其中第12窟有“游世界(朝廷)圣宫者”,第25窟有大面积发愿文,第29窟有众多的供养人榜题,其中有“沙州监军”、“瓜州监军”等职官名称。两窟群共发现有纪年的西夏文题记10条,其中有年代可考的5条,最早的是西夏大安十一年(1085),最晚的是正德二年(1128)。两窟群还有西夏时期具有年款的汉文题记8处,其中莫高窟6处,榆林窟2处,最早的是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最晚的是光定九年(1219)。这些题记内容多是巡礼题款、发愿文和供养人榜题[2]。
西夏洞窟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有自己的特点。敦煌洞窟自开凿后历经数百年,至唐代达到艺术顶峰,宋代已走向下坡路。至西夏时期虽未能恢复昔日辉煌,但在一些洞窟中却不乏精彩的艺术显现,特别是在莫高窟、榆林窟中引入藏传佛教内容,甚至将传统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融为一体,形成新的艺术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敦煌石窟艺术下滑的颓势,使西夏时期的石窟艺术达到新的境地。
(二)敦煌一带出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
在敦煌一带的文化遗存,除石窟艺术外,还在当地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文献、文物。早在1958年在敦煌石窟对面的土塔中就出土了多部西夏文佛经,其中有两种出图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9-11]。
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区陆续进行系统发掘,发现了很多重要文物、文献。从出土的文物和文献看,莫高窟北区主要是敦煌僧人的居住、坐禅的场所。在发现的文献中,有多种西夏文文献,涉及北区27个洞窟。尽管这些文献多为残片,但包含了不少重要世俗和佛教典籍,其中有不少是国内仅存,有的是海内孤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12-13]。其中有类似中原地区汉文《千字文》的西夏文字书《碎金》,有蒙书类西夏文字书《三才杂字》,有西夏文、汉文对照的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些文献都发现在敦煌僧人居住的生活区。可以推想,西夏时期敦煌地区居民,包括当地僧人借助这些通俗的启蒙著作学习西夏文和汉文,以便识读经文或其他读物。此外还有社会常用的西夏文文书残页,如按日期记录的记账薄、军队中所用物品的账目之类。
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文献绝大部分是佛经。其中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封面、《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封面、刻本《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及佛经诵读功效文等。第159窟还出土刻本佛经《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残页,经末有一长方形压捺印记,有汉文两行:
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
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
管主八是元代一位僧官,任松江府僧录。他曾主持印制多部西夏文大藏经并将一藏施于敦煌文殊舍利塔寺中。在敦煌莫高窟曾先后三次发现了与上述相同押捺汉文题记的佛经残页,另两件分别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日本天理图书馆②。可能在他所施经中都压捺了这样的印记。又元代平江路碛沙延圣寺刊印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记载:“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③由此可以推论,当年敦煌曾藏有一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是管主八大师印施三十余藏大藏经的一部。此残片当是施与敦煌的西夏文大藏经的一页。这说明西夏灭亡后,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一带,仍有不少西夏党项族居住此地,他们信仰佛教,诵读西夏文佛经。
莫高窟北区石窟中还出土多种西夏文活字版文献,如《地藏菩萨本愿经》、《诸密咒要语》等。除在西夏首府中兴府(今银川)、黑水城、武威等地发现活字本西夏文文献外,在敦煌又发现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更说明西夏使用活字印刷之广泛。包括敦煌北区发现的各种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品,都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十分珍贵。联系到在敦煌先后发现了大量回鹘文木活字,推测在西夏和元代敦煌是中国活字印刷的一个中心,敦煌在活字印刷史上的地位应予重视[14-15]。
在莫高窟北区还发现西夏文泥金写经残页、僧人职事名单、诗词残片等,同时在北区第243窟内墙壁上有朱书西夏文题记数处,其中有“肃瓜统军”字样,联系到南区洞窟中的西夏文题记也出现沙州、瓜州“监军司”、“统军”名称,证明西夏时期敦煌地区与瓜州等地的密切关系。
早在1908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莫高窟北区也发现了一些西夏文文书,多是残片,其中有《要集略记》封面、《正法念住经》等残页,还有活字本《地藏菩萨本愿经》以及上述有管主八押捺印记的西夏文《大智度论》第87卷末页。
西夏统治敦煌及其稍后的元代期间,在莫高窟南区开凿、重修洞窟的同时,西夏的僧人们在北区的众多生活洞窟中也留下了生活足迹并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
二 西夏学中包含有部分敦煌学的内容
在西夏时期,敦煌(沙州)是其西部的一个重要地区,军事上是西夏的一个监军司。西夏学的研究内容自然包括敦煌。
(一)西夏时期的敦煌
敦煌将近两个世纪在西夏管辖之下,是西夏的一个州(沙州),沙州为西夏最西部的城市。由于历史文献的缺载以及敦煌石室中出土的文献又不包含西夏时期的文献,因此在敦煌学中近两个世纪西夏统治时间几乎是空白,甚至西夏时期敦煌的建制如何也付诸阙如。
若求助近代出土的西夏文献则可以填充有关的认识。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为西夏天盛(1149—1169)初年所修订,其中有多处关于沙州的记载。如记载沙州监军司是西夏17个监军司之一。属中等司,国家派2正、1副、2同判、4习判共9位官员,此外还有3都案为办事吏员以及12名案头(司吏)。其所设官员比肃州、瓜州、黑水等监军司多1正、1副、1习判,可知沙州监军司比附近的肃州、瓜州、黑水等监军司重要。沙州又设刺史1人,刺史也相当中等司的地位,下设都案1人。监军司下属有军队,军队中在监军使下分层设置行监、正首领、首领等统领军队。沙州监军司也当有此设。
西夏政府在中央有都转运司,又于地方设置多种边中转运司,沙州转运司为其中之一,属下等司,设2正、2承旨,此外还有2都案。此地还设有沙州经治司,也属下等司,设2大人、2承旨。
这些职司都分别有印信,中等司印是镀银铜印,重12两;下等司为铜印,重11两。
由这些确切的资料可以知道西夏中期沙州的基本军事、行政建制[16]。
西夏《天盛律令》还规定,各地诸司的官畜、谷物等收支情况要按规定期限上报首都,有两地是一年一报,即沙州和瓜州;肃州、黑水等地半年一报;京师及其附近需要3个月一报。这是依据与京师的远近而有不同的规定[16]529-531。西夏时期沙州地处西偏,是与京师中兴府联系所需时间最长的地区。
(二)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的特殊地位
莫高窟在西夏人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在莫高窟西夏题记中有所谓“圣宫”,即是对莫高窟的称誉[1-2]。在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中敦煌洞窟被称为“沙州神山”④。西夏经济力量有限,在敦煌开凿或重修洞窟需要大量财力、人力。在西夏这样偏安西北地区的王朝,大型佛事活动应以皇室或地方政府为主才能举办。由此可以推想,大规模修建敦煌莫高窟石窟也应是西夏皇室或地方贵族所为。
在考察西夏石窟壁画时,除对大铺壁画的内容、布局、风格给予重视外,对石窟壁画的装饰图案如藻井、四披、龛楣、边饰等也要特别留意。其中藻井因所处位置的独特,应给予格外的关注。敦煌莫高窟很多洞窟内窟顶是覆斗形,藻井即窟顶部中央最高处的装饰,俯视全窟,位置十分显眼。其形制呈方形,由井心、井外边饰、垂幔三部分组成。井心向上凸起,四边为斜坡面,上窄下宽,构成覆斗形状。藻井名称依井心图案确定。西夏石窟中以龙或凤为图案的藻井十分普遍,龙、凤藻井成为西夏壁画的一大特点。依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载,在莫高窟有关西夏洞窟中,有覆斗形窟顶的洞窟占多数,有69窟,其中以龙、凤为藻井的最多,共32窟。龙、凤不仅是吉祥的象征,后来还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龙往往是皇帝的象征,凤是后妃的象征。《天盛律令》规定民间不准使用龙、凤装饰,正是这种中国式传统认识的法律化[16]282。莫高窟西夏洞窟中大量龙、凤藻井似也可以作为这些洞窟为西夏皇室修造的重要参考[17]。
在莫高窟中,供养人中的代表人物始终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第409窟主室东壁门南北两侧绘大型男女供养人像,南侧男供养人究竟是西夏皇帝,还是回鹘王,颇有不同意见。此供养人是一幅等身像,身穿圆领窄袖袍,上可见绣大型团龙11幅。上述西夏《天盛律令》明确记载只有皇帝才能有“一身团龙”的纹样。若将第409窟有一身团龙的等身供养人看作是西夏皇帝是顺理成章的,若看成是回鹘可汗则似乏依据。西夏管辖敦煌近两个世纪,在敦煌莫高窟修建或重修数十个洞窟,在其中绘制皇帝的供养像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此外,男供养像后有侍从持御用华盖、翚扇等物,这也是皇帝才能有的仪仗。《天盛律令》规定:“官家(皇帝)来至奏殿上,执伞者当依时执伞,细心为之。”[16]430伞即华盖,可见,西夏法典规定皇帝有华盖,与此图同,也证明这是皇帝而非王的形象。假若第409窟是沙州回鹘王的供养人,在后来西夏管理沙州时,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明显僭越的壁画,也不会容许它存在。西夏重新装修大批洞窟,对这种在西夏管辖区的违规犯法的冒犯皇帝的壁画,大概会毁弃重修。因此,第409窟供养人视为西夏皇帝比较合理。若如此,则敦煌莫高窟出现了皇帝供养像。
三 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书
(一)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书类型相近
20世纪中国有几桩大型出土文献的发现。按历史时代顺序有安阳甲骨文、汉魏简牍、敦煌石室文书和黑水城文书,后二者分别成为敦煌学和西夏学形成的重要学术资料基础。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出土了五万余件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其文书数量之多、文书内涵之丰富很快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由此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促进了敦煌学的诞生。敦煌学的诞生和发展,丰富了中国约七个多世纪历史的认识,填充了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空白。其中由于唐代的文书特别丰富,对唐代历史研究的推动尤其明显。这些文书相当一部分流失海外,一部分留存于中国。
1909年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的一座古塔中出土了大批文献和文物。当时以俄国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为首的一支探险队到黑水城寻宝,将所得文献运回俄国,今分别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黑水城发现的文献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有八千多个编号,数千卷册,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这批文献内容丰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包括中国中古时期宋、西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刻本和活字本,距今已有700—900年的历史,堪称珍本、善本。作为多学科研究对象的黑水城文献,不仅从多方面体现出西夏历史文化的内涵,还反映出西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内在的紧密联系,其学术价值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后来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也于1914年到黑水城寻找、发掘,得到不少西夏文献,藏于大英图书馆。
敦煌和黑水城同属中国的西北地区,一在西夏西部,一在西夏北端,皆为边远地带。两地直线距离约四百六十余公里。敦煌石室文献和黑水城文献有共同之处,它们都发现于20世纪初,都属多类型、多文种的集群性文献。两种文献都出自佛教建筑,都有大量佛经同时也包含着大量世俗文献,如籍帐、户籍、契约、状牒、信函等。这些文献都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原始资料,不是经人加工编辑或辗转记载的第二、三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由此衍生的敦煌学和西夏学都是新生的国际性的学科。
(二)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书的不同经历
敦煌文献以汉文文献为主,兼有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汉文文献识读较易,古藏文文献释读虽有一定难度,但藏语、藏文的使用一直传承至今,只要掌握古今藏文的对应规律,古藏文文献可以比较顺利地解读。所以敦煌石室文献较快地被整理、出版,其文献价值较早地被学术界所认识并及时予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为主,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相对较少。西夏文作为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早已成为死文字,随着党项族的消亡,西夏语也早已成为死语言。发现黑水城文献的时期,世上早已没有懂得西夏语和西夏文的人。因此西夏文被称为“天书”,解读西夏文文献成为一大难题。各国西夏学专家不畏艰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才基本上具备了解读西夏文文献的能力。这样在释读文献方面黑水城文献比敦煌石室文献落后了约半个世纪。
此外,黑水城出土文献长期储藏于书库,未能及时整理出版,与敦煌石室文献比较及时问世也形成了很大差距。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只能通过俄罗斯专家研究著述的图版中得到部分西夏文献资料。系统、大规模出版黑水城文献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进行的[18]。自《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出版至今十多年来,西夏学有了触手可及的原始资料而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得到学术界重视,关注、研究西夏学的专家逐渐增多,利用西夏文献深入探讨西夏历史、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科技的著述成果累累,加深了对西夏王朝多方面的认识,逐渐撩开西夏王朝神秘的面纱。一个学科原始资料的及时刊布对推动学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书时代相接
敦煌石室文献中包括5世纪至11世纪的写本和少量刻本,以宗教典籍为最多,占敦煌汉文文献的90%左右,官私文书约一千件。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文献。最晚的有具体年代的文献是1002年的写经,即在11世纪初的北宋时期,其中没有西夏文文献。
黑水城出土文献除大量西夏时期的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外,还有少量宋、金时期的文献以及一批元代、北元的文献,时间基本在11世纪初以后至14世纪中叶达三个多世纪。近代在新问世的有宋一代(包括辽、夏、金)文献中,特别是世俗社会文书方面,黑水城文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首屈一指,具有时代的代表性。这一时段正好与敦煌文献的时段相衔接,使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在历史时代上形成了长达近千年的古代文献长廊。这一衔接不仅展现出中国古籍文献的历史连贯性,大大填充了中国珍贵古籍的数量和品类,同时也提升了两大文献库各自的文献价值。
无论是世俗文献还是宗教文献抑或是民族文字文献,两种文献库都具有共同的相关性和各自的时代性。比如敦煌世俗文献中具有的类目,黑水城世俗文献中多数都有;两种文献库中的佛教文献也有很多的相同的典籍。但两种文献处于不同的时代,政权以不同的民族为主体,也就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如敦煌文献中卷装为主;黑水城文献中除卷装外,尚有大量蝴蝶装、经折装、缝绘装和梵夹装,反映了中国装帧形式的逐渐丰富及其发展变化。敦煌文献中以写本为主,刻本很少;黑水城文献中刻本数量很多,而且有了多种活字本文献,反映了西夏时期印刷术的发展和兴盛。敦煌文献中有不少藏文卷子,其中包括佛教和世俗的;黑水城文献中藏文文献很少,但用西夏文、汉文写印的藏传佛教文献却很多,反映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东传的现实。敦煌世俗文献的买卖、典当契约中,一般要写明卖地或借贷的原因,而黑水城文献中省却了这些当时看来不必要的文字,反映了契约趋向简明和务实。
两个时代相衔接的文献宝库,真实地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特色。
(四)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书都有力地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研究
敦煌文献展示了中国从两晋到宋初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为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为史学、文学、艺术、宗教学等领域深入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敦煌文献不是只反映敦煌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而是在空间上超越了敦煌,涉及更大的地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文献的代表。敦煌文献的发掘推动了文献相应朝代的研究,填补了相关朝代历史的诸多空白。
黑水城文献是以西夏为主的历史资料,展现了西夏的历史风貌。与敦煌文献不仅仅反映敦煌一地一样,黑水城文献的史料价值也绝不仅限于黑水城一地,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西夏王朝的历史面貌,促进了以西夏为主的研究。近些年来利用黑水城文献深入地研究西夏和宋代历史文化的成果很多,填补了西夏和宋代历史的诸多空缺。黑水城文献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很多文化元素,从这些真实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文化在那个时代的面貌和特点。
四 敦煌学与西夏学的互动
(一)西夏学应利用敦煌学研究的方法和经验
敦煌学历经百年,逐步走向成熟,不仅在洞窟艺术研究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在文书研究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对文书的定名、断代、补残、缀连、释读、考证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西夏文献刊布较晚,多数文献是近些年刚刚刊布或即将刊布,对文献的释读刚刚开始,敦煌学家的科学方法和成熟经验值得西夏学家学习和借鉴。我在介绍和探讨敦煌西夏洞窟时常常参考、引用敦煌研究院及其他专家的著述,我开始研究西夏文社会文书中的户籍和租税等文献时,请教过中国人民大学的沙知教授[19];在研究西夏社会文书中的借贷文献时,法国童丕教授的著作是我必须学习的参考书[20-21];在研究西夏文历书时,请教过中国文物研究所的邓文宽教授[22]。
(二)敦煌学和西夏学应进行比较研究
鉴于敦煌学和西夏学资料在时间上前后相接,在内容上品类相当,正可以互相联系,做比较研究。作为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文献资料,过去主要靠历代历史学家们记载和编纂的资料。利用考古发掘得到的更为可信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研究历史,主要是从近代开始的。甲骨文是商周时代社会的真实记录,居延、敦煌等地的简牍是汉魏时期社会的真实记录,而敦煌石室文献、黑水城文献是此后晋、隋、唐、宋、西夏、元代的社会真实记录,这些出土的原始文献形成了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另一有特色的链条,给中国历史研究补充了新鲜、可信的资料,开辟了新的途径。将敦煌石室文献、黑水城文献中的同类文献联系、对比考察,可以把文献放到更宽阔的时空中审视,能使文献增加历史的厚重感,便于理顺文献的发展脉络,在考察文献的异同中有可能碰撞出新的火花,得到新的体会。
敦煌的西夏石窟,无论是鉴别时代,还是深入研究,都不能孤立地进行。敦煌石窟艺术,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民族特色,还有时代特色。研究敦煌西夏时代的洞窟,离不开西夏境内的党项族、汉族、藏族和回鹘族,也离不开那个特定的时代。这些都可以在西夏学资料中找到更为广泛的资料,可以找到对比的素材。比如黑水城出土有西夏时期的三百多件绘画、宁夏宏佛塔出土有胶彩画唐卡多种,拜寺口双塔中西塔的天宫内也发现了西夏绘画作品,此外西夏文献中有木版画,其中除佛经卷首扉页外,还有单幅木刻版画。这些西夏绘画大大丰富了西夏的艺术作品,正可与敦煌石窟的壁画对比研究。榆林窟第3窟壁画中的犁耕图、踏碓图、锻铁图、酿酒图以及行旅图等生产、生活场景图也可结合西夏文献资料进一步深化研究。敦煌一些洞窟时代的确定可以从西夏学资料中找到相应依据。西夏学的内容可以补充敦煌学,西夏学的进展有助于敦煌学的深入。
(三)敦煌学家和西夏学家密切合作,推动两学科的发展
敦煌学门类繁复,博大精深。西夏学基础薄弱,又有西夏文字阻隔。对两个学科都很熟悉确实不易。如果两个学科的专家能联手合作,各展所长,便可以在敦煌学和西夏学交叉的部分取得新的成绩。
比如在敦煌学中,西夏时期的敦煌以及西夏时期的敦煌文献属薄弱环节,西夏学家可利用西夏文和汉文资料给予填充。在西夏学中,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是专深的学问,可由敦煌学家鼎力承担。又比如西夏时期的敦煌洞窟分期可能需要敦煌学家和西夏学家共同对话、考察、研讨,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联合敦煌石窟考察,就是敦煌学家和西夏学家良好合作的开端。那次的考察从西夏的视角对敦煌石窟做了比较全面的调研,改变了过去敦煌只有几个西夏洞窟的认识,确认敦煌有更多的西夏洞窟并通过洞窟题记的研究初步了解到西夏人在敦煌的一些佛事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未能联手继续进行下去。自那次合作至今已近半个世纪,敦煌学和西夏学都有了长足发展,科研条件也有了很大改观,今后可以在新的时期创造条件进一步合作,推动敦煌学和西夏学的共同发展。
注释:
①有的专家认为自1036年至1067年之后的30多年间,敦煌由沙州回鹘统治。参见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②一件是1908年伯希和在P.181号洞(即今第464窟)掘获的西夏文《大智度论》卷第87末页(残),现收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另一件是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使人挖掘北区洞窟所获一西夏文佛经残页,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
③中国国家图书馆、山西崇善寺和日本善福寺都有收藏。参见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二,座右宝刊行会,1966年。
④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山之名义”中有“沙州神山”条,译文为“凿山为佛像、寺庙,圣众住处多有”(译文系本文作者重译)。
标签:西夏论文; 莫高窟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文物论文; 敦煌学论文; 壁画论文; 敦煌博物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