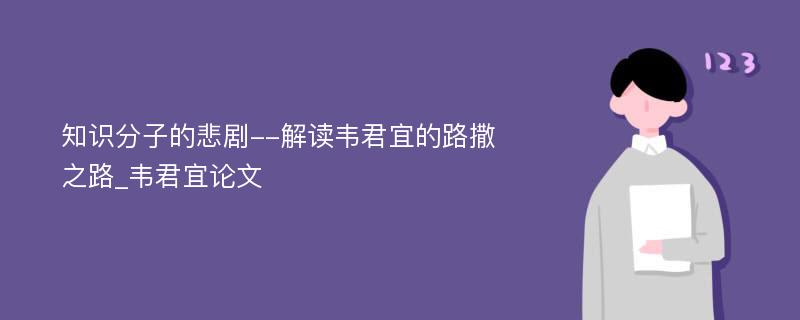
知识分子的悲剧——读韦君宜《露莎的路》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悲剧论文,韦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韦君宜说来,想写《露莎的路》这样一部小说并非近事。她说她早就想写,也早就可以写的,但是一直拖到病倒之后。她已经半身不遂,脑溢血发作使她的手脚不听使唤。她想,只要脑子还有一部分管用,只要一天能写一点点,总会有写完的时候,把藏在心灵深处大半辈子的这段亲历难忘的故事说给人听。韦君宜保证说:“反正我写的是我确曾涉足过的生活,我决不愿把虚夸的东西交给读者。”
为什么一个自称“衰残的人”非要将这部小说写出来不可?什么用意?什么“意思”?韦君宜说:“意思见于书本身,不再烦絮。”
这部小说是说四十年代初,年轻的大学生露莎离开官僚家庭辗转来到延安,又到前方,又到北平,一心奔走抗日。作者沿着露莎的足迹,以报告文学的真切生动的笔触和抒情散文的自然流露的挚情,描写露莎随部队进行农村调查,同鬼子周旋;又匆忙地同英俊的宋安然结婚,婚后才发现两人在文化和志趣上都不相同,终于分道扬镖,又和老朋友崔次英结婚诸种遭逢。“抢救”运动中,丈夫被打成特务,女儿也死了。运动过去,大家都平了反,她反而灵魂不安。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转移河北,她化装回北平探亲,是出国还是回解放区?露莎面临又一次选择。她终于回解放区去。
本书编者提示说:“能把抗日和情欲、革命和三角恋爱、真理与谬误等等毫不相干、水火不容的东西融为一体的是什么?是生活。能真实纪录生活的,是小说。”
从收到这本册子开始,一年多来,一团火攥在我的手里。
我净手端坐,打开作者1994年用颤抖的手歪歪斜斜亲笔题签的“收阅并希望惠予评说”的这本同年出版的新书。小说通过一个女学生追随革命的经历,真实地再现了延安时期的那场莫名其妙、不甚了了的政治运动和延安知识分子的领袖崇拜、虽苦犹荣的火热心肠。正是这场鲜为人知的“抢救”知识分子运动的“抢救”中的知识分子的被“抢救”引起我莫大的兴趣。由韦君宜笔下的这番描写我想到后来的文革以及文革中莫须有的“516”那桩公案,想到知识分子问题的非同小可, 想到什么才是一生颠沛、一身正气的老作家生前身后名——他们的人格修养和更高层次上的忠诚。
在绥德礼堂,一个不过十三四岁的学生开口就说:“我是国民党特务,我的阴谋罪行很大。我给同学们打饭,是用撒过尿的盆打的,盛饭是屎盆子。”又有一个女生上台像背书似地说:“我们女生组织的有美人计,口号是:你们的战场,是在敌人的床上。”后来竟然揪出六岁的小特务。露莎大惊,知情者告她:“你只要给他好吃的吃上,还不是要她说什么就说什么。”
传达中央精神,说是现已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混进边区,混进了党,要求全体干部自己检查自己是不是特务,赶快坦白。“资本家的大小姐还说不是特务?”“证据在哪里?”“证据就是你的父亲!”动员会后,一片坦白交代的热潮席卷了共产党的地委,所有的党员一下子都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或特务嫌疑分子。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地委里面越搞越热闹,一再传达中央指示,“开展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同时发出了一篇铅印的文章《抢救失足者》,署名“康生”。
“露莎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家里又有钱,不是汉奸能是什么?就是汉奸!”露莎等着有人揪她,“被揪好像无所谓冤和不冤,好像党现在需要大家当特务,那就当一当也是应分的。”“早知这样,就不来了。”
露莎的孩子死了,组织上还在动员丈夫坦白,迎接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坦白大会,说:“这是光荣的事,是立功的最好机会,现在坦白了照样给工作,再拖延失去机会,那可要送保安处了。别人已经交代了。”
露莎的爱人是这样坦白的:“我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一个国民党特务,真是可悲极了。为什么变的呢?因为党要我说的,国民党逮捕了我,凡是被捕的党员非当特务不可。我干了什么坏事呢?我当了一个理论方针性特务,就是不和任何别的特务联系,专从方针政策上破坏,搞一些反动言论。例如‘久假不归论’,‘南开中学论’,这些,使中央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坦白,竟然反映极佳:“他坦白交代的,才是国民党特务的高级阴谋,是他们的真‘红旗政策’,从方针上破坏共产党嘛。共产党怕的就是这一招嘛,比那些发展一大群小特务厉害多了。厉害,大特务,厉害!”这样,一个一个的,宣传部的科长级干部已经全部坦白,成了特务。运动宣布胜利了。
“延安搞‘抢救’运动,只有比绥德更厉害……毛骨悚然。”凡“说过延安吃饭不平等的,说过延安穿干部服的,反正说过延安一个字不是的,通通是特务,一个也跑不掉。”鲁艺一个教员全家自焚,“一二·九”运动成了“特务活动”,让人想起红军时期大搞根本就不存在的AB团。老红军孙以平说:“忍一忍吧,在共产党里,谁都得碰上这么一回。”
露莎哭了,“我们又不是古代的忠臣比干,皇上把我杀了,我还要忠于皇上,你说呢?”丈夫说:“那叫‘愚忠’。你知道不?毛主席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如果他不是对这个运动有些怀疑,他是不会这样说的。”露莎说,她读过一本《虞初新志》,“觉得我们以全力挣扎搏斗换来的天下,怎么越看越像明朝。说是皇上没有杀这个忠臣,就是英明,要磕头哭奠。凑巧今天也没有下令杀特务,不是也够英明的吗?”露莎非常激动,说:“成千上万的青年抛家舍业,不相信国民党的一切号召,情愿到延安来吃苦,都是白费的了。延安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不相信人们……还得口口声声热爱党中央,永远忠于毛主席。”她说:“这里就有这么个奇怪的逻辑,在我一心忠于党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说我不忠于党。在我心里已经实在没有什么信心的时候,却要我天天宣布自己一心忠于党。这是什么世界啊?”
可是露莎得到的好心的回应却是:“运动的事么,咱就不要再提了。”
可不是吗?二十多年再没有提起。文化革命中私下有人提起,文革以后传媒有所透露,四五十年后的今天,真相始见诸报端,见诸回忆文字、人物传记等,例如《炎黄春秋》发表了田方的《海燕事件——延安抢救运动中一个插曲》和宋晓梦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李锐——五味俱全的延安六年》等等,都对延安时期“抢救”运动做了实录,不过较早地以目击者的身份同时采用小说形式感同身受地将“抢救”真相公开披露的,《露莎的路》恐怕是头一份了。
在披露真相的同时,作者们也公开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抢救”运动搞错了的那番言词恳切的讲话。《李锐》一文这样写道:“1945年2 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时,主动地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个党校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他又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戴错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人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会好得多。最后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他把手举在帽沿上向大家敬礼,并诙谐地说:你们如果不谅解,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会场上报以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才把手放下来。”
王力在《传记文学》发表的《谈舒同》一文中关于“抢救”运动印证道:“在1943年开始的审干运动,开头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是不清醒的。在延安最早陷入了迷雾。舒同在1943年和1944年之交从延安到了山东,担任山东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当时分局的领导核心是罗荣桓,常委是罗荣桓、黎玉、肖华和舒同。舒同带来的是延安的也就是中央的审干的方针和经验。分局的整风审干由总学委领导,罗荣桓是主任,舒同是副主任。……延安的一套方针和做法,受到了罗荣桓的坚决抵制。他先是说这样做不合敌后战争环境,敌后的干部,敌人老早替我们审查过了。他先后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过不同意见。毛主席当面对我说过,罗荣桓了不起,他抵制了延安那个审干。(后来提出的)那个十条方针,那个对于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也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也是受到罗荣桓启发的。毛主席还对我说过,党的七大以后,还犯了三大历史性的错误,其中第二个,就是‘保安部门杀了一个王实味’。舒同也是了不起的,他不像那些带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打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招牌去蛮干,而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支持罗荣桓的正确意见,因而山东干部和人民有幸避免了在延安和其他某些根据地里发生的审干的灾难。”
在《露莎的路》的第104到105页,关于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这次有名的敬礼演讲是这样记录的:“这回弄错了,是我错,我给弄错的同志敬礼了。”说到这里,他举起一只手齐帽沿,做了个敬礼的姿势。又接着说:“我给你敬礼,你就要还礼。倘若我敬礼,你不还礼,那我的手就放不下来呀。”露莎还模糊地记得有“这回‘抢救’错了很多人”一句,但是本子上没有。“运动弄错了人”好像有吧。反正承认运动搞错了,这不会有错。
“我是原谅了,就是说,算了。你看,毛主席都认了错,向我们行了礼,我还有什么过不去的?这些事都算了吧,你呢?也算了吧!”
露莎微微点了点头,心想,也只能算了。说:“在这个自己关起门来统治的边区,大家可以算了,我们不说就完了。可是如果将来我们得了胜利,统治了全国,再这么干……”她的爱人次英说:
“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决不能再这么干!”
正像田方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如今虽则并不计较个人恩怨,也不追究个人责任,但是对人、对事、对史力求真实客观,‘誉人不增其美,损人不益其恶’,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还回历史原貌,避免今后重蹈覆辙,其意义显然是十分深远和重要的。”
这恐怕就是韦君宜说的其所以要写小说的那个“意思”,这个“意思见于书本身,不再烦絮。”这里,我想起鲁迅先生谈到他怎样写小说时说的话。他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病中的韦老太太就是这么做的。她的描写过份简炼,这似乎是小说做法之大忌,可是她的身体不允许她不简练,也只有像她这样的有过丰富的创作经验的作家才配有这份简练——增删锤练,披沙拣金,造就一手像鲁迅一样的朴实、老辣、深长的好文字,又难得有珍藏的各个时期对仗工整的旧体诗穿插其间,更显凝重和真实。作者简直忘记了自己的女性本色。总而言之,她的笔下,话虽不多,然而气韵生动,包含着惊人的真实,精、气、神俱全,这种取其神韵而不惜伤其筋骨的速写式的小说形式,于一位手脑不听使唤的重病病人说来,实在是个奇迹。
露莎经历的是一个S型的道路。她从“自忏误吾惟识字, 何以当初学纺织,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再到“塞下忽传胜利声,八年苦战竟全功”,“生还父老应犹健,子弟兵归唱大风”,再到由北平返回解放区梦醒之后不知“路在哪里”?历史的流变和咏叹,终于打破世俗小说大团圆的思维定势。
记忆犹新的韦君宜本以为《露莎的路》里崔次英所说的“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了。决不能再这么干!”会保证历史的悲剧不致重演,不幸二十多年后文革中“再这么干”了,而且愈演愈烈,酿成更大更惨的悲剧。延安时期的“抢救”殷鉴不远,文化革命又给人当头一棒,丈夫杨述的死使她五内俱焚,国难家愁逼迫她深深反思像她和杨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有鉴于此,她于 1979 年到1980年两年间完成描写文革之乱的小说《洗礼》和沉痛悼念杨述同时对杨述一生严于评价的悼惜散文《当代人的悲剧》。两篇作品可以视作韦君宜在认识上重要转捩的标志,而我们面前这部毫不隐讳自述传性质的小说《露莎的路》,无疑追本溯源,给她和她的丈夫以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以信史立传。为了知识分子不再被“运动”,韦君宜现身说法。
在《洗礼》里,同韦君宜的丈夫有着类似经历的老干部王辉凡的形象意味深长。王辉凡既不是“义不帝秦”的傲骨,也不是落井下石的佞臣,而是十足的忠良——忠而愚。愚忠造就了他听话的耳朵和顺从的双手,你说咋干就咋干,你指向哪里俺打向哪里。文化革命来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本来“左”得可以,现在却要批他极右;他本来是响当当的革命派,现在却成了不由分说的反革命。他迷惘,旋即又清醒。他发现党变成两个,是两个党相互打架,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终于,他明白了,面折廷争,冒死铮谏,大彻大悟。
在《当代人的悲剧》里,韦君宜写了一个人,这个人毁家纾难,变卖全部家产把整个家庭统统带到革命队伍,统统献给党。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杨述!这个人不但在那次“抢救”运动中受了罪,而且在这次浩劫中受了苦,比较起来他还不算最苦的。他最感到痛苦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和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作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代替自己的思想,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逼使他对于自己宗教式的信仰产生疑问。要知道这样的疑问多么不容易发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痛苦的代价!可怜的老伴、老革命,还没有来得及自我解剖,就怀抱这疑问而死去。韦君宜沉痛以告:“他的突然去世才使我感到自己在最后的时间里实际上也是在虐待他,我自己也同样有罪,虐待了这个老实人。”
作品的最后韦君宜说:“这些党员,而且是老党员,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这不妨被理解为韦君宜写完《洗礼》和《当代人的悲剧》十四年后用最后的气力坚持写完《露莎的路》的动机和“意思”。
《露莎的路》中的露莎同《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走着类似的革命之路。然而,她们之间存有差异:一个与敌人周旋与情侣周旋,奔走抗日,主要是革别人的命;一个在正义的革命内部同包括恋人在内的无情无义、虚情假义相斡旋,投身革命主要是革自己的命。要是说对敌斗争的爱情纠葛给予林道静的痛苦和磨炼刻骨铭心的话,那么,露莎在革命大熔炉中的被毁、被炼无异于经历一次可怕的炼狱的洗礼。要是说林道静挣破婚姻枷锁称谢党的知遇之恩激情满怀的话,那么,露莎做为一个文化品格较高的、善于鉴古知今的大学生,面对党的敌视和不信任而殷忧有加。要是说林道静的回忆豪情不减当年的话,那么,露莎的回忆却带有浓重莫名的苦涩。要是说林道静临终前可以说“出生入死,今世无悔”然后闭上眼睛的话,那么,已经走出“抢救”运动的露莎会怎么样呢?将要走完坎坷人生的韦君宜又会怎么样呢?韦君宜和露莎一样,也是“出生入死”,不过,无所悔又有所悔。文化革命的发生使韦君宜更认清楚露莎的路。露莎的路印证了文化革命本来就有劣根可寻,她十分想告诉人们些什么,她要告诉人们一点“意思”。梦牵魂绕,忧心忡忡,时不我待,闹得韦君宜的灵魂不得安宁,于是,她只好用那只颤抖的手举起沉重的笔,沉疴绵惙,辗转床笫,假语真言,写写画画,做起小说来,从而有《露莎的路》于1994年问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看问题,《露莎的路》是见证,是反思,是豁然开朗的了悟,是鉴往知来的警策,甚至是录以备考、指破迷津的嘱咐。恕我不敬:人之病笃,其言也直,其言也真,其言也怨,其言也美。它是韦君宜生前的德行,更是身后的美誉。只要你面对这份薄薄的、沉沉的作品的同时,回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好像没有尽头的马鞍型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你就不能不对韦君宜顿生敬意,而把长寿的祝福奉献予她。
韦君宜,一位家学源渊的才女型的老作家,从投身革命到文化革命,从青运干部到编辑家,出版家到作家,始终刚正率直、热情洋溢、表里如一、文质彬彬。
韦君宜,一位刚正不阿的老布尔什维克,一位不断地在道德上自我拷问、自我忏悔、自我完成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她代表着从年轻时起就投身革命、亲历历届运动的一代知识女性,她一开始就把心交给党,到了生命将尽之时交给党的仍旧是一颗不过洗礼得更加纯正的真心。
拜读《露莎的路》心里颇不是滋味。恕我引用冰心老太太1988年读报告文学《国殇》后关于知识分子的一段披肝沥胆的话:“我伤心而又担心。担心的是看到这篇文章以后能有权力处理的人,不会有时间来看它,看到它之后又‘忙’得未必伤心!”又说:“说一千,道一万,抢救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巧,这里又是“抢救”——引者),还得知识分子自己来做,‘殷忧启圣,难兴邦’,呜呼,请求,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有这个经验。”正是冰心,1936年,在英国,女作家伍尔芙劝她写这样一部自传:“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你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的参考的史料。”韦君宜要在垂暮之年完成的,正是这样一部可供“后人参考的史料”。
延安时期康生搞的那套“抢救”运动,同文革时期江青一伙搞的“深挖”(“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何其相似乃尔!他们所施用的计谋和暴虐人身的手段,甚至口出恐吓和逼供的秽言恶语,也几乎同出一辙。“抢救”“深挖”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深挖”是“抢救”的重演。前者的出现是悲剧(毛主席行脱帽礼时群情激动,其悲更悲);后者的出现是喜剧(没有人行脱帽礼,也没有一个说法,何等深重的喜剧啊!),但在历史上,“抢救”和“深挖”都成了闹剧。
我把《露莎的路》看做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苦难历程的一面镜子,当然,这面镜子照过去、照将来,也照知识分子自己,连同自身的污秽。做为知识分子,韦君宜让我更实际、更清醒,清楚自身的局限从而更加自爱、自信。
1996年2月9日 北京古园
※ ※ ※
不知不觉进入年节。北风凛冽。大年二十七我和宗蕙相约看望韦老太太。鼻饲,直僵僵地躺着,只有右手暗自哆嗦,连眼珠也一动不动。她直勾勾地盯着人,她就是用这双貌似呆滞的眼睛同人们对话。急了,嘴里咕咕噜噜,非护士综合判断概莫能解。我大声凑近她喊道:“我理解你!”她听懂了,用眼睛听懂了。临别时,我写了几句话,写着写着右手也哆嗦起来。上写:
我爱《露莎的路》,我写文章盛赞这心声和信史。我仰慕君宜愿她长寿!
眼前这几句话,她一眼看明白了,干枯的眼角旋即渗出泪珠。
人们忙着办年货,大街上换了一个世界。阵阵北风,我感到很冷。
1996年2月15 日协和医院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