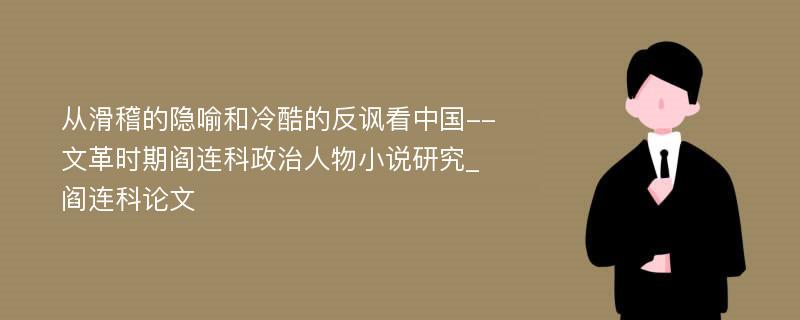
在谑虐隐喻和冷峻反讽里考量中国——阎连科“文革”政治人小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峻论文,文革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的外在忧患莫过于西方欧美强权辱国、东方倭寇蹂躏“母体”,内在恨事无 疑是“大跃进”、“破四旧、打砸抢”、“文化大革命”等破坏性到极致的一系列“红 色政治癫狂”事件。外在忧患体现在全民族有目共睹的“显性”创伤和愤慨,这种“显 性”以器物、物质的大面积遭到“夷族”毁灭和身心戗伤而备受同仇敌忾,但激发了全 中国人民千夫所指发愤图强;内在恨事(传统文化和经济生活、心理承受力几至毁灭性 边沿)却远非“显性”能指,而是大量的大面积的“潜隐”于民众内心世界,成为可怕 的“积郁”,这是政治机器刻在自己内心一条条沟壑似的血烙。在那些年月日里,跳着 “忠”字舞的中国人民在躯体上饱尝饥馑带来的苦难,心理上也备受“以阶级斗争为纲 ”蜂拥而至的精神摧残,扭曲的人格心理后效应在中国至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在这样 惨痛的毁灭性“国家教训”面前,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又像一群丧失“集体记忆”的“失 忆儿”,鲜有文化精神产品来周详系统阐发对上述“运动”忏悔精神、反省思想,以能 对后人产生警示效用,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产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则不 过触及了尘埃似的一层“民族苦难、思想浩劫”表象。70年代末,以《班主任》、《伤 痕》等一批反映“文革”流毒后效应、母女互遭政治癫狂而致亲情泯灭的文学作品应运 而生,但很快以其形式感强、表现手法粗浅、写作技巧糙拙、事相指向表象、流于宣教 痛斥层面而迅速退出阅读视阈,因为这些没有触及灵魂的作品难以臻达笼罩在“国家浩 劫”下全国人民渴望通过忏悔精神、反省意识来“自我疗伤”的界阈,用这来解释“伤 痕文学”在中国仅仅昙花一现就再合理不过了,这跟长达数十年的“文化、思想桎梏” 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一批经过“荒诞、夸张”处理的“文革想像叙事”在已故大 陆“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和风头正健的“新乡土作家”阎连科笔底逶迤产生,《王二 的革命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耙耧时空三部曲)等小说都在努 力勾起我们全民族曾经历练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未必遵循历史化的语言 叙述模式,更揆离现实主义写实化主旨,它是想像化的产物,来源于对悖谬时代的一种 变形、深刻的体认,用满纸荒唐言为全体中国人微缩一张“放大”的变形“政治人”地 图,苦难、荒诞、狂欢、疼痛、谑虐、讽喻是其小说叙事阵营里陈列的一组组群雕和微 雕、能指和所指,这些处于小说核心的关键词串联起一个又一个时代符码,并让它们飘 浮在今日中国上空,警示着深处消费时代和物欲时代“失忆”人们的内部神经,勾起我 们对悠长时空隧道里关于残酷记忆的视境“真拟”。本文欲就阎连科的一系列“苦难” 叙事、“文革”叙事展开考察,对他的“狂想现实主义”文本进行一番解读。
苦难:用土地与肉身丈量厚度
在阎连科小说中,苦难是弥漫在本文上空最浓郁的云翳,他状摹的一系列苦难事件是 中国大地千百年来苦难演绎中离我们视境最近的一环,然而这一环也是最为我们忽略和 轻视的,当我们在离这种苦难最近又最远的今日来重新审视时,发现缺失这种历史苦难 意识其实是在对生活的背叛。在当下这样一个文化、思想全球消费时代谈什么苦难的确 是不合时宜的,但当阎连科在20世纪末将一幕幕不远历史里的生存苦难陈袒在我们面前 时,我们还是在内心深处被重重划开了峡谷似的豁口,血红的豁口深不可测,只见赭红 的血水到处在贲张的血管里奔腾咆哮,这是从河南偏远山村里走出来的农民作家阎连科 带给我们的文本力量,这种文本力量是若干年来中国文学能给予人的极其稀少的能量。 1998年以来,阎连科像许多任劳任怨的黄河流域农民一样辛勤耕耘着他的耙耧三部曲, 让《日光流年》(1998年)、《坚硬如水》(2001年)、《受活》(2004年)沿着时间历史纬 度一一呈现出“荒诞中国”的“荒诞地图”,《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 都在复原这种看似荒诞的历史记忆片段:大跃进、破四旧、右倾下放、揪斗反革命、文 革十年,并用一种适合彼时语境的狂躁(癫狂与激躁)文体参与“受难”和“狂欢”,使 得这种审视达到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传释和反观。
“受难记”是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和《受活》的表面故事主线。在《日光流年》中 ,阎连科用近乎寓言、说唱的言说方略编织了一段河南荒陬僻壤耙耧山脉里三姓村在村 长司马蓝引领下为战胜喉堵绝症而进行的顽强搏斗史。在历史上,喉堵绝症让三姓村三 代村民代代做着活不过四十岁的噩梦,村人寿限的到期终止和肢体的畸形病症梦魇让三 姓村人世世代代都渴望找到病魔缠绕的根源,全体男女村人到教火院卖皮、九都卖肉( 淫)(用此换来物质和金钱)只为寻找到答案,致命答案很快在村里共饮的河渠水里找到 ,根治方法就是从百里山外引进延年益寿的灵隐渠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三姓村人饱受 寿限和畸病的折磨,而村长司马蓝寿限的即将到来和他誓将灵隐渠水引进三姓村的决心 加快了这种进程,于是一场进城卖皮、卖肉运动在三姓村轰轰烈烈上演,男人们等在教 火院外等待烧伤病人来订制自己躯体上的某块好皮,女人们在蓝四十的带领下到九都成 群结队的卖淫,目的都是想卖个好价钱回去开山修渠引灵隐水进三姓村,然而,等到费 了全村几代男女老少全部精力财力而修通的渠道将灵隐水引进三姓村时,三姓村人发现 引进的却是令他们大为失望的一渠脏臭不堪的污水:
所有的目光都哐哐当当集中到了水渠上。都看见沿渠而下的流水,最前的水头,泥黄 乎乎的在日光下,如不断卷着的一条席,有许多草棒树枝,在那半尺高的水头翻上又翻 下。……渐渐的那水头就近了。……果然地有一股冰凉的臭味扑将过来。是一股半盐半 涩的黑臭味如夏天各家院落门前酵白的粪池味。……黑臭的气味愈发浓烈,黏黏稠稠, 把秋天耙耧山脉的清淡都熏得微微黑起来。……所有的村人不再说话。一片惊愕的白色 目光。一片木然不知所措的土黄面庞。……村人们谁都不语,分开立在水渠两边,望着 流水从脚下哐哐咚咚流过,脸上莫名的不解,灰蒙蒙尘样漂着。发黑的污草,泡胀的死 鼠,灌满泥浆的塑料袋和旧衣裙、旧帽子,红的死畜肚,白的脏毛皮,推推搡搡,推推 捅捅在水面上又碰又撞。……有几个叫着爹娘,说这水咋这么臭呀,要把人都给熏死呢 。……日光被污水染得昏暗潮润。……(注:《日光流年》,花城出版社,1998年11月 ,第141~142页。)
十六年前司马蓝沿着山脉到灵隐渠道时,同行的还有蓝大豹的父亲蓝柳根。蓝柳根带 着已经五岁的蓝大豹,那时候灵隐水里处,只消用石头砌出一鳞小坝,把渠头上的三尺 泥土挖开来,灵隐水就能沿渠流进三姓村。然十六年以后,那儿的草房和庙宇不见了, 林地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县城改市后,工厂和住宅区向上游的飞速蔓延,使那水里 没了鸟,也没了鱼,只有河面上面汤般的黏丝、发霉的草木,漆黑了的女人的红裤头, 还有死猫、死猪、死雀和两岸堆满了的工厂、楼房和生活。(注:《日光流年》,花城 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47页。)
当三姓村人发现记忆中的灵隐渠清水变的那么令人不可思议,那么腥污肮脏,大失所 望之际,一个又一个开渠的三姓村村人选择了跳水、上吊自杀,几代三姓村人喝上引来 的灵隐水活过四十岁的梦彻底被打碎了,为修渠受尽的一切苦难都化为乌有,村长司马 蓝也在一片叹息中在四十岁生日那天“无疾而终”,司马蓝与其说是“喉堵症”发作, 不如说是深深的绝望而死的,因为他在面对引进的这一条“世外臭河”面前,一切仅剩 的活下去的希望都熄灭了,他怀抱他的青梅竹马“爱情”——蓝四十腐尸赍志而没,后 者为了表示对司马蓝的倾情,终身未嫁,为了司马蓝“活过四十岁”的梦想实现忍辱负 重率先去城里“卖肉”,以换回修渠所需的金钱。这一点,阎连科在《日光流年》卷首 语里寄托了他深深的忧思和写作由衷:“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 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通过三姓村人引水的失败引来 世外污水这个事相,阎连科意在提供一种悖论式“谶语”:解“难”之时却被更大的“ 难”围囿。“污水”作为阎氏埋伏的一个隐喻象征符号,表征出“自由人”对“政治游 戏”的恐慌难遏心理,寄寓了某种失望情绪和无助呼号。
司马蓝无疑是三姓村里受难的综合代表,他经历了当代中国农村所历尽的一切苦难, 蝗灾吃蝗虫,饥饿食观音土、鸦肉,为了兄弟姐妹活命他背弃了与蓝四十的爱情而娶了 家有囤粮的竹翠,为了修通渠道引进灵隐水消灾免病活过四十岁,他一次次的去卖躯体 上的皮,他最大的梦想是让三姓村人过上世外桃源式的自由生活。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里中国乡村饥饿、穷困、物质、金钱、情欲的两难受难处境逼现出作家阎连科深深的 悲悯情怀,他将这种全民族苦难受难体验浓缩嫁接在一个小小“耙耧山脉”里的三姓村 ,以此实现他用“血红骨白”苦难生活里满蕴象征寓意的用心。
《受活》是作家阎连科的一个高超小说营构巅峰,如果说,1998年《日光流年》叙事 主体还绝大部分停留在现实主义语境中端的话,那么,2004年的长篇小说《受活》则是 完全处在“狂想现实主义”的高端,甚至完全抛弃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现实主义写作之路 ,用奇诡想像力、隐喻反讽遍地横生的如椽之笔构设起一部中国“受难史”,使得阎连 科小说极具“永恒”、“不朽”、“经典”意义。
《受活》里的“受活”按照作者解释是“耙耧方言”,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 淋漓。但在三十万言的小说叙事中,“受难”才是“受活庄人”的最贴切指向,这个由 一百九十七个盲、哑、聋、瘫、瘸、儒等肢体残疾人组成的离奇村庄,地处与世隔绝的 耙耧山脉深处,战争和运动的不及使他们长期过着自给自足自由生活,同时,村人和村 落的特殊性使他们都处在弱势和被忽略位置,是周边三个县都遗忘的“自由”村落,即 使到社会主义红旗插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日都如此。他们在一个类似《日光流年》里司马 蓝身份的昔日女红军茅枝带领下长期“生活在别处”,意外的一次赶集,茅枝身上的红 军血液契合了山外如火如荼的革命改造运动,她带领受活庄一帮非瘸即残之人到双槐县 隆重“入社”,以期完成对组织的皈依信任,然而紧接而来各项运动(大跃进、铁灾、 红灾、黑灾、“文革”)对受活庄的摧残戕害使老红军茅枝决心向双槐县提出“退社”( 退出合作社),希望回到原来的“放任、自由、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于是茅枝走 上了漫漫的申请“退社”之路。而小说里另一个疯子式的“政治人”双槐县县长柳鹰雀 正为他的近乎疯狂的富县之举癫狂,他想以购买前苏联奠基人列宁遗体安葬于魂魄山来 发展带动本县经济,此时正为筹措那笔庞大的“购列款”大伤脑筋,茅枝的孜孜三十七 年“退社”和茅枝背后的特殊人群给柳鹰雀带来了更为疯狂的灵感,他同茅枝达成协议 ,由“受活庄”残人组成绝术出演团外出巡回演出,以残人特技赚取观众钱财来尽快筹 集“购列款”,作为回报,柳鹰雀同意受活庄“退社”回到“自由”状态。柳鹰雀的两 个谵妄、梦游式的疯狂和茅枝一心“退社”的憨愚执拗共同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受 难”结构,茅枝们肉体“受难”觉醒决心“退社”,却跌入另一个耍猴式的人格“受难 ”。
荒诞:在游戏和现实里思索神奇
对阎连科小说的荒诞性解读也是进入他小说世界的一个秘密通道,特别是对他20世纪9 0年代末发表的小说尤其如此。综观阎连科早期小说和其人生道路演变,阎连科属于山 村苦孩子出身,这在他的许多自传体散文中都有集中描述(注:在《返身回家》散文随 笔集里,阎连科用大量的回忆性散文涉及了他逃离乡村的辛酸往事,解放军出版社,20 02年6月,第193~265页。),所以他早期小说和世界观、历史观还是彻头彻尾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小说趣味的忠实执行者,他生于河南伏牛山脉穷僻山村,那里地处中原,曾是 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在大陆文明没落后,长期是中国最为贫瘠落后之地,上个世纪50 年代他降生于此,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破四旧、斗右派、“文革”、以阶级斗争为 纲等中国肉体和思想极为混乱火热的年代,形而下的山村生存残酷和精神桎梏使他肌体 始终处于饥饿状态,逃离山村土地的祈愿日甚一日,在二十岁那年,他才顺利走上了中 国农民出逃土地的唯一出路:当兵。在以后许多年时间里,他从事的仍然是中国意识形 态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出版了大量乡土小说,几百万字小说大多没有永恒的阅 读意义,是萨义德所谓的“政治知识”(注:“政治知识”这个概念出自已故著名美国 学者萨义德,大意为为政治意识形态轴心服务,并要求读者去实施这些概念化柔软意识 形态化的一种文化承载物,如斯大林主义文化、法西斯主义文化、中国“文革”样板戏 文化等。详见《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2~13页。)作品,当然,这种文 字在当时中国复制成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大多没有留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而对阎连科来说,将大量精力消耗在“日后没有勇气再读”(注:在阎连科为自己文集 出版的一篇序言中,他坦承自己对过去小说没有再阅读的勇气。)的过往作品中也是他 的一个遗憾,客观地说,阎连科早期小说都处在低端视境的创作阶段,即使在同样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群中也显得不够出色。进入《日光流年》创作阶段,他才由直击 乡村、人性形而下现实苦难转而思考形而上的荒诞性、离奇性“传奇”,高端的写作视 境使他的小说有某种腾翼感,他用无边的奇诡妙喻、辛辣反讽组成一个荒诞的想像世界 ,但有一点独立认知的中国人绝不把它仅仅当作“想像世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中 国世界”。
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受活》就是他构设“荒诞世界”的两个单元成果。《坚硬 如水》是“耙耧三部曲”又一个以耙耧山脉为背景的“文革”人性小说,这次是在北宋 理学大家“二程夫子”程颢、程颐故里程岗镇程村,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遗迹的山村 ,上演着退伍军人高爱军在“文革”高潮退伍回乡后的“革命夺权史”,并和乡村女狂 人夏红梅共同演绎“革命情欲“肉”史”,这是阎氏“政治人”小说系列中唯一以情欲 为中心,探究革命与情欲两者互动催化的癫狂文本。其游戏式的荒诞性、狂欢性、正面 性情节推进,是殊为不同于以往反映中国“文革”戕害人性、践踏尊严传统“文革”揭 露小说视角的,前者是外在的肯定而内心却蕴藏起强烈的悲情和可笑,后者只直观的加 以痛斥和教化;前者以游戏、癫狂为中心指向“文革”荒诞性内核,后者仅仅停留在表 象批判上,影响力、深刻性大大低于前者。《坚硬如水》荒诞性在于高爱军与夏红梅每 一次性欲高潮都要借助于革命的一次次胜利和成功来获得,革命音乐是他们做爱的最好 伴奏,在一次规划革命行动时,他们有如下的对话:
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
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
她说:“你不想那事了?”
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 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
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寒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注:《坚硬如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0页。)
高爱军在一次次革命成功中当上了村长、副镇长,随之他的性欲也水涨船高,为了保 持这种旺盛革命与高涨情欲,他在与有夫之妇夏红梅家地下挖通了一条长达五百余米的 地道,以供两人随时在地下“做爱”,革命与做爱此时已捆绑为荒诞的一体,“越是要 革命,越是要做爱;越是要做爱,就越是要革命。”这句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口号似乎 在当时“全球化”运用。
《坚硬如水》荒诞性的表现还在它通篇行文的“文革”政治咏唱叙事化,革命化豪放 唱词、民间信天游式的吟咏,加上严酷的打、砸、抢、夺权、革命狂魔现实构成了一个 巨大的荒诞性符号,阎连科没有在《坚硬如水》中一如“文革”小说惯常的一味揭露政 治混乱毒性,而是将身体作为主角取代政治毒性鞭斥,用身体内部蕴藏的无边欲望滥觞 来加强“文革”政治人的狂魔化、荒诞化特征,高爱军和夏红梅这一对“政治人”随着 政治狂想的成功也转化成“欲望人”巅峰。他们到处做爱,病态的迷恋做爱,甚至在《 坚硬如水》的结局里,革命积极、狂热让他们受到地委关书记的接见,高爱军要当县委 书记的革命梦想很快就要在这次接见后实现,却因为看到关书记写在“文革”发动者之 一江青照片背后“我亲爱的夫人”秘密而戏剧性身陷囹圄。等待接见之前他们在招待所 仍不忘做爱,在越狱逃亡路上他们依然在疯狂做爱。在得知死亡在即,他们还想着“革 命尚未成功”:没有炸掉二程牌坊和烧毁积藏二程书籍著作的程寺,于是越狱去完成革 命任务,在即将实施革命计划的时候,他们还刻意在堆满二程著作的书籍上进行最后一 次做爱以行革命“祭祀”典礼。做爱成了他们革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政治“图腾”仪式 。最后他们在完成毁灭“四旧”遗迹后回到监狱,发现让他们身陷囹圄的不是革命途中 的杀人、陷害、偷情举动,而是一次小小的偷窥地委书记秘密招致的,他们死在一张遗 失的江青照片这一荒诞性事件上,高爱军、夏红梅革命斗争高潮就在这一充满戏剧性的 荒诞事件梗阻下戛然而止。“文革”中火热革命、造反、激情被阎连科《坚硬如水》解 构性、荒诞性叙事阐发出入木三分的深刻,让中国人领悟了平面教化达不到的功效,对 “文革”的可笑、狂魔、荒诞有了深刻的现实省察、思考、体悟。
《受活》的荒诞性人物和事件比《坚硬如水》更富现实、苦涩、深刻、反讽意义指向 。《坚硬如水》将“肉欲”放大、夸张、疯狂到难以遽收的程度,兽性般做爱的密度和 频率一定程度上损伤到“政治荒诞”的效果产生,而流入当下消费文学的叙说圈套。《 受活》作为迄今阎连科思考最成熟、思想蕴含最深彻、视境笔力最开阔老到的文本,体 现了作家圆润奇崛的艺术创造和忧思现实的悲悯情怀,寄喻着作者对当代“中国世界” 的深刻理解与无边同情,镜现出当下中国由癫狂“政治人”和无助弱势群体构成病态“ 残疾社会”原景图,在外表亦庄亦谐看似不承载任何道义的行文里,内心却垒聚起冷峻 反讽的悲情之碑,使得这部小说成为阎连科考量中国的一个杰出思考成果。
《受活》里的受活是指对生活的享受,但小说中到处蔓延的是灾难、苦衷、无奈、失 望和惨痛“政治梦魇”再现。双槐县县长柳鹰雀如出《坚硬如水》高爱军政治狂魔一辙 的影子化身,成为“文革”后的新一代“政治人”,他同高爱军一样,有着狂热的政治 野心,他甚至将自己的头像偷偷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挂在一起,并开出了 自己当县长、地委书记、省长的政治演进图、时间表。购买“列宁遗体”安葬魂魄山致 富全县,组织受活庄绝术出演团筹集“购列款”等等都是他超级妄想狂的杰作,这是《 受活》小说构设的外在荒诞结构;内在荒诞结构则是受活庄全体残人围绕进社、退社、 黑灾、红灾、铁灾展开的一系列回忆,女老红军茅枝是这场荒诞史的核心人物,她梦想 还一个“自由社会”给受活庄人,历时三十七年要求“退社”,却受到县长柳鹰雀的“ 要挟”,只得以组成两个令人喷饭和怪诞的绝术出演团到处演出为疯子县长筹集“购列 款”来完成“退社”宏愿。在这里,作者对“退社”(退出?)是否还别有象征和隐喻。 最后,柳鹰雀和茅枝以一残一死来终结了这个极度夸张而富现实能指的游戏。大荒诞里 套着小荒诞构成了《受活》绝世的神奇世界和可笑现象,让残人们成为隐喻化象征的绝 想。
狂欢:以肉欲盛宴嘲弄政治荒诞
Carnival time(狂欢节)无疑是西方世界重要的放纵之日,“嘉年华会”也成了天主教 国家人民用“身体献礼参与纵情狂欢”的最盛典之日,与此相对应,被西方世界称为“ 中国狂欢节”的春节却只是一个“内敛”化期待式礼数谨小慎微的“狂欢节”,唯一外 化的是除夕之日彻夜燃放爆竹的狂欢,它同西方狂欢节用身体祭礼、喧笑狂欢的心态截 然不同(注:西方狂欢节在于用身体作为道具,肆意涂抹各色油彩面具化游行,狂欢滥 饮和喧闹心态是其主髓。)。自从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将Carnival(狂欢)引入文学 ,并将其延伸为“狂欢理论”以后,“狂欢”一直被用来解释文学中的某些价值颠倒、 秩序散失、想像力极度夸张的情态再现。巴赫金“狂欢”理论认为民间文化的本质及其 革命性就表现在狂欢上,而狂欢的实质就是荒诞的身体庆典,即丰盛肥美的宴席,滥饮 烈性酒精,放纵性欲。狂欢中的身体是物质化的、及时行乐的、感官洞开和低级的,不 再是精神的、可控的、理性的、对称的,以此来对抗嘲弄正统或专制、压制文化权力的 高压态势,对官方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知识”加以颠覆和戏讽。巴赫金认为“狂欢体” 在体裁上无疑传承自希腊罗马庄谐体文学,在同民间狂欢文化交汇后产生的。用这来阐 释阎连科的“狂欢体小说”文本就合理便捷得多。
在《坚硬如水》中,阎连科为我们构设了这样一个图景,在激进、非理性“文革”岁 月里患上革命狂魔症的高爱军、夏红梅为“革命翻新”夺取一个压制他们的权力系统, 这便是满腔革命热潮的高爱军受到来自于村长岳父的戏耍式对待愤懑,以及县城女将夏 红梅在面对软弱(阳萎患者)丈夫、道德家庭时的振臂一呼。一系列夺权行动都在激情荡 漾的革命歌曲和性欲绞结里奏效着,革命愈是成功,情欲狂欢就愈为高涨,高爱军以挖 地洞日夜偷情来显示这种身体狂欢的无法遏制,在《坚硬如水》里,大量的革命、做爱 激情迸射文字(“文革”唱词)成为狂欢的依据和理由:
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下岗来修地道敢把山移/爱情的汁水浇灌着耙耧的土地/革命的 种子开花结果定有期/共产党是亲娘将我养育/夏红梅高爱军红心相依/立志做一个中华 儿女/树雄心高举起战斗大旗。(注:《坚硬如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 42页、第83页、第173页、第174页。)
还有大量的革命与性欲同时飞扬的情态场面逼现:
把拳头捏出水来,捏得汗从手缝挤出来,把身上的躁动和对革命的饥渴全都捏在我手 里。我说:“红梅,闹不成功我能对得起革命吗?能对得起组织吗?能对得起你夏红梅脱 光衣裳大半天,我想看哪你就让我看哪的一片真情吗?”(注:《坚硬如水》,长江文艺 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2页、第83页、第173页、第174页。)
在性欲被严重粗暴阻断的“文革”岁月里,阎连科将高爱军、夏红梅疯狂的性欲置于 革命同等自由表达的顶点,当然不完全是为了迎合消费社会的阅读需求。有评论家对此 与论者颇有同感地这样评述,“阎连科在这里并不是要用性欲去写性欲压抑的年代,而 是用性欲狂欢撕碎荒诞化的历史情境——他用更为荒诞、疯狂的生命力量,对抗非理性 的社会革命。”(注: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 译出版社,2002年6月,第463页、464页。)他还进一步指出:“身体的狂欢历来或者说 曾经是民间用来对抗官方压制性文化的有效方式……阎连科用纵欲般的身体叙事替换了 政治叙事,那着了魔的身体就跟疯狂了的政治思想如出一辙。它既是隐喻,又是颠覆。 ”(注: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 2年6月,第463页、464页。)
如果说上述“情欲人”狂欢在小说中占据着极大的版图,那么,“政治人”狂欢则更 是《坚硬如水》的重要叙事要素,虽然它有时处于潜隐的角度,但它是支配前者的叙事 源。高爱军当上副镇长后与夏红梅在地道里偷情时的对话有效的说明了这一点:
她说:“你把那土粒给我弄掉嘛。”我说:“你是叫镇长去把那土粒弄掉吗?”她说: “高县长,你把我奶上的土粒弄掉吧。”我说:“天呀,你能用动县长了?”她说:“ 高专员,你用舌头把那土粒舔掉吧。”我说:“老天哟,你唤高专员就像唤你的孩娃哩 。”她说:“高省长,用你的舌头把我奶头儿上的土粒舔掉吧。”(注:《坚硬如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2页、第83页、第173页、第174页。)
“政治人”的政治狂想甚至还在夏红梅硕大乳房上一粒沙粒的舔掉,展开更为纵深的 抒情:
“我最最敬爱的伟大的政治家、天才的军事家,空前绝后的革命家,年轻有为的镇长 ,才华横溢的县长,一心为公的专员,又红又专、富于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的省长,我 最最热爱、最最忠于、最最信赖的皇上——高爱军同志……请低下你高贵、智慧、充满 了革命觉悟的头颅,去把那革命浪潮中涌现的伟大的女人的伟大乳房上黏的土粒舔掉吧 !”(注:《坚硬如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2页、第83页、第173页、 第174页。)
这种“政治人”的狂欢在《受活》中也俯拾皆是,“社校娃”柳鹰雀是中国政治生活 中的一个怪胎,他作为一个遗弃儿被宣传中共“政治知识”的党校柳校长收养,虽没有 上过一天学,却耳濡目染洞悉“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作规律和教义,以至在 养父病逝后以十五岁低龄就充当起社教工作教员的角色,他按照养父遗留的“登龙术” 按图索骥,一路升迁,直至当上县长,为此他在家里设了“敬仰堂”,用祭祀养父的“ 暗室”预挂他地委书记、省长、政治家的图像“地图”,当然他最后没有完成他的升迁 “狂想曲”,而是同高爱军一样,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后者被戏剧性的枪毙了,他则被 他的“政治狂想”遗弃,为其“残疾人生”划上句号。他自残了一条腿,加入了“受活 庄”的残疾人行列,一死一瘸,就是政治“狂欢”带来的两个文本喜剧式结局。
疼痛:吟唱于黄土深处的辛酸歌谣
文学自古以来就有显现揭示“疼痛感”功能的,历史上成长于盛唐苦吟于“安史之乱 ”的“一代诗圣”杜甫就曾为这种历史“疼痛”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号。《兵车行》里展 示朝廷横征暴敛扩戍延边强征民夫充军打仗,“车辚辚,马萧萧”声中爷娘妻女“哭声 直上干云霄”的送别惨状,这些民夫到头来都落得“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凄凉境地,而家中弱妻代耕虽勤勉劳作,仍然“禾生陇亩无东 西”,男人战死疆场并不能换来朝廷的一丝怜悯,依然催租急迫,行文至此可谓满目悲 愤凄惨,于是乎杜甫就借这些无处申恨的弱者抒出内心郁积长久的忿恨,喷薄而出“信 知生男恶,反是生男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诗里带火,火里带恨, 恨里带悲,悲里带绝。为百姓的生命“疼痛”而歌哭是奠定杜甫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地位 的最佳佐证,他的苦吟诗系列《春望》就浸泡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 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涕泣伤感里,在失去家国归属“疼痛”的“大痛”伤恻面前 ,杜甫只有“看花溅泪”、“闻鸟惊心”,焦灼忧国感时深入肌理;《天末怀李白》里 对友人遭流放远谪深为扼腕,诗中字字充涨着“痛感”式的怀念情愫,“凉风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 汨罗!”思友之痛借景物、时令、古今的互为影射互起作用臻达“屈原同冤”、“生不 逢时”的绝望境地,堪为杜甫的又一种“疼痛”的“小痛”。唐朝又一位现实主义诗人 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也直面反思唐朝倾国毁于重色的“疼痛”,可谓“国家之痛” ;长诗《琵琶行》则对社会底层商妇琵琶哀怨身世抱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深眷顾 ,可谓“民生之痛”。
20世纪杰出的俄国人道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也有类似的文学 “疼痛”出场,这是人类“内心”的“疼痛”,是人类普适的精神“疼痛”,纨绔子弟 富家公子聂赫留朵夫诱使善良的穷家姑娘玛丝洛娃失身于他,并无情地抛弃了她,玛丝 洛娃在遭到始乱终弃后就走上了一条她并不想选择的“卖身之路”,由此还被牵扯进一 桩命案被当作杀人犯候审,此时的聂赫留朵夫作为这桩生死攸关的杀人案陪审团成员出 现在玛丝洛娃面前,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自己才是玛丝洛娃的葬送者,是真正的罪魁祸 首,他经历“内心”忏悔啮咬后,让生命得以重新凤凰涅槃复活更生一次,为了让这种“疼痛”归于“平静”,他想法救出了玛丝洛娃,而这仅仅是满足他作为贵族阶层的“仁义”。托尔斯泰借《复活》痛斥了这种“罪恶”和“疼痛”的根源,对玛丝洛娃这些弱者给予深深的同情。
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在他的传世名作《阿Q正传》中,也为我们预设了关于“民族性疼痛 ”的界阈,阿Q是集汉民族千年文化累积起来劣根性于一身的象征符号,他活生生的活 在中国,现在或者将来,他举手投足都让我们如此熟悉,虽然他无名无姓,但他带来的 “疼痛”是无需有真名实姓的,因为这个人群太庞大了,这是我们民族心中的“痛”。 阎连科、余华等也分别在他们的作品《日光流年》、《受活》、《活着》、《许三观卖 血记》里展示了对“疼痛”的阐释。《日光流年》里,阎连科通过乡土寓言式文字勾勒 了以司马蓝为代表的几代农民在寻求“解除饥饿”、“活过四十岁”解决之道上经历的 坎坷往事,让“生存的疼痛”激荡我们的阅读神经,使我们久久徘徊在作者预设下的“ 生存之痛”陷阱里不能自拔,为活在耙耧山脉里三姓村村民这群时代的弱小人物不懈追 求生命韧性张力而深深感动。余华则用“生命的疼痛”来诠释他的小说人道情怀创作理 念,无论是《活着》里的富贵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都是在一种平民人道 主义写作精神的倡引下完成“痛感”设计的,在体验时间带来的“生命之痛”时,富贵 无奈地送走了一个个亲人的生命依然活着,许三观经历沧桑世事靠卖血几次挽救妻、子 生命,让生命能得以尊严的继续延绵下去。无论富贵在《活着》里将生命一次次送走还 是许三观在《许三观卖血记》里将生命一个个挽回,都体现着一种对“生命之痛”的认 同和趋求精神。
阎连科在展露一个弱小群体迎战“生存之痛”的同时,对原生状的乡村生活形态有了 充满质感的铺陈,用宏大叙事的构架为中国特定时代的“生命”(卖皮及肉体的耻辱生 命)、“体验”(蝗灾及饥饿的死亡体验)注上了欲哭无泪的“疼痛”(悠长的痛)注脚。 在《日光流年》里,阎连科将特定岁月赋予的苦难和深重灾难以一种近乎游戏的方式( 一切活动都围绕活过四十岁展开)消解,无边的“生存之痛”在乡土寓言式的言说中埋 葬了几代人(司马蓝、蓝四十等)的希望,在此岸建立的爱情(司马蓝、蓝四十青梅竹马 史)、长寿(活过四十)、吃饱(不再依靠卖皮、卖淫来换取)良好愿望,被等来的彼岸(爱 情崩塌、长寿灵隐渠引来的是世外污水)彻底瓦解,最后,作者以伤恻的心情用“血红 骨白的生活云涌雪飘、风硬得青一块紫一块”这样带“痛”的呜咽行文终结了本文。
在200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去赶集的妮子》里,过去的历史宏大叙事已经被打成碎片 ,杂糅于这个微型叙事的本文里,一惯的忧患、苦难、疼痛、伤恻情绪则躲在厚厚的生 活帘布后面,在微微掀起的角隅帘布里,凝视起一双捕捉隐匿在乡村日常生活里种种不 测阴谋的眼睛,引领读者通达这些乡村日常阴谋的另一面,将生命中一种短促的“痛” 静寂地着陆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阎连科在《去赶集的妮子》里就是要传导这种小型叙 事拥有的生活种种无边玄想和不确定性,使得生活本身的诸多悬念游离于阅读之外。小 说描写失去双亲、在奶奶严加管束中长大的少女妮子,十二岁了还没有一个人到镇街上 赶过集,独自赶集难以成行困扰阻滞了妮子顺利推进日常生活的想像,这里就潜藏着妮 子奶奶不放妮子独自赶集是对巨大社会充满不信任感,而妮子双亲早逝的悬念则在这种 不信任感里无疑充当了助推因子,乡村日常生活的种种阴谋、不确定性由此延展开来。 妮子受命去独自赶集是在奶奶预感去日不多而寿衣缺失一缕黄丝线的时机,当庇护妮子 、抗拒镇街以外生活使命行将结束时,奶奶只得无耐地让妮子独自赶集,于是在线铺女 店主殷勤的设问下,妮子的身世悬念被高高挂起,在完成购买黄丝线祈祝奶奶长寿,妮 子就完成了这次赶集之旅,故事却并未到此戛然而止,相反向着更为离奇的方向发展。 妮子被路边同为赶集人的汉子招呼到玉米地里吃甜秆,一个乡村阴谋由是突兀横亘在妮 子与汉子之间,汉子要看妮子的身体,而妮子不加反抗就将身体首次裸露在陌生人面前 ,只为讨得一句在奶奶严苛庇护下满足不了的“我白吗?漂亮吗?”成人式诺认,借助这 个诺认妮子想提前进入“她”的成人世界,让生活以后天天有类似“独自赶集”的快适 自由,最后奶奶的突然死掉,才使得妮子感到“被庇护”的珍贵性,在独自面对这个奶 奶不信任的社会时,妮子惊惶无比,高高悬挂的身世悬念再次回溯,“痛感”这次才惊 人地牢牢攫住真正占据了妮子的内心,像阴影样让她摆脱不得。
同《去赶集的妮子》“小型婉转疼痛”相比,《受活》的疼痛则显然震撼人心、弥久 深远,形成巨大的“疼痛”符号,从自始至终失败的受活庄残人,到先胜后败的“政治 人”柳鹰雀,都是疼痛的承载体,他们历时性的一切遭遇(黑灾、红灾、铁灾、入社、 退社)都在后来共时性的疯狂中(购列遗体、绝术出演团)走向“疼痛”的绝想,隐喻性 的吹奏起一首带伤的“中国政治歌谣”,给人以无边的叹喟和心灵撞击。
谑虐:把悖谬现实化为可笑传奇
谑虐在汉语世界指认的无疑是两元对立的话语状态和意义。谑是一种游戏式的玩笑, 比之常规玩笑带有更深层次的形体动作和亲昵成分,往往带有谋略性;虐则跟谑形成对 立关系,是一种残暴的变态的长期性的强加性的把玩(政治、身体、人格把玩),毫无疑 问也是有预谋性的。谑/虐的组合使其语义指向处于一种悖谬状态,但它同“黑白”、 “进出”、“买卖”等相近词性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区分。谑/虐为我们明晰的是一种对 中国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的考辨关系,这是上述词根本不具备的,它是形而上学意 义上组合,可以用以基本解答中国历史、政治、文学甚至思想、哲学诸多内在走向问题 。阎连科就在《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诸小说中采用此种方略表达叙述 追求。
谑虐是狂欢的一种变体,它的指向性根本归属是极端的笑与敛、乐与悲,他们都应是 表现狂欢的一个方向。巴赫金曾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有三个方面突出表现了这种 狂欢文化也即谑虐在小说中的运用。首先是亲昵和笑谑。在民间狂欢中有亲昵、插科打 诨、俯就、粗鄙等狂欢式的范畴。其次是讽刺性摹拟。夸张、扭曲、拉长、放大使之变 形,将崇高事件置于戏仿、摹拟中心。再次是小丑、傻瓜、骗子形象。这些形象是狂欢 广场必不可少的,他们边缘的身份有助于揭示世界的本质。(注:详见《巴赫金全集》3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插科打诨、笑谑在阎连科小说中最为明显,亦庄亦谐的叙事风格,似真似幻的叙述文 体,阐述的再阐述,历史的再历史,山歌、信天游、民间顺口溜式地域语言的大量运用 ,“文革”豪放空洞诗词的戏仿,都起到一种对主题插科打诨的作用,使得整个文风处 在一种弛大于张的语境中。《受活》里的残人们都操持一种唱词式的话语进行交流,如 受活庄遭受“热雪灾”,县长要搞受活庆发钱粮,受活庄残人召集大家的方式是:
唤:“喂,大盲家,明儿一早受活庆,县长要给咱发粮发钱啦。谁家不去谁家明春就 要饿灾了!”
唤:“喂——四瞎子,明儿一早受活庆,想明春饿死你就不用参加了!”
唤:“拐嫂子,你不是想见县长吗?那你明儿就去受活庆上演演吧。”
说:“小猪儿,回家给你爹娘说一声,说明儿日头一出,就在庄口连搞三天受活庆。 ”(注:《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41页。)
这种唱词、山歌、信天游式的言说在《受活》里俯拾皆是,即使在苦难重重的“黑灾 、红灾、铁灾”面前,受活庄残人们都没有放弃这种“放荡不羁”的“自由人”用语方 式,“政治人”柳鹰雀正是在这次受活庆上想出用他们组成绝术出演团以筹集“购列款 ”奇想的。而《坚硬如水》里高爱军、夏红梅对谈的“文革”、领袖诗词滥殇更是达到 一个中国当代小说说唱比例高度,这一点,中国另一个“说唱”作家赵树理也望尘莫及 。《受活》、《坚硬如水》都将笑谑和粗鄙、插科打诨视境、情态作为对历史、政治生 活的解读方式和理解模式,其反讽性突出不言而喻。
而在讽刺性摹拟上阎连科走得更远,通过《坚硬如水》中对“文革”“政治人”情态 的状摹,语言格调的还原“文革现场”,都起到戏剧性讽刺的效果。高爱军因错看一张 照片而戏剧性的跌落,并至枪毙下场;《受活》里“政治人”县长柳鹰雀发狂、荒诞不 经的创业奇想:用受活庄残人的绝术出演筹款建“列宁纪念堂”,都是表达其隐喻式的 讽刺。让病人(司马蓝代表的三姓村人)、残人(茅枝代表的受活庄残人)、疯子(柳鹰雀 代表的“政治人”)等不健全人出场参与本文狂欢,更是阎连科用以揭橥中国政治生活 、历史本源带来“病态”社会的良苦用心。
阎连科还在他构设的文本中用“他谑”来表达对中国过去癫狂政治的独特、解构式理 解。“政治人”柳鹰雀、高爱军、夏红梅精心营构的“政治梦魇”路线图,在他们痴情 而迷乱、狂热而诗意般的阐释下,逐步凸现出一出喜剧色彩浓郁的“可笑”传奇,将可 笑性、荒诞性、悲剧性、传奇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们对复杂纷繁的政治阴谋和政治 生活有深刻的体悟和反思,“他谑”来自于作者对他们的极尽嘲弄。用“自虐”来表达 对生活在“政治高压”时空下以耙耧山人为代表全体中国人的“苦(受)难”回望。司马 蓝领导下的全体三姓村“病人”和茅枝领导下的全部受活庄“残人”是“自虐”的主体 人群,引世外灵隐渠清水战胜病魔、活过四十岁与“退社”当自由人是他们“自虐”生 活的全部主题和祈望,为此他们的“肉身”(《日光流年》里卖肉)、“人格”(《受活 》里残人耍猴式绝术出演)都在遭受炼狱般的啮咬,“自虐”的结果是三姓村引来“世 外污水”,受活庄“退社”等来的是下一轮的政治“进社”,他们都成为新一轮的失败 者和失望者。谑/虐的对立为阎连科小说矛盾性、未知性结构方面提供了各种想像和思 考的可能性,使其小说更具现实指向性和拷问价值。
余论
将阎连科若干年以来小说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标本,是我在看完其小说后得出的一个 结论,其小说透射表征出的悲悯、苦难、荒诞主题是对中国“政治生活”最有力的注脚 。阎连科并没有平铺直叙的状写“受难”平面史,而是用狂欢主题遮蔽住政治事件的种 种流毒,让政治流毒荒诞性的流淌在“可笑传奇”里,一点一滴的烙印似的被恢复记忆 ,《受活》无疑使他的这种小说谋略达到他创作生涯的巅峰。
2004年2月11日—28日于北京北郊呜咽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