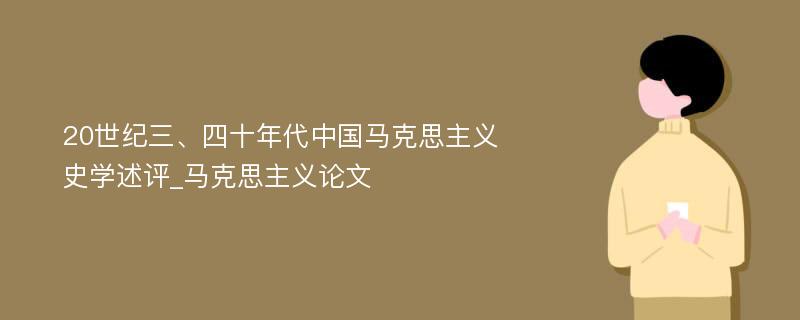
受命危难 展现辉煌——对中国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危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四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它既古老,又年青,因为它总能不断地闪耀出时代的光彩。中国史学从其发端到如今,两千余年的风雨历程造就了它坚韧的性格:越是社会出现大动荡,大转折,史学就越发显示出勃勃生机,从而自身得到不断更新。例如:我国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全国性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政治上,政权更迭、风云变幻;文化思想上,民族间的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吸收、交融,学无独尊。此时的社会显得混乱无绪。然而史学却如梁启超所说,“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独盛”。的确,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史学第一次大繁荣时期,修史制度有了较大的改进,史书体裁与体例有了发展,史学著作的数量增加,史学流派开始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史学在此时获得了独立地位。这一重大改变反映在群书分类上,就是史学从《汉学·艺文志》视其为经学附庸被划分在“春秋家”类而变为到东晋时按四部分类法占居群书之第二位,迈出了史学发展中的关键一步。这一改变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不仅促使史学观念的改变,也使统治者更加重视史学,使其摆脱了经学对它的束缚,独立地向更高层次发展。唐代大规模的史馆修史,刘知几《史通》的问世,无不是此时历史观念的影响所至。
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蕴育出来,封建专制制度已进入到衰落期,满清的入主中原,加剧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宋明理学已解决不了当时存在的深刻的社会诸问题,因而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历史处在大变革时期。严峻的现实促使史学家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私史大量涌现。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无论内容与思想都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其主要进步倾向是反对空言义理,推崇因时变革;主张治史须“经世致用”,以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揭露抨击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等早期启蒙思想。更有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出的卓越史学见解——“六经皆史”说。他在《文史通义》中写道:“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这不仅是对封建统治者捧为“圣经”的六经的否定,而且拓宽了史学范围,表述了六经之旨在于“经世”的看法,替史学界指示了一条从事研究工作的宽广道路。章学诚的史学标志中国古代史学又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一的史学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中国出现的新阶级——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急需建立本阶级的新文化,于是文化上的破旧立新首先从史学开始。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明确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为理论指导,对封建史学从其指导思想、内容、实质、编著体系直到文字组织都作了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封建正史中国人“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在批判封建史学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那就是史学应用来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的影响下,一批近代史学家致力于运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从而使中国史学跃上一个更高阶梯。
史学的进步、更新与社会的变化转型同步,这似乎已是规律,于上述可见。而史学的现实性品格也于其中显现出来,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于这一点,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史学最能作充分的证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阶级斗争、学派斗争与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的残酷性都集中体现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切反映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就是各种思想、流派异常激烈、尖锐地交锋。现实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造就了一大批史学大家,此时的史学无论在古代社会研究、通史的编纂、近代史的著述方面,还是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等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就,成为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也最辉煌的发展时期。
让我们从几位著名史学家的史学成就中了解这一切。
郭沫若(1892-1978)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他于1924年开始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在三、四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研究中国古史的著作,而发表于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则是郭沫若最早尝试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都为中国的前途感到彷徨和苦闷。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但在共产国际内部引起了争论,也逼迫着中国国内各阶级和各党派给予明确的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中国的国情重新进行认识。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初步确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个正确的分析遭到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的反对。国民党右派、改组派以及托洛茨基派都竭力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妄图取消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由此展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实质上,这场“论战”是文化战线上的一场反革命“围剿”与革命的“反围剿”之间的论争。在这种形势下,郭沫若决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作一次“清算”,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实际。他研究中国古代史,怀着对“未来社会的待望”,本着不只是“求实”,还要认真“求是”的原则,努力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郭沫若通过甲骨、金文、《易》、《诗》、《书》所提供的史料,于1928年到1929年间相继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和精神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等论文,汇编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他运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对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作了总体概括,得出了中国古代经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个阶段,走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走过的道路的结论,从而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有力地打击了反马克思主义学派,回击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各种奇谈怪论,鼓舞了大批处在彷徨中的革命者,增强了对于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要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信心。中国的史学出现划时代变革,从此走上科学轨道。
范文澜(1893-1969年)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抗战以前,作为教授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对中国经学、史籍颇有研究。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达延安,曾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成为一名革命文化战士。他自觉地把史学作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1935年,当时东北已经沦陷,日本帝国主义正妄图鲸吞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范文澜利用历史资料编写出《大丈夫》一书,他在该书前面的《凡例》中说:“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凌的事迹”。“每当外敌侵入中国的时候,总有许多忠臣义士,用各种方式参加民族间悲壮的斗争。……他们都换出血和生命,去保证民族的生存,是永远应该崇敬的”。可见,范文澜写此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提倡“民族精神”,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凡例》中又说:“一个国家要是政治腐败,民穷财尽,本身既非崩溃不可,外患自然乘虚侵入。明世宗朝防御倭寇的朱纨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因之衣冠之盗横行作恶,任何才人贤士,无法挽救堕落的国运”。矛头直指蒋介石集团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集团在文化教育中搞起“尊孔读经”,提倡封建复古教育,目的就是遏制思想自由,维护其一党专政。针对这股文化逆流,范文澜于1941年在延安党校进行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讲演。他在讲演提纲开篇的第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他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经学发展变化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经学依封建主义而萌芽,而发展,而没落,而死亡。”“经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如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还有人幻想着继承‘道统’,企图用‘读经’方法麻痹青年,放弃革命。这类人毫无疑问一定是封建残余分子或是投靠帝国主义的奴化分子。……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必需改变经学为史学,必须反对顽固性的道统观念。”毛泽东对这次讲演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四十年代,范文澜著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上下册)及《中国近代史》(上册)。当时,近代史研究基础还很薄弱,而且这项研究同现实息息相关,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密切关注。研究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同现实中如何推进这场伟大斗争、争取彻底胜利密切相联的。范文澜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真谛。他以极大的义愤和具体的事实,揭露和控诉了侵略者的残暴、诡诈和罪行;讴歌了中国人民“伟大团结的民族思想,生气蓬勃的农工群众,勇敢坚韧的反抗精神”;揭露了清朝统治者腐败堕落,对外妥协投降,出卖权益,甘当帝国主义的走狗,镇压人民反抗的丑恶行径。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画卷,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吕振羽(1900-1980)早年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摆脱殖民统治、振兴中华为己任。1930年1月,他与人合作创办了《新东方》杂志,同年10月又组织“东方问题研究会”。由于《新东方》逐步左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而解体。这一切引起吕振羽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思索:国家衰乱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独立富强的出路何在?从此,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来找出中国的真正出路。他的主要著作有:“《中日问题批判》(1932年)、《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1932年,与翦伯赞合作)、《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1934年)、《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7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1942年)、《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年、下册1948年)等。他史学成就的特点,是从经济分析入手,对中国社会当时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几乎非常正确的结论。他首先明确提出中国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本身力量微弱,处于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态,因而它对外不能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对内不能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反而依附于二者之下。其次,他又从资本积累、原料的生产和储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在“国家主权陷于不完整的状态”下,“中国的商业资本,便不会向工业企业资本方面转化”;“微弱的产业资本想脱离外国资本的支配,自己独立起来,不过是一个幻影罢了。”从而得出结论:“中国资本主义前途无望”。再次,1934年吕振羽将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了一个基本的概括,提出他的“西周封建说”,同时认为鸦片战争后,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样的术语来概括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直接汲取了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成果,从而影响了中国整个历史进程。吕振羽批驳了“资本主义社会论”、“中国封建残余论”等错误观点,认为“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在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完成资产阶级所未能完成的任务,而行的一种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客观上没有领导这个革命的能力,不能不由工农群众来代行”。“九·一八”事变后,吕振羽对时局进行分析:“市场的再分割,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继续不断的事实。中日问题因之在市场再分割的形势之下而展开出来。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本质的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满洲又是资本主义各国视为反俄的东方防御线。因此,中日问题的意义,又含了一个反俄的内容。”这个分析,实际已预示出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国际意义。正是由于吕振羽运用了唯物史观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才使问题分析透彻而深刻,结论正确而令人信服。
侯外庐(1903-1987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一面从事抗日宣传,一面致力于学术研究,“是他在学术上最活跃、最富于开拓精神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时期”。主要著作有:《社会史导论》(1939年)、《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3年)、《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等。侯外庐早年曾费十年之功译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曾说,“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正因为他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科学的方法论,才使他在学术研究上既“实事求是”,又“自得独立”,从而在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领域内取得开拓性的成就。他治史的显著特点,是把社会史工作和思想史工作互相配合。在《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史》一书中,“探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发展的关系,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与某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式的关系,学派之间同化与批判的关系”等,意在说明“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具体地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特别传统与其运行的特别路向”,发掘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以为所应批判地接受与发扬之明鉴”。在史学研究中,他主张详细占有资料,并去粗取精,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然后对历史作出评判。侯外庐把历史研究看成“虽不是革命指导本身,然至少也是推进社会发展与革命需要的辅助部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主张历史研究兴趣要服从于现实,历史家应“同时是社会运动者,政治改革家,而非如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使人片面化的所谓‘专家’”。侯外庐正是通过社会实践丰富了自己的历史研究,也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他参加了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成果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中。侯外庐第一次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为两个平行而不同发展的路径,他认为“亚细亚的古代”和“古典的古代”在马克思经典著作里,都是指奴隶社会,它们之间只是“路径”的不同,没有本质和时间先后的差别,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他说过,学习理论“不是念书,而是通过自己的实际生活,融会贯通武器的无敌性,在一定科学的活动领域内,使认识能动性的修养成为结实而经得起考验的力量,以期可以用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之‘矢’射中中国历史规律之‘的’”。因而,他全部研究的目的,就是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1938年10月毛泽东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侯外庐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史学研究上的最好实践。白寿彝先生这样评价侯外庐:“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领域的传播和发展中,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二十年代的阶段性的标志,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三十年代的标志,那么,在四十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应有他独特的地位。”这个独特地位,我认为,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上所论述,仅仅是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史学成就,还有剪伯赞、杜国庠、邓初民、胡绳、何干之、邓拓等著名史学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都作出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创立,是中国史学划时代的变革,是中国史学一次质的飞跃。它再次证明了社会变革与史学更新同步的规律性。这一规律本身又告诉我们,史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与时代的要求相一致,或服务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现实。
其实,整个中国学术,就其本质而言,是入世的,是积极干预政治和人生问题的,对此,梁启超曾有过清晰的阐述:“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而史学把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具有在继承我国史学中经世致用传统的基础上再加以科学化的特征。
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危难时世,造就了辉煌的史学,从而使史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埃德加·斯诺在他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的结尾这样写道:“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象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这里所说的“背后动力”、“有力因素”,应该是一种精神与信念,即虽饱经忧患与磨砺,仍不甘自馁与落伍的中华精神。而这种精神藉史学以保持,藉史学以发扬。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完全意识到自己”。中国人民正是从自己民族的历史中,看到了中华民族光明的前途,国家未来之所在,因而才能为争取美好的明天不屈不挠、前仆后继。
史之为用大矣!
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世纪之交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转折。史学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中国史学必将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再现时代光彩。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文; 历史论文; 侯外庐论文; 古代社会论文; 吕振羽论文; 范文澜论文; 新史学论文; 辉煌集团论文; 历史学论文; 金文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史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