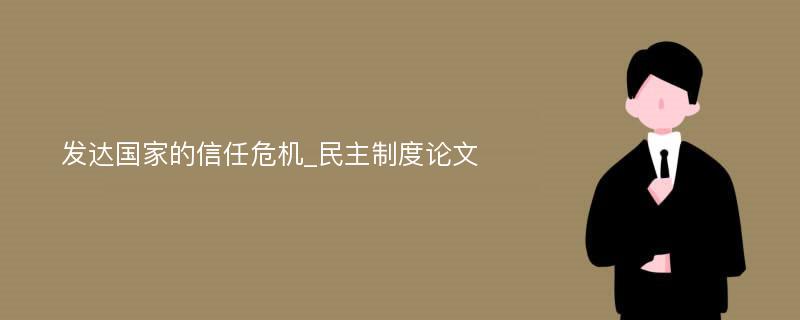
发达民主国家的信任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危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20个多元化民主国家里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相当一部分、有的甚至是大部分公民,对党派、政府、议会、高层行政机构、法院、军队、警察、工会、大公司、教会、电视和其他大众传媒等主要机构和组织“完全不信任”或“不太信任”。这一点也被其他民意测验所证实。搞这些民意测验的机构,事先并未互相协商;所调查的问题,其表述也各不相同,然而,这丝毫不能降低测验结果对于比较研究的有用性。当一个现象在20个国家里普遍出现,而且在每个国家不止一次地发生时,就说明这些测验所取得的社会学资料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公民所表达的“不信任”,恰恰是该制度的合法性所带来的长期后果。
民主制在世界的推广和它在发达民主国家的衰落
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采用了民主制度。最近几十年,民主制像商品一样出口,也作为仿效的模式进口;它或是被满腔热情地接受,或是被从外部强行加予,总之已经在近50个国家里实行或仿制出来了。民主制成了跨大陆的政治范式。在民主制的极盛时期,在老牌发达民主国家,民意测验的调查者们看到了民主衰落的征兆,看到它的机能逐步失调,逐渐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失去对它的最重要机构的信任。初听起来,这简直是奇谈怪论,然而,这是事实。
如果人们对国家机构的怀疑发生在专制国家或表面民主的国家里,那还比较好理解。但现在恰恰相反,对民主机构功能的不信任出现在发达民主国家里,这就使人吃惊了。因此,必须考察出现这种情况的特殊原因。
虽然,在目前的政治谱系中,尚没有一个新的民主思想可以取代正统的民主制,但是,人们不应忘记,民主不是僵化的模式,而是一个鲜活的、总是追求平衡的有机体。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政治思想家也没说过“民主已经完善”的话。民主制有其弱点,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被认为是能够趋向完善的。
今天,在全世界,大约有30—35个后工业国家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其中包括捷克和斯洛文尼亚,但不包括许多处于改制阶段、正在向民主制过渡的国家。发达的民主制是多种多样的,在分析它们的功能失调时,必须考虑它们的形态各不相同。然而,缺乏信任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仍是令人吃惊的,虽然不信任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
不信任的四个特征
有材料表明,对信任的侵蚀有四个特征。第一,这不是由特殊局势造成的暂时现象。实际上,近几十年在某些国家和更长时间内在其他一些国家所进行的民意测验证实,这是一个稳定的现象。失意和不满有可能成为时代性的特征。
第二,缺乏信任是普遍现象。这在所有发达民主国家都非常显著,甚至连瑞士这个“样板”国家也不能幸免,只有卢森堡例外。
第三,缺乏信任不仅具有时代性、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结构性,它涉及大多数重要机构。人们对这样的机构不再尊敬,政府权力弱化。
第四,这种不信任具有合理色彩。大多数被访者不是在意识形态基础、而是在实用主义基础上表示了他们的不信任的态度。也就是说,这种信任或不信任很少随着左派—右派或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轴心的变化而变化。
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人民对政治的失望与疏远
曾几何时,英国被视为民主国家的正统模式。而今,忧郁笼罩着英国的天空。
1995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英国人认为:政治体制运行不能令人满意;国家管理方式应该改善;议会对政府监控不力;必须实行全民投票;应该用选举大会取代上议院;应该通过成文宪法;应尽早确定立法者的全权期限;要改革选举制度;要制订一部关于信息自由的新法律,等等。
在丧失信任的过程中,是否有某个转折关头、某个点,自此以后制度就失去了合法性呢?意大利在这方面可以充当临床病例。在欧洲所有多元化民主国家中,意大利是一个从70年代开始对民主制运行不满的人就占有很高比例的国家。1987年这个比例是72%,只有26%的意大利人对现行制度表示满意。1973年至1991年期间进行的25次民意测验表明,每次总有超过70%以上的意大利人对现行制度作出了否定评价,只有一次,1987年11月,这个比例稍低些。意大利的社会学家、政治家写了成百本书,探讨诸如家长作风、贪污、内阁迭次更换、一党至上等体制弊病。近30年来的调查证明,对“体制”的批评、特别是从公民角度对统治阶级的批评,一直相当尖锐。然而,至今,意大利仍是个民主国家。只有一小部分人对制度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大多数人批评的只是制度的运行。改革而不是革命的呼声很高,这也蕴涵了对现行制度仍具合法性的承认。近40年意大利一直保持了经济的可观发展,其速度超过大多数欧洲其他国家,这也许是意大利人能够继续忍受现有制度的一个原因吧。
在美国,调查对制度的信任程度这种做法有悠久的历史。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多元化民主制可以与公民对各种机构缺乏信任共存;不信任的情绪可能贯穿整个时代;政治制度可以保存,尽管相当一部分公民对它缺乏信任;民主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尽管时常出现功能障碍;民主制仍然可以继续存活下去,像得了慢性病的人一样。40年来的调查显示,对制度不信任的美国居民广泛地分布在各个阶层。
60年代,85%的美国人把他们政治机构的运行当成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30年之后,1995年7月两个组织(一个跟民主党有联系, 一个与共和党有关)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93%的美国人谴责政府挥霍纳税人的钱,88%的人批评大选前乱许空头支票的现象,并对某些法律规定给予外来移民以高于美国人的优待表示不满,等等。
最近20年,2/3 的美国公民说, 他们对政治体制的运行不满。 1988年,只有16%的美国人对联邦政府表示很信任(而在1966年这个比例是43%);15%的人对国会很信任(1966年是42%);13%的人信任工会(1966年是22%);17%的人信任宗教组织(1966年是41%);信任大公司的占19%(1966年是55%);32%的人信任最高法院(1966年是50%);信任军队的有33%(1966年是61%)。1988年进行的另一次民意测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对政党的信任下降
近几十年,在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政党的形象都变坏了。各个党派成员都在减少。许多党派,昨天还是群众党,今天就几乎是政客们的党了。选民很少去参加选举,这就是对政党失望的结果,在美国尤其如此。当然,意大利一党至上的终结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政党只对选票感兴趣,选民的观点和渴望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这是许多国家的被调查者对政党的看法。就连在瑞典这个长期以来政党组织得很好的地方, 不信任政党的人也从1982 年的36 %上升到1992年的68%。政党作为一个组织让人失望,当然,这也与政党领袖缺乏魅力、意识形态逐渐淡化有关。
经济效率与合法性
由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公民对制度是否信任就与国家的经济效率相关了。民主在智利的衰落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危机有关,近些年智利年通货膨胀率为746%。 经济没有效率对德国和奥地利也是致命打击。经济失败会削弱制度的合法性,至少会削弱它的某些机构存在的合法性。苏联解体不是因为战败,而是因为经济极端缺乏效率。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搞得好,它的制度就有存在的合法性,至少有部分合法性。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能够提高政府的合法性,能相对自由地组织选举,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德国和日本的例子更引人注目,本来,它们的民主制是被占领军引进、在怀疑和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合法性,但随着“经济奇迹”被创造出来,它们的制度本身也结束了屈辱的状况而成为合法的,德国和日本也成了多元民主国家的主要成员。
结构性失业会使人们失望并产生异化,但它并不足以导致民主制的崩溃。30年代,尽管当时经济萧条、大批人失业,但人们对美好的未来尚有信心。90年代,结构性失业、上层人物贪污、社会不平等加剧和非欧洲移民涌入,使一些观察家有“导致突变”的担心。这种担心与极右运动联系在一起。可以谴责极右运动,但忽视他们的存在是不明智的。
不信任渗透社会各个阶层
通常各地的年轻人都比年长者对制度和领导更不信任,老一辈更相信教会、军队和警察,右派政治倾向的人比左派更不信任工会,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对制度和领袖更不相信,等等。但是,“受教育程度”变量和“年龄”变量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比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更高,只能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弄清这两个变量各自对信任函数的影响。受教育程度与对铅字(但不是对电子出版物)的信任度密切相关。男人和女人对制度(除了对教会)的信任并没什么大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底层的人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缺乏信任感。正相反,受到良好教育的中等阶级对工作不顺心和制度缺陷最具有批判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结论:公众对贪污比对社会非正义反响更为强烈,这可能与新闻报道有关。
虽然民主制的合法性在西方任何一个后工业国家都无可争论,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是最好的制度。长期以来对它的低信任度表明:我们是民主制严重功能失调的见证人。
公共交通的发展和国家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干预的加强造成所谓“政府负担过重”,断断续续的、每4—5年一次的选举仪式也不够成功。议会越来越失去政权头号中心的地位。政府无力满足公民的所有期待,这对它来说是个超负荷的、矛盾性的任务。
但是,信任危机应该被理解为集体对更大的民主的一种向往,而不能说民众已失去对民主基本价值观的信任。信任受侵蚀首先是社会政治成熟的一个特征。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与政治体制运行有关,从中吸取的原则性教训是:现在,在代表制的民主制国家里,选举的这一套“工艺流程”对于取得公民的信任是远远不够的。公众的意见不可能像以前一样每隔几年在选举时表达一次,他们需要每周每月都发言。在宪法法院监督下搞民意测验,可能会是公民选举的有益补充。因为在发达民主制(还有更多的另外类型的制度)的运行中存在许多功能失调,也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议会制已经被神圣化,所以,应该由议会外的人来代表群众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