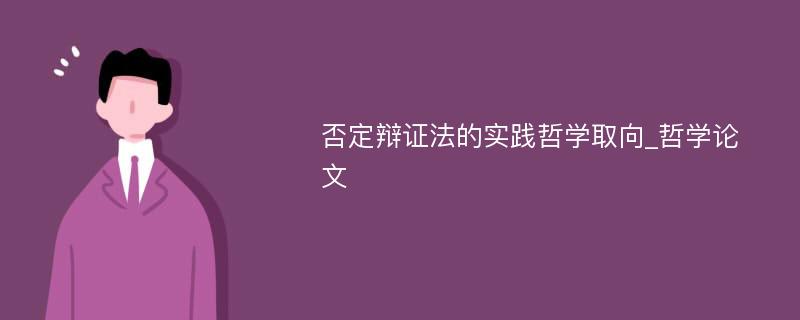
否定辩证法的实践哲学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取向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哲学转型的通常坐标中,阿多诺哲学的位置是相当独特的,确切地说,是充满矛盾的。阿多诺哲学的非同一性诉求和否定的方法足以使他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行者,以至于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人都承认对他有所继承;而就其对主体、客体以及理性等传统哲学范畴的坚持而言,阿多诺又会被批评为传统哲学的最后代表之一,最终仍没有突破近代哲学的影响范围。① 阿多诺哲学的这种双重身份展示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代哲学的转型是否必然地要以抛弃主体性或主体—客体的结构为前提,或者反过来说,在哲学转型的过程中抛弃主体—客体的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不言而喻,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深入到了当代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之中。在此,笔者愿引进一个关于当代哲学转型的更具包容力的坐标——即将当代哲学的转型理解为从理论哲学向现代实践哲学的转型②,从而对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作重新考察,以标定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位置,并对当下的生活世界话语作必要的反思。
一、非同一物的“痕迹”
我们认为,哲学范式的转型一般表现为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跳跃,但这决不意味着要否定哲学发展本身的连续性。因此,我们说近代理论哲学范式向现代实践哲学范式的转换,并不是对理论哲学问题框架的简单抛弃和全面替换,而是要首先意识到旧的哲学问题框架,并从中踏实地走出去。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要“超出这些问题自身并最终突破其整个的空间”。③ 阿多诺突破传统哲学的方法首先是揭示其内部原则的矛盾性,或者说是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本质。
一般而言,西方理论哲学的传统可以说是开始于对万物的原理的探索。这种原理为了保证其普遍有效性,就必须成为抽象的概念,与所有感性的、流变的事物分离开并成为这些事物的原因。④ 可以说,传统理论哲学的主题始终被锁定在这种原理之上,锁定在这种作为万物同一性的普遍性之上。但阿多诺却认为:“从历史上看,哲学真正的兴趣是在那些黑格尔及其传统一致地表示不感兴趣的地方:在于那些非概念的、个别的和特殊的东西;自柏拉图以来,这些东西就被作为易逝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来处理,被黑格尔贴上‘惰性实存’的标签。哲学的主题应该是被它贬低为在定额上可忽略不计的量的质。概念急切要求的是那些它够不着的、被它的抽象机制排除的东西,那些并未成为概念之样本的东西。”(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in Gesammelte Schriften,Bd.6,Suhrkamp Verlag,Frankfurt/M,1997,S.19-20;参见中译本,阿多诺:《否定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以下引文凡引此书,只注中英文页码。译文有改动,下文中此类情况不再注明。)显然,阿多诺在说,哲学的真正兴趣和主题始终处于哲学之外,始终只能是那些拒绝概念化和同一化的东西,因为任何一种哲学的原理最终都要声称对这些东西的有效性。按照阿多诺的论断,理论哲学的本质乃是“辩证的”:“凡在某个绝对的‘第一者’得到表明的地方,必定会谈到它的意义相关项,谈到那次于它的、与它绝对异质的东西;第一哲学和二元论走到了一起。”(S.142,第135页)
阿多诺这一论断的关键在于,他认定了处于概念体系之外、拒绝被概念化和抽象化的“绝对异质”领域的存在。并且,这一领域必然地是解理论哲学以及其概念体系之本质的一个部分,而绝非与这个体系不相关。所以,阿多诺发现,从古希腊开始,传统哲学的内部始终能找到非概念物或非同一物的涂抹不掉的“痕迹”。
阿多诺指出,柏拉图理念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感性的欺骗性和虚假性”,“将感性世界描述为不存在的东西”,这一基本观念是柏拉图综合爱利亚学派和赫拉克利特哲学的结果。然而,尽管柏拉图的理念论将感性的流变的领域贬低为“非存在”,但它却无时不受到这种“非存在”之物的困扰。柏拉图“关于零散的物分有(methexis)其向来所属的理念的学说”本就预设了“某种与理念相异的东西”,“如果没有与理念相异的东西,那么对理念的这种分有便根本不可能”;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的确可以说含蓄地提出了一些已是非常辩证的命题:没有‘一’的‘多’是不存在的,亦如‘一’、理念离开了‘多’也不存在;这个‘多’即是与理念相对立的零散的事物,而每个物都被包摄入理念的类之中”(S.30-31)。理念始终摆脱不了它的“反题”,这就表明被柏拉图称为“非存在”的东西恰恰是确然“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试图用概念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即提出“这个”(tode ti)和“质料”(hulee)这样的概念,将个别和感性的事物归到其名下。通过将这类概念确立为原理,亚里士多德就完成了对柏拉图的批判。这种批判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但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拯救理念论原则的企图。因为,“这个”和“质料”这样的概念仍然是十足的抽象,当我们在谈论这类概念的时候,事实上乃是给这一领域强加了一个形式。阿多诺说:“不能将它与这个形式自身的意义混为一谈。我们这里使用一个概念或谈论一个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根据那些自身不是概念、自身不是原理的东西来标明其意义的,这是质料这个概念的特质;只有理解了这一点,即质料这样一个概念的意义乃是非概念性,我们才正确地理解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S.106)看来,“这个”和“质料”就是已不能被思想的进一步操作消除的“某物”,它标志着非概念物在理论哲学体系中“最低限度”的存在是非同一物的痕迹。
如果说将思想的概念化“操作”用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显得有些“时代错位”的话,那么它对于近代以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则完全没有这个嫌疑。因为这里概念与非概念物的之间的紧张直接体现为主体的功能与其指向的对象之间的紧张。阿多诺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感觉作为‘某物’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存在者的位置。但感觉并不具有比任何别的现实存在者更优先的认识地位。”“但如果形式、即先验主体为了能够作用,即为了能够进行有效判断而非需要感觉不可的话,那么它在本体论上似乎就不仅依赖于纯粹统觉,同样也依赖它的质料,即统觉的相反一极。这必定会从根本上毁掉整个主体构造的学说,因为在康德看来,质料是不能归因于这种构造的。”(S.140,第134页)黑格尔对待非概念物的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相似,即以“极端特殊化的一般性概念”来代替特殊的事物,“例如实存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再没有特殊的东西”。黑格尔无疑也意识到了非概念领域的意义,并且阿多诺认为他已经提出了一种“特殊性的辩证法”。但是黑格尔害怕这种辩证法,因为“这种辩证法摧毁了同一性的第一性,理所当然地也就摧毁了唯心主义”。最终,在黑格尔辩证法中,“使特殊物成为辩证推动的东西,即其在总括概念中的不可分解性,被当作普遍的事实来陈述,仿佛特殊物就是它自身的总括概念,因此是不可分解的。非同一性与同一性的辩证法正是因此而变成了假相:同一性(Identitaet)对同一物(Identisches)的征服”(S.175,第171页)。
同一性所能征服的最终只能是同一物,而决不是非同一物。传统哲学理论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反而为我们提供了追索非同一物的踪迹。这可以说是传统哲学固有的矛盾,亦是阿多诺突破其概念体系的缺口。
二、“星丛”作为传统哲学理论方式的超越
非概念物的确凿存在构成了对概念本身的反思,这种反思告诉我们,概念本身不是自足的,概念的体系也不是封闭的。阿多诺说:“其实,所有概念都要涉及非概念之物,因为概念就其自身而言是现实的要素,这个现实首要地是为了控制自然的目的而迫使概念形成。概念的中介自身从其内部显得在其领域中具有优先地位,离开它什么都不可能被认知。这不应被误认为它本身的样子。这种自在存在者的假相使得它运动以免除它自身置身于其中的现实。”(S.23,第10页)概念只是现实的一个要素,那么真理就必定处于超越概念的地方。阿多诺认为,必须通过概念才能超越概念。这正是对新的哲学理论方式的探求。
既然是通过概念来超越概念,那就不可能完全抛弃概念,而是要通过概念表达非同一物的意识。这便是否定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虽然是从传统哲学中生发出来的,但它确代表着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非同一性的认识想说出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说出某物归在什么之下、作为什么的样本或表现,因而也就是说出其本身不是的东西。”(S.152,第146页)看来,这种非同一性思维首先意味着对其对象的一种全新的态度。正如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等人那里看到的那样,传统的理论方式实质上就是将概念的形式强加到非同一物之上,并试图认非同一物为其普遍性的例证。阿多诺认为,这一过程包含着对客体的粗暴统治和主宰。与此相反,否定辩证法的一个前提则是尊重客体的优先性。阿多诺认为,主体与客体始终处于一种相互中介的辩证关系之中,但这种中介关系内部又存在着某种不平等:“客体虽然只能通过主体来思考,但它总是某种与主体相对的不同于主体的东西;而主体在其本性上就先在地也是客体。我们不能想像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但可以想像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主体也是一种客体,这是主观性的一部分意义;但客体的意义却不包含其成为主体。”(S.184,第181页)如果意识到客体的优先性,那么我们对待客体的态度就会变得“温和”。
在主体与客体间非暴力的关系中,客体的内容无需逃逸,并以另一种统一的方式被保存下来。因此,否定的辩证法能够把握到客体具体的内容,而不是像传统理论哲学的概念体系那样,最终得到的只是一个虚空的框架。阿多诺说:“没有否定之否定,统一的要素也可以生存下来,但它用不着委身于那种作为至上原则的抽象,不是靠从概念到更一般的总括性概念的一步步递进,而是由于概念进入了一个星丛。这个星丛表明了客体的特殊的东西,这种特殊的东西对分类法的操作而言或者无关紧要,或者是个负担。”“星丛只是从外部来表达被概念在内部切掉的东西:即概念越想成为就越成为不了的‘更多’。概念聚集在其要认识的事物周围,潜在地影响着客体的内部,以思想的方式达到了那必然从思想中被切除的东西。”(S.164-165,第159—160页)星丛要表达事物的特殊的东西,表达“更多”,就必须着眼于事物的关联来认识事物,在这样的关联中,主体以及主体所使用的概念也仅仅是一个要素。这样,星丛就必定不是从某一总体性概念出发,或者说不是从一个单一的视角去认识客体,而是尝试将多个不同的视角保存下来。所以阿多诺说:“作为星丛,理论思维围着它想要打开的概念转,希望像开一个严加保护的保险箱的锁那样一下把它打开:不是靠一把钥匙或一个数字,而是靠一种数字组合。”(S.166,第161页)
事实上,阿多诺对星丛更多地是在态度上描述,至于这种新的理论方式应如何运作,阿多诺本人也言之甚少。但他告诉我们:“客体何以能被星丛开启?这更多地要从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得知,而非从对此不感兴趣的哲学中得知。”(S.166,第161页)这显然是从韦伯的社会学中得到了启示。他认为,韦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之前哲学家定义历史时所碰到的困难,因而拒绝了“种加属差”的模式,并要求最终的概念理解不能是探索的开端,而只可能是探索的终点。甚至在探索的终点,想要以某个单一的概念来揭示探索的对象往往也是不可能的。“在韦伯那里,星丛取代了系统的位置,人们喜欢指责它缺乏系统,所以他的思想就证明是在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S.168,第164页)在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中,星丛又以模仿的方式得到表达。模仿作为现代艺术的形式,它代表着审美主体与其客体间的一种非概念的亲和关系,因而它能够“收集那些长久以来被文明割除掉的东西”。⑤ 显然,模仿正是与传统理论中主体的建构相对,在这个意义上,“否定的辩证法”和“美学理论”是相互支持的。
可以看出,阿多诺对传统的哲学理论的超越仍未完成,但可以肯定,他在这个方向上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认定概念或理论仅仅是现实的一个要素,理论只能在事物自身的关联以及与主体的关联中认识事物。这里理论的有限性被意识到,理论的出发点从概念移向了对象,从抽象性移向了具体性。我们也就可以说,否定的辩证法是指向理论哲学之外的,从而也就是指向实践哲学的。
三、对生活世界话语的反思
我们不难看出,阿多诺哲学的基本结构是主体—客体的辩证法。由于客体始终具有的非同一性力量,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才被证明是虚假的;而要超越传统哲学的理论方式,则必须凭借概念自身的祛魅和觉醒,需要主体的第二次启蒙。所有这些都显得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话语显得很不合拍,因为一般认为所谓“主客二分”作为近代哲学的基本框架正是当下亟需超越甚至抛弃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否定的辩证法所释放出的巨大批判性力量,那么就有必要认真对待这种“不合拍”。问题的实质就是,超越传统的理论哲学,或者说走向实践哲学是否一定意味着抛弃主体—客体的模式,这种抛弃是否可能?抛弃和坚持又各自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发现,当今的生活世界话语中包含着两种不同倾向,一是强调哲学本身是主体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实践,因此,承认现实的生活世界乃是哲学这种实际活动的前提;另一种倾向则将生活世界作为一个特殊的范畴,它表示的领域先于任何对象性的活动,并为这种活动提供规范性标准。我们感觉到的那种“不合拍”显然是因为,阿多诺与前一种倾向较为接近,而当今生活世界话语的主流则是第二种倾向。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这两种倾向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正表明了阿多诺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分歧,我们可以从这一分歧中把握到问题的实质。哈贝马斯认为,否定的辩证法仍然在主体哲学的范围内活动。而只要这种哲学的主体—客体反映模式还被坚持着,那么暴力和控制就是不可避免的。否定的辩证法已经达到了这个范式的极限,它以虚幻的方式表达出的非暴力关系,其实只有在主体间的关系中才是现实的。因此,必须用“语言哲学的范式”也即主体间的沟通和交往来取代“意识哲学的范式”。在“意识哲学”的范式内,理性内在于主体并因主体而得到保证,而主体间的交往行为中的理性要得到保证,就必须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以作为交往行为的一个互补概念”。⑥ 这样,哈贝马斯就将哲学的基本结构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换为交往着的主体与其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背景的关系。
应该承认,哈贝马斯的确准确地指出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的难点,否定的辩证法的确已经达到其表达的极限,阿多诺留给我们的的确只是一个审美的乌托邦。但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范式的引入是否能够成功超越传统理论哲学的方式,超越所谓的“意识哲学范式”,抑或将收到相反的效果?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便可以肯定,他将阿多诺已经批判过的某些要素又重新引进了他的批判理论,而这些要素又使得他对传统哲学的超越成为问题。哈贝马斯说:“和一切非主题的知识一样,生活世界的背景也是潜在的,通过前反思才能表现出来。生活世界背景的第一个特征是一个绝对的明确性”,“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总体化力量”,“第三个特征是背景知识的整体论,它和绝对性以及总体化是联系在一起的”。⑦ 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是一个背景,“背景的在场让人觉得历历在目,又叫人感到不可捉摸”,“表面看起来是透明的,但实际上是无法穿透的”。对于理论而言,后天的知识和先天的知识、内在的知识和先验的知识在生活世界那里统一起来了。其实,哈贝马斯将理性的源泉从主体转到了主体间的共同背景之中,因此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乃是这个生活世界的概念。然而,这个生活世界对于理论本身而言乃是一个给定的前提,是一个匿名的领域。这里存在着的一个危险是,理论以及理论的主体对这一领域会失去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我们不难按照阿多诺的理论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提出质疑,如果考虑到这一概念的现象学渊源,那么这种质疑便更加可以理解。笔者以为,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虽然是直接从胡塞尔那里改造过来的,但其功能更加接近海德格尔的存在和世界,也即作为一个前理论、前反思的领域,主体、客体以及其间的理论性关系都必须在这一领域中找到其起源。而这正是阿多诺一贯反对的。阿多诺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可以说是所有哲学理论的宿命和原罪,是辩证法中的“非辩证”结构。阿多诺说:“对判断的每一个分析都导向主体和客体,这并没有建立一个超越这些要素的、自在的领域。它得出的是这些要素的星丛,而不是更高的,至少不是一个更一般的第三者。”(S.111,第102页)存在不具有超越性,因此也不可能绕开主体的反思,这是阿多诺对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的直接的批判。笔者以为,就生活世界对于理论主体的功能而言,也即就其前反思性而言,这一批判也可以用于哈贝马斯。因此,按照阿多诺的批判,生活世界可以说是理论哲学要素的另一种改头换面。如果说哈贝马斯敏锐地觉察到了星丛的困难,那么生活世界也不得不面对类似的困难,因为对生活世界我们只能略作勾勒,理论描述仍是不可能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有待追求的乌托邦,而后者则是作为一个先验性的设定。
那么,现实的生活实践在阿多诺那里处于什么位置呢?其实,现实生活仍可以视为阿多诺理论的前提,但是理论作为一种具体活动的前提,而非理论逻辑构造的前提。阿多尔诺认为,知识的批判就是社会的批判,美学的批判就是社会的批判,因此,在其哲学活动中,现实的世界始终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也是其理论活动的起点。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从现实的生活实践出发的。
注释:
①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9页。
②这种观点认为,哲学史上存在着两大哲学范式,即理论哲学范式和实践哲学范式。前者认为理论可以超越生活,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点,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后者则认为理论思维是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生活,并不能在生活实践之外找到立足点,因而理论理性要从属于实践理性。从马克思开始,哲学正经历着从近代理论哲学向现代实践哲学转型的过程。参见王南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③Theodor W.Adorno,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in Gesammelte Schriften,Bd.5,Suhrkamp Verlag,Frankfurt/M,1997,S.10.
④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2页。
⑤Theodor W.Adorno,Aesthetische Theorie,in Gesammelte Schriften,Bd.7,Suhrkamp Verlag,Frankfurt/M,1997,S.487.
⑥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第369页;以及《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⑦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第79—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