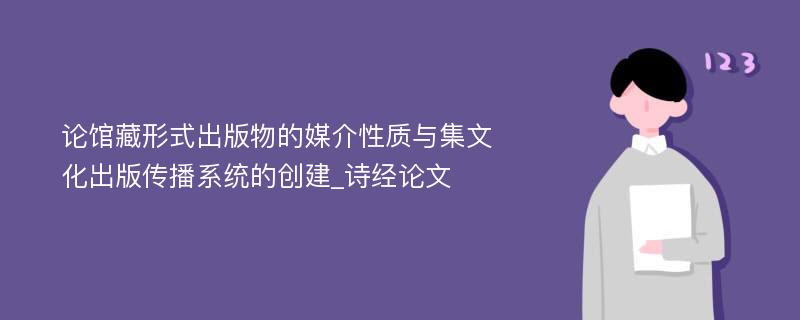
研究集形态出版物的媒介性质与集文化出版传播体系的创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物论文,媒介论文,形态论文,性质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G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0)05-0119-08
学术研究文集形态出版物作为一种既区别于专业图书又不同于期刊,或者说具有融图书和期刊两者某些功能元素于一体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传播媒介和载体,其类别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每年也都有一定数量的编辑出版。它在推进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刊载论文的数量之多、篇幅之大、信息量之广、作者研究之专以及探讨问题之集中,都是专业性和综合性期刊所无法比拟的。但当今由于科研评价体制机制的缺陷,以及各种人为的和行政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学术研究活动的行政化管理和对传播媒体不科学的定类分级(比如把出版社、期刊人为地划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奖励由所谓“高级别”媒体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造成在学术研究文集形态传播载体上发表的论文基本上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学术界对于图书出版种类的研究基本不涉及研究文集,而对于期刊的研究也把研究文集排除在外,以至于学界对学术研究文集形态传播媒介的研究较少。除了学术界外,在高等院校或者科研机构的一些科研奖励实施办法中,学术研究文集一般也被排除在外,既不能以论文形式单独申报,也不能作为著作类成果申报。另外,有的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也规定,论文集不得以主编、副主编名义参评。尤其在有关职称申报评审条件中,也同样明文规定论文发表的刊物不含增刊、特刊、专刊、论文集等形式的刊物,著作和教材不含论文集、习题集等,也同样把学术研究文集排斥在外。对于研究文集这样一种既不同于学术专著又与学术期刊有别的学术文化传播载体,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地位、价值和作用被有关部门或有关文件人为地以行政性的干预否定其应有的价值,造成学术界重视期刊和著作,轻视甚至否定和剔除学术研究文集的畸形评价状态,这种评价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迁延至对学术创作和学术自由的无形伤害。那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作为学术研究成果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或者说外在表现形式之一的学术研究文集,果真在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传播和创新方面没有什么价值吗?本文对此试从编辑出版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一番新的思考和探讨,期望学术研究文集形态的出版物在科学研究中回归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并纳入相关的科研评价体系之中。
一、关于研究集形态出版物的媒介性质、特征及其种类
在研究集这一概念中,“集”的内涵具有丰富的文化特色,含有收集、聚集、裒辑、汇集、汇编、集录等多种与编辑相关的意思,也指集刊、集子、文集、选集、全集、论文集等集形态的出版物载体;同时它也具有传媒性,并且是蕴涵着中国传统编辑思想与编辑智慧的一个词汇。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集一般是指把许多作者对于某一个研究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未曾发表过的),经过一定的审稿程序和编辑加工处理后出版的研究成果集;另一种是指把某一作者的或某一研究主题的有关研究文章(包括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按类汇集整理,经过审稿和编辑加工后出版传播。
在出版传播领域,这两类研究集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者说传播载体的形态,也一般多为图书的样式。从开本的大小、封面与版式的设计等方面来看,它和图书产品基本无差别,实际上也是图书产品的一个类别,比如版权页上也有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和出版单位、排版与印刷单位名称、版次、印次、印张、字数、中国标准书号、出版日期等,所以把研究集出版物看做图书产品的一个种类,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透过表象细而思之,由于研究集子所编辑的作品多数是独立成篇,并且每篇文章之间互不连贯,甚至有的研究集定期或不定期地编辑出版,而这一点又类似于期刊。特别在现实中,人们还是把研究集与传播系统的知识和思想理论研究的书籍相区别,所以严格讲它又不同于著作类和专著类的书籍。因此,从对单篇作品的汇集与编辑和传播的具体内容来看,研究集是一种既含有期刊的某些特征,而又以书籍作为载体的出版传播媒介,是具有融期刊与图书两种出版媒体某些功能元素于一体的一种特殊类别的媒介传播形态。也就是说,研究集这类出版传播载体虽然也具有杂志的某些特征,但又不能把研究集与杂志画等号,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性和差异性。若要进行准确的定位,笔者认为研究集则是介于图书和期刊之间的具有交叉性的大众出版传媒之一,它横跨于图书和期刊两种媒体的中间地带,并在两者之间扮演着纵横联通的传播纽带的作用。其交叉性特征主要表现在研究集是以图书的外在表现形态和期刊的编辑内容为基础,定期或不定期、连续或不连续地编辑出版,与图书、期刊具有某些共性的特征,其个性特征表现在融图书、期刊的某些功能于一体而呈现出跨媒体性的复合形态。由于长期以来,对研究集这类出版传媒在性质及特征上认识的模糊,研究的缺失和学术的偏见,以至于造成在此类研究集上刊发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也更无缘参评获奖。
由上分析可知,研究集形态出版物的媒介性质是指由出版单位把许多作者数量众多的单篇著作或者单张作品(包括未出版发表的和已经出版发表的两类),在一定编辑传播思想理论和文化优选理念的指导下,按照一定的研究主题和编辑主旨与编辑原则分类选择收集,使单篇散籍在归并的基础上汇编成册,编辑创构成具有较高品位的定期(比如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辑的《历史文献研究》,原称《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至2009年已连续出版28辑;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从1993年至2010年亦连续出版至第12辑;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学术》从2000年到2009年已出版至第25辑;再如陕西师大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也曾以书的形式连续出版,后改为期刊形式出版;另外也包括不同学术团体年会出版的论文集)或不定期(比如召开其他学术理论研讨会出版的文集以及基于某种研究需要选编、汇编出版的研究文集,等等)的一部或者多部、具有连续性或不连续性的文化传播载体,供研究群体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流传播。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研究集并非简单的汇编,一般要经过主编者的首次编选和编辑的再次审选,两次严格复选把关则赋予并提升了这些作品以新的内涵、新的学术生命力和历史意义与价值,因此它也是出版文化传播与出版文化创意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研究集形态出版传媒的编辑与创构,不仅发挥了科学研究成果传播的重要载体的作用,而且对于推进科学研究和科研交流也发挥了重要的媒体传播作用,因此研究集的编辑出版也是科学研究和出版传播业繁荣的标志之一。若从图书出版方面说,不同类型的研究集丰富了图书出版产品的种类;另一方面若从期刊传播方面看,研究集又弥补了杂志传播容量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者、编辑者、读者三方都达到了较高的满足度。所以,研究集形态出版传媒的创构,开辟了一个新的出版传播领域,使出版传媒业的面目也为之一新,在一定意义上丰富并创新了编辑出版文化。
研究集的种类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可谓丰富多彩。比如中国古代图书目录编辑分类和图书收藏所创造的经典分类——集部,虽然多以楚辞(以纪骚人怨刺)、别集(以纪辞赋杂论)、总集(以纪类分文章)三大类划分,但也有超过这三大类的。宋代编辑大家郑樵在编纂的《通志》总序中说:“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1]志二 他在汉唐诸儒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之一《艺文略》中,集部的类目就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总集、赋、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谐、奏议、论、策、书、文史、诗评,其所独创的一些编辑子目则总括了学术文化发展的新成就。元朝编辑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的集部,则划分为楚辞、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总集、文史。图书编辑分类在一定意义上记载并展现了出版物传播和学术文化发展繁荣的原始轨迹,具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文化传播功能。今天对于集形态出版物的编辑分类与古代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在世界文学的分类中,就含有作品集的类目,其作品集包括如下类别:诗歌集、戏剧文学集(包括电影、电视、广播戏剧集)、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集与杂著集、民间文学集、儿童文学集、民族文学集、宗教文学集。中国文学的作品集分类就更丰富了,除了上述世界文学的作品集分类外,还有全集、选集、文集、译文集、作品综合集以及中国古代的总集、别集等。[2]168-170此外,各个学会、研究会以及各学科不同领域有关专家学者定期或不定期就相关学术问题展开的讨论,其学术交流成果所选编出版的研究论文集,种类众多且博大精深,长期的学术成果积淀所形成的丰厚学术文化资源,不仅反映记录着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而且也是研究者创新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发展与创新程度,并也由此形成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文化繁荣的出版传播现象。
因此,我们在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学术创作的同时,对于传播研究者知识创新和学术成果的出版传播载体,也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宽容,既不能人为地把出版传播媒体(包括出版社和期刊)划分为三六九等,也更不能把某些出版传播载体——比如研究集排除在外,甚至机械地规定研究集形态媒体发表的学术成果无缘参评获奖和职称评定。殊不知,科研评价的不公正和功利主义的作祟不仅会挫伤研究者的积极性,而且也极易诱发和导致某些学术腐败的滋生。虽然报刊等强势媒体在近代产生后成为人们信息交流和研究成果发布的首选传媒,但研究集形态的传媒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其独具的文化厚重性为研究者所喜爱,尤其在当代媒体传播业日兴的信息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互联网、手机)相互交织、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地成为推动科学研究和信息交流的重要传播工具与载体,偏废任何一方都不利于科学研究和传媒业的科学、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研究集既是我国出版传播业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传媒形态,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延续至今仍被传承而发扬和光大,从而创构并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集文化传播链。
二、集形态编辑传播体裁的创构与集文化出版传播体系的生成
“集”是在文化传播与创新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编辑先贤创造的一种重要的编辑体裁和出版传播载体,它渗透并展现着中国编辑人的创造智慧,且在长期的编辑与出版传播历史过程中,延伸扩展并生成了以“集”为内涵的出版文化传播体系。在集文化出版传播体系的创构过程中,不仅催生了中国集学的诞生,使之与经、史、子三学并驾齐驱,而且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史、子、集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繁盛局面。
在我国悠久的编辑出版传播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创新发展的需要,编辑在文化传播与创新的过程中创构了各种类型并具有传世意义与价值的编辑体裁,内容博大精深、种类丰富多样的单本类和卷帙浩繁的多本类作品的编辑出版,使得中国文化以图书作为主要的传播载体和传播媒介而得以不断地传承和发扬光大、推陈出新。在各具特色的编辑体裁创构实践过程中,“集”这一形态的编辑体裁起源较早,且在历史上这种编辑传播方式代有续之,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集”为编辑主题(有的虽无“集”名但属于“集”类,如《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等)或以“集”命名的编辑作品(除了总集、别集的总名称外,如《荀况集》、《宋玉集》、《司马相如集》等),实际上创构形成了一种有序的集文化的创作、编辑与传播的有机链条,伴随着这类出版物的不断增多,也逐步形成了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一大编辑类目,以至于我国古代图书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收藏和传播。显而易见,“集”这种类别的出版物在历史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文化影响。
“集”形态的编辑体裁和编辑作品在历史上最早分为总集和别集两种传播类型,其中总集又划分为全集和选集两种编辑类型,总集是指编辑汇刻多人的作品所创构形成的一种诗文集,别集与总集相对,是指编辑个人作品而创构形成的一种诗文集。从历史的眼光看,集既是一种最早的编辑传播体裁,同时也是对文化发展与创新和社会进步影响深广的出版传播媒体或者说出版传播载体,在中国编辑出版传播历史上它的产生既早于图书(指著作类或专著类)媒体,也更早于期刊媒体,其传播的轨迹可谓源远流长,贯通了自古至今。这如同中国文学艺术的起源和传播发展的规律一样,是先有了诗歌体裁然后才产生了散文体裁,而编辑活动就是把这些体裁的研究成果编辑创构成册,把信息优化融为一体用新的文本形式向大众传播,因此与文学传播的逻辑规律相对应,作为诗歌的编辑体裁和传播载体首先也是以“集”的传播形态出现。从编辑出版传播学的角度简而言之,就是在“集”形态的编辑出版传播思想理论指导下,把许多作者分散的作品或者著作收集聚集在一起,然后分类目审选并编辑创构成新的出版物,意味着是众多人或者个人作品的汇编或选编,如《诗经》就被誉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先秦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四言诗高度发展的时代,作为记录和编辑传播这一时期诗歌创作辉煌成就的载体——《诗经》,是我国编辑出版传播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选编诗歌内容的编辑分类方面,按风、雅、颂三部分进行汇编,其编选的作品具有时代跨度大的特点,比如西周初年的诗歌作品大致包括“周颂”的全部和“国风”的大部分,西周末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包括“大雅”的一小部分与“小雅”、“国风”的大部分,东周的作品包括“鲁颂”和“商颂”。一般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编辑大家,《诗经》的编辑整理者是孔子。西汉史学家、编辑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3]卷47《孔子世家》《诗经》流传到春秋时已有淆乱,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卷47《孔子世家》经过孔子的编辑整理和作为教材对弟子进行教育,使《诗经》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传播。另外,也有认为孔子删诗之说不可信,“《诗经》包括年代久远,地域很广,且本身有完整的体系,不是经过长时期的收集、整理和编辑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大约是出于周王朝及其诸侯各国史官、乐师之手”。[4]第一节《关于诗经》这种看法虽然没有史料依据,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属于合理的推测。从出自周王朝及其诸侯各国史官、乐师之手或者是孔子编辑整理《诗经》的说法也可以看出,“集”是中国编辑人最早创造的一种编辑传播体裁与编辑传播方法,也可以看做是运用较早的一种出版传播媒体,这一出版传媒的创构使单篇散籍在重构的基础上得以保存流传,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以集的形态编辑创构的《诗经》其名初称为《诗》,至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设立五经博士后,改称为《诗经》并与《周易》、《尚书》、《仪礼》和《春秋》被尊称为儒家经典。《诗经》的成书经过了一个搜集、整理、修订的编辑过程,其所反映的内容大致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中国北方的社会现实生活,时间长达500多年。这些诗篇作为集体的创作成果,起初是以单篇的形式传播,之后被编辑整理成为选集类的总集,因此《诗经》不是某个人的作品集,而是集体创作智慧的结晶。尽管是多人的作品集但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且在后人的不断研究中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出版了众多的研究著作,以至于生成了以《诗经》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和出版传播有机结合的文化链条,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诗经》学。
继《诗经》之后,另一个被以“集”的传播形态编辑整理的新诗体,是反映中国南方楚国地域文化的《楚辞》。《楚辞》作品集的编辑,创构了总集编辑个人创作成果的新纪元,在中国书目文献编辑出版史上,直接以编辑命名的书名作为图书目录分类的类目,除了经部(如易、诗、书、礼、春秋等)外,在子部、吏部都没有,而在集部则唯有“楚辞”,以至于“楚辞”遂成为诗歌总集的一大编辑类目,其编辑创新意义可谓影响深远。于是,由《诗经》编选所开创的编辑集体创作成果集,《楚辞》开创的编辑个人作品创作成果集,两者都成为中国总集编辑出版传播史上辉煌的编辑篇章。
西汉成帝时期,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图书编辑整理活动开始,通过搜求天下遗书,不同版本的书籍堆积如同丘山一样众多,有的年代难辨,有的散佚、错讹甚至真伪杂糅。据史书记载:“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5]卷32《经籍-经》编辑家刘向在整理古文献过程中,把楚国诗人屈原、宋玉所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代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所创作的拟骚诗汇编成16卷的集子,并以《楚辞》命名所编辑的作品集。关于《楚辞》名称的由来,司马迁的《史记》曾有记载,“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3]卷122《张汤传》这是最早的有关《楚辞》名称的历史记载。另据《汉书》朱买臣传所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说明《楚辞》一名在汉武帝时代或之前已经有之。于是,刘向在编辑整理这类作品中也就优选了“楚辞”一名来作为所编辑集子的名称。对此,宋代黄伯思在《新校楚辞序》中概括说:“楚辞虽肇于楚,而其目盖始于汉世……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6]卷92到了东汉安帝元初年间,校书郎王逸给《楚辞》作注并补入自写的《九思》和班固的二叙,又定名为17卷本的《楚辞章句》,因刘向编辑的16卷本《楚辞》已亡佚,于是《楚辞章句》遂成为最早的注本和今本《楚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所编辑整理的《诗》其地位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一般的文史典籍而上升到儒家经典的高度,被尊为经书而称之为《诗经》,按古代传统图书收藏编辑整理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分类法,原先隶属于集类的《诗经》也就上升而位列于经部。于是,在集部类目中《楚辞》就成为了集部之祖而列在首位,到清代编辑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时,《楚辞》这一古老的中国文学经典一直成为集部类的第一部书目,在四库编辑提要中强调指出:“集部之目,《楚辞》最古”,[7]卷148《集部总叙》其编辑价值和历史地位于此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与后人对于《诗经》的研究一样,对于《楚辞》的研究也同样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出版了不少研究著作,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学术文化传播链和专门的学问——《楚辞》学。
由上可知,《诗经》和《楚辞》都是以“集”形态的编辑体裁和编辑方法汇编而成的,并以“集”形态的传播媒介为载体使得古代文学创作的成果——风(《诗经》)、骚(《楚辞》)得以保存和广泛传播,也同样因编辑创构而不致散佚从而成为了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丰碑。尤其是后人在研究过程中也并没有因为它们是作品集的汇编而贬斥之,相反则把它们视为古老的文史典籍而予以高度的重视。这与今人重期刊、专著而轻(甚至贱)集子,对研究集形态出版载体价值的评价上一味否定,不承认其所刊发的文章简直判若天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老的集形态出版物和独具特色的集文化的一种偏见。科研成果发表的传播媒体,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图书、期刊形态出版物外,集形态的出版载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类别,并且集形态的出版物浸润着民族文化的基因,是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传播媒介,应当承传和光大之。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7]卷148《集部总叙》可见,集形态的研究成果和编辑传播轨迹是按照一定的文化传播逻辑循序而进的。继《诗经》之后散文创作崛起,后又有《楚辞》编辑传播,中国古代文学到了魏、晋、齐、梁、陈时期又得到长足的大发展,作家的人数和文学作品的数量之众多都远远超过了前代,于是数量众多的“楚辞”类、“别集”类和“总集”类的编辑作品相继诞生,出版传播业也处于一个相对繁荣的丰收时期。据唐代编辑《隋书》经籍志所统计,集部有“楚辞”10部、29卷,通计亡书11部、40卷;别集437部、4381卷,加上亡佚的共886部、8126卷;总集107部、2213卷,通计亡书合249部、5224卷。“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5]卷35《经籍志四》“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5]卷35《经籍志四》而“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的发展盛况按《隋书》所载,当时编辑的集形态的书已达554部,6622卷,若加上亡书,合1146部,13390卷。“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是故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编辑家们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研究和作者创作的需要,“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7]总集类一在对文学作品品鉴别裁、芟繁剪芜的过程中,编辑创构了大量的文学总集(包括全集类、选集类),但多已亡佚,而所能见到最早、影响最大的通代“选集”类总集便是《文选》。而同样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传播现象,则是后人对于《文选》的研究也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亦称选学)。
集形态编辑体裁的创构和集形态作品的创作,以及与之相关编辑出版传播活动的开展,已经初步形成了集形态作品的编辑与编选和传播的出版传播链,尤其是在集文化根基上相继诞生的《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和诗文评、词曲等,使得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厚、更加博大,同时这也是集文化出版传播体系生成的重要标志。伴随着集形态作品创作和编辑出版物数量的日渐增多,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中国古代的藏书机构或藏书家也创造性地把集作为图书编辑分类的一个大的类目,官方和私人在编制的收藏书籍目录中,大都设立了集部来著录相关的图书。于是,集文化出版传播体系就生成了这样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循环往复特征的传播轨迹:作者对集作品的创作→编辑对作品文本的编辑或编选加工处理→复制出版传播→读者购买阅读→藏书机构或私人收藏和编目→作者对集文本的再创作。每一次的循环往复过程都使集文化形态得到更新和创新,从而创造了中国编辑出版传播历史上集形态出版物日渐繁盛的文化景象,也使得集文化出版传播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走向成熟。
从目录学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古代官修和私编的目录学图书都多设有集部,分类汇编有关楚辞、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总集、文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在图书收藏的编辑分类体系中,集部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相互承袭、创新与演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集部的创生与集文化出版传播体系的发展两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传播关系。
西汉时期编辑家刘向刘歆父子撰写的编辑著作《别录》和《七略》,在图书编辑整理中“剖析条流,各有其部”,[5]卷33《经籍志二》创设六部——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分类编辑所整理的相关图书,这时虽有类似集部的诗赋类目,但还没有出现集部之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编辑出版的这类书籍也日益增多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于是作为反映其研究和出版成果的国家藏书的图书目录也应时诞生。比如魏国的郑默“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8]卷44在魏明帝青龙三年(235),编辑了14卷的《魏中经簿》著录图书,西晋武帝时期秘书监荀勖在此基础上于咸宁五年(279)和“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8]卷39《荀勖传》并首次采用甲、乙、丙、丁(按著录图书次序类似为:经、子、史、集)四部分类法著录当时的图书。东晋穆帝时期李充就任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李)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8]卷92《李充传》编制的《晋元帝四部目录》,共著录图书达3014卷。李充首次调整了荀勖编制目录中乙和丙所著录的书,虽然也是按甲乙丙丁四部,但顺序却调整为类似经史子集的顺序了,因此秘阁以为永制。南朝时期的全国图书总目编辑,宋朝秘书丞王俭“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9]卷23《王俭传》所编的《七志》(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艺术志、图谱志)仿照刘歆的《七略》,其中的文翰志则相当于集部。到梁朝时,阮孝绪又在《七略》和《七志》的基础上于普通四年(523)编制了《七录》,分为内篇(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佛法录、仙道录),于是,集部之名开始出现。阮孝绪在自序中阐发了他改王俭《七志》类目中“文翰”为“文集”的原委,“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10]卷3值得注意的是这句“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颇有学术眼光和见地,其创新意义不可低估,因为当时对文词作品的编辑“总谓之‘集’”,所以变“翰”为“集”不仅彰显了这类出版物的编辑特色,而且一字之改遂成定论,后世相互沿袭之。由此可见,集部之名的创生从汉代到南北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由刘歆《七略》的“诗赋”→王俭《七志》的“文翰”→阮孝绪《七录》“文集录”。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文人创作了大量的有关楚辞、诗赋、杂文等作品,而编辑出版传播业也主动地与文人的文词创作活动形成互动态势,共振并形成了文词创作和编辑出版相互依托的合力,大量相关书籍的编辑与出版,为集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传播载体,于是在图书收藏方面,原来的类目“诗赋”、“文翰”都不能涵盖或恰当地揭示这类出版物的性质。比如《七略》编录的图书包括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杂赋、歌诗五种,《七志》中“文翰志”主要纪录诗赋,阮孝绪根据当时文词创作和出版的情况,不仅改“文翰志”之名为“文集录”,而且还去掉了《七略》的诗赋总名称,创建而析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类。所以,后人评价《七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5]卷32《经籍志》其分类体例“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详尽、最杰出的一种,为后来确立四部之制,奠定了基础,在我国目录学的类例发展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1]55图书收藏类目的新创和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文集形态出版物创作和传播交流的数量已经较多,而及时创新为“文集”类目,既能标示出这类出版物的含义,又便于读者阅读、研究以及收藏和传播。
唐朝官方编辑《隋书》时,其《经籍志》的编修在吸取汉魏六朝图书目录成就的基础上,就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作为图书收藏的分类法,“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5]卷32《经籍一》其中的集部删除“杂文”子目而保留了楚辞、别集、总集,后代官方和私人编辑的书目都沿袭四部分类法(仅个别子目有所变动),集部也都设有楚辞、别集、总集的子目,比如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也是按四部分类,其中集部分为五大类,分别是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可见,集文化形态出版传播体系,是由作者、编者、藏者(包括政府馆藏和私人藏书与藏书家,在出版传播中扮演着“中继站”的角色,过去学界对于编辑出版学的研究仅仅注意到了作者、编者、读者,而忽略了对藏者群体在出版传播中作用的研究,从历史与现实的眼光来看,学术研究链条不够完善,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缺失)、读者四方共同维系和创造,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出版传播体系。从相关作品文本的创作和编辑加工到出版传播,以及对出版物的收藏和著录为传播载体和传播渠道,集文化出版传播呈现出体系化、完备化发展的状态,从而也使得集文化的内涵呈现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不断创新发展,以及日臻完善和更加丰富的特点。其传播过程中由点到面和点与面的结合及其互动性发展,使得集文化传播的机制也逐步体系化,可以说这是我国文化发展史、编辑出版传播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创新和出版传媒创新,也是学术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集形态作品的创作和编辑与出版物的传播所创构形成的传播机制,使“集”亦生成了一种文化传播符号,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研究集形态出版物的学术文化价值与学术史意义
作者文本的创作和作品集形态传媒的创构以及相关出版物的编辑出版与传播,在长期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积淀并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集文化出版传播体系,这一体系的创构不仅使集形态的出版物连续编辑出版而形成集文化的传播链,而且也显示并赋予了这类出版物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与学术文化史意义。
第一,作品集的编辑出版,使众多作者创作的单篇散籍式的论文免于散佚并得到最佳的保存和传播,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传承意义。
学术研究和研究过程中生成的学术文化作为一种优质的文化资源,它的传承与传播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其传播渠道除了培养弟子接续研究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传播渠道就是把相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单篇散籍汇编成册形成研究集,并以此为传播媒介和载体在较大的研究范围内与读者进行有效的互动式传播和交流,从而推动学术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创新发展。尤其在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抄本传播时代,作者的研究成果多以单篇的形式传播,由于作品复制手段停留在相互辗转手抄的发展水平,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不仅大量的文论作品亡佚或者散失,甚至造成“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5]卷32《经籍志序》因此,把单篇作品编辑整理使之归并,创构成为研究集的传播形态,使之免于散失则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正是由于学术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需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了编辑作品集的文化高潮,虽然这一时期编辑出版的不少集子多已亡佚,但其编辑传播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比如《昭明文选》就是这一时期创构的编辑名作,这些被编选的作品和《昭明文选》本身都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和史料。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手稿文本,在整理和编辑出版后也仍多以研究集的形态传播。
第二,研究集展示了学科建设过程中群体或者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创作与研究的探索足迹,在学科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因而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研究集编选的论文大多是围绕着某个学术领域中的一些并未定论的问题展开学术思维和研究,其研究方法既有运用本学科的理论进行学术思考,也有运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比较学科等相关理论进行相互渗透、相互嫁接式的研究,从而催生了学术创新的生长点和增长点,具有一定的学术真知灼见。另外,研究集多以单篇文章组构而成,虽然表面看起来所收集的文章多是互不相连的,但由于是围绕某个学术主题展开的学术思考,因此每篇文章之间其内在的学术关系和学术理路则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连接性,可谓“形散而神不散”,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某一历史时期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填补了研究的空缺。这也是学术史研究值得关注和总结的领域,具有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对研究集形态出版物学术评价的失当和排斥,以至于造成有的在研究集出版物刊发的文章,再次在相关的期刊发表,这就人为地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甚至有的研究集出版物的名称淡化“集”字或者不用“集”字,从名称上看很像一部学术著作,但从目录和内容来看仍是单篇文章的汇集或选编,似应称为“研究文集”最妥当。而要矫正这种鱼目混珠、名不副实、不伦不类的出版现象,就必须正确把握和认识研究集形态出版物的价值,使研究集刊发的成果与学术著作或者和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享受同等的评价和科研奖励。
第三,从学术研究传播的逻辑规律来看,先立论然后才能逐步形成学说,而研究集所编辑的论文则强调以立论(论点)为主,著作以立说(学说)则是指在论点形成的基础上条理化、体系化、理论化后才能生成学说,因此研究集对论点和学说的形成与生成具有辩证的促进与媒介传播作用。
研究集形态的出版物汇编了研究者不同时期创作的单篇学术作品,由于学术论文撰写的字数一般在万字左右,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也不必要面面俱到地进行论述,而只能在某一点上有所创新,因此作者对论文的创作一般都要穷其精力进行精雕细刻,并力求提出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大多是佳作。众所周知,研究集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功力和研究水平。而著作一般对字数不限制,由于篇幅过大和内容体系庞大,面面俱到的阐述造成其内容也有陈陈相因之处,甚至作者难于驾驭时就用材料进行填充,以至于造成著作常含有较多的水分,其创新程度远不如单篇论文。当然,论文创作和著作撰写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前者是学术基础,后者是学术正果,从事学术研究的总是要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或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来优化和优选出能够反映自己学术水平的代表作,以确立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一般来说是先有论文后有著作,著作是在论文的基础上扩展生成的,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单篇论文包括集子的作品相对于著作的内容庞杂、水分过大而言,最富创新性,其学术价值也高。当然,“书籍所装的东西无非是有系统的思想,有系统的知识,因为这些思想和知识,需要传播,其他的形式都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出版,用书刊的形式进行传播”,[12]1学术著作由于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理论体系支撑,其厚重的学术性和参考价值也是论文所不可比拟的,因此两者之间是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各有千秋,可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总而言之,集是中国编辑先贤创构的一种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编辑体裁,集形态创作成果的编辑创构和出版传播,使得研究集也成了文化创新的媒介与大众传播的载体,这种具有创造性的编辑发明不仅使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集文化传播体系,而且也生成了一种集文化出版传播体系,集文化的创生与集文化出版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优势合力,也不断地催生和推动着中国集文化体系的发展创新和繁荣昌盛。
收稿日期:2010-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