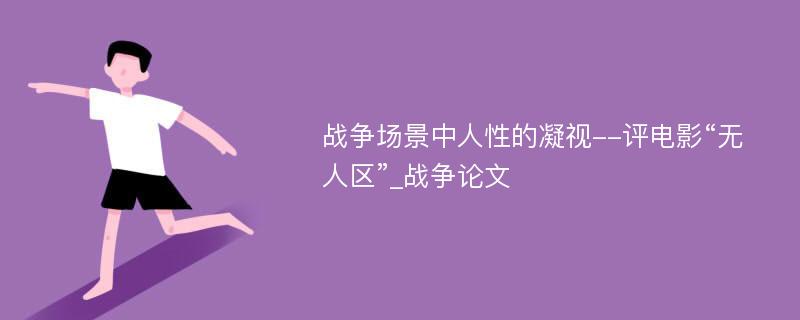
战争镜头中的人性凝视——评电影《无人地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文,镜头论文,战争论文,地带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人地带——这是一片生命难以留存的地方,是现代文明的任何权力无力管辖的地方,也是人性的任何智慧和道德无力涉足的地方。战争是为着某些人的目的而发动的,但战争一旦发动,自有它自己的运转逻辑,人的生命和文明在它面前只能是永远的输家。在波斯尼亚族导演塔诺维奇的电影《无人地带》中,夹在临时停火的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两族阵地中间的一段堑壕和木屋空地无疑指涉了以上意思。电影运用视听语言把这一深刻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影像在表意方面的能力,让人不得不感慨:人类的文化真的进入了视觉文化的时代!
导演塔诺维奇亲历波黑战争,“他自称用摄像机记录下自己深爱的祖国遭受破坏的全过程”[1],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影片更像是一部纪录片而不是故事片。导演认为自己祖国当时的状况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的复杂矛盾。所以他对反战主题的处理与以前出现过的同类作品明显不同。影片的镜头运用是冷峻而客观的,影片中没有血肉横飞、炮火连天、撕心裂肺、震耳欲聋的煽情镜头,全片的战争场面只有开头的时候前去接应部队的波斯尼亚小分队在黎明雾散以后遭到塞尔维亚人歼击的那一场,而后主要的戏剧冲突都是在夹在两军阵垒间的那段堑壕和木屋内外这片小小空间中展开。一系列的戏剧性事件在这片让两军暂时熄火的回旋空地上发生,越来越多的人牵涉进来,却都像那三个士兵一样不由自主陷入不可解脱的困境。事件被由小到大地铺排,冲突像是被讲述者精心组织起来的,又像是来自它本身,从两个士兵的命运逐渐发展到影响战争的整套现代机制,一系列的事件和冲突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来,包括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它的长官、士兵、排雷专家,包括无处不在的电视媒体和它的从业人员。在战争这块是非之地上互相作用,一个个直观的镜头让人看见的是埋藏在人心里的永远的战争隐患——仇恨、疑虑、恐惧、隔膜、自私、党同伐异。直观、精确的影像虽然无法直接表述抽象的概念,但却让观众在接受这些视听信息的同时,在心里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上述一系列内涵。在这个过程中,信息通过流转的方式,从影片的视听语言出发,经由观众最终生成了。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波黑战争的最后阶段,《代顿协议》已经生效,成千上万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已经进驻前南地区。一段隔开对阵双方的堑壕中,缺乏战斗经验的塞族士兵尼诺和世故油滑的波斯尼亚穆族士兵西基,在这片因战争而造成的“无人地带”中互将对方扣为人质,忍受着煎熬,等待解脱一刻的到来。影片上半段展开波斯尼亚士兵西基(Ciki,波斯尼亚演员布兰科·德加里克Branko Djuric饰)和塞尔维亚士兵尼诺(Nino,克罗地亚演员雷尼-彼得拉亚奇Rene Bitorajac饰)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有两场戏很有意思地表征了战争的一种逻辑:西基和尼诺在棚屋里分坐在门的两边,他们的身后远处是暂时熄火显得平静的战场。两人在骂骂咧咧中对攻是对方的民族掀起战争,毁坏了这个美丽的国家,谁也说不服谁,突然西基将手里的枪指着尼诺逼问他“究竟是谁挑起的战争”,就像他前面用抢逼着尼诺投降、尼诺只能从命一样,尼诺在枪口下只有闭嘴缄默。后来在救助另一个波族士兵(即先前被以为是死人而被塞族士兵在身下埋了重力式引线不可撤销炸弹的塞拉Cera)的时候,趁西基不防备,尼诺抢回枪,并用枪指着西基重新逼问他“是谁挑起的战争”。深信谁拿着枪谁就有力量的西基知道此时只有同意是自己一族发动了战争。
在战争的逻辑中,道德的标准已经难以辩说,理性也成了无言的矮子,武力成为决定的关键。谁有枪谁就有说话权,谁就能定是非曲直书写历史,两个士兵之间是这样,作战的各方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道德反而成了武力驱使下的懦弱小丑。至于武力是否在理性的一方或是在正义的一方并不见得能改变战争的血色。战争一旦运转起来,会把所有涉入进来的人和各因素都转化成它可利用的工具,人道的正义、热情、善良在它的面前都显得无能,同样人道的正义、善良、热情似乎也只能给人和人之间带来片刻的共存、理解、协作和安宁,相反却稍有不慎那些埋藏在人心里面的战争隐患就会像这颗不可撤销的炸弹一样爆炸。
正像著名的前南导演库斯图里卡一样,塔诺维奇在本片的叙事风格上也采用了黑色幽默。只是不同前者的热烈浪漫,塔导在镜头的处理上显得更为冷峻克制,大量使用长镜头以保持时空的相对完整,体现出事件的真实性。景别大多维持在一个旁观者的距离,体现出一种客观的观察视点。光线的运用采用了自然主义手法,镜头表现的是自然光线条件下正常的光效。这一切表现手段,使故事在喜剧发展的表面推进着一层深沉的悲剧,其对荒谬性的批判不仅指向发动战争的双方,而是指向所有被战争裹胁进来的人。他这里没有所谓的正义方和非正义方,所有让战争机器得以运转、所有无法让战争停止运转的人都难逃杀戮生命和践踏人道的谴责。
导演对风格的选择也许是继承了巴尔干地区的文学和电影传统,但我更相信是那个地区长期以来由民族、宗教、政治等各复杂矛盾纠结起来的新仇旧爱早已经模糊了道德和理性的边界,不能不让人放弃经典电影那种善恶两分的战争叙事模式,也不像现代电影那样还有一个对美或者爱、或者理性等绝对力量的呼唤。他在嘲讽和质疑中用镜头显露出他对现实的批判。
影片开场提供了一个夜半深雾的环境,大雾既是全片第一个关于困境主题的比喻,又是全片的核心意象,那个由一段战壕、一片空地和一个棚屋组成的“无人地带”的第一次亮相。
影片没有采取人工的照明辅助,保持了自然的光效,大雾之中一切都很模糊,暧昧不明。同样是雾,白天的雾可能引向浪漫柔和,让人联想爱和美,而夜里的雾则是湿的和冷的,让人感到不安和危险。在这里影像的精确性把夜雾的特点表现得极为准确和充分,一种湿冷、不安和危险在观看过程中迎面扑来。前往本部的一队波斯尼亚穆族士兵就在这样的深夜大雾中迷了路。是误打误撞早点赶到本部,还是为了避免误撞险途就地休息等天亮雾散去再说呢?领路人很坚决地选择了后者。大家坐下后一位士兵问他的战友是否知道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差异。对方没有答出来,他解释说:“一个悲观主义者认为事情已发展到了最坏的地步,而一个乐观主义者则认为事情还能够向更坏的方向发展下去。”周围的伙计们都笑了。笑谈似乎是针对这时的迷路,又像是闲谈。看到此处我和影片中的士兵一样并不知道他们的处境是要往那么一条坏的路子上去。而看完全片再回过头来琢磨这段话,才发现它似乎是对后面命运的一种暗示,又像是在隐隐传达导演对祖国前途、对人类的类似困境表示悲观的观点。这几个段落极有力地证明影像表意具有非独立的特点,一段影像其最终的意义必须在结合其他影像的基础上才能被确定下来。
影片里,大雾中的理性并没有带士兵们躲过危险,大雾中他们不知道他们停留的地方正在塞族的射程之内,他们更不知道他们在一片“无人地带”。大雾散去,无人地带迎来的不是朗朗乾坤,是西基没有料到,塞拉没有料到,谁都料想不到的越来越不可遏制的糟糕。
之后的段落里,清晨来临,第一个镜头保持了相对长的固定镜头拍摄,清朗的天空、树冠茂盛的大树、葱绿的草地,士兵们倒在树下横七竖八地睡觉,一片宁静。然后有人缓缓地醒来,大家纷纷起来,辨别方向,镜头继续保持安静和相对慢的节奏。突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尚未反应已有人仆倒在地,转瞬间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活人已变成死尸。只有西基带伤踉跄躲进堑壕边的棚屋。在这个段落里,视听节奏从低点突然拉升,给观众形成了强烈的震惊。第一个长镜头所营造的舒缓节奏和后面一组短促、音响强烈、繁杂的镜头所形成的紧张、激烈的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个段落里,镜头的形式手段和内容完全一致,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保持了高度的和谐。
再接着,日头渐高,塞族这边在停火后不清楚敌人是否全部被歼击,新兵尼诺和一个老兵被派过来侦查情况。老兵世故且对战争的残酷早已安步当车,他以为被震昏的塞拉已是死人,在塞拉身下埋了炸药。他得意地说只要敌军过来清理尸体,当尸体被抬起的刹那间炸弹就会引爆,这是谁也不会防备的一记杀敌决胜招。只是他这个战场老手也万万没有防备旁边的棚屋里还躲了个没死的穆族士兵西基,结果被偷了枪的西基冲出来一把打死。尼诺被西基扣留,被强迫脱了衣服向塞族这边呼喊,以使塞方停火。穆塞双方在对这片无人地带都感到不明的情况下停了火,把营救两名士兵的事情上交给联合国维和部队。
本性善良、初受战火考验的尼诺在与西基的对峙中小心地平衡着警惕和恐惧,并在可乘之机夺过西基的武力优势让自己掌握发言权。一把枪在两个男人手中轮换掌握,互相控制着对方,很像香港黑帮片中经常出现的敌对几方互相用枪指着的那种典型情境的改写,互指的双方谁也不能挣脱谁,谁也不能压服谁。面对一个共同的特殊困境,其实还需要相互依赖,但提防和不信任却阻隔着合作。在一次次的误解、欺骗中,对峙在反复的轮换的控制中升级,终于压过两个人心里残存的那一点点温情,破灭了友善共存的可能。在影片的前半段,两个人还能面对面抽着香烟谈着双方都约会过的一个姑娘,感觉命运的红线正在将他们的心灵拉近。但先是西基没料到自己在查看地上苏醒过来的塞拉、放下戒备的时候被尼诺夺了枪并受胁迫。后塞拉以讨烟抽的骗局帮助战友西基夺回了枪。之后在维护小分队第一次到来却要受命放弃解救,尼诺情急下打算跟小分队回去讨救兵,却被西基认为是试图逃跑而被枪击腿部以后,尼诺之前对西基出于民族、出于阶级、出于教养、出于男人的自尊等等的隔阂完全就转化成了一股不泄不足以平愤的仇恨了。而后在维和部队,在国际媒体都在场的情况下,尼诺瞅机会向西基挥去了复仇的一刀。西基也在同样有众人监管的情况下蓄谋着找到了向他报复的机会。两个男人之间争端的生成和发展像是两族矛盾的一个缩写版,一开始似乎还寻得出个是非曲直的理由,后来就只是非理性冲动下的血腥。
塞拉身下的炸弹是形成整个困境危机的核心戏剧元素,它加剧了困境的危机感,增加了西基和尼诺之间矛盾的压力。塞拉哪怕一点点透露生命需要的活动,比如翻翻身,比如小便喝水都有可能引爆炸弹让自己粉身碎骨。这样的极端情境设计不免让人想起一些世界极端组织安排的一次次人肉炸弹的攻击。导演身在那样一个杀戮和血腥冲突不断的地区,对人类族群之间极端非理性仇杀活动的感受想来颇深,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情境设计单纯只是艺术创作的灵感闪现。
塞拉身下的炸弹像是一个测试器,拷问着人类理性和良知在面对暴力荒谬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表现。西塞答应塞拉作为好兄弟一定不会扔下他不管,言下之意会陪他同生死,但他最后是在意欲射杀尼诺的时候死在维和部队阻止的枪口下。尼诺出于他的本心是不忍伤人而愿救人于生死之间的,但他最后所有的心思都被仇恨控制了。维和小分队的队长马祖德出于道义和对责任的理解违抗上级不涉入的命令,借助电视台记者珍妮胁迫上级,一直试图能救援这三个士兵,但他却没能阻止住西基和尼诺之间仇恨的升级和爆发。最后出于道义也好,出于维护联合国机构和官员的体面也好,出于新闻报道背后的商业利润也好,当所有的人汇聚在一起打算看一出精巧的人类技术达成的充满悬念的现场戏剧转播的时候,最高水平的拆弹专家却宣布这是一颗一旦上弦就没有办法拆除的炸弹,于是所有的事件变得像是一场闹剧。维和部队在维护和平、遏制地区间冲突上的作用在影片中很明显受到了质疑和嘲弄。而国际新闻媒体的形象在这里也非它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代表着正义,它可能是商业或权力的工具。战争是人性危机的集中爆发,是人类一切争斗的最高级别,在它的面前一切的手段都似乎无力,只显出人类更大的难以逾越的困境。于是,影片中所表现的个体事件最终成为了表现战争本质的象征符号。
全片现实主义的影像处理和黑色幽默的叙事态度相结合,使这个不可能的故事仿佛成为现实的纪录,折射出现世中那些我们引以为真实、正义、美好、善良的东西的虚幻和不可靠,折射出理性之无力超越的荒诞,直观、具体的影像表现抽象意义的能力在影片中被发挥到极致,导演对现世的反思和人性的疑虑通过镜头凝聚为一个困境的意象。和文字符号的被动接受不同,观众对于影片所要表达的内涵是一种自我主动接受,尤其是影片客观的镜头运用使观众似乎替代镜头成为现场的观察者。当影片结束,困境的意象同时也自然地在观众心中凝聚成形,导演对战争的看法变成了观众自我的认知。影片反思战争的目的至此完满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