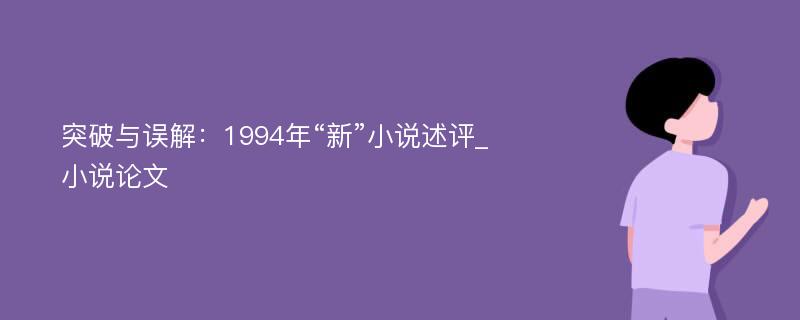
突围与误区——94年“新”字号诸家小说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误区论文,字号论文,诸家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之后,当文学史家回眸94文坛时不能不记上一笔旗幡林立的“新”字号诸家小说。不,不用十年,即使今天,不论你称赞或是反对,对这“新”字层出迭涌,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你怎能置之不理呢?新体验小说,新状态文学,新市民小说,新都市文学,新闻小说,加之前几年已有的新写实、新文化、新历史、新感觉、新乡土及新言情新武侠等各类小说,可谓之林林总总洋洋大观矣。颂赞者对其评价甚高,说它贴近时代生活,显示文学对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应性,文学表现了“少见的活跃”,在当代文学应“占有一席之地”;批评者则认为它们是“迎合的悲哀”,是“贴标签”,是“商业行为”,是“媚俗”,甚至斥曰:“众刊物林立派别的结果,是只能构成对文学的束缚、扼杀、戕害的”,一言以蔽之,这一切是“文坛的‘新败象’。”然而我则认为,“新”字号小说今春伊始,时至今日方刚十几个月,便下断言结语似嫌过早,它还在变异中。我们不妨将它放在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期的历史背景下,就现象论现象,对各家文学主线与创作实态多作一点具体分析,探其得失觅寻轨迹。
当考察“新”字频繁现象的时候,我以为不能不审视文坛另一频率很高的字眼,这就是“后”,后新时期,后现代,后解构,后文化,后殖民,后乌托邦,后人道等“后”字的排山倒海。你对“新”与“后”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挑剔与斥责,它们自身也确有多种缺陷,但我觉得,“后”与“新”二者出现不是各自孤立而是彼此相关的,不是偶然而是涵有特定时代风韵的。因为,“后”的理论多少看到了新时期文学历史前与后色彩的蜕变,对历史提出了某种阐释与思路;“新”字小说表面上绝对不谈“后”,但它们也在反思新时期文学历史,尤其思考着转型期的文学起点在哪里,跨世纪文学未来究竟应是什么样的面目。就此而言,我认为,“新”与“后”二字乃是考察今日文坛的一个了望孔,“后”是企求对昨天文学作出某种理论阐释,是历史的告别;“新”字则是诸家文学新主张,它是对于今与明日文学的一种呼唤。
“新”字诸家小说即然从历史反思中寻找自我今日之文化方位,自然痛感到文学所面临的重重包围。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刷,金钱这魔鬼对文学崇高精神的无情亵渎,色情与打斗之庸俗品类脏水泼撒得文学面目全非。“新”字小说尽管文学主张各有不同,价值取向迥异,但它们也有同一追求,都在鼎力的突围。这种闯出包围圈的努力,主要表现力于求提升各自的文化与文学的品位,恢复那曾经疏离的文学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纽带。“深入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写“当下的状态”,突现“新闻价值”,等等,不论话语何等有别,但指归是明显的,真诚的人生态度,重在参与,强化文学关注生活热点和百姓的生存状态,在“新”字变异中寻找文学与刊物的新的生存方式,因此涌现了《预约死亡》《天使悲歌》《家道》《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牙买加灯火》《呆坐街头》《在小酒馆里》等一批颇有份量的新作。
然而,它们打出新的文学旗号亮出了引人注目作品的同时,也暴露了理论与创作的匆促,一面在突围一面又陷入某种误区。第一,94“新”字号小说突围的出发点是追求新型的文体与刊物的独树一帜,但作品往往迷失文体的特定主脑而步入了无特色一般化的误区。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各种文学旗号层见不穷,但它们有名有实各有各的追求。譬如,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文学主张主要在于创作精神与艺术方法之别,前者主张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而后者则张扬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又如,菏花淀派与山药蛋派为什么是一个不衰败不消亡的历史话题,其因就在于各自具有与其它流派相别的独异风格与气魄。“新”字诸家小说不是创作原则不是风格流派之分,总体上它们都属于小说家族,同是一母所生。倘若标新立异,即在小说母体之上确立各自的文体特点,就是说,在小说这一点上它们是一家,各树一帜的“帜”在于新××体的小说,如新状态应该区别于新体验的小说文体。所以说,“新”字诸家小说必须明确自家文体的主脑是什么,假如它与别家小说毫无二致,也就流于虚张声势而自行消亡了。就以新闻小说而言,它当然是新闻与小说相嫁接的一种文体,但二者并非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其主脑更不是小说,倘若如此它即无新闻性的价值,又与别家小说相混同。只有确立新闻性是这一文体的主脑及统帅的地位,刊物的立足之地,作家的文体追求,读者的欣赏期待,这才有了一个明晰而认同的座标。《春风》今年刊发的新闻小说,单就技艺而言,难分高下,但从新闻属性论评,各篇价值一目了然。《一部悲剧的制作》开头写道:“儿子把亲生母亲告了,罪名是母亲十年前杀害了父亲。”可是小说丢下了这一新闻事件,却去写扮演母亲的演员如何伤心落泪。请问,读者关注的,感兴趣的究竟是那新闻案件及其包容的社会与人性的内涵,还是一个演员的表演细节?这是不言自明的。《天使悲歌》的审美性不一定高于《制作》,然而它特别注重新闻小说主脑特性的实现。它的主要价值还不是沈阳一家妇婴医院由病毒感染而致死数十新生婴儿(报刊已有报导),而是它第一次揭示了地方极力封锁新闻与北京几家新闻单位冲破层层的封锁,以及它描绘了几个敢于追求公理与正义的那种令人钦敬的记者形象。
突现新闻价值是新闻小说的一个层次。它还有另一个重要层次,这就是它的新闻性区别于一般传播媒介的新闻报导。作为“人学”的文学,新闻小说还要特别强调“人”的视角,从新闻事件透示人的复杂心理与灵魂的世界,透出社会历史笼罩的人的命运感。如述平的《最后的浪漫》所写的一个罪犯未进牢门之前,携带脏款与旧日“情人”“幽会”了一番,“浪漫”倒是够“浪漫”了,但它并非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没有多少人生命运内涵,作为新闻小说它是失败的。耐人寻味的是,新闻小说旗帜还未亮出来的去年,述平发表的《晚报新闻》却是一篇相当成功的中篇小说。顾名思义,这篇作品前前后后摘录了十三条犯罪新闻,作者还特别声明,所录新闻都是“出自国内几家有影响的晚报,作者未作任何改动”。而这篇小说描述的故事,即是作品结束时所引的最后一条犯罪新闻作为依据的,甚至主要人物姓氏也未加更动。青工陈某与刘某无怨无仇,居然举刀剁其手,“造成刘某终身残废”,这的确算得上一条新闻了。但是笔墨止于此,也就够不上一篇像样的新闻小说。作者最关注的是陈某原是文明职工,为什么突发凶暴呢?小说写“人身伤害案”只是作为一个观察的孔道,目的在于探求其性格,心理与情感的犯罪之源。原来,晚报新闻里所提到的“女青年”即小说里的安红,乃是陈某从小学时代即崇拜的女神,但他的纯洁、神圣的感情,却被安红与其经理当成作爱时所嘲弄的佐料,加之陈某又被那个经理无端的打掉牙齿,他再也无法忍受而要复仇了。而陈剁掉刘某之手,与其说是因为刘的嘲弄与较劲,不如说是他对安红、经理那种不可遏止的痛苦与复仇情感的大喷发。于是,这篇小说不只是一个伤害罪的新闻报导,而是提升为人性的透示,作品蕴示一种人生情感与命运的悲剧。值得玩味的是,这篇好新闻小说却产生于新闻小说倡导之前,之后,同一作者的《最后的浪漫》反而失败了。这是为什么?这类文学现象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远的不说,仅以85“文化热”推出的“寻根文学”而言,李杭育在寻根热流中及其以后写的小说,再也没有超越他从前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的高度。在明确的文学主张与鲜明旗号下写的小说,反倒没有超越或达至从前“浑沌未开”时写出的作品水平线。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学现象,但那是另一篇文章回答的问题。在这里只想提出,包括新闻小说在内的“新”字诸家小说,当你突围时谨防误区,只有突现各自文体的主脑,强化文体的独特意蕴与色彩,它才有可能在残酷竞争中获得生存的权利与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从审美趣味与美学角度考察,94“新”字诸家小说所强调的亲历性、纪实性、新闻性等,自然适应了如今读者讲究“真格”的欣赏要求,然而文学的魅力是由纪实与虚构两个极端相辅相成而结构的。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我们面对小说在强调纪实特点时何必就要拒绝想像和虚拟这一小说创作规律的东西呢?虚构与虚拟绝非虚假,它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虚构与纪实都是将真实视为文学的生命。作为小说当强调纪实性而放弃虚构时已步入误区,因为你实际是拒绝了艺术想像力与对生活深度广度的总体把握力。就如《半日跟踪》吧,它出自小说名家陈建功的手笔,他所跟踪的四川业余作者邱忠义,写不出小说而又自称“周克芹第二”。这个人物很有开掘与剖析的价值。邱发表不出作品本因文化、文学素质或思维方式而造成的,但他却归罪于别人结伙忌妒他打击他。像这样的人物形象,我们并不陌生。在那浩劫的年代当沉滓泛起的时候,不是常常有人控诉“修正主义路线”如何如何打击迫害他,于是便轻而易举的博得一顶“右派”桂冠吗?建功在作品中也说:“就说北京,有多少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出版不了的罪责,推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排挤或者推给‘极左路线’的打击!”可见,邱忠义及其心态和思维,是特定历史与政治腹胎孕育的畸形儿,是一个很有探索价值的典型。可是建功未从他自己的思路展开,而是更多的将它归结为精神病症之一的“偏执”。小说情节又拘泥于编辑部门前的“蹲坑”与火车站的“远望”,对这个扭曲的人物只写作者的“亲历”,至于邱为什么“偏执”的精神原因却未能得到充分地探掘与展示。邱的“周克芹第二”的迷梦,虽然始发于新时期,但那种心态却是荒诞政治所孵化的丑剧。邱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戏也许不是最后一个悲剧,但对这一应该向过去告别的喜剧式形象,文学却不该完全拒绝必要的虚构、想像与历史的把握。建功在倡导新体验小说十位北京青年作家虽然署名最后一个,但我视他为新体验小说的先行者。他这两年先后发表的《放生》《前科》这两部中篇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作家自我对派出所民警对北京养鸟老人的“跟踪”。这是建功单枪匹马的先行探路,对于小说这一新写法的阅读感受,我曾跟建功谈过,也曾写过评论文章,那两篇将作家的亲历性、作品纪实性与对人物故事的想像和总体的把握,有机融为一体并灌注了作家的独特体验,我以为那两篇应该列为近年优秀小说行列。可惜将这种写法这类小说一旦正式命名新体验之后,《半日跟踪》作为“头题”却失败了。这是不是像他在小说中“交待”的那样,由于催稿急迫临时换题而来不及细想匆匆“对付”出来的?可是他最近写出的《天道》却是一篇叫响的“绝活”。千把字咫尺之篇,竟然活活画出一个干部子弟那种骄纵霸道的心态。在丁囡囡看来,即然“老爹打下的江山”,她就该风骚独领“这天下”。政治热,她牢执权柄;经济热时,她就当上“富婆”。直到绝症使她爬不起来,丁囡囡终于顿悟,人死了“只占巴掌大的地方”,活着何必“争竞半天,管屁用”,而且还自忏自悔,“我活着时给别人留的路太少”了!这一“新体验”的确是大彻大悟,其生死之道与人生哲理很让人一思再思。
第三,亲历或新闻的纪实性,作家与作品的当下状态性,新都市新市民的题材鲜活新颖性,这都是突围中文学追求的特点。但它也要防止步入另一个误区,我们不能轻忽一更深的层次,那就是时代制高点的哲学眼光,民族灵魂与国民性的审视,人文精神的注灌,否则必然出现平面化的狭小平淡与平庸的作品。毕淑敏的《预约死亡》为什么引起热烈反响?以纪实手法揭开了临终关怀医院的帷幕,自然会吸引读者目光的,但它的魅力主要不在这里。我们小说曾写了卑鄙的死与英雄的死两类现象,但是作为人人必归的普遍性人类死亡意识与死亡现象,长期来被作品忘却了,忽略了。我看毕淑敏是以作家与医生双重眼光在审视这别人不大涉足的领域。这篇小说不仅仅是采访记录,不仅仅是写一个个的死亡状态,而是“炼蜜为丸”,从大量素材、情节和人物中深入提炼出她的独特体验。正如生,对于死,人人无法回避的。可是面对死亡,每个人却有每个人的死法,恐惧,迷恋长生药,消极等待等,临终形态无奇不有。《预约死亡》对死亡现象却灌注了人生的意蕴,展示人应怎样死,从体面的尊严的死亡升华为真正的人生与人性美,在死亡现象中小说启引人们哲理之思,毕淑敏为什么如此深刻地写出新体验小说,还是用她自己一段话来回答吧:“新体验小说光有情感体验我以为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体验里不仅包括了感觉的真谛,更需涵盖了思想的真谛。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炼蜜为丸》《北京文学》1994年3期)我想,作家不一定人人是思想家,但你要当一位大小说家,你就要成为人文思想家。毕淑敏的小说家与思想家的话中外文学名家早已有云,并被历史证明了的,但它对于“新”字诸家小说,尤其对于蜕变中的转型期文学创作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又如李功达的《呆坐街头》,应该说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从来京打工小伙子身上看到乡下人与都市人的鸿沟,他用下馆子,大把大把花钱,企图买到他所渴望的“平等”,从窃取贵妇钻戒窥见他的报复心理。打工仔严志勤形象使我联想到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木匠儿子于连·萦菲尔。这部世界名著原型是1827年巴黎轰动一时的,也是工匠之子的贝特尔案件,但作家写作时不是单单强调亲历与纪实性,而是从射杀市长夫人的枪声及其种种野心,抗争之中,小说提炼出一个典型,一个低层人渴求打破贵族阶级统治而获取平等、财富与权力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大变动的典型形象。中国今天正处于改革大时代,低层与上层的冲突与沉浮,财富与权力的裂变与重新的散聚,这是由大一统计划经济走向纷繁的市场的历史大趋势。《呆坐街头》从进城打工的农家子那种企求平等、尊严与财富中,它已触摸到了大变革历史的门楣,可是它逾门未入,擦边而过了。尽管作者想方设法使小说主人公这个憨厚的小伙子多吐露一些心趣与故事,作者也想多角度的理解与透示他行举的社会内涵,但由于亲历性纪实性的限制,时代视野、人生哲学与历史把握力局限它未能成为一部人文风骨厚重、有历史深度的大作。
历史对待文学有情又是无情的。文学流派与艺术主张的兴衰沉浮,作为一种文化命运现象是迷人而又百解不烦的。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文学虽非丰年,也未挣脱清淡低徊的局面,但它时而呈现好小说,这里也就不作一一例举与分析了。“新”字诸家小说不能说是少数“炒家”或搞商业包装;对于“新”字各家的缺陷与误区,自应严肃批评,甚至说点过头话也无伤大雅,但不必全盘否定,呵责它们是拉“山头”搞“计划文学”,应该看到它们还是在重重危机中作出突围的尝试。至于说各家命运谁短谁长,谁冷清准显赫,无须过多预言,还是让物竞天择的自然扬弃与历史老人抉择吧。不过,既然提起历史,我们考察“新”字小说时不能不联想到历史这面清澈的镜子。今年的文学幡旗四起与八十年代“文化热”颇有相似之处,当年举凡带个“新”字,无论新观念新方法新小说无不令人不加思索地狂热接纳。然而,在多元多样色彩缤纷中真正在历史上留下一身的,也只有现代派、寻根文学与新写实小说等少数几家,况且前二者也来去匆匆,而八十年代后期与九十年初期的文坛,诸种派别中有实力有影响也只有新写实小说了。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它们火爆与消沉的历史命运告诉我们,谁紧紧拥抱时代生活与读者的关注点,谁有坚实的文学业绩,谁就生气盎然而非倏然消匿。寻根文学与现代派以其先锋锐气曾使文坛焕然一新,前者打开了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与文学之根的大门,使新时期文学由政治反思走向文化反思,但由于偏执地域古老文化习俗与博厄斯的文化归因主义及文化决定论而疏离了读者。现代派是西洋文学的“窃火者”,但正如当时论者批评的那样,它“好像生活在云端里”,似乎是“‘精神贵族’。和人民距离太远了!”新写实由云端回到大地,从古老习俗走向当今的世俗,它不是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史诗篇章,但捕捉了变革期的百姓心态与社会情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亢奋的文化热走向退潮期,人们关注由社会、集体转而为个体的生存活法与当下的个人实惠,激情开始冷却,崇高反受嘲弄。神圣,理想,奉献,悲壮这些曾经灼烫心灵的字眼,却由世俗、实利、平庸、琐碎所取代了。恰在此刻,新写实站出来,文学中心位置由俗事凡人代替了叱咤风云的英雄,轰轰烈烈的人物场景换成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小家小户“过日子”的景象。小日子,家务事,儿女情,这是十七年与“三突出”文学期所压制所讨伐的东西,新写实却进驻了当代文学这一块空白地,而且用衣食住行生存状态的写实,拨动了众所关注的也是时代敏感的一根神经。新写实确有缺陷与局限,笔者曾多次提出它在展示人的生存窘态这一世界性命题时,不该抛掷了文学传统的为人生,并因人生血脉不足而使新写实没有达到它应达到的高度,所以我主张现在与未来的文学则是写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在文章结尾时所以稍稍回叙一下当年群雄纷起的文学往事,不是“借古讽今”,而是一种期待,期待“新”字诸家小说警惕误区,多创实绩,比翼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