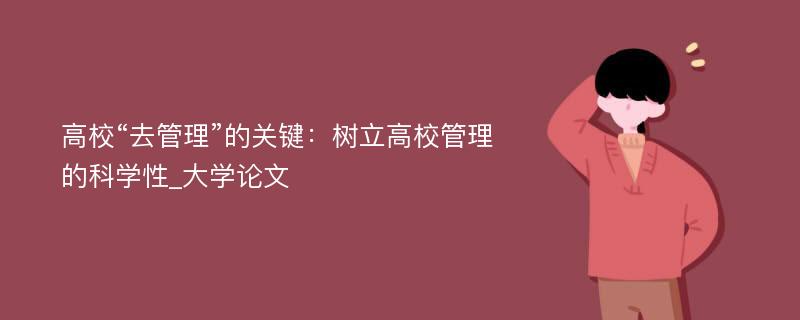
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科学性论文,行政管理论文,关键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强调,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6月6日,国家公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7月29日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再次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去行政化”的改革取向:“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1]就政策层面而言,大学“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改革方向——尽管加了“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这样较为审慎、也较有弹性的修饰词。但是,大学“去行政化”何以须为?仍然有辨析、澄清的必要;大学“去行政化”何以可为?也不无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大学去行政化”:绝不等同于取消院校的行政级别
对于逐步淡化或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有多位著名大学的校长、书记发表了不同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津大学校长龚克的担忧:“目前社会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官僚体系,高校里若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就不知道该和谁对话,找不到省里的主要负责人,甚至连厅局长都可能不愿见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令你事难办。”龚克的坦言,涉及了当今不容回避而又令人无奈的“行政化”、“官僚化”的社会现实。确实,高等院校的“行政化”倾向,仅仅是全社会日益严重的“官本位”问题的“冰山一角”。如果连著名大学校长都会因为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而“求见”无门、对话无人,更遑论普通教师的建言献策或平民百姓的投诉、辩白了。今天的中国非要总书记批示或总理发话,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失地农民的温饱才有人问津。这些报道在让人们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民务实作风的同时,也凸显了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的“官僚化”作风和对百姓疾苦麻木不仁的恶习。同样,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官本位倾向,各级党政机关不从根本上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新”的价值观和执政观,则大学的“去行政化”是难以真正落实到位的。
话说回来,大学的“行政化”固然与实际存在的院校行政级别有关系,但“去行政化”又并非依赖淡化或取消“副厅”、“正厅”或“副部”、“副省”此类级别就能见效或完事。解决此类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身居大学管理高层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富贵于我如浮云”,还是“丈夫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提级时”?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也好,与行政级别完全脱钩也好,对一个真正献身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大学校长而言,应当是无足轻重的。1950年代中期,身为云南省省长的郭影秋主动向中央请缨,出任南京大学书记兼校长,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云南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说:“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匡亚明作为1920年代即投身革命的高级干部,在省级领导与新组建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时他们并非没有行政级别,但他们志存高远,不为级别所束缚和牵累,将心思放在研究、探索教育、科研和办学规律上。他们后来能够成为有思想、有见地且有建树的大学校长,由革命家“华丽”转身为教育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境界超越了个人名利和荣辱,他们的“兴奋点”与关注点集中在“育天下英才”、“进学术前沿”和“办一流大学”,他们真正做到了“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防止行政管理的越权和“异化”
长期担任剑桥大学学术副校长的阿什比勋爵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黑体由原作者所加)”。[2]毫无疑问,200年前的柏林大学,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共同体”,或者说“学术共同体”。数十年前阿什比主政时期的剑桥大学,也是学科不多、规模有限的“同质体”。在这样的“同质体”大学,其内部事务基本上由专家学者兼管,大学在实现基本自治的同时,也做到了教授治校。
但是,时移势迁,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学的体量、形态、使命和功能均发生了根本变化。1963年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哈佛大学所发表的豪情万丈的演说,形象地展现了这一历史性变迁的画面:19世纪中叶纽曼所赞许的大学,充其量是“一群僧侣居住的村庄”;20世纪30年代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也不过是“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它们都难以与加州大学这样“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多元化巨型大学”相匹敌。 [3]曾经担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18年的弗兰克·H.T.罗德斯,则用一组数字突出反映了大学规模的扩张、学科的繁衍、功能的拓展是如何改变了大学管理的性质和文化——“不断增大的大学的多样性带来了大学校园规模的扩张。早期的美国本科生院是小而紧凑的同质体。200年前,哈佛大学录取了大约57名学生,100年前是3373人,到今天达到了18700人,其中有6800人是本科生。……1891年的时候,密歇根大学的校长詹姆斯·安吉尔还没有秘书,他的所有回信都是手写的,亲自为所有的文学院学生注册,教授国际法和合同史,做礼拜仪式,他认识所有的103个教工,以及2420学生中的好几百个。‘他清楚课程的每一个部分’……”[4]中国大学的情况同样如此。30年前,拥有13个系科和6000余学生的南京大学在江苏省是数一数二的大学。如今,仅就规模而言,2.5万名在校学生数的南京大学,也许难以跻身全省高校的前10名之列。
现代大学已经是这样一个巨型的复杂系统,或者说“矩阵结构”。它不仅要培养数十个学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而且要进行数十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它既要与各级政府打交道,从它们那里获取财务、经费的支持和政策、法规的指令,还要与相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周旋,既向它们“输出”自己的“产品”——从毕业生到科研成果,又吸纳相关的“输入”——从信息、经验到资金、技术装备;它既从事着文化整合、知识创新这样难以估价的精神生产,又经手着数亿甚至上百亿的巨额资金运作……大学依然是学术共同体,但它已经不是昔日纯粹的“同质体”而拥有纷繁复杂的行政管理事务。它一方面要循着学科专业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它又应该按照行政事务的程序决策行事。我们看到两个最基本的事实:
其一,“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和操作这种材料的基本活动;这些任务分成许多相互紧密联系但却独立自主的专业;这种任务的划分促使形成一种坡度平坦、联系松散的工作单位结构;这种结构促使控制权分散;最后,目标必然是模糊的。”[5]
其二,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巨型联合体。它具有双重含义:即“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广泛多样的,高等教育组织是由多种不同的成分组成的”。这样一种巨型联合体产生了大量管理事务,而事务性部门(business side)则接近于其他社会组织类型的“责任金字塔”,其等级性远甚于“学术性部门(academic side)”。“一条相对清晰的指挥链从一名‘行政主任’或行政和财务副校长传往下属各部门负责人(注册主任、人事处长、财务处长等),这些人的办公室挤满虽有各种不同头衔但在任何意义上人们都理解为‘雇员’的办事员。”[6]
当大学的规模较小、学科有限、任务与使命单一而“同质性”较强时,教授治校是可以实现的,由教授学者兼任管理工作、参与所有决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现代大学已然是复杂的巨型系统,就不可能再由教授学者来承担大学治理的所有事务。一方面,学科的分化和深入发展使得教授的知识结构向纵深拓进而在跨学科的拓展上遭遇挑战;另一方面,诸多与社会沟通联系、博弈妥协的事务,特别是资金的筹措、财务的决算、多校园的管理等等,也决非那些在天体物理领域如鱼得水,或者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不断拓进的教授们所感兴趣,或者说所能胜任的。
此外,让这些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教授学者舍其所长、取其所短,实在既不科学,更不划算。因此,聘任专职的和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解脱教授学者的“俗务”并为之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就在所难免。任何一所现代大学,都已经形成学术与行政管理的两个系统、两支队伍、两种逻辑,就像“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一样不可或缺。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去行政化”绝非不要行政管理,更非取消或取代行政管理团队。
从上面推论可见,我们所批判并决心革除的大学“行政化”弊端,并不是指正常的、必须的行政管理事务,而是行政权力的越位、专权与“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异化劳动理论,阐述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7]。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们生产的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成为统治和支配人们自己的外在力量。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分析大学的“行政化”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大学所聘任的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本来是为大学的教学和学术活动提供服务、创造条件,目的是解脱教授们日益繁重和复杂的行政事务,让他们更自由、更潜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本来是“为教授搬板凳”的行政管理人员,却成为“指挥教授搬板凳”的人;行政权力逐步成为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并管辖、控制甚至挤压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异己力量”。“主人”变成了“公仆”,“公仆”变成了“主人”。这种“主”、“仆”颠倒是高校权力异化的典型形态。
伯顿·克拉克教授等学者曾经分析了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在学术单位和高等教育系统的亚文化中,最不引人注目但重要性日增的趁势是管理人员文化与教师学生文化的分离。”由于“专业”的管理干部“取代了由教授兼职,导致一套独立的规则和一种独特的利益的出现”[8],伴随而来的是“教授权力的相对下降”,特别是在关键决策领域。“行政管理人员不再主要是由教学人员担当,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把教授和学生充其量看做是最缺乏理解的人,甚至是制造麻烦的人和敌人。”[9]大学“行政化”的关键,在于管理人员的文化与大学组织文化的主流,学术文化相分离、相背离,并出现了“独特的利益”和“利益集团”。他们将行政管理的权力无限扩大以挤压学术权力的空间,甚至变相“寻租”、牟利。
因此,大学“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取消行政团队,回到19世纪大学教授治校、兼任管理的状念,而是“诸神归位”,“主”“仆”分明。明确大学的行政团队是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教师、学生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在大学的整体利益之外不能有自己的“独特利益”,更不能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私立大学董事会与工厂企业的董事会有着不同的本质特征:“尽管外行董事会的地位在某方面优于教师,然而他们不应该把他们的作用等同于企业中的董事会。后者的目标是为他们的股东获取更多的利润,而前者的目标是促进和提高学者的工作。………由于教师是为难以确定价值的长远目标工作的,因此不可能像计算企业或商业人员的价值那样来计算学者的价值……学者在监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自治条件下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10]私立大学的董事会尚且如此,公立大学的行政管理团队更应将“促进和提高学者的工作”以让其教学、科研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个意义上讲,防止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越位、专权和“异化”,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使命。
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尊重大学的组织特性
大学“行政化”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关系,即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除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管理人员“指挥教授搬凳子”而不是“为教授搬凳子”外,大学“行政化”的另一个重要涵义就是:“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也就是说,大学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延伸,过多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失去了大学的独立性。”[11]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位法国商人在被问到国家如何振兴商业时说,国家只需做好诸如修路、铸币、制定灵活的汇兑法等事项,剩下的“由我们自己来干”。康德认为,这一回答也适用于大学,特别是哲学院与国家的关系。[12]但是,时移势迁,大学早已不止文(哲)、法、神、医四科,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不仅“承担大量教育经费的州,现在越来越坚持为大学定调”,而且,相当一批学者专家也认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3]
由于现代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大学能够承载的社会责任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也远远超越了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大学和19世纪“象牙之塔”时代。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既涉及国计,更关联民生。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弗兰克·H.T.罗德斯充满睿智地界定了进入21世纪的研究型大学的核心活动:“作为一种公众信任的研究”——“研究需要自由和独立性,但它代表着公众义务和信任;研究源于个人的求知欲,但却需要公共支持;研究属于个人发现,但它提供了公共知识;研究需要个人洞察力,但它产生社会利益;研究以基础知识为根本,但它要运用于实践。”[14]这一界定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当代大学的重要特性,即它们不再是少数精英学者的集合与“基于闲暇好奇”的探索与追求,它们在保持个人自由与独立性的同时,也越来越与公众利益、社会需求甚至国家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因此,国家的关注、支持和管理、问责,是不可缺失的。但是这种管理和问责的前提,是尊重大学组织的特性和大学活动的特质,而不是将大学视同政府部门的延伸或附庸,采用指令性计划或简单、粗暴的令行禁止方式管理大学。
大学组织特性之一是“学术共同体”。到目前为止,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院校,仍然被视为“学术共同体”。“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正是这些掌握了“高深思想”、“高深知识和方法”的学者教授,组成了以专门化为特征的学科专业。尽管近年来学科的分化与学科的整合使得传统的学科界限有日趋模糊的倾向,但学科的实力、水平和特色,依然是高等学校竞争力的主要标志。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个特性是不同学科间的差异性,不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技术学科迥然不同,即便同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政治学与教育学之间也相去甚远。这种学科差异性延伸出另一个特性,即结构松散,各学科专业发展目标的自主、清晰与整个组织系统目标的模糊。有人将之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混乱的有序”。
尊重现代大学组织特性,就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严格区分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切忌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去处理学术问题,更不能以长官意志来判别学术争鸣的是非曲直;其二,坚持以学术管理为主而非行政主导。
现代大学的组织特性之二是“群英荟萃”,大学是高智商、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富集之地。正如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汇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 [15]大学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经费等物质条件,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人,在于高水平的学者教授。能否吸引学富五车的大师,能否吸引和造就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青年才俊,已经成为衡量大学核心竞争力强弱的主要指标。
对“群英荟萃地”的大学的管理也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特征,即科学探索与知识创新的“非线性”、非均衡性;遵循人才培养的诸多特性:群体培养与个性培养的结合,可计量与不可计量的交叉,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兼有、人才培养周期较长而效应滞后等等。二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心理特性。近年来许多政府管理部门像办企业、抓经济那样看待大学建设和发展,把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发现与创新视同物的生产,用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考核大学的绩效,要求立竿见影、限时见效。许多高校也盲目引进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推崇计量评估和“重奖制度”等等,将大学教师等同于工厂流水线上的“计件工”,直接、间接,有意、无意地挫伤了大学教师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政府和社会公众必须承认大学是不同于政府部门、军队、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承认大学的活动——培育人才和发现新知——不同于物质生产、商贸活动和军事、执法等其他社会活动。高明的政府理应明白:让“大学自治”,而不仅仅是有限地“下放”本就属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其实正是激发大学活力、发挥大学功能的最佳选择,也是最终符合国家利益和公众期望的教育管理之道。200年前柏林大学成立之时,首任校长费希特教授在履职演讲中说:“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追求真理为主旨,它不是依据政府一时的政治利益和党派、教派的狭隘眼光来安排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恰恰相反,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主旨。”[16]我相信,这也是所有中国大学的高远志向。
大学“去行政化”的出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或者说让真正的教育家来办学,与淡化、取消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两项互为表里的举措。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其实质就是被遴选或聘任到大学领导层面的教授学者,其价值追求不是循着“副厅级”、“厅级”乃至“副部级”的“仕途晋升”,而是要修养、历练成为真正理解教育、钟爱学生、尊崇学术、精通管理的教育家。
真正的教育家的涌现,有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是政府营造宽松、自由、多样化发展的氛围及环境,让大学能够自主、自律,“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办出特色,办出个性;其二是大学校长、书记们对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行政管理的投入与执著,不是将大学领导的职务视为晋级、提升的台阶,也不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将大学管理作为副业或者说“苦差事”。有学者指出:“目前校长的岗位不大可能把一名学者培养成教育家,只能将其历练成官吏,成为通晓关系的‘政客’。”[17]其实就是强调在大学“行政化”倾向严重的现实面前,无论是外部范围,还是主管追求,都不利于真正教育家的生成。
现代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在急剧增加,无论是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还是院校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发生着“从非专业性人员向专家的转化,非专业性人员为以行政为生涯的人所替代,他们是各行政领域的专家,任期长,采用聘任制而不是选举产生。协调机构的构成也转变到更多地依靠专职的永久人员,而较少依靠兼职的一般性人员”[18]。这些管理专家,即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院校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的专家,相当一部分是由学科专家“变身而来”,即他们原来是物理学、化学、工程技术学,或法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通过院校管理实践,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视野,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和领导能力。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卓有建树的大学校长,就是由学科专家转换角色,成为成功的教育实践家和思想家的。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其取向是成为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实践家或教育理论家。人们期待中国能像美国那样也有一批大学校长成功实现从学科专家到真正教育家的角色转换。这批有思想、有创见,更有建树的教育家的出现,既标志着“大学去行政化”的成功,也可进一步推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去行政化”,进一步调整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
真正的教育家办学,还有赖于大学管理中日益增多的专职、专业管理人员。他们大多是具有管理学、教育学、科学学领域硕士、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他们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掌握了管理、协调较大和较复杂的高教系统的方法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相对各具体的学科专业比较超脱。因而从理论上讲,也可能有“适应从高层观察的思想”[19]。我理解所谓“从高层观察的思想”即高屋建瓴把握趋势,全局在胸参与博弈的思维和能力。这和诸多学科专家教授往往从自己所在的系科甚至自己所擅长、所钟情的学科方向出发的思维与价值判断是有明显不同的。
但是,这些堪称管理专家或准管理专家的专职行政人员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一是他们缺乏相应的学科背景,也缺乏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亲身经历,如果高高在上而又不深入系科实际,就可能难以理解、支持第一线的教授学者;二是如果他们形成“独立的文化”,即形成了基于自己的利益与权力的特殊“文化”,则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大学“去行政化”的要义,就是既承认现代大学的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必要性,更强调大学的行政管理有别于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特殊性,在大学组织文化的“场”内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即服务并切合大学的学术活动、教育活动的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大学“去行政化”有利于那些由教授、博导、院士出任校长、书记的学科专家向真正的教育家的转变,而且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教育家,成长为职业性的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