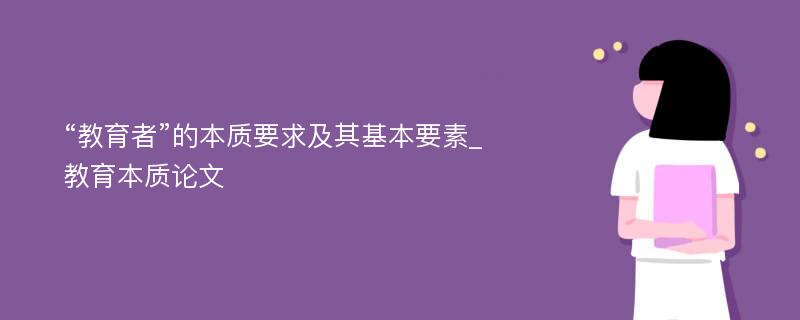
“教育者”的本质诉求及其基本要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义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11-05
中图分类号:G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186(2008)01-0069-05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作为教育者而存在,因此,我们会时常面临着这样的追问:“我(你)也算是教育者吗?”“怎样才算是好的教育者?”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构成我们日常教育经验的重要部分,也是教育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们当前的教育研究中,尽管有很多对于教师的规范性探讨,但缺少对教育者本质的深度追问。对教育者本质的追问与对教育本质的追问密切相连,我们对教育本质的探讨已日益深入,需要对“教育者”展开更为深入的反思。
一、日常教育实践中对“教育者”的本质追问
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作为教育者而存在,这并不是说他可能会从事教师职业,而是指在其日常生活中,在很多种情境下,在其与他人的交往关系方面,他可能作为教育者而存在。不仅教师对学生而言,而且父母对子女而言,长辈对晚辈而言,兄长对弟妹而言,乃至朋友对朋友而言,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晚辈对长辈而言,都有可能是教育者。尽管中国古人云:“人之过,在好为人师。”但我们却经常会发现自己时常难逃做“教育者”的宿命,即便我们不去选择教师职业,但一般而言我们总会为人父母,需要抚养教育自己的子女;我们也总会成为长辈,需要关心晚辈的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积累许多经验,掌握丰富的知识,形成较为坚定的信念,这也需要传递给别人。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人的生命需要汇入人类文化的历史洪流才有意义,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就在于每一代人的自觉努力。从这个意义而言,人是注定要作为教育者而存在的,这是人类文明赋予每一个人的使命。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教育者,甚至有的人根本就不配做教育者,当然,更多的人是不知如何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做教育者的责任。同“学习者”这个概念一样,“教育者”并非是标定某种制度性社会角色与身份的概念(如“教师”这一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性概念。在交往过程中是否作为“教育者”而存在并非完全取决于外在的制度性规定,而主要取决于自身所施加影响的性质,即便是在师生交往过程中,教师也未必始终作为真正的“教育者”,在亲子交往以及其他类型的交往中同样如此。当然,教师是最典型的作为教育者而存在的,但并非每一个教师都是好的教育者。只是一旦从事教师职业就意味着人们对之寄予着成为好的教育者的期望,因此,教师会时常面临着来自自身或外界的追问——“我(你)也算是教育者吗?”“究竟应该怎样做才算是好的教育者?”——究竟怎样才算是“教育者”?怎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教育者的责任?这理应是教育学所要探讨的核心性问题,因这种探讨不仅限于学校教育领域,所以可以称之为一种广义教育学的探讨。
二、当前教育研究领域中“教育者本质”问题的凸显
近年来,在教育研究领域,关于教师问题的研究可谓是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教师应当是怎样的”以及“如何成为优秀教师(即教师专业发展)”两个方面。其中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更为根本,其核心是教师的专业素养问题。叶澜教授在这方面的探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新世纪教师专业素养初探》一文中,叶澜教授认为教师专业素养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具有与时代精神相通的教育理念,并以此作为自己专业行为的基本理性支点。她认为,新的教育理念,主要是在认识基础教育的未来性、生命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教育观、学生观和教育活动观。其次,教师的专业素养在知识结构上不再局限于“学科知识+教育学知识”的传统模式,而是强调多层复合的结构特征。具体包括三个层面,处于最基础层面的是有关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第二个层面是具备1—2门学科的专门性知识与技能;第三个层面属教育学科类,主要由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构成。最后,因当今社会赋予教师更多的责任与权利,提出更高要求和期望,教师要胜任就需要新的能力。尤其需要强调以下几种能力:理解他人和与他人交往的能力、管理能力、教育研究能力。她说:“对人类的热爱和博大的胸怀,对学生成长的关怀和敬业奉献的崇高精神,良好的文化素养,复合的知识结构,在富有时代精神和科学性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教育能力和研究能力,在实践中凝聚生成的教育智慧,这就是我们期望的未来教师的理想风采。”[1]这种对于“教师应当怎样”的规范性研究,对于引领教育实践中教育专业发展的方向以及教师教育都发挥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在对于教师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始终居于主流性的地位,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取向。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些“设问教师”的方式。日本学者佐藤学把对教师的研究区分成三种方式:规范性方式,设问“教师应当如何”;制度论方式,设问“所谓教师是怎样一种职业”“教师的责任与作用是什么”;存在论方式,设问“教师是怎样一种角色”“教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您)是教师”。他认为,对教师进行研究的“规范性方式”源于启蒙主义的传统,“制度论方式”源于近代的技术理性的传统,而“存在论方式”则继承了源于卢梭的浪漫主义的传统。“存在论方式”深入到教师对“教师角色”体验的经验世界,旨在获取教师自身的存在与自己工作意义之证据的意识,亦即探究作为教育主体的存在证据与教育实践中“真实性”的意识,具体表现为一些无论怎么探究也不可能达到稳定之解答的“两难问题”。这将不再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进行“微观叙事”的研究。他认为,由于当今从根底里支撑教师之存在与实践的学校教育的“规范性”与“正统性”日益式微,教师对“教师角色”的体验正经历着深层的存在论危机,具体体现为教师工作的三方面特征——“回归性”“不确定性”“无边界性”。教师的存在论危机,是在“学校”这一制度性建制所规定的教师的身份,与教师在其自身的世界中活生生的身份感悟的裂缝之中表现出来的。重新设问“教师角色”,意味着引导教师真正基于自身的经验感悟进行实践反思与再造。[2]
这种对于“教师角色”的设问,对于“教师究竟是谁”的追问,在我国当前的教育研究中,也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吴康宁教授率先对“教师是社会代表者”这一惯常似乎不被认为是问题的问题进行了发问与阐发,并在随后引发的讨论中,将观点进一步引向深入。诚如他所指出,“当今时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质疑的时代、批判的时代。这一点对于教育研究来讲同样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对教育的反思不可谓不多、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但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对于教师的属性的反思,对于‘教师究竟是谁’的追问”。他在一些关于教师的既有的定论与常识性的观点中,发现了问题之所在。他说:“事实上,长期以来,‘教师究竟是谁’似乎一直都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不是吗?我们对于教师的‘属性’似乎早已有了定论。这一定论在法律中有明确的呈示,即所谓‘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年10月31日颁布);在学术界也有比较普遍的共识,即教师是‘向受教育者传递人类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需要的人才的专业人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至于其他形式的官方与民间的带文学色彩的表述就更多了,诸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是培育祖国未来的辛勤园丁’等。总之,不论是在支配阶层的期待中,还是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抑或普通大众的眼光中,教师都一直是被视为一种‘社会代表者’的。”他基于自身作为教师的体验及对问题的洞识对这样一些主流性的表述提出了疑问:“教师是社会代表者吗?这些年来,作为教师的我却对这个问题逐渐产生了怀疑。随着社会变迁速率的加快,我的怀疑愈发加深。我感到,无论是从事实判断的角度,还是从价值要求的角度,我们对这个问题都很难给出一个圆顺的答案。”[3]在随后的进一步阐发中,他认为,教师事实上是一种悖论性的社会角色。教师既不应成为纯粹的支配阶层代言人,也不应成为纯粹的公共知识分子。教师所应且所能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半支配阶层代言人半公共知识分子”。支配阶层与公共社会的双重角色期待所造成的“教师角色扮演困境”是导致教师社会角色具有悖论性特征的直接缘由,教育自身的适应与超越之矛盾则是教师社会角色具有悖论性特征的根本原因。[4]吴康宁教授这种对“教师究竟是谁”的追问,对“教师是社会代表者”这种表述的质疑,一反我国教师研究中的“规范论”“制度论”传统,直指教师的生存实在及社会角色扮演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悖论。这有些类似于佐藤学所说的教师研究的“存在论方式”,但他并没有采用纯粹微观的叙述方式去深入刻画教师的生存体验世界,而是运用社会学的方式对教师的社会角色选择困境予以探讨。
这种对“教师究竟是谁”的“存在论追问”蕴涵着一种“解构”与“解放”的力量,引导教师直面自身的角色扮演困境并自觉寻求解决与超越,而非诉诸来自外界的强制性约束与过高苛求。这样一种探究方式将我们对于问题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但并没有从正面回答“什么是教师”或者“当教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本质性追问,而这正是传统的“规范论”与“制度论”所力图回答的。正如我们所经历的,单纯的“规范论”与“制度论”方式往往将教师置于角色扮演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如何面对对教师的本质性追问?我们应回归到对于“教师之为教师的最根本方面”的探寻上。或者,“教师”是一个太过社会角色化的概念,我们更应该回归到对“教育者”内涵的追问上。这样一种研究需要回归到人类文化整体之中,在其中可以重新找回“教育者”的根本性位置与特征,现象学“本质直观”的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方法的启示。
从人类文化总体来看,教育承担着“继往开来”的文化使命,是人类对自身成长的自觉,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下》)的活动,是对人之成长的关怀与促进。由此可知,教育者之为教育者的根本所在理应涵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否有明确的教育性意向,即对人之成长的真正关怀;其二,是否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即以自身对文化内涵的敏锐把握启发学习者。
三、对人之成长的真正关怀的教育性意向是成为教育者的直接条件
教育是助人成长的活动,其核心是对人的生存与成长的关注。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其中一方(通常是年长者、教师、父母等)对另一方(通常是年轻者、学生、子女等)施加积极的影响,但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而施加的影响的类型很多,并非所有的这些影响都是有教育性的。判断这些影响是否具有教育性最根本的一点是看这些影响是否体现着对人之生存与成长的关注,是否是出于助人成长的目的,即是否具备教育性意向。
即便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并非所有的交往影响都出于教育性意向,有时仅仅是为了控制住对方;有时仅仅是为了让对方服从自己以达成自己的目的,把对方仅仅当成是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有时仅仅是一些简单的交流或信息传递,仅仅是一些表面的敷衍与应付;有时甚至仅仅把孩子当成自己的游戏对象或自身所郁积的不良情绪与怨恨的发泄对象。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影响都不是出于教育性意向,在这些情况下,即便是教师或父母也都不是作为教育者而存在的。诚如加拿大教育学者范梅南所说:“毋庸赘言,并不是所有人之间的影响在本质上都是有教育性(pedagogical,agogical)意义的。每一个成人和儿童都始终受到:相互间的、文化传统的、语言的、他们自身历史的、社会物质环境的等各种影响。但成人和儿童间只有某一种影响是出于向善的、为儿童好的动机——这种动机具有教育性意向(pedagogical intent)。而且,这种意向是为了加强儿童‘生存和成长’(being and becoming)的各种偶发的可能性。”[5](23 24)正是这种明确的教育性意向才使一个人成为自觉的教育者。做一个教育者意味着这样一种责任:“保护和教导年轻一代如何生活,学会为自己、为他人和为世界的延续与幸福承担责任的这一神圣的人类职责。”[5](10)
具备教育性意向意味着对人之成长的真正关注,其中包含着对人之成长的可能性与方向的主观判断与积极促进,而这需要建立在对受教育者的当前状况及其内在需要与愿望的确切理解与敏锐把握基础之上的,否则,这种意向很容易成为强加自己的意志于对方的一种托词,很难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就如《学记》中所说:“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弗。”任何教育性意向都应尊重儿童本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教育性意向就是尽最大可能地加强儿童的任何积极意向和品质。
范梅南指出,教育性的意向也是我们面对孩子的最基本的体验,我们将孩子看作是走进我们生活的另一个人,他向我们提出要求,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教育性意向也可以看作是我们面对孩子时我们发现被召唤时的一种主动的回应。[5](27—28)“无论如何,将教育性意向摆在我们抚养孩子的经验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性意向体现了大人希望孩子生活顺利的愿望。[5](29)他认为,“教育性意向不是简单的思维信念,也不是我们写在纸上的课程计划和学习目标。教育性意向牵涉到我们区分什么对孩子好、什么对孩子不好的所有的积极思考”。[5](32)教育性意向事实上体现着对人性向善的坚定信念,体现着一种关爱支持性人际关系的建立。
正是教育性意向使一个人成为教育者,其对象并不仅仅限于儿童,也可以指向成人,可以存在于朋友之间,也可以是面向大众的社会教化。孔子曾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点出了教育者(仁者)教育性意向的品质。教育性意向本身蕴涵着一种复杂的关心品质,其真正实现需要借助于多方面的条件,尤其离不开对人类文化(即教育内容)的自觉把握。
四、教育者基于真正的文化自觉,以对文化内涵的敏锐把握启发学习者
教育通过文化的传承造就人性,培育新人,若没有世代积累起来的文化,人类势必退回到野蛮状态,若不凭借既有的文化,个人的成长也无从谈起。教育承担着人类文化承前启后的使命,教育者必须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唯有如此,才能凭借对文化内涵的敏锐把握启发学习者,使其健康成长。
历代思想家都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认为这是教育者之为教育者的根本所在。唐代思想家韩愈对教师所做的经典界定流传至今,似乎很难再出其左右,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核心是点明教师文化传承之使命。为师的前提首先需要将所要传授的文化、道理了然于胸,需要对人类的文化整体有自觉的把握,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欲明人者先自明。”“夫欲使人能悉知之,能决信之,能率行之,必昭昭然知其当然,知其所以然,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贤者于此,必先穷理格物以致其知,本末精粗晓然具著于心目,然后垂之为教。”[6]否则,若自己于道茫然未有所得,大义不知其纲,微言不知其隐,“实则昏昏也”,是不配也不能充当人师的。
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人赫尔巴特曾论述过他心目中教师的理想形象:“有一种青年,他能敏锐地感知到各种思想的吸引力,并能看到教育思想的美与伟大;他不怕献身于时而希望与时而怀疑、时而快乐与时而烦恼的无穷变幻中。这种人,假如他具有思考力与知识,能用人类的思想方法去观察与描述作为一个庞大整体的片段的现实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在这样的现实中教育一个儿童达到较高的境地。于是他自己将会说,真正的、正确的,并适合其儿童的教师不是他,而是人们曾经感受到的、发现并想到的全部力量。而他只不过是被派去对儿童作明晰的讲解和作为儿童合适的陪伴的。”“把迄今尝试中的全部收获,不论是教训还是告诫,集中地献给年轻的下一代,这就是人类在其繁衍的任何时候所能作出的最崇高的贡献。”[7]教育者的职责就在于以其所领悟与感受到的文化中的智慧与力量去启迪学习者的心智。
强调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强调教育者的文化自觉,并非意味着教育者必定要进行知识的灌输。文化的生命在于其对现实社会人生所发挥的作用,教育者的文化自觉就在于对文化在解决现实社会人生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充分认识,并能以此启迪人的智慧使人更好地生存与成长。作为教育者,要引导别人更好地适应社会、学会生存,而这,离不开对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即真正的文化自觉。孔子所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道出了典型的有文化自觉的教育者形象。
正是对人之成长的真正关怀的教育性意向以及对于文化在启迪人生成长方面所发挥作用的文化自觉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教育者”,这构成了教育者的真正本质。除此以外,我们还会强调教育者的一些相关品质,如为人师表、率先垂范,掌握教育的原理、技巧与方法,具备基本的知识、素养与能力,能够进行反思性实践研究与创造等,所有这些都是由上述本质性内涵所派生的,相对来说是居于表层的对教育者的规定。本文所旨在探讨的是对“什么是教育者”的深层追问,明于此,方有可能在众说纷纭之中不至迷失了方向,方有可能在现实的教育经验与困惑中作出基本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