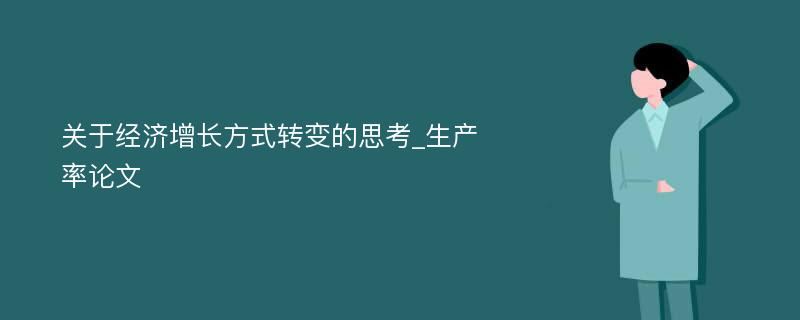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若干问题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实现‘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之一以来,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和论证。从流行的解释和观点来看,笔者感到在理论上有些问题值得商榷和澄清。本文提出一些疑问,并略抒管见,以求与各方学者共同探讨。
一、关于“粗放”和“集约”的解释
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很多文章都把“粗放”和“集约”这一对概念同经济增长学中的“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混为一谈,或者与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的“外延”和“内涵”这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等同起来。当然,谈到“增长方式”用后两对概念来解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增长首先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要扩张生产能力只有两种方法:一是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将它们与“粗放”和“集约”等同起来就在理论上出现了概念的混乱。如果我们对此不及时澄清,很容易引起理解上的误区。
首先,“粗放”和“集约”这一对概念在经济学上不是表达不同经济增长方式,而是表达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概念。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粗放”是指相对少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与相对大量的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集约”是指相对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与相对少量的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前者一般是在地多人少,土地成本较低情况下采取的方式。后者一般是在土地资源稀缺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且成本较低条件下的配置方式。而经济增长方式则是生产能力和产量增大的方式。马克思经济学把它解释为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并且用“外延”表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投入量的增加,用“内涵”表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代经济增长学中用“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这对概念来表达这两种增长方式。更严格地说,前者是指在技术条件一定情况下,通过生产要素投入量同比例增大而带来经济增长的方式;后者是指在技术条件变动基础上,以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可见,“粗放”和“集约”不等于“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也不等于“外延”和“内涵”。它们与后两对概念所涉及的理论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粗放”和“集约”这一对概念可不可以放在工业生产或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上来说?工业生产和宏观经济当然也要涉及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对概念也并不是不可以从农业引申到工业,从微观放大到宏观。然而,即使是这样,它们也不能与经济增长的两种方式相提并论。“粗放”和“集约”与“要素投入量”或“外延”和“要素生产率”或“内涵”在界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相对量上是相反的。“粗放”是在相对多的土地(或一定量的土地)上较少量地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要素投入量”或“外延”则是在技术条件一定情况下,较多量地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反之,“集约”是相对于较少的土地较多量地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要素生产率”或“内涵”则是在改进技术条件基础上,以较少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推动更大的生产能力,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方式。因此“粗放”和“集约”所涉及的变量与其他两对概念是相反的。将它们等同起来,在实践上怎能不造成误导?
第三,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外延”就是“粗放”,“内涵”就是“集约”,在德文里它们是同一对词,只不过是翻译不同而已。这种看法未免有些偏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外延”和“内涵”明确地解释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马克思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内涵上扩大。[①a]关于“粗放”和“集约”这对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谈到地租理论时也使用过。他把这对概念解释为农业耕作上的两种方式,并且指出这里指的是它们“在经济学上的意思”。“粗放”和“集约”这对概念从古典经济学以来一直用来解释农业耕作的不同方式(即生产要素与土地不同的配置方式)。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把它们与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等同起来。因此,即使在德文里它们是同一对词(因为它们都有“广度”和“浓度”的含义),在经济学上也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况且,上述三对概念在经济学上早就有了东西方公认的明确的理论界定。我们可以在各种“经济学词典”中找到对它们的解释。我们将“粗放”和“集约”无论同增长方式联系起来,还是与其它两对概念硬划等号都显然是不合适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粗放”和“集约”这对概念理解上的混乱是由来已久的。比如,有人在谈到这两对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作过这样比喻:“农业上粗放经营,通过耕地面积的扩大来增加产量,这就是‘生产场所的扩大’,是属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采用新技术措施,进行精耕细作,就会‘提高生产资料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农业上的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由此可见,是否采用新技术,劳动生产率有没有提高,是划分内含与外延、集约与粗放的扩大再生产的共同标志。”[①b]这种看法正是把这两对概念的本质区别搞混了。严格来说,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都与资源的一定配置方式有关,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然而,农业上的粗放经营是土地相对于资本和劳动的扩大,是资源配置比例的变化。这和马克思讲的“生产场所的扩大”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技术条件和其他因素(包括资源配置因素)一定情况下,靠生产要素投入量同比例扩大而造成的生产场所扩大。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场所扩大,并不是因为土地相对便宜而改变了资源配置比例,而是生产能力的扩展。而且粗放经营情况下,土地面积的扩大如果是以节约使用较昂贵的劳动和资本为前提,这种方式就可以通过降低投入成本而提高投入——产出比,因而属于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变化带来的产量的提高是合理配置资源的效应,不是“外延型”而是“内涵型”扩大再生产。我们不能仅仅因这种“场所扩大”而把它误认为是“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反之,集约经营情况下,如果技术条件不变,靠提高劳动和资本的密度来提高的产量,从一定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要素投入量带来的,因此,也可以把它看成外延型增长,尽管场所没增大。当然,精耕细作往往与采用先进技术分不开,但技术提高因素带来的产量是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属于“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带来的产量,属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这两种效应的区别不能因并存而消失或等同。换句话说,在其他条件(包括技术)一定情况下,“粗放”和“集约”式经营都可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扩大生产能力,并带来产量的提高,因而又都可能是“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因此我们说,判断这两对概念的标志,不是看是否采用新技术,也不是看是否提高生产率,而是看要素之间比例不同,还是要素的作用不同。要素比例变化带来的产量是资源配置效应,而要素质和量的不同是要素“内含”和“外延”效应。无论是否改变技术条件,它们都存在各自不同的本质特征和不同的效应。
综上所述,目前理论界在解释“粗放”和“集约”这一对概念上混乱的原因在于理解上误区;这一对概念本身用在解释经济增长方式上不妥。如果我们采用马克思的“外延”和“内涵”或“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这样的概念,或许会避免上述混乱。
二、何谓“转变”?
“转变”之所以必要,不少文章中是这样解释的:后一种增长方式比前一种增长方式的投入——产出比高,是一种与先进技术相结合的、进步的增长方式;而前一种增长方式的投入——产出比低,是一种浪费的、低效落后的增长方式。甚至有人用这样的公式表达:
粗放型=要素投入量型=低效
集约型=要素生产率型=高效
于是“转变”显然就是以“先进”取代“落后”的问题。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其实,在任何社会条件下,“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都是并存的。在经济增长学中,它们是共同决定经济增长率的两个变量:经济增长率=要素投入增长率×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这两个变量反映的是生产能力的量和质的两个方面。因此,这二者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更不能以一方面取代另一方面。
从理论上看,经济增长实际上是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的函数。它一方面反映经济增长中生产规模在“外延”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反映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无论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没有把它们对立起来。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外延”和“内涵”这两种形式都首先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促进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量和质的区别。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单单资本量的增加的同时也就包含资本的生产力的增加。如果说资本的量的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那么反过来说,一个更广阔的、扩大的资本主义基础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再积累,即使它最初只表现为生产在量上的扩大(同样的生产条件下投入更多的资本),但在某一点上也总是在质上表现为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具有较大效率”[①c]。
用西方经济学主流派新古典(最右翼学派)的理论观点来看,在任何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生产规模的“外延”式扩张的区间。这种扩张的边界是:边际成本=边际收入。换言之,在生产技术一定的条件下,只要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成本小于它所能带来的收入,生产规模的继续扩大就是经济的。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某种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使要素投入的边际成本(从而平均成本)下降,还会使边际收入提高,从而带来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当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边际成本提高,从而超过边际收入的情况下,厂商减少使用生产要素,将资本更多地投入改进技术条件等方面来提高要素生产率,并以此来提高边际收入。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代替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仅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或成本)情况,还要看它们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只有成本最小而产量和收入最大才是最佳的选择,才能带来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在增长经济研究史中,关于增长方式问题出现过至少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积累决定论”,另一种是以战后新古典的“索洛增长模型”为基础的“技术决定论”。前者强调资本积累是生产能力扩大的“源动力”,后者则把技术进步看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实践上看,这两种观点的产生是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在亚当·斯密时代和他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本的积累速度是一致的:积累越快,增长越快。因此在理论上,一直到现代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都没有放弃积累作为增长源动力的认识基础。然而近几十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发现,战后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积累速度。这种现象被归因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技术进步的作用。1956年美国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索洛用“余值法”计算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增长中有83%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如此看来,资本积累在增长中的作用小的可怜。从“技术决定论”思想基础出发,索洛在1957年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Tofal Factor Productivity)分析方法。这样,一方面对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大大得到了推动,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决定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尽管在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然而仍然还没有真正解决“技术进步内生化”问题。他们把技术进步归结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无法解释它的发生机制。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还表明,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是同向变动的;而且两种增长方式总是交替发挥重要作用。只是到了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这并不意味要素投入量不再起作用了,而是在绝对量上继续增长。
“技术决定论”只从量的测量上确定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没有看到技术进步也是积累的质的方面。且不说索洛的“余值法”计算技术进步的作用是否严格,只从量的测量上来确定它的作用大小是不够的。技术进步本身不能孤立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首先,没有生产要素一定的投入量,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用于生产;其次,从一定时期看,技术进步的突出作用也是以这些国家长期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的积累作为基础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生产资源和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力素质的变化都使得要素投入量的“外延”式扩张遇到了成本不断提高的障碍。因此,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依赖手段。如果要把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变化称作“转变”的话,也只能是从以“外延”增长方式为主导向以“内涵”增长方式为主导的转变。我们可以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看作以“外延”式增长为主的历史阶段,将战后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看作以“内涵”式增长为主的历史阶段。这种转变一方面不能排斥或否定要素投入量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要素资源变动的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可见,“转变”不完全是以人的主观判断(“先进”与“落后”)为转移的。
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是一种“源动力”,不会因它的技术条件不同而改变。在技术条件、资源配置和销售等条件既定情况下,资本积累以“外延”的形式来扩大生产能力,就是它的量的作用。一般在生产资源充足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利润较高,因而增长速度也比较快。资本积累质的作用是通过“内涵”的形式来扩大生产能力,包括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管理和组织方式(包括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和合理的资源配置等等。一般在生产资源相对稀缺或趋于昂贵,而社会进步和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这种“内涵”型增长尤为突出。
由此可见,要素投入量(或“外延”)扩大型与要素生产率(“内涵”)提高型增长是资本积累量和质的不同,不是好与坏的区别。我们没有理由取其质而否其量。
三、怎样提高要素生产率
关于怎样提高要素生产率,目前较普遍的看法是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中的技术构成。更具体的建议有(1)广开财源引用新技术;(2)控制人口增长;(3)加大教育和科研与开发的投入,等等。这些建议都是很好的,但在短期内实现恐怕还很困难。这涉及发展问题,尤其是人口和教育问题。经济增长是生产能力和产量的逐年增长,因而必须考虑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技术进步并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唯一途径。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单靠发展技术来提高生产率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综合国力水平条件下,普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利于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资源。我们首先会遇到的是资金短缺问题,其次是劳动力素质问题。这些问题即使能够在短期内解决,我们也很难在“九五”和2010年前将我国众多的人口数量降到理想的水平。这样,在普遍提高技术构成后,必须造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不但是一种资源浪费,更严重的是由此带来的就业压力很难使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平衡。这样的经济增长将是极不稳定的。
其实,提高要素生产率有很多种方式。现代经济增长学中关于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归纳为三个方面:(1)资源配置;(2)规模节约;(3)知识进展。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也论述过:“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的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①d]而且,马克思对技术条件不变情况下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如分工、协作和自然条件的改变的作用。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述了采用新技术的成本限度,比如马克思在谈到机器大生产时曾指出:“……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如果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小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②d]
靠提高技术密度尽管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但如不考虑有关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成本,不顾现有的资源状况,那么技术所能带来的投入——产出比也是有限的,甚至会发生反方向变化。
从宏观看,采用哪种方式更有利于加快增长,一方面取决于一国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资源的利用程度。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至少有三种情况:
1.在现有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采用“外延”式投资,可使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成本较低。这种增长,因为生产资源丰富,成本较低,一般以“外延”式扩张为主。
2.如果现有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但就生产要素的组合来看,社会产品总量却不是最大的。这时调整生产结构,改善资源配置,经济仍可增长。这种社会总产品产量增长方式就是资源配置效应带来的“内涵”式增长。
3.如果现有的生产资料和技术已经得到充分利用,而且资源配置正确,产量和产值都达到了最大化水平,这时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提高生产资源的素质,可使原有的生产能力的水平得到质和量的提高、生产转移线向更高的生产资源和技术水平扩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技术密集型”增长方式,是“外延”与“内涵”相结合的并以“内涵”为主的增长方式。
在现阶段的中国,技术、资金、现有资源和劳动力素质正处在多层次和普遍较低的水平上。在实践中,怎样合理配置、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生产能力是我们首先应考虑的大问题。我们应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和文化水平,根据各地区、各个企业的不同情况,一方面更多地、更有效地采用非技术性方法提高要素生产率,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众多的、文化素质较低的人力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尽最大努力,积极开发和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逐渐改变我国生产技术落后的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浪费和重复建设的浪费,才能真正实现生产要素的提高,并加快经济增长。
注释:
[①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92页。
[①b] 罗季荣:《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第122页。
[①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96页。
[①d][②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428和430页。
标签:生产率论文; 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经济论文; 内涵和外延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社会再生产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