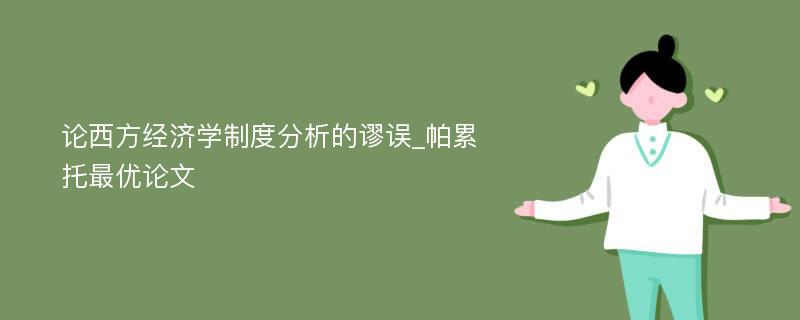
论西方经济学制度分析之谬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谬误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制度,是指社会生活中一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总和,其中包括法律、规章、条例、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等。本文旨在说明:1.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所从事的制度分析,在基本思维路径上走错了方向;2.虽然罗尔斯试图扭转上述错误方向,但罗尔斯自己所从事的制度分析也同样走错了方向。
一
自边泌提出功利主义学说以来,社会科学家普遍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得最大幸福的就是“好事物”,反之即为“坏事物”。于是,在制度分析上,社会科学家们也就自然认为:1.若某种制度比其他所有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这种制度就是最优制度;2.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从理论上努力寻求最优制度并促其实现。
然而,纵观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为何众多学问家寻求千年福王国的努力总是失败?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终究未能以其教义一统天下;儒家“仁义”、道家“清静无为”、墨家“兼爱”种种学说也未能征服世界;摩莱里、马布利、莫尔、康帕内拉当年一个个对理想社会的描绘如今都被公认为梦想。亚当·斯密似乎棋高一着,打出一番如意算盘:让人们在市场制度中充分展开自由竞争,让每一个人在市场制度中直接追求私人利益而最终间接实现最大社会福利,而国家只起“守夜人”作用。然而,这番如意算盘面对如下五大难题却不得不落空。这五大难题是:1.自由竞争本身必然生出垄断;2.自由竞争免不了会带来“外部性”(包括外在经济和外在不经济);3.一旦涉及公共产品(例如国防)生产,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立即失效;4.在市场上参与自由竞争的有关各方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由此必然带来委托、代理之间的相互欺诈;5.政府成员既不比普通公众更卑鄙,也不比普通公众更高尚,只要自我判断收益大于成本,他们就会利用“守夜人”身份谋求自身利益。
自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出发深入探讨,试图修补斯密的“如意算盘”,以便找到一种完美的最优制度结构。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能使整个社会所有稀缺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从而实现社会总产值最大化,即表明在经济制度上实现了社会最优。
庇古认为,只要通过政府干预克服外部性(包括克服外在经济和外在不经济),使社会生产的每一个部门边际私人纯产值都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即能实现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从而实现社会最大福利。
帕累托在庇古基础上提出“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最优”,认为:只要使一切可能存在的“帕累托改进”穷尽,从而到达“帕累托最优”,即意味着寻找到了社会最优或实现了最大社会福利。
科斯认为,在产权明晰前提下,只要能最大限度节省社会成本,或最大限度节省社会交易费用,就实现了最优制度结构。
布坎南认为,一切“自愿”(或“同意”)达成的交易,都是有效率的,只要通过立宪民主,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愿”(或“同意”)交易,即实现了社会最优。
与上述各个学问家略有不同,凯恩斯试图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操纵宏观经济过程,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最优制度结构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
罗尔斯精明地发现,以上种种寻求最优的努力,统统都着眼于“结果”最优,这肯定无法实现。他试图撇开“结果”,而寻求“过程”最优。他认为,只要让人戴上无知面纱(或躲在无知之幕背后)建立起合乎正义的“自由”与“差别”二原则,即可保障“过程”最优。他同时以为,这是人类唯一可能实现的最优制度结构。
实际上,自新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的上述种种分析,都内涵着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二
众所周知,自新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的以上各种学说的倡导者,都共同承认主观边际效用价值说,即共同承认:1.社会生活中,各个人具有不同偏好集;2.个人是自我主观价值判断的唯一源泉;3.在各个人之间,主观价值不可比较、不可通约、不可加总。由这三个命题的总和,又必然推导出: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个人都必然是、且只能是具有自我主观理性的以自我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于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在本来意义上的基本格局就是:任何个人,不论置身于社会何种位置,都必然只能站在自我本位立场上,运用自我既有的知识结构,为尽可能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而采取各种自以为是的游戏(即博弈)策略,来与他人、与社会(以及与自然)开展各种游戏(即博弈)。
进一步,我们又可自然而然地推导出:古往今来的任何学问家——包括任何一个在理论上寻找最优制度结构的经济学家,同任何他人一样,也必然是具有自我偏好集、具有自我独特主观价值参考系、拥有自我主观理论的以自我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任何一个理论家,特别是,任何一个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他以为自己是站在芸芸众生之外,为芸芸众生寻求最优制度结构时,他即把整个社会的基本格局以及把自我在整个社会基本格局中的位置搞错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是:1.整个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大牌局,其中每一个人都是大牌局中的一个普通参与者。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大牌局之外或凌驾于大牌局之上来设计、规范或指导大牌局如何运作。2.大牌局的任何个人都分别具有自我独特的主观价值参考系,每一个人都分别是自我主观价值判断的唯一源泉,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其余任何个人(更不用说代替其余所有人)作出主观价值判断,从而在此基础上确立最优制度结构。因此,任何学问家(包括宗教领袖)或任何经济学家,试图代替社会中所有人寻求最优制度结构,都只能是妄想。
当代西方经济学,就其主流而言,其主张归纳起来不过是:1.通过市场制度运作实现社会稀缺资源优化配置,或实现社会总产值最大化;2.通过政府干预实现优化的宏观经济目标。这两种主张都蕴含着具体的优化制度安排。然而,面对着社会中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不同偏好集、不同主观价值参考系,面对着所有各个人之间主观价值不可比较、不可通约、不可加总,面对着政府官员可能采取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面对社会生活中所有各个人都分别是具有自我主观理性的人本主义者,“阿罗一般不可能性定理”业已证明:不论采取何种程序,一般说来,都不可能从个人选择次序推导出社会选择次序。即:一般说来,不可能找出符合所有个人偏好的最优制度安排。
所以,微观经济学所追求的社会稀缺资源最优化配置,社会总产值最大化的最优制度结构,只能是新时代的“乌托邦幻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所追求的“看得见的手”也同样不可能采取社会最优的制度安排。
如果说,微观经济学因谋求社会总产值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因寄希望于政府官员用“看得见的手”造出一个合乎理想的经济格局而在基本理论构架上陷入谬误的话,那么,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则同时犯下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双重错误,既错误地谋求社会总产值最大化,又错误地寄希望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实现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处处相等。
至于以帕累托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其“改进”、“最优”的思维路径也同样错误。
帕累托“改进”与“最优”的实质在于:在既有资源条件下,产出越多越好(或者,在既定产出条件下,投入越少越好)。然而,在动物保护者眼里,捕鲸船效率越低越好。在主张戒烟者看来,烟草生产效率越低越好……。面对这一切,“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以及由这两者推导出的“契约线”、“总效用边界”等等)实在是缺乏解释力。退一步说,即使把这一切“特殊情形”撇而不论,在一般或普遍意义上。“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以及“契约线”、“总效用边界”等等)分析也仍然是“中看不中用”。因为,如前所述,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个人都是、且只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就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个人而言,都总是以自我独特偏好集、自我独特主观价值参考系为自我存在之本。举例来说,战场上甲乙两个伤员,面对一副担架,只能抬走一个伤员。旁观者(例如帕累托或艾奇渥斯,或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无法判定,在此条件下,何谓帕累托改进,何谓帕累托最优。这时,可能出现如下六种情形:1.甲乙两人都偏好利他,先抬走任何一位伤员,都会使未被抬走那位伤员获得福利增进,而同时侵害被抬走那位伤员福利;2.甲乙两人都偏好利己,先抬走任何一位伤员,都会使被抬走那位伤员获得福利增进,而同时侵害未被抬走那位伤员福利;3.甲偏好利他,乙偏好利己,但先抬走的恰好是甲,于是同时侵害甲乙两人福利;4.甲偏好利他,乙偏好利己,先抬走乙,使甲乙两人都获得福利增进;5.甲偏好利己,乙偏好利他,先抬走甲,甲乙两人福利增进;6.甲偏好利己,乙偏好利他,先抬走乙,同时侵害两人福利。即使面对这一仅涉及两人的六种情形,旁观者也难以判定究竟应当采取何种行为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或才能到达帕累托最优。更何况,当涉及社会生活中千百万人利害关系时,几乎处处信息稀缺,谁又能判定如何才能导致帕累托改进,如何才能到达帕累托最优?特别是,倘若甲乙两人都偏好利己,或甲乙两人都偏好利他,在这两种情况下,按照帕累托学说,不抬走任何一位伤员即是帕累托最优。倘若伤员不抬走的结局是死亡,则在此条件下,所谓帕累托最优意味着让两位伤员等死,这岂不显得荒诞可笑?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本真的行为逻辑决不是先求解出何谓帕累托改进、何谓帕累托最优再去行动,而是、且只能是依照自我主观价值参考系,根据自我知识结构,采取自以为是的游戏策略,去谋求尽可能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在这种适合于任何个人的行为格局中,所谓“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实际上毫无用处。
如前所述,布坎南正是由于发现新、旧福利经济学内含着逻辑前提谬误,所以才提出以“自愿”(或“同意”)作为类似于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的效率标准,并力求以立宪民主来保障自愿充分展开,从而实现具有最大效率的社会最优制度结构。
的确,在许多场合,人们都可以观察到,自愿交易(例如,在双方自愿前提下,农夫用小麦与铁匠交换农具)能为交易双方带来好处(即实现帕累托改进或到达帕累托最优)。然而,以上见解并非毫无问题。请看以下各例:
1.某人去某家商场按商场标价买一件自我感觉满意的衣服,这是典型的买卖双方“自愿”(“同意”),最初一看,似乎可把交易结果称为帕累托改进。然而,当购衣者买好衣服逛第二家商场时,发现与他业已买定的同种衣服相比,第二家商场价格便宜一半。这时,我们还能说先前的自愿(同意)交易结果是帕累托改进吗?
2.某人自以为廉价地买到了一大筐水果。实际上,卖水果小贩克扣了他许多重量。若依实际重量计,他买得太贵,吃了大亏。这样一来,就有两种情况需要考虑:第一,若他事后复秤,发现吃了大亏,我们能说他自愿交易结果是帕累托改进吗?第二,若他事后不复秤,一直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于是,在主观自我感觉上,他同真正占了便宜的小贩一样以为自己划得来,从而错误地把自愿交易结果看作帕累托改进;但从客观上说,这显然并非帕累托改进。问题是:在理论上,我们究竟应顺应他的主观感应把这判断为帕累托改进呢?还是应根据客观事实把这看作非帕累托改进?
以此为例可知,布坎南等经济学家以“自愿”(“同意”)作为帕累托改进判别标准,显然不够严谨。1.有关各方都自愿(同意)采取的交往或(交易)行为,并不一定能导致帕累托改进;2.并非自愿(或并非同意)采取的交往(或交易)行为,也可能导致帕累托改进;3.对“自愿”(“同意”)本身难以给出经济学意义上的精确定义;4.结论是:不应把“自愿”(或“同意”)作为社会状态是否改变称为帕累托改进的判别标准。
在布坎南心目中,最能体现自愿交易好处(从而最能增进人们福利)的形式是“俱乐部”这种制度结构。所谓俱乐部,它的特点是:当事人是不确定的,任何人都可自由加入进来,又可自由退出(即可“用脚投票”)。这实际上就是:任何个人,只有当他自我盘算觉得有利时,才会加入俱乐部,否则即退出。
其实,经济学家们发现,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俱乐部。请看:某个人摆摊卖苹果,凡愿光顾他摊点、按双方议定价格买苹果(即加入苹果俱乐部)的人(包括卖者和买者),都必定是认为买卖对自己有利的;凡觉得按买卖双方议定价买卖苹果吃亏的人,都可以不加入(或“用脚投票”退出)苹果俱乐部。从购买角度来看,也可以组成“购买者俱乐部”。例如, 10 个买苹果的人组成俱乐部去低价批发一大箱苹果再分成10份,就可能会比单个人购买划算。
既然俱乐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何不可能处处运用俱乐部规则?
由于人们所面对的各种公共选择具有不同特征,因此,处处运用俱乐部规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凡是不可能做到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公共选择场合,都不可能运用俱乐部规则。试设想,几位普通消费者能组成一个购买原子弹的俱乐部吗?几位卖菜小贩能组成一个选举皇帝的俱乐部吗?
除了不能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场合不可能实行俱乐部规则外,即使在可实行俱乐部规则的场合,也免不了:1.俱乐部中人为谋求自我利益而采取狡猾策略暗中破坏俱乐部规则,使加入俱乐部的其他人的福利受到损害。例如,在前述“苹果俱乐部”中,卖苹果的小贩暗中克扣重量,或将坏苹果埋藏在好苹果下面按好苹果价格卖出去,使自己获利,使买者受损。2.在有些俱乐部,除了俱乐部成员通过狡猾游戏策略相互侵害外,还可能会出现下列情况:业已加入俱乐部的成员感到不仅无利可图,相反却遭受到自我福利损害,本想退出俱乐部,但退出成本极其高昂,以至于退出成本大于留在俱乐部中遭受到的自我福利损害,于是,只好被迫留在俱乐部中。因此,任何人都切莫以为,俱乐部体制自身在运作中不会出毛病。也不要以为,只要有了俱乐部,就万事大吉,就会确保所有加入者都必然获得自我福利增进。
可见,俱乐部并非一定如布坎南所设想的那样,必定是能增进加入者福利的最优制度结构。实际上,事情的本质仍然是:任何个人,不论是否组织或是否加入,是否退出俱乐部,归根结底,都是在采取自以为是的游戏策略,以谋求尽可能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在此基本格局中,不可能存在具有普遍、一般意义的“最优制度结构”。可见,任何一种学说,只要不首先把社会中所有个人(包括提出学说的学问家本人在内)如实地看作具有自我主观理性的博弈者,而试图旁观地站在芸芸众生之外代替所有个人寻求具有普遍、一般意义的最优制度结构,则这种学说必定会因其前提错误而无法成立。
三
除以上所述各家学说外,罗尔斯虽然机敏地意识到,由于每个人之间主观价值(或福利)不可比较,不可加总,因此,要想从“福利结果”上去寻求最优制度结构必然是“此路不通”。然而,由于他试图把自己放在芸芸众生之外去寻求一种体现为“福利选择过程”的最优制度结构,这就注定了他的学说仍然免不了陷入谬误。
罗尔斯认为,既然无法在选择结果上求得美好,就不要再去选择结果的美好,而去寻求“选择过程”的美好。只要选择过程是美好(即合乎正义)的,则不论结果如何,所有参与选择的个人就都是自愿接受的。假定有四个人偶然聚在一起玩扑克牌,倘若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与自己牌技相比差距如何,也不知道自己将会被分到哪些纸牌。在此条件下,若站在这四个人旁边的发牌者故意把好牌发给某些人,而同时又故意把坏牌发给另一些人,则这种游戏就是非正义的。反过来,若发牌者随意无偏颇地发牌给四个人,即使一些人得到的牌好,另一些人得到的牌坏,即使最终结果是四人之中有输赢,或甚至输赢差距很大,则这种游戏也是正义的。
罗尔斯认为,任何个人出生于世,都是偶然地加入了一场与他人一同进行的赌牌游戏。这游戏是否合乎正义,不在于赌博结果谁输谁赢,或谁输多少,谁赢多少,而在于游戏规则是否公道合理。因此,所谓建立美好社会,不过就是要建立一种合乎正义的游戏规则(或使选择过程合乎正义)的社会。
然而,在既有的现存社会中,每个人都业已站在了一个特殊位置上,有人位置站得好(例如富贵者、身体健壮者),有人位置站得不好(例如贫寒者、身体先天残疾者)。在此条件下,若让人们从既有位置出发去议定规则,肯定无法达成共识。每个人都会主张实施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而否决对自己不利的游戏规则。倘若如此,则合乎正义的游戏规则就会胎死腹中,尚未被议定出来就宣告破灭。
面对上述难题,罗尔斯的设想是:要想议定出合乎正义的游戏规则或合乎正义的社会契约,其前提是,所有参与社会游戏的人在游戏开始前都必须戴上无知的面纱(或都必须躲在无知之幕背后)。这样制定出的游戏规则或社会契约,必定是合乎正义的,且必定是对任何个人都无偏颇的。
那么,合乎正义、对任何个人都无偏颇的游戏规则(或社会契约)内容是什么呢?罗尔斯认为,基本内容应包括两条,这就是:1.平等自由原则;2.有利于弱者的差异原则。所谓平等自由原则,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在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方面相对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具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且每个人在自由的权利上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干涉别人的自由,也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自由权利去压制或取消另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所谓有利于弱者的差异原则是指:“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要得到调整,以使这些不平等(a)既能合理地预期到为每一个人的利益服务,(b)又能伴随着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位。”
罗尔斯的平等自由原则能实现吗?让我们借助经济学家哈特提出的例证作简单分析。
假定某人有一块私有土地,根据罗尔斯自由原则,他就拥有不允许任何人穿越他私有土地的自由;假定另一个人是一位旅行家,同样根据罗尔斯自由原则,他拥有到处随意走动的自由。现在,倘若旅行家想穿越私有者土地,又当如何实现平等的自由?结果是,作为“美好的正义社会”根本基础的平等自由,将不得不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困境:若让旅行家自由穿越私有者土地,他就压制了土地私有者的自由,或使土地私有者失去了自身的自由;若不允许旅行家自由穿越私有者土地,就反过来压制了旅行家的自由,或使旅行家失去了自身的自由。于是,归根结底,所谓“平等的自由”,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一样,都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
除平等的自由无法实现外,作为罗尔斯总体设想的“正义社会”根本无法实现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即使把“正义社会”的所有游戏规则(或社会契约)统统都完美地制定出来,也无法插进人类历史。实际上,在人类历史运作过程中,不论何时,每一个游戏者都总是在按既有规则游戏着,又在努力把既有的游戏规则改变得更有利于(或最有利于)自己。倘若有人(例如罗尔斯)向着历史喊一声“暂停!从此以后按新规则游戏!”人们会停下来吗?会接受新规则吗?特别是,所有那些自以为按既有游戏规则游戏比按罗尔斯新规则游戏对自己更有利的人,他们不仅不会欣然接受罗尔斯新规则,而且必然会为保护自我既得利益而向罗尔斯新规则宣战。只有那些自以为按罗尔斯新规则游戏更划算的人,才会赞许推行新规则。于是,接下来就是这两类人之间的争斗。争来斗去,表面看来似乎是要不要实行新规则之争斗,实际上仍然是:各个人分别为谋求实现自我主观价值而奋斗。即使打着实行罗尔斯新规则旗号而争斗的人们胜利了,作为胜利者,他们也不会实行罗尔斯新规则。因为,他们的本意是为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而不是为谋求“正义”。
因此,说到底,罗尔斯的如意算盘,只要往人类历史身上一碰,就必然会被碰得粉碎而落空。
其实,我们在前面早就指出过,加入社会生活的任何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主观价值参考系,都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自以为最优的游戏策略去谋求尽可能充分地实现自我主观价值(或自我福利)。既然如此,则每一个人就都不可避免地既要谋求尽可能对自己最有利的“社会选择结果”,又要谋求尽可能对自己最有利的“社会选择过程”(或社会选择规则)。
因此,在一般或普遍意义上,谁也不要指望:1.通过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谋求实现最优的社会选择结果;2.通过制定罗尔斯正义两原则,谋求实现最优的社会选择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