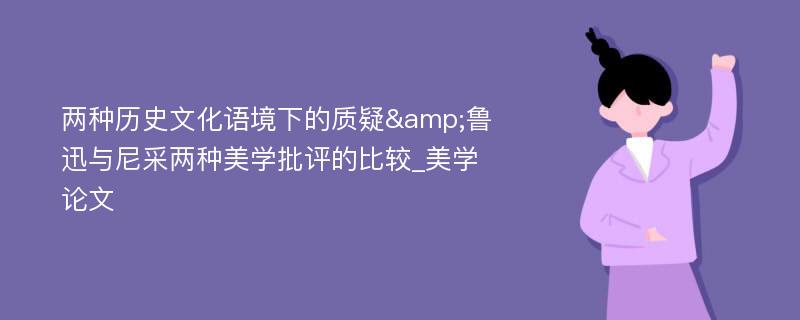
两种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追问——鲁迅、尼采的两场美学批评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鲁迅论文,两种论文,语境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现代中国对尼采的接受史中,鲁迅和尼采的关系历来被视为重头戏,并在研究中取得相当成果。美中不足的是,人们侧重从人生哲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视角来认识他们的关系,而较少从艺术哲学(或曰美学)层面来把握他们之间的契合与冲突,更少有人关注他们悲剧观之关系。悲剧观作为重要的美学概念在这里提出,是因为由此我们可以探寻到生存主体精神深处最本真的对于生命的体认与质询。从悲剧观层面来观照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能将此研究推向深入。
这一角度对于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也有意义。长期以来,“仅仅从一种例外的社会性不幸来理解鲁迅的悲剧观”,浅化了鲁迅的重要思想背景,这“是鲁迅美学思想不能深化的原因”。[1](P275) 限于篇幅, 本文着重从美学层面谈谈鲁迅尼采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所分别开展过的美学批评活动,藉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悲剧人生面前共同表现出对生命之“动”的眷注,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生命气象。
二
通过对鲁迅和尼采人生哲学的综合观照,我们不难认识到,他们实践人生的根本方式是对生命悲剧性的沉潜与超越,当然这沉潜不同于沉湎,超越也不是超脱,如果再从美学角度对他们进行思考,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鲁迅和尼采分别进行过一次规模不等、出发点不同,但同是美学效果层面上的批评行动,即尼采对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悲剧“净化(Katharsis)”说的批评和鲁迅对朱光潜“静穆”美学观的批评。我认为,这两次批评行动分别基于尼采和鲁迅对悲剧效果的理解和态度,切近他们的悲剧观,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比较是有必要的。
西方传统美学中对悲剧效果的解释,以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为代表。亚氏认为,悲剧能唤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进而使人的情感得到净化。这种观点尽管有争论,但它一直是西方悲剧美学理论中的权威。而尼采根本不作如是观,他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于悲剧效果还从未提出过一种解释,听众可以由之推断出艺术境界和审美事实。”[2](P97) 意思是说,历史上从没有把悲剧当作最高的艺术来欣赏,而是将之排斥在美感领域之外。他问道:“真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怜悯和恐惧因悲剧而得以宣泄,使得听众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家去么?精神历程可以减少人的恐惧和迷信么?”[2](P201) 他反对从病理学或伦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悲剧效果,而强调悲剧的“超越”性与纯美学境界。他认为怜悯、恐惧和崇高不属于悲剧快感,只是人对现实的自然反应。悲剧的伟大力量在于它能鼓舞人,使人以主动姿态迎接人生苦痛,并享受悲剧带来的愉悦感。
尼采在对希腊精神的观照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悲剧诞生于日神和酒神的互动关系中:“悲剧中日神因素和酒神因素的复杂关系可以用两位神灵的兄弟联盟来象征: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终说起酒神的语言来。这样一来,悲剧以及一般来说艺术的最高目的就达到了。”[2](P95) 尼采在他的哲学中明显倾重于酒神精神,他说“酒神因素比之于日神因素,显示出永恒的本原的艺术力量。”[2](P201) 在悲剧中,狄奥尼索斯是背景,阿波罗在上面镶绣华美的表象,而狄奥尼索斯在下面不断发出低沉的怨声。悲剧是一种在对立的势力中由酒神主宰的奇妙而危险的游戏。酒神最终是这场对立的胜利者,但日神也作出了贡献,它将悲剧中的悲剧因素发展成为戏剧,又将戏剧中的悲剧因素表达出来,它同是组成希腊精神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对《悲剧的诞生》的阐释中,一度出现了歧义:有人认为尼采是将日神的“梦”和酒神的“醉”、“统一”为对现世的逃避,有人从中读出酒神精神在全书中的卓越地位。这两种读法在现代中国的美学家中分别有所投影,前者以朱光潜为代表,后者则以李石岑为代表。(李石岑从“新民”之意和报国之心的角度解读《悲剧的诞生》,倡导以酒神精神扫荡颓靡之气,重振民族雄风,与朱光潜等以日神精神净化人心的“美学济世”截然相反。因与本文无直接关系,从略。)
朱光潜说:“在我心灵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3](自序) 他如此解释《悲剧的诞生》:“依尼采看,希腊人的最大成就在悲剧,而悲剧就是使酒神的苦痛挣扎投影于日神的慧眼,使灾祸罪孽成为惊心动魄的图画。从希腊悲剧,尼采悟出‘从形象得以解脱’(redemption through appearance)的道理。”[4](第二卷P554) 原来,朱光潜看到的是酒神的“挣扎”在“日神的慧眼”中变成了一幅可供欣赏的图画,从而他认为是日神精神整合了酒神精神,它在悲剧中的地位较酒神精神突出——尽管这远离了尼采的本意。朱光潜在1933年之前表示:
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都是逃避的手段:酒神艺术沉浸在不断变动的漩涡之中以逃避存在的痛苦;而日神艺术则凝视存在的形象以逃避变动的痛苦。[3](P148)
鉴于对《悲剧的诞生》的如上认识,朱光潜于1935年12月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提出了“和平静穆”是“诗的极境”,是美的最高境界。他的“静穆”是超现实、超功利的,是一种置身世外,无视是非、善恶、忧喜、功过的和平之境。这跟他重视日神精神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尼采的日神精神作为外来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激活了本存于中国文化结构内部的士大夫的隐逸情绪。一般认为朱光潜的“静穆”观来自西方传统美学中的“静穆”和“净化”说,这很有道理。因为朱光潜对《悲剧的诞生》的解读根本违背了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倾重,自然会走上西方传统美学的路子,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尼采对传统美学的背叛。
鲁迅在当时批评了“静穆”美学观。他认为“历来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静穆的’”。[5](第六卷P430) 还举例说明了艺术的“反静穆性”。应该看到, 鲁迅此举无疑带有明显的社会功利目的,但从纯美学角度看,这场批评行动正源自他对生命悲剧性的独到看法。他通过对“静穆”的反拨与责难,树起了生命之“动”的旗帜。这与尼采的酒神精神形成了内在的的对应。
所谓生命之“动”,即肯定生命意义,弘扬生命意志,正视悲剧人生,注重一种“动”的生存状态及由此而产生的悲剧之“动”的快感。对尼采来说,这种眷注既表现为对希腊精神中斗争精神与献身精神的阐发与继承,也表现为象征“动”的酒神精神逐渐摆脱日神精神的笼罩,并成为权力意志的主题精神;对鲁迅来说,它既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投入性关注和对以“静”为本位的传统美学精神的反叛,又表现为他在生命哲学和美学思想上呈现出“反抗绝望”的精神和勇气。
鲁迅尼采都认为,悲剧自身的深刻性与悲壮感不允许生命个体做无意义的逃离。正如鲁迅所说:“悬虚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5](第六卷P428) 正视生命的苦痛,才能真正深入本真意义上的生活,体验到生命之“动”的悲剧美感,悲剧效果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全面实现。
三
尼采和鲁迅的如上两场批评从悲剧效果层面展现了他们悲剧观的契合与冲突,体现出他们对生命之“动”的悲剧性眷注。这一结论可从比较中得出。
相同点:1、它们都源自鲁迅和尼采对生命悲剧性的深刻体认方式,即强调意志、肯定生命创造力。尼采在反对“净化”说时,特别强调了悲剧对“恐惧和怜悯”的超越。他在推崇酒神精神的同时,感到真正的悲剧情感“既被亚里士多德误解了,更被我们的悲观主义者误解了”。[2](P334) 他认为, 肯定生命就不应该片面强调悲剧的“净化”作用,而要在悲剧体验中得到酒神式快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悲剧的“净化”作用即是对生命意义的放弃及对人生苦痛的浅层次理解——“净化”说远不能涵盖悲剧的意义和效果,尽管尼采确实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悲剧的效果正在于此并且仅在于此。”[2](P97) 可见,他的批评以正视生命悲剧、肯定生命意志的根本态度为前提;鲁迅批评“静穆”观时,认为朱光潜的“极境”是“虚悬”的,这与他本人面向黑暗的搏斗意识截然不同。“极境”在生命态度上忽视了悲剧“苦痛”的、“毁灭”的美感,“静穆”的旁观者的出路就是“绝境”。这里也强调了生命“投入”的精神指归及以此为基础的生命创造力。总之,这两场批评跟他们对生命之“动”的悲剧性眷注是分不开的。
2、它们都反对悲剧效果在阐释中被浅化、表面化的倾向。 “净化”说认为达到悲剧效果的只能是介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中间人的“过失”,并特别强调了情节的作用,“性格”倒是占了第二位。这种认识浅化了悲剧的深刻性,轻忽了悲剧体验中的非理性特质,从而悲剧对人类灵魂的巨大冲击和感染力受到弱化。尼采以悲剧使人“超越恐惧和怜悯”并产生“悲剧的喜感”的观点来反对之,其实在悲剧效果层面强调了悲剧固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基于对生命悲剧性的遁逸。他由尼采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推演出“演戏的和看戏的”两种人生观,认为自古以来大哲和大诗人如柏拉图、庄子、但丁等都不在“演戏”,而是在“观看”中实现人生的最高目的。而他本人则将“当看戏者”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此,生命的悲剧成了他人的悲剧。这种“幸福”的生命看客自然无法走进真正的悲剧情感,从而造成悲剧效果的表面化理解。由此看出,朱光潜忽视了酒神精神的形而上方面,认为悲剧的快感只可能是单纯的“日神式”的“静”的快乐。鲁迅的批评无意切中了这一对悲剧效果理解上的倾斜,在此意义上与尼采的批评异曲同工。
3、它们同时显示出鲁迅尼采的文化反叛性。 尼采以酒神冲动作为悲剧精神的内核,将悲观主义从悲剧中赶走,审视传统文化,怀疑并重估一切价值,以孤独者的姿态,于高处凝望芸芸众生,谕之以查拉图斯特拉的警劝,同时体验着生命悲剧的痛苦和欢乐;鲁迅则以大无畏的否定勇气,对历史和现实现象予以鞭策性描绘,在生存毁灭感和现实苦痛的双重夹击下,独自咀嚼着“苦的寂寞”,他的韧性战斗便是其悲剧精神的独特发挥。鲁迅尼采的生命方式和心灵选择及其对悲剧精神的呼唤,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了深远的美学影响。如上的两场美学批评同时从正面显示了这一点。
不同点:1、两者的出发点和历史意义不同。 “净化”说中的“净化”指向对灵魂的治疗,这首先是个道德问题。尼采反对之除了表明其“关于艺术的古老怀疑”,更有明显的“反道德”倾向,并试图由此建立一套全新的道德体系。这最终构成了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首要内容。鲁迅的批评也体现了其否定精神,但带有较明显的时效性。在特定的年代,此举强调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意识,确立在时代危机中的民众进取秩序。由于对“动”的提倡,这一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西方美学史上,由于拒绝采取道德的人生观,尼采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建立起将道德与审美过程分离开来的全新审美方式,这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美学史上,“静”的审美状态一直受到推崇:从老子的“涤除玄鉴”到王国维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静为本位的艺术精神形成了一个美学观上的“链”。李大钊在1918年说:“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6](P89) 鲁迅早已看到了这一由来已久的现象。他对“静穆”美学观的批评表面上指向具体的论争,实际上是对传统美学的挑战。
2、鲁迅对“静穆”美学观的批评除了显出他与酒神精神的沟通, 同时表明对“日神精神”不以为然。“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的哲学精神以及对社会美的关注使他极力反对日神式的观照态度,或者说,他认为日神式的梦境只能在梦中实现。在承认梦的酣美的同时,鲁迅担心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5](第一卷P159) 而尼采在批评“净化”说时,其理论前提是将希腊精神的二重性表述成“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结合”,并以此作为武器。换言之,尽管尼采在其全部哲学中倾重于酒神精神,但他对日神式的梦境并未完全抛却,这实际上给他的酒神精神镀上了一层梦幻般的光环——或许尼采的艺术人生真的离不开日神?那么,同是对生命之“动”的悲剧性眷注,何以形成上述差异呢?
1、社会和历史环境不同
尼采出现于资本主义急速上升的德国。当时由于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胆怯而私通”和工业不够发达强大的缘故,普鲁士君主制最终取得了统一德意志的胜利,从而贵族的特权仍然得以保存在德国社会。尼采哲学正是以这种社会和历史环境作为背景的。他情不自禁地以贵族后代自居,因而他的哲学多少代表了贵族的话语立场。他对“贱众”的蔑视与此有很大关系。他的“人类之爱”正表现了他与人类的对立方式: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读出了现代人的精神凋敝与病弱,并不厌其烦进行着鞭策性描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超人”的推出做了铺垫。他的人生实践方式也是以对立者和拯救者的双重身份沉潜于人生的苦痛与毁灭境遇,这似乎是个悖论,然而它在尼采身上却得到了矛盾的统一。因此尼采的悲剧乐观主义(喜感)是一种抽象的、高远的纯美学境界。
鲁迅处于中国社会历史激烈转型的时代。近代中国由于战乱及民族文化危机,民众陷入了不堪之境。在改革图治的一败再败中,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时代责任,一方面感到力不从心的苦痛。鲁迅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尽管他和尼采一样看到了人性残忍的一面。他的爱是复杂而具体可感的。鲁迅是在对社会、人群的留恋与愤恨之间,时而怒骂,时而打诨,并在精神上“彷徨于无地”;他是在对社会的强烈关注与人生毁灭感之体验的碰撞中,出现了与尼采不同的对于“死亡”和“朽腐”的“大欢喜”。
2、个性与经历有异
尼采一生孤傲,极少交友,跟社会保持着距离。他疯狂热爱音乐等艺术。为了寻找气候适宜的住处,自25岁至去世,他一直在国外。生活地点的变换更加激发他开辟出无所不包的视野。他对祖国的挚爱与仇恨由于这种距离感而更加深刻。在这种经历中,尼采的心灵尤其变得敏感和丰富。在这种审美的生命状态下,艺术成了尼采的心灵港湾。事实上,尼采一生反对理性形而上学,但时时不忘用艺术形而上来对苦痛的人生施以慰藉。艺术在现实世界的象征性与超脱感决定了尼采“悲剧的喜感”总是远离了社会美。
鲁迅出生在封建社会中的富裕家庭,曾在家族的没落中受尽冷眼,这使他从小关注社会现实。他在留学日本时弃医从文,是因为他看到中国人灵魂需要“疗救”;他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现实精神密切关注社会,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与尼采相反的是,鲁迅将艺术视为“撄人心”的兴奋剂,强调它的社会功用。鲁迅不无悲怆地感到,人生之苦岂是艺术能够了结?这种艺术观决定他醉心于展示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悲剧,由此而产生的“喜感”不仅是深刻的生命体验,而且是一种“含泪的微笑”,或“黑色的幽默”。它建立在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之上,进而表现为对整个人类生存处境的悲悯。在这种“喜感”中,鲁迅将他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融入了对普通人的爱心之中,由此而形成的复杂的精神生活是非常独特的。他的美学追求自然以此作为出发点。
标签:美学论文; 朱光潜论文; 尼采论文; 文化论文; 酒神精神论文; 鲁迅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