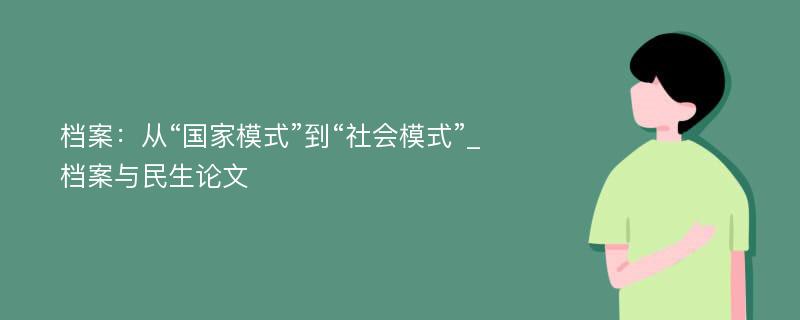
档案事业: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事业论文,档案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社会全面进步的30年,也是我国档案事业蓬勃发展、档案工作不断提升的30年。纵观过去30年,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我国档案事业正经历着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过渡的巨大变革。
1996年,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指出:“本世纪档案论述的主题是什么?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根据国家档案概念建立起来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化。”“档案事业在传统上是由一个国家建立,为这个国家服务,作为该国统治结构和机构文件的组成部分。档案理论因此在国家理论、模式和概念中建立了合法地位。现在情况不同了,20世纪末期公众对档案的认识,或至少对用纳税资金建立起来的档案馆的认识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档案现在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简而言之,他认为,档案理论和实践正经历着从“国家模式”(“国家范例”)向“社会模式”(“社会范例”)的转变。事实上,当前我国如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在经历着这种档案理论和实践的范式变迁。
“社会档案观”的形成
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指出:“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统一地管理机关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国家各项工作的利用。”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指出:“在档案工作统一管理之后,各级档案管理机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可见,建国初期人们对档案的基本认识是:所谓“档案”即是“国家档案”、“党政档案”;档案馆是党和政府的附属机构,而不是公共性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因而,党政机关之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档案不被认可、不受重视,普通民众更是难以步入档案馆的大门。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国家档案观”逐步悄然发生变化。1983年4月,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档案馆工作通则》规定:“档案馆是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基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该通则明确了档案馆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性质,也拓展了档案工作的服务范围。1987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时,档案界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档案工作是一项社会的公益性事业,而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政治性活动。因而,在《档案法》中,档案是指“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档案工作基本原则也从原来所提倡的“便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利用”发展为“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1996年修正后的《档案法》再次肯定了这一定义与原则。
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档案观”越来越为我国档案界所认可。许多有识之士撰文呼吁:还档案馆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的本来面目,传统的综合档案馆应该向公共档案馆转型,要强调档案馆的公益性、服务性、开放性。2001年杜长安同志在《上海档案》第1期发表了《打造真正的“公共档案馆”》一文,最早提出建设公共档案馆。2003年时任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档案馆馆长的刘南山同志在上海市第二届档案论坛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建设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公共档案馆》的演讲,2004年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开馆,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举办了“公共档案馆利用服务社会化研讨会”,自此国内掀起了研究和建设公共档案馆的高潮。2005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刚同志在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调研时特别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工作。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教授提出,档案馆应该基于“社会档案观”实行“亲民”战略。①
在“社会档案观”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档案部门将档案工作的重心从高层、宏观转向基层、微观,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科技、文化、生活领域,从党政机关转向企事业单位、社区、农村和家庭,从服务党和国家转向服务社会和老百姓。2003年9月的全国社区档案工作座谈会,2004年4月的全国农业和农村档案工作经验交流会,2005年4月的全国民营企业档案工作座谈会,2006年3月的全国档案馆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座谈会,2007年国家档案局杨冬权局长在“中国·沈阳家庭建档与和谐社会建设高层论坛”提出家庭建档这项工作有“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家庭、社会、档案工作,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上述档案工作重心的转移,说明了“社会档案观”的深入。
尤其是2007年9月,王刚同志对做好民生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2007年12月,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使“社会档案观”更具“以人为本”的理念。
“‘社会档案观’将公共档案馆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天地”。②“社会档案观”的形成是档案工作向从“国家模式”过渡到“社会模式”的思想根基和前提条件。
馆藏档案的多元化
1999年,赵跃飞同志在《中国档案》上发表了《未见平民史》一文,感叹在中国历史中几乎看不到社会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精神历程而导致了历史的残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平民丧失了历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平民几乎没有历史记录——档案。“在旧中国的档案中,基本上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记录,大量的普通百姓的历史记录被排斥在外,使大多数的历史档案有形无神,有骨骼而无血脉肌肉毛发。”③在古代西方,档案也从来只是“国王的安慰”和“君主的珍宝”,而不是人民的记忆。民主社会之前,档案馆只收藏记载统治者“丰功伟绩”的档案,而不保存反映普通老百姓“油盐柴米”的记录。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把这一现象称为“档案的空缺”。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批评档案工作者在收集档案时“偏心于社会权贵,而忽视卑微人群”。
随着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的增强,现在,“极少数公民会同意将他们交纳的大量税金用于资助其馆藏大多反映政府官僚活动的档案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的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④于是,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主席F.杰拉尔德·汉姆提出,档案应该“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霍华德·津恩呼吁,档案工作者要“创造一个反映普通百姓生活喜好、需求的全新的文献材料世界”。实践中,以加拿大的“总体档案”战略为代表,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将私人档案纳入国家档案馆收藏范围,让档案更充分地反映社会活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历史档案室计划到2008年年底为100个个人博客进行备份存档,到2010年年底对在新加坡注册的所有博客进行归档。
过去受“国家档案观”的影响,我国档案馆主要收藏党政机关形成的文书档案。例如,1986年2月国家档案局颁布的《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就明显表现出,重视党政机关形成的档案,轻视基层企事业单位形成的档案,尤其轻视普通民众形成的档案的倾向。以至于各级综合档案馆的馆藏几乎是清一色的“红头文件”。据上海市虹口区档案馆统计,在馆藏118,521卷档案中,反映政务内容的档案占84.6%,而反映科技、财务、艺术等内容的档案只占15.4%。⑤
20世纪末以来,“社会档案观”促使我国档案馆开始调整档案收集范围。全国各地档案馆一方面大力帮助基层社区、农村乡镇、民营企业、普通家庭等建立档案,并有针对性地接收部分社区档案、农村档案、民营企业档案、家庭档案进馆保存;另一方面加强与老百姓学习、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非行政类专门档案进馆保存。例如,沈阳市档案部门自2002年起连续六年在全市广泛开展“档案进家庭”活动,帮助13万户左右家庭建立了家庭档案。长春市档案馆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涉及100万余人的工人调配档案提前接收进馆。浙江省各级档案馆加强婚姻、房产、移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档案信息的收集,不断提高馆藏民生档案比重。截至2007年年底,全省已经接收婚姻档案的档案馆67个,占总数67%,共接收婚姻档案120余万卷;接收公证、房产、移民、山林延包等档案的档案馆72个。⑥许多档案馆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家谱、照片、书信、日记、合同、账本、粮票、布票、成绩单、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奖状等记录家庭生活、个人成长的档案材料。一些档案馆还着手采集口述档案。
2007年12月,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强调:“要积极调整馆藏收集范围,……建立面向民生的多元化档案资源体系。”馆藏档案来源与内容的多元化,是档案工作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体现。
档案服务的社会化
1794年法国穑月七日档案法令提出了“档案的人权宣言”——档案开放原则。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颁布了信息权法,公民利用档案的信息权成为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今天,个人档案用户人数占到西方档案馆利用总人数的80%左右。
过去,我国档案和档案部门一直被蒙着一层秘密性、政治性色彩,改革开放以后才慢慢揭开神秘的面纱。1980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1986年国家档案局发布了《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暂行规定》,为档案开放奠定了基础。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此后,《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1991年)、《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1991年)、《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1991年)等有关档案开放的法规、规定相继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档案开放的法规制度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档案馆不断拓展社会化服务功能,扩大社会化服务范围。2000年深圳市档案馆建立了全国首家现行文件档案资料服务中心,从而揭开了全国各地档案馆开展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的高潮。2005年6月,全国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现场会在青岛召开,至此全国已有2,367个国家档案馆开展了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工作,占总数的76%,累计接待利用者100余万人次。
全国各地档案馆还持续创新服务机制,完善服务制度。湖北省档案局提出了“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利用者”的档案馆服务工作“四贴近”原则。上海市档案部门推行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和无理由投诉制,实行节假日照常开馆,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许多档案馆开通了网络档案服务平台,提供网络档案检索、浏览服务,使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利用档案信息。截至2006年年初,深圳档案网站访问量已经超过250万人次,“上海档案信息网”、“青岛档案信息网”的访问量都突破200万人次。各档案馆在宣传教育人民、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帮助民众维护自身权利、帮助百姓排忧解难、提供市民休闲娱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长春市2,198名下岗职工在利用市档案馆档案办理社会养老保险中受益。⑦浙江省淳安县档案馆为3万多名移民及其子孙提供了档案证明,帮助他们获得国家的移民补助。
2007年12月,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努力建立服务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确保民生档案及时服务社会”。
档案服务社会化使得档案工作能更充分地实现档案的社会价值,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与支持,是“社会模式”的又一重要特征与体现。
注释:
①②⑤冯惠玲:《论档案馆的“亲民战略”》,《档案学研究》2005(1)
③陈忠海:《档案馆应该保存什么样的社会记忆》,《档案管理》2005年(2)
④[加]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版
⑥《规范 整合 共享——对我省民生档案工作现状和发展的思考》,《浙江档案》2008(1)
⑦杨冬权:《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开创档案工作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中国档案》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