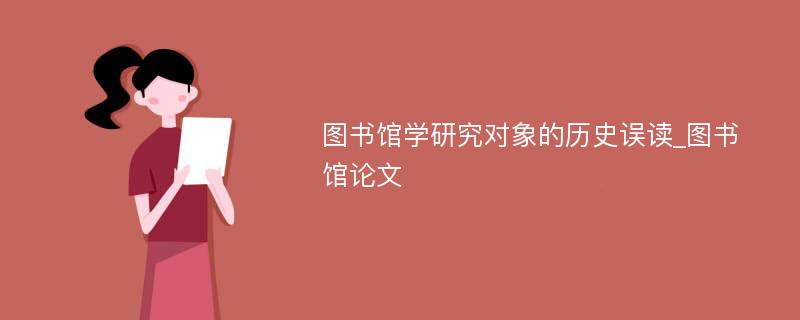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误读论文,研究对象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赖以建树的基石,也是图书馆学与其他科学知识相区别的依据。图书馆学的定义也主要是根据其研究对象来规定的。因此,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一直是图书馆学最根本的元问题。
从1807年德国图书馆学家施雷廷格(M.W.Schrettinger)首次使用“图书馆学”一词起,各国图书馆学者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随着图书馆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与深化。可以说,受不同时代的文化影响,各种研究对象的释义也都具有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的文化烙印。总的发展进程来看,它们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直觉经验到科学抽象、从封闭研究到开放考察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些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认识,象不同时间里撒下的理性种子,每一粒都含有宝贵的思想价值。我们今天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探寻,正是建立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合理地继承来进行的。也唯有此,我们才可能向真理更加迈近一步。
但是,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者在总结前人学说,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种种观点条分缕析之时,却出现了某些严重的误读现象,而且影响甚广。这种误读不仅对先贤观点作出了不公正的评价,也影响到我们从学术遗产获取营养价值的准确性。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澄清,那么仍将对今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探索发生误导作用。
2 文献上的曲解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探索,在我国经历了“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交流说”等阶段,这是图书馆学界广为人知的常识。然而,如果对历史文献重新细读,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已经转化为一种常识的知识,其中也有严重的错误。以“要素说”为例,图书馆要素的观点是存在的,但图书馆学史上,那些提出要素说的人却从未有谁声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就是图书馆的这些组成要素。
解析并且研究图书馆事业的要素,国外久已有之。在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史上,最早提到图书馆要素的,首先是杜定友,而不是现代学者们众口一词的陶述先。1921年杜定友在广州市民大学演讲“图书馆与市民教育”时就说过,设立图书馆,“除金钱外,以人才、书籍、房屋三者为最重要。而三者之中,犹以人才为最重。”〔1 〕他还分别就此四者之关系做了详细说明。1925年,杜定友把建设具体图书馆的这个“四要素说”,又上升为图书馆事业的“四要素说”,称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兴替之要因有四端:人才、书籍、财力、时势。并取去前“四要素”中“房屋”而代之以“时势”。论曰:“有人才、书籍与财力,而尤须有时势之因应。苟当时之社会,全无图书馆之观念,无图书馆之需求,则虽欲谋发达,焉可得哉?”〔2〕
1932年9月, 浙江省图书馆总馆(杭州市大学路新馆)举行开馆典礼,杜定友、洪有丰、刘国钧受邀参加,杜定友在题目为“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的讲演中论道:“整个图书馆事业,其理论基础实可称‘三位一体’。三位者,一为‘书’,包括图与书等一切文化记载;次为‘人’,即阅览者;三为‘法’,图书馆之一切设备及管理方法管理人才是也。三者相合,乃成整个之图书馆。”他说,书、人、法三者,因时势变迁,中心也有转移,传统藏书楼时代以图书收藏为重,突出“书”;第二时期,即五十年来图书馆之设备与管理大见进步,“书”乃不见十分重要,而以“法”为重;第三时期,即最近数年来,图书馆事业极其发达,“书”既丰富,“法”亦讲究,于是转应重“人”。〔 3〕这就是后世被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广为评说的杜定友“三要素说”。
从上述介绍我们可看出,首先,杜定友的“三要素说”是从以往“四要素说”基础上发展演进出来的。其次,在“三要素”中,杜定友强调“人”(即阅览者)的重要性,并要求以“人”为目标来办理图书馆,说明他已看到了读者需要是图书馆事业发展之动力这一关键命题。叙述及此,笔者认为,杜定友先生的要素说是值得学术史研究者认真整理研究的,图书馆事业的要素也是图书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与范畴,但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杜定友先生并未在此过程中提出过,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图书馆事业的各个要素。倒是他在1926年根据美国图书馆学者麦耶(H.B.Meyer )的观点给图书馆学下定义时说:“图书馆学专门研究人类记载的产生、保存和应用,所以是人类学问中一种很重要的科学。”〔4〕
陶述先生的“三要素”是在杜定友“四要素”说之后提出来的。1929年还是武昌文华图专学生的陶述先,在《图书馆广告学》一文中开篇即言:“现代所谓新式图书馆,其要素有三:书籍,馆员,与读者是也。”〔5〕此文乃因专门研究图书馆广告学内容, 故而陶氏并未对此“三要素”充分展开论述,他也并未说:此三要素就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1934年,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要旨》中提到图书馆成立的四要素有: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但他语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时却说:“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 ”〔6〕显然,在刘国钧先生看来,图书馆的要素,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两回事。1957年1月,刘国钧为回答图书馆学是否为一门科学之问题, 专门写了《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此文刊载后,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刘国钧先生在该文中正式提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他认为,研究图书馆事业,“就是说要研究整个图书馆事业——它的历史,它的作用,理论基础,建设原则,总结各类型图书馆的经验等等。”同时也要对图书馆事业进行要素解析,分别就“(1)图书馆,(2)读者,(3)领导和干部,(4)建筑与设备,(5)工作方法”进行深入研究。〔7〕当年5月,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行的1957年科学讨论会上,许多人针对刘国钧先生之观点进行了辩驳争论。如有人称“五要素”的划分,“会把图书馆学导至形而上学的道路”,走上‘超政治’的道路,抹煞图书馆学的党性和科学性。”〔8〕这种批评带有“上纲上线”色彩。刘国钧先生会上后来申诉, 他之所以主张对图书馆事业所组成的五要素分别研究,是因为图书馆本来是一个复杂的事业,由诸多因素组成。分要素进行研究方可使认识深入。区分五要素并不等于孤立地对待每一要素,并未割裂图书馆事业。这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并非研究内容问题。〔9〕因此,据上所述, 刘国钧先生谈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显然是指“图书馆事业”,“五要素”的提出,只不过是具体规定了研究中应怎样深化的问题。
然而,1981年北大、武大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在总结上述历史上有关图书馆学对象的认识时,首列“要素说”,把陶述先、杜定友的“三要素”、刘国钧的“四要素”、“五要素”统称为要素之说,并指出:提出“五要素”的刘国钧先生认为,“分别就这五项要素进行研究,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整体,中心内容是工作方法。”〔10〕这个结论,完全是对刘国钧先生本义的曲解。刘国钧先生原文现并不难找,遍读其文,不见刘先生自己说过:“对五要素”的研究“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整体”。如上所述,无论是杜定友、陶述先,他们均未表示过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谓的“四要素”、“三要素”。刘国钧先生阐明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五要素”是图书馆事业范畴的进一步细划。他并未把“五要素”单独列出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因此,《图书馆学基础》把历史上这些“要素说”当作研究对象来展示,完全是一种主观虚拟。
《图书馆学基础》是我国“文革”后影响最大的一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前后5次重印,印数多达12万册,影响甚广。 它把“要素说”列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历史认识,从此使国内数种教材无不效尤。而且令人奇怪的是,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修订本,依然本其旧说,甚至借刘国钧先生之口,说《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明确指出:“分别就读者、图书、领导和干部、工作方法、建筑与设备五项要素进行研究,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整体。”〔11〕修订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刘先生,然后对“要素说”进行批评说,要素说有其局限性,“①它只是对图书馆表面现象的描述,没有涉及到图书馆的实质;②它只限于对个体图书馆的分析,没有涉及到图书馆事业的全局”。〔12〕演绎至此,前人之说已面目皆非。古人说:“书三遍,虚成虎,鱼成鲁”,此可为其矣。治图书馆学者最懂版本学、校勘学之意义,然而对原始文献竟发生如此重大之误读,不能不令人惊骇。
3 概念上的混乱
人们知道,对图书馆、图书馆事业下定义,与给图书馆学下定义是两回事。同理,如何认识图书馆与如何认识图书馆学也是不能相互混淆的问题。但是,我们见到的一些图书馆学概论之类的书籍,却往往把对图书馆的认识,当作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来阐释。如杜定友、陶述先关于图书馆事业的“三要素”的观点,实质上都是有关图书馆事业的一种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却被后来的图书馆学研究者们当作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待。刘国钧先生虽然曾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图书馆事业的五个要素,但基本定位还是“图书馆事业”。把“要素说”当作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看待,这不仅仅出于文献上的误读,而且也属概念上的混乱。
《图书馆学基础》(1991年修订本)所犯概念上的错误不止一处,比如在介绍国外有关研究对象的认识上,专门提到了巴特勒(P.Butler)的观点,述曰:“巴特勒于1933年出版了《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他认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工具,而‘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他还从科学的、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方面,阐明了图书馆的作用”〔13〕在这段话中,修订者出现了以图书馆观代替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概念错位。巴特勒从各方面论述了图书馆的作用,并不代表这就回答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巴特勒是怎样表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呢?从《图书馆学基础》(1991年修订本)却无从证考。倒是较《图书馆学基础》(1991年修订本)早出五年的吴慰慈、邵巍主编的《图书馆学概论》一书,对巴特勒的观点介绍颇为简要及准确。吴书称巴特勒“把读书现象与图书馆的本质属性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发现了社会知识是以图书为媒介,通过人们的阅读行为进行传递交流的现象。”因此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与读书现象。”〔14〕《图书馆学基础》在1991年修订时,应该看到了吴书,但为何作此不着边际之说明,令人费解。
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图书馆学从哲学高度的深入探讨,国外出现了一些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方面的认识,比如美国谢拉(J.H.Shera )的“社会认识论”、德国卡尔施泰特(P.Karstedt)的“历史、体系、知识社会学”,以及波普尔(K.R.Popper)的“世界3”理论。 这些理论认识为图书馆学的深入开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因此,也就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有效的理论基础。但是,我国的图书馆学者,却在一些图书馆学教材中将其表述为一种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如南开大学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1986年)与北大、武大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1991年修订本)。尤其后者在阐述西方研究对象诸说时,分别把由布鲁克斯(B.C.Brookes)移植于图书馆学中的“世界3”理论归为“知识基础论”,谢拉的有关社会认识论归为“社会认识论”,统属“社会知识交流说”之下。这部教材的修订者将一种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当作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新说,这里显然也犯了概念混乱的错误。《图书馆学基础》(1991 年修订本)曾引用布鲁克斯原话说:“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不能不引起图书馆学家、情报学家的注意,这是因为它是第一次从纯粹实用观点以外的角度,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专业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5〕,同时也认为,“谢拉以社会认识论作为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的科学依据,并在这个基础上阐述了他的图书馆学理论。”〔16〕但是为何要将作为一种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的“知识基础论”、“社会认识论”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等同起来呢?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难道能等同于研究对象吗?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谢拉曾明确说过,图书馆学“从根本上讲,它研究的是人类思想和伟大探索的文字记录之间的那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关系。”〔17〕这句话蕴义丰富,值得认真探究,为谢拉对图书馆研究对象从哲学高度的阐释。为什么我们就往往予以忽略了呢?
4 分类上的随意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既是图书馆学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图书馆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图书馆学者孜孜以求,艰辛地探索,产生了百种以上的认识与理解。对这些认识、理解进行梳理,择其要者进行分类、排比,按基本论点讨津溯源,以概括总体发展脉络,这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较为科学地认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但是,综观我国80年代以来出版的图书馆学教材,各家分类繁芜杂乱,叫人摸不着头绪,吴慰慈、邵巍的《图书馆学概论》(1985年)罗列国外研究对象的认识有“实际技术”、“图书与读书现象”、“知识社会学”、“社会认识论”、“知识基础论”,国内的研究对象的认识有“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交流说”等。南开大学《理论图书馆学教程》(1986年)列举国外有“图书馆过程”、“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活动”、“图书与读书现象”、“世界3理论”,国内有“图书馆事业及要素”、“矛盾说”、 “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活动”、“图书馆”、“知识交流”、“文献信息交流”。北大、武大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1991年修订本)把国内外研究对象各种认识混成一体,概括出“图书馆整理说”、“图书馆实体说”、“社会知识交流说”三大类,每类中又有具体观点介绍,如“社会知识交流说”中有“知识基础论”、“交流系统说”、“社会认识论”等。武汉大学郭星寿的《现代图书馆学教程》(1992年)采用的也是国内外研究对象观点统一编排的做法,列有“整理论”、“知识论”、“管理论”、“结构说”、“要素说”、“事业说”、“整体说”、“活动说”、“过程说”、“矛盾说”、“文献开发和利用说”、“交流说”等。可以说各有各的章法。一个图书馆学入门者初读一部图书馆学教材,相信他对于研究对象的演变还能建立很清晰的观念;如果再读一部教材,很可能疑窦丛生;如果读了第三部、第四部,那么就会坠入雾中,掩卷长喟了。
从理论上说,前人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与认识,如同历史上发生了各种事实而具有不可变异的历史客观性。如果我们后人对其文献进行认真解读,经过仔细梳理,是可以分辨出同异,进而归纳成不同的演变体系的。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上述种种教材的编纂者,应该说各有其本,都力图在历史溯源中表现出合理与公正。不过,整体上产生如此纷杂的分类,其中不能不说包含了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我们仍以《图书馆学基础》(1991年修订本)为例,该书在介绍研究对象的第一种“图书馆整理说”时,述完施雷廷格的观点后讲道:我国古代刘向、刘歆《七略》、郑樵《通志·校雠略》,以及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孙庆增《藏书纪要》等著作所述内容,“基本上也是以图书整理作为研究对象的。”〔18〕因此修订者也把他们归入了“整理说”派。此种定位令人费解。其一,总结图书馆整理、藏书方法经验的著作,与专门阐述研究对象观点的理论论述是两回事情,二者怎能牵强并论呢?其二,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藏书理论处于一种经验总结的形态,还未上升到以科学方法为图书馆学预设研究对象的水平,怎么能随便拉来作为研究对象一个派别而列出呢?
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看,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如数学的研究对象人们曾认为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生命过程及疾病的发生、防治,植物学研究植物,动物学研究动物等等。研究对象一般说来是一种客体存在,或是一种物,或是一种现象(包括精神现象)。图书馆学也如此,如果研究对象不明确,那我们很难判定学科之间的界线。比如人们常常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混淆,就是对二者研究对象判别不清的结果。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各种认识可谓众矣,但是我们在分析这些不同的认识之时,紧紧把握住它们指向的客体存在物,那么就会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从而做出科学的分类。例如我国图书馆学界曾指出来的“矛盾说”、“规律说”、“事业说”、“活动说”等等,其实他们指向的客体存在物都是“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已不是一个具体的图书馆,而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已涵盖了“图书馆事业”这个意义。因此,这些不同的认识,都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指向客体存在为整个图书馆事业,按照基本共同点,可以将其总括为“图书馆事业说”,这样就容易理解与把握了。当然,“交流说”、“知识说”指向的客体存在物与众说有别,主要指向的是文献所包含的知识,因此就不能简单归入“图书馆事业说”中了。
总之,如何对历史上众多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认识进行合理归纳与分类,这不是本文论述的范畴,笔者仅想在这里申明: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认识,在不同的时代与社会有不同的取向,它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今后这个过程还会延续发展(连数学这样的古老学科,至今其研究对象也尚未有定论)。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出一种科学方法来分析、归纳这些认识,使之能够分类合理、脉络明析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我们图书馆学史的一个基本责任与义务。
5 结语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误读,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效用。其一,它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并且导致我们对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重要思想发生误解,进而失去对他们的正确认识与评价。其二,它显示出图书馆学界还存在着一种不良的学风。尤其在颇具权威的教科书中存在严重错误,说明我们图书馆学这个“科学共同体”在治学上还缺乏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那种严格实证的学风与素养。现在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在写文章时人云亦云(包括作者本人亦不能免)。甚至已习惯使用“二手”材料,更懒于因一段引文而去核对原始文献。似乎我们已经不再明白:只有认真翻阅那些泛黄的原始文献,才能获得历史的现场感;只有仔细解读那些繁体字乃至文言文,才能领悟先贤的睿智与感情。当图书馆学迈入一个全新的世纪之初时,这些存在的问题难道不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吗?
(来稿时间:199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