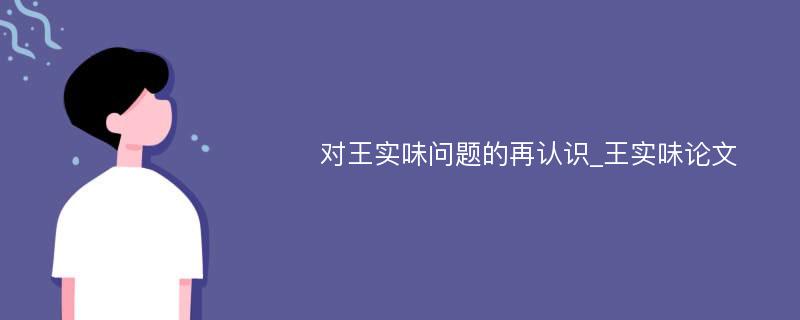
对王实味问题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王实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2000)04-0056-05
王实味问题终于平反了,整个案件经历了从1942年到1992年长达半个世纪之遥的历程,王实味虽然昭雪,但案件本身留给我们的深思和反省则当是永远的。
一、丁玲、王实味等在延安倡导的救亡、启蒙的文学思潮
王实味的问题,起初应该仅仅是一个文艺思想问题。中国新文学从20年代末倡导左翼文学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高张民族的大众的革命文学大旗,特别是在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强调歌颂光明、歌颂英雄人物已蔚然成风,初步形成了工农兵文学的主潮。这实际上,为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理论概括的基础。
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来自上海的亭子间。他们曾经是反帝反封,要求民主自由的先进青年,在文学上,深受五四文学启蒙意识、民族批判精神的影响。当他们满怀激情奔赴延安时,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一动听的歌词的深层含义并不十分理解,因而对延安艰苦的环境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况且,延安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在文化修养、兴趣爱好、性格习性方面又与他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作为延安文艺界的领导,《解放日报》主编的丁玲,自然能坚定地按照党的政策积极为抗战,救亡运动而呐喊,以发挥文学的功能,为民族的救亡运动唱赞歌;另一方面,丁玲作为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影响而崭露头角的著名女作家,她仍肩负启蒙思想的重任,在解放区力图倡导救亡启蒙双重文学新潮,以自己的作品揭露抨击革命队伍内部的陈腐、消极的思想意识,从而展现出对现实更真实更深刻的独到描写。
丁玲当时认为:“现在这一时代仍然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暗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的自由都没有……即使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世界是相连结的。而我们却只说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她还说:“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我们需要杂文》,见《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5日)上文中,丁玲所说的“这里”自然指的是解放区,她认为解放区同样与旧中国、与几千年封建恶习的土壤有着联系,因此不可讳疾忌医,而“更需要督促、监视”,否则仍会让懒惰和怯弱这类国民的弱点滋生发展。
由此,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既表现“救亡”的主题,又注重启蒙思想的传播,在丁玲的影响下,解放区基本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学思潮,于是他们抱着热忱之心,以昔日在国统区那样勇猛的批判精神,在歌颂光明的同时,也揭露阴暗面,高张救亡图存、思想启蒙两面大旗,触及一切人的灵魂,争取言论自由和人格、人权平等。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丁玲写出了杂文《三八节有感》,小说《在医院中时》;另外,还有一批作家也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创作。比如,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王实味的《硬骨头与软骨病》,《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都属于这一思潮孕育出的作品。王实味则是这一文学思潮的突出代表。
他们的作品针砭延安存在的问题,犹如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把整个延安炸开了锅。
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主潮以何等的努力才争得正宗地位,而延续到解放区文学时期更有所发展。这种一统独尊地位的取得是经过血的洗礼换来的,要冲击它,要对它说“不”,谈何容易!
其实,从丁玲、艾青、王实味等来说,他们的用意和出发点无非是为了发扬“五四”文学的传统,为了推进新文学的发展,似乎并非存在全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思。毛泽东在谈到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时也说:“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是,到延安文艺界开展文艺界整风运动后,丁玲、艾青、罗烽等都作了自我批评,转变了立场,而王实味因被诬为“托派分子”,加之不愿作自我批评等等复杂原因,受到多次批判,最后冤死于山西蔡家窑。
王实味冤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最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这一文学思潮的突出代表,他的这篇杂文正是反映了以上内容。
应该说,丁玲等倡导的这股文艺新潮对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工农兵文学主潮,无疑是一个补充和丰富,它将促进整个新文学健康而完满地发展。但是,这一文学新潮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问题。倡导者们对这一敏感问题是早有考虑的,丁玲对这种关系的处理说:“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方向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是写黑暗也不会成为问题的。因为这黑暗一定有其来因去果,不特无损于光明,且光明因此而更彰。”王实味对此与丁玲有十分相似的见解,他说:“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他还以宽大的胸怀指出不要怕被国民党利用:“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诬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可见,他们对歌颂与暴露的实质关系是有正确的认识的。王实味的这些认识都写在《野百合花》一文中,为什么当时只看到了他对延安阴暗面揭露的那些具体文字,而看不到他写这些文字的指导思想和良苦用心呢?
当然,王实味文字的尖刻,对某些问题认识的偏颇以及嘲讽的文风也是很明显的。他的这种“冷嘲暗箭”令毛主席极为反感,说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因此,从一开始毛主席就指出他是立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现实,为了保证从政治思想军事生活上取得抗战的胜利,使全党目标一致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已经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而王实味的这些言论,无疑会对头脑不清醒者,意志薄弱者带来与党存二心的不良后果,从而削弱革命力量,涣散革命斗志,对整个革命事业是极为不利的。
二、康生极力推行极左路线
当时的延安确实存在着一股潜在的“极左”思潮的干扰。康生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副手。回国后,王明推行一条向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1940年,党的6届6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动了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清算,而获得了军事和政治的领导权,康生旋即把“王明万岁”、拥护王明的《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改成“打倒王明”、“打倒他的《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在短短3年里,从组织上把与王明的攀附纠葛甩得干干净净,而成为延安掌了实权的显赫人物,尤其是担任在毛泽东任主任的一人之下的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直机关总学委主任的要职,掌握着延安万名干部的生死大权。
康生虽然从王明路线中摆脱出来,然而他在苏联学习的几年,深受斯大林在共产党内部“清洗”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模式以及对“托派”的高度惊恐的影响是并没有随王明路线一起消除的。而当时的延安,对共产国际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顶礼膜拜的。因此,由康生领导的整风运动必然会受到“左”的干扰。
刘雪苇后来在《王实味和〈野百合花〉》8人访谈录中说,他当时“把和王实味争论的情况正式告诉中央研究院的秘书长徐建生和党委书记李言”,而被安排在大会上揭发王实味,致使王实味问题严重化,他感到要负很大的责任,十分愧疚。然而,他又说:“确实在我是始料所不及”。批判大会后,他曾在研究院支部会上表示:“要把王实味的问题”上升为政治组织问题,证据不足。“从此,对王实味的院外斗争会,我就没有参加”。他承认向组织举报王实味与他平日争论托派问题的情况“并不是无意间提起。这种事情的发生,在当时并不奇怪。只要了解王明、康生回国以后延安的政治气氛和刚开始的整风的前奏——‘忠诚坦白’运动,就会明白的”。由此可见,当时王明、康生从苏联斯大林那里承袭来的左倾思潮,造成的人人如惊弓之鸟的恐怖气氛是何等的严重!
尽管毛主席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甚至对王实味也从来没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但是在康生的干扰下,无法否定的王实味脾气的暴躁、个性的硬倔以及对某些问题认识的偏激,决定了他没有能像丁玲、艾青、萧军等倡导文学新潮的同人们一样得到毛主席的召见和聆听他关于文艺的若干意见。其实,那时毛主席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酝酿成熟,在彼时彼情的特殊年代,毛主席几乎全部身心都集中在思考如何夺取政权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无疑,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也并不会例外。因而,《讲话》体现的历史性、时代性、政治性的意义和影响也就更为重要。这自然是丁玲、王实味们在倡导文学新潮时所不曾料到的,同时,看来也是不合时宜的。所以,《讲话》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更规范地强调了工农兵文学的主潮,并开始用政治的批判模式去制约文艺所具有的个性特征。
因此,虽然王实味的问题开始是个文艺问题,但它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必然会发展成政治问题。
恩格斯曾经指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这正是王实味悲剧的实质之所在。
三、王实味与托派
王实味的问题定性为政治问题的重要依据是被确认的“托派”。
且不说王实味在绝大多数场合拒不承认自己是“托派”,当然,在压力下他也被迫承认过自己是“托派”,而且据说还写过材料,填过表,这些材料已毁,无处查找。即使确认他为托派,其理由又有哪些呢?
最重要的根据大概是王实味曾经因陈伯达对他乱扣政治帽子而为站稳脚跟向组织详细交代过他与托派往来过的关系。即他与北大同学王凡西和陈清晨在30年代的最多不到10次的交往。显然,王实味没有在组织上加入托派,也没有在政治上完全接受托派的观点。据王凡西在《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中写道:他“怀疑反对派另起炉灶,重新建党来领导革命是否可能。他希望大家始终都在党内,即使被开除也不能企图自立门户。”他虽然曾徘徊在“中央派”和“反对党”之间,但是,最终他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奔赴延安是再有力不过的说明了。
王实味在思想上确实受到了托派的影响。
他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的估计、对斯大林清党的认识等都与托派某些见解一致。例如,他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任;”在批判大会上,他回答众人的提问说:“我认为托派对立三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我看到‘八一宣言’觉得还和托派国民会议的主张差不多,看到鲁迅答托派书,我才站到统一战线上来。”他和刘雪苇平时争论时说:“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托派的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
在批判大会上,他开始不承认自己有托派思想,后来在众人的反复质问下,他承认:“我说过:我对托派进行小组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苏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他承认与托派王凡西、陈清晨有过往来,而且觉得陈的“人性”是好的,对他们至今仍念念不忘。还说:“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在文学思想上,当时把王实味关于人性、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等方面的见解上升到托派思想的高度加以挞伐。其实,王实味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影响是很深的,该书完成于1924年,是一部基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论著作,反映了托洛茨基的文学基本思想。而托洛茨基的政治问题却发生在1927年前后,因此,把王实味受到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影响说成是受到托派文学思想的影响显然是错误的。
关于人性,主要是因王实味对托派陈清晨的人性有较好的印象,哪怕是在强大攻势的批判大会和决定他政治生命的审讯时,他也从不否认这一点。那是因为陈清晨留给他的印象确实太令他难忘了,在北大,陈清晨在同学心目中是以“老大哥”的形象出现的。他永远是那个揣上两个窝窝头,风尘仆仆跑进跑出的样子。1930年刘莹(王实味之妻)小产,这“老大哥”还将自己仅有的30元硬塞给他们。在北大时,陈清晨的“小脚夫人”从乡下来看望他,听说,他的妻子对他哭着说,害怕他抛弃她另娶。陈清晨说:“我能做这种事么?我要革命,自己倒去损害旧制度的受害人!”后来,他虽然加入托派,但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积极投身民族解放战争,1942年被日本宪兵杀害。王实味并不因陈清晨参加了反对党,与自己在政治上、阶级上绝然不同道,而否定他作为一个人的丰富复杂的个性特征,从而坚持“他的人性好”的观点。可见,王实味在被作为整风对象的腥风血雨的特殊而又严峻的时刻仍能坚持正确处理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对文艺大众化的认识,王实味不仅没有托派思想,而且他的认识比较深刻,触及到了“大众化”的实质问题。他认为“文艺大众化,绝不是单纯的文艺运动所能实现,它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作前提”他说:大众化没有完全实现的“基本原因是我们的革命没有成功”。
至于攻击他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有托派思想,完全是陈伯达的诬陷。王实味撰写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主要内容是与陈伯达、艾思奇和胡风三人进行商榷。该文提出如何科学地界定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他对“旧形式新内容”的提法发表了不同意的看法,他说:“文艺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只抽出形式而称之为‘旧形式’这是不太科学的”,认为“旧瓶新酒”中的“瓶”只应是“格式体裁”,“绝不是形式内容不可分的形式”。关于形式与内容这一文艺理论问题直至今日,仍是文艺工作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而在40年代,王实味就显示出了他思想敏捷、理论功底的扎实。
王实味的这些文学思想纯属学术问题,而且早在40年代他就能有较为独到深刻的见解,并能坚持己见,实在称得上文艺界的一位颇具才华、富有求实精神的文艺理论家,理应受到重视和培养。然而,在当时特定的革命时代,又由于某些人极力推行“极左”思潮,将这些学术问题无限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层面,进行武断地横蛮干涉和无知地批判,更为可笑的是捕风捉影地为了先验的结论——托派的罪名,去找理由,不管是黑还是白,只要不合当时某些人口味的东西,就能成为定罪的材料!
王实味的时代早已成为了历史,历史的沉渣再也不会泛起!然而,从沉痛的教训中,我们的人民将会以什么眼光去瞻望将来呢?将会怎样去捍卫真理、搏击人生呢?
收稿日期:2000-03-11
标签:王实味论文; 丁玲论文; 王明论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中国托派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野百合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