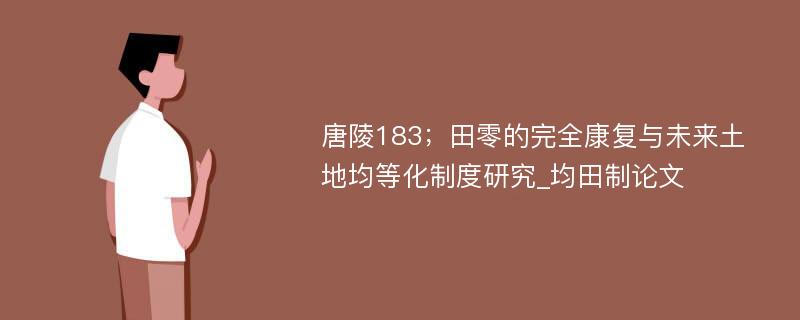
《唐令#183;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田制论文,完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使我们对唐田令有了完整的认识
唐代均田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上重要的一环。此前,国家政权对土地制度或有立法,或极力加以干预;此后,基本上是“田制不立”。要了解唐代的土地制度,就要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实施状况。要了解唐代均田制的实施状况,首先要了解唐田令是怎么规定的,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探究它是否按唐田令实施。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唐六典》、《通典》等史籍都记载了唐田令的一些条文,但它们都不是原原本本地照录唐田令的令文,而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撮田令大意,择要介绍,因而多有错漏。《资治通鉴》卷一九○武德七年四月条记唐田令最为简略,仅31字:“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什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所记仅限于《唐田令》第2条的前几句,丢了《唐田令》第2条有关民户原有土地处理办法的至关重要的一句——“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至于“初授田”之后如何运作,更是只字未提。《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记“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所记虽较《资治通鉴》详细,但同样漏了“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一句。虽然它谈到“初授田”之后的土地还授,但未交代田土不足时,如何进行土地还授。《通典》卷二《田制》记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田令最详, 其中有关均田制部分多达1600多字,但许多关键问题仍被遗漏了。唐开元二十五年,均田制已近尾声,加之以唐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是否基本上只是武德七年田令的重申,中外学者仍多有分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通典》所记田令的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日本学者中田薰、仁井田陞、铃本俊、菊池英夫与中国学者王永兴、宋家钰等都曾利用中国传世文献并参考日本《养老令》或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力图复原唐田令,虽然成绩斐然,但终究未能复原唐田令原貌。1999年,戴建国先生首先发现天一阁明钞本宋《天圣令·田令》随附有唐田令49条,再参考《唐律疏议》、《宋刑统》、《通典》、《唐六典》等书相关条款复原唐田令剩下的另7条,终于使《唐令·田令》原貌得以完整复原。(注: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新见的《唐令·田令》令文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了解唐代均田令极有帮助。复原后的《唐令·田令》共56条,其中44条,即第1—44 条,与官民授田以及职田、公廨田等有关,今人习称之为均田令;另外12条,亦即第45—56条,今人习称之为屯田令。《通典》卷二《田制》记唐田令最详,但复原后的《唐令·田令》均田令部分与之相比,多了16条(第14条、第17条、第25条—第36条、第43条、第44条),占均田令总条数的36.4%。此外还有2条(第6条、第37条),《通典》记载不全。(注:《通典》失载或记载中有重大遗漏的均田令约占均田令总条数的40%。)由此亦可见《通典》记均田令缺漏之多。至于《唐六典》等书,缺漏就更多了。而其所缺漏者,往往事关均田制实施时的具体做法。
如均田制下官、民初授田问题,除《通典》、《白氏六帖事类集》记载官、民“先有永业者”可以“通充口分之数”外,其他各书都无此条记载。新复原的《唐令·田令》不仅明确了官、民“先有永业者”可以“通充口分之数”(注:《唐令·田令》第2条。), 而且明确了官吏“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时的程序,即先在原籍陈牒,经原籍当局“检籍知欠”,然后录牒管地州勘给,而后再“具录顷亩四至”报本贯上籍。(注:《唐令·田令》第14条规定“诸请永业者,并于本贯陈牒,勘检告身,并检籍知欠,然后录牒管地州检勘给讫,具录顷亩四至,报本贯上籍,仍各申省计会附簿。其有先于宽乡借得无主荒地者,亦听回给”。引《唐令·田令》中的黑体字部分为我国传世文献原先所未见的《唐令·田令》的令文,下同。)这使我们对均田制的“授田”办法有了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
再如均田制下的土地还授问题。《旧唐书·食货志》与《唐会要·租税上》都谈到口分田要还授(注:《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虽未直接谈到口分田要还授,但谈到“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日本广池学园本),《通典·田制》等则未明确谈到土地还授。),但都没说如何进行土地还授,特别是没说受田不足情况下如何进行土地还授。因而有学者认为,在受田严重不足情况下,各地就按各自另行规定的低于田令规定标准的受田基准额进行土地还授,永业田也在还授之限。(注:西村元佑就认为:“唐代西州一丁男的受田基准额是10亩,这是比一丁应受永业田额都要低的受田额,即使如此,为了忠实地贯彻均田行政,当然也要着实地进行班田收授。”还说:“唐代律令制的基本原则是不管如何狭乡化,各个地区都要根据丁中法贯彻均田制。”见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同朋舍1968年,第428—429页。)新发现的《唐令·田令》第27条却显示,《田令》明确规定:“诸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豫校勘造簿,至十月一日,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对共给授,十二月三十日内使讫。符下按记,不得辄自请射。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乡有余,授彼乡;县有余,申州给彼县;州有余,附帐申省,量给比近之户。”原来,《田令》此条在“诸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豫校勘造簿,至十月一日,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对共给授,十二月三十日内使讫”一句之后,在“乡有余,授彼乡;县有余,申州给彼县;州有余,附帐申省,量给比近之户”一句之前,还有二句:“符下按记,不得辄自请射。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什么叫“符下按记,不得辄自请射”,虽尚不得其解,但“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一句,意思却很清楚:土地还授之际,退田户的田土,先在户内进行帐面调整,在充分满足户内应受田口的应受田之后,若再有剩余,才要退田还公;若无剩田,就不退田。(注:《唐令·田令》第30条规定僧尼、道士、女冠,“身死及还俗,依法收授。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受”,亦系此意。)换言之,土地还授之际,首先考虑的不是该乡该里其他各户的应、已受田情况,而是考虑该应退田户减员之后该户田土是否充分、足额。这一规定类似于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 年)令所规定的“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注:《魏书》卷一一○《食货志》。)。所不同的是,北魏太和九年《地令》是着眼于进丁受田,而《唐令·田令》则着眼于减员退田。比较而言,《唐令·田令》的规定更明确,可操作性很强。按《唐令·田令》此条规定,狭乡已受田在35亩以内之户,宽乡已受田在60亩以内之户,无论如何减员,只要不绝户,都不必退田。(注:狭乡民户应受田标准最少是35亩(不含居住园宅地),宽乡民户应受田标准最少是60亩(也不含居住园宅地)。)永业田不退(注:按《唐令·田令》规定,永业田除非绝户都不在还授之列。),口分田也不退。不仅无须退田,而且还应补充授田。上面说的还是减员到只有老男或寡妻妾、中女、18以下中男、小男、小女、黄男、黄女一人时的情况。倘若减员之后,各户还有一丁(或一18以上中男),那么,上述标准更要提高到狭乡60亩,宽乡100亩。唐前期敦煌出土的户籍、手实显示的情况,就像20世纪30年代铃木俊所揭示的那样:“各户的田土都是将农民的现有土地,以永业田为基础,套用均田条文”,“凡是已受田额多于规定永业田额的户,必然会有规定额的已受永业田,而且一定会有口分田。反之,已受田额少于规定永业田额之户,都没有口分田”。(注:铃木俊:《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与均田制》,《史学杂志》46—9,1935年。)简言之,也就是“永业田常足,口分田恒不足,永业田不足者悉无口分田”。其实质就是土地还授之际进行帐面调整。(注:参见拙作《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45页。)过去许多学者(包括铃木俊先生)曾将这种现象归结于未按田令实行土地还授。(注:铃木俊:《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与均田制》,《史学杂志》46—9,1935年。)笔者也曾持此观点。现在看来,上述提法并不正确。应该说,敦煌户籍、手实所显示的土地还授之际的先在户内帐面调整田土这种情况,正符合《唐令·田令》的规定。(注:唐代西州(即吐鲁番地区)户均已受田不及10亩,沙州(即敦煌地区)户均已受田不及50亩,在此情况下,除极个别户在极特殊情况(在特定时限,主要应受田口都去世,而只剩下老寡黄小当户)下有田可退外,绝大多数人户都是除非绝户都无田可退。人老、身死退田是进丁受田的前提,人老、身死既无田可退,进丁受田自然无从谈起。)
再如口分田的“务从便近,不得隔越”问题。过去我们只知道《唐令·田令》于“给授田”之时有“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的规定。土地还授之际,田土分布情况又将如何,不大清楚。敦煌户籍、手实显示,各户的田土都相当零碎,不符合《田令》关于“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的规定。有学者据此推论均田制并未实行。(注:参见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民户田土的零碎与均田制下土地还授有关(注:参见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或者说,正是土地还授彻底实行的结果。今见新复原的《唐令·田令》,始知唐《田令》不仅在其第24条规定了“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而且在其第26条还明确规定了“诸应还公田,皆令主自量为一段退,不得零迭割退。先有零者,听”。换言之,按《唐令·田令》规定,土地还授之际,应还、应受之田都不应割零。
二、《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解决了许多长期争议的问题
《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使许多长期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得以解决。举其要者,就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武德七年田令与开元七年田令、开元二十五年田令的同异问题
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唐六典》、《通典》等史籍对唐《田令》都有所记载。《旧唐书·食货志》、《唐会要·租税》、《资治通鉴》卷一九○明确标示所记为武德七年令,《通典·田制》明确标示所记为开元二十五年令。《唐六典》虽未明确标示其所记为哪一年的令,一般认为其所记为开元七年令。因各书记载的内容与行文多有不同,故今人多认为武德七年田令与开元七年田令、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有所不同。如认为武德七年令规定老男当户应受田60亩,而开元七年令与开元二十五年令则改为老男当户应受田50亩等等。(注:实际上,唐开元四年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索住洛老男当户“应受田叁拾陆亩”,若按宽乡计,就已是老男当户应受田50亩。件见《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245页。)但也有人认为, 尽管武德七年以后,于贞观年间、永徽年间、景云年间、开元年间一再修订、重颁律、令、格、式,但就其中的《田令》而言,却始终未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注:参见拙文《关于北朝隋唐均田制立法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理由是,《旧唐书》、 《唐六典》、《资治通鉴》只记武德七年田令,而不叙其后有何变化;《通典》记开元二十五年田令,亦绝口未提武德七年田令。如果唐田令前后有重大变化,专记典章制度沿革的两《唐书·食货志》与各种政书是不会,也不应该不措一辞的。上述各书不记唐田令沿革,实际上也就表明,唐田令前后没有什么变化。至于上述各书所记在文字上的差异,只是上述各书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撮田令大意时行文上的差异而已。(注:《资治通鉴》、《旧唐书·食货志》、《唐会要·租税》同记武德七年田令,行文上的差异就非常大。)《新唐书·食货志》、《唐六典》记唐田令,未标示其为哪一年之田令,也表明其为有唐一代之令。(注:《唐律疏议》、《宋刑统》、《白氏六帖事类集》、《夏侯阳算经》与日本的《令集解》等称引唐田令,一般也都是径言“田令”、“唐令”、“授田令”,而不强调其为哪一年之令。)《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终使这一长期争议的重大问题得到解决。新复原的《唐令·田令》的大多数条文出自宋《天圣令·田令》附录的唐《田令》。关于《天圣令》的编修原则,《宋会要辑稿·刑法·格式》载:“(天圣七年)五月十八日详定编敕所止(按:“止”为“上”之误)删修令三十卷……凡取唐令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注:《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四。)这就确证新近完整复原的是《唐令·田令》,而不是某年之令。同时也进一步确证武德七年田令与开元七年田令、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与王应麟《玉海》卷六六《天圣新修令》引《书目》也都是说《天圣令》依据唐令旧文益以新制而成。这表明时人也认为《天圣令·田令》所参考、所“随存”的是《唐令·田令》,而不仅仅是开元二十五年《田令》。由此又可证明,时人并不认为《唐令·田令》前后有实质性变化。)新复原的《唐令·田令》既然是有唐一代之令,那么,它就不仅适用于开元二十五年以后的均田制研究,同时也适用于开元二十五年以前的均田制研究。(注:戴建国先生率先完整复原《唐令·田令》诚系嘉惠学林的盛举,但他将新复原的《唐令·田令》定名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不能不说有画蛇添足之憾。)明确这一点,意义重大。
(二)唐律令是否承认私田合法存在问题
均田制下是否存在私田,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西川正夫发表文章,认为均田制外尚有公认的自田即私田存在。(注:西川正夫:《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简所见的“自田”》,《史学杂志》64—10,1955年。)此论一出,立即引起史学界的热烈讨论。日本学者山本达郎与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均田制下存在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田。(注:山本达郎:《对均田制末期敦煌地区土地四至记载的考察》(一),载《东方学会创立25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1955年;《对均田制末期敦煌地区土地四至记载的考察》(二)、(三),载《东方学》53(1973年)、56(1974年);张维训:《唐代敦煌地区户籍和手实中的“自田”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杨际平:《从唐代敦煌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胡如雷:《也谈“自田”——兼论与唐代均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则坚决反对均田制下还有私田说,他说“最近有人认为唐代存在不属于均田制的被称为‘自田’的公认的私有地。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原先的各种观点,不论是均田制施行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要从根本上改变其观点,因为包含均田法规在内的唐田令各条以及与此相关的唐律各条都是以不得公开存在这种私有土地为前提制定的。如果这种应公开否认的东西又得到公开的承认,那么,就连律令存在的意义本身都必须重新考虑”(注: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432页。)西嵨定生先生既把问题提到如此高度,可见均田制下是否存在私田确实事关均田制研究之全局。
实际上,唐代律令体制并不否认私田存在的合法性。新复原的《唐令·田令》第34条就明确规定:“诸公、私田荒废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听。”这里所说的“公田”,亦即“官田”,与之相对的就是民户的“私田”或通常所说的“民田”、“百姓田”(注:唐代西州堰别青苗簿就将田土分为“官田”、“寺观田”、“百姓田”三类。)。《唐律》卷一二《户婚律》“诸盗耕种公私田”条、“诸妄认公私田”条、“诸在官侵夺私田”条,所说的“公田”、“私田”,也是这个意思。(注:《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紘传》载,开元十四年初废京司职田。议者请于关辅置屯,李元紘表示反对,他说:“今百官所退职田,散在诸县,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垦,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须公私相换。”其所使用的公私田概念亦属此意。)《唐令·田令》第34条对公私田荒废地的借荒,采取明显不同的政策。私田虽废三年,原主要自耕,应先尽其主。公田借荒九年才还官,私田三年就要还原主。限满之后,若借荒者口分、永业田不足,可以申请将所借耕之官田荒废地充当其口分、永业田,私田则不可。凡此等等,皆可见政府对民户私田的土地所有权的充分尊重。(注:这其中既包括登记为民户永业、口分田的“私田”,也包括民户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田。)包括《唐令·田令》在内的唐代律令体系既然明确承认私田合法存在,先前不承认私田合法存在的学者确实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其观点。
(三)《唐令·田令》和“乡法”与“户部式”的关系问题
关于唐代均田制实施状况的讨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利用敦煌出土的户籍资料进行研究。敦煌户籍资料显示,各种应受田对象(丁、中、老男、寡妻妾、勋官等等)的应受田标准,完全符合《田令》规定。但多数受田不足,且无一定标准,只是把各户的现有土地,以永业田为基础,套用均田令文。玉井是博、铃木俊等学者据此以为均田制下的土地还授没有实行。(注:玉井是博:《关于敦煌户籍残简》,《东洋学报》16-2,1927年;铃木俊:《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与均田制》,《史学杂志》46—9,1935年;铃木俊:《均田、租庸调制度研究》, 刀水书房1980年,第108页、123页。)这一时期,土地还授否定说占上风。但也有学者认为土地还授还是实行了的。如仁井田陞就认为,唐代敦煌户籍的田亩四至中有“退田”字样,吐鲁番出土文书(引者按:此指流散在日本的大谷文书等)中又有“还公”、“死退”、“剩退”等字样,因而不能否定唐代土地还授的实行。(注: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书的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利用经过整理的大谷欠田文书、退田文书、给田文书进行研究。大谷文书反映的那种田制,一丁受田的基准为10亩,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土地还授。永业田同于口分田,也在还授之列。但一丁10亩这一土地还授标准又明显不同于《田令》规定的标准,永业田还授也不合《田令》规定。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西嵨定生提出:“除了田令所规定的宽乡和狭乡的应受田额之外,恐怕还要根据乡原之法,考虑各地的特殊情况,由式来规定适合于该地的田额。”(注: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56页。)西村元佑也认为,“唐代律令的基本原则是,不管如何狭乡化,各个地区都要根据丁中法贯彻执行均田制”,亦即都要还授。他还提出:“户籍所示的应受田额,是作为公示天下的大原则的令制的基准,在这个大原则范围之内,还存在着适应各地区实际情况的,作为因地而异的实施细则的‘式’的基准。西州一丁10亩的基准额,恐怕就是西州地方行政细则中规定的。”进而推论:“班田收授文书,不仅在西州,而且在内地,每年也是由乡里作成,着实进行班田收授。只是因为这些文书不同于户籍,不必长期保存,所以没过几年就废弃了。敦煌石室没有残存此类文书,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注: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29、424、462页。)西嵨定生、西村元佑的论断,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一时间几乎被视为定论。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如宫崎市定就认为,一丁10亩的收授田标准不是来自均田制,而是来自屯田制。(注:宫崎市定:《论吐鲁番出现的田土文书的性质》,《史林》43—3,1960年。)由于当时刊布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还很有限,宫崎市定论断的论据不足,结论也不准确,所以未为学界多数学者所采纳。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广泛运用传世文献资料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深入研究。1959—1975年系统发掘吐鲁番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墓葬群陆续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为均田制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注:这批出土文书于1981—1991年分成10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新出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显示,从唐军征服高昌第二个月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起,地方当局即将民户的田土,按唐田令规定的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因为各户原有田土多寡不同,所以各户的“已受田”多寡也不同,有的民户更是应受田全未受。这种按田令规定的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登记各户“已受田”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开元年间。这种授田制下,各户的“已受田”,仍是多寡不同,其中有些户的“已受田”,明显超过一丁10亩,有的且超过甚多。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唐廷颁布《巡抚高昌诏》, 指示“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注:《文馆词林》卷六六四《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武进董氏影印本,1924年版。)。随后,我们便看到地方当局遵诏将部分官田授给原佃官田的国家佃农,授田的标准是一丁常田肆亩、部田贰亩(按:相当于一丁常田肆亩、三易部田陆亩,计10亩)。(注:见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前后侯菜园子等户佃官田簿,《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第239—240页。 该件无纪年,同出文书有纪年者为贞观十八年。该件未标明为官田,但同出文书多件与官田(包括上、中、下价)有关,联系该件所示超过授田标准继续纳高额租价的情况看,无疑是官田。所授官田是否为废屯,不详。但入唐后曾废部分屯田(总数不少于50顷)却信而有征。开元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废屯税子粟麦四千石”即可为证。见《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61页。)原佃官田不及此数者,注为“欠”(“常田”、 “部田”互不抵折);原佃官田超过此数者,按上、中、下价照旧纳租,上价亩租9斗,中价亩租7.5斗、下价亩租5斗。(注:此“上价”、 “中价”、“下价”标准系池田温计算而得,见池田温《初唐西州土地制度管见》,《史滴》5号(1984);《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有译文, 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在此前后,西州当局又将“移户”(强制内迁户)的田土分给百姓,授田对象、授田标准同于“官田给百姓”的一丁常田肆亩、三易部田陆亩。(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第243—269页。移户的田土原非官田,但强制内迁后,其田土便作为官田处理。)上述两种文书所反映的授田制与开元天宝年间的大谷欠田文书、退田文书、给田文书所见的田制一脉相承。从大谷欠田、退田、给田文书所见的情况看,官田给百姓的田土是要还授的。这种田制的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应还授田土类别、给田文书的编造手续、所给田土的分布情况等等都不符合《田令》规定。《田令》规定的应受田对象是丁男、18以上中男、老男、寡妻妾以及当户时的中、黄、小男女。应受田标准是宽乡丁男100亩,狭乡60亩(注:《田令》上述规定也入于“律”,《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曰:“王者制法,农田百亩,其官人永业田准品,及老、小、寡妻受田各有等级。”);而西州“官田给百姓”的授田对象仅限于丁男(注:中男、寡妻妾虽具受田标准(常田2亩,三易部田5亩),但实际上,中男未见单独作为应受田对象,寡妻妾更未作为应受田对象(只是在夫亡后可以暂时保留以上数额的田土)。),授田与土地还授标准是一丁常田4亩、部田(三易)6亩。《田令》规定永业田不在还授之列(注:《唐律》虽未明文规定永业田不还授,但规定了户内永业田要种桑榆枣果等,实质上也确认了永业田不还授。);西州“官田给百姓”制,永业田则也在还授之列。《田令》规定,“诸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豫校勘造簿”,亦即里正应豫校勘造欠田簿、退田簿、给田簿。(注:《唐律》卷一三《户婚》也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失一事,笞四十,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可见里正是收授田土的主要责任人与直接责任人。县令只是负领导责任而已。)而西州“官田给百姓”的给田簿则是由县令填写的,受田人也是由县令指定的。(注: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58页。 )《田令》规定“诸给口分田,务从近便,不得隔越”(注:所给之田应在本乡里范围之内。只有在他乡“有余”前提下,才可以隔越授田在他乡;也只有在本乡“有余”情况下,才可能允许他乡人在此受田。)。而西州的“官田给百姓”,因为所受的是官田,所以受田者的田土常隔越在他乡、他县,从而形成此乡人受田于众彼乡(甚至于彼县),众彼乡人又受田于此乡的田土分布犬牙交错情况。因为西州的“官田给百姓”制度,几乎所有的重要方面都不同于《田令》规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唐代西州一丁10亩的田制,不属均田制范畴(注:关尾史郎:《吐鲁番携来唐代田制文书的理解》,《集刊东洋学》61号,1989年;金铎敏《唐代吐鲁番地区的退田、给田之意义》,《五松李公范教授退任纪念东洋史论丛》,1993年。),或径直认为唐代西州存在两种授田制度。(注:杨际平:《唐代西州欠田、退田、给田文书非均田说补证——兼论唐代西州的两种授田制度》,《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也谈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再论唐代西州的两种授田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但也有学者仍然认为,一丁10亩的田制属均田制范畴。如卢向前先生就认为:“式又是令的‘通变’”,因而,“属于均田制范畴,不同于田令规定的授受土地额是一直存在的”。他还认为:“唐代西州田制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注:卢向前:《唐代西州均田制的普遍意义》,《文史》第44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
迄今为止,唐前期可确证真正实行了土地还授的,就是唐代西州这种一丁10亩“官田给百姓”授田制。如果唐代西州这种田制属于均田制范畴,那么,唐代均田制下的确实的土地还授就有了例证,而且还可以以点带面,进而推论其他地区也可能真正实行了土地还授。否则,这唯一的例证就不能成立,一切都又另当别论。正是因为这样,唐代西州一丁10亩的官田给百姓制是否属于均田制,就成为当前研究唐代均田制实施状况的争论焦点。而其关键就在于“式”可否通变“令”。如果“式”可以通变“令”,那么,两种授田制还勉强可以合而为一,否则,就不能不承认它们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授田制。
《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使这个本来相当棘手的问题变得很容易解决。《唐令·田令》有关均田制部分计44条,其中既包括基本原则,也包括十分细致的实施细则。大体上说,第2条、第3条(有关民户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第6条(有关官吏应受田额)、第7条(有关永业田性质)、第24条(有关口分田不得隔越的规定)、第19条、第20条(有关土地买卖的规定)属于原则规定;第4 条(有关狭乡新受田口分田减半规定)、第5条(关于易田倍给规定)、第9条—第14条(关于官吏永业田请授、继承、追收办法的规定)、第17条(关于官吏口分田追收办法规定)、第22条(有关因王事没蕃、伤残、身死者的田土处理办法)、第25条(有关退田时限的规定)、第26条(有关还公田不得割零的规定)、第28条(有关授田顺序的规定)、第29条(有关换田的规定)、第33条(有关河道改流,新出地处理办法的规定)、第34条(有关公私荒田借耕等的规定)、第35条(有关竞田收益处理办法的规定)、第35条(关于水卤、沟涧等不堪耕种地的处理办法的规定)、第21条、第30条、第32条(有关工商户、僧尼、道士、女冠、官户、在牧官户奴等授田办法的规定)等等,都属于实施细则范畴。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显示,唐《田令》的多数条款本身就已经是实施细则。(注:过去许多学者认为,《令》只是基本原则,而《式》则是《令》的实施细则,凡《令》都必须通过《式》来实施,这种看法不合唐代实际,至少说很不准确。)
《唐令·田令》提到“乡法”的有两处:其一是《田令》第5 条“诸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宽乡三易以上者,仍依乡法易给”;其二是《田令》第8条“诸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 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注:此据《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复原。有的学者尝据《通典》卷二认为此条为“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汪篯《唐田令试释》(载《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据《唐律疏议》引田令,认为《通典》“每亩”为“每户”之误。宋家钰《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永业、口分田的区别及其性质》(《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又予以申说。 戴建国先生则参考《天圣令》将此条复原为“诸永业田,每户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笔者以为《唐律疏议》既然明确称引此条为“诸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即当以此为准。)《田令》中有关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应给田土的分布等条款,皆无“任依乡法”的规定。
《唐令·田令》提到“式”的共三处:其一是《田令》第34条“诸公、私田荒废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听……其借而不耕经二年者,任有力者借之,即不自加功转分与人者,其地即回借见佃之人。若佃人虽经熟讫,三年外不能耕种,依式追收改给”;其二是《田令》第47条“诸屯应役丁之处,每年所管官司与屯官司准来年所种色目及顷亩多少, 依式料功申所司支配”; 其三是《田令》第51条“诸屯每年所收藁草,饲牛、供屯、杂用之外,别处依式贮积”。此三处提到的“式”都是对《田令》相关条款进行补充,而不是对令文进行什么“变通”。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武德七年初颁《田令》时,并没有“式”。《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记“式”的渊源:“后周文帝初辅魏政,大统元年,令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七年,又下十二条之制。十年,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谓之《大统式》。”《隋书》卷二五《刑法志》记此事为:“周文帝之有关中也,霸业初基,典章多阙。大统元年,令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奏之。七年,又下十二条制。十年,魏帝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班于天下。”可见,《大统式》产生于“典章多阙”之时,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对“今古”典章制度进行变通的产物,在当时兼有律、令性质。论者由上引《唐六典》记载得出“式又是令的‘通变’”的一般性结论,显然于法无据。(注:大统十年,只有《式》而无单行的《令》,《令》既不存,自然谈不上由《式》对当朝的《令》进行所谓“通变”。)隋及唐武德年间皆曾修《律》、《令》,但当时却并无《式》。直到贞观十一年后,《律》、《令》、《格》、《式》始并存。《旧唐书》卷五○《刑法志》载,贞观《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书省列曹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计帐名其篇目,为二十卷”。据此可知,《户部式》为其中一篇。《户部式》是否单独成卷,不详。唐代,户部司“掌户口、土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姻婚、继嗣之事”(注:《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户部式》亦当包括上述内容。唐前期户部司的主要职责是管财政收入,所以,《户部式》的重点理应放在籍帐管理与赋税征收上。(注:《唐律疏议》卷二八《捕亡律》“疏议”在解释“边要之地”时引《户部式》:“灵、胜等五十九州为边州”。)就目前所知,《户部式》与《田令》有关的,只有上引《田令》第34条提到的1条。 卢向前先生称引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与《户部式》有关的3个例证中,(注:卢向前:《唐代西州均田制的普遍意义》。)一例(高屈富请地事)件残,不知是否与公私田荒废地有关;另两例(麴孝逸请退“沙卤不生苗子”地与康大智请“废渠道见亭无人营种”地事)其案卷批语中提到的“式”应即《田令》第34条提到的“式”,其内容恰好与借耕私田荒废地与借耕、请射公田荒废地等事有关。《唐会要》卷八五《逃户》有二处提到“式”(户部式),其一是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裴耀卿营公田建议中谈到“其狭乡无剩地客户多者,虽此法未该,准《式》许移窄就宽,不必要须留住”;其二是“广德二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前者之《式》应与《户令》有关,可置勿论;后者之《式》也恰是上引《田令》第34条提到的那一条与《田令》第2、3条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的规定无关的《式》。
再从《令》、《式》关系角度来看。《令》与《式》并非平行关系,《令》高于《式》,规定《式》;《式》则服从于《令》,服务于《令》。具体点讲,也就是《式》不违《令》,《令》有明文规定的,严格依《令》而行;《令》所未详者,《式》予以具体化。如有关水利灌溉与碾硙用水问题,《唐令·杂令》规定:“凡水有溉灌者,碾硙不得与争其利……凡用水,自下始。”(注:《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员外郎”。)至于如何管理用水,则语焉不详。《水部式》则对《杂令》所未详者予以具体化。《水部式》规定:“诸水碾硙,若拥水质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硙即令毁破。”“诸溉灌小渠上先有碾硙,其水以(已)下即弃者,每年八月卅日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自余之月,仰所管官司于硙斗门下着锁封印,仍去却硙石,先尽百姓溉灌。若天雨水足,不须浇田,任听动用。其傍渠疑有偷水之硙,亦准此断塞。”再如从军征讨、从行与公使于所在身死者的处理问题,《军防令》规定:“征行卫士以上,身死行军,具录随身资财及尸,付本府人将还。无本府人者,付随近州县递送。”《丧葬令》规定:“使人所在身丧,皆给殡殓调度,递送至家。”《兵部式》则规定:“从行身死,折冲赙物三十段,果毅二十段,别将十段,并造灵舆递送还府。队副以上,各给绢两匹,卫士各给一匹,充殓衣,仍并给棺,令递送还家。”(注:《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引。)皆可见,《式》只是对《令》所未详者作补充,而不是对《令》明确规定的条文作“变通”。《式》与《令》论理是不应该有矛盾的,万一发生矛盾,那就应该通过修改《令》、《式》,使之统一。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有关祭祀礼仪的一场争论就说明了这一点。 时《祠令》取郑玄说,圆丘祀与南郊祀并存,《吏部式》取王肃说,“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载圆丘”。礼部尚书许敬宗就认为“《式》文既遵王肃,《祠令》仍行郑义,《令》、《式》相乖,理宜改革”。时《祠令》划分了各种祭祀的等级,但对祭仪中的笾豆之制未做明确规定,而《光禄式》则规定了各种祭祀的笾豆之制。时《光禄式》规定:“祭天地、日月、岳镇、海渎、先蚕等,笾、豆各四;祭宗庙,笾、豆各十二;祭社稷、先农等,笾、豆各九;祭风师、雨师,笾、豆各二。”许敬宗又认为此制与《祠令》规定的祭祀等级不相符合,说“寻此《式》文,事深乖谬”。唐高宗接受了许敬宗的建议,准备对有关令、式作修改,“诏并可之,遂附于礼令”(注:《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诏令虽高于《令》、《式》,但未到统一修改《令》、《式》时仍未立即修改《令》、《式》,而是暂以诏令的形式附于《礼》、《令》。)。由此更可见,《式》只能对《令》所未尽事宜做补充,而不能违背《令》文规定,另搞一套。综观《唐令·田令》全文,我们可以确信:《田令》对民户各种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的规定,对永业田不必还授,口分田不得隔越,里正对土地还授负直接责任等等的规定,都很明确具体,既无需《户部式》再做补充,更不容《户部式》进行什么变通。《式》、《令》关系如此,自然不可能将唐代西州明显不合《田令》的一丁10亩的官田给百姓制人为地纳入均田制范畴。
三、《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对均田制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纠正了人们对《田令》、对均田制的片面认识,解决了均田制研究中许多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同时也给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讨论均田制是实行,或者没有实行。而实行与否的标准就看是否实际收授田土。以为只有实际收授田土,才算实行均田制,否则就不算。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不合《田令》精神。按《田令》规定,由政府实际收授田土是均田制的实行,把各户原有田土登记为已受田,或以户内帐面调整方式进行土地还授,也是均田制的实行。因此,讨论均田制是否实行已经毫无意义。今后要研究的是均田制如何实行?主要是按《田令》的哪些条款施行?
《唐令·田令》既规定了应受田口的应受田额,又规定“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体现了立法者的土地国有理想与土地私有制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的矛盾。在具体实施均田制时,这两者可以统一起来,但有先后主次之分。实行均田制时,首先要做的显然是将各户原有的土地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然后再考虑是否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实际授田。政府给民户实际授田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各地政府掌握足够的官田与荒废地。如果没有足够的闲置的官田、荒地,政府的实际授田就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政府实际授田之前,先要研究土地资源情况,亦即研究各地官田、荒地的情况,测算其大体数量,了解其使用情况(注:官田的使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是否可能用于授田。军屯可以用于授田,但这样做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对军队的供给。所以实际上很少用军屯来授田。采用租佃方式经营的官田如果用来授田,通常也是授给原佃官田的国家佃农,一般不会采取大规模夺佃另授他人的办法。否则,又将出现如何安置原佃官田的国家佃农的问题。),研究政府对官田、荒地所采取的措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准确把握均田制的实施情况,才有可能具体了解均田制对社会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产生了什么影响,产生了多大影响。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均田制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关于政府授田,还有个形式问题。把部分官田分给贫民并非均田制特有的做法。如西汉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就“罢中牟苑,赋贫民”(注:《汉书》卷七《昭帝纪》。)。东汉永平九年(公元66年),也“诏郡国以公田赐贫民各有差”(注:《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公元786—848年),也在那里计口授田,每人10亩。随后的归义军时期,也以请田方式将大量田土分给百姓。上述这些措施,虽与均田制有一定的共同性,但都不具均田制的基本特点,所以人们都不认为是均田制。类似措施,唐前期也应存在,亦应作如此观。因此,我们在研究唐前期的官田给百姓时,就必须研究其特点,看它是否具有均田制的特有形式,是否属于均田制范畴。
如前所述,均田制下究竟如何授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原先的土地占有情况。因为各地官田、民田的数量及其占有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很难用一两个典型事例加以概括。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均田制实施状况时,不仅要注重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实证材料,而且还要努力发掘、利用传世文献资料(包括时人论均田制、井田制,唐前期民户著籍情况等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唐代的均田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也才有可能还唐代均田制真面目。
最后还想提一点希望。由于史籍记载上的问题,过去对《田令》与均田制的了解都比较片面,因而许多历史教材与著作介绍唐《田令》与均田制时也比较片面。现在《唐令·田令》既已完整复原,对唐《田令》与均田制的介绍理应有所改进。《唐令·田令》文长,全面介绍或有困难,但至少可以做到:在介绍《田令》第2条时, 不遗漏“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一句;在介绍《田令》第27条时,不遗落“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一句。这样就可以避免读者对《田令》与均田制产生误解。
附《唐令·田令》各条在《天圣令》中的相应位置
《唐令·田令》顺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在《天圣令·田令》中的位置 1 2
在《天圣令·田令》随附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唐令》中的位置
《唐令·田令》顺序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在《天圣令·田令》中的位置
3 4 56
在《天圣令·田令》随附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3031 3233 34
《唐令》中的位置
《唐令·田令》顺序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在《天圣令·田令》中的位置 7
在《天圣令·田令》随附 35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唐令》中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