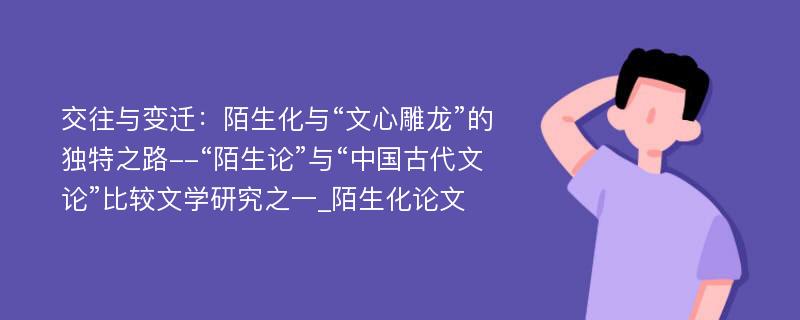
通与变:陌生化与《文心雕龙》的殊途同归——陌生化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比较文学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比较文学论文,文论论文,殊途同归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3)04-0095-04
一 文学艺术活动的演进规律与陌生化理论
按照通常的理解,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劳动。鲁迅先生更认为,作为劳动号子的“杭育杭育”即是最早的文学作品,其流派也属“杭育杭育”派。即便是作为劳动的号子,也要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花样翻新。贡布里希则指出,即便纯粹的游戏也需要不断增加花样和难度,以避免单调进而获取游戏的满足。他甚至把这种现象叫作“有层次逐渐复杂”的过程[1]。而文学艺术发展、演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之极其相似的过程。
任何一种文学艺术样式或者文学艺术创造,一经产生,无不显现新颖与鲜活,充满无限吸引力,经过无数的一代代作家的琢磨、推敲和开掘,使之逐渐走向丰满完备,最后达到或近于达到成熟的顶峰,也就是达到“体大虑周”的地步时,则不可避免要由顶点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中的旧程序“随着不断的使用会变得僵化,结果是逐渐丧失自己的功能和活力”[2],“不再成为有效的东西,而习以为常的事物已不为人所注意逐渐成为无意识的东西;新的程序作为异端被提出,好像是进行对照,以便把认识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性中引出来。”[3]“规范程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衰败。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独出心裁的创新。追求创新的反对矛头一般指向规范的、传统的、‘一成不变’的程序。”“衰败的、陈旧的、古老的程序令人感到是复活的残迹,已失去意义但任凭惯性继续存在的现象,活人中间的死尸。相反,新程序则以其超凡脱俗使人耳目一新。”[4]
作为文化的独特样式的文学艺术,它们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有着与文化一样的大致轨迹。整个文学艺术的内部发展规律,说到底,就是一个背离——程式化——背离或者程式化——背离——程式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陌生化”扮演着根本动力的角色。不管是对一个词的别致使用,或是对一种色彩的异想天开式处理,还是对整个艺术观的根本颠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变形”“变异”“偏离”和“背反”,一浪推一浪地推进着文学艺术实践不断走向成功,不断走向深入,不断走向未来。也正是这些“变化”“变形”“变异”和“背反”,源源不断地为欣赏者提供着全新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震撼,促使他们不断深入体悟人生,体悟世界,体悟生命的本质意蕴。
艺术实践者们求新、求异、求奇、求变和求超越的趋势,正是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极力宣扬的陌生化的本质内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说:“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感觉,则没有新的表现”[5]固定的模式,固定的方法,不变的刺激,种种机械重复早经文艺实践证明是造成“文学死亡”的根源,因此求新、求变、求异就成了文艺实践的永恒追求。“肯定创造、肯定变化、差异和多样性,反对公式化、单一化、反对‘榜样的力量’也就是具有进步的倾向性。与之相反,那些因循守旧,秉承统一的意志和使用规定的‘创作方法’制造出来的作品,以及提倡和肯定这些作品的理论,则具有封闭、保守、趋于单一的倾向性”[6]。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宣称:“艺术家总是使事物造反的罪魁祸首。”[7]
我国学者王国维则说:“盖文体通行日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士也难于从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8]
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和人们接受事物的心理物理规律双重作用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这个偏爱诗歌的民族,不断创造出四言、五言、七言、律诗绝句、词、散曲和小令等等一系列诗歌体裁。当唐诗的潜能耗尽之时,宋代诗学以议论入诗的风气,给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诗至清末衰微之际,一种此前不入流,被贬为“小说家言”的“卑不足道之体”——小说,勃然兴发。而当文言文日益与口语脱节,表明其不适于表达新观念新现实之际,白话文运动骤然兴起,在数年间,摧枯拉朽,风靡天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原有文学样式或文学创造的基础上求新、求异和求变的结果,在陌生化原理看来,仍然属于陌生化的功效。而陌生化的方法,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回归或复原,也就是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用歌德的话说就是:“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是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常的平凡事物中现出引人入胜的一面。”[9]另一条途径则是“暴力突破”,即发生根本的质变,也就是“狂飙突进”的过程。
二 文学艺术活动的演进与陌生化“度”的问题
在陌生化看来,“作家或艺术家全部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使作品成为具有丰富可感性内容的物质实体,使所描写的事物以迥异于通常我们接受它们的形态出现于作品中,借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延长和增强感受的时值和难度。”[10]变形,被视为艺术的手法,求新求异求奇被认为是艺术的普遍诉求。“变形”可以说是艺术的“铁律”,但是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别林斯基在谈到典型时说:“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11]雅各布逊也指出:“只有以熟悉为背景,不熟悉的才能被理解。”[12]如果没熟悉的基础与前提,不熟悉就不能被理解,这也就是说,变形也好,背离也好,反拨也好,背反也好,都必须把握一个度,过了那个度,陌生化将陷入不可知的泥淖。马雅可夫斯基在《怎样写诗》中谈到:“当写出一首准备去打印的诗时,一个人必须考虑到印出的文本大致会怎样被人当作印出的文本而接受。一个人必须注意到读者的平均水平,一个人必须采用各种方法将读者的接受大致带到它的作者所赋予诗行的那一形式中去。”艾亨巴乌姆也强调:“艺术的生命力在于接受”[13]。陌生化的目的是增加接受的难度,但绝不是拒绝被接受。文艺家如果只一味求新求异或者不顾读者的实际水平,造成自己与欣赏者之间的过大距离,其结果是作品虽将广大读者从索然无味中拖了出来,却又立即将之推入迷雾之中。因此,旧形式不是被任意破坏或解构,不是彻底消亡,而是从中心变为边缘,从主流变为支流,从前景退到背景,从显在过渡到隐在。“任何一种文学中的继承,都首先是一场斗争,是对旧的整体的破坏,和以旧因素为基础的新的建设。”[14]
如果说,文艺家和欣赏者之间有一个默契的话,这个默契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必须随时不断得到突破和更新,从而形成新的默契。过分的稳定和过分的剧变对文艺的接受和沟通来说都是不利的。过分的剧变就会造成作家自设门限,拒绝接受;而过度的稳定,则是不思进取,故步自封。
艾亨巴乌姆对超稳定的情形作过猛烈抨击:“我们对因循守旧的喜爱,有时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总是兴致勃勃地重复同一样东西。规范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文学史中具有这样强大的抵抗力。在这里,它常常达到令人着魔的程度,同一僵死的模式可以存在一二百年。”[15]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并不去努力寻求新鲜感和距离感,而是用一种超稳定结构极力抹平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差距,专意迎合人们的认知定势、心理定势和接受定势,以熟悉的叙述方式,让人们陷入语言上、思想上和感受上的惰性。它也提供刺激,但这些刺激早已程式化和套路化,并不能提供给读者任何新的东西。港台的一些动作片、武打片、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应该属于此列。通俗文学的目的就是使读者不经过任何努力就完成文化上的消费,而对文本的理解和重建,对体验的开拓和深化,对认知的提升和胸襟的开阔等等毫无意义。通俗文学说白了就是文化快餐,一盒与一百盒全一个味。
三 《文心雕龙》对文学艺术活动演进规律的辨证
“陌生化”理论的提出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但是对陌生化所揭示的关于文学艺术活动演进规律的体验和艺术实践绝非某一时代或某一民族所独有,而是古今中外文艺实践活动中最基本最受普遍关注的基本命题。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南齐末年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关于文章写作、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的一部最全面、最有系统性的著作,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精深、结构严谨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公认,对文艺理论研究者来说,《文心雕龙》是必须研习和精读的论著。只有把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的精华与现代文艺实际和西方现代文论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壮大和发展。对文艺演进的问题来说,这一路径同样适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通变》《神思》《体性》《夸饰》《定势》等多个章节中,都涉及文艺演进的内容。在《定势》中首先承认近代辞人逐奇好诡的倾向,并指出这是出于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的结果。“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刘勰认为这种“逐奇好诡”“穿凿取新”的根本方式给人的感觉就是难,就是反常,就是异态。“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而且刘勰进一步指了这种“反正”“效奇”的具体作法:“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16]。这种情况特别接近“陌生化”理论的观点。
在刘勰看来,“厌黩旧式”“穿凿取新”的确是一种趋势一种倾向,但这种趋势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文艺演进过程中“度”的问题,因而他在《定势》中指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17]。怎样才能做到不温不火,恰如其分呢?刘勰认为应该是“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18]。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真正熟练旧规、精于领会的人,才能由新奇而达到巧妙的艺术境地,而那些一味只求奇异的人,却因既失去原来的体式又达不到创造的目的,成为不伦不类的丑八怪。刘勰强调文艺活动的创造性,认为“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术,谋篇之大端也”[19]所谓“玄解”“独照”,指的是深邃和独到的体悟,也就是独创性的发现。刘勰承认差异,承认文学家应该各有特点,各有风格,“各师成心,其异如面”[20]。认为文艺的创造过程,往往打破既有的规范。他在《神思》中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21]在实际创造过程中,表现内容的复杂性就会导致变化变异的发生。“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22]虽然这些新意不过是《定势》中所说的“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23]的结果,但这种创新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功效,以至于吸引为数众多的实践者不断探索。《夸饰》中说,“于是后进之才,奖气挟声,轩翥而欲飞,腾掷而羞局步。辞入炜烨,春藻而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调。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感则声共泣偕。信可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24]这里的“披瞽而骇聋矣”让我们又一次想起了杜甫的名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当然,要真正实现有意识的求新求变求奇,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对艺术规律的精深拿捏。因而只有《神思》所谓“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25]
刘勰对文艺演进的认识是相当全面的,在《通变》一节里专门论述了文艺的演变及其规律。首先梳理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之前各朝各代文体文风的演变。“是以九代咏歌,志合天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而且指出了这种演变的原因:“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26]
当然,文艺并不是一味的创新求异,还有个继承的问题。刘勰则以具体的事例说明了这个道理。《通变》说:“夫夸张声貌,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杨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刘勰指出:“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27]
刘勰对文艺的演进的认识也是相当辩证的。“陌生化”理论指出,所有的创造、创新、求新、求异、变异和变形,甚至荒诞和谬误,都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熟悉的背景上进行,是以旧因素为基础的新建设。也就是雅各布逊说的,只有以熟悉为背景,不熟悉的才能被理解。
刘勰特别强调了文艺创造过程中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指出文艺创造有不变的因素,有可变的因素,首先要紧的是掌握不变的规矩,然后才可以去求变、求新、求异和求奇。所谓“通变”者,通同与变化也。“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28]
在解决好“通”与“变”,“陌生”与“熟悉”的辩证关系以后,刘勰进一步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9]文艺演进的规律就是这样,“通”与“变”,“陌生”与“熟悉”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通”和“熟悉”是文艺发展的根源,是其赖于存在的基础,而“变”和“陌生”则是文艺发展的动力,文艺发展的永远的未来。“日新其业”,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每一次创造时都要铭记的原则,否则就不能叫创造,而是重复自己,对文艺和文艺创作者来说,这意味着死亡。刘勰更是鼓励人们,顺时求变不必犹豫,更重要的是抓住时机促成飞跃,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大家、巨匠,为文艺的发展作出跳跃性的贡献。尤其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无疑跟我们一直坚持的陌生化的两条途径发生了奇妙的吻合。“望今制奇”,指的是结合当代的实际情况,“暴力突破”,出奇制胜,产生陌生化的效果。而“参古定法”即是复归或还原,“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恢复文艺古老的诗性本质。如此巧合,令人不能不惊叹古人的深邃与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