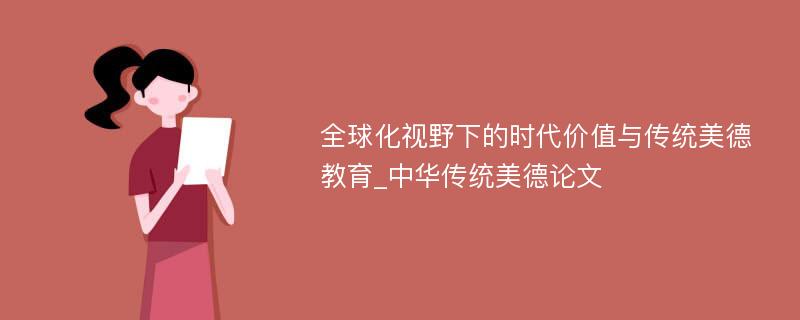
全球化视域下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及现代教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传统美德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怎样对待文化道德继承问题,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备受学界学者关注但又未有共识的开放式课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道德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党的16大报告明确和深刻地提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表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极其重视对传统道德伦理资源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试图在全球化特殊的际遇下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及现代教化这一视角,探寻传统美德承接如何可能的问题,力图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承接的理论和实践难题提供一种分析与解答路径。
一、全球化际遇和传统美德的现代失落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本质体现。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在全世界的运作和扩张过程,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元素,资本具有扩张的本性,因此,早在资本形成之时,就预示着将会出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明确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安家落户,到处开放,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奔走于世界各地,开辟国际市场,把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了全球性的。”[1]一个半世纪后的世界现实图景印证了这个科学预言。到了20世纪末,以信息与通讯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所提供的新基础设施为根基,以及在政府和国际机构所执行的解除管制与专业化政策的协助下,世界经济真正变成了全球性的。正如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描述的那样:“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向全球体系迈进,这种渗透被愈益显著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历史上的人类所聚居的世界显然不同。”[2]中国作为“后发”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在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前打开了紧闭多时的国门,全球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际遇。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使命,一踏上平稳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就面临着席卷而来、无所不入的全球化浪潮。这股浪潮方兴未艾,使世界越发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比“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起步时的全球性扩张要深刻得多、广泛得多。全球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际遇,不仅给国人带来了器物上的改观,而且夹杂着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结构、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气质,从而推动了时代精神的嬗变,冲击和消解传统的伦理价值理念,同时也建构和催生出新的伦理价值理念。在现代化的全球视野里,任何民族对现代化道路的寻求最终都要求索伦理道德精神的现代化之路。我国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方式开启了。也许没有人否认经济是开启现代化的动力,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其思想的变革却是以‘伦理的批判’为先导的。无论是20世纪初‘历史进程意义’上的开启,还是20世纪末叶‘经济变革意义’上的开启,都无一例外地与伦理的批判相伴随。这与其说是一种偶然,不如说是一种必然。这个必然性至少蕴涵着这样的问题: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化思想资源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中国现代化的开启与传统的批判认同具有不可分割的意义。”[3]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可供今天借鉴的道德资源,但是中国传统道德在中国现代史上经历了一段长期被否定的历史。“五四”运动时期,出于对民主科学理性启蒙的急切期待,激进的启蒙者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从理论上对延续了五千年而不衰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引来了“德先生”、“赛先生”,企图以此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认为这是中国五千年从未有之大变局,除此别无他途。然而,过于急切的做法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并未能让中国跟上西方国家前进的轨道,反而如同鲁迅笔下描述的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泼掉的结局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加分析地摒弃了。当时批判的重点是旧道德,亦即传统道德,这种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反对其专制的、等级的、封建的消极因素,无疑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而不是冷静的、理性的、在分析基础上的合理批判。建国后阶级斗争一度成为治国之纲,把阶级的对峙、斗争与决裂简单地移用到文化继承中,用政治方式解决文化和思想问题,出现了一种否定传统、摒弃“旧”文化的倾向,结果造成了重大的历史悲剧。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到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这些原属“传统道德的继承问题”的学术探究,被错误地定性为政治态度问题,由此,学术探知彻底演变成了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全面否定传统、毁灭文化道德遗产的简单粗暴态度扼杀了所有理论和实践上继承探索的努力。到了20世纪末叶,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我国再一次掀起了文化反思的高潮,此次的传统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对西方文化的充分肯定,把反传统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新旧交替中的焦虑,价值转换的真空,成为人们投向西方文化的契机。今天,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步向深入之时,全球化叩开国门之际,“传统继承”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这次我们需要的是深思熟虑的理性考量。我们不能再漠视传统美德在现代的失落,而是应该发掘其深含的时代价值,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二、全球化视域下传统美德的价值彰显
在全球化际遇下,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在文化和道德上的特殊性,这个民族将会部分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性。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并非全然与全球化生存方式格格不入,其精华性的、作为优秀文化积淀的精神理念深深地注入民族性格之中,仍是全球化时代人们弥足珍贵的文化传统与基本价值。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下我们应该对支撑民族的历史、组建当代人生存方式的传统抱以尊重和敬意,努力维护和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和道德的特色。全球化视域下传统美德的价值彰显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这是源于多元文化的寻根意愿。全球化并不等于雷同化,坚持和发展文化多元性,这是人类必须确立的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文化立场。当前我们是从多元文化的角度,特别是面对全球意识背景下所出现的寻根意愿出发来探讨传统美德的价值。各国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强烈依恋很可能不是全球化趋势所直接造成的,但却是全球化带来的间接后果之一。寻根意愿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封闭,或是坚守固有的文化传统。对于自己的传统尤其是源头性的传统,我们不能采取一味的理性追求的态度和方法,而应该尊重我们的传统,并以此作为文化和精神上的家园。“传统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4]而我们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对传统的反复解构和涤荡,一次又一次动摇了人们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家园,是造成目前中国的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重要根源。应该说,传统,尤其是源头性的传统,因其不可“解释”,首先应该是人们认同的对象,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理性反思的对象,对于它,包括对日后一些产生过深远而复杂影响的传统,合理的态度应当是“理解”,甚至是“同情”、“敬意的理解。”[5]事实上,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有何种想法,无论以何种方式“反传统”,传统始终是反不掉的。所以我们要有开放的心灵对待我们的传统,而不能在割裂传统结构的基础上,对传统进行不可靠的问题讨论与价值抉择。我们需要的是对传统予以理性的审视、批判的扬弃,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发展、积淀传统。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互相激荡的际遇下,放眼世界,我们必须植根本土,重新回到自己文化的根源,从自己的文化根源出发,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其次,这是源于文明对话的现实期待。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1998年第5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定,以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从文明冲突到对话,这是一次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观照视角的转换。全球化是以多元化、消解中心、开放互动、和谐协调为特征,以不同文明的共在共存、互补双赢为表现形式,这些特征和表现形式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当下全球化进程的必然态势。而要维系这种全球文明的发展态势,必须要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来实现。作为后发的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冲撞中,西方伦理价值观的渗入和中西文化与价值的冲突与碰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生长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中西伦理观念在成长基点、人文环境和基本准则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在中西伦理观念的矛盾与对仗中,由于中国伦理文化长期“处于一种长期孤立封闭性自生自长的文化空间结构之中,缺少在多种文化差异中进行比照、交汇、冲撞,从而进行自我反省和调整更新的外围环境与激励机制”[6],面对突如其来的外来价值观念的冲撞,矛盾性、无序性、困顿性就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出现了现代化初期伦理秩序与价值的混乱局面,甚至出现较严重的道德沦落现象。因此我们应在全球化进程中采取积极和主动的应对,应坚守中华民族创建的“道德家园”及其道德传统,自觉地与世界不同的文明传统进行对话,在丰富世界的同时实现自我发展。“在各种文明的冲突和对话中,人们必定要对自己原有的价值体系作出反思和变革,从而追求某种更具有普遍意义和更为健全的文明价值。”[7]由于在各种文明的冲突和对话中往往突破了人们原有文化价值体系的边界,特别需要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与认同,相互借鉴与改造,因此经过历史文化积淀,具有人类共同性、普遍性的道德价值的传统美德也特别需要加以传承和教化。
三、全球化视域下传统美德的现代教化
“教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一种实践智慧——塑造人的精神整体。《说文解字》中解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解释“化”为“教行也”。“教化”者,教而化之也。《北史·苏绰传》中对“教化”有一段形象生动的描述:“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为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使人敬让……。此之谓教也。”可见,“教”需明示,“化”需熏陶;“教”是外部灌输,“化”为潜移默化。具体来说,“教”主要通过道德教育来完成,“化”主要通过营造道德环境,辅以正确的道德评价为手段来实现。教化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人的生存方式。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提到“教化是生活的一种形式,其支柱乃是精神之修养和思想的能力,其范围乃是一种成系统的认识。”[8]他进而在论及西方传统“教化”的现代性意义时,指出:“古典世界为所有塑造西方人的因素提供了基础。在古希腊,关于教化的思想第一次被充分地实现和理解,并且其理解的方式从那时起就一直适应于每一个有理解力的人。在西方,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起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当这个世界被遗忘的时候,野蛮状态总是重现。正像一艘船,一旦割去其系泊的缆绳就会在风浪中无目标地飘荡一样,我们一旦失去同古代的联系,情形也是如此。”[9]他充分认识了西方教育传统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积极意义,对于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而言,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全球化际遇根本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伦理生态与精神价值环境,现代人的道德价值世界在现实境域中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并不容乐观。尽管国家以务实的态度,在全体社会成员当中提倡社会主义道德,然而由于传统道德的价值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作为民族文化根基的伦理道德在人们心理上失去了原有的存在意义,因此,社会主义道德也就丧失了植根的基础。传统美德的现代承接和延续,主要是靠教化来实现。而与传统社会辉煌的道德“教化”功绩比照,在全球化际遇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当下实存的道德的“教化”功能与作用却难有昔日景观。人的生存境遇业已发生了根本置换,但道德教化却还未实现与时代变迁互动、共进的真正的现代性转换,其教育功效与价值无法有效走出低靡处境。如何在全球化的际遇下和现代社会的基础上重整伦理道德,振兴民族精神,挽救中国人的道德危机,已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不妨从“我们生命所系的历史传统中汲取力量的源泉”,充分重视传统美德的资源性价值,通过传统美德的现代教化,突破传统道德教化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对之重构与开新,使之获得“现代性”的品格,真正成为有现代生命力的教育资源。因此在全球化特殊际遇下,传统美德的现代教化不仅是传统伦理体系与秩序向现代伦理体系与秩序转换的桥梁,而且承载实现现代伦理精神构建与现代人格塑造的历史使命。
首先从基础道德教育体系的建构入手,以民族性作为基本前提,确保伦理道德的中国特色,寻求传统美德在普遍意义上被接受的可能性。我们要从传统美德的知识教育入手,使人们具有传统美德的知识。每个民族的人应该首先了解并认同本民族文化。如果人们连传统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何以继承发扬。我们必须关注传统美德的情感体验。传统美德的现代教化,必须激发主体的内在动机、内在生命体验,让个体在真实的关系中产生、积累、孕育情感经验,进而接受传统美德。我们必须深入进行传统美德的养成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道德德性的获得是要后天的实践并通过习惯而逐步养成的,而不能像人的理智品质那样仅靠知识的传播和认知就能有效的。多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比较缺乏这种实践中的养成教育,因此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进行传统美德的养成教育和训练。
其次借助民间与政府两方面的力量,营造适应传统美德教化的人文环境,推动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道德教化是人的内在心灵的整体生长,所以需要现代社会道德环境的支持和营养。优化现代社会道德环境,关键条件之一是社会伦理精神的积极向上。黑格尔认为一个具有现实性的民族必要条件是有其自己的伦理精神实体。积极向上的伦理精神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文化资源之上,并符合当今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现代社会的道德环境应是在经济的必然性之上,启发人们感受到人际的情理联系的意义和价值,并取得和开拓其精神空间,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有积极的作用。社会各界要努力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尤其要发挥社会舆论的威慑力,建立一个扬善惩恶的社会伦理机制。在贯彻和关注社会宏观引导的基础上,有合理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传统美德就会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成为一种促进社会良好发展的伦理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