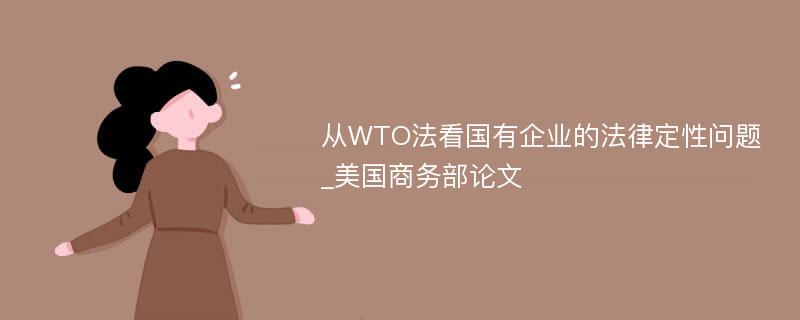
WTO法视野下的国有企业法律定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视野论文,法律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72(2016)03-0005-18 doi: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16.03.001 国有企业改革正在不断深化。但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如何定性,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国内学界和实务界也缺乏深入讨论。①所谓国有企业法律定性,指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应被看作一般商业企业还是被看作与政府性质类似的“公共机构”。在国际经贸法律关系中,这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的大问题。本文以中美反补贴贸易纠纷为例,评析WTO法和美国法对国有企业法律定性的看法,意在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国企改革若能关注国有企业法律定性,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厘清国有企业的法律性质提供依据,则将为对外经贸谈判中维护我国利益提供有力支撑。 一、国有企业法律定性在国际经贸规则和谈判中的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应被看作一般商业企业还是被看作与政府性质类似的“公共机构”,从国内国企改革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进行时,当前的国有企业既带有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控制企业的痕迹,又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并形成了市场化的经营机制。②另一方面,不同的国有企业性质各不相同。有的由于所处行业特点,承担较多政策性业务,公益属性较强;有的则已充分贯彻市场机制、融入商业竞争,具有较强的商业属性。③因此,“一刀切”地为国有企业进行法律定性,以当前国企改革实践情况来看并不可行。 然而,在国际经贸法律关系和对外经贸谈判中,国有企业始终是一个敏感议题。由于国际经贸法律规则中承担国际义务的主体主要是成员国政府,④而非一般商业企业,将国有企业认定为一般商业企业还是政府公共机构对于我国的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若将国有企业认定为与政府性质类似的机构,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经贸规则下就将承担本应只由中国政府承担的义务,这将大大扩展中国承担国际义务的主体范围。首先以贸易救济为例,反补贴措施纠正的是政府补贴对市场造成的扭曲。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a)(1)条规定,提供补贴的主体是“政府”或“公共机构”。若将中国国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则国有企业便与政府一样,一成为提供补贴的主体。换言之,任何企业只要向中国国有企业购买产品或原材料,便如同接受了中国政府补贴,其产品在出口时就可能遭受反补贴调查。 再以投资谈判为例,国有企业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是一项重要议题。⑤作为美方谈判基础的《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第2条第2款规定,“当国有企业或其他人行使该成员赋予的约束、管理或其他政府权力时”,协定成员的实体义务也适用于该国有企业或其他人。尽管有“行使政府权力”的说法作为限定,但美国将国有企业直接纳入双边投资协定的实体义务范围,可见其认为国有企业与成员政府并无实质区别,在承担协定义务时应同等看待。 第三个例证是政府采购。中国正在谈判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现有《政府采购协定》成员方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将国有企业的采购也纳入《政府采购协定》义务范围,本质上是将国有企业与中国政府同等对待。⑥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中,国有企业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国企改革问题放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主题下论述,这说明,国有企业法律定性问题事关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若国内的国企改革不能在国企的法律定性问题上取得突破,在对外谈判中,仅依靠外交人员折冲樽俎未必能在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在复关和入世谈判早期的经历。中国于1986年递交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但复关初期的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主要缘于《关贸总协定》对缔约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要求与我国当时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存在冲突。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谈判人员感觉制约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复关和入世谈判才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⑦如今,同样是事关基本经济制度的议题,中国国内在国企改革中对国有企业的法律定性直接制约了对外经贸关系中中方对外表态的立场和方式,以及中国在国际协定中可能承担的义务范围。 二、美国和WTO关于国有企业法律性质的认定 美国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心怀警惕,倾向于在法律定性上将国有企业与政府归为一类,以使中国的国有企业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虽然美国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国企改革的不完善之处,但从整体上看美国的认定标准比较偏激。对此,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予以坚决回应,但解决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一)反补贴调查:美国关于国有企业法律性质的认定 美国与中国关于国有企业法律定性的矛盾突出表现于贸易救济反补贴调查中。2007年的铜版纸案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第一起反补贴调查。美国商务部在该案中认定,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受政府控制,符合提供补贴的主体资格。⑧因此,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国铜版纸生产企业接受了中国政府补贴。随着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案件不断增多,美国商务部在2009年的厨房架反补贴调查中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法律定性问题。⑨ 美国商务部认为,所有中国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都属于《1930年关税法》第771(5)(B)条规定的“公共机构”。⑩将政府控股的公司作为政府本身对待是美国商务部的长期实践做法。在1987年的荷兰鲜花案中,美国商务部提出五个判断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的要素,分别是:(1)政府所有权;(2)政府在企业董事会中的地位;(3)政府对企业活动的控制;(4)企业是否执行政府政策;(5)企业是否由法律设立。(11)尽管名义上有五条判断要素,但美国商务部承认,在大部分案件中,主要判断要素只有第一条,即政府在企业中的所有权。只要政府在企业中的所有权达到控股水平,即50%以上,就足以证明企业受政府控制和指挥,其余4条判断要素几乎必然满足。这是因为,如果政府拥有企业的多数股权,则通常会任命企业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这些政府任命的董事会成员再选择企业管理层,并做出重大决策,相当于给了政府对于企业活动的控制权。(12)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商务部认为,仅依据政府占多数股权的事实就足以在反补贴调查中将一家国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被调查企业和出口国政府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出口国政府在该国有企业中的多数股权并未导致政府控制企业活动。(13)换言之,政府占多数股权的事实构成了国有企业是“公共机构”的“有罪推定”,除非国有企业所在国政府能提出证据证明其没有控制国有企业的活动。 (二)WTO“双反”案:国际法对国有企业法律定性的初步澄清 2008年9月,中国将美国对华实施的四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裁决(简称“双反”)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审理,即“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DS379)。(14)该案一个主要争议点就是美国在这四起反补贴裁决中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认定为与政府类似的“公共机构”的决定是否符合WTO规则。其中涉及的中国国有企业既包括国有工商企业,如宝钢,也包括国有金融企业,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5)美国商务部依据中国政府占多数股权的事实,将提供贷款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销售热轧钢、橡胶和化工原料的中国国有工商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因此,接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或从国有工商企业购买上述原料的中国企业都被认定为接受了中国政府补贴。中国主张美国商务部的决定违反了美国在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下承担的义务。(16) 首先,要解决国有企业是否是“公共机构”的问题需要廓清“公共机构”的法律含义。中国主张,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a)(1)条将“政府”和“公共机构”并列作为提供补贴的主体,说明二者在功能上是近似的。一个实体要成为“公共机构”,就应当行使政府赋予的职权,且该职权应具有政府的功能和特点。(17)中国认为“公共机构”的根本特征是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并为此代表国家和社会整体行使职权。(18) 在初审阶段,WTO争端解决专家组驳回了中国的主张。专家组认为,中国将“公共机构”类比于“政府机构”是对“公共机构”的概念限定得过于狭窄。(19)在专家组看来,解释“公共机构”含义最重要的参考概念是第1.1(a)(1)(iv)条中的“私有机构”,“公共机构”和“私有机构”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公共领域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关系。(20)既然私有企业是由私人所有而不受国家控制的企业,“公共机构”就是受国家控制的实体,而所有权是判断是否存在控制的关键因素。(21)专家组认为,当政府在企业中的股权达到50%以上时,政府对企业就形成了“控制性利益”。(22)政府占多数股权的事实本身就是证明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清晰且具有高度指示性的证据”。(23)专家组也承认,在极少数情况下,政府拥有的企业在运营时可能完全不受政府影响。但是只有相关企业和政府才拥有企业不受政府控制的证据,因此负有证明该国有企业不是“公共机构”的举证责任。(24)具体到本案,专家组认为中国政府和涉案的中国国有企业未能提出足够证据证明这些企业完全不受中国政府控制。最终,专家组裁决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国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的做法没有违反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a)(1)条的规定。(25) 专家组的裁决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国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的法律依据和判断标准。鉴于专家组阶段的不利结果,中国于2010年12月提出上诉请求。WTO上诉机构的终审裁决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专家组在法律解释和判断标准方面的错误,但是,裁决中的一些说法却为中国国有企业埋下了潜在的不利影响。 在解释“公共机构”含义时,上诉机构首先区分了两组概念,一组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a)(1)条中包括政府机构和“公共机构”在内的政府性实体,另一组是第1.1(a)(1)(iv)段中的私有实体。根据第1.1(a)(1)(iv)段的规定,当私有实体受政府委托或指导,行使一种或多种通常由政府享有的给予补贴的职权且其行为与政府通常从事的行为没有实质差别时,该私有实体的补贴行为可以被归为政府补贴。上诉机构认为,对于私有实体来讲,要认定政府补贴,必须首先建立政府对于私有实体的“具体行为”的委托或指导关系。而对于“政府性实体”来讲,其“所有行为”只要符合法定的补贴形式,就都构成政府补贴。(26)上诉机构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由于政府机构和“公共机构”在性质上同属于“政府性机构”,一个实体若被认定为“公共机构”,那么该实体的行为就应具有政府属性。 对于何为政府属性,上诉机构进一步解释道,《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a)(1)条将“政府”与“公共机构”两个词并列,说明二者在性质和基本特征方面有共通之处。(27)政府的特征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政府通过行使法定职权,享有管理、控制、监督个人或约束其行为的权力。政府的上述特征有助于理解“公共机构”的性质和特征。因此,上诉机构认为,“公共机构”与政府的核心共通特征就在于二者均履行政府职能或者被赋予了履行政府职能的权力。(28)至于哪些职能和权力属于政府职能和权力,上诉机构认为,这要依据各WTO成员国内法进行判断。换言之,一国国内法对于本国政府职能和权力的规定会影响一家国有企业在该国法律框架下是否属于“公共机构”的法律定性。(29) WTO上诉机构还援引其他国际公法原则佐证其对“公共机构”含义的解释。上诉机构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条有助于解释“公共机构”的含义。(30)第5条的标题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其正文内容规定:“虽非第4条所指的国家机关、但经该国法律授权而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但以该个人或实体在特定情况下以此种资格行事者为限。”第5条的释义中指出,该条所涵盖的个人或实体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被授权行使政府职权中的特定内容,国家在某一实体中拥有资本或所有权并非将该实体的行为归于国家的决定性因素。上诉机构由此认为,被赋予政府职权才是“公共机构”的关键特征,而政府所有权尽管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与其他因素一起考察时,也可以成为判断某一企业被赋予政府职权的证据。(31) 至此,上诉机构在解释“公共机构”的含义方面做出了对中国比较有利的结论,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a)(1)条框架下的“公共机构”是拥有、行使或被赋予政府职权的实体。与美国和初审专家组都十分看重的政府所有权不同,上诉机构认为,政府所有权只是判断一家国有企业是否是“公共机构”的证据之一,贸易救济调查机关应当综合所有证据,对国有企业的核心特征和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做出认定。(32) 若上诉机构就此搁笔,中国对于“公共机构”问题的上诉可算获得全胜。但上诉机构似乎意犹未尽,在报告书第318段对如何判断企业是否被赋予政府职权做了进一步阐述,为中国国有企业被认定为“公共机构”留下了隐患。上诉机构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国有企业既具有“公共机构”的特征,也具有“私有机构”的特征。许多证据都有可能证明国有企业被赋予了政府职权。例如,如果一家国有企业在履行政府职能,尤其是履行政府职能的行为是持续和系统性的行为,这便是企业被赋予政府职权的证据。紧接着,上诉机构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表述,它认为“因此”就能说明,如果有证据表明政府对国有企业及其行为实施了“有意义的控制”(meaningful control),则该证据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证明企业拥有政府职权并且为履行政府职能而行使了该职权。政府和国有企业仅在形式上存在联系并不足以证明企业拥有政府职权。但是,如果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是多重的并且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行使,则可以推断企业行使了政府职权。(33) 上诉机构此处的论述存在两个重大问题。首先,从企业履行政府职能的例子直接过渡到政府对企业实施“有意义的控制”,其间缺乏逻辑联系和必要的解释。其次,何为“有意义的控制”,上诉机构没有进一步阐述。履行政府职能和拥有、行使或被赋予政府职权的说法本来已经比较清晰,但上诉机构凭空创造出“有意义的控制”这样一个新概念,又没有任何解释,使得本已清晰的问题再度变得复杂。所谓“有意义”(meaningful),在英文中的含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内涵、值得关注的、重大的”,另一种是“具有某种意图或目的”。(34)若取第一种解释,则“有意义的控制”的程度难以确定,即达到何种程度的控制才算“有意义的控制”是不清楚的。若取第二种解释,所谓“有意义的控制”就变成了政府对企业“有目的的控制”,则证明的角度主要在政府的意图和目的,而不在企业拥有或被赋予的职权。这与上诉机构此前的论断不尽一致。无论如何,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书第318段的表述很容易被曲解,为中国国有企业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埋下了隐患。该问题有待上诉机构在后案中进一步澄清解决。 具体到本案争议的四起反补贴调查,上诉机构首先指出,美国商务部作为贸易救济调查机关,负有主动搜集证据证明中国国有企业是“公共机构”的义务。(35)这直接否定了美国商务部仅凭政府占多数股权就将国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的“有罪推定”,证明公共机构的责任在美国调查机关。对于涉案的中国国有工商企业,上诉机构注意到,美国商务部在反补贴调查过程中,除了中国政府在这些企业中拥有控股权的事实以外,基本没有调查其他证明这些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的证据。上诉机构再次重申,政府所有权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府对企业实施了“有意义的控制”。若无其他证据配合,仅有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中控股的事实无法证明中国的国有工商企业被赋予了履行政府职能的权力,因此无法证明这些企业属于“公共机构”。(36) 对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上诉机构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裁决。上诉机构注意到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认定为“公共机构”时不仅依据中国政府在国有商业银行中拥有绝对控股权的事实,还提出了以下证据:(1)中国的《商业银行法》第34条规定,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2)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仍然缺乏足够的风险控制和分析能力;(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均由政府任命,且党在选择管理层时拥有很大影响力。(37)上诉机构认为,这些证据说明,美国商务部已经考虑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受中国政府控制并履行特定政府职能的证据,商务部还提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事实。因此,美国商务部做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属于“公共机构”的决定是有证据支撑的,没有违反WTO规则。(38)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诉机构裁决美国商务部没有违反WTO规则时存在一个审查标准的问题。上诉机构审查的是美国商务部的反补贴贸易救济裁决。根据WTO法规定,在审查国内调查机关的贸易救济裁决时,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仅能审查贸易救济裁决结果是否有充分证据支撑以及调查机关对现有证据是否做出客观分析,而不能抛开调查机关的结论、根据在案证据重新做出认定。(39)换言之,上诉机构判决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认定为“公共机构”的决定没有违反WTO规则,并不完全意味着上诉机构认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就是“公共机构”,而只是说明上诉机构认为美国商务部在做出认定时的方式和程序合法。 (三)《分析报告》中美国对WTO关于国有企业法律性质裁决的回应 作为DS379案中的被告,美国为执行上诉机构的裁决,于2012年5月18日由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执行上诉机构在DS379案中的裁决:关于中国的“公共机构”问题的分析报告》(以下称“分析报告”),系统阐述了在DS379案判决之后,美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法律定性的看法。(40)然而,分析报告结论使中国国有企业的处境比DS379案判决之前更加不利。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依据多数股权原则,仅将中国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认定为与政府类似的“公共机构”。而在分析报告中,美国商务部根据上诉机构在DS379案中提出的“有意义的控制”原则,大大扩展了认定为“公共机构”的企业范围。分析报告结论认为:所有中国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都是“公共机构”;所有国资参股但需要执行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都可以被认定为“公共机构”;拥有很少或没有国有股份的企业也可能成为“公共机构”,只要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政府对该企业实施了“有意义的控制”。(41) 分析报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中国法律框架下,什么是上诉机构所说的“政府职能”;二是中国政府如何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意义的控制”,使国有企业成为履行“政府职能”的工具。 对于第一部分,即中国“政府职能”的认定问题,美国商务部注意到,上诉机构在DS379案中认为,“公共机构”是拥有或被赋予政府职权,以此履行“政府职能”的实体。各国“政府职能”不问,需要依据各国国内法确定。美国商务部认为,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中国政府具有控制和指导经济发展,以保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职能;制定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履行该职能的重要方式。(42)为了论证该结论,美国商务部首先提到,中国《宪法》第5条和第6条分别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类似表述还见于中国《物权法》、《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政策和措施。(43)美国商务部认为,这些规定说明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政府的职能超出了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市场的一般范畴,还包括干预和指导经济发展,以保障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力量。(44) 接下来,美国商务部指出,中国政府履行上述政府职能的主要方式是颁布和实施各种产业政策。通过这些产业政策,中国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发展目标提出指示,根据政府的意见指导资源配置和企业决策,以达到维护国有经济作为主导力量的目的。(45)产业政策的形式包括五年计划、支持性立法和各产业发展规划。中国各级政府必须执行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不仅为国有经济提供了竞争优势,还控制并指导国有经济发展方向,并要求构成国有经济的国有企业执行政府计划。(46) 在第二部分,分析报告详细讨论了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意义的控制”,并以此得出中国国有企业拥有或被赋予政府职权进而属于“公共机构”的结论。概括而言,美国商务部所谓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有意义的控制”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国有企业在履行维护国有经济占主导力量的“政府职能”中具有特殊职责和地位,享受了诸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指中国政府实际干预和控制了国有企业的行为和决策。分析报告分五点论述了上述结论。 首先,中国政府利用国有企业维护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并通过国有企业执行产业政策,达到政府控制和干预经济发展的目标。(47)第一,美国商务部注意到,中国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享有许多优惠政策,包括获得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接受政府官员的政策指导,以及在基础或支柱型产业中占据垄断地位。这些举措都确保中国政府按其意愿塑造经济结构,使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48)第二,美国商务部反复提到中国各级政府的五年计划、产业规划和执行产业政策的支持性立法。在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中国政府通过审批、控制投资准入、发放进出口许可、限制产能、鼓励技术改造等手段实现预先设定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目标。至于国有企业在其中的作用,美国商务部认为,若中国政府无法控制国有企业的投资和兼并重组等具体决策,很难想象政府能实现其预定发展目标。(49)第三,中国政府通过“抓大放小”的管理方式,引导国有资本向政府指定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聚集,并通过国资委规定国有企业的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以确保企业符合政府指定的发展方向。(50) 其次,中国政府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竞争关系。(51)例如,在电信领域,只有国有企业才能获得市场准入。政府还对国有电信运营商进行重组和资源分配,以避免过度竞争。尽管中国政府声称这是为了让企业更加注重营利,但这最多是有限和受控制的竞争关系。另外,中国政府还干预国有企业的投资和兼并重组等具体项目决策,例如要求日照钢铁兼并亏损的山东钢铁,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资本做大做强的产业政策目标。(52) 第三,中国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国有企业实施控制。(53)美国商务部认为,尽管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国资委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而不能行使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但通过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仍然不能摆脱政府控制。(54)例如,《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管理办法(试行)》中都提到国资委要监督、管理或批准中央企业的投资计划和投资决策,确保投资方向符合政府的产业政策。(55)美国商务部还特别提到国资委负责实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认为该制度通过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利润以及政府向企业重新分配资本,以达到控制企业发展符合政府产业政策的目的。(56)此外,国资委不仅承担出资人职责,还扮演管理者角色。截至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19项部门规章和104项规范性文件;地方国资委发布了超过1600项管理措施。(57) 第四,中国政府控制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并以此确保政府产业政策目标得以执行。(58)美国商务部指出,尽管国资委在名义上有权任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但任命国企最高管理层的实权掌握在中组部手中,副总级别的任命由国务院国资委的党委负责,其他高管人员由国资委人事部门负责任命。(59)中组部的人事任免权对国有企业的运营有重要影响,党委和政府可以通过任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来干预企业经营决策。(60)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可以在相互竞争的企业中轮岗。美国商务部援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说法称,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首先是政府干部,其次才是企业家。另外,中国《公务员法》也将国有企业高管归入公务员序列。(61) 第五,中国政府通过党组织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意义的控制”。(62)中国《公司法》规定,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可以设立党组织。尽管法律没有规定党组织在企业经营中的角色,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美国商务部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2条规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美国商务部认为,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在企业战略决策和人事任免中发挥积极作用,董事会仅负责执行已经制定好的决策。(63)此外,美国商务部还指出,中国民营企业中也广泛存在党组织。因此,美国商务部认为,未来在判断民营企业是否受中国政府控制时,党组织的作用将成为一项考虑因素。(64) 与DS379案之前相比,美国商务部这份分析报告大幅放宽了中国国有企业被认定为公共机构的标准和范围。分析报告恣意发挥并歪曲了上诉机构的裁决,对此中国政府本可以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提起执行之诉。但由于该报告中大量涉及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党和政府的作用问题,内容比较敏感,中国至今也没有将该报告提交WTO进行裁决。 (四)印度诉美国反补贴措施案:WTO对公共机构法律标准的进一步澄清 中国并非美国恣意认定“公共机构”的唯一受害方。在随后“印度诉美国特定热轧碳钢扁平轧材产品反补贴措施案”(DS436)中,“公共机构”问题再次成为主要争议点,上诉机构得以进一步澄清“公共机构”的法律含义,特别明确了“有意义的控制”的法律性质。 印度与中国相似,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改革开始时间比中国更晚。印度国内有大量国有企业,在向美国出口产品时遭遇了与中国相同的问题,其国有企业被美国贸易救济调查机关认定为“公共机构”。这成为印度将美国反补贴措施诉至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主要诉因之一。在DS436案中,争议的国有企业是印度国家矿产开发公司(NMDC)。该公司98%的股权由印度政府持有;公司董事会13位董事中,2位董事由印度政府直接任命,7位董事的任职须获得印度政府批准。(65)另外,该公司的官方网站上明确写道:“印度国家矿产开发公司接受印度政府钢铁和矿产部钢铁司行政控制。”(66)在初审阶段,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接受了美国的抗辩,依据上诉机构在DS379案中提出的“有意义的控制”理论,认为美国贸易救济调查机关在反补贴裁决中将NMDC认定为公共机构是适当的。上诉机构于2014年12月8日发布DS436案裁决报告,驳回了专家组的初审裁决,并明确判决美国贸易救济调查机关将NMDC认定为“公共机构”违反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a)(1)条规定。(67) 在上诉过程中,美国主张,依据上诉机构在DS379案中对“公共机构”法律含义的解释,当存在政府对国有企业“有意义的控制”时,贸易救济调查机关不需要再判断该企业是否行使政府职权。因此,一个受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例如政府可以像使用自己的资源一样使用该企业的资源,即属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下的“公共机构”,无论该企业是否拥有政府职权,或为履行政府职能而行使政府职权。(68)美国在DS436案中的主张与在前述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分析报告中的基本立场一致,即以上诉机构在DS379案中的法律解释为由,将判断公共机构的法律标准由“履行政府职能和行使政府职权”替换为政府对国有企业“有意义的控制”。 面对专家组的裁决和美国的主张,上诉机构指出,“公共机构”的法律标准在DS379案中已经明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a)(1)条下的“公共机构”是指“拥有、行使或被赋予政府职权的实体”。判断一家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需要审查该企业的核心特征和职能,它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法律环境。因此,有多种不同的证据都能证明一家企业被赋予了政府职能。(69)例如,“有关一个实体事实上正在履行政府职能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该实体拥有并被赋予政府职权”;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对一个实体及其行为实施有意义的控制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该实体拥有政府职权或为履行政府职能而行使政府职权”。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贸易救济调查机关在决定一家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时,都必须考虑并评估与企业相关的所有特征,避免只考虑某一项特征而对其他相关特征不予考察。(70) 针对美国提出的受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即构成“公共机构”,不需要再考察该企业是否行使政府职权的主张,上诉机构明确指出,实体法律标准和证据标准之间的界限不能混淆。(71)上诉机构对于引起争议的“有意义的控制”的法律性质做出明确定位,即政府对企业实施“有意义的控制”并非判断该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的法律标准,而只是相关证据之一,同时,贸易救济调查机关应避免只关注某一项证据而忽略其他相关证据。至此,美国试图将判断公共机构的法律标准由“履行政府职能和行使政府职权”替换为“政府控制”的企图被上诉机构彻底否定。 具体到涉案的印度国有企业NMDC,初审专家组根据印度政府持有NMDC98%的股份、有权任命和批准董事会成员以及NMDC网站上关于其受印度政府行政控制的表述,认为美国调查机关将NMDC认定为公共机构符合WTO规则。对此,上诉机构指出了两点错误。第一,专家组将印度政府具有控制NMDC的能力当作判断NMDC是公共机构的决定性因素。(72)上诉机构认为,并非任何受政府控制的企业都是“公共机构”。(73)专家组引用的证据,包括印度政府的股权、任命董事的权力以及行政控制的表述,更恰当地说,仅构成“控制的形式标记”。这些证据与认定公共机构相关,但并不足以决定NMDC构成公共机构。尽管印度政府具有控制NMDC的能力,但专家组并未分析印度政府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行使了对NMDC及其行为的有意义的控制。(74)第二,专家组对印度提出的NMDC享有经营自主权的证据没有给予恰当的考虑。印度政府称,NMDC拥有日常经营的自由,印度政府的指令或政策没有影响NMDC的交易或定价决策。(75)上诉机构认为这些证据与分析印度政府对NMDC的控制程度和NMDC的独立自主程度是直接相关的,(76)不应被忽略。由于专家组和美国调查机关都仅关注印度政府对NMDC形式上的控制,没有全面考察所有相关证据,判断印度政府实际控制NMDC及其行为的程度,上诉机构推翻了初审专家组关于美国调查机关将NMDC认定为公共机构符合WTO规则的裁决。(77) 经过DS379案和DS436案的判决,上诉机构基本澄清了认定“公共机构”的法律标准和证据规则。简言之,要将一家国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贸易救济调查机关必须证明该企业拥有、行使或被赋予了政府职权。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对国有企业有意义的控制可以作为认定公共机构的证据,但并非决定性的法律标准。政府对一家国有企业控股以及任命董事会成员的权力仅构成“控制的形式标记”,并不足以将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调查机关必须调查政府实际行使控制权的情况和对企业的实际控制程度。调查机关在调查上述情况时要综合考察所有相关证据,不能忽视那些证明企业具有独立性、不受政府控制的证据。 三、对美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法律定性的评论 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分析报告可以代表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基本看法。分析报告结论认为:所有中国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都是“公共机构”;所有国资参股但需要执行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都可以被认定为“公共机构”;拥有很少或没有国有股份的企业也可能成为“公共机构”,只要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政府对该企业实施了“有意义的控制”。该结论十分偏颇,不仅不符合WTO上诉机构在DS379案和DS436案中的判决,其对中国国内法律和政策体系的描述也有许多谬误,反映了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偏见。 (一)美国商务部分析报告不符合上诉机构确立的个案全面分析原则 WTO上诉机构在DS379案和DS436案判决中均指出,对于一家国有企业,贸易救济调查机关必须综合考察所有相关证据,判断企业核心特征,才能决定该国有企业是否行使政府职权和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共机构。上诉机构的判决隐含了一个推论,即没有哪一类国有企业必然是公共机构,认定公共机构必须进行个案分析。美国商务部分析报告仅用38页篇幅,就将中国所有企业(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非国有企业)盖棺定论。其论据看似洋洋洒洒,但若遵循上诉机构个案分析的原则,具体到每家国有企业则难免挂一漏万,违反上诉机构要求在综合考察基础上具体分析的证据规则。 另外,上述机构在DS436案中特别指出,调查机关不得忽略与证明国有企业自主性和独立性有关的证据。然而,美国商务部分析报告仅狭隘地着眼于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无视中国国有企业的多样性和多年改革发展的成果。尽管国资委“管好资本”的职能定位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但不干预具体经营活动,使国有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在实践中已是事实。(78)《企业国有资产法》早已明确:“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的经营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79)对于证明中国国有企业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证据,美国商务部在分析报告中刻意忽略,没有按照上诉机构判决的要求,对所有相关证据做全面综合分析。分析报告的视角和论据是片面的,则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二)美国商务部对中国政府职能和职权理解错误 上诉机构在论述政府和“公共机构”的特征时谈到了政府职能和政府职权概念:“政府的本质特征是有权管理、控制或监督个人或约束其行为,并通过行使法定权力达此目的。……这部分来源于政府履行的职能,部分来源于政府为履行职能而拥有的权力。”(80)这说明,上诉机构是在政府区别于个人所拥有的强制权力这个意义上谈到政府职能和职权概念的,而并非空泛地谈与政府相关的所有特征。相比之下,美国商务部分析报告将中国的政府职能和职权定义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以《宪法》和《物权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等表述作为证据。这是对中国政府职能和职权的错误理解。 首先,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为包括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在内的所有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国政府有职责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同时也有职责鼓励和发展非国有经济。《宪法》、《物权法》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都有明确表述。美国商务部报告选择性地将中国政府职能定义为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失之偏颇。 其次,中国《宪法》序言中所谓“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不能等同于“政府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中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81)《宪法》序言已经对“国家”的概念做出了提示,即“国家”应当包括“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其概念范围远大于中国政府。而美国商务部分析报告以中国《宪法》和《物权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等表述作为证据,试图证明中国政府在中国法律框架下的职能和职权,这是错误理解了中国《宪法》的关键概念。(82) 最后,中国《宪法》和《物权法》中的上述表述是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宣示和共识,表示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用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所有人和事。上述表述不应被理解为规定作为公权力代表的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具体职能和权力。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解释《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条时明确指出:关于个人或实体行使政府职权的规定不包括国内法律对从事某种行为的宏观授权。(83)换言之,与判断“公共机构”行使政府职能和职权相关的法律所授予的必须是某项具体的政府权力,而不是政府对社会宏观管理的职权。中国《宪法》和《物权法》中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就是宏观性的宣示,并不涉及任何具体政府职权。尽管中国政府有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的职责,但这种政府职权并非上诉机构在解释“公共机构”含义时谈到的具有具体规范性质的政府职能和政府职权。 (三)中国国有企业执行产业政策无法证明国有企业是“公共机构” 美国商务部分析报告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是“公共机构”的主要论据就是国有企业需要执行中国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根据分析报告的逻辑,通过发布产业政策干预资源配置和企业决策,中国政府控制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并提供竞争优势,最终实现维护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政府职能。因此,发布并要求国有企业执行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意义的控制”的主要手段。 分析报告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分析似是而非。第一,产业政策是各国政府广泛使用的干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并非中国政府独有,也非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手段。对于产业政策,至今缺乏明确定义。但一般认为,产业政策是国家基于特定目的对以产业结构为中心的产业要素进行管理的规范体系,也是许多国家长期使用的经济管理手段。(84)各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可能使用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必要的干预和引导,这并不必然导致政府对某类企业的控制。美国也有产业政策。2012年2月,美国白宫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85)旨在提供一系列激励措施和政策环境,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但并不能因为该战略计划的实施,就认为美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受到美国政府控制。中国的产业政策与美国相比,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有一定歧视性,对特定产业采取特殊保护或扶持,但这与政府控制企业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中国的产业政策与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没有必然联系,也说不上是实现这个所谓中国政府职能的重要方式。美国商务部分析报告对中国政府职能和政府职权认定错误前文已述。即使分析报告对中国政府职能的认定没错,中国的产业政策与维护基本经济制度有交集,但也没有必然联系。中国政府颁布的产业政策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各行各业。当前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根本目的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86)有些产业政策与国有企业有关,更多情况下与国有企业无关。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都作为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主要方式,无异于说美国总统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主导地位一样荒谬。 第三,中国国有企业执行产业政策并不能说明国有企业是“公共机构”,履行政府职能并行使政府职权。中国政府颁布的产业政策不论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其适用范围都是国民经济中的所有主体。不仅国有企业需要执行,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都需要执行。(87)尽管产业政策反映政府意志,但执行产业政策不能说明一家企业履行政府职能。 (四)分析报告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部分控制方式仅构成“控制的形式标记” 美国在DS436案中为证明印度政府对NMDC实施“有意义的控制”,提出的证据包括印度政府在NMDC中持股比例达98%;政府有权任命董事会成员;以及NMDC网站上明示其受印度政府行政控制。在上诉机构看来,这些证据仅构成“控制的形式标记”,并不足以认定NMDC是公共机构;美国调查机关还应考察印度政府实际在多大程度上行使了控制权。 依据上诉机构提出的证据标准,美国商务部分析报告中证明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意义的控制”的部分证据也不过是“控制的形式标记”。首先,分析报告结论中将国有控股企业都认定为公共机构,这沿袭了美国商务部以国有股权作为单一要素判断公共机构的做法。单凭控股权不能证明国有企业是公共机构,这是上诉机构在DS379案和DS436案中反复重申的结论,而分析报告仍然明知故犯。其次,分析报告提出的部分其他控制方式也仅是“形式控制标记”。例如,分析报告将中国政府控制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任命作为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重要证据。但是,分析报告并未考察中国政府任命的高管在企业实际经营决策中是否保持独立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听命于中国政府的指示。(88)分析报告提到企业中的党组织是中国政府控制企业的手段。但除了援引《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原则性规定外,分析报告并未指出党组织在企业经营决策和人事任免中实际发挥了哪些作用。分析报告还提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认为该制度通过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利润以及政府向企业重新分配资本,以达到政府控制企业行为的目的。但这只是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运行方式的基本描述,至于该制度在实践中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分析报告并未进一步论证。 尽管如此,分析报告也提出了一些证据,即使以上诉机构确立的证据标准衡量,也可能证明中国国有企业是公共机构。例如,中国政府有时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如要求日照钢铁兼并亏损的山东钢铁,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另外,《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国资委监督、管理或批准中央企业的投资计划和投资决策,确保投资方向符合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些证据都反映了中国政府为达到特定政策目标,实际控制了国有企业的具体经营决策行为。在此情形下,中国政府不仅对国有企业及其行为实施了“有意义的控制”,受控制的国有企业也确实成为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 四、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创造平等竞争的商业环境,激发各类企业主体活力。国有企业可以与其他市场主体实现公平竞争,这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明确表达。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法律定性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国有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的偏见尚有存在土壤。尽管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国有企业认定为与政府性质类似的“公共机构”有不少谬误之处,但其分析的确抓住了中国国有企业一些改革不完善的问题。要彻底推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偏见、维护中国在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利益,有赖于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厘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及其配套文件(“1+N”改革方案)中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全面落地。 必须尽快完善国有企业分类,根据不同企业类型分别制定不同改革方案、形成不同的对外表述口径。公益类国有企业承担了保障民生、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责,具有类似政府的职能,可以考虑承认这类国有企业为“公共机构”。对于以竞争性业务为主的国有企业,应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外表述时也应据理力争,避免其他国家将这类企业不恰当地与中国政府等同,损害国家和企业的利益。而对于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应尽可能使其竞争性业务板块与特殊业务板块分离,根据企业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和对外表述口径。 与此同时,应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的行政色彩,强化其市场主体属性。国有企业在经营决策和人事任免方面与政府的紧密关联是美国商务部将其认定为“公共机构”的主要原因。目前国企改革中推进董事会建设、建立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选聘制度、强化管好资本而不干预企业具体经营活动等措施都是在向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淡化行政色彩的方向努力。只有将这些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平等的一员,才能有力回击外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提出的诘难。 注释: ①目前国内文献中关于国有企业法律性质的讨论多集中于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具体问题,如土地使用权出让、企业法人财产权、职工持股、兼并收购等法律问题;而与国有企业整体性质相关的学术讨论主要限于经济学领域,很少有从法律角度探讨国企定性问题的文章。 ②季晓南.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N].经济日报,2013-06-21(13). ③黄淑和.国有企业改革在深化[J].求是,2014(3):23. ④此处的国际经贸法律规则主要指国际贸易、投资等领域带有国际公法性质的规则,如WTO法和双边投资协定等。这些带有公法性质的国际规则下承担义务的主体主要是成员国政府。 ⑤梁勇,东艳.中国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J].国际经济评论,2014(4):54,57. ⑥刘锐.中国加入GPA的主要挑战及其应对策略[EB/OL].中国日报网[2015-05-23].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2013-10/29/content_17065439.htm. ⑦王毅.世纪谈判——在复关/入世谈判的日子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34-39. ⑧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for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of Coated Free Shee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t p.55,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SDOC"),C-570-907,Oct.17,2007. ⑨Issues and Decision Memorandum for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in the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of Certain Kitchen Appliance Shelving and Rack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Kitchen Shelving IDM"),at p.43,USDOC,C-570-942,July 20,2009. ⑩Kitchen Shelving IDM.at p.42. (11)Kitchen Shelving IDM.at p.43. (12)Kitchen Shelving IDM. (13)Kitchen Shelving IDM.at pp.43-44. (14)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u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DS379),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379_e.htm. (15)DS379,Summary of Key Findings. (16)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8.53. (17)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8.55. (18)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8.58. (19)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8.63. (20)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s.8.68-69. (21)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8.69. (22)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8.134. (23)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8.135. (24)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8.136. (25)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paras.8.138,8.143. (26)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284. (27)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288. (28)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290. (29)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297. (30)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309. (31)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310. (32)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317. (33)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318. (34)http://www.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meaningful. (35)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344. (36)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346. (37)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349. (38)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355. (39)"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tandard of Review and Impact of Trade Remedy Rulings",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03-824,at footnote 40 and p.24(explaining the standard of review under Article 11 of DSU,which applies to countervailing duty determinations). (40)"Section 129 Determination of the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of Circular Welded Carbon Quality Steel Pipe; Light-Walled Rectangular Pipe and Tube; Laminated Woven Sacks; and Off-the Road Tir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 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TO Appellate Body's Finding in WTO DS379"[Hereinafter "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Office of Policy,Import Administration,Department of Commerce,May 18,2012. (41)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5. (42)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6. (43)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6-7. (44)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8. (45)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9. (46)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10. (47)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14. (48)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14-17. (49)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17-20. (50)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20-21. (51)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24. (52)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24-26. (53)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26. (54)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26-27. (55)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27-28. (56)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28. (57)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29. (58)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30. (59)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30-31. (60)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31. (61)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32. (62)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33. (63)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33-34. (64)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at pp.35-36. (65)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33. (66)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P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35.原文为:"NMDC is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f the Ministry of Steel & Mines,Department of Steel Government of India." (67)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55. (68)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i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6. (69)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29. (70)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10. (71)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37. (72)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i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36. (73)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 (74)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43. (75)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40. (76)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44. (77)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47. (78)黄淑和:各级国资委不干预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EB/OL].新华网[2015-5-28]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2/19/c_118622457.htm. (79)《企业国有资产法》第16条。 (80)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AB,para.290. (8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5-06-01].http://www.npc.gov.cn/npc/xinwen/node_505.htm. (82)美国商务部分析报告对中国法律,尤其是中国《宪法》规定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美两国宪法体系和内容的区别。美国宪法基本结构是限权(力)和确权(利)。宪法正文七条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规定联邦和州政府的权力范围和两级政府的关系。因此,美国宪法除了通过“权利法案”和后续修正案确认公民权利以外,其正文的规范内容主要就是政府职能和政府职权。但相同的体系结构并不适用于中国宪法。上诉机构在DS379案中明确指出,哪些职能和权力属于政府职能和政府职权要依据各WTO成员国国内法判断。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国内法的判断和理解水平有待加强。 (83)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Facts,with commentaries,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United Nations(2001),at p.43.上诉机构在解释“公共机构”概念时特别参考了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第5条的内容。 (84)宋彪.论产业政策的法律效力与形式[EB/OL].中国经济法制网[2015-06-01].http://www.cnela.com/article/default.asp?id=314. (85)"A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d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February 2012,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iam_advancedmanufacturing_strategicplan_2012.pdf. (86)杨明.完善政策体系,护航产业结构调整升级[EB/OL].中国工业新闻网[2015-06-07].http://www.cinn.cn/wzgk/wy/270493.shtml. (87)以《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的通知》(国发[2011]47号)为例,其第三章“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任务”第六节的标题为“推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协调发展”。该节第一段要求:“在规模经济行业促进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扶持发展大批具有‘专精特新’特征的中小企业,加快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调发展、资源配置更富效率的产业组织结构。”此处的“大集团”和“中小企业”应理解为包括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并不特指国有企业。 (88)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India,WT/DS436/AB,para.4.45。上诉机构否认了印度提出的任命董事和高管人员只是印度政府控股权的衍生权利的主张。但是上诉机构强调,在考察政府任命高管人员的权力之外,还应当考察这些高管人员在经营决策中的独立性。标签:美国商务部论文; 国企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wto论文; 法律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有商业银行论文; 反补贴论文; 中国商务部论文; 证据规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