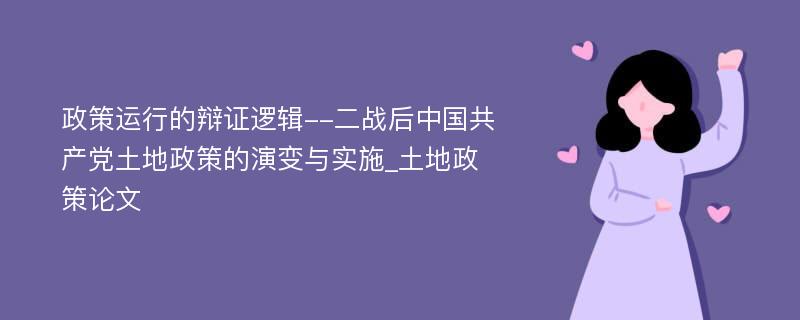
政策运作的辩证逻辑——战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与执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逻辑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政策论文,战后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放弃战时的减租减息政策,首先在解放区继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普遍而深入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时间长、范围广、强度大,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也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和调整。关于中国土地改革史的通论性著作,大都详细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对土改政策在各地的实际执行情况也多少有所涉及。①另有许多专题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相关问题,其中台湾学者陈永发和大陆学者杨奎松的论文颇具代表性。陈永发认为,土改期间发生的“左”倾过激行为并非领导者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的结果,而是毛泽东为“达到充分动员贫苦农民和大量汲取农村资源”而采取的一种“政治谋略”。②杨奎松与之相反,强调战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急剧转变和调整,除了受意识形态支配和国共关系影响外,主要都与中央对基层真实信息的掌握程度密切相关。③但就笔者所见,迄今还很少有学者从公共政策学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与执行进行了深入探讨。欲全面而真实地理解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事件,须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政策与政策指导下的土改实践区别开来,既要厘清其土地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更应关注这些政策在各地的实际运作情况,并对政策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延续与变迁
政策过程中既有稳定性的因素,又呈现出变迁性特征。为此,一些公共政策学者发展出一种“间断-平衡”理论,尝试从问题界定和议程设定的角度去解释政策延续与政策变迁之关系。④土地改革史研究者往往以政策性文件为标志,将土改运动分为不同的阶段,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土改的整体面貌和阶段性特征。但常为人所忽视的是,在政策演变和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前后阶段间往往呈现出相互交叠的面貌。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到以《五四指示》(即1946年5月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为标志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确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两个阶段之间又存在显著的延续性。一方面,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土地占有状况,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之间经历了一个以“清算”为中心的过渡期,从而使政策转变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相比,抗战中的减租减息政策无疑要温和得多。但从政策实施的后果来看,减租减息与税制改革共同作用,对乡村社会的土地占有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累进税制,土地和财富逐渐从富裕者向贫困者转移、分散,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在事实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均衡。弗里曼等人发现,冀中地区到1941年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社会平均化,36%和20%的雇工分别上升为贫农和中农,28%的贫农上升为中农,35%和8%的富农分别下降为中农和贫农,传统精英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一道逐步流失了。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静悄悄的革命”⑤。在被称为“封建堡垒”的陕西米脂杨家沟村,地主承担的赋税比例远远高于贫农和中农,他们把地租和其他收入统统拿出来也不够缴税,为了补亏只好卖地,从而导致了地权的平均化。⑥战时政策所引发的“静悄悄的革命”,事实上为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从抗战结束到《五四指示》下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继续推行减租减息,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清算”运动获取更多的土地,实现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毛泽东在1945年底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将减租和生产作为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要求冬春两季在整个解放区发动一次大规模减租运动。⑦不过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与抗战时期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一是与同时进行的清算斗争紧密相连,声势浩大;二是不再强调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迅速触及地主土地。⑧所谓“清算”(又称“反奸清算”)主要是处理抗战时期的各种遗留问题,但就其实际效果而言,清算也是以土地再分配为特征的“初步的土地斗争”,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的一种斗争方式”。⑨有学者指出,华北乡村的自耕农占据绝大多数,佃农只有三成左右,仅以减租减息的方式很难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斗争,而通过清算斗争则可以向自耕农分配物质利益,可以更有效地动员农民参加革命。⑩清算运动的具体情形,可以韩丁笔下的张庄为例略作说明。反奸清算的打击对象应该是抗战期间与敌伪合作的人,其中既有在村里拥有较多财富和地位的传统精英,也包括大量的贫苦农民。但在清算运动中,工作队干部引导群众认识到汉奸身份与地主富农身份之间的密切关联,在事实上将反奸运动转换为阶级斗争,从而使很大一部分传统精英受到了严厉打击。张庄所在的山西省潞城县,某分区约一半的地主、富农在反奸运动中受到了惩罚,许多人的财产被部分或全部没收,“旧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相当一部分物质基础被摧毁了”(11)。
在清算运动中,工作队以各种名目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例如,山西长治县在1945年底的反奸清算和“双减”运动中,土地变动率已达到13%,部分村庄已经“实际上达到了耕者有其田”(12)《五四指示》下发前夕,山东渤海区党委承认过去“在经济上消灭得很凶,均产思想严重”,“如减租减息弄不光,即算村负担,找负担还不光再找工滚利,于是经济消灭地主”。乐陵县某村经减租减息斗争,17户地主已经全部降为中农或贫农。南皮某村三个地主原有20顷地出租,经过多次减租,再找“工夫帐”、“出伕帐”,到土改前夕已削弱十之五六。当时许多地方已经意识到,减租减息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地主一斗即光”;“算帐无钱即折地准帐,如同分地”;“挖穷根如果成为行动的口号,一定是转移地权”。(13)
到中共中央下发《五四指示》之时,多数老区、半老区都已进行过大规模的减租减息和不同名目的清算运动,土地占有状况和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14)同样重要的是,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已将解放区的农民广泛动员起来,乡村民众的阶级意识开始形成,为此后土地改革的全面开展做好了铺垫。到1946年4月底,各个新解放地区发动起来投入斗争的群众,均达到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如苏皖区有200余万农民群众参加斗争,30多万农民收回了土地,全区仅有七分之一的村庄未发动。(15)清算运动与减租减息的开展,使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也彰显出前后政策之间的延续性。
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与执行的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会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而分别强调政策的“变”或“不变”。在某些情形下,土改领导者会强调前后阶段之间的延续性。抗战结束后的反奸清算与减租减息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针对汉奸而发,后者是在阶级话语框架下针对地主而发。但在高层领导者看来,发动群众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因此“反奸诉苦复仇清算运动不过是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的准备与过渡”,它“不仅不是用以代替或取消减租减息,相反的要经过反奸诉苦更好的来完成减租减息工作”。(16)政策发生变化后,前一阶段的做法不一定会被废止,而可能继续执行并被赋予新的含义,以利新政策、新目标的实现。在《五四指示》下发以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做法仍然得到鼓励,但更加强调利用这些手段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在给各地的指示中,中共中央一再提出,应该利用对租息、额外剥削、无偿劳役、转嫁负担、霸占吞蚀、人权侮辱等问题的清算,使地主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的名义下向农民手中转移。(17)
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又可能反其道而行之,突出政策变化的一面。1947年的一份文件阐述了这种做法的必要性:“运动一开始,我们就强调的提出耕者有其田与减租减息根本不同,前者是消灭封建,后者是削弱封建。同时我们也估计到,在四六年四月份咱们的运动中断了,所以我们确定了,必须来一个重新发动,来一个大规模的检查。假如我们不强调政策的根本不同,不重新大规模的发动,封建是不会彻底消灭的。”(18)突出前后政策的“不同”,有助于营造一种新的气象,借以对民众进行新的大规模动员。在领导者看来,群众运动必须经过“大发展”、“大斗争”之后才能转向“深入运动”的阶段,所以在政策发生变迁的初期阶段,突出政策之变动足以成为“大动”的契机。由此不难想象,对政策延续性的强调往往意味着土改实践中的温和倾向,相反,突出政策的变迁则可能导致运动的过激化。
表达与实践
美国学者黄宗智曾经指出,清代法律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存在“表达与实践”的背离。(19)从战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和执行过程来看,同样是如此。其中既有客观上的背离,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中的种种偏差,尤其是“左”的过激化倾向;也有主观上的背离,主要表现为党内指示与对外宣传的区分,以及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执行之偏差的利用。鉴于许多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对土改期间的过激化倾向作过深入探讨(20),此处不拟赘述,而着重考察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如何利用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
土地改革的主旨之一,是通过土地再分配来动员乡村民众,确立统治合法性,汲取人力物力资源。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又须借助种种策略使这一基本目标与当前的现实需要相一致,因此,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与国内政治局势有着密切关联。在抗战结束初期,共产党必须充分考虑自己在全国各地区、各阶层中的政治形象,不能轻易改变抗战时期帮助自己赢得政治优势的减租减息政策,公开恢复战前实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公开表达和宣传的土地政策,仍以减租减息作为主要目标,但在党内文件中已开始突破减租减息的基本框架。毛泽东在1945年11月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写道:“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21)允许减租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发生,显然是默许甚至鼓励对原有政策的偏离。
1946年初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也要求共产党在以联合政府形式求得“政治解决”之前,继续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五四指示》下发以后,党中央还专门指示,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暂时不要在报纸上宣传,“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22)。但是为了巩固根据地的民心和尽快实现新解放地区的农民动员,土地再分配又已被证明为最有效的武器。所以在党的各种指示中,总是一方面要求按照政策行事,一方面又强调不能打击农民的积极性。当中央政策仍然停留在减租减息阶段时,许多地方已开始自发地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财产,提前实施党在下一阶段将要进行的工作,这就不能简单地视为下层对上层、实践对政策的偏离,而应该意识到,这种偏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下层之间的共识。
有意味的是,基层干部和农民自发对政策的偏离行为,反而使党处于相机而动的有利处境,既可以依据原有政策对下级提出批评,使之成为教育和监控基层精英的理由;又可以将这些偏离解释为形势发生变化和群众呼声高涨的表征,藉此对政策作出调整。标志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调整的几个重要文本,都把农民群众对前一阶段政策的偏离作为政策转变的重要依据。《五四指示》开篇即描述了各地群众运动是如何突破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政策的,然后由此出发,指出过去的政策已不适应形势需要,并对那些严格执行政策的地方干部进行批评,进而正式提出“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23)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也以“农民要求”作为颁布《五四指示》的合法性依据。1947年底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就采用了这种说法:“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24)
政策执行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权变性,即为了适应新情况或意外特例而对政策予以变通执行,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25)在土改运动中,政策的制定要赋予群众运动以合法性,故须全面、合理,让各方满意;政策的执行却要以实际效用(尤其是乡村民众动员的程度)为基本衡量标准,故无须严格遵循政策规定。建国初期的一份土改思想汇报,生动地描述了基层干部在执行政策时的权变性:
我们(指知识分子)时常喜欢讲原则讲法律条文,例如要占有多少土地才算地主的问题,我们总觉得应该定一个原则或标准。老干部同志们总说:“我们灵活运用吧。”我们喜欢提出许多假想的情况来分析,他们总说:“等遇到具体问题发生再说吧。”起初我们不很了解,认为他们头脑不够深刻,缺乏分析力。但是后来从经验中慢慢领会了。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总是很复杂的,任何先定的原则总不能够不多不少地恰好应用。只有掌握着大原则,其他问题必须就个别情形加以解决。(26)
政策执行中的权变性、灵活性之所以必要,除了政策制定者的策略考虑之外,还取决于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受战时交通通讯条件所限,中央政策传达到各地基层乡村需要较长的时间,从而可能出现政策滞后的现象。在内战爆发前夕制定的《五四指示》,传到山西潞城县时已到了内战的高潮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威胁迫在眉睫,县委提出了较《五四指示》更为激烈的土改标准,即所谓“三透、四有、五不留”(揭发透、斗争透、翻身透,无地少地的农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地种、有房住,不留一个贫农、不留一个落后分子、不留一个问题、不留一点封建思想、不留一个地主)。(27)正因如此,各级领导机构往往既强调政策的原则性,又提醒在执行政策时“对于一切事物,均须作具体的分析”(28)。如论者所说,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自己在预见和决定基层问题上的局限性,因而鼓励在政策运用中的“灵活性”,只要能有效地实现目标即可。(29)
其二,各阶层都会对政策作出自己的判断、预期和相应的行为选择,使政策执行面临更多的变数。太行区党委就曾从这一角度对《五四指示》提出了质疑。该指示既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原则,又考虑到了缩小打击面以分化敌人的策略问题,按说是一个考虑比较周详全面的政策条文。但在实践中却因地主和农民的不同预期而发生了变异,农民看到党的政策较为谨慎而不敢放手去斗争地主,相反地主却“预期会有一个拉的阶段到来,也打量农民不敢把他怎样”(30)。从而,政策的周密反成了政策执行的障碍。在此情况下,只有依靠政策执行者的灵活运用,才能在实践中弥补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行为选择对政策实施带来的阻力。
温和与激进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及其执行中的温和与激进,是土改史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通常认为,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框架下作出的让步,没有触及土地所有权问题,呈现出显著的温和特征。1946年的《五四指示》主张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帮助无地少地的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但前提是不侵犯中农,不变动富农土地,并适当照顾中小地主,仍然比较温和。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渐趋激进,1947年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没有具体规定农村阶级划分标准的情况下,大力推动没收并平分土地,致使绝大多数地区发生了斗争范围过大、程度过重、方式过激的“左”倾偏差。进入194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又出面全力反“左”,调整纠偏,使混乱局面得到控制。(31)笔者想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政策过程中温和与激进的辩证关系。
《五四指示》在党内下发以后,各级领导机构在解释政策时大多强调它从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到解决土地所有权、从削弱封建剥削到消灭封建剥削的转折性意义。(32)但后来的党史研究者多认为它对中小地主、旧式富农、开明士绅等照顾太多,不利于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具有不彻底性。(33)韩丁认为,《五四指示》与当时共产党所有政策的“防御目的”一致,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土地制度变革文件。(34)弗里曼等人则指出,该指示反映了共产党既拉拢穷人中最穷的人,又不疏远绝大多数自耕农的意图。(35)不过应该注意到,《五四指示》的温和特性是相对于次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而言的。与前一阶段相比,《五四指示》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从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从渐进主义向激进主义转变的开端,因为它明确触及土地所有权问题,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基本方针。事实上正是在这份文件颁布之后,各解放区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各种方式去剥夺地主土地,成为“我国土改史上夺取地主阶级土地的方式最为灵活多样的一个阶段”(36)。
《土地法大纲》是在国共全面内战的背景下制定和执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激进特征。与《五四指示》和建国后的《中国土地改革法》相比,1947年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呈现出显著的激进特征:主张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浮财而不只是其多余部分;明确将富农作为打击对象;取消了对中农、军工烈属的照顾政策;以“按人口统一平均分配”作为土地分配的基本原则;规定了贫农团在土改中的领导地位。(37)在政策执行中,紧张的战争局势会同时产生两方面的作用:农民可能因为恐惧而退回分到手的土地财物,或者悄悄向地主交纳地租;干部和积极分子也可能出于忧虑而再次发动对地主、富农的进攻。黄宗智认为,土改运动的过激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国共双方的军事争夺,当村庄位于两党激烈战斗甚至反复争夺的区域时,村庄内部的极端行动在战局的压力下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38)当国民党军队推进到离张庄仅有一百多里远的晋城时,张庄的村干部和贫农积极分子将所有被斗户尚存的成员再度拉上群众大会,“由于敌军日益逼近,反革命威胁与日俱增,运动开展后人们的情绪更加激烈,而且更多地使用了暴力”(39)。天镇县曾有地主组织“还乡团”杀害干部,县委由此产生“非杀他百分之八十不能开展工作”的极端思想,一月之内杀死70多人,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和还乡团成员也往往不加审讯即被处死。(40)《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很快出现“平分土地”运动的高潮,并普遍发生追挖底财、浮财的斗争,扩大打击面、斗争过火的现象非常严重,迫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土地政策进行调整,从激进重新走向温和。
建国后新区土改的基本依据,是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41)。此时土地改革的背景已和内战时期大不相同,政策取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在对《土地改革法》与《土地法大纲》进行细致比较后,归纳出《土地改革法》的十项要点:强调在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满足雇贫农要求,后者服从前者;保留富农经济;保留小土地出租者出租土地;不动地主浮财;保护工商业;保护中农;大城市近郊不适用土地法;强调划阶级订成份;旧法规定“镇压地主破坏土改”,新法“禁止在土改当中的若干人破坏生产行动”;新法强调看条件,防止政策上的混乱。(42)美国学者许慧文指出,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充满了试验性和错误,而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可以更加安全、自信和坚定地执行其农村政策。(43)比较之下不难发现,由于内战状态已经结束,共产党已从局部执政党变成全国执政党,建国后新区土地改革的总体性格变得更加温和、稳健。内战期间共产党对乡村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征粮、征兵、支前)的庞大需求,势必更多地剥夺地主、富农乃至中农利益;建国后党和国家则更倾向于从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对富裕阶层采用较温和的政策。如1950年编印的一本土改教材所说:“蒋介石反动政权已被打垮了,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了,摆在咱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进行经济建设,不动富农就使中农情绪更加稳定,积极生产,土改中也可避免侵犯中农,富农也会积极生产,有利于国家由战争转到和平建设,克服当前财政经济困难。”(44)
政策的温和抑或激进,也可能是政策制定者为实现特定目标所作的主动选择。陈永发指出,在群众运动的不同阶段,党的政策会呈现出不同的倾向:运动初期需要广泛动员贫苦农民,法令不可多所限制,甚至要设法扩大贫苦农民的活动空间,在作风上要大刀阔斧,甚至不惜纵容暴力,此即“放手发动群众”;而在群众发动起来、出现各种偏差之后,又须不失时机地进入巩固阶段,对群众的过激做法加以限制。(45)
1945年9月,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对群众运动中的“左”倾偏向作了深刻分析:
群众从重重压迫阻挠下一旦翻身,“左”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些“左”的行动是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操纵的行动,是无害而有利的。所以,判断“左”与右,应以土地政策基本目的为标准。首先要发动群众起来,这应是坚决的;依靠广大群众,树立群众优势,这应是基本的。对于地主,不能和平的团结,必须是有斗争有团结,而且是先斗争后团结,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斗争后当然要团结,但过早的强调团结为主,则群众就起不来,便会陷于根本失败。(46)
这段话,生动地道出了政策过程中温和与激进的辩证法。温和意味着团结、秩序、建设,激进意味着斗争、活力、破坏,所有这些都是党在领导乡村社会变革时必不可少的。不破不立,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才能激发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但破是为了立,只有适时地从激进转向温和、从斗争转向团结,才能将群众被激发起来的热情控制在党所期待的范围之内。斗争至上或者稳定至上都是片面的看法,重要的是认清形势,看准时机,该“左”则“左”,该右则右。在温和与激进之间适时而如意地转换,正是以群众运动实施民众动员和乡村治理之所必需。
上级与下级
在西方政策学者构建的政策执行理论模型中,政策执行者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性、同质性的主体。例如,史密斯将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视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四个基本要素,麦克拉夫林认为政策执行过程本质上是政治执行者与受影响者之间相互调适的互动过程,巴达奇强调政策执行人员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博弈过程,都没有把政策执行群体内部的纵向和横向关系作为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建构的综合模型提到了“执行机构间与机构内部的层级整合”,也只是将其列为“政府本身的规制能力”之一,并未给予充分强调。(47)但从战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政策执行者并非同质的整体,而是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层级,他们在政策过程中的立场和行为并不完全一致。
在现代科层制结构中,上下级关系的常态是命令与服从,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政党来说,情形更是如此。1947年前后土地改革的过激化偏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命令-服从”关系的结果。正如日本学者田中恭子所说,农民虽有均分土地的要求,但是提出均分政策的毕竟不是农民而是中共上层。(48)在历次群众运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高层领袖逐渐形成了一种宁“左”勿右的政策取向。毛泽东很早就提出:“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9)相应地,各级党组织和基层干部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取向,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如论者所说,在斗争“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右倾主义分子”方面表现积极,决不会受到惩罚,相反,缺乏这种积极性则会影响自己的前程。(50)在此氛围中,土改执行者们常常出于政治前途考虑而表现出过激的言行。在冀南地区的土改中,“左比右好”、“左了立场稳”成为干部党员的普遍意识,产生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眼硬心狠看得惯”、“敢打敢斗是英雄”等过激口号。(51)冀南一地委许多党员积极分子“为了表示立场就很(狠)整地富,大的地富没东西了,就过分整小的或下降户”(52)。张桥村的干部“为了获得个斗争彻底名誉”,而在复查中提出“不拔锅,不揭席,不算彻底”的口号。(53)为了取得更大的“成绩”,区村干部乃至县委干部都可能纵容或鼓励农民的过激行为,甚至强迫农民参加斗争。有的村庄因为土改复查时“搞得户数太少”、“没打死人”而受到分区委批评。(54)有的分区干部说“××庄100户杀了20户,多么彻底啊!”鼓励其他村庄仿效。(55)从基层土改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土改期间过激行为的普遍发生,既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脱离实际的结果,也与地方组织和基层干部在执行政策时对上级的主动迎合密不可分。
但除了命令与服从,上下级之间同样存在批评与抵制、推诿与抗拒的关系。韩丁曾详细描述了来自基层的工作队干部与潞城县委关于政策及其实践的不同观点,这对我们颇有启发意义。据他描述,工作队在复查整党期间的一些过激做法,实际上主要来自县委对基层党员成份不纯的严重估计和对工作队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但是在几个月后纠正“偏向”时,县委又对这些做法提出了严厉指责。过激化的错误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县委王书记说:“县和专署的领导人应当负责。但是,基层干部也应作自我批评。县里领导人的估计还不是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情况作出的吗?基层干部不是有时随便解释政策吗?他们往往抓住符合自己偏见的个别部分,而忽视了全局,难道不是这样吗?‘依靠贫农’是我们土改政策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内容,然而农村干部们却过分强调了依靠贫农这一点。”但基层干部们不能接受这种指责,因为那些口号毕竟不是他们提出来的,并与县委陈书记发生了直接冲突,使会议陷入僵局。最后县委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上面的干部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才换来了基层干部们对自身责任的反省。(56)
战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在温和与激进之间经历了多次变动,每次变动都可能引发上级与下级在原有政策的得失评价、过去偏差的责任认定方面展开一番较量。上级的逻辑往往是,自己的形势估计和政策制定都是以下级提供的信息为依据的,因此下级应该为政策不当承担责任;下级的逻辑则正好相反,自己是在上级政策的指引下行事的,责任当然应该由上级来负。《五四指示》下发后,许多领导机构对严格局限于减租减息的做法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当时曾强调了一九四二年的土地政策与中央屡次指示,而没有看到新的情况下这些政策与指示已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认为没出什么问题,觉得自满。”(57)“(基层干部)没有考虑到政策是否符合群众的要求……主要是搬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的减租政策,然而,实际上是泼冷水,上级泼一盆,到下边变成一桶一缸。”(58)这样的指责显然过于苛刻,制定政策本是中央的任务,各地党组织和基层干部只应负责贯彻和执行,现在却要他们对中央政策是否符合形势需要和群众要求做出判断,并为政策脱离实际的偏差承担责任。从中可以看到政策执行中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复杂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执行逐渐成为西方公共政策学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关于政策执行的不同理论模型。所谓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59)政策执行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蕴含着一个未明言的预设,即政策观念(文本)与政策执行(运作)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既有耦合又有背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牵制的持续互动关系。
本文从公共政策学视角出发,考察了战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与执行情况,并对其中展现出的政策运作逻辑作了初步探讨。政策演变的前后阶段往往呈现出相互交叠的特征,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形和需要而分别强调前后政策之间的“变”与“不变”,这是延续与变迁的辩证逻辑。政策执行可能偏离政策规定、产生种种偏差,政策目标与政策宣传可能背道而驰,政策制定者也可能有意利用政策执行之偏差、将其作为政策调整的契机,这是表达与实践的辩证逻辑。温和意味着团结和秩序,激进意味着斗争和活力,政策的温和抑或激进既与政策制定和执行时的客观形势密切相关,也可能是政策制定者为实现特定目标所做的主观选择,这是温和与激进的辩证逻辑。政策执行者并非同质性的整体,上下级之间在政策演变和政策执行中不断互动,其间既有命令与服从,也有批评与抵制、推诿与抗拒,这是上级与下级的辩证逻辑。由此出发,本文或许可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境中,为政策执行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案例。
注释:
①其中较有代表性者如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永泉等《中国土地改革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等。
②(45)陈永发:《内战、毛泽东和土地革命———错误判断还是政治谋略?》,(台北)《大陆杂志》第92卷第1~3期,1996年。
③(31)杨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中央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京都)《东方学报》2007年第81期。
④[美]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5~149页。
⑤[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页。
⑥[美]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载冯崇义等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⑦(21)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68、1068页。
⑧⑨(15)(36)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311、307、313、323页。
⑩(48)[日]马场毅:《田中恭子著〈土地与权力———中国的农村革命〉》,载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中国21(19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27)(34)(39)[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228、227、233~234页。
(12)(18)《长治县土地改革运动总结》(1947年4月),载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办公室编《太行土地改革资料》第三分册,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90-1-36-1。
(13)《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年6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26-01-0240-001。
(14)(23)《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页。
(16)中国共产党华东中央局:《关于目前群众工作的指示》(1946年4月8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六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17)《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194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情报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5月19日),载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3页。
(19)参见[美]黄宗智《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0)例如罗平汉《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及其纠正》,《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张永泉《对1947年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原因新探》,《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9期;牛崇辉《略论晋绥土改运动中的“左”的偏向》,《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2)《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05/13),载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24)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46页。
(25)张国庆主编:《公共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26)陈体强:《从土改中学马列主义》,载皖北文教社编印《土改与思想改造》,1950年版,第20页。
(28)《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具体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及中央局指示的决定》(1946年7月28日),载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29)(43)Vivienne 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5,p.9.
(30)《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总结》(1947年6月25日),载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
(32)(57)例如《中共晋察冀六地委关于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的结论》(1946年7月21日),载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4页。
(33)参见管春林、温瑞茂《如何认识〈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杜敬《关于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高青山等《“五四指示”和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党史研究》1982年第5期。
(35)(50)[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49页。
(37)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5~88页。
(38)[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5期。
(40)《对天镇县执行政策的材料》(1948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520-1-349-1。
(41)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3页。
(42)《1950年9月12日向明同志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转引自《关于山东完成与结束土地改革工作的检查》(1954年8月7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A001-01-0158-026。
(44)西北局宣传部编:《土地改革地区农村政治教材》,新华书店西北总店1950年版,第28~29页。
(46)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1945年9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五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8~379页。
(47)(59)参见张金马主编《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394、383页。
(4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7页。
(51)《冀南区土改总结(草案)》(1949年7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25-1-144-9。
(52)冀南一地委:《十二月份向区党委的工作报告》(1948年12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28-1-8-8。
(53)《桓台县索镇区张桥村土改材料》(1949年6月27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26-01-0269-001。
(54)长沙区工作团:《长沙区各村土改复查情况的调查》(1949/10/19),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24-01-0145-012。
(55)五莲县委:《辛玮等对五莲县两月来复查运动的总结发言记录》(1947/08/31),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24-01-0121-003。
(56)[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41、42、55、56各节。
(58)《刘杰同志关于察哈尔省土地改革的汇报》(1947/01),载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