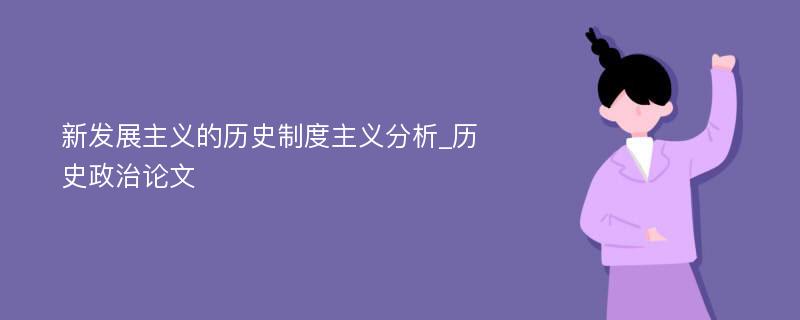
新发展主义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新发展论文,制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主义曾是主宰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范式,其基本命题是发展带来民主。但是,发展不但没能带来民主,反而导致“政治衰败”,发展主义因此式微。第三波民主化为发展主义注入活力,“新发展主义”应运而生。在知识脉络上,如果说李普塞特提出了发展带来民主的发展主义的经典命题,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则把发展主义研究范式化,那么,在民主化的“第三波”后,李普塞特重整旗鼓,其修正了的发展主义再放光芒。在“第三波”的鼓励下,曾经给发展主义致命一击的亨廷顿似乎也改变了立场,其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的著名论题也带有浓厚的发展主义气息。而将新发展主义研究更加复杂化的则是政治学的一批后起之秀,其代表就是D.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E.H.斯蒂芬斯(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J.D.斯蒂芬斯(John D.Stephens)。这些看起来彼此独立的人物及其著作,其实有着内在的方法论和知识体系上的关联。关于新发展主义的知识脉络,本人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发展主义》中有系统的评介①,因而本文不再涉及新发展主义本身的内容,而是旨在评估其解释力、适用性及其问题。我认为,新发展主义的新制度主义要素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同时,其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又限制了其适用性和解释力。
一、新发展主义的“政治性”变量
新发展主义对经典发展主义的突破所吸取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制度主义。众所周知,经典制度主义(法制传统)主宰政治学为时已久,对于制度、法制、结构的强调是政治学一个渊源深远的面向,后经理性选择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冲击,经典制度主义一度衰微;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马奇和奥尔森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恢复了对结构、制度的关注,将政治学的传统途径复兴,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者以及“回归国家学派”,更是明确地“将国家带回来”(bring states back in)。当然,新制度主义对旧制度主义进行了改造,比如加入了观念因素、在历史的维度中考查制度和行为的关联、制度分层等等。
新发展主义既然是比较政治学中的新兴事物,它的理论资源就必定集成了许多其他范式的成分,在我们看来,最多的借鉴来自历史制度主义。新发展主义不同于经典发展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政治性与历史性。
新发展主义“把政治因素带回来”(bring politics back in),这同经典发展主义的“经济发展—民主”的简单“乐观方程式”迥然不同。经典制度主义注重制度因素、政治因素、结构因素。新发展主义吸取了这一资源,在论述经济发展(或说现代化)与政治民主的关联时,不再像奥唐奈尔批评李普塞特那样,仅用一个简单的“乐观方程式”一笔带过,而是在二者之间加入了诸多中介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李普塞特1993年的《民主的社会前提(修正版)》和1959年的《民主的一些社会前提》来观察他的变化。
在1959年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李普塞特花大量笔墨探讨了经济发展(以及细化的诸多指标)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虽然在文章的末尾他也讨论了“政府的形式与民主”这一板块的内容,并得出两党制比多党制、联邦制比单一制、区域代表制比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民主这样的结论,但李普塞特明确表示:“虽然关于政府体制的变量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远远不如社会结构因素那么重要……我并不认为这些政治结构的因素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如果基本的社会条件是有利于民主的,就像我们在瑞典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多党制、比例代表制和单一制这样(不利于民主)的政治体系,也并没有严重削弱民主。”②可见,50年代末,作为经典发展主义代表的李普塞特,对于社会因素必然累积带来民主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而政治的变量则被远远置于社会因素之后。
而在1993年的修订版本中,李普塞特增加了大量关于政治方面的变量。在讨论哪些因素有利于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时,李普塞特专门列了“制度化”一节,认为新兴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必须被制度化、巩固和合法化。他认为,一国的政府合法性、政府形式(总统制或议会制)、选举形式(地区代表或比例代表制)、市民社会程度、政党支持度,都会深深影响民主的巩固和存续。他开始意识到,仅仅通过受教育程度、人均GDP等社会因素的观察,是无法直接推出民主是否会在一国生根发芽的,必须加入其他重要的变量,而政治因素是无法忽略的。
50年前的李普塞特对于政治系统的关注仅仅可以用“有效性”(effectiveness)一笔带过;而50年后,政治因素涵盖了政治系统的方方面面,包括政体、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法治、宗教、市民社会等等。政治因素不再仅仅作为一个附属变量。
二、新发展主义的“历史性”变量
新发展主义的另一个突破之处,就是对历史的重视。这同经典发展主义静态的、万能的“结构—功能范式”迥然不同。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性特征。
第一,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和行为之间的考量是在历史的框架中进行的。历史制度主义的代表保罗·皮尔森指出:“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它们认为政治发展必须被理解为一种随时间而展开的进程。”③另一位代表人物斯考切波也认为:“相对于理想选择制度主义而言,历史制度主义者们更愿意随着时间展开去追踪事件发生的顺序,用来阐明先出现的事情是如何改变随后出现的事情。”④这包含两个含义:(1)需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复杂历史过程的因果关系;(2)注意事情的先后出场次序。因此,“同样的原因不一定会导致同样的结果”⑤。
第二,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历史进程的偶然性。正如伊格玛特所表明的,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历史的无规则性而不是规则性。因此,历史制度主义不寻求建立一种普遍化的模式,而只能去找出并建立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因果逻辑和相应的理论模式。⑥
第三,历史制度主义注意考察“世界时间”,将世界时间与全球背景结合,在世界历史的纵坐标中观察全球历史事件。斯考切波认为摩尔的不足就是在分析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时缺乏国际和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念。
了解了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历史性”,反观我们所讨论的新发展主义的一系列特征,会发现二者是契合的。新发展主义除了前文所介绍的“将政治因素带回来”以外,另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具有“历史性”。
新发展主义的代表作《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在方法论部分就提出了两种已有的研究路径:跨国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研究。作者明确采纳了后一种研究方法,介绍了比较历史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通过历史的次序和考察打开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关联的“黑匣子”。“在研究三对权力关系时,我们坚持用历史的、次序的方法。先前的国家结构和制度形式会形塑之后的政治发展;最初的阶级组织以及相关的阶级利益结构会对后来基于阶级的集体行动造成影响。重大事件——例如镇压、成功的军事政变或内战——将从长远意义上塑造对于机遇和威胁的认知。另外,很多政治形式的制度化是需要时间的,通常要几代人的时间。最后,次序是很重要的。国家建构、阶级形成、工业化的不同次序、民主动议的首次提出、还有世界历史发展,都赋予不同国家以不同的情境。”⑦可以说,新发展主义的这些发现又验证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
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在作者的解释框架里,(1)民主是一种权利,它是否成功要看很多复杂因素,要看从属阶级的情况、阶级联盟的机会、支配阶级对民主的反应、国家的作用以及跨国力量的干涉;(2)民主是否能够巩固、制度化,与发展效应关联不大,却与阶级力量平衡、是否将民主放在政治议程中关联紧密;(3)民主的启动需要复杂的阶级妥协。考虑到现实中阶级力量的分化和差异,民主其实是一种脆弱的现象。
作者通过考察欧洲、拉丁美洲、中美洲的不同情况,分别考察了每个国家、地区内部的阶级关系、阶级联盟、民主出现的机会、国家—社会关系、国际情势,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大地主阶级是最大的反民主力量。如果在经济上由他们掌控或影响国家,那么国家在这一历史阶段将排斥民主权利的扩张。
第二,资产阶级与民主的关系不是正相关的。“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相左,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是民主的主要代理人。我们只能说资产阶级与民主的关系因时因地而异,主要取决于当时向他们开放的利益结盟选项,还有过去的意识形态遗产。”⑧例如,德国、瑞典、丹麦的资产阶级支持早期的自由改革,但当工人阶级的诉求带到议会,成为他们的潜在危险时,他们就会反对议会政治。在拉丁美洲,资产阶级总是倾向于终止议会政治,支持军事手段结束公民自由权,尽管他们这样做的代价是,随后的军事独裁通常剥削他们进入国家政治层面的通道。
第三,工人阶级是民主的最大推动力量。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其实这是误解,这个命题只反映了部分国家的部分历史。事实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民主,相反,民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的产物。资本主义的主产品是资产阶级,他们并不促进民主;副产品工人阶级却与民主息息相关。工人阶级自组织力量的强大,才给民主创造了机会。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看法,认为民主化、尤其是大众民主的真正到来是19世纪中叶以后工人运动的产物,其中马克思主义功不可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即民主有社会主义属性。⑨
第四,中产阶级的作用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与他们与国内支配阶级的关系有关,当国内支配阶级与国家紧密结合,这个利益同盟就会主导城市、农村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态度是模糊的,这与他们在国家阶级的梯队中的位置有关。在拉丁美洲,中产阶级对民主的姿态严重受制于他们与上层阶级的同盟关系。如果他们无法与上层阶级联盟,而此时工人阶级力量强大,工人运动又轰轰烈烈,他们就会转向民主。
第五,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民主之间呈正相关,这与多元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如出一辙。但是必须注意,作者认为理解市民社会的作用需要落脚到它对阶级关系的作用上来,看它与民主的关系。
第六,国家与民主的关联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可能会是民主的反动力量。在拉美,国家成为反民主的一个巨大力量,支配阶级通过军队绑架了国家,使从属阶级被踢出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大地主阶级的对抗者,从而对民主有益,而且,民主议题应当出现在国家统一完成之后。
第七,国际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民主出现的契机。
通过以上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的方法论带有历史制度主义的典型特点。比如,对各个地区的研究,考察这些地区或国家的历史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考察不同阶级、国家—社会关系、国际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得出的结论有很多带有不确定性,因为这些因素与民主的关系是“因时因地”的,这与历史制度主义讲究“历史无规则性”是一致的;而全球背景下的考察也与历史制度主义者的“世界时间”概念吻合。
另外,李普塞特1993年的文章也反复强调,导致民主出现或巩固的因果链条是非常复杂的。“具体的结果依赖于特定的情境。这些情境包括:初始的选举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是否与该国的族群分化相适应?该国的经济状况如何?当然还要看主要政治行动者的能力和策略。很显然,我们不能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一切。”⑩
李普塞特在这一点上突破了自己50年前的研究局限。当时,他的“经济发展—民主”乐观方程式曾经影响过几代人,包括其后将发展主义推向巅峰的“结构功能主义”。作为60年代西方比较政治学领军人物的阿尔蒙德,其完美的逻辑模型和解释框架曾支配着比较政治学界,这种静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化范式完全比照西方的政治经验,以抽象的政治术语试图将世界各地的政治现象整合进一个“普适”的模型,这一点最终被其继承者摒弃。
三、新发展主义的问题:依旧西方中心主义?
鉴于发展主义是西方比较政治学如此重要的一种范式,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其中,索姆吉(A.H.Somjee)的《发展的理论:批评与考察》是比较全面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今发展学研究存在的两个大问题之一是西方中心取向。(11)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
西方中心主义是发展主义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籍政治学家奥唐奈的作品《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就曾作为对经典发展主义的强烈批判,反思了工业化—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政治维度和社会经济维度之间的诸关系是一种具有时限性的相互影响,并且只有纵向视角才可以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摒弃那种静态、横向的研究方法,转而对当代南美各政治体制的某些基本特征提供一种起源性的解释。”(12)奥唐奈通过“官僚威权主义”这一概念,否定了经济发展—民主的必然联系,进而认为,南美较高和较低程度的现代化与非民主政治体制相联系,而政治民主只出现在中等程度的现代化中,高度现代化则与官僚威权主义紧密联系。
经典发展主义虽经如此批判,却逐渐复苏。虽然作为其继承的新发展主义已经在方法论和研究对象上淡化了西方中心的痕迹,比如有意选取非西方个案,关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摒弃现代化理论的简单二元划分。但是,新发展主义仍然难逃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首先,新发展主义对于政党的认知完全是西方式的。新发展主义针对经典发展主义,将“阶级”纳入了思考框架,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这使经典发展主义幼稚而乐观的论断加入了左翼思想家的观点,变得丰满了许多。然而,受结构—功能范式的深刻影响,新发展主义在论述与“阶级”紧密相关的“政党”作用时,仍然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对政党功能的介绍也多围绕着其“利益表达”的功能。
比如,在李普塞特1993年的修正版代表作中,对政党的定位是这样的:“政党必须被视为国家和公民之间一个重要的协调中介机制。”(13)再如,《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在全书分析中很少提到政党,但在行文最后补充了对于政党的思考。全书的逻辑框架是围绕着阶级关系展开的,显然,作者将政党作为各阶级利益代言的工具。(14)
政党的功能真的只是“利益表达”吗?在萨托利关于政党制度的经典之作《政党与政党制度》中,他将政党的功能列为三项:(1)表达;(2)引导;(3)沟通。萨托利专门指出,意见表达功能是政党多元主义(即政党属于一个政党体系)的特征。这个功能是三种类型中包含范围(适用范围)最小的。可见,意见表达功能只是政党功能非常小的一部分,它是有条件的,即政党多元背景。而“政党多元,在多元主义世界观不曾浸润的地区,运作不良或不能长久,也是极为明显并少有例外的”(15)。可见,新发展主义中关于政党的描述,片面地以西方政治实践为模板。其实,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党的含义绝不仅仅是“表达利益、沟通国家与社会”那么简单,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深远而广泛的。西方的政党大多是议会政党,以表达利益、夺取席位为己任,而后发国家的政党却可能身兼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数个角色,并且处在艰难的转型中。(16)
其次,新发展主义对于“国家”的作用估计不足。新发展主义大多秉持了国家—市民社会二元法,并将社会放在了更显著的位置。尽管《资本主义与民主》考虑了国家的作用,却仍然是透过国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来评判国家,并未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在李普塞特等人的文章中,国家更是一个不被提及的话题。李普塞特1993年的文章仍然大力提倡市民社会的重要价值,对于国家层面,也只是谈了政治体制和选举体制。而我们认为,在许多转型国家转型成功或失败的问题上,“国家的角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及其变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状况,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国家成功的关键。
最后,新发展主义只谈“什么有利于民主”,却很少意识到,“什么不利于民主。”新发展主义与经典发展主义一样,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条件有利于民主的产生、转型与巩固?”这样的问题,解答的思路必是参照成功经验,以西方为模板,从“西方工业化国家有什么要素”这个思路入手,推广到非西方世界。问题是,如果换一个思路,从“非西方国家没有什么”这个思路开始的话,很多结论就大相径庭了。
西方工业化国家有什么?答案是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以识字率、交通、人均GDP等指标来界定),发达的市民社会,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利益表达工具的政党,选举制度,等等。新发展主义者仍然以这些指标作为非西方世界演进的标杆。
非西方国家没有什么?或者说,有哪些因素是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先天不足的障碍”?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国家大多是在解决了国家统一、民族认同这些起码的问题之后,才“遭遇”民主问题的。而非西方国家由于革命的历史和长期的贫穷、战乱,积累了根深蒂固的种族冲突、贫富差距、利益结构二元化鸿沟。这些先天不利条件很少在新发展主义的视野里出现。
李普塞特在1993的作品中,对分歧与冲突持肯定态度,认为这些是稳定的政党支持的根源。他特别指出印度的例子,认为历史上印度的种姓制、语言和宗教团体对于民主的制度化是有功的,因为它制造了“强烈的政党忠诚度”。有趣的是,萨托利却认为,我们不能将阶级社会、印度的种姓制度、非洲的分散部落体系都称之为“多元”,这些与西方的多元主义是有本质差异的。多元主义的本质精神既不是共识,也不是冲突,而是异议,或者赞许异议。要区分两种层面的共识或冲突:(1)共同体层次与政府层次(政策层次);或者(2)基本事项层次与议题事项层次。区分了这两个层次,我们可以推论,共同体层次/基本事项层次的冲突不是民主政治可能的基础,甚至也不是任何政治体可能的基础,因为这种冲突乃是真实的冲突,其唯一的解决方式可能是内战和分离。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并未参与其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其运作则在基本事项的正当性危机已获解决之后。(17)
借鉴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危机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没有解决认同冲突和危机的前提下是引入“民主”游戏,必将导致畸形民主,使民主成为政客操纵统独的工具。
最后,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看待新发展主义的西方中心倾向?从一开始,发展主义就含有强烈的政策动机和“输出民主”的意味,出于含蓄考虑,才将目标由“民主”改为“政治发展”。西方比较政治学界在进行发展研究时,尽管越来越多地考虑了区域的不同特性,也将政治与经济手挽手前进的神话打破,但是由于“民主”这个词汇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其界定也是缘于西方的政治实践,所以在考虑“民主的社会条件、民主巩固与转型的要素”这个问题时,必定会或多或少地带有西方人自己的主观色彩,以“强国家—弱社会”、选举民主、多党竞争、权力分立为标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在“民主”这个含义上与西方学者达不成共识,对发展主义的西方中心倾向就将永远怀有警惕。但是,如果完全否认“民主”的含义,则失去了学习人类先进政治文明成果的机会。比较理性的态度是,对于发展主义(无论新旧)中不适合自己情境的部分有所放弃,对于某些历史上共同走过的经验和教训有所吸纳和借鉴。而对于新发展主义的贡献与局限,同样值得中国比较政治学者慎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经验应该能够给予新发展主义另一种不同声音的回应。
注释:
①参见曾毅:《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路径》,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②Seymour M.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No.1(March1959),pp.69-105.
③Paul Pierson,"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29,No.2,April 1996,p.126.
④Theda Skocpol,"Why I am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Polity,vol.XXVIII,No.1,Fall 1995,pp.103-106.
⑤⑥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271页。
⑦⑧(14)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 &John D.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Polity Press,1992.p.76,p.271,p.287.
⑨杨光斌:《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论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318页。
⑩(13)Seymour M.Lipset,"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9,February 1994,p.17,p.14.
(11)A.H.Somjee,Development Theory:Critiques and Explorations,London,Macmillan,1991.pp.127,pp.129.
(12)[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15)(17)[意]萨托利:《最新政党与政党制度》,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2、22—26页。
(16)参见陈明明:《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关于政党及其革新的一项词语梳理》,载肖滨、郭忠华主编:《中大政治学评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标签: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