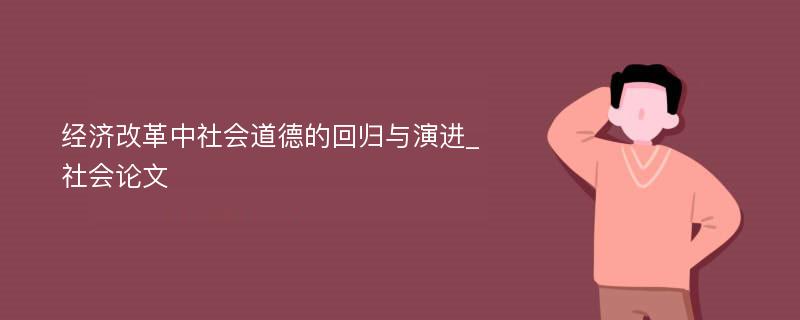
经济改革中社会道德量的回归与进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改革开放21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思想解放所催生的巨大经济动能改变了我国贫困落后和僵化保守的形态,一个充满朝气和进取性的民族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由物质进步带动的利益神经的觉醒,呼吸着长期沉淀的逐利本能,利益意识向全社会扩散,逐渐为人们所认同与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范围急剧拓展,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如魔法一般喷涌而出。但缺乏规范的商业意识和逐利行为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经济具有过分商业化的倾向,原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标准受到冲击,不少人的思想找不到归宿,原来具有道德思想的人在思想变迁中感到失落和痛苦,尚未建立坚定道德观念的年轻人则在新旧道德观念碰撞中迷茫,还有人甚至认为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衰落是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必要代价。一时间,“道德滑坡论”、“道德让位论”、“道德降调论”纷纷粉墨登场。道德观念方面的混乱倘若不及时澄清,将会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众多的概念难以量化,也难以衡量和比较。在此,为研究的需要,本文先提出三个关键词的定义。一是“道德量”,我们将其定义为:在某一时刻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意识中所具有道德的总水平。道德量是不断变化着的。二是“标准道德量”,我们将其定义为:在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时,为满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人们所应该具有并能够具有的最高道德量。标准道德量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内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在社会变革中才能相应地发生变化。三是“道德水平”,我们将其定义为:某一时刻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道德量与该时刻社会应该具有的道德标准量的比值,即:某时刻社会道德水平=该时刻社会道德量/该时期道德标准量,期望道德水平是指人们心目中所满意的社会道德水平。这里要说明的是,无论道德量还是标准道德量,其数值只能靠人们主观的评判(如专家打分)和心理感观获得,而道德水平可以在道德量和标准道德量量化后计算取得。
二
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中,我国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之中,人们相互信任、团结,相互帮助而不求回报。以我们的定义,当时的社会道德量是比较高的。计划经济更为注重集体利益,个人的物质需求很低,社会物质供给也很低。虽然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但因为整个社会生产力很低,人们物质生活比较贫困。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如缺乏强有力的观念支撑是迈不开大步的,而且这种观念必须具突破重重传统束缚的冲击力。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要关注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实质,他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几十年,到现在还是人民生活艰难、国家贫穷落后,这怎么能称得上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必须要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物质财富不断增长。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将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邓小平同志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以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看,物质利益占了相当的比重。利益追求是深得社会发展最基本要义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最后达到共富的政策是深得最广大社会成员欢迎的致富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致富浪潮推动着中国各地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GDP连续20 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物质财富急速涌现。而当前的相对过剩市场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作了物质追求上的极好注解。在这过程中,利益追求逐渐深入社会经济各肌体之中,产生了所谓“一切向钱看”的粗俗真谛。诚如民谚所言:“50年代跟着革命走,握着同志的手;60年代跟着斗争走,挥舞钢铁般的手;70年代跟着运动走,握着没准儿的手;80年代跟着感觉走,牵着梦的手;90年代跟着市场走,抓住钱的手。”改革开放、经济转轨时期,在观念意识方面,人们对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概念如“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进行质疑和思考。人们在50年代所建立的人帮人、团结、彼此信任、对人坦诚的社会道德氛围开始流失,其道德量和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并落后于人们心目中的期望道德水平。于是,人们感到人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物质利益化、“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部分人出现了思想偏向现实化,价值取向实惠化,道德标准双重化,择业行为短期化,文化兴趣多样化,婚恋观念开放化,消费行为超前化等现象。尤其在个别人中,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本位主义日益严重,享乐主义逐步扩展,拿来主义随波逐流。甚至出现了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经济动物”,不择手段、见钱眼开的“道德思想坏死者”。由于社会道德量下滑,在商务活动中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短斤缺两纷纷出笼。
追求经济利益的狂热不仅在经济领域愈演愈烈,而且把个别社会管理部门如政府行政部门、司法系统等也深深地卷入进去,“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全民经商、“下海”成为时尚,公司犹如雨后春笋,甚至形成了好象不经商、不下海就不是时代中人的风气。非物质生产领域如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科学、基础科研部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评价开始松动,陷入低谷。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在利益追求的冲击下开始急剧演变,而新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念体系尚在孕育之中,社会进入道德观念整合时期。在物质进步的映衬下,日益暴露出中国缺乏强大的维系社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标准。利益追求观念在推动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唤醒了人类本身的攀高心理,从一个巨大破坏和冲击传统体制的强有力武器转变为社会经济转轨的催化因素,同时使得社会道德量在其作用下开始走向嬗变。
三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367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 我们愈来愈清楚地感受到精神文明和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6年中国共产党十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了这一目标,并且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文化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建设并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体系已被清晰地列入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和目标之中。
随着在思想路线方面对精神文明和道德观念建设的认识深化和强调,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又开辟了精神文明的战线:大力弘扬、宣传和灌输正确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在全社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如“七不规范”等;对社会不同职能领域和部门、即市场商业运行和社会公共服务部门进行严格界定,对政法部门等退出市场运作的规定等;提倡职业道德、规范服务和商业文明;加强各种法规和制度建设,尤其是对市场运作行为的规范和约束。
精神文明建设有力地抵制和消除了“金钱万能”、极端的利益追求倾向和市场混乱局面,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在逐步出现;各地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爱心活动蓬勃开展,慈善事业蒸蒸日上。在去年全国抗洪救灾中涌现的动人事迹和忘我牺牲精神,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最生动体现。
但是,当前在精神文明和道德观念建设方面仍有缺陷。首先是我们还是比较注重精神感化和个人的内在修养,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机制规范,在实践中制度漏洞留给极端利益追求者较大的活动空间;其次是在道德观念和经济伦理的内容方面缺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适应性和融合性,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状况,形成经济运行实践和伦理观念两层皮,这就很可能产生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再次是道德观念和经济伦理对促进市场经济深化和发展方面存在功能欠缺,或者说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需要的道德观念的内核尚缺乏深刻了解和把握。
当然,提出精神文明和道德观念问题已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即在一定发展阶段,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已让位于精神方面的难题,并且这一问题正在被充分重视。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我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主义还在应该那些方面体现出自己的特征。
在社会达到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社会理性和精神文明建设使原本陷入低谷的社会道德量重新充盈,道德水平以较快的速度接近期望道德水平。社会道德量的回升拉动社会道德水平的上扬,扫黄打非、惩治腐败、打击犯罪等有力措施,净化了社会风气;同时,香港和澳门回归、人民币不贬值、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重新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打开世界窗口以后,人们客观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盲目乐观也不过于冲动、急于赶超,而是从落后中找到自己的差距和民族奋斗的方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于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道德水平重新向期望水平回归,人们惊异地发现“雷锋又回来了”。
四
道德标准和道德观念是有阶段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中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条块分割模式,强烈要求各市场经济参与者对利益追求的途径、手段及其内涵抱有深刻的认识,并以此为核心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道德标准。
道德观念的发展和变迁依赖于当时社会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即必须符合时代的基本发展要求,超前和滞后都将使这种道德标准缺乏生命力。从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分析,其在宏观上不能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路线相背;在实践中也不能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利益规律相对抗。道德标准不是用来制止人们追求利益和满足的,也不是把个人利益追求贬为道德低下。我们所需要的新道德标准和观念必须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创建出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竞争有序的社会文明和氛围。
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道德标准只是一个幌子,如果缺乏特定的追求目标是无法评判道德标准正确性的。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发展与改革则要求道德遵从合理追求利益的前提,由此实现社会有序、快速的发展。在改革初期缺乏规范、粗俗追求利益的阶段,社会道德抵挡不住物质诱惑,社会道德量是流失的;同时,道德标准是苍白无力的,是一个空虚的数值,难以达到和实现。在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在一个规范的经济环境中,为顾客服务、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市场经济商业文明的精髓,而且还为社会文明重塑了一个着力点和抓手。那些真正为顾客服务、赢得消费者信任和欢迎的企业和经营者,才能在经济生活中生存和发展;而那些搞假冒伪劣、欺骗人们的厂商,最终将被理性市场和人们所唾弃。这种新的具有商业文明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将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历史的发展,为我们古老的观念如诚、义、信、礼等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内容。新的社会标准道德量在对过去标准道德量重新进行调整后,又加入了市场经济的道德理性标准,对传统理论和标准实现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我们必须打破传统伦理和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开拓,追求国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一度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使社会道德标准与现实产生某种脱节。现在,我们在经济改革已经在物质上取得一定成就时,就必须重新冷静地审定社会的标准道德量及其内涵,发现并纠正以往的不足之处,并重新定位社会精神理念。经济改革在初期由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过激和粗放使社会标准道德虚化,人们的期望道德水平难以实现。而在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经济改革为社会的标准道德量注入了全新的内容,社会的道德标准得以新生和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衰落或不再进步不是人种的退化,而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使其缺乏新的素材。”(注:罗素:《中国问题》,第152页。)而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仅在物质财富上滋润着中国人民,而且在社会标准道德量上也实现了量与质的飞跃和重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随着经济改革中社会道德量的回升、社会标准道德量的重新衡定,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将越来越接近人们心目中的期望道德水平,人们将生活在理性有序、平等竞争的21世纪。
标签: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精神文明论文; 道德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