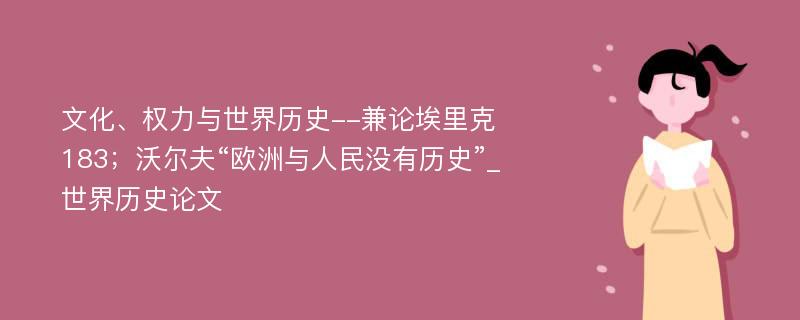
文化、权力与世界历史——兼评埃里克#183;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沃尔夫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权力论文,埃里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建立一种科学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以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具体到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则需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本文在评价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的基础上,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文化、权力等问题,以期揭示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和国家之间高度互动的横向联系,而不是将之看成“欧洲中心”的力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过程。
一、埃里克·沃尔夫的生平与学术
埃里克·沃尔夫1923年2月1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年少的沃尔夫被家人送往英国求学。1940年,英国开始拘捕来自敌对国家的外国人,沃尔夫只得前往美国。同一年,沃尔夫进入纽约王后学院学习。二战期间,沃尔夫在军队服役三年,战争结束后又重返学校,于1946年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随后沃尔夫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①
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是美国人类学研究的重镇,弗朗兹·博厄斯曾任执掌人类学系多年,这里还汇聚着拉尔夫·林顿、露丝·本尼迪克特等知名学者。当沃尔夫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时,博厄斯已经去世,他所开创的人类学研究风格,即所谓的“历史特殊论”——反对古典进化论单线进化和寻求人类普遍进化的法则,主张研究特殊地区的特殊历史,强调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性和独特性等,已不再盛行。时任系主任的是以提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而著称的朱利安·斯图尔德。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的发展与其所属的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具体的环境塑造了特定的文化特征。不过,斯图尔德并不是环境决定论者。在他看来,环境与文化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它们构成了辨证的能动关系。相似的生态环境可能会造就不一样的文化形貌,而不同的生态环境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文化形态,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世界各地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②博厄斯和斯图尔德的思想对沃尔夫都有着深刻影响。
沃尔夫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该校的政治风向是向左转的,马克思的理论在学生中影响巨大,沃尔夫也从中获益良多。这些政治上的理念在他后来的学术著作中都有所反映,我们可以从他毕生关注的权力、政治、农民、殖民主义等主题中清楚地看到。像当时许多左派学者一样,沃尔夫学术研究的起点是从拉丁美洲开始的。在完成了关于波多黎各农民的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后(1951年),沃尔夫前往墨西哥进行实地研究。他系统考察了墨西哥前西班牙时代到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历史,试图从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找到墨西哥民族性形成的原因。这一成果后来以《颤动大地之子》为名出版。③
沃尔夫的研究从一开始便体现出一名人类学学者并不多见的历史视野,他擅长将人类学家偏好的微观分析与宏观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印证人类学的某些理论或结论。1969年出版的《20世纪的农民战争》是沃尔夫的一部力作,在这部极具全球视野的著作中,沃尔夫对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六个国家的农民战争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总结出农民战争特别是胜利了的农民战争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1.推动农民战争的中坚力量往往是农民中的中间阶级;2.最具反抗倾向的农民总是处于国家有效的政治和经济掌控之外,他们既有较多的政治自由,也更愿意维护他们的传统文化;3.农民运动只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它发展成民族解放战争还需要外在力量的领导,但后者实施工业化的措施却要终结农民的生活方式,这就使得农民既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受益者也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受害者。④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沃尔夫的研究,他的一个贡献就在于为人类学引入了历史的分析方法。虽然任何一部人类学著作都必然涉及历史内容,但是,人类学家更多地是把历史资料当作当前民族志的背景,而不是当作人类学分析不可或缺的部分。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对“空间”(相对单一静止的社会)的兴趣要高过对“时间”(历史变迁)等问题的关注。纵然某些人类学家能够深入历史背景之中,但他们也不是就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展开他们的论述,而是将历史作为探讨文化演变的有效结构。这种只是将过去机械地应用于现在的方法并不能让那些更具历史感的人类学家满意。以主张弥合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分歧而著称的萨林斯就一再强调,历史维度的引入对分析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十分重要。他认为,文化是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⑤吉尔茨则进一步指出:“人类学家不应当只对过去感兴趣,还应当对历史学家赋予过去以现代含义的方式感兴趣”。⑥
对沃尔夫来说,历史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人类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避免因专注于封闭社会和田野调查而产生的简单化倾向。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沃尔夫就呼吁人类学家应当去书写一部系统的世界历史(a systematic history of the world)。⑦这里所谓的系统的世界历史,是指涵盖多重视角的、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多种世界图景的全球互动的历史。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沃尔夫在70年代便开始着手构思写作一部人类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可能性,力求证明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乃是一部多样复杂且高度互动的族群关系史。沃尔夫坚信,近代任何社会或文化绝无独自发展而不与其他族群交融的可能,着眼于单一民族或国家的个案研究,无法掌握人类社会问题的真相。这一思想最终结晶为《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⑧
除了上述著作外,沃尔夫尚有多种专著与合著问世,并有大量论文及评论散见于各种重要刊物。1999年3月6日,在出版了最后一部书稿《展望权力:统治与危机的意识形态》⑨后不久,沃尔夫与世长辞。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沃尔夫以其特有的历史视野和历史分析方法在推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交汇中成绩斐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夫对欧洲与非欧洲社会之间关系所作的全球性历史分析,以及他对非欧洲社会在参与和塑造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地位的肯定,都为我们客观全面地理解世界史、乃至全球史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
二、再思文化
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前言中,沃尔夫劝诫学者们应回到以博厄斯、克鲁伯等人为代表的旧式人类学曾经有过的洞见上,即努力发展一种全球文化史,以此表明人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中建构他们各自的文化的(前言第1页)。⑩这就要求学者在研究特殊社会文化的同时,必须摆脱单一文化或民族的局限,将之放在文化交往的背景下或全球框架内加以考察。
然而,以往的人类学家在看待不同的文化时,总是从价值优劣的角度对之进行评判,得出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进步的论断。爱德华·泰勒就认为,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是从同一起点、沿同一途径单线进化而来,现代欧洲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体现了进化的最高水平。他宣称:“文化实际上存在于不同发展等级的人群中,这就使得我们能够选取特定的例子来作比较和评价。欧洲和美洲(指北美——引者)的高度文化的世界,就当这样做,把自己的民族放在社会序列的一端,而把蒙昧部落放在另一端,并按文化程度把其余的人群分配在这一范围内。”(11)博厄斯等人与之不同,他们认为各种文化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因环境条件和传统功用的相异而无法比较,没有所谓普遍的、绝对的文化价值标准,一切文化的价值在全球文化场域中都是相对和相等的,不能把某一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于另一不同的文化上。博厄斯指出:“对普遍化社会形态的科学研究要求调查者从建立于自身文化之上的种种标准中解脱出来。只有在每种文化自身的基础上深入每种文化,深入每个民族的思想,并把在人类各个部分发现的文化价值列入我们总的客观研究的范围,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12)今天看来,正是这种对文化价值相对性的理解才促成了现代人类学中文化概念的产生,并由此引导出以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将文化视为复数的结论。
复数的文化概念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与源自18世纪欧洲思想的单数文化概念截然不同。在后一种观念中,文化被认为是固定的、单一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它的出现与当时欧洲民族主义的勃兴紧密相连。按照沃尔夫解释,在那个特定时期,“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谋求统治地位,而其他国家正在谋求自身的认同和独立。每个正在奋斗的国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社会,都受其特殊精神或文化的激励,这种观念无非是为了证实它想形成自己独立国家的愿望和正当性。独立的、一体的文化概念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文化方案。”(452-453页)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往往被视为封闭而非开放的体系,这些体系的基础便是特定的语言习惯、领土疆域、以及创造了居住在其中的人群所具备的民族特性等。文化或文化产品也因之被用以向人们传达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之情,以此来培养人们强烈的民族意识。(13)
如果说单数文化概念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不无关系,那么它的深化与发展则是近代欧洲殖民扩张的结果。在这个被布克哈特称作世界的“发现”的过程中,(14)欧洲得以近距离面对各种异文化并对它们进行描述与研究。这是一个欧洲在不断丰富和扩充其传统学科——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博物志,以及创生新学科——人类学、比较语言学、字典编纂学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利用各种学科制造知识的权力,去限定其对象的过程。具体说来,欧洲在审视与界定异文化时,通常基于一种主客分离的二元认识论前提,它把欧洲文化视作一种不变的原型(主体),其他各种异文化都被笼统地划分为具有某种共性的另类(客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只有进入以欧洲文化这一主体为中心的评介体系当中,才会显现其内在价值。(15)在构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诉诸文化上的“想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16)其中,异文化要么被不断地他者化,推向欧洲的对立面;要么被极大地均质化,消除其文化上的特性后纳入欧洲的解释模式之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单数文化概念由此成为欧洲审视非欧洲文化的一个重要准则。
单数文化概念的这一特点在作为知识创造者的欧洲和作为知识客体或对象的非欧洲之间划出了一道人为的界线,并使得欧洲与非欧洲原本空间上的距离转化成了时间上的差距。对文化概念的这种单一理解,构成了18世纪以后世界历史编纂的理论基础。反映在历史认识论上,非欧洲的历史开始被证明滞后于欧洲的历史或者被排斥在欧洲的历史之外。正像黑格尔所论及的,只有欧洲才有“历史”,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因为它们还处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之外。(17)
沃尔夫显然反对这种历史认识论。在他看来,欧洲不只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处在世界历史之外的民族”并不是在消极地等待欧洲将它们带入世界历史,它们也在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因为复数的文化概念告诉我们,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它们处于不断的相互影响之中,正是依靠这种文化间的流动,世界才被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基础上,沃尔夫引入了“文化丛”(cultural sets)这个概念,强调居于文化丛中的各种文化在社会联系的多重作用下,处于不断的建构、解构和重建之中。没有哪种社会或文化是既定的,依靠内部的本质统合在一起。因此,“固定的、统一的和有界限的文化概念必须让位于文化丛的可流动性和可渗透性观念。”(453页)当然,文化之间的流动、混合与影响并不是一种抽象行为,它只有借助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互动才会发生。所以,文化必须被置于变化着的、多重的社会联合体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这样,沃尔夫就将对文化概念的再阐释很自然地转移到对人类整体历史的探讨上。为了表明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广泛联系在欧洲历史这一主导叙事之前就已存在,沃尔夫特意选择1400年作为人类全球历史的开端,而不是多数学者所认定的1492年或1500年,并把对欧洲之外地区的考察放在首位。(18)这一时期,尽管欧洲扩张的序幕还没有拉开,那个被称作全球化初始阶段的时刻尚未来临,但是,无论是旧世界还是新世界——从近东到东亚,从北美到南美——各种文化和族群依靠霸权政治(帝国)的征服与融合、长途贸易(商业)的推动与作用,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东、西两半球,各种人群通过可渗透的社会边界相互影响着,创造出混合的、交织的社会与文化实体。即使存在孤立社会的话,那也是暂时的。”(87页)沃尔夫试图以此说明,在1400年这个业已形成的全球系统内,欧洲是没有什么特殊地位的,它和那些被认为后来才“进入”世界历史的地区——非洲、亚洲和美洲——一样,都是这个全球系统中平等的一员。即便1492年之后,由于欧洲的介入,世界形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系统,但是在沃尔夫看来,这个新的系统并不是什么开创性的产物,它不过是对以往世界性联系的一种延续,使“世界各地人民进入一个新的相互依赖的状态”之中(15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沃尔夫的整体世界历史观中,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虽然此前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分别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作了颇具洞见的考察,但他们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欧洲是怎样通过扩张逐步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中来,即中心是如何征服边缘的。(19)这样做的话,必然会疏于考虑欧洲之外社会的复杂性,它们在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的生存方式,以及此后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工业资本主义是怎样逐步渗透、征服和破坏或吸纳这些生存方式的。沃尔夫提出,应当用人类学家考察小规模人群的方式去关注欧洲之外的社会,借用马林诺夫斯基话来说就是,应当以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来看待欧洲之外的社会。(20)这就要求人类学家在对待不同的个案时,必须依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去创设一种与他所观察的对象——那些不同于自己的文化持有者——的文化状况相吻合的解释。对于这一点,吉尔茨有过更为直接的表达:“人类学的分析就是力图按事物的本原结果所呈来操作,而不是按人类学家在心灵上所认其为应是如此或需要如此的结果而操作。”(21)这就是说,在对欧洲之外的社会进行考察时,学者们必须抛弃既有的定见,不能再以欧洲的标准对之作出解释,因为如此以来只会制造出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对立,而对客观理解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不利。
回到沃尔夫的认识上来,他反对用独立而分离的文化系统分析模式来看待世界,强调世界历史无论在包容性体系层次还是在小群体层次上都是同时进行的发展过程。人们之所以忽视这一点,是夸大了欧洲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把它塑造成打破了各个封闭社会的“世界历史”的开创者形象。沃尔夫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在欧洲最终主导世界之前,那个被称作“世界历史”的状态就已经在普遍联系中存在了。作为普遍联系的世界的一部分,欧洲的特殊性不在于它是所谓的“创造者”,而在于它是一个推动者——将世界推向更为紧密的联系之中,且这种推动也只能是在普遍联系之中发生的。因此,世界历史不应该被描述成是一种从地方封闭状态向世界日益一体化和同质化发展的历程,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认为世界历史是随着新兴的普遍主义力量“渗透”到各个不同的区域而展开的观念也是没有依据的。因为现实世界自始至终有着复杂的联系。(22)这也是沃尔夫为什么要大书特书“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原因。在他看来,现代世界的形成正是由这些“没有历史的人民”与“有历史”的欧洲,交互作用而造就的历史。虽然身为弱者,但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对世界历史的参与和创造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绝不低于“有历史”的欧洲强权。“无论是那些宣称他们拥有自己历史的人,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都是同一个历史的当事人。”(32页)离开了前者,我们是无法洞察世界历史的真相的。
三、权力与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历史编纂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欧洲思想的产物。尽管在古代世界,东西方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但是,他们所撰写的历史还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书写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只有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散时才具备了条件。(23)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力量驱使欧洲人遍及世界,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以往建立在道听途说和零星记录之上的对世界的认识将让位于欧洲人更为全面的对世界的亲眼观察和切身体验。不论是对异国请调的过分渲染、外部世界的如实记录还是对“野蛮他者”的无端想像,欧洲人总是试图将各种异域文化纳入他们所追求的“内在一致性”或合理性当中。从这一点来看,欧洲人在编纂世界历史时,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具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不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欧洲资产阶级给世界带来巨变时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4)——欧洲人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部世界历史。
客观而言,以某种民族或狭义上的种族为中心看待其他文化,并对之产生否定和排斥或许是人类社会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将之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实践的高度却是欧洲的发明。(25)勿庸置疑,欧洲人在书写世界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中心主义”与其历史传统、近代以来在物质与技术上取得的巨大进步,甚至殖民主义关系密切,但也不能忽视欧洲在知识创造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才使得欧洲对过去的建构方式被普遍接受和承认,成为一种智识上的霸权。自福柯首次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作出独创性的评论后,这一理论已远远超出对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组织形式和知识形式的批判。(26)特别是萨义德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欧洲对东方的重构与支配,并由此展开对欧美主流人文科学的批评时,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就成为解构欧洲话语的一个重要着眼点。(27)通常认为,欧洲关于自我知识的进展体现了将自身独立于甚至对立于外部世界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断将欧洲之外的世界降低为欧洲的他者,以此来强化欧洲自身的特殊性与优越意识。在这种权力的作用下,新知识的创造以一种更加“科学”的形态——即所谓的“社会科学”——逐渐成为世界标准。它不仅使欧洲人因为享有“科学”的方法而对自我知识的合理性以及对非欧洲社会评价的客观性深信不疑,也深深影响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以及本民族历史的看法。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学术文化正是欧洲之外的人民所缺少的,即使他们拥有学术文化,他们也将成为欧洲的研究对象。从16世纪初开始,在欧洲扩张和在殖民地建立高等学府500年以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非欧洲的人民甚至怀疑自己的学术、文化与传统,因为这种学术在欧洲教育机构和欧洲的语言中是不曾被描述的。(28)
作为一位西方左派学者,沃尔夫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权力问题,在生前的最后一部书中,他总结性地说到:“多数优秀人文科学著作的一个缺陷在于,它们不愿也未能去理解社会关系与文化配置是怎样与对权力的考量纠结在一起的。”(29)基于这一点,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对欧洲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作了深刻检讨。沃尔夫首先质疑的是,既然联系无处不在,那么人们为什么还坚持把动态的、相互关联的现象转化成静态的、没有关联的事物?沃尔夫将之归结为西方人认知历史的方式,即认为历史具有一种复杂而连贯的一致性,并从这一特性中推导出一套西方特有的系谱。“根据这部系谱的说法,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工业又与民主一道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而美利坚合众国则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第9页)沃尔夫认为,这种发展图式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它把西方的历史变成了一个道德成功的故事,且依靠这种内在驱动逐步走向世界历史的终点。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诸如“国家”、“社会”、“文化”等抽象概念被想像成具有内在同质性和外在独立性、封闭性的实体;另一方面,西方与非西方的历史都被作了本质主义的划分,西方历史被提升到一种世界历史意义的高度,非西方历史则被推向原始或静止的状态,落入到“没有历史”的境地。世界历史也因此被理解为欧洲的文化经验和制度体制逐渐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的过程,或者说由欧洲逐渐打破各地的封闭状态,将世界整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
不仅历史学如此,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也都具有类似的特征。沃尔夫指出,在19世纪中期,西方的社会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变,对自然和不同人类的研究分裂成了独立的(和不平等的)专业与学科。虽然这种分裂有助于产生知识的专业化,但这种分裂也是致命的。它不仅导致了对人类生存的特定方面的深入而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把为这一分裂辩护的意识形态理由转变为专业本身在智识上的正当性(13页)。因此,这些专业学科首先都是从特定的角度去理解世界的,缺乏一种联系的视野。其次,这些专业学科都力求将自己的观念和方法上升到一种认知世界的普遍方法论高度。沃勒斯坦同样认为,现代知识结构的一个特点就是主张普遍性知识的存在,主张在真理的构成中不承认可能的理论变异。(30)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欧洲的社会科学体系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证明欧洲的特殊性,并将这种特殊性放大,形成种种世界历史性的命题。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势必会妨碍人们对历史差异的理解。(31)不过,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当欧洲人将这种源于自我经验的历史观念推广到欧洲之外的世界时,他们正是凭借着对现代知识的绝对权力,给那些早已存在且高度发展的社会组织(如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等)的历史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甚至是替换。欧洲之外的社会要进入世界历史,就必须首先借助一些欧洲性的范畴或概念,如现代、进步、理性等,来反观自身以理解这个世界。然后,根据这一预设的目标,将自我的历史重新演绎成一段为什么没有获得成功(欧洲式的)和怎样才能获得成功的故事。
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书写中的现代性叙事为例,这一叙事将获得现代性视为落后的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范畴中的一种手段)。要展开这一叙事,就需要设定一个“前现代”的概念来凸显现代性的出现是一种必要的超越。由于和过去之间的断裂是叙述历史变动的关键,因此,前现代就必须被设想成具有不同于现代世界的本质。一方面,前现代的某些文化传统被视为对现代性的抗拒,原有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模式也被视作社会转型的障碍。另一方面,尽管前现代与现代并不相容,但是它的某些价值观念还是被认为有可能孕育了现代性的某些特质,以便从中引导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现代性叙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勾画了一幅迈向成功的蓝图,但是它在方法论上并没有摆脱欧洲知识与权力的束缚,它所要表达的意图——若不是欧洲地缘政治力量的打断,世界其他地区迟早也会进入现代社会——仍然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式的历史再现,或者可以将之称作“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主义”。(32)此外,由于对“前现代”和“现代”作出了实用主义的划分,现代性叙事便轻率地排除了自我历史中某些重要的经验和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自我历史的否认。
对于这种状况,沃尔夫有过鞭辟入里的评论:“对共识的控制使得意识形态的主宰者可以强行推行某些范畴,而人们正是借助这些范畴来认识现实的。反过来,这也赋予人们拒绝接受新范畴的能力,将之归于无序和混乱的领域,使它们变成社会层次和象征层次上的盲点。”(454页)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况,认识到那些被忽视了的认知上的盲点呢?拉纳吉特·古哈建议人们去思考欧洲所限定的世界历史范围之外的那些没有被考虑到的事物,(33)也就是说,应当以一种欧洲之外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更为复杂也更为多样的历史。
四、世界历史中的地方视野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主要是美国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编纂方法发生了重要转变。一些更具宏观视野和理论抱负的历史学家开始反思先前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之上的旧式世界历史的种种弊端,他们主张超越西方史学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范畴的叙事传统,对探索跨文化和跨民族的大规模历史过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跨文化贸易、环境变迁、经济波动、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的传播等得以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34)在上述方法论的嬗替中,“全球史”的出现显得尤为醒目。尽管全球史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新理论,但与传统的世界史相比,它在研究视角、编纂范围、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话语特征诸方面都有所突破,显示出新的世界历史编纂模式。(35)更有学者试图将全球史与世界史区分开来,认为全球史不仅是对历史编纂中民族国家架构的超越,还在于它首先关注的是全球一体化的历史,既包括全球化的当前阶段,也包括对历史上全球化因素的追溯等。(36)
以全球史为代表的新的世界历史编纂方法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它作为国际会议的主题而倍受西方与非西方学者的共同关注,还在于它这一次所采取的更加中立的立场,引起非西方学者的热切拥抱。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所谈论的权力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会因为“全球史”的出现而消失吗?蒲乐安指出,当今世界历史领研究域内的一些动向(moves)主要是一种美国现象。(37)理查德·范恩(Richard T.Vann)也承认,全球化的历史书写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少数几个国家,他并不主张将这一源于西方的历史编纂模式“全球化”,而是强调历史学著作应吸收世界各国的丰富文化并尽可能地抵制因国际资本主义和强权政治而造成的同化,倾听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38)同样,国内也有学者对全球史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对全球史观中难以祛除的欧洲中心主义痼疾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担忧。(39)
正确地看待全球史,就必须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既要看到它在揭示人类发展规律中的积极作用和合理成分,也要看到其中所所蕴含的权力本质,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同质化倾向。为此,我们应当去深入理解世界历史中多样复杂且高度互动的横向联系,以及不同地区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有过精辟论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0)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论证了各民族、地方的历史通过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的联结而形成世界历史的一般过程,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联系和依赖的重要性。结合当前的全球史语境,我们也应当从全球进程的两种结构——全球和地方两个角度同时作出考虑。正如多米尼克·塞森麦尔指出的:“任何带有明确的全球化观点的史学研究也必须要找到能平衡普遍与特殊的方法。它必须对全球化结构的内部多样性和许多地方力量的全球化程度同时保持敏感。”(41)
因此,就目前的世界史尤其是全球史的编纂而言,当西方学者提出将历史全球化(globalizing history)或将全球化历史化(historicizing globalization)时,(42)我们则主张将全球史地方化(localizing global history),也就是说将全球史放在不同的地方情景中加以理解,以便能够重新审视作为总体性的世界历史与各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关系。将地方视野引入当今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来,并不需要从某些新的理论中汲取灵感,传统的世界历史编纂中仍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资源。传统的世界历史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由于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事务中的主角,基于民族国家框架的历史研究传统并不会消失,一个抽象的将民族或国家排除在外的全球或世界也并不存在。地方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世界历史中以民族、国家等小地点为单位的研究方法的重新认识,以更具操作性的区域意识(文化区域或经济区域)来应对全球意识的挑战。坚持一种从地方到全球进行概括的倾向,有助于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新理解当今的世界历史。
首先,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中包含着充满差异的多样性。差异使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也由此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在对世界历史作出理解时,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世界历史体现了对地方历史的依赖。因为正是借助地方性单位,历史学家才不但能够取得易控制的地方性专门知识,而且可以以此为基础,将各种地方性特点投射到更广大的空间和概念网络中去,进而分析大规模的历史过程,并注意到其中的普遍联系。其实,无论是沃尔夫的“系统的世界历史”,还是全球史或者现今被称作“纠结的历史”(43)的研究方法,强调的都是地方或区域之间的互动交流,关注的都是不同地区的相互影响与冲击,彼此的交流与塑造。不同的地区都是一个更大的历史的共同组成部分,而不是孤立的不同单位。沃尔夫一再强调的“没有历史的人民”对世界历史的参与和创造体现的正是这层意思。
其次,世界历史需要一种“以小见大”的视角。考虑到世界历史包含全球性历史与地方性历史两种维度,且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交融状态。因此,一切大历史或所谓的全球性变迁,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体系的建立等,最终会在较小的层面上有所反映。透过这些较小的单位去分析大规模的历史过程完全是可能的、可取的和必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世界历史进行研究时,必须重视从较小的层面去反观总体性的世界进程。既要看到全球性力量是如何给不同地区带来巨变的,也要关注各种地方性力量是怎样共同促成这一变化发生的,以及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传统世界历史中民族或国家这样的研究单位由此会获得新的意义,它们在参与世界历史创造中的主体性也会得到体现。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任何一部世界历史都不能回避全球范围内客观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依附性等事实。这一问题在传统的世界历史研究中已经被广泛提出,当今的世界历史研究也必须去思考这一问题和找到解决它的途径。所以,对世界历史或全球历史的探讨就不能仅限于物种交流、疾病扩散、技术转移等表层现象,还应当去揭示隐藏在这些全球性力量背后的不平等的权力和支配,以及各种地方性力量对统治与权力的抵制。(44)综合各种地方诉求并把多种地方声音纳入当今的世界历史中来,将有助于展现一幅更为全面和公正的世界图景。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再次借用沃尔夫的话——“无论那些宣称与历史有特权关系的人民,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命运”(457页)。
注释:
①本节对埃里克·沃尔夫生平的介绍主要参考了以下两篇文章:Ashraf Ghani,Eric Wolf,"A Conversation with Eric Wolf",American Ethnologist,Vol.14,No.2 (May,1987),pp.346-366; Jonathan Friedman,"An Interview with Eric Wolf",Current Anthropology,Vol.28,No.1(Feb.,1987),pp.107-118。
②参见Julian H.Steward,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5。
③Eric R.Wolf,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
④Eric R.Wolf,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9,pp.292-294.
⑤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⑥Clifford Geertz,"History and Anthropolcgy",New Literary History,Vol.21,No.2(Winter,1990),p.333.
⑦Eric R.Wolf,"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and American Society",in Dell Hymes,ed.,Reinventing Anthropology,New York:Random House,1969,pp.251-263.
⑧Eric R.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⑨Eric R.Wolf,Envisioning Power.Ideologies of Dominance and Crisi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⑩本文对《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观点或内容的引用均据中文译本。参见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1)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2)弗朗兹·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刘莎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13)关于文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可参见Anthony D.Smith,Nationalism.Theory,Ideology,Histo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p.33-36。
(14)在布克哈特看来,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为代表的近代早期欧洲文化经历了一个从“人的发现”到“自然的发现”再到“世界的发现”的过程。从人的“小宇宙”到世界的“大宇宙”认识观的转换,被认为是欧洲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观念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来认识世界的。布克哈特的相关论述,可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四编《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对这一观念的批评,可参见Walter D.Mignolo,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15)安妮·萨尔蒙指出,客体在西方思想史中具有消极意义,因为它们无法进行言说、思考和理解。让客体成为保持缄默的他者,是民族志中对待异文化的常见手法,它也是形成欧洲主体意识的重要来源。参见Anne Salmond,"Self and Other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in R.Fardon,ed.,Counterworks.Managing the Diversity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1995,p.41。
(16)笔者曾将“文化想像”定义为一种欧洲以否定他者的策略对非欧洲进行认知、表述与研究的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对非欧洲社会的虚构、否定与排斥。参见张旭鹏:《文化想像与“欧洲观念”的建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7)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版,第123页。
(18)对大多数西方学者而言,将1492年作为全球历史的开端是一件既合乎情理又理所当然的事。虽然有些学者认识到其中所包含的欧洲中心主义因素,但既然要对世界历史作出一种分期,1492年作为全球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还是能够接受的。这种矛盾心情在威廉·格林的一篇文章中得到淋漓尽致地表达。格林这样说道:“将1492年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分界线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假如横跨太平洋的行为并非那么困难,假如是中国人在 1492年发现了美洲,我们也非常有可能将这一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转折点。”参见William A.Green,"Periodizing World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34(1995),p.111。
(19)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的观点可参见他们分别出版于1974年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和1978年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中译本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20)Bronislaw Malinowsk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E.P.Dutton & Co.,Inc.,1961,p.25.
(21)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22)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前现代的世界就已经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并就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可参见 Philip D.Curtin,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Barry Cunliffe,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 of Interaction,New York:Methuen,1988; Janet L.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K.N.Chaudhuri,Asia before Europe.Econom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等等。
(23)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中,从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建立的角度详细论证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机制,此处就不再赘述。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可参见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第一部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5)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翰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序言第3页。
(26)福柯对权力的集中论述,可参见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ed.Colin Gordo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80。
(27)参见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28)阿里夫·德里克在描述欧洲学者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国人反思自我形象所产生的影响时,曾援引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黼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首先,我们缺乏科学。无论是在个人或国家的竞争中,决定成败的乃是知识程度。……在嘉庆和道光皇帝时西方科学之基础已经奠定,而当时我们的前人仍在写八股文,谈论阴阳五行。第二,到十八世纪中期,西方在运用机器来创造财富进行战争,而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及军事仍追随唐宋时的模式。第三,西方在中世纪时的政治样貌极似中国春秋时的情况,文艺复兴后则近似战国时期。西人培养起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深厚民族精神。而我们仍僵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总之,至十九世纪,西方世界已享有所谓的近代文化,东方世界仍深陷在中世纪。”参见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版,第285-286页。
(29)Eric R.Wolf,Envisioning Power.Ideologies of Dominance and Crisis,p.ix.
(30)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31)关于这一点,可参见一些学者对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分析”与“世界体系分析”方法的批评:Craig A.Lockard,"Global History,Modern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Approach:A Critique",The History Teacher,Vol.14,No.4 (Aug.,1981),pp.489-515; William B.Taylor,"Between Global Process and Local Knowledge:An Inquiry into Early Latin American Social History,1500-1900",in Oliver Zunz,ed.,Reliving the Past:The Worlds of Social History,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5,pp.115-181。
(32)“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一说法出自沃勒斯坦,参见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第194页。
(33)Ranajit Guha,History at the Limit of World-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p.7-8.
(34)对西方史学界世界历史研究方法的转变及其影响的评价与展望,可参见Michael Geyer,Charles Bright,"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4(Oct.,1995),pp.1034-1060.
(35)何平:《全球史对世界历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36)Bruce Mazlish,"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28,No.3 (Winter,1998),p.389.
(37)Roxann Prazniak,"Is World History Possible? An Inquiry",in Arif Dirlik et al.,eds.,History after the Third Worlds.Post-Eurocentric Historiographie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p.221.
(38)理查德·范恩:《历史编纂学一定要全球化吗?》,郭大光译,《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第35、37页。
(39)参见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黄洋:《全球史的陷阱》,《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第6版。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41)多米尼克·塞森麦尔:《全球史——挑战与束缚》,郭艳秋、王昺译,《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6页。
(42)Jerry H.Bentley,"Globalizing History and Historicizing Globalization",Globalizations,Vol.1,Issue 1(Sep.,2004),pp.69-81.
(43)对“纠结的历史”的评价,可参见于尔根·科卡:《国际历史学会: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齐克彬等译,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9页。
(44)当前,西方与非西方一些致力于后殖民理论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影响,甚至成为当今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支派。参见Mary Louise Pratt,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Nicholas Thomas,Colonialism's Culture.Anthropology,Travel,and Gover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Gyan Prakash,ed.,After Colonialism.Imperial Histories and Postcolonial Displace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Bernard S.Cohn,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The British in Indi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沃尔夫论文; 人类学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