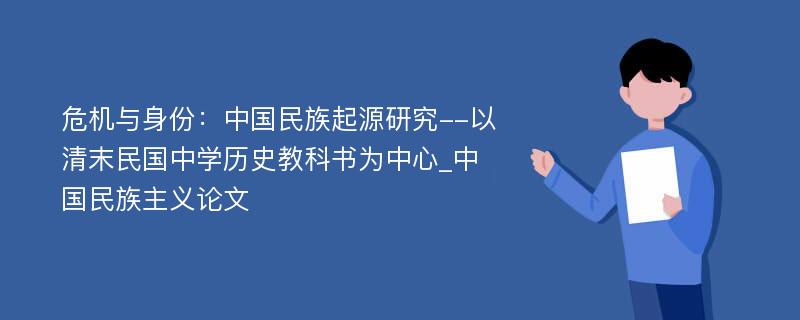
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溯源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清末论文,教科书论文,中国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溯源研究很重要。经过这种溯源,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来源,并在时间深度上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民族本身就是赖共同起源记忆赖排除外人的人群组合,因此当历史研究者对本民族溯源,或对本民族有密切关系的他族溯源时,经常难以脱离研究者自己的民族意象(ethnicselfawareness),以及对他民族的异族意象(the sense of otherness)。也就是说,常常民族溯源研究本身成为一种主观上诠释当前族群状况与反映族群情感的工具;学者以重建历史来阐述本民族为何优越,他族为何低劣,以及表达对本民族的期望。”(注: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75页。)在民族主义发展中,对本民族历史的寻根,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表现,也是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民族的溯源,即是对中国人种来源的追问,在20世纪前30年是个广泛关注的话题,具有相当的影响。在20世纪上半期,对中国人种起源的探究有个演变的过程,表现出几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10年代前后,这是相信中国人种西来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此时对西来说表示出一定的怀疑。第三阶段则是30年代以后,西来说被否定,土著说得以确立。中国人种起源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于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时期,是危机中寻求民族认同的一种努力。而民族溯源的这一变化,又反映出近代中国建构民族认同中的曲折历程。
20世纪初年,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生的时期。安德森认为,在民族主义形成中,“印刷资本主义”为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政府可以通过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来推动民族主义(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46—55、115页。)。在民族想象中,教科书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是建构民族形象的工具。对教科书的研究,是认识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路径。清季以来出现的新式教科书,都有着对中国民族(人种)来源的叙述,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材料发掘还不够(注:王尔敏较早注意到“中华民族西来说”的“思想史”意义,建议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目前,对中国人种来源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王东杰:《中国人种西来说与清季民族主义》,末刊;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中国人种来源的讨论,涉及到中国人类学、考古学诸领域,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本文的意图,是通过对清季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人种来源的表述,来探讨20世纪上半期近代中国在危机中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
一、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人种起源说
在中国人种起源上,传统的汉文文献认为是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向周边扩散。明代中西交通后,一度认为西方文明来源于中国。19世纪末,随着中西交往的加深,“中国人种起源”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出现。“汉族自有史以前久居其土乎?抑自他处迁来,其迹尚有可考者乎?此近人所谓‘汉族由来’之问也。昔人暗于域外地理,即以其国为天下,此说自无从生。今则瀛海大通,知中国不过是世界列国之一;远览他国史乘,其民又多非土著;而读史之眼光,始一变矣。”(注: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中国民族溯源是传统的“天下”观念动摇、近代的国家观念产生后出现的。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人种来源上,存在着非洲说、澳大利亚说、亚细亚北方说、美洲说、埃及说、印度说和古巴比伦说等,以“巴比伦说”影响最大,通常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即指此说。创此说者为法人拉克伯里,其在1894年出版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即《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中,列举了中国和古巴比伦在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科技发明和政治制度方面近百种相似之处,断定中国文明是从古巴比伦东迁而来:
奈亨台(Narkhunte)者,即近世Nai Hwang ti与爱雷米特Elamite历史所称之Kudur Nakrhunte相同,于底格里士河边有战功,当纪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或谓当纪元前二十四世纪至二十七世纪)率巴克(Bark)民族东迁,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葛尔(Kashgar)(即疏勒)沿塔里木河(Tarym)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其一族者,与其本族分离,向北方近烟尼塞河流域旅行。今日于河边,发现其用当时文字所成之古铭;而同时又有未达东方者,与北西藏之民族,结合而为一部族。此东迁之酋长,以中国古史证之,即黄帝也,又曰莎公(Sargon)者。于当日民族未知文字,为记事实,用火焰形之符号(案中国古史称神农用火德王,以火命官,故曰炎帝),是即中国所谓神农也。又曰但克(dunkit)者,近世Taanghieh迦勒底语为Dungi,亚多人Chalden。曾传其制文字象鸟兽爪之形,是即中国所谓仓颉也。巴克者,本当时命其首府及都邑之名,而西方亚细亚一民族,用以为其自呼之称号。今此语之存于西亚细亚古史者,即巴克之国Country of Bak,此民族其后有东迁者,是即中国所谓百姓。昆仑Kuenln者,即“花国”(Flowery land)以其地之丰饶,于后世子孙之永不能忘,既达东方,以自名其国,是即中国所谓中华也(注:(法)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转引自观云:《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37号。)。
拉克伯里此说一出,即有人附和: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著《支那文明史》(即《中国文明史》)对此进行了介绍;观云(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中国人种考》长文,对拉克伯里“汉族西来”说做了较为详尽的发挥,并从中国古史记载中为之论证(注:观云:《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37号。)。《中国人种考》影响甚广,“关于汉族由来,‘西来说’最盛行。此说始于蒋观云,蒋氏因我国古史传说,把一切文明的原始,集中于黄帝,疑惑不解,适见法人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说黄帝是从巴比伦来到中国的一个酋长,他从相信中国文明是由巴比伦来的。后来国人再依《山海经》,《穆天子传》、《遁甲开山图》等伪书加以附会,‘汉族西来说’遂盛行。”(注:朱翊新编著、陆光宇校订:《(朱氏)初中本国史》第1册,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4—6页。)《国粹学报》第1期也对拉克伯里的学说作了介绍。中国的一些学者,也相信西来说,从中国古籍中搜罗证据,为之证明(注:中国学者,像刘师培、章太炎、丁谦、黄节等人都曾著文介绍西来说。)。
中国文明源自巴比伦说经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著述而得推广,在国人蒋智由等的倡说下,被较多的中国人所认可。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多采用此说。
二、清末民初教科书中中国人种西来说
中国近代教科书是在清季教育改革中出现的,最初的教科书多是从日本引进,或是由日本教科书改编而成的。清末,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桑原骘藏、市村瓒次郎等人的相关中国史著述都被作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使用(注:参阅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译介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清末民初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民族起源的叙述上,大多采用中国人种西来说。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即是如此。在《东洋史要》中,桑原认为汉族在远古时候从巴比伦移居中国内地,栖止于黄河两岸,然后繁殖于四方。桑原在论述黄帝时直接引用拉克伯里的学说:“黄帝长于姬水。盖即今底格里士河,约直西历前二千二百八十年间,有王名廓特奈亨台者,属丢那尼安族,用兵平莎公后诸国寻率巴克民族东迁,从土耳其斯坦横断亚细亚中部山脉,由此东向,经新疆莎车府疏勒府,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出吐鲁番哈密二厅之边,抵中国之西北部,循黄河而入中国奈亨台。盖即中国之所谓黄帝巴克本民族之号;而中国之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以此地丰饶示后嗣,毋忘既达东方,遂以名国,即中国,之所谓中华也。又有人名,但克者,亚尔多人曾传其制文字象鸟兽爪之形,是即中国之所谓仓颉也。其余同处尚多。”(注:(日)桑原骘藏著,金为重译:《东洋史要》第1卷,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第15页。)
桑原的《东洋史要》被梁启超推为当时“东洋史中最良者”,“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专为中学校教科用,条理颇整……简繁得宜,论断有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东籍月旦》,第98页。)同时,市村瓒次郎编著的《支那史要》也持同样的看法:“汉人来自西北,渐及繁殖,遂渐逐于南方。汉人既斥苗人种,遂占有势力于支那本部。”(注:(日)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支那史要》卷一,广智书局印行,光绪二十八年初版,第4页。)市村在此虽未明言汉人来自巴比伦,但汉人从西北迁入则很明确。
上述的《支那史要》和《东洋史要》是日本人编著的中国史。清末中国自编的中国史,在中国人种来源上,基本上秉持了相同的说法。
夏曾佑在其《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注意到了中国人种来自巴比伦说:“至吾族之所从来,尤无定论。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据下文最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人与欧洲之文化相去近,而与吾族之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夏曾佑怀疑中国人种来自古巴比伦。他认为,世界人种“在上古时,大约聚居亚细亚西北之高原,其后散之四方,因水土不同,生事务异,久之遂有形貌之殊,文化之别。然其语言文字之中,犹有同者,会而通之,以观其分合之迹,此今日之新科学也”。夏氏此处即暗含中国人种外来之意(注: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光绪三十年初版,光绪三十二年再版,第9页。)。
刘师培则明确服膺西来说:“汉族初兴,肇基迦克底亚,古籍称‘泰帝’、‘泰古’,即‘迦克底’之转音,厥后逾越昆仑(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夏(今中亚细亚),自西徂东以卜居于中土。故西人谓华夏之称起于昆仑之花国(西人谓‘华’字起源,由中国开基祖东渐时,途径昆仑山下,有雄大之邦名曰‘华国’,心醉其隆盛,因记而传之子孙;及后人继先祖之志,遂称为‘华’。)”刘师培列举了盘古和天皇地皇人皇氏等人,认为“皆汉族初入中国之君也”。刘师培的说法与桑原骘藏如出一辙,系根据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再证之以中国古籍的记载(注:刘师培:《中学历史教科书》,《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8页。)。
民国建立后,在新编或重新修订的教科书中,也多是坚持中国人种外来说。民国元年校订的《中国历史》即是如此。该书由吕瑞庭、赵徵璧编著。在论述“汉人种”时,谓“此人种太古自西北而来,渐次移植于东南方,蔓延中国内地”。谈到“人民的繁殖”时,认为“中国内地,人民繁殖之始,邈不可考。然距今约五千年前,即栖息黄河扬子江之人民是也。是等人民,即苗人种和汉人种。汉人种由西北而来,居黄河沿岸。苗人种由西南而来,栖息扬子江沿岸,后渐繁殖。汉人种蔓延各地”(注:吕瑞庭、赵徵璧编著:《新体中国历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光绪三十三年版,第6-8页。)。中国人民是指居住在黄河和长江一带的人,这里的居民,不论是苗人还是汉人,都是由外地迁来的。
20世纪初年,对中国民族溯源和对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认可,有其复杂的动因。强调中国民族从西方迁来,能够增加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力。19世纪末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西方强大与中国落后的现实中,民族自信开始动摇,要完成“保国保种”的使命,必须唤起国民的民族自信,建构民族认同。“一种独特的思想线索把黄帝与西方人联系起来”,寻找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寻求一种民族上的平等,而这时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正好提供了很好的论据,“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种族平等得到了拉可伯瑞(即拉克伯里)关于两者在古代近东共同起源理论的支持”(注:(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09—111页。)。将中国民族的来源定于西方,可以取得与西方民族平等的地位。“西来说”反映出中国历史学者在体认到民族危机与挫折时,重新诠释本民族的起源以期望民族复兴的努力(注: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75页。)。“倡中西文化同源,希望借此增强国人的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其良苦用心值得肯定”(注: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第154-157页。)。
三、20年代对西来说的怀疑与反对
中国民族西来说在20世纪初年最为盛行,1910年代以后渐渐沉寂。到了20年代,对中国人种外来说的态度是“相信”与“怀疑”并存,而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日渐普遍。
20年代的教科书中,“西来说”的影响依然存在。1923年吕思勉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就坚持汉族“西来说”。吕思勉从中国古籍中寻找证据,证明中国人种来自西方。吕思勉提供了两条“证据”:一是关于“昆仑”的考证,认为今于阗河上源一带,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汉人西来之后,还祭“昆仑之神”;二是“汉族”的名称,古称“夏”或“华”,“夏”在阿姆河流域,古代汉人,居住在葱岭和帕米尔高原一带,这里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吕思勉认为,“这两条证据,似乎都还严谨的”,“其说自极可靠”(注: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篇,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3页。)。
1926年初版的《(评注)国史读本》也对汉族西来说持肯定的观点。该书原为李岳瑞编著,后来印水心进行了改编并加以评注。印水心指出:“近世西人有潘伯赖者,在中亚细亚发掘地层,证明纪元前八千二百五十年前,该地土质膏腴,当为古代文化散布之地。后经地质上之大变动,骤变为干燥之沙漠。其地居民,不得不迁散,移植于世界各地。此可为汉族东迁之一确证也”(注:李岳瑞原编、印水心修订:《(评注)国史读本》,上海世界书局1926年版。)。这里,李岳瑞和印水心认为不仅汉族来自西方,而且整个的“黄种人”都是来自西方的。
20年代,西来说的影响虽然存在,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在中国人种西来说较为流行的日本,就有不同的看法。著名的京都学派奠基人之一内藤湖南就反对此说,称力倡“西来说”的拉克伯里为“怪论家”,其说毫无根据(注:(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中国国内如缪凤林等人也对西来说进行了驳斥。缪是柳诒徵的弟子,柳诒徵对西来说持否定态度。柳诒徵对一些人以中国古史记载来附会此说,深为不屑,认为“中国古书,多不可信,年代对比,亦难正确”(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4—5页。)。缪承续了其师的观点,从时代、地理、人种等方面对西来说进行了反驳(注: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
部分教科书也对“西来说”表示怀疑和批评。梁园东在《本国历史》中谈及“中国的原始民族”时,对“民族外来”就持一种存疑态度。“地球上最初有人类,是在三十万年前;那时中国有没有人,还不明白。三十万年前的人类和现在世界上的人类,不是一种。现在人类,约是十万年前传下的。这十万年的人,怎样来到中国,变成中国人,现在也考察不明白。”至于汉族的来源,梁园东认为,“他们的来源,有说是4200年前从巴比伦迁来的,有说本是黄河流域的土著,更有说是东海岛民;这些都已不能确定”(注:梁园东编著,江恒源、苏甲荣校订:《初中本国历史读本》第1册,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版,第1页。)。梁园东虽未明言中国人是中国土著居民,但怀疑由西方迁来是很明显的。
金兆梓明确反对中国人种西来说。其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本国史教科书》中认为,“汉族西来之说,其持论殊嫌穿凿。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屈原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杨朱屈原去古未远,言犹如此,克知尧舜以前,即中国固有之传说,且多附会,至以巴比伦为汉族所从来,尤不可信。惟汉族先居昆仑而后东下,移植于黄河流域,案之载籍,或可差信”(注:金兆梓编,李直校:《新中学本国历史参考书》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2页。)。金兆梓认为,西来说本身的立论就存在问题,而以中国的传说来附会,更不可信。
1920年代对西来说的怀疑与否定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无法解决中国民族的真正起源。前引缪凤林的文章也是如此。缪凤林分析了当时认可汉族西来说的原因:“乃者拉克伯里、白河次郎辈,中有所蔽,不能明观乎是,既已凭其一知半解,著书立说,中土学者,于此新来之说,复不能审思明辨,或阙疑慎言;惟知巧为附合,助之张目,甚且并巴比伦史亦不知研究,徒拾彼等所说之一二以相矜夸”。缪的反驳,不仅仅指出信奉西来说的国人是有所蒙蔽,喜其新异,更是联系到了民族情感上,指斥他们认可西来说是背宗忘祖,“奉西戎为宗国,诬先民而不恤。”(注: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在缪凤林看来,接受西来说,在民族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缪凤林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反对中国人种西来说的人的观点。
由于教科书特殊的教化作用,对外来说的反对,其影响不可低估。这种向西方寻求民族自信心的民族溯源,到3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民族意识的高扬,终至抛弃。
四、中国人种土著说的确立
中国人种土著说出现甚早,1862年法人罗苏尔(Leon Rossomy)就开始倡导。1916年,英国人洛斯(G.Ross)著有《中国民族之起源》(The Origin of Chinese People)一书,赞同罗苏尔的说法,认为中国人种为土著。英国人罗素(B.Russell)和韦尔斯(H.G.Wells)也认为中国文化为自己发生,独立发展,没有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注:参阅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59—60页。)。中国人种土著说出现远较“西来说”出现为早,却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直到1930年代,才逐渐确立。
朱翊新坚持民族来源上的“土著说”。在其1930年代编著的《初中本国史》中认为,“汉族由来,旧时主‘西来说’。但经近年地下史料的发现、考古学者的研究,已证明汉族实我国北部土著,把‘西来说’推翻了。”不过,朱翊新同时也指出,“惟此种史料,现在发现的还不多,确定的断定,尚待未来”(注:朱翊新编著、陆光宇校订:《(朱氏)初中本国史》第1册,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4—6页。)。
罗香林在《高中本国史》中谈到汉族的起源的时候,认为:“此为最初于吾国境内组织统一的中华国家之民族。其语言文字文明教化,皆自成系统,一线相承,至今益盛。……汉族初居黄河流域,渐向长江粤江两流域发展,分布全国各省。”(注: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14、39—41、48页。)罗香林否定了“西来说”,坚持了我国民族的“土著说”。“吾华国族,虽内包汉、满、蒙、回、藏、苗、越等七族,然同属黄种,起源相同。吾国学者,自昔无人种学研究,故于本国人种来源,初无述论。惟西国《旧约》,早言亚洲为世界人种产地,近世西人且主张世界之第一人类为中国人。此问题虽尚待充分证明,然亚洲人类由来之古,中国人种之出自本洲,则可由此略见一斑矣。”对“中国民族西来说”,罗认为“不可靠”,他的看法是:“与其轻信中国民族来自西亚,毋宁先假定其为发生于吾国本部,而再搜寻证据,致力于人类考古之学,或从事地下发掘,以为正确谳定为较愈也。”(注: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14、39—41、48页。)这里,罗香林与前面反对“西来说”的学者的方式基本相同,即认为“西来说”存在着问题而不可信,相信中国民族出自本土。
1930年代的教科书中,中国人种土著说得到了肯定,这种肯定不仅仅体现在对西来说的否定上,从教科书的内容安排上也可体现,即在上古史的叙述上增加了“史前史”一节,从石器时代讲起,新增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前引罗香林的《高中本国史》就用了一章的内容来介绍“太古之文化与社会”,分为“人类进化之程序”、“中土之猿人时代”、“中土之旧石器时代”、“中土之新石器时代遗迹之发现”、“中土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社会”几个部分,从文物、考古、文献等方面来证明中国人种为土著居民。金兆梓在谈及汉族的由来时说,“前人本各异其说,而以西来说最为有力;但均出于牵强附会”。在谈到“中华民族之起源”时,金兆梓从“石器时代文化之发见”、“新石器时代遗物之发见”开始叙述,认为汉族出于中国本土(注: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11—15、15页。)。显然,其用意在说明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文明一脉相承。
从1930年代教科书对中国人种起源的态度来看,“西来说”已经动摇,而“土著说”的确立却显得有点牵强。“土著说”的依据是1920年代的中国考古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认为中国是世界人类之发源地,中国人远古就居住在中原地区。但是这时的考古研究还难以和中国人种就是土著居民建立直接的联系。因为这期的考古发现,不仅为中国人种土著说提供了“证据”,也为西来说提供“证据”。20年代初的中国彩陶文化的争论和中国文明西来说的重新提起即是基于考古发掘(注:参阅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59—60页。)。
相信土著说,与其说是出于学术追求,倒不如说出于民族的情感,是增强民族自信的需要。比如金兆梓,在对汉族土著说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就是“暂行断定”的:“在没有其他地下史料发见之前,可以暂行断定汉族在石器时代,已经是黄河流域的主人翁了”(注: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11—15、15页。)。而罗香林对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汉族土著说甚为痛心:“惜乎自十五万年前以上,至一百万年前猿人时代以下,其间凡数十万年,尚以发掘未周,材料未备,无以论述,为可憾耳”(注: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14、39—41、48页。)。这种情感,与1920年代缪凤林指斥信奉“西来说”的人“背祖忘宗”是相同的。这一时期学术环境的改变也是土著说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0年代后,中国民族意识逐步增强,民族主义运动逐步高涨。1929年南北统一后,国民政府明确地将“民族主义”列为民国的教育宗旨之一,以“延续民族的生命”;强调历史地理学科,要“阐明民族的真谛”(注:《教育宗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册,传记文学社1971年版。),从而“养成自重自信之国民,以期恢复民族精神”(注:《短期小学或短期小学班课程标准》(1932年),《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发行,第3824页。)。民族主义的高涨和通过历史教科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从1929年后的两起教科书案中可见一斑。1929年,顾颉刚等编著的《本国史》教科书因为怀疑“三皇五帝”而遭到查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认为:“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与国家不利”,“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注: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1935年,吕思勉因为《白话本国史》讲述“宋金和议”时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而牵连官司。反对者认为“有害民族性”。国民党要求学者们在研究中注意鼓舞民众的民族自信心,“殊不解际此国势凭凌,凡所以鼓励精忠报国之精神,激扬不屈不挠之意志,在学术界方当交相劝勉,一直努力。”(注: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历史上的荣光是国民民族情感的培育和民族自信心的恢复的重要源泉,通过追溯本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建构一个伟大的起源来重建民族的自信。放弃西来说而相信土著说,一方面是养成国民民族自信心的需要,也是国民民族自信心增强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建构民族认同的要求。
在中国民族溯源上,20世纪最初的30年间,经历了一个对“西来说”的肯定、否定到“土著说”的历程。对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肯定、怀疑与否定,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并非矛盾;相反,则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民族溯源是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进行的。对西来说的认同,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它是在危机中正在“形成”的中华民族寻求自信与认同的努力。同样,怀疑或否定西来说而相信土著说,也是重建民族认同的表现。要重建民族自信心,建构民族认同,必须回到本民族的历史中,发掘本民族历史的荣光。从最初的认宗西方,到后来的“相信”中国土著,近代中国民族认同建构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无奈与悲情。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中出现的民族溯源,其发生与变化正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曲折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