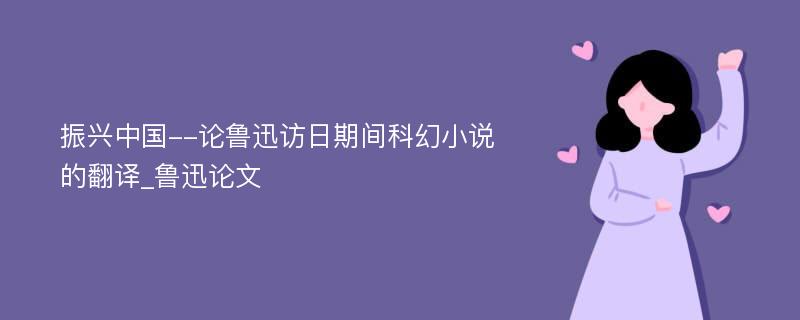
幻兴中华:论鲁迅留日时期之科幻小说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华论文,科幻小说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的文学生涯自翻译始。在他的早期译作中,《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和《造人术》均是科幻小说,这是值得注意的。学界多从鲁迅崇尚科学、希望实现“科学救国”的角度对此加以评述;此言大体不错,但失之过简,如果结合鲁迅的生活经历、文学道路、晚清“小说界革命”对“科学小说”的倡导以及科幻小说的文类特性来考察鲁迅在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翻译,当可全面、深入把握此项活动之于鲁迅及晚清文学史、文化史的意义。
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由于外语能力以及知识不足,留下了不少误译。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没有忠实原作的想法,不仅采用了意译的方式,还有很多随心所欲的增删。故翻译时“随阅随译,速度惊人”①,而往往与原作出入甚大。鲁迅晚年回忆起这样的翻译时,承认“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②,不无懊恼之意:“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③不过,鲁迅的翻译策略很快发生了变化。如《造人术》的译文,除了一处人名改动、另一处添加一句外,连改行、符号等也与日译本相差无几,是忠实于原文的中文翻译。④虽然《造人术》只是一篇千余字的微型小说,但至迟在1905年,已经可以在鲁迅的翻译实践中发现“直译”的取向。⑤
不过,也正是因为不受翻译底本拘牵,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等作品时行文流畅生动,激情奔放而又不失优美,使译作具有相当好的可读性,至今读来仍觉意兴盎然。如《月界旅行》第三回“巴比堪列炬游诸市观象台寄简论天文”述及众人欢呼情景:
加之天又凑趣,长空一碧,星斗灿然,当中悬着一轮明月,光辉闪闪,照着社长,格外分明。众人仰看这灿烂圆满的月华,愈觉精神百倍,……到了半夜,仍是十分热闹,扰扰攘攘,引动了街市人民,不论是学者,是巨商,是学生;下至车夫担夫,个个踊跃万分,赞叹这震烁古今的事业。凡是住在岸上的,则在埠头;住在船上的,则在船坞;都举杯欢饮,空罐如山。那欢笑声音,宛如四面楚歌,嚣嚣不歇。
笔者将本段译文与凡尔纳原著和井上勤日译本⑥中相应文字进行仔细比照后发现,日译本较凡尔纳原文增删颇多,且多了些即兴发挥,如“欢呼笑叫之声恰如楚歌,四面不绝”(声ハ恰モ楚歌ノ如ク四面ニ絶へス)、“实在是自古未有的境况”(实ニ古来未曾有ノ景况ナリキ)。虽然不能排除英译本影响的可能性,但“楚歌”这样的中国文化典故被用到译文中,自然是因为井上勤不拘译格。汉文调的日译本已经相当生动,而由鲁迅信笔译来,文采飞扬的四字词接二连三,而“云气四散”变成“加之天又凑趣,长空一碧,星斗灿然”,“空壶堆积”形象化为“空罐如山”,凡尔纳原本平实的描写越来越华丽,井上勤和鲁迅这两位“豪杰译者”真可谓“俱怀逸兴壮思飞”!鲁迅之“意译”,虽不准确,但却很能体现其个性和蓬勃朝气,“开始译笔,颇受严几道的影响,但后来却一变而清新雄健,在当时译书界已经独树一帜了”⑦。
另外,鲁迅对小说形式的改造,也值得注意。在鲁迅的译笔之下,《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态。两部译作的每一章前,都有鲁迅自撰的对仗回目,如“新实验勇士服气,大创造巨鉴窥天”(《月》十二回),“拼生命奋身入火口,择中道联步向地心”(《地》第四回)⑧。《月界旅行》每回末,都有鲁迅自撰的散场诗,如第五回回末:
正是:
啾啾蟪蛄,宁知春秋!惟大哲士,乃逍遥游。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地底旅行》虽然没有散场诗,但和《月界旅行》一样,多择紧要处煞笔,大有“话本”之风。如“天文上的疑问,都已解释;那器械却如何商量呢?下回再说。”(《月》第三回末)“不知何时,忽闻有弹窗以呼者曰:‘亚蓠士!亚蓠士君!’亚蓠士心中一跳,跃然而起。”(《地》第一回末)
文中偶有穿插诗文,这也是鲁迅自己的即兴发挥。如《月界旅行》第一回:
晋人陶渊明先生有诗道: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像是说这会社同社员的精神一样。
第五回:
此等人或生性拘迂,或心怀嫉妒,某诗说什么,“高峰突出诸山妒”⑨,这是在在皆是的。
至于翻译的语言,《月界旅行》“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⑩,《地底旅行》也是如此操作。《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11)。《造人术》则纯是古朴拗口之文言,但又有简洁、明快的特点。
受“小说界革命”启发而进行的翻译,意在引介新文类,但译作又体现出一派古典小说的艺术趣味,叙述语体也杂糅混乱,这种矛盾是晚清作家普遍面对的困境;具体地说,《月界旅行》等小说的翻译,受《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影响甚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造人术》尚直译,言古拙,这又反映了鲁迅翻译策略的调整。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北极探险记》托蒋智由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时,竟被编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快意增删,用语也随心所欲,而且并不觉得自己的译法有什么不妥,《月界旅行》出版后欣然寄给周作人一阅,甚至在《地底旅行》篇末开了一个颇为自得的玩笑(12),翻译《北极探险记》则继续翻新花样,“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多少有些顽皮。商务印书馆这位编辑的当头棒喝,显然给他不小的打击,也迫使他反省自己从前的“译法”。而翻译语体由“俗”转“文”的原因,或与鲁迅深层思想的变动有关。袁盛勇指出,鲁迅的复古倾向与其民族主义思想有密切关联,当鲁迅超越留学生的普遍水平而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文化民族主义的高度,“才在更高的意义上真正开始了独特的文化建构活动,他所由此而具有的‘复古倾向’也才真正显现了自身的积极作用”(13)。恰恰是在仙台,鲁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项义华认为,鲁迅在东京时,生活在留学生社群中,“可以在思想上做一个异类,但毕竟在现实中还是同类”,而他虽不乏爱国情怀,但对当时的激进革命势力还是有所保留的,是以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离开漩涡中心东京,来到偏僻的仙台。在仙台,鲁迅是孤立的中国人,变成了“现实中的异类”,民族意识强化,民族情感也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当时日俄战争正在中国东北激烈展开,鲁迅也非常关注。早在东京,日本人对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告中立”便大加嘲讽,鲁迅还曾因此与当地人发生过冲突;此刻仙台市民多次举行庆祝日军攻占中国东北城市的大会、游行,势必给鲁迅更为强烈的刺激。在这种情绪下,鲁迅得到《黑奴吁天录》后一口气读完,随即在写给朋友蒋抑巵的信中,感叹黑奴悲惨命运,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
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14)
而要光大“黄帝之灵”,重铸国魂,时人多认为应求诸华夏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所以鲁迅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表现出复古倾向——既要以小说“新民”,又要让这种文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说鲁迅返回东京后所撰写的几篇极为重要的文言论文是“文学复古”蔚为大观的表现,则译作《造人术》可称为“文学复古”之先声;而用如此古拙的言辞表现以科技创造生命这一极具现代色彩的幻想,在中国科幻小说史和世界科幻文坛上都是罕见的奇观。
基于以上对鲁迅科幻小说翻译的细读,我们可以上溯鲁迅早年的成长经历,进而概括出促使他在留日时期热情洋溢地译介科幻小说的几个主要因素。
第一,少年时代博览群书打下的根基。少年鲁迅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涉猎极广。他受过较为完整的传统教育,“几乎读过十三经”(15),但兴趣广泛,常常“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16)。这其中有不少可归于幻想文学之属。比如,《朝花夕拾》中提到的《山海经》,让鲁迅获益匪浅,“第一是这引开了他买书的门,第二是使他了解神话传说,扎下创作的根”,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他恣肆汪洋的想象力:“那些古怪的图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没有脑袋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形天’,这比龙头人身马蹄的‘强良’还要新奇,引起儿童多少奔放丰富的想象来呀。”他读过的书中还有《西游记》、《镜花缘》、《封神榜》、《聊斋志异》等幻想文学,至于《绿野仙踪》、《池北偶谈》、《酉阳杂俎》、《阅微草堂笔记》等广涉神怪、灵异的作品,更是不一而足。它们都引导着少年鲁迅神游天外。科幻小说为幻想文学一脉,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引《山海经》、《镜花缘》为例,大概其潜意识中觉得这些作品中的奇山异水、神秘鸟兽和《月界旅行》中“光怪陆离”的幻想不无契合之处。此外,据周作人回忆,有段时间鲁迅看了《十洲》、《洞冥》中的神话,奇想大发,于是“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的讲,颇极细微”。翻译本就是二度创作,而译《月界旅行》时鲁迅的日文水平尚不是很高,又采用意译,兴致勃勃地在底本上多加发挥,就更有“创作”的意味了。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认为是他早年“口头幻想文学创作”的延续吧。
第二,学习自然科学的影响。鲁迅自陈:“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17)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早年喜读《花镜》并动手栽培植物,不过真正受到较为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是在南京求学的时候。他“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18),算是个“工科学生”。在矿路学堂里,鲁迅习矿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测算学、绘图学等多门现代科学,兼阅《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医学著作,从而具备了较好的自然科学素养。留日初期,在弘文书院的学习也增加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积累。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仙台习医”。
科幻小说对读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除了对生活的理解,还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较好地欣赏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常常以某种科学技术的幻想为基本的情节推动力,而在叙述中又渗透着科学知识乃至科学的理念和向度,其审美价值和思想内蕴与这些特点有着密切关系。鲁迅钟爱科幻小说,亦与自身科学素养有密切关系。他学矿出身,对地质学和矿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有下矿洞的经历。《地底旅行》恰是一部以地质学和矿物学为基本知识背景的科幻小说,其主人公列曼和亚蓠士都是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自然让鲁迅倍感亲切,而大地深处的景象,也能唤起他对矿洞的实感。此外,熔炼学与测算学之于《月界旅行》,地质学、地理学之于《北极探险记》,医学之于《造人术》,都有显而易见的联系。
在理念上影响了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的,则是进化论。严复编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对晚清思想文化界有重大影响。鲁迅早期思想受《天演论》影响很大,(19)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认为这部小说“写此希望之进化”,并高呼“冥冥黄族,可以兴矣”,体现了他基于进化论的观念对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理解和发挥。《地底旅行》在第九回插入底本所无的“胜天说”,显然也是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
第三,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如果说留日学界的政治氛围促使鲁迅爱国热情高涨,那么他在文学方面的作为——翻译《哀尘》、《斯巴达之魂》和几篇科幻小说,则更多地体现了“小说界革命”的影响。鲁迅回忆早年读过的文学作品时,说: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到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20)
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中也回忆道,当时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三个人分别是梁启超、凡尔纳和林纾。兄弟二人举出的这三位作家,正是晚清“小说界革命”中的关键人物,也恰从三个方面影响了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可以说,梁启超所宣扬的以小说“改良群治”“新民救亡”的理念,在这个时期直接规定了鲁迅对小说的取向。凡尔纳是晚清时期作品被译介第三多的外国作家,(21)其《海底旅行》和《十五小豪杰》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起到了示范的作用,让鲁迅大开眼界,领略了科幻小说之魅力。而鲁迅早年读过林纾最负盛名的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就成为林纾的忠实读者,林译随出随买。相应地,“桐城美文”的笔法也在纯用文言的《造人术》中依稀可见;至于《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在删节原作之后复而“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22)的译笔,和字里行间的勃勃兴致,则颇有林译的味道。
在晚清文学文化语境中评析鲁迅留日时期的科幻小说翻译,可有如下之结论:
首先,这是化身为“小说救国”的“科学救国”。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痛感外人“船坚炮利”,进而认识到外人不仅有此利器,更重要的是“制器精也”,而“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23),根本上在于科学的领先。甲午惨败震惊中国上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大潮中的强音。如严复所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救中国之亡须学习西方,“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也。”(24)作为“科学救国”的积极支持者,梁启超联接“科学救国”与“小说界革命”,鼓吹“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而成的“科学小说”,自是理所当然。受其影响、又具有相当科学素养的鲁迅作《说钼》、《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篇章,译科幻小说,这些行为都带有深深的时代印记。
其次,在翻译这几篇科幻小说的过程中,思想上的变化对鲁迅的翻译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迟至1909年周氏兄弟才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明确表示“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并在译作中全面贯彻忠实原文并“词致朴讷”的翻译原则,但这种原则早在五年前鲁迅翻译的《造人术》中就得到了体现。其深层动因,如前所述,是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一般意义上的反清反帝向文化民族主义的转变。由于鲁迅自觉地以政治理念指导自己的文学文化活动,所以翻译策略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更体现了一位思想者的知行合一。
第三,作为“科学者”和“文学者”的鲁迅,在翻译科幻小说这样的活动中,都得到了体现。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凡尔纳是通常意义上的“硬科幻”作家,其学识的丰富和创作态度的严谨使他的作品不同于后世某些科幻小说的“皮以科学,实以言情”,而真正做到了“经以科学,纬以人情”。因此,对于鲁迅而言,自然科学教育形成的知识背景和在对东西方文明的思考中逐渐形成的科学理念、科学精神,在对译本的选择和改造中也得以体现。即便在弃医从文之后,他对科学的思考也没有终止,《科学史教篇》(1908)中对科学的批判理解和接受便是明证。另一方面,弘扬科学的出发点部分地落实到翻译科幻小说上,又体现了一个文学者的特征。归根到底,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门类,笼统地称为“自然科学和进化论的介绍和论文”和“文学批评或文明批评”之间的“过渡形态”(25)并不合适。鲁迅自己说,在受到“幻灯片事件”刺激之后,思想发生转变,认为“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6)。但是,笃信文艺能够“新民”,提倡文艺运动,难道不是从热情洋溢地译介科幻小说就开始了吗?多年后鲁迅仍然说作小说“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27),可谓“吾道一以贯之”;溯洄从之,这种思想最初的表现就在于科幻小说的翻译。以此为起点,鲁迅的“科学者”和“文学者”的品格都在延伸,并整合在政治诉求之中,完成于他对异质的西方文化从整体和本质上——而不是割裂成“科学”、“文学”、“政治”等诸多板块——的把握(28)。
最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还可得出两个有意思的命题。碍于篇幅,本文不能进行深入探讨,但笔者不揣浅陋,试进行初步的勾勒:
科幻小说在东亚的接受。晚清中国能掀起“新小说”的高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在大量的翻译小说中,若以译者所据底本语种统计,译自日文的小说应是第一位。(29)就科幻小说这一文类而言,更是直接受到日本科幻小说热潮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了掀起科学技术启蒙的高潮,推动自然科学即“实学”的发展,大量翻译凡尔纳科幻小说。基本可以判定,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出现的“科学小说”这个名词,源自日语。尔后,梁启超、鲁迅、徐念慈、包天笑等多位科幻译者均依据日文科幻小说进行翻译,凡尔纳和以创作科幻、冒险题材著称的日本作家押川春浪也双双跻身晚清时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最多的五大外国小说家之列。(30)伊藤虎丸认为,鲁迅翻译科幻小说,是鲁迅与明治三十年代文学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同时代性”的表现之一,而与其说鲁迅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如说是鲁迅在“西欧冲击”的某一阶段共同的时代思潮或教养当中自身所面临的选取什么和怎么样去选取的问题;那么,也可以说,科幻小说这一结合了科学与人文、富于现代性的文类在东亚两个文化相近、渊源颇深的国家相继兴起,两国文学文化界对这一新兴文类的接受既有相似(如以科学启蒙为基本目的;科幻多蕴含政治主题;原创在译本的持续影响下出现等),相似中又有差异(如科幻译作出现二十年后押川春浪才创作了第一部日本原创科幻小说,而在中国,仅仅相隔四年;明治时代的科幻热潮之后,日本科幻小说或与政治小说结合,或变身为面向少男少女的科学冒险小说延续下去,并经梦野久作、海野十三等人的努力而不断壮大,中国科幻小说则在晚清之后陷入长时间的沉寂),实质上反映了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科学)冲击之下所面临的选取什么和怎么样去选取的问题,以及两个国家不同的回答。其中蕴含的丰厚文化意蕴,值得深入探讨。
《月界旅行》及其它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翻译问题。在19世纪,凡尔纳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一经问世很快便被译成英文,继而被翻译成更多的文字,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出版,旋即被译介到英美,井上勤从英文转译日文,(31)复有鲁迅之中译。《月界旅行》由法国到中国,也几乎“环游地球”,不过耗时三十八年。这一跨越四种语言文化的幻想之旅,无疑是“艰险重重”的:英、日、汉的译者统统是“豪杰译”的好手,凡尔纳的作品抵达中文时已经面目全非。米勒(Walter James Miller)在《详注版月世界旅行》(1978)的序言《儒勒·凡尔纳的多面世界》中对19世纪的英译本批评道:“(译者)大量删削原文的结果,使得凡尔纳的科学、性格造型、幽默,及其欲传达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声音都遭消解。”(32)井上勤和鲁迅也不乏自作主张的发挥。此外,不同译者译介凡尔纳小说的出发点也不一致,更可追溯到不同的时代背景乃至民族性格。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奇思妙想和寄寓其中的深刻思考无疑拓展了人类的胸怀,而不断“接力”的翻译则组成了不同文化碰撞交汇的历史画卷。这幅画卷,仍然等待着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来打开!(33)
注释:
①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杨良志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②《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③同上,第99页。
④[日]神田一三著,许昌福译:《鲁迅〈造人术〉的原作》,《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
⑤据熊融、戈宝权等研究者查证,《哀尘》译文和雨果的法文原文甚为吻合,应为直译(《关于鲁迅译述〈哀尘〉、〈造人术〉的考说》,《文学评论》(1963.3);《关于鲁迅最早的两篇译文——〈哀尘〉、〈造人术〉》,《文学评论》(1963.4);两文收入陈梦熊《〈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鲁迅佚文佚事考释》,1-16,17-19);而据工藤贵正论述,鲁迅译文中的“译者曰”是对日译者森田思轩所撰序文的改造。
⑥英译本尚待确认。
⑦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杨良志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⑧据山田敬三称,《月界旅行》日译本的回目与原作完全一致,而《地底旅行》日译本已经模仿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回目分两行对句,回末有“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可见,文化背景相近的东方译者在改造西方文本时,在翻译策略上显示出某种同构型。
⑨语出康有为《出都留别诸公》(之一),全诗为:“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庭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据马自毅选注《康有为诗文选》。
⑩《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1)《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12)第十二回:“德意志人,也从此都把两颗眼球,移上额角。说什么惟我德人,是环游地底的始祖!荣光赫赫,全球皆知!把索士译著的微劳,磁针变向的奇事,都瞒下不说。”按,鲁迅译此书时署笔名“之江索士”,故此处“索士”乃其自况也。卜立德用戏谑的口吻评论道:“索士是鲁迅译此书时用的笔名,也就是说他在抱怨1863年德国人胆敢向1903年才动笔翻译的鲁迅掠美!一般人只知道1920年代在巴黎有超现实主义派,不知道东方已有个鲁迅抢先。”([英]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13)木山英雄也认为鲁迅和周作人“文学复古”的深层动因,在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周氏兄弟共通的反功利主义,是遵循庄子式的‘无用之用’的逻辑,希图依靠文学的力量使同胞纯粹无垢的灵魂觉醒,从而使衰弱的古老文明保有再生的希望: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反功利主义是为远大的功利服务的。”(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14)《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15)《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16)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杨良志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7)《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18)《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19)《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79页。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20)《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2页。
(2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2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85页。
(23)李善兰:《〈重学〉自序》,陈亚兰译注:《李善兰华蘅芳詹天佑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2页。
(24)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46页。
(25)[日]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26)《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27)《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28)[日]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页。
(29)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30)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31)[日]山田敬三:《鲁迅与儒勒·凡尔纳之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
(32)同上。
(33)目前各国研究者从跨语言文化角度对《月界旅行》以及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翻译已有一些研究,如Arthur B.Evans,Jules Verne's English Translations,Science Fiction Study 95(2005.3),80-104;卜立德的《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凡尔纳、科幻小说及其它》,以及上面引用的几篇日本学者的论文。但这些研究多局限在两种语言之间,卜立德虽然勉强做到了参照四种语言的文本,但其探讨中存在不少问题:所看的日译本仅为一小部分;对日译和汉译辨析能力较弱;从文化背景差异角度进行的分析还不够深入;等等。其中有一些想当然的论断,不够严谨,如“英美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法国作者大同小异,情趣约摸一致,因而艺术上的鉴赏大概也差不多”(《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29),又如卜立德只看了《月界旅行》一小段日译,《地底旅行》和《造人术》日译未曾得见,在好几处颇为武断地认为某些改动是鲁迅所为。真正能够深入把握四种语言的文本,跨越多种文化进行透彻分析的研究,尚付诸阙如——无疑,这样的命题是对研究者学养的极大挑战。
标签:鲁迅论文; 科幻小说论文; 鲁迅研究月刊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 读书论文; 凡尔纳论文; 天演论论文; 旅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