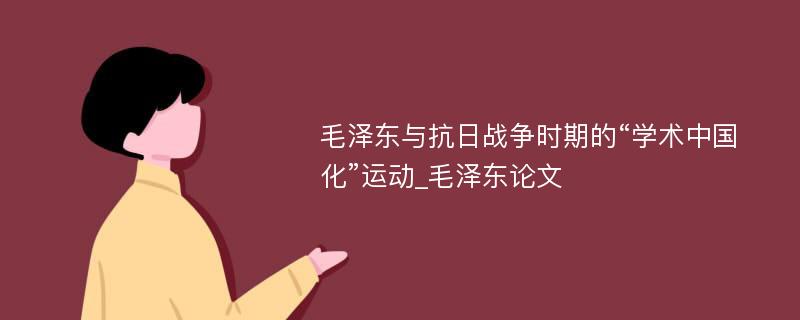
毛泽东与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学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5)03-0272-06 DOI:10.14182/j.cnki.j.anu.2015.03.002 “学术中国化”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始于重庆,影响及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沦陷区,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此时期虽未明确使用过“学术中国化”概念,但他以其科学的思想理论和学术实践,影响着“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方向。 1939年2月10日,重庆战时文化社出版的《战时文化》月刊第2期上发表了张申府的《论中国化》一文。4月1日,由重庆生活书店发行的《读书月报》第3期上开辟“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发表了潘菽的《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柳湜的《论中国化》、逖的《谈“中国化”》三篇文章。同月,《理论与现实》季刊在重庆创刊,刊物宗旨为“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1],创刊号上发表了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侯外庐的《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两篇文章。这样,以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以相关理论刊物为阵地,以系列理论文章为标志,“学术中国化”运动于1939年春在重庆拉开了序幕。 “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发动,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对外来文化的不能消溶吸收。近代以降,在西洋文化被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改变了人们思想学术的同时,出现了如下问题:“机械地把别国现成的形式和方法由一种条件搬到别一种条件里去,由一个国家搬到别一个国家里去”“把国际的学术、思想、理论当作千篇一律的教条”[2],结果导致对外来文化的囫囵吞枣、食而不化。这种状况发展到抗战时期更趋严重。二是对本国文化遗产不能批判继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文化珍品,它们的光辉在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中并没有得到绽放,相反却时常湮没在所谓“保存国粹”的陈词滥调之中,致使封建糟粕不时沉渣泛起,急需“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3]。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最前进的科学的结论,但他们对于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的许多所珍贵的传统,很少研究”[4]。三是抗战建国的现实需要。“伟大的抗战建国时代,正是中国学术开足马力的前进时代。学术研究缓慢地落后于抗战军事,这是一个大遗憾。”[5]为此,就“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具体地说,即要使它适应于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的历史要求”[1]。 导致“学术中国化”运动发生的更直接原因,源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6]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而且围绕该命题作了一系列理论阐述,为“学术中国化”运动提供了思想先导。《论新阶段》首先刊登在同年11月2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第57期上。12月7日至10日,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四天连载。同月,《论新阶段》单行本分别由延安解放社和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发行。12月30日,柳湜撰文《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批判离开中国特点谈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要“加深一步的学习理论,要求新的学术运动,要求文化工作都分工合作,要求多吸收,多消化”[7]。3个月后,柳湜的《论中国化》一文援引《论新阶段》中的阐述,批评盲目西化论者、奴化论者,推崇“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认为“这里是具有反‘洋八股’,反‘空洞抽象’以及各式的教条主义的重大意义的”[8]。 张申府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更为推崇。他在《论中国化》一文中引用了《论新阶段》中的阐述,并在“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关键性词句下面加上着重号,然后指出:“我们认为这一段话的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由这一段话,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3]作者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欢喜赞叹”毛泽东这段话的个中原委,强调“中国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毫无疑问,张申府对“中国化”的思考,导源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启迪。茅盾后来也说:“‘中国化’问题,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先生。”[9] “学术中国化”运动由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所引发,不仅运动的发起者持此观点,而且运动的反对者和旁观者亦如此认为。如,三民主义理论“健将”叶青就说:“从今年四月起,有了‘中国化’的呼声。这当然在毛泽东的同志所编的刊物上。就我所见到的说来,共有三个刊物六篇文章一致地解说毛泽东那一段话……现在的‘中国化’呼声还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这便是学术中国化之所由来。要明白学术中国化的意义,必须从这个由来说起。”[10]徐获权指出:“自毛泽东氏《论新阶段》一书出版以后,从今年四月起,开始有了‘中国化’的呼声。在《读书月报》、《战时文化》及《理论与现实》三种刊物上,先后有张申府、潘菽、柳湜、潘梓年诸人,为文论著。他们想使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现阶段的任务而造成一个划时代的文化运动,颇引起各方面之注意。”[11]后来,桂馨、伯劳在谈到“学术中国化”时也认为:“但考这一名词的来源,它的生产地是在陕西的延安”“所谓‘学术中国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2]这些阐述表明,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到“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正式发动,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上的前后继起性,而且存在着因果上的内在关联性。 “学术中国化”运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构成了直接动因,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重大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主动呼应。 “学术中国化”运动在重庆发端后,上海、成都、桂林、延安、曲江、汉口、长沙等地的报刊上,相继发表和刊登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开展论争。这些论争从运动发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歇过:有的在重庆一隅激烈展开,有的在国统区与抗日根据地、沦陷区之间唇枪舌剑。综合这些论争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数是由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而引发,或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而展开。 还在“学术中国化”运动发生后不久,独立出版社《时代精神》月刊创刊号开辟“中国学术与学术中国化”专栏,刊发系列文章批评“学术中国化”思想,攻讦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毛起鵕一方面指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来,到底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指责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动机令人“感觉得失望”。毛起鵕将其理由歪曲为两点:“第一个理由在中国的共产党人只有认识中国历史遗产的兴趣,而无继承中国历史遗产的意志。”“第二个理由在中国的共产党人有厌恶教条主义的情绪,而无摆脱教条主义的能力。”[3]“第一个在中国化问题上散布有毒的歪曲思想”[4]的叶青,更是极力贬损毛泽东的这一命题,他说:“毛泽东虽然倡导中国化,却不懂得中国化应作何解。”“毛泽东的中国化始终只有两个意思:具体地说,即依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生动地、通俗地,用中国写作方法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中国化。”[10]那么,叶青所标榜的“中国化”内涵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化是一般的或外国的学术思想变为特殊的中国的学术思想的意思。它必须变其形式,有如一个新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样才叫做化,才叫做中国化。所以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之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也都不是中国化了。”[10] 叶青等人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歪曲,其主要目的是以所谓“把握中国特殊论”和“国情论”为由,攻击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继而认为,“中国是不需要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了,因此它也就不需要共产党。”[15]既如此,当然也就不需要“学术中国化”了。针对这些谬论,杨松批驳道:“中国共产主义之传播和中国共产党之产生,不是像叶青之流所说的‘由于外烁’,而是由于共产主义之在中国有适当的土壤。”[16]艾思奇也指出:“叶青所谓的中国化,在实际上是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反对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是要想从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手中,夺去了最锐利的科学思想的武器。”[14]“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决不是如一般的表面观察,说这是纯粹外来的。”[17] 艾思奇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核心内容,又挖掘了该命题的丰富内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毛泽东自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后,再次运用该命题的场合并不多。①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18]的新提法。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沿用,同时作了补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9]707此后,这一提法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标准话语。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此后较少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不但得以保持,而且得以强化和展开。 除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有关论争外,“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其他如历史文化遗产问题的论争、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的论争、全盘西化问题的论争等,乍一看似乎毛泽东并没有与这场运动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较量,但是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思考,对于正确理解“学术中国化”以及大力推动“学术中国化”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譬如,如何对待西洋文化?这是“学术中国化”运动中一直争执不休的问题。按照“学术中国化”运动发起人的解释,所谓“学术中国化”,“就是把目前世界上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用来研究中华民族自己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具体问题,使我们得到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切问题。就是说,要使世界上已经有了的科学,不是始终只能由我们借来陈设一下的东西,而要把它成为自己能用、自己所有的东西;把世界已经有了的科学,化为中国所有的科学。”[20]这就是说,对于西洋文化,我们既不能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应该谨慎地拿来,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要“精通现在已经有了的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20]。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9]706毛泽东又指出: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我们都应当采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方法,“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9]707他还特别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19]707毛泽东对待西洋文化的立场,连叶青也不得不承认“非常之对”[15]。这一辩证认识及其思想观点,是对“全盘西化”论的有力回应,对“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导向作用。 此外,对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毛泽东也开出了药方:“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他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9]708毛泽东的这些阐述,对于回击“国粹论”“中体西用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等论调,推动“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同样起了积极作用。 分析和阐释“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原因,剖析和回应“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各种论争,是“学术中国化”运动的题中应有内容。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要让“学术中国化”“成为各学术部门研究的总方针、学习和写作的最实践的态度”[8]。这就是说,在学术领域坚持和贯彻“中国化”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之进行深入检讨,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达到中国各门学术的马列主义科学化”[16],同样是“学术中国化”运动的重要使命。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理论著述和学术活动来看,虽然他未明确使用过“学术中国化”概念,但他以实际行动支持、推动着“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还在“学术中国化”运动发起之初,潘梓年就指出:“我们的学术运动,差不多因抗战而停滞了。除了从遥远的一角,因其迄未停止学术的劳作,最近更见奋勉,常常把它浓郁的春风吹拂到我们的襟怀里来以外,我们是‘久矣不闻管弦之声’了!”[20]这里提到的“遥远的一角”,指的就是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当全国的学术运动因全面抗战的爆发造成很大破坏的时候,延安的学术运动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倔强地生长着。换言之,当“学术中国化”运动在重庆正式发动之时,延安的“学术中国化”工作早已在此之前开展了起来,且对全国“学术中国化”运动起着积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是延安“学术中国化”运动的践行者、推动者、引领者。早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之前,毛泽东就在延安着力推进哲学中国化工作。1937年春夏,他在抗大作辩证唯物论讲座,讲授提纲后来被整理成《实践论》《矛盾论》。它们被和培元誉为“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和培元指出:毛泽东“对辩证法原则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的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21]。所谓“新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区别于以往的一切旧哲学。在推动新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延安新哲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新哲学会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于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目前做的不很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22]。1940年6月21日,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学术年会,毛泽东等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勉励大家加紧理论研究,克服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在毛泽东等人的关心和指导下,新哲学会一方面组织力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要求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国哲学等问题,其发展态势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在边区,新哲学差不多已经成为每一个工作人员所必须学习的理论武器,逐渐更普遍地要深入民间而成为一般民众的共同的世界观。”[23] 除了亲自参加新哲学会等组织推动“学术中国化”研究外,毛泽东还指导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观察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清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唯心论和封建糟粕,以推动“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1939年1月,何干之将拟定的《中国民族文化史》写作计划和研究大纲函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复信,表示支持。何干之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即学术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与现实相结合。[24]143同年春,陈伯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墨子、孔子的哲学思想进行解读,撰写了《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两文,并送毛泽东处请教,毛泽东看得很仔细,且先后写了三封长信,对孔子、墨子的哲学思想作了集中论析,成为他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总结的代表性文献。[24]156-165同年11月,毛泽东看了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送审稿后,对其中把整个农村社会说成“旧的”“老中国”的提法提出批评,指出:虽然农民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但是他们“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25]。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中国革命实际情形,对农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此文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1940年9月,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讲演。毛泽东曾到会听讲两次,后因病没有出席。他对范文澜的讲演给予很高的评价:“用马列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24]296范文澜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对讲演提纲作了整理,也发表在《中国文化》上。此外,范文澜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著述《中国通史简编》,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当然,毛泽东对“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最主要贡献,还是集中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上。继《新阶段》之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特征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考察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领导力量等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著作因此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同时成为“学术中国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收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后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20多年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分析和解决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典范,被艾思奇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14]。胡绳谈到“学术中国化”运动期间中国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时也强调:《新民主主义论》“虽不是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在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时,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说是提供了重大的贡献。”[26]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了集中的阐述,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9]698“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1]698“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708这些阐述,为“学术中国化”运动昭示了前进的方向。“假使说民国二十八年中国文化界的基本口号是‘学术中国化’,那么去年(二十九年)的基本口号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23]“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学术中国化”这两个基本口号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陈垦认为它们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内容,而‘学术中国化’则是其表现形式。”原因有三:“(一)学术中国化不能不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表达革命文化的内容”;“(二)学术中国化不能不是以中国进步学术之姿态充实世界进步文化之内容”;“(三)学术中国化不能不是文化反拨作用最有力的武器”。[27]也就是说,“学术中国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间本质上没有矛盾,而是具有内在一致性。“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是对“学术中国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学术中国化”运动终究要融入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中。正如无邪所指出的:因为“学术要‘中国’化,这个中国指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此时此地的现实的中国,而这样的中国,就正是为了要争取整个新民主主义(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同样也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着的中国。这样,学术中国化就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二者构成了内在的必然联系。后者展开了,补充了,同时更深刻了前者。”[23] ①民主革命时期至少有三次:(1)1939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2)1941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彭真汇报晋察冀工作,毛泽东在此过程中插话道:晋察冀分局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见《彭真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3)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标签:毛泽东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