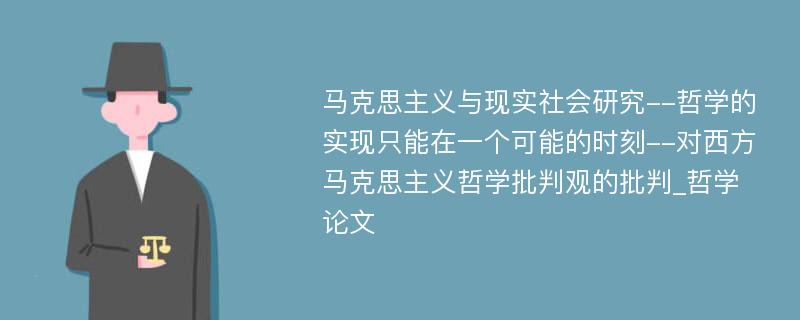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研究”笔谈——哲学的实现只在可能的瞬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观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只在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6-0001-17
栏目主持 吕世荣
一、哲学究竟能以何种方式以及是否可能把握外部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众所 周知,康德早就把“迄今为止我们仍无法逻辑地证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这件事, 称为“哲学和一般人类理性的耻辱”。而马克思则说,哲学对现实世界的纯思想式把握 ,肯定不同于艺术、宗教与实践等方式对世界的把握;而哲学的最大耻辱莫过于它“只 是解释了世界”。所以他的最高理想是“哲学的世界化”或曰“世界的哲学化”。
但值得玩味的是,20世纪以降的现代哲学不再以自己不能“现实化”为“耻”,反以 此为“荣”!如海德格尔便对康德的观点做了反其道而行之的解释:“哲学的耻辱”不 在于至今尚未完成“我之外的物的定在”这一证明,而在于人们还是再三再四地期待着 和尝试着这样的证明。[1]到1960年末,晚年的海德格尔在《四个谈论班》中则含蓄地 指责马克思的“让哲学现实实践化”的《提纲》,是技术主义与人类中心论的。作为海 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更明确地批评说,在欧洲哲学史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开创了让“哲学非政治化”的政治哲学传统;而马克思与黑格尔则反其道而行之,让哲 学政治化,认为政治实践是实现哲学的惟一途径。这就颠倒了柏拉图所确立的思想高于 行动、沉思高于劳作、哲学高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而“一旦有一个哲学家,为了使 哲学在政治中得以‘实现’,离开了哲学,便意味着政治哲学的末日降临”。[2](P397 -398)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现代西方传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居 然不约而同地照着海德格尔的样子,共同反对马克思的《提纲》所坚持的解释世界服从 于改造世界的立场。如阿道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开头便说,哲学的幸运就在于它还 没有机会实践自己。为了避免使自己成为一种实证科学或者技术工具,哲学宁愿选择了 不“与时俱进”的、无限推迟自己实践时机的失败主义策略。他这样满腹牢骚地说,既 然“武器的批判”已经禁止了“批判的武器”,既然“贫困的理论”已经被群众所掌握 而变成了可怕的“物质力量”,哲学便不再打算成为“武器的批判”,而转向无情地批 判自身。[3]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与传统,大体上说都是理论上的“强者”与实践上的“弱 者”,且多是“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理智上的悲观主义者”。他们在理论上离经叛道 ,提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并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他们“谈方 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4]在他们看来 ,哲学不应当也不可能以实践的方式使自己彻底现实化。哲学应当是“介于科学与乌托 邦之间的东西”,是“介于不可能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可能性”,它的实践表现是个人生 存体验或体验审美性的瞬间状态。马克思哲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是介于在场与不在场、 可能与现实、乌托邦与科学之间的状态。哲学作为乌托邦,它不可能在人类历史过程中 “在场”或变成现实。哲学的“本真世界”,是个人瞬间体验想象中所把握到的那个诗 情画意般的生命总体性,或总体人的辩证法,而不是客观的历史辩证法。
进而言之,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实践方式 的把握,其结果不是一种现实的科学,而是一种特殊的乌托邦。因为任何科学都会导致 对现实的非批判的肯定。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力图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 学和现实,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趋势却是要摒弃那些“科学”的部分,重建乌 托邦的尊严。“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即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能够从科学,转向 乌托邦,并非是从乌托邦到科学”。[5](P595)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在于它是一种 激进的变革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它只是取代了那 种空洞地设想美好未来而无法或不愿意从根本上变革现实的古典的空想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看是反对让哲学直接现实化(肯定化)的否定辩证 法,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一种观点就认为,哲学可以现实化实践化,但它不是一个 宏观的历史过程,而是多种可能性的、个体化体验的瞬间,种种“永恒的”、“可能” 的时刻。其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本雅明与列斐伏尔。
三、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及其另类,本雅明就认为哲学的实现乃是某种特殊 的历史想象瞬间。他反对他的战友阿道诺的哲学批判所采取的“闭眼不看世界”的“冬 眠政策”:问题不是无限期地推迟哲学实现的时间,而是争取在每一个瞬间向本原时间 的回归,在每一个瞬间从现代性的时间和历史中挣脱出来,实现对现代性世俗性的一种 当头棒喝。在他看来,现代性世界是一个最终由商品生产、流通和交换所造成的幻想与 假象的世界。他试图通过辩证想象突破这一物化世界,旨在将梦中的集体从梦中唤醒。 他引用马克思《德法年鉴》中的话说:哲学的实践,即“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 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6](P418)“每一 秒钟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每一秒钟都可以通向革命。这 样他就把马克思主义与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结合起来。而他所说的“革命”,就是发生 在历史的旷野中的向着过去的辩证跳跃,即跳向历史中那个始终没有实现的真正解放的 理想,那个“永恒的在场”,即人类从一开始就为之奋斗的真正解放的理想。“革命” 的哲学版本,就是拆解历史上被物化和神化的虚假连贯性与史诗性,把“本原”作为一 个单子从这种空洞的连续体中爆破出来。革命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历史的急刹车。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所向往的既不是“同质的”,也不是“连续的”对历史的阐述, 而是为了受压迫的过去而斗争的革命机会,为了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 程中爆破出来,把一个特定的人的生平事迹从一个时代爆破出来。这就是马克思的“革 命”瞬间,或者说是典型的弥赛亚式的时间。这也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本原”或“本真 世界”:不是“起源”——即某种东西在某一特定时刻产生,而是“Jetztzeit”(当下 ),它的意思不等同于“Gegenwart”(现在),而意味着“永恒的现在”。这个短暂的瞬 间包含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的压缩。真可谓“一天等于一万 年”,或曰“万古长空尽在一朝风月”!这种瞬间只能是对历史与生活的一种辩证美学 想象。
四、与本雅明相类似,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学派的创始人,列斐伏尔 也不一般地绝对地反对哲学的现实化介入。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实现哲学与日常生活的 融合。哲学的现实化,即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就是“让日常生活 成为艺术”的那个壮丽的瞬间。他一方面非常赞同阿道诺《否定辩证法》所坚持的反实 践主义哲学,含蓄地批判了青年马克思简单地将哲学变为改造世界的政治工具的技术主 义实践观,并试图对马克思的哲学政治化的革命思想“偏向”进行纠正。他认为,哲学 的现实化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必须用改造世界来取代解释世界,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应该 得到同样的尊重。
另一方面,在列斐伏尔看来,我们今天实际上处在一个“后哲学”的文化时代,同时 应当避开两个思想陷阱:或者认为古典哲学已经死亡,或者认为今天的哲学仍然是古典 哲学的继续。哲学既没有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而寿终正寝或被实证科学技术语言所 取代,也没有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设想而以政治革命实践的方式而自我现实化,哲学仍然 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出路,不是青年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哲学”或使哲学“自我现 实化”,而是哲学要回归到日常生活这个创造性的源头,实现哲学与日常生活的融合, 让哲学在促使日常生活的转变过程中,即总体性文化革命的实践中,成为文化革命的一 部分。哲学要“通过全新的方式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日常生活的分析和转变”,哲学的 “真正的答案是日常生活,去重新发现日常生活”。哲学不需要终结,而需要在回归日 常生活的过程中即在现代性文化批判与重建的过程中获得新生。[7](P202)所谓让哲学 重新发现日常生活,关键就是让日常生活艺术化,恢复日常生活的美学艺术的维度,就 是焕发日常生活的诗性与生命创造力,让日常生活从传统的理性主义、生产主义思维方 式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克服日常生活和节日间的冲突,使节日重见天日并受到推崇,让 古代节日与现代都市生活相融合。这种新型的日常生活将一扫工业化社会令人沉郁窒息 的技术官僚制度云霭,将使现代人类走向一片阳光明媚、玲珑剔透的新天地。在这种都 市化的日常生活中,人类将重新找回农业社会或古代社会节日的喜庆那种快乐感觉与欢 乐场面,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
列斐伏尔满腔热情地预言,社会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解除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技术化组 织化控制,让人类沉睡于其中的潜能重见天日。这种理想化的日常生活的典型是节日, 它是一种被现代性所遮蔽,但从来也没有完全被夺去光彩的场面。在前现代社会,以狄 奥尼修斯式的狂喜为象征的节日与日常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与共同体的存在及自然界的 节奏丝丝相扣、心心相印。它既包括每个人的所有的感觉、身体与精神品质的自发的与 无拘无束的全心倾注,又包括所有公社成员不分等级贵贱的平等参与。而在资本主义社 会,分层与制度化达到了极点,节日成了例行公事而与日常生存相脱离,并屈从于商品 化与情感的升华。而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形而上学并没有给人带来精神家园,它的 深层焦虑和对自然的深刻畏惧感,驱散了前工业社会节日中那种人与自然的欢乐融融、 天人合一的奇妙境界。节日的复活标志着娱乐与日常生活冲突的和解,标志着人类异化 的超越和民众庆典精神的复苏。“未来的革命将结束日常性……这种革命将不局限于经 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其独特的目标即消灭日常生活……”[7](P36-37)
五、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把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化实践理解为一种文化 革命。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决定论与新的政治浪漫主义。其过错之一在于,它们过于极 端地把文化革命与工业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脱离工业化这种强大物质基础 的都市文化革命设计,只能是一种可爱而不可行的空中楼阁。其过错之二在于,它们抛 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变革之核心思想, 而试图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使其具有主导性,从而寻找医治现代性痼疾的良方,这是“舍 本求末”、“以星为月”的政治弱智的表现。他们有意地避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 内在基本矛盾及其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层理论逻辑,把马克思的宏观历史解放预期降 解成为一种微型的、瞬间性在场的都市生活艺术想象。这充其量只是对近代启蒙主义的 那种“面对面”的、契约式的、誓愿式的“广场政治”理论模型的另外一种聚象化的重 塑。
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观的有益启示是,它让我们必须从另外角度反思哲学作 为乌托邦而介入现实批判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于这样一种哲学实践观:它 要让现实之“可能”或“应该”通过实践都成为“现实”。它用一种逻辑上的统一性的 暴力,去消灭、“同化”现实的异质性多样性的可能性。它要让一切“可能”都成为“ 现实”,让“梦想成真”。20世纪人类各种规模宏大的乌托邦实践,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要让世界不可能再有“可能”,要让一切“可能”都变成“现实”。因而20世纪的人 间世界一度成了“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的、恐怖的“神话世界”。它剥夺了作为“ 不在场”的“可能”的权力。要求一切“可能”都“到场”,如果不“到场”便是注定 被消灭的“异端”(诸如那些非科学的“牛鬼蛇神”与封建迷信现象)。其实,哲学完全 可以想象一些只是“可能”的生活与世界。这些“可能”不作为“应该”、“还不是” 状态而让我们操心与等待,而作为我们之“所是”的“不曾是”、“不再是”、“不会 是”的异质态,作为“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 的那种种可能性”[8](P437)而向我们敞开,成为我们批判我们之“所是”的无限想象 与参考视野。这正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哲学所诉求的“异邦”或“他者”的想象。 21世纪的哲学作为人学,作为一种乌托邦,不复是追求种种理性化或逻辑同一性理论的 同质化实践过程,而是追求各种不确定性的、异质性可能状态的异托邦(Hétérotopic )。
标签:哲学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科学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