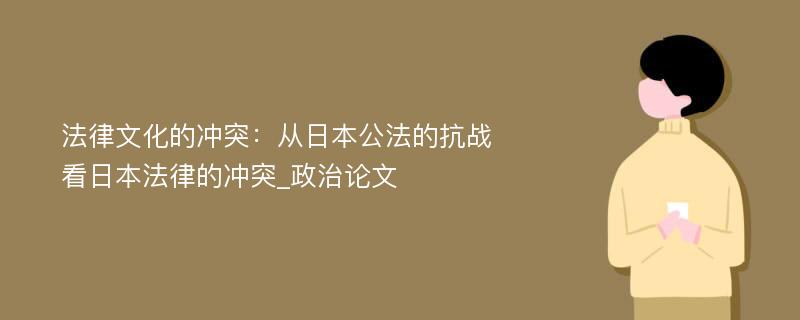
法律文化的冲突——从日本公法的阻力看日本法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冲突论文,公法论文,阻力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的发展与任何其它文化现象一样,都是伴随着特定文化圈的共同发展而发展的。现在的日本法,按其结构看,与西方没什么不同,这在极大程度上是受明治以来日本法制史上“泰西主义”的影响。当然,在其整个过程中包含了值得称道的批判主义态度。但是,日本法毕竟是在日本特有的传统文化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而这种条件,是在同西方文化没有发生多少长期接触的情况下,经过好几百年才形成的。为此,在法的结构与职能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虽然它们通常应是彼此相适应的。有些日本学者早已看到了这一矛盾,他们惊奇的是,为什么日本不去实行自己的法律(虽然他们知道这样作是可能的),为什么他们不利用立法机制,也不诉诸司法。日本法如何起作用,被日本法当作榜样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法律如何起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越加明显。
应当看到,日本法发展上的这种矛盾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当然,无视日本法过去在解决法律文化冲突问题上所作出的非凡努力及成功经验是不公平的,但是以过去的成就而否认现实的矛盾,这种作法同样也是麻木不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英美法尤其是美国法的影响进入日本社会,促成了普通法与明治时代进入日本社会的大陆法的竞争,这种情况使日本法兼收并蓄两大法系的特征,在法律文化的发展上开辟了新的途径,日本法在向西化的方向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但这种西化也仍然仅仅限于法的外部结构和立法技术上,而隐藏在西方化的法律结构背后的日本的传统法律观念并没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样一来,使得任何试图对日本法给予简单西化的评价都成为不可能。
我们说日本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历经坎坷,基本上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就日本的立法与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尤其是二战以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而言的。如若从社会生活的整体,尤其是从法律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法律文化在日本的境遇并不佳。实际上,“受西方影响的法典所设想的社会结构与自由精神在日本实际生活中只在很小程度上存在”〔1〕, 尽管日本人在一丝不苟地依法行事。由于西方的法典原是为信奉理性主义的社会制定的,法典的抽象结构大多是来自于西方笛卡尔主义的思想的产物,这对于非常尊重现实,注重实际的日本人来说,就不可能象西方人那样有理智地对待法律。所以,“在日本实施现代法难免不与日本人的神秘的温情主义发生冲突,日本人更迷恋的是诗情画意而不是逻辑推理”〔2〕。 在日本法西方化的背后仍存在着西方的法律观念与日本传统法律观念的冲突,而日本法日益西化的努力对传统法律观念的转变并没产生重大影响。正是由于立法与法律观念的不同步,所以,西方法的职能一旦转植于日本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壤,便常常走样。这在其公法领域表现甚为突出。
西方民主的日本化:观念与现实的悖离
在公法方面,一位日本政治思想史专家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政治体制的特征是“形式上的宪法主义”。
战后46年的日本宪法,虽然对民主政治的规定随处可见,美国式的民主思想不仅落实在宪法的形式上,而且也体现在具体内容上,但是,法律所确立的民主制度,在具体适用中却是阴差阳错。其原因当然不排除美国式民主制度在日本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麦克阿瑟作为占领军司令的强迫,而这种强迫的作法对于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民族来讲的确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根本原因则在于:一方面,美国人所强加给日本人的民主思想,日本人并未全部接受,而是给予了实用主义的理解。从日本战后的经济惨状着眼,所谓民主主义的思想仅仅迎合了日本人试图利用西方经济民主的思想和科学技术以恢复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作为总体社会意义的西方民主思想,在日本便变成了单纯的“经济民主”。这一点不仅从战后美国占领军及日本政府所做的大量努力和制定的措施上可以得到证明,而且从战后至今与日本经济立法大量增加、逐步完备形成明显对比的,旨在完善社会民主制度立法方面凤毛鳞角的立法现实上,也能得到印证。显然,基于实际的需要,武断地以经济民主取代或掩盖政治民主,成为了日本战后宪政发展上的一个事实,因而,一个旨在通过宪法的民主思想推进整个日本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的设想,成为了“乌托邦”。另一方面,日本人对西方民主的理解完全是建立在传统的法律观念的基础上的。而这样一来,西方的民主便完全地日本化了,无论是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讲都是如此。这对一个在最近以前对亚里斯多德仍缺乏了解的国家来讲,应该说是极自然的情况。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所谓的民主,通常被理解为最具日本特色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的思想支柱是来自于儒家学说的“和”的观念,因而它便无法具有西方式的理性色彩。在政治生活中,虽然西方人也是以某种见解的一致来体现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意志,但是,日本人的一致与西方相比,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西方人的意志一致,是通过每个成员在独立思考、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见解的基础上达成的,在日本,则是通过首倡人提出,其它成员附和的方式形成的。显然,这种“一致性”的达成多少反映了日本式的民主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压制,以及为达成所谓政治或社会团体内部的调和,迫使团体中的成员以服从团体利益,将团体代表的意见作为自己意见,从而牺牲自己的独特见解的情况。由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深受社会团体意识的影响,所以没有人会对既已出现的代表性意见表示坚决的反对,甚至会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而将个人的意见主动地融化于代表性意见之中。每个社会成员都十分清楚的是,以独立的个体对抗团体不仅有悖常理,而且也是应当受到斥责的。另外,从儒家思想所引伸出的等级观念,使得日本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一样,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道德标准,尽管这些道德标准并非出自社会政治生活中大多数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只来自于领导层的同一意志。并且,这种标准常常使法律规范几乎无效。但人们却并不感到奇怪。更令人惊讶的是,由此而形成的封建家族式的团体常常使西方人自叹弗如。日本人特有的集体意识产生的短处和通过“调和”而形成的团结所带来的一致性的长处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既克服了西方民主所带来的自由化倾向,同时更极大地破坏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从而严重地阻碍着日本当代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针对这一情况,许多日本知识分子认为,日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国家”。其实,这种认识或主张,同被称为日本“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早在1918年就提出的批评并无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尾崎行雄认为,民主主义的种子播种到日本之后,它就始终“只能在日本人封建思想方法的框框里成长”。尽管对日本人的这种民主观我们不能作好或坏这种简单评价,但它却说明了日本与西方的民主完全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因此,以为日本战后法律结构的西方化已经改变了日本的法律传统,是不合实际的想法。
由于法律观念及政治民主生活的现状,导致了日本人在所谓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生活与西方国家的迥然不同。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政治依然是少数大人物的天地,他们宁愿让大人物去统治,对于他们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之类的理论既无从体会,也不感兴趣。不言而喻,宪法中的民主制度与原则以推动公民充分行使权利,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目的化为乌有。值得注意的是,非但一般人如此,既便是法律界人士也抱有同样看法。许多外国的观察家与学者认为,日本法律人士无论在行政机关还是立法机关都非常少见。这种状况与其说是由于日本社会对法律没有给予必要的尊重,不如说是法律界人士自身对政治生活所抱的态度过于消极。如日本律师界中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就是对社会上那些非常尖锐的政治问题退避三舍。诸如日本全体国民都非常关心的北方领土问题,内阁要员丑闻,或者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研讨等问题,日本律师的反映几乎是零。
日本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政治民主及社会发展、国际政策等方面问题的关心,始终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被外界人士称为“最坦率和最频繁地对日本政治发表意见的社会阶层”。但是他们对政府和政治的现实状况基本上是不了解的。象美国的亨利·基辛格,巴托·莫伊阿纳那样深入地介入现实政治生活的知识分子,在日本基本上没有。为此,在意识形态上,日本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着强烈的进步倾向,他们对政治秩序和民主制度怀有崇高的理想,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根本没有在今日的日本建立起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秩序的现实设想,并且对社会文化的改造也没有承担起本应承担的责任。
由于在整个社会中,人们自愿放弃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加上对各种政治倾向的评价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念色彩,因此,在欧美被视为民主主义不可或缺的东西,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后也没能在日本得到确立。如相互对立的政党交替执政的习惯。相反,基于普遍的传统意识,转借而来的西方制度,却变成了事实上的“当代新型专制政体”。
三权分立:来自非法律因素的干扰
日本宪政上的冲突,在国家权利的分配上仍然得到表现。47年宪法引进了美国的分权与制衡的政体模式,使日本明治以来对西方权利分配理论的接受在法律上得到了最高体现。从形式上讲,日本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权的确立与行使,显然是典型的西方式形态,但是这一制度一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就不可能发挥出该制度原有的效果。有人就此曾谈到:“日本政治令人费解的原因在于这些制度不能象英国和美国那样顺利地行使职能。更为伤脑筋的是,在日本政治秩序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各种因素里,存在着宪法上没有规定,但因实际工作需要而产生的东西,甚至还存在着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东西。”〔3〕显然, 在日本这个“以和为贵”,重视社会及人际关系协调发展的国家,“团体本位”的精神使得权力分立在实践中极大程度上被变成了“和稀泥”式的权力协调理论。
无论是议员或是首相,甚至法官,每当依法作出决定,行使职权时,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尽管他们很清楚,这一切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然而,他们更清楚的是,法律规定并非天经地义。按照日本国宪法,日本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会。可是作为实际问题,国会的权力却受到制约,而这种制约因素并非来自所谓权力的制衡,而是来自各种非法律确立的院外势力的影响。结果,日本国会的委员会只保留了很小一部分美国议会的委员会的性质。日本国会的委员会审议,已经彻底变成了与现在的英国议会的“质问时间”相同的东西。在那里进行的是在野党千方百计地设下使政府代表感到为难,使自己的主张得以采纳的圈套,而政府代表方面则力图为自己的施政方针打圆场。双方都不大重视自己的主张会对审议中的法案产生多大影响,而侧重于对下次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实际上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在日本式的依靠全体“一致同意”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到目前为止,所有修改宪法的动议,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日本宪法规定修宪的议案只需要三分之二国会议员的支持即可生效。但是,对政府来讲,仅仅依靠执政党在国会中拥有多数议席而强行通过多数国民不支持的,或在野党强烈反对的政策的尝试,无疑是一种危险的赌博。1960年,由于当时的首相岸信介在推进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过程中采取了合法的,然而是武断的作法,引起了全体国民的强烈抗议,美国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因此取消了原订的访日计划。首相本人也因此被迫辞去了首相职务。可见,冒合法而武断的风险,其代价是惨重的。而原因就在于这种行动不合乎日本的政治传统。非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法律的程序会受到阻挠,即使在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政府如果无视各种院外势力和传统做法而武断专行,也同样会引起议员之间的激烈争吵或在野党议员对国会审议的抵制。
根据日本国宪法,日本的最高裁判所享有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样的“违宪审查权”。但是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这一职能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这不仅表现在最高裁判所实际上行使这一权力的次数上,而且也表现在法官们对待这一职能的态度上。达维曾对此说到:“最高法院在对合宪性进行监督时,即使不能说犹豫不决,至少也是小心翼翼的。”〔4〕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对法律的监督, 不如说是对立法者滥用权力的放纵。
综上可见,埋藏在日本法律结构深层的传统法律观念与法律方法,既成为当代日本西方式法律结构与法的职能在实践上的冲突表现,也有导致这一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虽然从法律文化传播方式上看,作为一种具有特色的由外向内地选择吸附型的日本主体法律文化,在近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并没有拒异质法律文化于大门之外,而是历经多次由外向内吸收融合异质法律文化的浪潮,承受多种而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冲击与刺激,并且屡屡从异质文化提供的文化因素和信息的机会中主动地对各种外部文化进行比较和选择,从而使这种外部刺激作为自身发展的新的起点,但是,由于日本主体法律文化是在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这种主体法律文化便包含了极为深刻的封闭性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正象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不断地强化了主体文化的自信心理,使主体文化始终保持着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增强了立体文化的凝聚作用和文化认同作用。所以时至今日,日本法虽然形似西方的法律,但其结构与职能仍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其西化的外观并不能掩盖其传统的内在属性。
注释:
〔1〕〔2〕〔4〕勒内·达维:《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第507页,法律出版社出版。
〔3〕《日本精神与风习》第175页。
标签: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法律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法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日本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