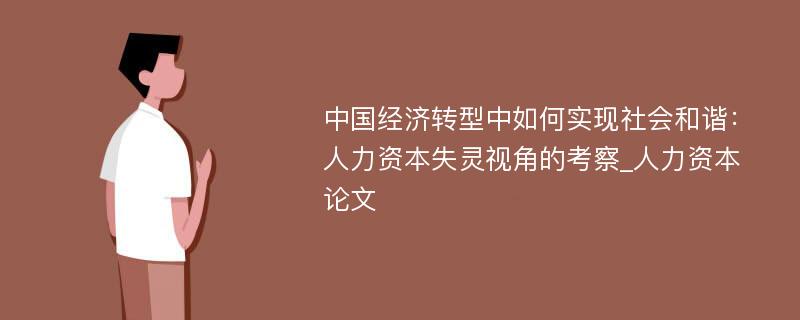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基于人力资本失灵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如何实现论文,视角论文,人力资本论文,社会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在坚持“五个统筹”(最大程度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同时,防止“三个失灵”(最大程度上防止市场失灵、防止政府失灵、防止人力资本失灵)。国内学者对“五个统筹”和“两个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基于经济学视角的论述是比较充分的,而基于人力资本失灵视角的论述却不够充分,这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本失灵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以便利用这个框架来分析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
人力资本失灵是李培林、张翼(2003)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们发现,在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存在着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文化程度、技术水平以及经验)对于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进其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市场的知识需求和职业结构变化,使下岗职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了断裂。这一概念在刘平(2004)的论文中得到应用和拓展:人力资本失灵现象不仅是对市场需求状况的验证,也是对构成人力资本必要前提的劳动者是否具有自由选择主体意识的验证;人力资本失灵不仅是人力资本要素本身的失灵,也是社会机制的失灵。笔者认为,人力资本失灵概念对于理解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人力资本失灵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它不仅仅是中国改革中的独有问题,而中国特色的转型环境和约束条件为识别和理解这一有用的概念提供了很好的“实验室”。中国过去应对人力资本失灵的经验,对于经济转型中社会和谐的实现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传统定义的基础上,笔者对人力资本失灵概念进行了更具一般性的界定和概括;人力资本失灵是指劳动者现有的人力资本不能像以前一样发挥自身的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人力资本失灵看似包含人力资本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的“双重失灵”,但它有时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用的失灵,有时主要表现为社会作用的失灵。人力资本失灵和人力资本折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力资本失灵是基于非预期的角度,非预期的变化决定了人力资本失灵;人力资本折旧则是基于预期的角度,预期的变化决定了人力资本折旧。不管是人力资本失灵还是人力资本折旧,它们都是由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造成的,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断裂。人力资本失灵或人力资本折旧的程度也往往由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的程度所决定,因为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程度的制度专用性或技术专用性。
二、人力资本失灵的成因与类型
人力资本失灵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当社会需要的人力资本劳动者不能提供,而劳动者能提供的人力资本社会又不需要时,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就不能相交,致使需求与供给不能有效“匹配”起来,进而导致人力资本失灵。这种供给—需求分析法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或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的最大特征是非激励难以调度(周其仁,1996)。激励理论(拉丰、马赫蒂摩,2002)提出,人力资本必须满足最基本的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否则,人力资本的“闸门”就会自我关闭。激励相容约束能使人力资本多的劳动者不能“装成”人力资本少的劳动者,而人力资本少的劳动者也不能“装成”人力资本多的劳动者。参与约束能使人力资本多或者少的劳动者至少获得凭自己能力可以获得的基本收益(保留收益)。很明显,在不符合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供给会发生扭曲,对社会有益的人力资本就可能供给不足,从而造成“供给型人力资本失灵”。如果劳动者在激励机制扭曲的环境中长期生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发生严重的扭曲(只针对当前的约束条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社会对人力资本类型的需要发生很大的外生或内生冲击性变动,就会形成“需求型人力资本失灵”,社会需要的人力资本劳动者几乎不能提供。长期的体制性“供给型人力资本失灵”可以造成短期的结构性“需求型人力资本失灵”,因为长期关闭的“闸门”会有“锈死”而打不开的可能。换句话说,“需求型人力资本失灵”是由人力资本的另一个特点决定的,即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某些人力资本的形成会受到年龄的限制,过了某个年龄段再积累某些人力资本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因此,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特别是制度变迁)除了要考虑政府的因素(政府要适应形势,保持宏观稳定,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企业的因素(企业要具有“自生能力”,可以形成有效的经济增量),还要考虑人的因素(劳动者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对“人力资本失灵”),而渐进式改革恰恰能兼顾到三者,使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在社会博弈中厘清市场的边界,找准自己的定位。对于转型经济而言,必须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因为没有经济效率就很难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社会稳定也很难有经济发展,对二者必须进行有效的权衡。
人力资本失灵是由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引致的原有激励机制失灵(制度安排的失灵)造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关(林毅夫,2002)。政府失灵(如政府的“掠夺之手”)会造成人力资本失灵,市场失灵(如外部效应、垄断力量以及信息不对称)也会造成人力资本失灵,所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人力资本失灵,因为经济行为主体要根据由约束条件决定的成本和收益来做出自己的决策。这种成本—收益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政府失灵造成的人力资本失灵主要表现为,最优秀的人才不是进入生产性活动领域,而是进入寻租性活动领域,结果导致整个社会不是生产性努力最大化,而是寻租性努力最大化。“政府型人力资本失灵”带来了人力资本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的异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社会福利损失严重。市场失灵造成的人力资本失灵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能对经济机会进行有效的反应,从而错过生产机会或投资机会,这种失灵既可能是由物质资本投资不足造成的(所谓“套牢”问题),也有可能是由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造成的(所谓“保守”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者或企业家(企业)的组织能力或组织资本不足有关。市场失灵扰乱了正常的信号传递,导致“市场型人力资本失灵”。“政府型人力资本失灵”往往是大规模的,而“市场型人力资本失灵”往往是小规模的,二者对社会和劳动者造成的影响并不一样,前者较后者更为严重,因为政府的试错成本比市场的试错成本更大且更难以分散。
供给—需求视角的“供给型人力资本失灵”和“需求型人力资本失灵”与成本—收益视角的“政府型人力资本失灵”和“市场型人力资本失灵”可以相互包含、相互转化,但其出发点都是劳动者本身。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技工荒”既属于“需求型人力资本失灵”,也属于“市场型人力资本失灵”。“供给型人力资本失灵”和“市场型人力资本失灵”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经济作用的失灵,“需求型人力资本失灵”和“政府型人力资本失灵”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社会作用的失灵。
三、人力资本失灵的治理与对策
治理人力资本失灵既是转型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所有国家在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过程都会遇到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人力资本失灵问题在事前(ex ante)往往是隐性(看不见)而不是显性的(看得见),人们往往在事后(ex post)才知道它的存在,而知道它的存在时已很难立刻出招化解。这看上去像一个“布利丹之驴悖论”:不知道吃哪堆草更好,吃了这堆草就不能选择更好的那堆草。从这个角度看,对付人力资本失灵,防范比治理更加重要。小规模的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所引起的人力资本失灵程度比较轻微,“症状”可能不太明显;而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所引起的人力资本失灵往往比较严重,而且“症状”非常明显。从这个角度看,为了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最好把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失灵变成多次的小规模人力资本失灵。也就是说,渐进式改革比激进式改革更可取,因为人对环境的变化需要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对于“供给型人力资本失灵”,要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加以纠正,如发挥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对于“需求型人力资本失灵”,要通过强化职业教育加以纠正,如转岗、转业培训和在职培训。纠正“政府型人力资本失灵”需要深化政府改革,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让优秀人才在市场中得到的报酬比在政府中得到的报酬(包括寻租收入)更高;纠正“市场型人力资本失灵”,需要深化市场改革,加强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中的作用,对具有正外部性的职业技术教育进行补贴或转移支付。对于人力资本经济作用的失灵,需要纠正的是激励机制,需要完善的是市场机制;对于人力资本社会作用的失灵,需要纠正的是协调机制,需要完善的是政府机制。只有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双重作用下,人力资本的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和谐统一、相互促进。
人力资本失灵不可避免地会与失业联系在一起,因为人力资本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的弱化乃至丧失正是通过失业这个最终结果表现出来的。理解失业的作用机理,对于如何治理人力资本失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隐蔽性失业”往往意味着“隐蔽性供给型人力资本失灵”,“结构性失业”往往意味着“结构性需求型人力资本失灵”,“摩擦性失业”往往意味着“摩擦性市场型人力资本失灵”,“自愿性失业”往往意味着“人力资本经济作用的失灵”,“非自愿性失业”往往意味着“人力资本社会作用的失灵”。但是,上述各种形式的小规模人力资本失灵未必能够表现出各自的“症状”,换句话说,只有达到一定临界规模的人力资本失灵才会出现自己的“症状”。在中国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力资本失灵,将不可避免地与“公平—效率权衡”(the equity-efficiency tradeoff)(Schotter,1985)联系在一起,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力资本失灵的背后就是“公平—效率权衡”。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利益与资本方(主要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利益发生冲突时,是从公平的角度照顾劳动者,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照顾资本方,是必须进行权衡和折中的问题。如果采用一种相对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效率增进非常大的话,以效率为主就会成为可行的选择,但会释放出许多冗余的劳动者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劳动者人力资本失灵;如果采用一种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可以被公平带来的努力所补偿的话,以公平为主就会成为可行的选择,但这样可能会造成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失灵。“效率为主,兼顾公平”意味着各方的议价力量(bargaining power)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因为有效率的组织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变成无效率的组织,而原本公平的组织也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变成不公平的组织。人力资本失灵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它的治理既要考虑效率,也要顾及公平。完全消除人力资本失灵是不可能的,但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人力资本失灵带来的效率损失和福利损失是可能的。
四、经济效率与社会稳定的权衡
我们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人力资本失灵的规模为N, 其中有α(0<α<1)比例的人力资本失灵者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充电”)重新获得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本,有1 -α比例的人力资本失灵者没能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充电”)重新获得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本,通过让人力资本失灵者N失业,可以获得经济效率的提升E(N),同时获得R(αN)的经济收益, 但也带来由于社会不稳定所导致的成本C[(1-α)N]。这样一来,净收益Δ(N)就是:
Δ(N)=E(N)+R(αN)-C[(1-α)N] (1)
假设E(N)对N的一阶导数大于0且二阶导数小于0,R(αN)对N的一阶导数大于0且二阶导数小于0,C[(1-α)N]对N的一阶导数大于0且二阶导数大于0,由Δ(N)对N求导,可以得到:
Δ′(N)=E′(N)+αR′(αN)-(1-α)C′[(1-α)N](2)
因为Δ″(N)=E″(N)+α[2]R″(αN)-(1-α)[2]C″[(1-α)N]<0,所以Δ(N)在(2)式等于0时(N=N*)取得最大值:
E′(N*)+αR′(αN*)=(1-α)C′[(1-α)N*]
(3)
这样,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两个命题。
命题1: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在每一既定的阶段(α保持不变时), 存在一个由政府控制的最优人力资本失灵程度,这个最优值由(3)式决定。
命题2: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在连续变化的阶段(α可变时), 政府控制的最优人力资本失灵程度随着α的增大而增大,随着α的减小而减小。
命题1、2表明,渐进式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明显的成果,是因为它不仅考虑到政府和企业的因素,还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激进式的休克疗法因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失灵而忽视了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所以在绩效上不遂人愿。我们的观点实际上扩充了林毅夫(Lin,2005)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即计划经济的企业未必是新古典意义上的企业,因为它未必具有自生能力。同样的道理,计划经济的劳动者也未必是新古典意义上的劳动者,因为他们的人力资本可能是失灵的。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的转型必须充分考虑被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的暗含前提。
五、结语
人力资本失灵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含义,它开辟了一个看待和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崭新视角。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以人为本权衡轻重,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防范人力资本失灵。人力资本失灵理论为中国如何在经济转型中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分析思路,我们既不能把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的劳动者看成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者(认为二者具有同样的人力资本),更不能认为二者具有同样的防范人力资本失灵的能力(不同国家有对不同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的权衡)。实现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需要在最大程度上防止人力资本失灵,要在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折中点。姚洋(2005)提出,“我们需要处理三个层次的问题,在第一层次上,我们要明确什么样的权利是必须平等地分配给个人并受到国家保护的;在第二层次上,我们要处理好一个积极的国家如何对社会进行干预;在第三层次上,我们要处理好提高效率和提高公民能力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人力资本失灵。总之,没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中国不可能实现繁荣强大;没有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国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中国转型加发展的双重特征,决定了我们需要在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之间进行正确的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