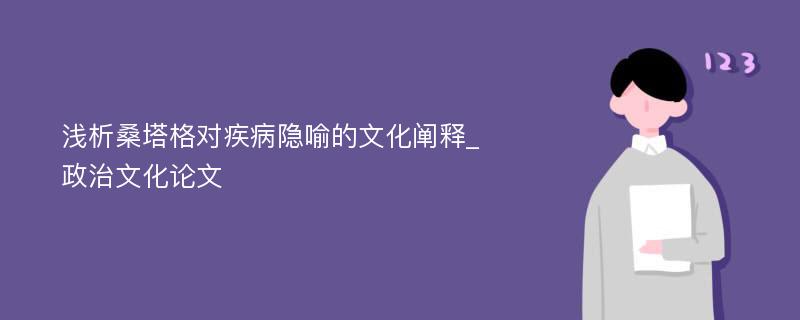
浅析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疾病论文,文化论文,桑塔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一部重要的著作,被誉为桑氏用其“反对阐释”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一次具体的实践,意图把附加在疾病之上的众多“意义”剥离去除。此书是桑塔格于1978年出版的《作为疾病的隐喻》与1989年出版的《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文章的合集。这两篇创作时间相差十二年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对疾病意象及其隐喻的剖析,批判疾病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文化压迫和道德审判的悖谬,使疾病摆脱隐喻,恢复本来面目。
一、疾病隐喻:政治修辞的手段
作为一名拥有“目光最敏锐”的评论家美称的先锋理论家,桑塔格以其独特的视角,洞悉了疾病在意识形态中因隐喻造成的“意义”泛滥现象。桑塔格犀利地剖析了疾病隐喻背后的政治修辞色彩,正如《疾病的隐喻》中文版译者程巍所揭示的那样,“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①。
在人类历史上,疾病作为政治修辞的例子并不少见,并形成了一种想像的定式,即瘟疫或疾病尤其是流行病等邪恶之物的起源往往被归于异族或异邦。如:“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②这种关联与通常关于异邦的想像是合拍的:祸水和入侵者的角色总是由异族、异邦担任,疾病类似于邪恶的入侵者,那么把疾病归于他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桑塔格指出,“把可怕的疾病同外国(或那些受人鄙视、战战兢兢的少数民族)联系起来的做法,屡见不鲜”③。桑塔格指出,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也偏好使用疾病意象,把疾病纳入政治修辞。如“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④。纳粹对疾病的隐喻化使用打开了以后把犹太人扔进集中营和焚尸炉的通道,等同于癌瘤的东西必定是邪恶的,在针对他族使用癌症意象的修辞背后包含着极端的政治意图,在所有的疾病意象中,癌症是被赋予政治隐喻最多的疾病,癌症因为病因不明(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通常被等同于死亡,所以是最极端的疾病隐喻,“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使用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⑤。人们在这种思想的怂恿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缺少对于政治事件或文化问题的深层思索。桑塔格似乎找到了使用疾病意象的内在动机,把疾病变成一种文化符号以区分“本族和非我族类”,因此,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中立的、清白的。桑塔格对此种政治修辞进行了深刻的思索:“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⑥此外,值得提出的一点是,疾病意象在政治修辞中的使用不关乎使用者的政治面目,不专属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左翼使用之,右翼也使用之。如希特勒在陈述他的政治理念的一本书中把犹太人比作“一种恶性的结核病”。前苏联的历史上也充斥着疾病意象,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驱逐出国后,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理想主义或激进主义的革命家往往把现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定义为“病入膏肓”,因此需要采取史无前例的“激进”疗法。当然,桑塔格也指出,癌症的隐喻与其他疾病的隐喻一样,是动态的。她预言,当癌症的病因最终明确,神秘性消除,治愈率大幅度提高,不再被视为死亡的代名词时,“癌症隐喻就必定发生重大改变”⑦。也就是说,一种疾病越神秘,与死亡的关联度越高,其产生的疾病隐喻就越恶劣。
癌症的隐喻尚未消解,艾滋病的出现又成了另一个在隐喻的极端程度上与其等量齐观的疾病意象。在桑塔格看来,欧洲、前苏联都存在一种有意为之的强调,突出艾滋病病毒的“非洲起源”说,更情愿把艾滋病看作是来自彼处的“入侵者”。而某些种族主义者和本土文化保护论者甚至把艾滋病与第三世界的移民潮关联起来,警告人们这是一个关系到文明存亡的问题。一个在冷战时期常被用来批评西方在与苏东集团对抗中表现不力的词语——软弱——这次又因艾滋病用在了西方头上。这种政治偏执狂的语言典型地透露出其对多元世界的疑惧。实质上,统治阶层,尤其是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往往利用重大疾病来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以此来促进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作为流行病的艾滋病便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它的隐喻地位不断地被提升。
福柯指出,医院不仅是一个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⑧。而“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和健康政策,在实质上就是一种‘疾病政治学’”,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源头。“国家借助于新型医疗制度的完善,一方面表现出对全民生命的关怀;另一方面又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对全社会的生命历程的控制和统治。”⑨这一想法与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阐释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桑塔格看来,所谓的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的必要性”⑩。疾病的隐喻俨然已经被加上了浓厚的政治修辞的色彩,成为国家机器压制民众的工具。
二、疾病隐喻:“他者化”的同谋
毫无疑问,在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健康/疾病这一对二元关系中,疾病是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一方。自然,被排挤的疾病也就没有其本身应有的、与健康同等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一种人类生理现象的疾病本身被健康所代表的主流话语所压制,而这种压制则是由隐喻来完成的。在所谓共同的想像和权力话语的策划下,疾病被赋予种种隐喻,而患病的人,即疾病的承载者,则被种种疾病的隐喻扭曲成了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的“他者”。于是,疾病便成了强权文化使部分群体“他者化”的同谋。
福柯在《词与物》中阐释了在文化作用下的词与物的分离,而疾病及其隐喻正是文化霸权下词与物分离的体现。被怀有各种目的的文化阶层异化和边缘化的疾病丧失了其本来面目,如同现象与本质的剥离。现象代替了本质,疾病本身被其隐喻所遮蔽,而被隐喻“他者化”的患者则不能获取其应有的正当身份。
艾滋病是被“他者化”的疾病中最具代表性的。艾滋病患者往往来自被认为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是被社会所蔑视的群体中的一分子。这种认识使艾滋病患者进一步被边缘化,成了被唾弃的“他者”:疾病成为“他者”的同时,患者也成了“他者”。而把疾病患者“他者化”的方式通常是这样的:“每一种令人恐惧的流行病,尤其是那些与性放纵有关的流行病,总是在该流行病的假定携带者(这通常只是指穷人,而在美国,则指有色人种)与那些被界定为‘普通人口’的人们之间——作这种界定的人是卫生专家和其他官僚——划出一条先入为主的界线。”(11)把疾病患者划分为“他者”的是以卫生专家为代表的特权阶级和统治阶层。正如福柯所说,现代医学是现代社会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进行区隔和等级分类的“科学”基础。(12)这使得艾滋病和癌症这样的疾病成为一个被界定或被建构的产物。对病症尤其是艾滋病的界定已经超出了医学范畴,一系列的隐喻使携带病毒的健康者也被打入了患者的行列,使他们成了“终身为贱民的新阶级”。患者就这样被剥夺了公民权和话语权,被逐出社会,成为“他者”。
“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13),这种隐喻实质上是把疾病看作外来的“他者”。这样把某些疾病打上耻辱烙印的后果是:“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是疾病的牺牲品。”(14)这些隐喻扭曲了患者自身对于疾病的体验,使疾病从单纯的身体体验转变成了带有道德评判的心理体验,妨碍了患者正确、及时有效地获得治疗。
三、疾病隐喻:道德评判的工具
把疾病与“天罚”联系起来是西方话语实践中常见的现象。桑塔格追本溯源,发现古希腊、古罗马及后世都把疾病看作是上天对人类道德堕落的惩罚。这种观念可见于《伊利亚特》、《奥德赛》、《十日谈》等著作;而基督教亦把疾病赋予更多道德含义,“在疾病与‘受难’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关联”(15)。疾病隐喻化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而不仅仅是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时,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16)在普遍认识中,健康是德行的证明,而疾病则是堕落的证据。
《疾病的隐喻》一书列举了若干疾病隐喻所具有的道德标签意义:疾病乃人格之显现这一观点在19世纪开始流行。不同疾病的患者往往被打上不同人格的标识。这种观点认定患者的人格特性是其患病的诱因,不同的人格特性导致了不同的疾病。结核病患者往往被看作“雅致、敏感、忧伤、柔弱”的,而癌症患者则往往被认为是“冷酷、无情、损人利己”的。然而,这种对于人格的疾病隐喻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19世纪时认为癌症的诱因是狂躁或犹豫的人格类型,而到了20世纪癌症人格的描述则转变为“心灰意冷、自我憎恨、情感冷漠”。疾病的不同人格标识即意味着疾病被加上了道德评判的色彩。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是道德方面的。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17)而正是那些重疾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由于强加在疾病身上的道德批判,患者不仅得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背上了耻辱的印记。
四、疾病隐喻:文化等级的折射
在疾病被“边缘化”和“他者化”的同时,不同疾病在隐喻中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形成了若干疾病“神话”,成了一种等级意识的体现;其隐喻随着文化霸权阶层的变化而变化。从某方面来说,《疾病的隐喻》是福柯所倡导的知识考古学具体而微的实践。(18)福柯认为:“任何社会历史事件的出现和实际影响,都离不开身体这个最重要的场所。当权力试图控制和驾驭整个社会的资源、人力和组织的时候,它首先所要征服的,就是身体。身体是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最重要的中介场域,是连接个人自我同整个社会的必要环节,也是把个人自身同知识论述、权力作用以及社会道德连接在一起的关键链条。人的身体实际上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而在历史上演变的。……权力系谱学研究的是人的身体在历史上的各种不同的遭遇,就是各种社会历史事件的见证;在人的身体上面,留下了各种社会历史事件的缩影和痕迹。身体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社会历史事件的烙印。……揭示历史和身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揭示历史如何渗透到人的身体而逐渐地肢解和粉碎了身体,把身体侵占,加以殖民化,使身体扭曲和变形,使身体分化成各种游戏的工具和对象,成为满足社会历史需要的各种手段。正因为这样,身体成为了系谱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领域。”(19)因而,对于身体的疾病之隐喻的剖析是研究社会文化的最直接的入口。
结核病曾经是生成隐喻最多的疾病。程巍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译本的注释中认为,结核病产生的隐喻是贵族阶层在与资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和经济领导权失利以后,为了争取自己在文化上的领导权而臆造的。“被剥夺了政治特权又丧失了经济优势的贵族阶层以此来争夺资产阶级所忽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领导权,以此来贬低资产阶级的物质性优势,这样,越少显示物质性的东西,似乎就越能显示精神性,追求一种高度的贫瘠(消瘦、苍白),与资产阶级的富裕形成对比。”(20)结核病的隐喻体现的是没落的贵族阶层在道德上和文化品位上贬低其他阶层的等级制成见。贵族把自己所谓的“气质”依托在了结核病身上,于是结核病成了具有贵族色彩的优雅浪漫病或“激情病”,成了一种脱离粗鄙庸俗的符号。桑塔格发现,在隐喻的作用下,结核病被提升到“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的境界,它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成为“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其最终导致的死亡使人获得了某种“超越”。为了说明这点,桑塔格列举了19世纪的数部文学作品,从《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董贝父子》中的保罗,到《尼古拉斯·尼克贝尔》中的斯迈克,无一不弥漫着对于结核病的浪漫描写。在浪漫主义时期,结核病已经成为一种贵族争相效仿的时尚,以至于拜伦说“我宁愿死于痨病”。桑塔格则深刻地揭示了结核病隐喻背后掩盖的文化社会症状:“18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21)这种当时的所谓对于疾病的新态度被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结核病不仅是一种审美化的存在,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同时也是身份、权力与文化的符号。
结核病被神话般的光环笼罩着,以至于“当描绘垂死的结核病人时,就把他们塑造得更美丽、更真诚,而当刻画垂死的癌症患者时,就尽数剥夺他们自我超越的能力,让他们被恐惧和痛苦弄得毫无尊严”(22)。结果,癌症则被贬斥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23)。因此有了文学作品中凄美的结核病患者形象,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对于癌症患者的“卑贱、痛苦”的描写。究其原因,是癌症被隐喻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病,一种与“富贵、奢华相联系的病”,是贵族阶层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压制与偏见。在所有的疾病意象中,留给资产阶级的则是痛风、中风和癌症——那些与脑满肠肥和情感匮乏有关的疾病。而到了20世纪,癌症的经济学隐喻则演变成了“扩张、投机、畸形增长”。各种不良的社会文化现象不断地被投射在癌症上,因而“癌症成了那些拥有极其可怕的能量的东西的一个隐喻;这些能量最终将损害自然秩序。对那些思想更复杂一些的人来说,癌症标志着受到伤害的生态圈的反叛:是大自然对一个邪恶的技术统治的世界的报复”(24)。不仅如此,“当今广为流传的把癌症视为工业文明的一种疾病的观点,与那些极右团体的‘无癌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破坏分子的世界)的幻觉一样,在科学上都站不住脚。两者都不把癌症仅仅当作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作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25)。此外,在权力话语的影响下,人们习惯用战争的语言来隐喻癌症,如:癌细胞具有“侵犯性”,在推行“殖民化”;而对于癌症的治疗也被比喻为充满进攻、防御等军事色彩的“战争”。
当癌症不再是最恐怖的疾病后,疾病隐喻就要寻找新的宿主,艾滋病成了人们赋予隐喻最多、承担隐喻范围最广、隐喻的恶劣程度最高的疾病;其隐喻成为了一种文化排斥、社会空间区隔、政治压迫的手段。人们对于头号恐怖疾病的隐喻是最多的,从结核病到癌症再到艾滋病,疾病的“隐喻实践”在发生变化。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疾病从头号致死性疾病的位置上退下来,另外的恐怖疾病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文化的想像和权力话语的变化,各个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疾病隐喻,虽然关于疾病的想像和隐喻不断地生成变化,但始终不变的则是形形色色的疾病隐喻加入权力话语的建构,进而造成对公众意识的污染以及对于患者的伤害。
五、结语
“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26)这种隐喻只是压迫性权力话语的政治修辞学,在这种修辞学的背后是疾病被纳入和服务于权力话语的需要的论调中。这种修辞使疾病获得各种“意义”并使其失去本来的面目。然而,所有被隐喻的疾病,以癌症为例,要正视它,就必须恢复它作为疾病的本来面目,桑塔格如是说,癌症既不是灾祸也不是惩罚,它本身没有“意义”。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做的,就是挑战这些修辞隐喻,使疾病去除“意义”,恢复疾病作为一种自然生理现象的本来面目。使事物恢复其本来面目,是桑塔格一贯持有的观点。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疾病在被怀有各种目的的文化阶层进行强加意义的阐释后,其本来面目被遮蔽和扭曲,丧失了其应有的作为疾病的言说权利。桑塔格对于去除疾病隐喻的种种努力实质上是在向创造疾病隐喻的权力意识形态提出挑战;她试图通过对于疾病隐喻的批判来批判和颠覆意识形态中各种专制的压迫性话语,以消解“意义”的方式来恢复疾病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⑩(11)(13)(14)(15)(16)(17)(18)(20)(21)(22)(23)(24)(25)(26)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第121页,第127页,第72页,第77页,第76页,第135页,第5页,第103页,第87页,第88页,第40页,第8页,第53页,第2页,第26页,第27页,第17页,第18页,第62—63页,第64页,第86页。
⑧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7页。
⑨(12)高宣扬:《论福柯对国家理性的批判》,《求是学刊》,2007年第11期。
(19)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