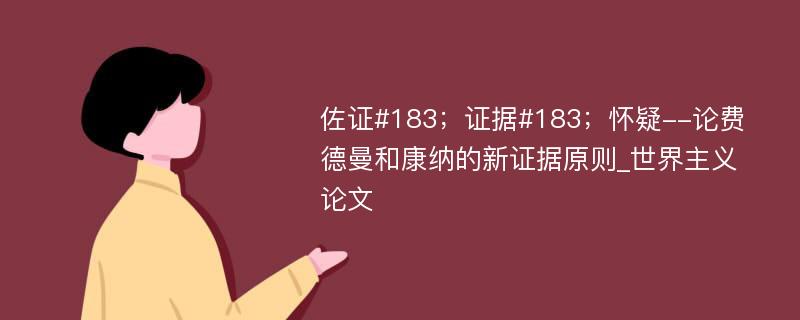
确证#183;证据#183;怀疑——评费德曼与柯内的新证据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据论文,确证论文,主义论文,评费德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3-0027-07
我们因相信而存在,但相信一般不能和理性相悖;或者说,我们相信什么需要得到确证或者需要拥有好的理由。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就明白写到:“作为我们的义务,如果信念不能基于好的理由得到规范,它就不能赋予任何事物。所以,信念不能和理性相反。”①那么,何谓确证或者如何拥有好的理由?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即信念只有在人拥有充分证据的时候才是合理的。也有人提出否命题:“无论何时、何地对何人而言基于非充分的证据而相信总是错误的。”②一般认为,证据主义在法律、宗教、政治事务等领域得以滥觞的逻辑理据即在于此。启蒙时代以来证据主义势头强劲,但它影响到知识论研究却不过几十年。齐硕姆、诺齐克、苏姗·哈克等人正是在近几十年内才相继提出了知识或确证的证据主义。费德曼与柯内的新证据主义也是这种思潮的产物。费德曼与柯内宣称他们的新证据主义是当今“最好的”确证理论,其不仅能够克服主流学派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克服怀疑主义困扰。本文认为,费德曼与柯内的证据主义有自我夸矜之嫌,它是否真的如此美好,是否能够应对怀疑主义不能仅靠一家之言,需要受到人们理性的回应。基此,本文拟对此种证据主义予以批判性检讨。
一、当代主流确证理论的困境
证据主义产生之前,当代知识论关于确证问题的研究主要在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等主流学派之间展开,但这些主流学派在多年的论争中暴露出严重的问题,陷入了无法自解的困境之中。概言之:
1.内在主义主张:确证地相信是认知主体的义务,认知义务要求在确证之时认知者必须对确证者有所把握;由于外在客体无法把握,因此,只有认识主体的内在状态才能成为真正的确证者③。内在主义的问题有:(1)义务论有导向意志论之嫌,普通认知者并不能任意主导信念的确证。④(2)把握主义会导致不合理的高层要求,即如果在确证之时必须把握确证者,则是否还需对确证者进行把握?如果需要,则无限把握的高层要求将不可避免。⑤(3)内在状态的概念不明晰。内在主义无法说明内在状态是信念抑或感觉?是经验还是情绪?是血液的PH值还是肝脏的大小?⑥
2.外在主义(主要指信赖主义)主张:认识者可信赖的认识过程决定其信念的确证。⑦外在主义的问题有:(1)认识过程的普遍性问题。比如,某人看见一棵树,看见属于知觉过程,但知觉的准确性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如此一来如何选择认识过程的类型就成为问题。⑧(2)认识过程的可信赖性问题。即在何种意义上谈可信赖?是基于成真的比率还是什么?⑨(3)恶魔问题。即如果存在不同的认识世界,在不同的认识世界里认识过程的可信赖性是否一致?⑩
3.基础主义主张:信念的确证必须最终建立在基础信念之上。(11)
基础主义的问题主要是:基础信念的确证问题。即若基础信念本身需要确证,则基础信念就构不成基础信念;若基础信念本身无需确证,则基础信念的合理性就面临问题。(12)
4.一致主义主张:信念的确证在于待证信念和认知者的信念系统的其他信念必须保持一致。(13)一致主义的问题有:(1)认知回溯问题,即信念a的确证需要信念b,信念b的确证需要信念c,信念c的确证需要信念d,信念d的确证又需要信念a。(14)(2)信念系统的元确证问题,即信念系统如何确证的问题。(15)(3)经验的输入问题,即认识者的经验如何进入信念系统。(16)
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等主流确证理论所暴露出的严重理论困境,充分表明了当代知识论的主流理论依然无法有效地应对怀疑主义的质疑,费德曼与柯内正是在对主流理论的批判基础上形成了新证据主义。
二、新证据主义的基本定位及理论归属
1.基本定位
新证据主义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证据主义”与“内在主义辩护”两篇论文中。在“证据主义”中,费德曼与柯内开宗明义说:“在知识论中我们倡导证据主义,我们所说的证据主义认为,信念者的证据质量决定着信念的确证。不相信和悬置判断在认识上也能得到确证。一个人所确证地具有的信念态度就是契合于认识者的证据。”(17)
新证据主义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在时间t,S关于命题p的信念态度D在认识上是确证的;当且仅当有关p的命题态度D在时间t契合于S的证据。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新证据主义至少有以下五个特点:(1)确证概念是认知上的,而非心理或道义上的。(2)确证涉及相信的命题态度,还涉及不相信与悬置判断的状况。(3)确证完全基于证据。(4)确证有时间性。(5)确证和证据质量有关。
基于对证据主义的特点分析,费德曼与柯内二人提出了最优理论的观点,即“证据主义不求哗众取宠或立意创新,我们把它视为关于确证本质的最可行的观点。”(18)
2.理论归属
分析新证据主义的论证特点可以看出,费德曼与柯内对证据主义的“最可行”所做的辩护和它的理论归属紧密相连,而这种理论归属也集中体现了证据主义“最强的”解题能力。从证据主义的理论归属来看:
(1)证据主义是一种改良的内在主义。
诚如费德曼与柯内所言,新证据主义首先是一种改良的内在主义。但它与主流内在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抛弃了主流内在主义的逻辑前提:义务论。而且,这种改良的内在主义是一种彻底的心灵主义。费德曼与柯内认为,改良的内在主义具有强大的解题能力,能够解决主流内在主义面临的一系列难题:
其一,抛弃主流内在主义的义务论,能够避免饱受外在主义强烈攻击的意志论问题。义务论主张:相信是对认知义务的履行,遵守义务相信就会被允许;反之,违反义务而相信就会受到谴责。主张义务论的直接结果就是要求相信的意志论,就是说,S确证地相信p;当且仅当S能够直接控制p。但正如阿尔斯顿指出,一般而言,人类不具备直接控制信念的能力。比如,当我看到一辆卡车沿街急驰而来时,我无法任意的相信卡车是否急驰而来。阿尔斯顿认为,即便是有诸如道德和宗教这样的一些直接控制的信念特例,但对我们的大多数信念我们是缺乏直接控制能力的。(19)由于义务论会带来诸如意志论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放弃义务论成为内在主义的心隐之痛。在前期“证据主义”一文中,费德曼与柯内似乎还对义务论难以割舍,在鞭挞其他各类义务论之时偷偷保留了所谓“合理”的义务论即是证明。(20)但在后期的“内在主义辩护”中,费德曼与柯内完全摈弃了义务论,认为内在主义根本无需这一前提。
其二,作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心灵主义,改良的内在主义还有如下优点:可以解决内在主义的二分问题,即分为把握主义与心灵主义的问题。因为把握主义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心灵状态,心灵主义的简单明了还能避免把握主义的烦琐要求。可以解决可能世界的问题,因为它规定:任何可能世界中心灵状态相同的两个认知者,他们的信念同样能够得到确证。可以解决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划界的问题。因为内在心灵状态是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划界的最佳选择。可以解决内在状态的不明问题,因为它把内在状态仅仅局限在个人当下的和倾向性的心灵状态、事件和条件。另外,改良的内在主义作为心灵主义还具有与心灵哲学、心灵伦理学同质的效果,以及还可以解决内在主义与先验知识的联系问题,等等(21)。
(2)证据主义不排斥外在主义。
虽然费德曼与柯内的证据主义总体看是一种改良的内在主义,他们的证据主义和外在主义并非水火不容,他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证据主义完全可以和外在主义的典型流派信赖主义保持等值。
费德曼与柯内是这样论证的:虽然信赖主义主张,信念的确证来自于可信赖地导致真信念的信念形成过程;但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它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有完满根据的理论。按照证据主义的完满根据理论,信念的确证当且仅当该信念基于完满的根据。而信赖主义主张的可信赖的信念形成过程,完全可以理解为信念具有完满根据。如此,信赖主义和证据主义明显具有等价性,若有区别也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当然,在费德曼与柯内看来,若要实现信赖主义与证据主义的事实等价性,信赖主义还必须解决认识过程的“普遍性问题”与“可信赖性”的理解问题。但正如许多论者指出,“普遍性问题”与“可信赖性”的理解问题已经重创了信赖主义。因此,费德曼与柯内认为,信赖主义离能够应用还很遥远。不过二人指出,既然信赖主义存在再造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把信赖主义视为证据主义的一种。(22)
(3)证据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基础主义。
证据主义明确主张信念的确证基于证据,这种基于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基础主义观点。但费德曼与柯内的自矜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证据主义能够避免基础主义的难题。如前所述,基础主义的难题是:要么基础信念需要确证,从而就不成其为基础信念;要么基础信念不需要确证,从而基础信念就缺乏合理性。费德曼与柯内在解决内在主义的高层要求时“解决”了基础信念的难题。诚如上述,内在主义面临高层要求的难题。但费德曼与柯内认为,内在主义根本无须承诺高层要求。他们指出,拥有正确的证据本身即能确保相应的信念得以确证;理由是确证和合适证据的内在拥有事实上同时发生。(23)当确证与合适证据的内在拥有同时发生之时,基础信念的确证与否就不再成为问题。
(4)证据主义对一致主义保持同情。
证据主义同情一致主义。这体现在费德曼与柯内对整体一致主义问题的解决上。整体一致主义主张,信念的确证依赖于整个信念系统,即是说待证的信念需要和整个信念系统的其他信念保持一致。这种对整个信念系统的依赖直接导致了储存信念“同时记起”的不可能性的指责。在费德曼与柯内看来,这种“同时记起”的不可能性的指责构不成对整体一致主义的挑战,证据主义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方式是,不管所有储存信念的合取是否被意识到,只要它和待证信念发生矛盾,此合取将自动构成待确证信念的击败者。另一种方式是,只需把确证局限在一类储存信念,太过复杂从而无法把握的信念集合将被排除在外。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范围狭小的一类储存信念的把握来确定待证信念的确证与否。费德曼与柯内认为,这种确证的根据就是基于确证与合适证据“同时发生”原理。可以认为,虽然费德曼与柯内从来没有直接提出证据主义就是一致主义;但他在证据的意义上对一致主义的辩护,至少可以说明这种证据主义对一致主义保持同情。(24)
综上所述,新证据主义是一种内在主义倾向明显的理论,但由于外在主义、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等主流学派也有一定的理论优势,所以,新证据主义又杂糅了这些学派的长处、表现出向它们示好的意象。但新证据主义并不满足于此,恰是因为各种主流理论的弊端已经充分显现,所以新证据主义用所谓的证据理论统筹了各方观点,大胆提出这种理论具有最强的解题能力;最重要的是,新证据主义还宣称怀疑主义可以避免。但新证据主义真的能够避免怀疑主义吗?
三、怀疑主义的诘难
正如费德曼在为《知识论指南》写的“证据”的词条中所承认的,新证据主义若要摆脱怀疑主义质疑,必须要对以下三个问题有所交代,即“什么是证据”、“证据如何把握”以及“证据怎样支持信念”。(25)在费德曼与柯内看来,这些问题并无什么严重之处,但本文以为,恰是这三个基本问题构成了对新证据主义的直接挑战。
1.什么是证据
证据是证据主义的核心概念,新证据主义理应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该理论的一大明显漏洞就是,在费德曼与柯内的新证据主义论证中并没有找到一个关于“证据的”明晰界定。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从费德曼与柯内的代表作中找到一些关于证据外延的逻辑理解的论断。在“内在主义辩护”一文中,费德曼与柯内多次提到内在状态或内在证据因素只能局限于个人当下的和倾向性的心灵状态、事件和条件(26)。既然证据主义是改良的内在主义或心灵主义,那么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所谓的证据就是指个人当下的和倾向性的心灵状态、事件和条件。但必须指出,“个人当下的和倾向性的心灵状态、事件和条件”比较笼统模糊,所以,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耙梳出证据的逻辑外延,然后再来分析这些证据的事实可行性。
在“内在主义辩护”中,费德曼与柯内给出了六对典型案例以此论证内在主义的合理性。在对六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专家证言”、“感觉经验”、“观察”、“回忆”、“反思”、“洞察”、“逻辑推理”等都是证据。在论文的他处还可找到,诸如“看见”、“信念”、“直觉到”、“旁证”、“倾向性”、“冲动”以及“先验洞察力”等皆是证据(27)。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费德曼与柯内对证据理解覆盖面广泛,不仅涵盖了人类认知的所有理智手段,而且还纳入了诸如冲动、倾向性等非理智领域的东西。如果我们对这种证据论做一判定的话,我们认为这种证据论如同一锅“杂烩”,因为,这些所谓的证据既可以理解为内在主义的认知手段,也可以理解为外在主义的认知手段,除此之外还包含有当代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都没谈到的冲动等手段。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新证据主义在理论上并不成熟。当然,费德曼与柯内绝不承认我们的判断,他们直言这些所谓的证据都可以称为内在心灵的东西,是内在主义的。我们认为,把诸如感觉、经验、逻辑推理、证言等都归入心灵状态显然太过牵强。而且即便我们承认以上手段皆可成为获取证据的方式,但以上手段能否作为确证的有效方式,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尚都悬而未结。以“看见”这种知觉手段为例。笛卡尔以来,哲学史上就存在着“梦幻问题”、“恶魔问题”、“缸中之脑”等怀疑主义问题,而这些问题促成了诸多哲学学派的形成。比如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在论与现象论或表象论;理智论与常识论,等等。可以说,这些学派关于“知觉”的定性至今没有共识,以一个本身合理性存疑的前提作为论证的手段,要么暴露了新证据主义的太过武断,要么说明这种主义比较肤浅。
2.证据如何把握
费德曼与柯内的证据类型广泛,但如果从证据把握的角度进行归结不外两类:当下的证据和既往的证据。巧合的是,费德曼与柯内有着和我们相近的概括。他们把证据分为“当下的”和“倾向性的”两类。这样就涉及两类证据的把握问题。姑且我们像所有内在主义者承认的那样,即当下证据容易把握;但既往的证据如何把握呢?戈德曼对储存信念的疑问就直指这种证据的把握的不可能性。戈德曼的论证大致如下:
莎丽拥有许多确证的信念,这些信念曾经都有十分确凿充分的证据支持但随后她忘记了这些证据。在认知评价的时刻,她回忆不起她曾拥有的充分证据。去年莎丽在纽约时报“科学”版上读到一则有关饼干的健康益处的故事,于是她确证地相信饼干的健康功效。现在她仍然持有该信念但却记不起证据之源。然而她的饼干功效的信念依然是确证的,而且,如果该信念是真信念还可以视为知识。证据主义如何看待这种证据遗忘但信念仍然确证的状况呢?在费德曼与柯内看来,依靠回忆或背景信念可以解决该问题。但戈德曼继续假设:即便我们承认莎丽现在还拥有支持饼干功效的信念的证据,这些证据即莎丽回忆起来的而且都是通过正常的认知途径得到的背景信念,但这些所谓的证据对确证充分吗?戈德曼认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即便假定莎丽回忆起来的背景信念都是通过正常的认知途径得到的,但事实上她有关饼干有益健康的信念不是来自纽约时报“科学”版,而是来自并不可靠的“国家探寻”,那么,莎丽当前所有的背景信念也不能确证既有的饼干有益健康的信念。总之,费德曼与柯内的新证据主义用所谓的倾向性的信念来解决证据遗忘以及我们记忆中的确拥有大量确证信念的状况不具有说服力,或者说是极其牵强的(28)。
3.证据怎样支持
即便我们承认新证据主义能够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但如何保证我们拥有的证据能够有效支持信念的确证。无疑,费德曼与柯内用“同时并发”的原理无法有效解释证据的支持问题,刘易斯的“被给予”的理论已被证明是一种神话。所以,新证据主义必须解决证据的支持问题。关于证据支持问题主要涉及到:“证据的效力”、“证据的适用条件”以及“证据的结构”等系列问题。
证据的效力问题是证据主义必须直面的问题。要解决证据效力问题首先要解决证据效力的指向问题。这就至少涉及证据指向真理、合理性还是知识?如果证据指向真理,那么就涉及信念的确证仅当证据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信念成真。如果证据指向合理性,那么就涉及信念的确证仅当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信念是合理的。当然证据还有更高的指向,即指向知识,这就涉及在何种意义上证据能保证确证的信念成为知识。然而,从费德曼与柯内的论断中几乎看不出证据主义确证论真正指向,所以证据的效力问题就很难谈起。以证据的效力指向真理为例,假设证据的效力指向真理,我们就需要知道证据导致信念成真的比率以及判断的依据。需要知道成真的比率是50%还是多少?是客观概率还主观概率?如果新证据主义无法解决此类问题,那么阿尔斯顿对戈德曼信赖主义信念成真的比率以及判断依据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新证据主义。(29)
证据的适用条件。在新证据主义中我们只笼统地看到“在时间t”的简单规定。应当说费德曼与柯内并没有对证据适用的条件做出明确规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新证据主义的论证中理出,证据的适用范围基本上局限在“日常世界”里。比如,在费德曼与柯内对确证进行分类界定时对“肯定确证”是这样例证的。“在正常环境下一个心理正常的人,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看到眼前有一片绿色的草坪,他相信眼前有某个绿色东西的命题态度就是契合于他的证据的,这就是信念在认识上得以确证的理由。”(30)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在二人的论证中找出很多,因此,我们不妨把新证据主义的证据适用理解为适用于“日常世界”。但从费德曼与柯内对内在主义的论证中,却可以明确看到,费德曼与柯内把内在主义界定为心灵主义,其根本动机就是为了解决内在主义在可能世界的适用问题。由此观之,新证据主义的证据适用徘徊在“多个世界”之间。但基于日常世界的论证能否适用于可能世界呢?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疑问,这里,费德曼与柯内并没有给出明确论证。当然我们依然可以从戈德曼为可能世界寻找依据面临的困境看出该问题的难度。戈德曼为解决可能世界问题,首先以“事实世界”为依据,但遭到批判;接着他又以“正常世界”为依据(31),又遭到指责(32);最后戈德曼只能退到认知“德性”来解决问题(33),但又遭到无情围剿。(34)戈德曼面临的困境可以说就是新证据主义的一面镜子。
新证据主义还面临证据支持的结构问题。这个问题和以上两个问题紧密相关,主要涉及证据的确证问题。也即证据在何种意义上是适当的。而要说明这个问题,立即就会陷入证据论证的基础主义或一致主义的论争中。从费德曼与柯内的论证中可以看出,二人试图用所谓的“并发原理”解决证据的结构问题,从而避免基础主义或一致主义面临的问题。但这种解决方式就类同于“被给予”的神话,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我们对费德曼与柯内的新证据主义判断如下:
新证据主义是在当代主流确证理论都陷入怀疑主义困扰之时提出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在提出之始似乎给人以柳暗花明之感,也的确提供了重新审视确证理论的一个新视角;这些是新证据主义对当代知识论所做的贡献。但新证据主义的确理论缺陷明显,并无法担当实现当代知识论重建的任务。具体体现在:
首先,新证据主义本身不具备理论体系的特点,把它称之为有关确证的一种“观点”较为合适。因为一个负责任的理论家在构建理论体系时一般需要从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公理及原则等方面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而费德曼与柯内在亮出新证据主义基本观点之后,并没有从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公理及原则等方面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反证这种迂回的方式证明其他理论驳不倒证据主义。应当说,用反证法反证某种观点的正确与否比较合适,但对构建一个理论体系的作用并不明显。
其次,新证据主义在理论内容上看似包容性很强,但其实类似一个拼图游戏。因为,新证据主义试图包容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等主流学派,宣称能够扬弃这些理论的所有弊端;但恰是由于新证据主义没有一个基本的论证规范,所以虽然雄心宏大,但结果只能是镜花水月。这就像由各个拼版虽然能够拼成一架飞机的造型,但真正制造出一架飞机却不是那么容易。新证据主义的缺陷就在于没有能够基于“证据”这条主线把各种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实现某种新理论重构的升华。
最后,新证据主义没有就证据主义的核心命题进行论证,所以常常出现论证上或不知所云,或以常识代替理性,或以未证进行证明的严重错误。如上所述,在整个理论的建构过程中,费德曼与柯内始终没有交代证据的内涵与外延,读者自始至终不清楚为何“知觉”这些存在理论疑问的东西,缘何都可以被新证据主义作为逻辑论证的前提。
一言以蔽之:由于新证据主义存在重大理论缺陷,该主义既非最可行的理论、也谈不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怀疑主义问题。不妨这样说,确证问题归根结底属于证据问题,但新证据主义现在并没有完成确证的使命。新证据主义如果还想继续作为,就应当在“体系”理论上多做些文章。
注释:
①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A.C.Fraser (eds),New York:Dover,1959,pp.413-414.
②William K.Clifford,"The Ethics of Belief" in http://philosopedia.org/index.php/w.k.Clifford.
③(28)Alvin Goldman,"Internalism Exposed" in Hilary Konblith(eds),Epistemology: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1,pp.208-227.pp.214-215.
④Alvin Plantinga,Warrant:The Current Deb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45.
⑤(19)William P.Alston,"Internalsim and Externalism In Epistemology",Philosophical Topics,Vol XIV,No.1,Spring,1986,pp 196-201,pp.196-201.
⑥Alvin Plantinga,"Justif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Ernest Sosa (eds),Knowledge and Justific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759.
⑦⑩Alvin Goldman,"What is Justified Belief",in George S.Pappas (eds),Justification and Knowledge,Dordrecht:D.Re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0,pp.17-18.
⑧John L.Pollock & Joseph,Cruz,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2nd editio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p.117.
⑨(17)(18)(20)(22)(30)Richard Feldman and Earl Conee,"Evidentialism",Philosophical Studies 1985(48),p.26,p.15,p.16,p.22,pp.25-31,p.15.
(11)Antony Quinton,The Nature of Thing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3,p.119.
(12)Ernest Sosa,"The Raft and the Pyramid",in Epistemology:The Big Questions,pp.190-191.
(13)Laurence Bonjour,"The Coherence of Empirical Knowledge",Philosophical Studies,1976,30,p.286.
(14)Laurence Bonjour,"The Dialectic of Foundationalism and Coherentism",in The Blackwell Guide to Epistemology,Blackwell Publishers,1999,p.118.
(15)Alvin Goldman,"Bonjour's The Structure of Empirical Knowledge",in John W.Bender(eds),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oherence Theory,Dord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pp.106-114.
(16)Moser,Mulder and Trout,The Theory of Knowledge:A Thematic Introduction,p.85.
(21)(23)(24)(26)(27)Richard Feldman and Earl Conee,"Internalism Defended" in Hilary Konblith(eds),Epistemology: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Blackwell Publishers,2001,pp.233-236,pp.250-251,pp.249-250,p.234,pp.236-256.
(25)Richard Feldman,"Evidence",in Jonanthan Dancy and Ernest Sosa(eds),A Compantion To Epistemology,Blackwell Publishers,1994,pp.119-122.
(29)William P.Alston,"Goldman on Epistemic Justification",Philosophia,1989(19),pp.115-129.
(31)Alvin Goldman,Epistemology and Cogn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07.
(32)Susan Haack,Evidence and Inquiry,Blackwell Publishers,1993,p.149.
(33)Alvin Goldman,"Strong and Weak Justification" in Jack S.Crumley Ⅱ(eds),Readings in Epistemology,Mayfield Publisher Company,1999,p.394.
(34)John Pollock,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Totowa,Rowman and Littlefield,1986,pp.118-119; Ernest Sosa,"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Virtue",The Moist,1985(68),pp.224-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