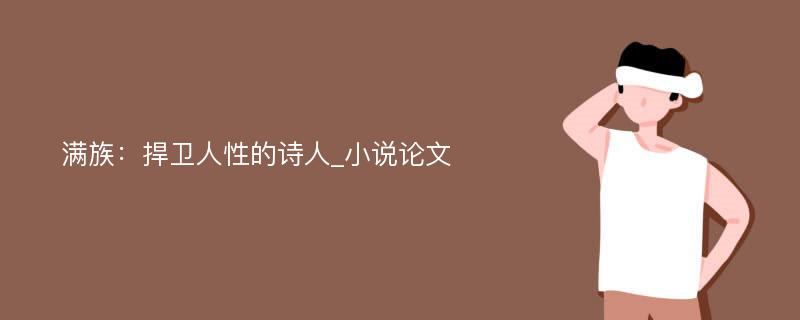
满都麦:捍卫人类天性的诗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性论文,诗人论文,人类论文,满都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满都麦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满都麦小说选》荣获了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举办的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充分证明了满都麦近30年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
作为一个蒙古族作家,满都麦的小说当然体现着蒙古民族的特色,独特的题材范围,独特的人物形象,独特的思想情绪。所以,有不少论者对满都麦小说的民族特色进行了探讨,得出很多真知灼见。有鉴于此,本文的重点不是谈满都麦小说的民族特点, 即不打算站在“我们”的角度谈“满都麦们”,而是企图从满都麦对人的关注入手来接近他的小说。
满都麦作为一个当代少数民族的作家,有着古今中外所有作家都有的庄重与真诚。在满都麦的小说中,人及人的尊严被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他并不仅仅是站在自己民族的角度说话,他是站在人的角度说话;他不仅仅是为蒙古族人说话,他在为全部的人说话。这样能更好解释满都麦小说所具有的影响力。当然,他说话的起点是他自己的民族,这是容易理解的。
对做人的正常权利的肯定与执着是满都麦小说中经常强调的主题。《元火》(注:满都麦:《满都麦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所涉及作品及其引文均引自本小说选。)是一篇亦真亦幻的小说。在好似虚幻的梦境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尊严的真实故事。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蒙古族人民的很多东西要被当作“四旧”什么的破掉,包括头饰、火镰等。但是,在蒙古族,由于历史、地理、气候等方面的缘故,这些东西已经和他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拥有火镰和头饰就等于是拥有了人的尊严,而失去这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人的尊严。正因为这样,25年之前,父亲冒死将这些东西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送到山洞之中,而父亲却在藏好这些后被冻死在卧牛石旁边。小说中的另一个线索是“我”与葛玛的爱情。人当拥有自己的爱情,但是,“我”当年和指腹为婚的葛玛野合被支左工作队的队长喝散,“我”和葛玛被关进牛棚,并且立即发出通知要开批斗会。葛玛逃了出去,却从此没有了讯息。25年后,“我”在一个山洞中发现了当年父亲寄藏的火镰和头饰,而且在这个山洞中,我也“发现”了葛玛。在“火镰之火点燃的篝火”的照耀下,洞穴中那些远古的壁刻也活起来了。“东侧洞壁上刻有野生图案,有鹿、狍子、盘羊、黄羊……而且成双成对地互相追逐交欢。在西侧洞壁上刻的则是蒙古包、勒勒车、牲畜,其中有座蒙古包没有毡幪,里边有干活儿的赤男和哺乳男婴的裸女。”小说以壁刻为手段,拉长了作品所表现的生活时段,加强了作品的涵盖性。远古的壁刻宣扬的是人的尊严,25年前父亲保护的是人的尊严,今天的我所找寻和虚幻中得到的,也是人的尊严。
《圣火》写了一个草原女性对人的尊严的守望。这个在13岁时就被喇嘛和大兵奸污的女性,难以在有情爱需要之后和心上的人成亲。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和环境,这个女性和心上人没有复杂的相爱过程。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那么纯粹。作品也没有猎奇性地渲染这位女性的屈辱遭遇。相反,作者在这篇作品中通过这位女性的眼光对男性美作了赞美性的描写。在这位女性看来,“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足可以扛走骆驼的壮士。是男子汉就应当是这样的。”这就够了。这位女性对心上人的爱,剔除了一切庞杂的背景,几乎是纯粹的男女之爱。但是无定的生活导致心中的壮士再也没有出现。即使这样,这位女性坚信心上人会来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等待。作品采用时空跳跃的手法,将故事写得非常具有沧桑感。作品不注重讲故事,而是突出一种情绪,突出一种信念,突出一种对人自身选择的坚定。与《圣火》相比,《三重祈祷》中的女主人公更体现着做人的尊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草原女性往往具有更深刻而悲惨的命运。这种深刻与悲惨主要是由于草原女性常常是无助的和孤独的,有时甚至连一个倾述的对象都难以找到。一生中,这个女性与三个男性交叉发生并保持着两性关系。这种畸形现象,既与一定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也与当时独特的社会现实有关系。应当指出的是,将这种沉重的负担压在一个草原女性身上,就显出这种背负的更加沉重。她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但是这一切不影响她维护自身的尊严。主人公将自身的沉浮起伏置之度外,她牵挂着自己的男人,但更挂念的是自己远走他乡的儿子。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让一个脱身于自身的人得到精神的关爱和护罩,这就是她的尊严。
满都麦小说中人物对自己的尊严的肯定与执着并不过分,都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方面,而在作品中又恰恰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才体现出这种肯定与执着的可贵。
与此相联系,对做人的正常权利的丧失或被剥夺的慨叹与愤怒也成了满都麦小说的一个方面。《在那遥远的草地》是主人公对一段情爱往事的怀念。作品一开始就做了深沉的表白,为全文奠定了基调。一个下乡知青,由于寻找自己的坐骑而与一位少女由相遇到相爱,但是这种爱并没有成为恒久的事实,而是成为永久的怀念。作品以富有深情的文笔,回想了这段往事,既是对纯洁情感的尊重,也是对遥远草地那位少女不无忏悔的尊重,深深的遗憾与默默的慨叹浸入骨髓。同样,《巅峰顶上有情歌》也写了一次敖特尔使得一对年轻人相遇并且相爱,本来约定来年相会,但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坐在高山之上唱起相思之歌。两篇小说具有相同的构思,相同的构思传达和强调着一个相同的意念:对应当拥有的东西的失去的怀念。两篇小说都不涉及太多的人物和故事,腾开笔墨非常专注地对人物及其内心进行描写和刻画。
如果说上边的作品是真情遭遇了阴差阳错无可奈何地失落的话,那么《雕龙玛瑙鼻烟壶》就写了尊严被强夺之后的回复。向来叙事沉稳很少玩什么表面技巧的满都麦在这篇小说中也搞了一次巧合。 当年的贵族子弟洛布森年迈之际在北京遇到了自己当年被当作“四旧”收缴走和无奈卖掉的鼻烟壶。这到底是生活中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小说通篇述说的是“是你的终归是你的”这一命题。这篇小说的心理刻画也非常好,语言特色是调侃之中寓庄重,庄重之中见调侃。庄重对应的是历史的必然,调侃对应的是历史的扭曲。《欠债人》将这种回复发展到了残酷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为黑色反革命的额尔德木特古斯为了得到一个红卫兵袖章而将众兴寺喇嘛朝尔吉暗杀。时事的发展,历史的前进,人性的醒悟,额尔德木特古斯认识到这是一个罪过。于是他通过喝酒麻醉自己。但是他终于觉得无法还清这个债而决定“以命抵命”。在小说的结尾,有一段沉痛而又庄重的描述,实际上是主人公内心最深处真情的流露。小说既反映了历史对个人的嘲弄,揭示了一种异己力量对人的左右;也写了人的觉醒,人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小说具有强烈的自我反省意味和非常的反省举动,额尔德木特古斯以自己的死捍卫了做人的尊严。
满都麦对人竭尽做人的义务进行了赞美。带有传奇色彩的《鹫雕岩上》就是这样。中纳顺的额吉得了癌症,据说“只有用鹫雕的心肝或粪便制一种药才能治好”,于是照日格吐等冒险到南山秃鹫岭获取这些东西,小说表达的主题就是友爱、团结、智慧、勇敢。 这篇小说总体上说还有概念化和公式化的痕迹,但是有不少细节非常精彩。小说故事完整、脉络清楚、用意明显,人物语言中也有不少直接点题的地方。《瑞兆之源》中艾德布为了寻找一股跑散的马儿,遇到了在边疆生活的苏布达额吉。作品既写了苏布达的警惕勇敢,又写了苏布达的热情善良。她不仅多年尽心尽力收养别人家跑散的各类牲口,而且关心每一个遇到困难的人。作品通过一个“饲养失散牲畜的”额吉,表达了做人的本分,“咱们蒙古民族穷得讨吃要饭也没有贪占别人东西的习惯”。作品还通过苏布达额吉表达了母爱主题。作品用笔专注,充满发自内心的深情,对人所具有而且是应当具有的友爱、慈善做了肯定和赞美。
《雅玛特老人》这篇小说非常专注地写了雅玛特老人。雅玛特老人是琼古勒峡谷中唯一一户人家的主人。这个老人放养着自己的山羊,也看护着野生的盘羊和岩羊。她以自己的生命热爱动物,包括野生动物。雅玛特老人孤独而又不孤独,她与动物构成了一种彼此依靠的关系。雅玛特老人和她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雅玛特老人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看护着一只一只的山羊、盘羊和岩羊,老人与动物之间发生了不少美妙的故事,老人也与动物一起经历了不少难以理解的遭遇。错乱的政治阻止了老人的慈善与仁爱。当历史艰难地翻过一页之后,老人坚决放弃了“五保户”的待遇,毅然重新回到峡谷,继续着她和羊儿狗儿的故事。小说包含着特有的痛楚与伤感,犹如一幅凝重的油画,为我们展示了草原深处的一段历史,一个饱经沧桑而又具有深厚活力的老人形象。作品语言非常细腻,处处体现着作者对草原生活的真切体察与准确把握和表现。
当人的本分和义务出现差错或者沦落时,满都麦毫不犹豫地要进行修复和批判。《碧野深处》写了号称“马上磁铁”、“马上阎王”的纳吉德马失前蹄导致小腿骨折。这种意外使他经历了更独特的一场遭遇:纳吉德首先是遇到了一只受伤的黄羊。纳吉德他企图将这只黄羊抓住,以此来平衡他因马失前蹄小腿骨折的心理。其次他又遇见了一大一小两只饿狼。纳吉德与黄羊一下子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相同的命运使得纳吉德重新认识了黄羊。纳吉德放弃了猎杀黄羊的想法,转而以自己的勇敢与强壮面对了狼。小说以一种特殊的安排让人处于与黄羊相同的位置,设身处地地想象野生动物的遭遇和“心理”,终于找到了与黄羊的一致之处。《马嘶·狗吠·人泣》中的白头老翁之所以选择葬身火海,一是对孥马殉情的回报,同时也是对现代文明的失望。白头老翁将对强占自己心上人的仇恨与毁坏桦树林的仇恨交织在一起。作品非常专注于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描绘与刻画,笔力集中,体现了凝重的批判与决裂。《四耳狼与猎人》也是对人的尊严的反面强调。当年巴拉丹为了卖钱而抓回几只幼狼。幼狼却把这当作是巴拉丹对它们的好心饲养。后来一匹幼狼生病,巴拉丹怕它死掉卖不了钱而在它耳朵上剪口放血,使这匹狼成为“四耳”。多少年后,当年被与巴拉丹同居的杭日娃女人偷偷放掉的“四耳”,在荒郊野外制止了一群饿狼对巴拉丹的围攻,回报了巴拉丹的“养育”之恩。小说以人们心目中凶狠恶毒的象征狼的善来衬托了人的恶。《夜茫茫,他在荒原上》写了一个身在异国的蒙古族学者,怀着对父母和故乡的怀念回到了草原,但是由于政治因素再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他不仅远离了自己的妻子,远离了自己的女助手,远离了自己的研究,而且被怀疑是潜入进来的特务。他对《黄金宫青史》的研究成果也变成了群专头头意欲掠夺的对象。他终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深夜,他独自一人爬行在草原上,是做人的尊严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生存欲望。整个作品基本上是对他一个人的描写,用大量的篇幅来对其内心做了细致的描写和展示。
与这一用意相一致,满都麦在小说中对动物临死时的描写也非常细致,而且是一往情深,意在唤起人们的良知。《雅玛特老人》中这样描写一只盘羊的被猎杀:鲜血顺着它那被枪弹击中的左前腿流淌下来。它摇晃着身子到了雅玛特跟前,像是给她看看伤口,突然一下子栽倒了。“我可怜的宝日呀!”雅玛特呼唤着它的名字扑了上去。额日和宝日转动着充满泪水的双眼,频频撅着嘴,仿佛在向老人倾诉着它的不幸。《巅峰顶上有情歌》也是这样描写盘羊的被猎杀:可怜的盘羊,仿佛要告诉他某种极为重要的事情,吃力地向他撅起抽搐的嘴唇,吭哧吭哧地喘息着,殷红色的鲜血从它腋下喷涌而出,染红了紫褐色的山崖……。《马嘶·狗吠·人泣》中对青羊被猎杀的描写是:终于在又高又密的莎草丛中,发现一只成年的母青羊受了重伤,两只花眼里噙满了泪水,卧在那里痛苦地嚎叫。看见白头老翁从马上俯身望它,便吃力地抬起头来,操起那个被青草的汁液染绿的尖嘴头儿,像是有什么重要遗嘱要留下来似的,朝老翁使劲地叫着。……青羊已经慢慢地咽了气,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它的那双牛犊一样的花眼睛,平时不论在何时何地,目光都是那么怯懦、柔和,而在这最后泯灭的一刻,却由于担惊受怕瞪得老大,形成了冷峻而严厉的定格,把它生命的弥留之际经历的最后情感:厌恶、愤怒和仇恨永远留下,闪着顽强的绿光,仿佛是要向皇天后土告状打官司,不打赢就死不瞑目似的。
老满的这些文字啊,动人心魄!
总体上看,满都麦的小说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赞美和歌颂,也有贬斥和批判;既有对美丽往事的怀恋,也有对冷峻现实的思考。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围绕人的尊严展开。像一个人地活着,这就是满都麦的理想与追求。正是这一理想与追求,和所有具有良知的人的理想与追求合拍,满都麦的小说获得了文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诗人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是随处都带着友谊和爱情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不管地域和气候的差别,不管语言和习俗的不同,不管法律和习惯的各异,不管事物会从人心里悄悄消逝,不管事物会遇到强暴的破坏,诗人总以热情和知识团结着布满全球和包括古今的人类社会的伟大王国。”(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第13页。)满都麦就是这样一个人之尊严的坚定捍卫者。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满都麦的小说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艺术特点,如单一叙写对象的设置,时空跳跃手法的运用,梦幻情景的使用,人物心理流程的展示,场面细节的出色描写等等,充分显示了满都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宽阔的现代视野。此外,郭永明(郭语桥)、色·钢土木尔、哈达奇·刚、曼德尔娃的翻译也非常出色,是他们无私的再创造让我们领略了满都麦的艺术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