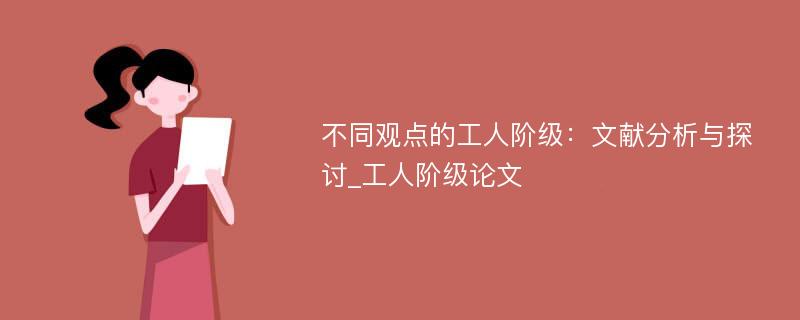
众说纷纭的工人阶级:文献分析与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阶级论文,众说纷纭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2)05-0212-08
改革开放是中国全新的现代化努力,说它是现代化是因为其核心内容依然是工业化,说它是全新的是因为此次现代化接纳了市场,使其成为现代化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的此种特征对我国的工人阶级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工人阶级的规模和素质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根据人力资源效用的不同而对劳动力的差别配置和回报,不仅在社会结构上分化了工人阶级,而且也在价值方面塑造了工人阶级的观念世界。现代化中的工人阶级引起了国内外学界极大的研究兴趣,本文围绕工人阶级变迁、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工人阶级形成三个主题,简明扼要的分析和评议现有的研究文献。
一、工人阶级变迁:地位与分层
市场经济的推进在不断的重塑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集团在市场机制的塑造下,根据其获得资源方式和占有资源多寡的不同,重新排列其在社会结构上的位置。工人阶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有优势地位的,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了哪些变迁呢?学界的研究集中在地位变迁和结构分层两个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导地位正在发生变化,由改革之前的虚化状态逐渐实在化。“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并未能真正落实。实际上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并没有达到理论宣传上所讲的‘水准’,因而显得有点‘虚’。”国企改革逐渐使企业获得独立的经济人格,也使工人获得自主性,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就是“以企业劳动者所有权代替国家所有权,劳动者首先属于自己,实现权责利上的完全个体到位”,由此可以说工人阶级的整体地位有明显的提高。然而工人阶级地位的变迁又是不平衡的,产业工人阶层与非产业工人阶层相比、普通职工与管理者相比、公有制企业工人与非公有制企业工人相比,在地位提高方面明显不平衡,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主体部分”与“非主体部分”在地位提高方面是不平衡的,“主体部分”滞后于“非主体部分”①。
对工人阶级地位的观察不能局限于内部比较,如果以其他社会阶层作为参照物将有不同发现。虽然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都从改革中获益,但是工人阶级却是获益较少的群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减少了,工人阶级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工人阶级并没有平静的接受地位的衰落,劳资冲突时显紧张,工人的抱怨、集体请愿、罢工、阴谋破坏乃至对管理层的人身暴力近年来频频发生。国家虽然颁布了保护工人阶级权益的法律,但是法律执行的效果欠佳,工人阶级缺少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不满。②显而易见,在工人阶级抗争与制度化接纳之间存在断裂,那么中国工人阶级不断发展的抗争性是否意味着严重的政治后果呢?答案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工人抗争的政治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律和制度问题,是否有行之有效的法律来保障工人阶级的权益,是否有制度性渠道来减少工人阶级的不满,从而使得工人阶级的抗争活动制度化,是决定工人阶级抗争的政治后果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工人抗争的影响力取决于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能力,然而由于工人阶级的多样性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内部冲突限制了集体行动的能力。
实证研究显示工人阶级内部冲突日渐严峻。改革以来工人阶级内部关系已不再是职工队伍内部关系所能涵盖得了的,“不仅过去在‘职工’队伍内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矛盾、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范围有所扩大,“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管理中户籍制度、工人-干部界限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又导致了新的矛盾的产生,即土生土长的城市‘职工’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间的矛盾。由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市场竞争,也导致了城市‘职工’与乡镇企业工人间的竞争和矛盾。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些矛盾关系,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社会转型及其所引致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不同部分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甚于计划体制内‘职工’内部各部门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③。由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客观存在可以想见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分化,学界的对此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工人阶级分层问题上。
工人阶级分层有两个问题值得争论:分层机制和分层状况。就分层机制而言,冯同庆认为是从计划体制中的行政规范性分层演进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开放性分层④。李路路则持相左的判断: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城市社会阶级阶层相对关系的再生产特征会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所谓阶级阶层相对关系的再生产就是指阶级阶层的继承关系占主导地位,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分布模式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社会没有出现社会分层模式的重组。“社会分层模式的再生产,产生于国家或权力优势阶层所主导的制度转型过程。政治权力、社会利益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相对独立于市场或经济机制,并与其相互作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主导力量在一个渐进改良式的市场化过程中仍将占有优势地位”⑤。李路路的理论针对性十分明确,工人阶级分层机制上不是市场独自而是权力和市场共同作用,并且主要是权力在起作用,这种见解得到了很多工人阶级分层状况研究者的支持。
由于研究者对工人阶级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不同,因此在工人阶级分层状况上学界有着不同的见解。郑杭生等学者认为工人阶级经历了阶级意义上的工人阶层、身份意义上的工人阶层和职业意义上的工人阶层三个阶段,故而当代工人阶级就是指在产业部门直接从事商品生产活动的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由于直接使用生产资料并从事商品生产,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占有相对较少的社会资源,相对其他阶层(如技术阶层、管理阶层)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受损更大。”以职业为基础界定的工人阶级在外延上就包括“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两个阶层⑥。陆学艺领衔的研究在工人阶级内涵和外延界定上与前者略有不同,“工人阶层是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直接操作生产工具,生产物质产品、提高劳动服务,或者为这些生产、服务提供辅助性帮助,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属于后者的群体。”⑦作者将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作为一个阶层看待,没有提出“在岗”与“下岗”的区分,但是值得重视的见解是认为制度转型带来了工人阶层由计划体制下的异质性到市场体制下同质性的转变,即同处于工人岗位的人员具有相同类型的体力和技能资源,不同所有制和城乡分割造成的身份标签趋于模糊;并且由于社会流动机会的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
由前面的讨论不难发现社会学家在论及工人阶级分层时,主动回避了“工人阶级”这个用语而代之以“工人阶层”,这就是把传统工人阶级中的普通职工作为一个阶层来分析,客观上是将其作为工人阶级来认定,却也不触动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概念。传统的工人阶级在内涵上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凭借体力和脑力劳动、以工资为基本收入的社会集团,在外延上主要包括产业工人、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是个身份未定的社会群体,所以工人阶级主要包括产业工人和国家干部。
沿用传统概念所内含的思路来分析工人阶级分层的研究,一般都是认为工人阶级有着多重的阶层,全国总工会1992年的调查认为工人阶级分成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四个部分组成,1997年的调查则认为有公务员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企业工人群体、经营者群体和下岗职工群体五个部分组成⑧。“群体”只不过是“阶层”的模糊性表述罢了,有研究者直言当代工人阶级存在党政干部、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普通职工等四个阶层。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掌握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始分散,经济资源落入经理人员阶层手中,文化资源落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手中,于是二者就与依然掌握着政治资源的党政干部阶层初成鼎足之势,构成了工人阶级的上层、中上层、中中层,而普通职工明显缺乏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就同这三个阶层拉开了差距,成为工人阶级的中下层⑨。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变化巨大,传统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趋于明显,将普通工人群体作为一个阶级看待,不只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当然将普通工人群体视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进而从事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比较,也是一种可取的研究思路。至于选择把普通工人群体视为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层,则取决于所研究问题的性质。
二、工人阶级意识:传统与新生
工人是否具有阶级意识以及具有怎样的阶级意识,是决定工人阶级是否形成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究竟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学界的研究发现,计划体制时期培养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没有消失,反而在市场经济中被激活,并且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构成要素。
阶级意识是先锋队政党和国家从外界灌输给工人阶级的,对于工人阶级自身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灌输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事后再发现的过程,即是在国企改制引发的抗争中发现工人使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动员,如李静君所言,当国家宣称阶级斗争的结束,并从官方话语中清除阶级语言的时候,“国企社会主义工人的阶级意识反而变得明显。”⑩陈峰认为工人抗争中诉诸的权利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利观念,然而这种集体体验还是有利于阶级意识的形成(11)。其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经验是阶级意识形成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只有当经济改革造成了剥削劳动力的市场,重构了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并激发了阶级冲突之时,潜藏在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中的认知资源才会被激活。”(12)易言之,只是当市场化改革将工人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即解除其工人身份的时候,工人的阶级意识才凸显出来,作为工人阶级存在的证明。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主人翁意识在工人非抗争性的社会行动中也明显的表现出来,传统的主人翁地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升华为自尊。尽管市场经济给工人利益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的自尊反而强化了,工人期望能够有自尊的生活和工作,所以虽然对社会变革不满却竭力自我约束、选择容忍,从自己出发调整同社会变革的关系,尽力化解市场经济给他们造成的冲击(13)。工人的自尊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中的“生存保障型”工厂政治密切相关的,国企凭借其资源保障工人利益进而培育了工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成为社会主义传统的基本内容,工人以此作为解释其生活境况的文化资源,相对于其他与之竞争的思想观念来说,社会主义传统在社会动员上显出了更强的力量(14)。
国家主人翁意识是存在的,并且是构成阶级意识的重要元素,社会学界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判断。吴清军认为当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包括认同意识和冲突意识两个维度:认同意识是对传统身份与权利的认同,还有对新时期国家政策赋予的权利与利益的认同;冲突意识则是直接指向企业管理者的。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在逐渐失去的体制身份以及与之相连的权利与福利的体验中,在国家政策赋予的新权利与利益的被侵害的体验中,产生了强烈的不公正感,进而意识到自己与其他社会群体存在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形成区别于其他阶级阶层的利益共识(15)。由此可见,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法律和社会政策的促使下完成的,所以工人阶级虽然获得了不同于计划经济年代的阶级意识,但是这种阶级意识受到了“市场霸权”的塑造(16)。
如果说上述分析体现了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传统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观念结合起来的努力的话,那么徐小洪的研究则体现了探索工人阶级意识新趋势的努力。徐小洪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多种形态的,它与历史、人文环境密切相关,也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既不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式的阶级意识,也不是计划经济中那种国家主人翁意识,而是权利、法治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互利合作意识。“合作、互利、建设意识,它区别于资本主义时期的革命意识;主体、自主、权利意识,它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固定工制度上的阶级意识。简单地说,就是在权利基础上的合作意识。现实中的工人群体已经逐步形成这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工人阶级意识。”(17)
党史学界则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当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一方面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阶级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了嬗变,嬗变的核心是“以经济为本、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日益觉醒和发展,追求物质实惠,实现个人价值取向日益明显和强化”,这是对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旧价值观念的变革和更新,主流是进步的;另一方面嬗变的过程尚未完成,且嬗变有矫枉过正的趋向,表现为将对某一价值的否定上升为对整体价值观的否定,将追求的某一新价值观念上升一种根本价值观,所以工人阶级自身无法形成新的阶级意识,必须坚持从外部灌输的立场,强化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社会主义信念和集体主义原则,在继承与变革中构建当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18)。党史学界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中的工人阶级的新阶级意识正在生成,另一方面因其遵循国家主人翁意识的标准,因此呼唤一种与现状不同的、符合工人阶级历史地位和使命的新阶级意识。
学界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当下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人政治意识“碎片化”(fragmentation),换言之,工人不再以传统的阶级分野为基础来形成政治意识,而是以社会转型带来的焦点问题为基础形成政治意识,于是形成了工人政治意识多元化的状态。工人政治意识“碎片化”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工人没有系统化的阶级意识,但在焦点问题上能够形成一定的共识;二是即使在焦点问题上,工人不同群体也难以有统一的意识。
黄岭峻以工人平等观为研究对象,发现了国企工人对不平等的拒绝。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权利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损害了工人的权益,所以工人拒绝不平等,这种拒绝不是对不合理的不平等的拒绝,而是对所有的不平等一概拒绝,特别是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权利不平等分配,妨碍了工人解决利益诉求的渠道,使得工人对公正的不平等失去信心,进而出现了否定市场经济的极端情形(19)。刘爱玉则以身份认同为研究对象,她发现以往相对统一的身份认同开始分化,地位期望和高低成为划分工人阶级的重要因素,普通工人各个方面的地位期望与评价最低,管理人员各个方面的地位期望与评价最高,技术人员居中;工人阶级开始和较低的地位联系起来,地位较低的普通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显著代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工人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尤其是对管理人员属于工人阶级的认同很低,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开始主动或被动的剥离出工人阶级范畴。(20)李培林领衔的研究同样揭示了工人内部的分化问题,针对“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一设问,发现越是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士,对单位内部负责人与普通员工的关系越是悲观,而越是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士即那些越可能具有负责人身份的社会阶层,态度就越是乐观。这就是说工人内部不同阶层在同一问题上意见比较分化(21)。
工人政治意识的碎片化应该是事实,碎片化究竟是阶段性的现象还是一种发展趋势尚难定论,但是国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将十分关键,如果国家不能妥善的维护工人的权利,那么工人“碎片化”的政治意识就可能聚集在一起,由一种分割的状态依照某种逻辑叠加在一起,进而结束“碎片化”的状态,最终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
三、工人阶级形成:国家与市场
改革对工人阶级的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基于身份概念的工人阶级急剧的分化,传统产业工人的轮廓逐渐清晰,开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集团存在,另一方面则是规模巨大的农民涌入城市并在各种产业中从事劳动,从而以农民工的身份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工人阶级结构的变迁在形态上呈现出多么复杂的表象,现象的背后则蕴藏着工人阶级形成的问题,在理解阶级形成时存在两种理论视角:一种看重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影响,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一方面是传统国企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农民工锻造为新工人(22);另一种注重国家的关键性作用,认为尽管新的阶级和阶级关系正日益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但是国家在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中仍然扮演着如同在毛泽东时代一样的决定性角色,市场经济导向的仍然是国家力量主导的阶层分化的社会(23)。当前海内外学界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争论,基本上都可以纳入到市场视角或者国家视角中进行分析和评价。
潘毅以农民工为对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她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变革过程中,阶级的形成与解体过程同时存在。大量的农村青年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打工阶级在结构上形成了;但是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以及对阶级话语的警惕、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对阶级话语的压制、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排斥等因素造成农民工在工人身份认同与农民身份认同之间模糊不清;故而打工阶级一开始就处在多种力量共同构筑的结构性压制之下,阶级主体本身无法言说,整个社会也对此议题普遍失语。“然而,尽管一个有组织的打工阶级的形成道路受到阻塞,但是一有机会,打工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罢工等集体行动。在对抗性集体行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日常生活的抗争”(24)。简言之,中国的打工阶级正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今天挣扎出世,它不是抽象的形式而是“行动者的回归”。潘毅的研究视野开阔,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全球化、国家行为以及相关的制度结合起来,揭示出了一定结构性条件之下工人阶级的艰难处境。
与农民工不同,传统产业工人在国企改制中实现了转型。此种转型是在国家推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力和利益的被剥夺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共同促使下的阶级再形成。为了置换工人的身份和保障市场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国企改制一方面取消了工人在单位体制下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则通过法律和政策赋予工人新的权利和利益,但是新的权利和利益由于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的阻碍未能实现,于是工人的权利和利益事实上被双重损害。正是在制度赋权与侵权的过程中,而非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过程中,工人获得了共同的经历,在制度变迁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共同促使下工人形成了新的利益共识和群体认同,实现了工人阶级在市场社会中的再形成(25)。制度及其变迁是国家影响工人阶级形成的基本方式,考察界定工人阶级权利与利益的制度变迁自然是分析的切入点,但是制度变迁往往是多个制度相互联系着进行的复合的变迁过程,所以对于制度变迁与工人阶级再形成之间关系的考察,特别需要从制度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来考察其与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关系,而且这个考察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要解释制度变迁对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要解释工人阶级再形成对特定制度的影响。
如果从系统的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审视工人阶级形成,那么就难以得出工人阶级再形成已经完成的结论。许叶萍、石秀印认为“工人已经处在客观剥夺状态,但是阶级意识形态尚未形成,资源贫乏则限制了他们的组织和行动”。在这个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并不‘愿意’、也并不‘主动地’形成阶级,而是愿意和主动地‘不形成阶级’”(26)。当前工人在劳资纠纷中的行为具有低目标性、高风险回避、中等合理性的特征,工人行动绝大多数是在体制之内的。工人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转换,首先取决于工人所遭受剥削的程度是否严重到威胁其生存和就业安全,其次取决于资方或是国家对其要求的回应。如果所受剥削主观感受并不严重,或是虽然很严重,但是国家能够对此积极的回应,建立一套制度用以平衡劳资关系,缓解工人所受的客观剥夺,那么工人就保留在体制内不形成阶级;如果工人感到被严重剥夺,国家不作为进而堵塞了制度内解决问题的渠道,那么工人将在体制外开展抗争活动进而形成阶级。要言之,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推进制度变革,以提供协商工人利益的渠道。
其实国家早就具备控制工人动员的劳动体制,特别是对工人的组织方式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一个预先存在的(即先于工人动员)、能有效控制工人组织行为和动员方式的劳动体制,使得国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处在能够先发制人地制约工人行动的有利位置,而国家对这一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则进一步提升了国家限制、化解和防范工人动员的能力,或者说降低了工人动员的能力。”(27)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中国形成超越经济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还颇为遥远,因此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存在一个在体质内外进行转换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既然并不存在一个国家制度控制之外的工人阶级,又何谈将其体制化呢?事实是国家正在竭力控制组织化工人的出现和发展,其途径就是通过国家的劳动立法主动保护工人的权利,从而一方面使国家政权免于成为工人直接抗争的对象,另一方面不断的将工人个体而非阶级整体纳入现存体制。
四、总结与讨论
当前学界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变迁、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比较关注国家与市场两个要素;将工人阶级置于国家——市场的二维空间中来认识和理解当然是深刻的,但是还不完整,因为在浸染于市场经济之前,工人阶级曾长期存在于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单位制企业中,彼时的产业工人都是国家职工,工人阶级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身份。阶级经历是塑造工人阶级的基本力量,恰如汤普森所言“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唯一的定义”(28),所以研究工人阶级必须将工人阶级自身的历史经历考虑进来。
历史经历在现象上表现为工人阶级曾长期生活于单位制企业中,但是其内涵则是一种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特定关系。美国学者魏昂德很好的诠释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特定关系,他认为革命创造和塑造了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打断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形成过程,国家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就在中国制造了新的工人阶级,也就是在公有制部门工作的工人阶级,在就业压力下国家推行的城乡分割政策又使得工人阶级成为一个依附于国家的封闭社会集团。简言之,中国工人阶级在结构上的形成不是市场塑造的结果而是国家政策塑造的产物,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与政治判断,越来越多的是来源于党的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29)。
应该说单位制企业中的工人阶级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工人阶级,它不仅依附于国家,接受国家灌输的意识形态,而且借助于单位体制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工人阶级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经历、意识形态及其同国家的关系,不会在市场经济时期自动的消失,而且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就对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工人阶级关于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记忆将顽强的保存下来。当然,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自构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深受意识形态霸权的塑造,所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能在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冲突与调和中形成,而正是这种冲突与调和孕育了工人阶级的自主性。此种自主性的实质内容是指工人阶级在思想观念上相对国家的独立性,可以肯定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工人阶级的存在形式、行动空间,进而塑造工人阶级的未来。
注释:
①(18)刘卓红等:《现代化建设主体》,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3~146页,第181~184页,第275~289页。
②White Martin King,1999,"The Changing Role of Workers",In Goldman Merle and MacFarquhar Roderick ed: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73-196.
③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1997中国职工状况调查·综合卷》,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④冯同庆、许晓军主编:《中国职工状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5~48页。
⑤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⑥郑杭生:《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⑦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⑧全国总工会编:《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工人阶级》,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44页;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1997中国职工状况调查·综合卷》,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年,第131~133页。
⑨邵慧萍:《当代工人阶级内部分层》,南宁:《经济与社会发展》,第4卷第7期。
⑩李友梅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11)Chen Feng,2003,"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workers' resistance in China",Modern China,Vol.29,No.2:pp.237-262.
(12)Lee Ching Kwan,2002,"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Theory and Society,Vol.31,2002:p.191.
(13)冯同庆:《企业改革中个人的自尊》,北京:《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4期。
(14)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北京:《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5)(25)吴清军:《国企改制与传统产业工人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2~168、36页。
(16)Marc Blecher,2002,"Hegemony and workers' politic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170:pp.283-303.
(17)徐小洪:《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阶级意识研究》,北京:《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第21卷第1期。
(19)黄岭峻:《当代中国国企工人平等观辨析》,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第19卷第5期。
(20)刘爱玉:《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福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21)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3~105页。
(22)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63~191页。
(23)Alvin So,2003,"The Changing Pattern of Classe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33,No.3:p.364.
(24)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广州:《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26)许叶萍、石秀印:《工人阶级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转换》,南京:《学海》,2006年第4期。
(27)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形成》,北京:《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28)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前言。
(29)Andrew Walder,1984,"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1949-1981",Modern China,Vol.10,No.1:pp.3-48.
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