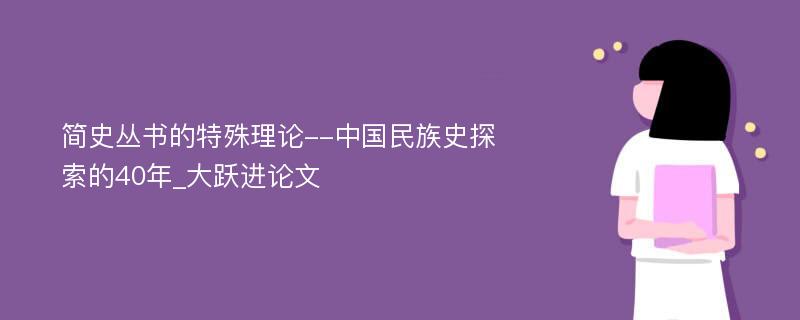
简史丛书非凡说——中国民族史探索4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史论文,中国论文,非凡论文,丛书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13(2001)01—0056—04
1954年考大学时我选择了历史学,1956年大学分专业时便选定中国民族史,195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全国人大民委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俗称“云南组”,下同)治彝族简史;从此我的命运便与中国民族史连在一起。以下问世的一些文字:《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下同),《彝族简史》(参编,1983),《基诺族简史》(1985),《探索历史法则的足迹》(1986),《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1996)第四章《中国古代民族问题历史述评》,《基诺族文学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对彝族主要源流的商榷》(以下为1962年后十余种社科期刊发表的论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与凉山彝族的奴隶制》,《云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复辟的历史教训》,《越过奴隶制是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吗》,《元代罗罗斯土官的建置与评价问题》,《元代罗罗斯土官宣慰使研究》,《元代云南的土官制度》,《土官职称及其演变考释》,《明四川行都司土官未因元制考》,《土官与土司异同考略》,《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忽必烈与云南》,《兀良合台出师安南考》,《试论〈大理战书〉》,《〈大理战书〉与朱元璋的平滇国策》,《攸乐(基诺)人解放前的社会历史初探》,《基诺族文化特征与氐羌的渊源分析》,《攸乐城遗址——清朝治理南疆水平的历史座标》,《傣族农奴制与西欧农奴制比较》,《中国古代史分期与农奴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个性问题初论》,《文明时代始于农奴制者比始于奴隶制者多》,《云南成文史发展特征探讨》,《跨时代历史跳跃——贵州民族历史的发展特征》,《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略》,《中华民族凝聚力树状结构说》,《中国古代民族问题两大类型说》,《宏观综合研究与中国民族史学》,《共时态宏观规律现象——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试论历史规律性与异变性的对立统一》等,就是笔者在中国民族史学领域不断探索中留下的较明显的足迹。
以上文字问世的原由,主要是时代或社会需要。如《彝族简史》在1958年就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俗称《简史丛书》,或简称“简史”,下同)中的重点书。20世纪80年代初,该丛书又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以下简称重点项目)。《基诺族简史》亦属重点项目的简史丛书之一。其它书文虽非重点项目,其面世的主因仍在时代需要。书文问世的主因之二,在于该史域的学术内涵异常丰富,尤其踏入史苑面对的彝史犹如学术迷宫,一旦入门就令人流连忘返,这也构成笔者治民族史的原动力。如《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一书,讲的是元代今凉山彝州一带的建置沿革,事体本不算大,但它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魏源《元史新编》、柯劭忞《新元史》中竟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本人自知功力浅陋并无匡正古史大家巨著的奢望,只因写到元代凉山彝族史时感到无所适从,不得不在拾遗补缺上多下笨功夫,加上留心实地考察,尤感李绍明同志的关助,才使这本小书有了问世的可能。为求其考据无误笔者曾将该书呈古文大家四川大学徐中舒教授指正,徐先生的谆谆面教与精辟点批令人难忘,但书中并未给予铭谢,这也反映了十年浩劫不久的敝人的大文化水准。前述滇川黔等地史文,包括奴隶制、农奴制等多篇文字,约占如上篇目的一大半,都与治彝史有关,因为彝族分布于我国西南诸省,直至20世纪中叶仍存在农奴制、奴隶制与原始村社,故我不得不潜心于这一史学领域,更对其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进行考察。1979年《云南蒙古族简史》的问世亦与元代彝族史研究的投入有关,还涉及学人的学术良心,其简单的理由是:正因忽必烈平大理国才使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然这伟大贡献并未使云南通海县聚居蒙古人的地位有所改善,反因其不具备作为民族依据的民族特征四要素而难以正式确认,历史与现实的如此不和谐加上通海蒙古代表人物的敦请,才促使笔者投入几年心力,包括实地访古中得到不少可贵史料,加上某种机遇才使之顺利出版。谁知这本小书竟成为确认云南蒙古人族籍的“身份证”,元蒙史学界的反映亦颇佳。本人对基诺史的调研始于1958年,2000年节为期一月的调研已是对其第23次的持续考察,这也与彝史攸关,因为人们原以为基诺人近于彝族,如得到证实将使彝族简史中的原始社会大为增色,这便是作为彝族分组成员的我于1958年奉命识别基诺人的动因。由此可见,笔者所以能在40多年的中国民族史苑留下一点足迹,在于时代需要的研究方向与引人入胜的史学资源,其中也包涵个人的孜孜求索。
治史40多年的以上概说,可见本人与民族史有缘,才学有限却尽心尽力,似可说是无愧于时代。耳顺之年后精力有限,不宜再开拓新史域,但愿在多年史学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一点必要的再研究而已。尤其近年的著述中对简史丛书任意贬煞的现象出现后,更觉此事非同寻常,有必要进行认真反思。如有位先生的大作中称:55个民族简史问世忽略了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深感“困惑”云云。此说措词委婉,却关系简史的命运,因为这一“困惑”本身就意味着简史存在价值的动摇。任意贬煞简史丛书的代表作是一个大部头,可谓之民族学“专史”(注: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著:《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被列入该书第七章“‘反右’斗争和‘大跃进’中的中国民族学”的“第三节”。见第193页。), 它竟直接将简史丛书与“大跃进”连在一起,在章节结构与史料选材上精微地将其描绘成“左”的怪物。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还利用特殊条件下的名人之言作为简史的盖棺定论,从而把简史的学术价值抹煞殆尽了。因此论者从总体上否定简史丛书,故可称之为简史无用说,或简称无用说。
无用说的出现与近50年来的历史大背景有关,也有中国民族史学发展方面的非常原因,尚需专题研究。但需指出的是,其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宏观史角,忽略基本史实,为了阐明吾人的观点,也思考了一个与无用说相对的概念:简史丛书非凡说,或简称非凡说。非凡说的主要论据,有以下三点。
1、 简史丛书是非常时期的民族史学人对中国民族史学的非凡贡献。中国古史文献浩如烟海,1958年前也曾有中国民族史类的书问世,但它们只能反映一部份文献记录较多的民族史,不能反映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历史,而1958年开编的简史既利用了过去的文献资料,更在实地收集近现代社会经济历史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简史的出版计划,这理应是中国民族史学前所未见的功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曾打乱国人的正常生活,“左”的潮流泛滥,民族史学人虽莫能外,但却以简史作为部门“大跃进”的标志,进而集结众多人力物力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民族社会历史调研,在非常时期从事了一种大体上属于民族史学的科研事业;其间虽历种种“运动”乃至浩动,但终在30多年后大功告成,这理应是对中国民族史学难能可贵的贡献。
2、简史丛书奠定了现代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根基。 中国民族史学的根基雄厚,大致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为底层,主要由1900年前的史学文献构成,其量与质均可称世界之最,过去已在其基础上写出许多著作,今后还会从中概括出许多新著,但它总体上属于中国古代民族史的范畴。第二层为中层,简史本身包括为写简史而收集的各民族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大量资料,就构成了中层的中坚;当然,它还包括1956年“抢救落后”中收集的大量资料,以及1949年前留学回国的民族学者留下的民族志资料等,这一层次的文献与国际不同学派相关,故可与世界历史接轨,构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研究的根基。其所以如此的一个根本原因是,50年代的民族社会已成历史,不能再复活。中地办曾通令各省市(州)编写地方志应以民族简史为准表述民族史问题,非常重视简史丛书,把它作为修志的重要依据。当然,简史丛书开编于非常时期,且无先例可寻,质量不理想是可想而知的,但它的问世仍在总体上为较高质量的中国民族史问世提供了条件。55个少数民族简史的面世,对进一步推进更高质量的科学的中国或中华民族通史面世打下了基础,这种55个少数民族史与中国通史、通志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似应是中国民族史学健康发展的一种过程。这也是55本简史奠定了现代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根基的史学方法论方面的原因。
3、简史出世过程反映了中国民族史学的非凡特性。55 本简史的出世过程各有千秋,本人无此全面实践又不曾进行认真研究,不敢妄言其精微,但就笔者以彝族分组组长主持编修过的彝、白、哈尼、纳西4 本简史言之,(其涵盖人口700多万,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1/10强)言之,也可发现一些端倪。其中首先应当说明的一个基本史实是,简史开编至出世的关键时期在1958至1964年,前期仅彝族简史就在不断编修中出过油印稿两次,铅印稿两次,1983年问世的彝族简史只是在原第二次铅印稿基础上的再次增修。前述本人40年治史概说亦证明,正是1958至1964年的治简史奠定了笔者的史学根基。而1958至1964年恰是“大跃进”至“四清”运动前的七年,“左”的运动曾危及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简史又何以能在此时从事研究性编写呢?这就自然成为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应当承认,简史开编七年间曾因“运动”付出许多无效劳动与时光,但如进行具体分析,这只是治简史大环境的一个方面,它所占时间的比例还不太大。据个人所知,因应“运动”的经验有如打太极拳,“运动”高潮时我即柔性后退,因为这是人力无法抗拒的,但“运动”退潮时我即柔性前进,来潮时更作退进自如状,这整个过程宛如太极拳的柔性圆运动,而其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治简史,这才是非常时期七年间大部时间与精力的主要投向。此过程可称之为太极柔中,或简称柔中法。此法看似平淡无奇,但它在利用“运动”机遇时表现出的能量却很不寻常,如:1959年我任彝族分组组长不久即从宏观史学角度提出考察四川凉山奴隶制的构想,具拟了调查提纲,其理由就是提高彝族简史的学术质量,经云南组领导批准并拨发经费后,组织了包括吾师杨堃(1901~1998)、方国瑜(1903~1988)等滇川北京20多位学人,于1960年1—2月间实施;有关此次调研成果已载于作为重点项目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方国瑜先生事后出版的《彝族史稿》亦因此次调查而得益,全体参与者皆因此次考察而各有所获。可以反映柔中法能量的另一例,是本人1962年筹划并主持的对滇西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与永宁摩梭人(民族识别中归纳西族)母系家庭两个专题的考察,此事所以跨越了彝族,是因1960年大学师生返校,调查组人员大减,原来单独分组的白、哈尼、纳西三族简史归属彝族分组,故作为分组组长的笔者便提出此次区域性跨族籍的专题考察计划,其实施理由也就变为提高编写彝语支诸族简史的学术质量;彝族分组成员大部分参与了此次调研,时间短则数月,长则一年,事后出版的民族调查资料上百万字,有关专著亦近百万字,即使非常时期的此次考察有种种局限性,但其调研成果的宝贵价值是众所周知的,并从调研方法论方面所提供的经验,包括柔中法在非常时期释放非常能量的经验,都是中国民族史学史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可以反映柔中法力度释放方式的另一例,是不计门派容纳诸家的开明或开放性,如云南组领导为提高彝族简史质量于1959年礼聘国内专家方国瑜(云南大学)、冯汉骥(四川大学)、马长寿(西北大学)等发挥专长,参与调研,结果方、马二位先生各写了数万字的彝史文稿(即时油印刊出事后均在增修后以专著形式公开出版),从而为开编不久的彝族简史提供了两种借鉴稿。冯汉骥先生则对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进行了考证研究并写了论文发表,为简史利用考古资料提供了可靠依据。杨钊(北京师范大学)、宓宪澄(贵州民族所)、宋蜀华(中央民族学院)、张传玺(北京大学)、钱安靖(四川大学)、木芹(云南大学)、李绍明(四川民族所)等专家为提高彝族简史质量而尽心切磋的神情,至今令人难忘。据笔者难以完全的记忆,为彝族简史编写作出过贡献的同仁有:杨堃、方国瑜、冯汉骥、马长寿、林耀华、马曜、侯方岳(云南组实际领导)、莫扬、谭碧波、耿正果、费明辰、李埏、王宏道、缪鸾和、杨钊、宓宪澄、张正东、熊锡元、马忠民、金国富、刘尧汉、王叔武、宋蜀华、吴恒、钱安靖、萧远煋、苏夏、柳春、朱宁、李克珍、张传玺、官开甫、汪宁生、梁冠凡、赵廷光、韩忠、韩公仟、陆思明、陆惠英、白章富、刘德超、关梁、邹世恒、朱宝田、曹成章、徐柏操、桑耀华、詹承绪、杨万全、严汝娴、木芹、徐文德、李绍明、杜玉亭、邵献书、张恩耀、李忠明、李兴唐、李壮伟、李方、罗承伦、齐廷槐、朱惠荣、葛绍英、孙代兴、夏肇勋、周裕栋、王树五、张群辉、张青、赵玉池、匡世昭、王寅生、黄吉可、周泮池、王承权、杨宗德、张灿庚、余文松、戴开威、赵家发、汤正彪、李凯、蒙绍禧、刘茁生、黄志绂、黄美椿、谢世宗、张清润、颜怀德、杨运东,等等。为一本简史而借用国内诸家这么多人才,并大体做到人尽其才,这对过去说是史无先例,即使40年后的今天也难以如期。还需在此一说的是,太极柔中的张力不限于治史,也延及人际关系,如:彝族分组有二位先生在“运动”中被戴上不同的“帽子”,作为组长的本人却待如师友,充分发挥其专长而对其“帽子”视而不见,还适时帮其中一位摘掉了“帽子”,故能成为忘年之友。类似事例还有不少。足见太极柔中无论在学术还是在人脉上,都曾在“运动”磨难一面的背后营造了一种近于智慧的超常境界,从而在非常时期增进了民族史学子的学业,提升了简史质量,实现了学术对“运动”的总体超越。这或许就是中国民族史学人在漫漫非常年代表现出的一种史学传统特性。
非凡说的以上三点论据,皆由客观史实构成,有的是个人亲历,亦具人证物证。如看了此节再审照本人主持编修过的彝、白、哈尼、纳西4本简史与个人编著的《基诺族简史》,那么, 人们就会在实事求是的中允间发现这五本简史各有特色,也各有其学术内涵,因此就不会为它们的存在感到困惑,也不会生发出“谁也不看”的无用说,(注:王建民、张海洋、 胡鸿保著:《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被列入该书第七章“‘反右’斗争和‘大跃进’中的中国民族学”的“第三节”。见第202页。 )更不会视之如“大跃进”时代的怪物。一句话,非凡说用确凿的史实对无用说进行了质疑。当然,不可否认,“专史”的无用说也是事出有因的,特别是它充分利用了“大跃进”时期的许多材料,不仅皆有出处且非常生动,但这些典型材料多为表现“运动”高潮时的一面,它们被利用得越多越动人,就越发使得简史近似全国共性的“大跃进”,以致体现简史个性的一面被埋没殆尽;结果,构建无用说的“专史”也就不能不失真了。这里还有必要就简史的两个基本史实略加说明,其一是简史出世时间:整套丛书从开局至出齐的时间是1958年至1985年共27年,扣除1964年至1978年停编的14年实为13年,单本简史的时间投入是1958至1964加公开出版前的约二年修定,凡8年,扣除其间“运动”的支出约1年实为7 年。简史的第二个基本史实是参与者出处与时间投入,其特点是方方面面的参与者多,而全程投入者少,如彝族简史上述90余位参与者中,大学师生约占一半,此外的各方协作者约占四成,构成云南民族调查组的实体方人员约占一成(包括中科院民研所与云南方人员),他们参与彝族简史的时间分别是:一年以内者70多人,(注:参与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还有四川组、贵州组及广西组的“大协作”者20余人,此处未计入。)二年者15人,三至四年者7人,全程参与者只笔者1人。以上两个基本史实亦是简史丛书的两个基本概念,或其个性史,自是研究简史丛书中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但“专史”无视简史的这一个性,任意将其塞入“大跃进”的共性框架,(注: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著:《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被列入该书第七章“‘反右’斗争和‘大跃进’中的中国民族学”的“第三节”。见第193页—202页。)这样,也就使得“专史”自身难以成其为信史了。“专史”的同类问题还表现在民族识别上。大家知道,中国民族识别的起止是1953至1979,凡26年,这就是民族识别的基本史实或其个性史。当然,学界至今仍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方主张民族识别尚未完成应继续进行,因而就坚持已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另一方则主张民族识别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告完成,进而认为它在实践与理论上均遇到许多新问题故不应再坚持昔日的刚性理论。但“专史”不顾学界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忽视民族识别的个性史,而将其定位于1953至1957凡4 年的章节框架。看来,这不仅涉及治史通则,还涉及了门派问题,因为“专史”的民族识别论属于某家几十年一以贯之的理论模式,它的被打破无疑如某家内部门庭大乱,怎么得了?回思40年前治简史不计门派容纳诸家的境界,再看看今日“专史”的治史误区,特别是将简史丛书的学术个性抹煞于非常年代“左”的共性之中的似是而非,难道不应作为中国民族史学史中的一种非常情结,加以认真研究吗?
【收稿日期】2000—0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