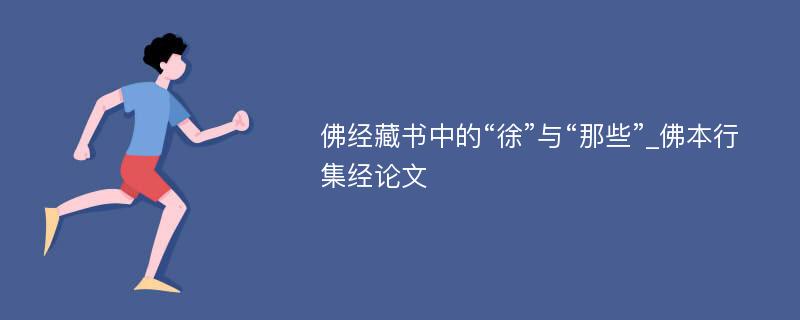
《佛本行集经》中的“许”和“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1《佛本行集经》,隋·阇那堀多译。阇那堀多(Janagupta),北印度犍陀罗国人,公元523年生,幼年出家,公元559-560年至长安,止于草堂寺,以后渐通汉语,应周明帝之请,为其翻译佛经。公元585年至洛阳,继续从事译经事业,公元600年逝世。生前共翻译佛经39部191卷,是隋朝重要的佛经翻译家之一。《佛本行集经》是其译经中重要的一部。
1.2隋到唐初,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可能既包括基础方言的转变,又包括语体的改变),语言中出现过错综复杂的变化,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这个时期的口语文献稀少,又使我们无法作深入的研究。佛经文献因其性质决定,应该是比较接近口语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佛本行集经》的语言,颇有那个时期的特色。例如,处置式中介词已开始用“将”,“把”仅见1例;动补式已开始使用,“得”、“却”已有了状态补语的用法,"Vt+O+Vi"格式也同时使用;结构助词“底”还没有出现,却可见其他词语用法上呈现向结构助词发展的趋势。从这些语法现象看,《佛本行集经》的语言应是早于唐代,但又不远离于唐代的。换言之,说它是隋朝的作品,应当是可信的。因此,我们希望《佛本行集经》能够弥补中古后期到近代前期汉语文献的不足,通过对它的研究了解这个时期的汉语概貌。
1.3以上我们说过,《佛本行集经》中结构助词“底”还没有出现,其中使用的类似结构助词用法的词,有“许”和“者”。本文将介绍《佛本行集经》中“许”和“者”的用法。
二
2.1.1“许”在《佛本行集经》中类似结构助词的用法主要用于代词之后,使用的格式多为“代词+许”,也有“代词+许+名词”。
(1)此象谁许,欲将何处?(一三)
(2)此一封书是汝释种摩那摩许,遣我送来。此一封是尼娄驮许,此一封是难提迦许,此一封是拔提伽许,此一封书是难陀许,此一封是阿难陀许,自外诸书各各是彼诸释种子,寄与汝来。(二七)
(3)汝等当知,彼罗刹女,不久应来,或将男者、或将女者,显示于汝。……汝等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许,我非彼物,非我男女。(四九)
(4)又时夜渴,见他澡盥,谓言自许,遂取而饮。(五五)
(5)希有我子,大有福业,从生已来,所作饮食,色香味具,倍胜他许。(五八)
(6)汝不知乎?从来为此摩尼娄陀所造饮食,恒常十倍胜他人许。(五八)
(7)若无因缘,自许眷属,犹不亲近,况复他人。(二一)
(8)自许左右,及眷属等,悉舍魔王,诸方奔走。(二十六)
(9)犹如童蒙小儿辈,戏于自许粪秽中。(二十八)
(10)我今宜以自许报身,往见世尊。(三十八)
(11)自许左右,及眷属等,悉舍魔王,诸方奔走。(二六)
(12)我等亦为此朋友故,亦复各为自许物,来此林内,求彼淫女。(三九)
2.1.2“许”的上述两种用法也见于其他魏晋译经中:(注:以下5个例句转引自梁晓虹1994。)
(13)龙王明日现,来与王相见,语王:“王有大恩在,我许女昨行,为人所垂,得王解之。”(《旧杂譬喻经》下)
(14)彼等谁最在前出者,即去上衣自恣著而已,随意而去,亦不专求自许本衣。(《起世因本经》)
(15)中靥有一鬼,担死人来著前,后有一鬼逐来嗔骂前鬼:“是死人是我许,汝何以担来?”(《众经撰杂譬喻经》)
(16)此诸宫殿,玉女营从,尽是我许。(《出曜经》)
(17)“识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识。”因指北壁有一囊挂锡杖及钵云:“此是杯渡许,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著函中,别有一青竹杖。”(《高僧传》)
这些“许”字的用法和《佛本行集经》中一样,也都是用在“名词+许/名词+许+名词”两种格式里。
2.2.1以上两种用法中“代词+许”的一类,尤其值得重视。在现代汉语里,“代词+的”表示领有,是“的”字的功能之一。但在古汉语中,“者”和“之”均无此功能,直到唐代以后,“者”才出现了类似用法,(注:以下6个例句转引自冯春田1992。)如:
(18)麦地占他家,竹园皆我者。(《寒山诗》)
(19)休佑以己手板托言他人者。(《酉阳杂俎》)
(20)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客。”即取自己者食之。(《幻异志》)
(21)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黑而加文,竞不知是何祥也。”(《开天传信记》)
(22)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唐国史补》)
(23)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茶经》)
以上六例,前三例用在代词之后,后三例用在名词之后。“者”字的这种用法被认为是唐代新出现的。此后,结构助词“底”也有了类似的用法:
(24)洞山云:“就师乞眼睛。”师曰:“汝底与阿谁去也?”(《祖堂集》五)
2.2.2结构助词“的”在现代汉语里可以出现在以下6种格式中:
A名词+的+名词(我的书) A′名词+的(我的)
B形容词+的+名词(新的书)B′形容词+的(新的)
C动词+的+名词(买的书) C′动词+的(买的)
其中A、B、C是古汉语中“之”的功能,B′、C′是古汉语中“者”的功能,A′在古汉语中没有一个相应的词,中古以后“许”开始出现在这一位置上,填补了以上系列中的空缺。或者我们可以说,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从功能上看,应该有三个来源,名词前作定语的来自“之”,动词、形容词之后的来自“者”,名词之后的来自“许”。这正如我们过去曾指出的,现代汉语许多虚词的功能,就好像是从侧面看一块沉积岩,其上的每一条花纹实际上都是一层历史的沉积,当我们展开它们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虚词在历史发展中可能不断受到其他虚词的影响,融进其他虚词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讨论一个虚词的历史来源时,应该把视野扩大一些,要把时代相近、功能相关的词放在一起去考查,而不能仅局限在一词、一字之中。如果局限在一词、一字之中,我们就很难说清这些虚词的历史。
余霭芹先生《广东开平方言的“的”字结构》一文中介绍,在开平方言中,定语和名词之间没有标志(A、B、C),名词化(A′、B′、C′)的标志用“个”(“个”用作结构助词的产生过程和它在近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我们曾专门介绍过(注:“底”的发展过程请参阅曹广顺1995。))。开平方言中“的”字结构情况提示我们,现代汉语中结构助词“的”的功能可能可以分为两大类,而其前身,也可能是分两个步骤聚合在一起的,A′和B′、C′的合流是其步骤之一。《佛本行集经》中的“许”正好提供了说明这一合流步骤的原因和过程的材料。
2.3中古“许”字用法比较丰富,其中有两种用法可能和上述用法的“许”字有关。
1.表示处所。如:
(25)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主客无间。(《世说新语·文学》)
(26)我欲赴沙门许受戒,此蛇何以当我前?(《众经撰杂譬喻经》上)
(27)如来世尊,今者外许,别有五百客比丘来。(《佛本行集经》三六)
江蓝生先生(1988)认为,“X许”原意为“X那里”,经过词义虚化,变为“X的”义,表示领有。
2.梁晓虹先生(1994)认为,佛经中除“许”外,“所”也有类似的用法,而“我所”是“我所有”的省略,“所”再影响到“许”,使“许”有了表示领有的用法。
佛经中“所”字确实有例子类似结构助词,例如:
(28)谁能救济我所寿命,我当终身善好奉事。(《撰集百缘经》)
这样的例子在佛经中似很少见。同时,如果“我所”是“我所有”的省略,那么,在没有中心语时,“X所”应该是用作转指,指代其后省略的中心语。但是,在实际使用中,“X所”却经常作为表示“自指”的助词使用。如:
(29)王子佛所,生尊重心。(《佛本行集经》三)
就我们所见的材料看,虽然不能说“所”和“许”表示自指和转指是处于互补状态,但是“所”多用于自指,“许”多用于转指的倾向是明显的。因此,说“许”是由受到“所”的影响而产生了表示领有的用法,有一定的困难。
比较两种意见,从处所引申出表示领有可能更合情理,在汉语中除此之外也还有类似的例子。
三
3.1“者”在古汉语里是结构助词,主要用于B′、C′两种格式中,唐代以后“者”变为“底”,功能扩展到A、B、C、A′四种格式里,逐步形成了现代汉语“的”的语法格局。(注:“底”的发展过程请参阅曹广顺1995。)上一节中我们介绍了《佛本行集经》中由“许”构成的格式A′,以及唐代“者”进入格式A′的情况。但是,“者”进入A′并不等于它可以进入A、B、C,因为二者的功能并不相同(如果A、B、C和A′、B′、C′中的结构助词的功能相同,古汉语中“之”、“者”的区分就没有必要了)。如果我们把A类的功能看作是限定,A′类的功能则可能是表示具有某种性质或特征。A′类有可能变成A(当把某种性质或特征和物体联系在一起时),A类却较难变成A′(把限定的对象去掉时,限定成分无法表示具有某种性质或特征的事物)。由此推论,其变化过程应是从A′到A。《佛本行集经》反映的语言正好在变化之前,应有一个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
3.2《佛本行集经》中出现了一些“之”、“者”连用的例子,如:
(30)五种衰相出现之者,尊必不久,当下兜率,生于人间。(五)
(31)时彼场内所有人民,观看之者,悉唱呼呼叫唤之声。(一三)
(32)外方邻邦亦无侵夺,欲共圣子斗战之者。(一七)
(33)汝诸人辈,所问之者,是何妇女?(三九)
(34)又如诸龙雪山最,飞行之者空最高。(三九)
(35)是时至处,无有一人能解如是议论之者。(三八)
(36)若有女能供养于此神明之者,其女所可有心求愿,即得成就。(四五)
(37)彼人以此虚妄语故,受是尊重供养之者,彼人头破,作于七分。(四六)
以上8例,前5例“之”用如助词,“者”用如代词,意为“……的人(龙)”。例(35)、(36)、(37)则有所不同,这三例中“之者”也用在动词性短语之后,但动作的施事或受事,在句子的前面已经出现过了,其中的“者”无法解释成代词。此时的“之者”应该是连用的结构助词,它们构成的是一个格式C′。“之”进入格式C′带来两种可能:1.“之”受“者”的影响,A类格式中的名词可脱落,产生A′类;2.“者”受到“之”的影响,进入格式A。从后来的发展看,唐代进入A类格式的“者”呈增加的趋势,“底”出现后发展加快,到宋代时,开始全面出现在A类三种格式中;“之”则始终没有出现在A′类。(注:唐代“之者”连用及“者”用于格式C的例句,请参阅冯春田1992。)
魏晋其他译经里,也出现过上面介绍的两种“之者”连用的用法,前者如:
(38)佛说四非常,在之者,众祸殄,景佑昌。(《六度集经》三)
后者如:
(39)彼兔王者,或能值见飞鸟走兽命尽之者,为我作食。(《撰集百缘经》四)
3.3《佛本行集经》中也有个别例子“者”用在格式C(动词+者+名词)中:
(40)时净饭王为于太子,造三时殿……拟冬坐者殿一向暖,拟夏坐者殿一向凉,拟于春秋二时坐者,其殿调适,温和处平,不寒不热。(一二)
类似的例子从汉代起就可以见到,如:
(41)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42)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三国志·魏书·袁刘传》注引《英雄记》)
这样的例子虽然出现的较早,但使用却一直不多,这可能是因为“之”、“者”的分工在古汉语中始终比较清楚,限制了这种混用例句的出现。唐代前后“之者”连用的情况增多,模糊了二者的界线,才使混用的例子有所增加,并最终导致了兼有二者功能的结构助词“底”的出现。
四
4.1以上我们讨论了《佛本行集经》中“许”和“者”的使用情况,在近代汉语结构助词“底”的来源上,我们倾向于吕叔湘先生的意见,认为从功能上看,“底”更近于“者”,应是从“者”演变而来的。《佛本行集经》中的“许”和“者”,前者给“者”进入格式A′的演变添加了一个环节,后者为其进入格式A、B、C提供了一个基础。就现有的材料,其演变过程可能是:古代汉语中“者”用在B′、C′两种格式里;中古后期,“许”的出现产生了格式A′,同时,“者”和“之”混用的情况增多;唐代以后,“者”进入A′,接着又演变为“底”,先较多地用于格式C,然后是B,宋代进入A。其演变顺序,受到语法、语义限制的影响。其他词语(如王力先生主张“之”、冯春田先生主张代词“底”)虽然也有演变为“底(的)”的可能,但从功能上看,都有较大差距;从材料看,也缺乏一个完整的变化过程。
4.2我们曾指出,从量词发展来的助词“个”,可能从形成之初就是一个有方言色彩的词。同样,从处所词发展来的“许”,也有这种可能。“许”出现的时间、文献范围都比较有限,它和“者”替换的时间又正好是中古到近代的转换时期,不少学者主张,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转变是一个基础方言的转变,“许”的消失,或许也是这一转变的结果。
4.3汉语不同方言之间,相同的语法功能却往往采用不同的虚词承担。例如,被动式北方采用蒙受义的“被”和“叫”、“让”,南方有些方言采用给予义的“给”;完成助词大部分地区采用“了”,但西南有地区采用“到”,等等。在结构助词上我们似乎又碰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北方沿用古汉语的结构助词“者(底)”,南方则选择了从量词来的“个”,或许还有什么地区曾经选择过“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