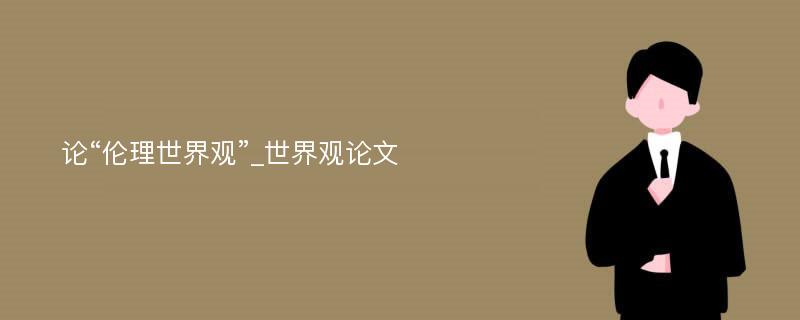
论“伦理世界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观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与方法
如果认定伦理、道德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实践理性,那么,它们就应当有两个研究对象:意识和意志,准确地说,它们应该以“意识—意志”的复合为对象。这样,合理的伦理体系和伦理精神,就必定需要两个理想的要素: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自我意识,法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客观意志;或简称为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哲学意义上的伦理。由此,伦理学的研究和伦理体系的建构就有两个方法论的结构:现象学的;法哲学的。合理的伦理体系和伦理精神,必须是道德自我意识和伦理客观意志的整合,因而在方法论上就要求由关于意识的现象学考察走向对于意志的法哲学分析。难题在于,道德自我意识与伦理客观意志如何在伦理体系和伦理精神中有机璧合;现象学研究与法哲学分析,如何在概念上相互过渡和彼此链接。显而易见,体系上的璧合和方法上的链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由很简单,建立个体内在生命秩序的道德自我意识,只有透过客观的伦理意志的扬弃,才能形成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而对伦理体系和伦理生活来说,合理的个体生命秩序和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的结合,才是根本目的所在,其中,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乃至比个体生命秩序更具有主导性和根源性意义。对被现代性碎片扎得支离破碎的现代伦理秩序来说,更是如此。
黑格尔哲学为这个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学术资源。他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分别确立了道德自我意识与伦理客观意志两个要素,并提供了现象学和法哲学两种研究方法的范型,但遗憾的是,黑格尔并没有完成要素整合和方法论过渡的课题,甚至没有提出这个课题。因为,正如人们已经了解的那样,他在有限的生命中没有能完成计划中的“精神哲学”的体系,而《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在相当意义上只是他的精神哲学体系的两个环节。或者说,黑格尔没有完成,甚至没有来得及进行现象学与法哲学、道德自我意识与伦理客观意志的链接与整合,虽然他天才地揭示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辩证关系。
进行道德自我意识与伦理客观意志的整合,以及由意识的现象学考察走向意志的法哲学分析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找到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中介和概念环节。黑格尔虽然没有直接解决这个课题,但却为它的完成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在“照着讲”的前提下,鼓起“接着讲”的勇气,可以作出一个大胆的理论假设,这个使道德自我意识向伦理客观意志转化,使现象学向法哲学过渡的中介和概念就是:“伦理世界观”。
二、从“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提出一个重要的,但至今在伦理学研究中未引起必要关注的概念:“道德世界观”。
在他的思辨体系中,意识的自我运动在“精神”阶段经过“伦理—教化—道德”的辩证发展过程。其中,伦理是“真实的精神”,教化是“意识自身异化了的精神”,道德是“对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精神一旦进入道德阶段,便出现关于纯粹的道德自我意识与“他在”,或者“绝对义务”与“自然一般”即所谓“完全无意义的现实”之间关系的规定,出现道德意识“自己个体性的世界”。由此,道德世界观便在自我意识中诞生了。
“从这个规定开始,一个道德世界观就形成了,这个道德世界观是由道德的自在自为存在与自然的自在自为存在的关系构成的。这种关系以两种假定为基础,一方面假定自然与道德(道德的目的和活动)彼此是全不相干和各自独立的,另一方面又假定有这样的意识,它知道只有义务具有本质性而自然则全无独立性和本质性。道德世界观包含着两个环节的发展,而这两个环节则处于上述两种完全矛盾的假定的关系之中。”[1]
从以上规定可以发现,道德世界观具有三大要义。第一,道德世界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问题,是道德和自然的关系。第二,这种关系以两个假定为前提:其一,自我意识中道德与自然、道德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分立与对峙,它是对道德与自然混沌未分的原初同一性的否定,在原始同一性阶段,意识任凭自然摆布,自然规律统驭道德规律;其二,道德世界观之成为“道德”自我意识,是因为它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的对峙中,执著于义务的本质性,在意识中以道德规律驾御自然规律,从而有别于以自然本性为基本概念的“生物”世界观或“自然”世界观,而成为“道德的”世界观,或“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第三,道德与自然的现实统一,必须透过道德行为扬弃两种假定之间的矛盾,从而道德规律不仅抽象地而且现实地成为自然规律。
这个规定中难以理解的,可能是“义务”何以在道德世界观中成为本质并与“自然”相对峙。如果参照《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义务的规定,这个问题可能很容易得到诠释:“在义务中个人毋宁说是获得了解放。一方面,他既摆脱了对赤裸裸的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在关于应做什么、可做什么这种道德反思中,又摆脱了他作为主观特殊性的所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他摆脱了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定在,也没有达到行为的客观规定性,而仍停留在自己内部,并缺乏现实性。在义务中,个人得到实体性的自由。”[2]义务使人从生物的自然冲动中解放出来,从人的个别性与偶然性中解放出来,是对人的真正解放,是人的真正自由的获得,因而是道德自我意识升起的标志和道德自我意识的真谛。
显然,在黑格尔体系中,道德世界观的意义是:1)精神或意识的自我确证,是“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2)道德自我意识和个体道德自我在意识中生成的标志,“道德”的自我肯定;3)“道德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见,道德世界观,无论对道德哲学体系,还是现实道德生活,都是基本的概念。
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概念难以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这种个体性的道德自我意识,如何转化为社会性的客观伦理意志和伦理秩序?具体地说,个别性、主观性、多样性的个体道德意识,如何凝聚为社会性、客观性、统一性的伦理意识,并透过合理的统一意志,转化为对多样性和偶然性的、被称为“冲动形态的意识”的行动,具有现实性的普遍伦理意志和伦理行为?这个问题既是伦理体系和伦理生活的难题,也是黑格尔道德世界观理论中没有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但是,黑格尔事实上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道德世界观中内在着一对矛盾或悖论,这个矛盾由两个相反的命题构成,第一个命题是:“现实地存在着道德自我意识”;第二个命题是:“没有道德上现实的东西”。[3]“现实地存在着道德自我意识”是道德意识一般,它的核心是所谓绝对义务;而所以“没有道德上现实的东西”,是因为任何道德自我意识都无法现实地解决道德(或义务)与幸福(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这里他将“自然”换成“幸福”来说)的矛盾。道德与幸福的矛盾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已经提出,康德通过“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两大预设化解这个矛盾。这种矛盾或悖论的存在,可能使自我意识走向它的反面,使道德与自然的关系由和谐变为不和谐,由道德沦为非道德。黑格尔所揭示的道德世界观内在的由这两个命题构成的矛盾,也是他的体系所内在的矛盾。黑格尔超越这个矛盾的思路,一是沿袭康德的老路,借助宗教,将道德自我意识引向“绝对精神”;二是在康德的基础上前进,试图以“道德行为”或所谓“冲动形态的意识”现实地超越那个“没有道德上现实的东西”。第一种路径显然只是一种虚拟,无论他如何具有思辨的天才,现实中的悖论总是存在依然。第二种路径又没有被贯彻到底。他虽然强调“现实的道德意识是一种行动着的意识,而且正因为它是行动着的,所以它的道德才有现实性”。“因为行为只不过是内心道德目的的实现,只不过是去产生出一种由道德目的所规定的现实,或者说,只不过是去制造出道德目的现实本身的和谐。”由于道德行为可以实现道德目的,因而也同时“包含着被称为享受和幸福的那种道德目的的实现”。但是,归根到底,他不得不承认,“道德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应该是自在的(或潜在的)和谐,不为现实意识所知的和谐,不呈现于意识中的和谐,相反,呈现于意识中的,倒不如说只是道德和自然两者之间的矛盾”[4]。最后,道德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还只能在宗教、在天国中才能化解。
无论是内在于黑格尔道德世界观中悖论的超越,还是道德自我意识向伦理客观意志的转化,在理论上都必须进行一种努力,即由以意识为对象的现象学向以意志为对象的法哲学过渡,在特殊与普遍相统一的伦理意志及其所引导的社会性、实体性的集体行动中,而不是个体性的偶然的和主观的冲动中,消解道德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悖论,达到道德与自然的具体历史的统一。而当这样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努力就是:必须找到由个体性的道德自我意识上升为社会性的伦理实体意识,并赋予实体性的社会伦理意识以基本的统一性和同一性,进而可以转化为实体性的伦理行动的那种中介和概念。
具备以上品质的中介和概念就是:“伦理世界观”。
意识发展中道德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矛盾的扬弃,必须透过意识向意志、现象学向法哲学的演进,这个推进的关键性环节,就是个体性的“道德世界观”,向社会性的“伦理世界观”的辩证转化。
三、“伦理世界观”的辩证结构
作为“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伦理世界观与道德世界观既联结又区分。最基本的区分在于二者的品质构造。道德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即道德自我意识,“道德世界观的这种客观方式不是什么别的,只是道德自我意识本身的概念,只不过道德自我意识把它自己的概念弄成对象性的东西而已”[5]。伦理世界观则不同。由道德世界观向伦理世界观的转换,不仅要将个体性的道德自我意识凝聚、转化为社会性的伦理实体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由个体性向社会性的转化中,作为“冲动形态的意识”的行为,也必须被凝聚和转化,由个体行为上升为社会行为或实体行为。如果说个体行为还可以当作“冲动形态的意识”的话,那么,社会行为就必定包含集体意识、普遍意志或客观意志两个环节,否则就难以形成“集体的冲动”。这样,伦理世界观就不像道德世界观那样,是道德自我意识或关于道德自我意识的一维结构,而是内在着社会伦理意识和客观伦理意志的二维结构,或者说是“意识—意志”的同一结构。道德自我意识是意识,而“意识—意志”同一的结构,则是另一种品性,这种品性有一个特殊的概念,就是:精神。
“精神”是在中国哲学和德国哲学中被凸显的概念。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译者王造时先生的考察,“精神”包括理智(意识)和意志,而且后者的意义更较前者来得明显,是包含人类整个心灵和道德的存在[6]。“精神”与“意识”的差异,在于它包含了意识和意志,并与道德具有文化上的直接联系。“精神”是一个兼具现象学与法哲学双重意义的概念。伦理世界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道德意识,而是特殊的“社会伦理精神”,或者用黑格尔的语式表达,伦理世界观是关于“社会伦理精神”的概念。正因为“精神”包含意识与意志,因而作为特殊社会伦理精神的伦理世界观,才可能作为由现象学向法哲学过渡的概念环节。因为,在现象学与法哲学相整合的意义上,个体道德向社会伦理的转换,不仅需要意识的凝聚,更需要意志的客观化与普遍化。“社会伦理精神”,是“伦理世界观”之不同于“道德自我意识”的“道德世界观”的特殊概念品性。
道德世界观和伦理世界观,是关于“道德自我意识”与“社会伦理精神”的不同概念。但是,这并不妨碍二者在结构体系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甚至同质性。
根据“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的诠释,伦理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伦理世界与自然世界、伦理实体的伦理精神与它的自然冲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伦理的”世界观,1)它肯定伦理与自然、伦理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对峙与对立,这种对立和对峙是社会伦理精神自觉的表现;2)它以伦理精神的自我肯定为前提,在两个世界的对立中以伦理尤其是伦理义务为本质的存在,伦理或伦理义务是伦理世界观同一性的基础;3)伦理与自然的冲突,只有透过社会性的伦理行为,才能被现实地扬弃。以上三个要素分别构成伦理世界观的存在性、价值性和现实性的前提,是伦理世界观成立的基本条件,也是伦理世界观的辩证结构和伦理世界观生长的辩证过程。
与道德世界观一样,伦理世界观形成的前提,是社会伦理意识“一般”,与“自然一般”即所谓“他在”的对象化关系。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形成社会性的伦理意识,“伦理意识,由于其直接性的缘故,乃是一种特定的精神,只隶属于各伦理本质性中的一种本质性,本身包含着没有自觉的知识这样一个方面”。其特点是“本身知道义务,履行着义务,并且以之为它自己的本性而隶属于这种义务”,因而是一种“性格”[7]。在伦理意识中,含有它与一个“他在”的关系,这个“他在”是独立于伦理意识但却是无意义的现实或“自然一般”。在这个阶段,伦理意识和“他在”都是自在的,前者是“伦理意识一般”,后者是“自然一般”。自在的伦理意识与自在的“他在”彼此独立,构成有机整体中的一种特定关系,即义务与自然的关系。以义务为绝对本质的抽象的社会伦理意识,以及作为它的内在否定性的“他在”即自然一般,在对峙中构成一个整体即一个完整的世界,这是伦理世界观形成的前提。
但是,伦理世界观是以自在自为的伦理与自在自为的自然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伦理世界观的第一个结构或生长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所谓“伦理意识一般”。这种“伦理意识一般”是一种原初的伦理意识,它是现实的和能动的,但却是抽象的现实性和能动性,它把义务当作本质,在它自己的抽象的现实和抽象的行动中履行着义务。“伦理意识一般”是一种抽象的义务意识,在这个阶段,伦理意识停滞于实体性的伦理动机,伦理行为与它的结果即所谓幸福处于分离的状态。“自然和伦理(伦理的目的和活动)全不相干和各自独立”,是这个阶段的基本假设。抽象的义务意识,义务与现实、伦理与自然的抽象的存在(彼此分离),是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伦理与自然、义务与现实之间的独立与对峙,这是伦理精神原初的具体,是伦理世界观的第一个阶段,即感性具体阶段。
然而,伦理精神现实性的基本条件,却是伦理与自然、义务与现实之间的预定的和谐。无论是道德世界观还是伦理世界观,在确立义务与现实的独立与对峙之后,都必须在意识和精神中确定或预定它们之间的和谐。正如黑格尔所说:“道德意识决不能放弃幸福,决不能把幸福这个环节从它的绝对目的中排除掉。”“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和谐,是被设想为必然存在着的,或者说,这种和谐是被设定的。”[8]设定即是要求,其真义是说,有某种尚非现实的东西被设想为存在着的,它具有必然性,但还是在信念中存在的必然性,而不是现实的必然性。这种情况就是说,伦理与自然、义务与现实之间的和谐,必须在“伦理精神”概念中被预设或信念地存在。伦理精神将二者的统一,当作精神自身的目的,也当作世界的目的。因而它们的统一被当作精神或理性的一种要求。所以,我们发现,在任何民族的伦理精神和任何成熟的伦理体系中,伦理(道德)与自然(幸福)、义务与现实之间的和谐,都必须预设于其中,并在终极的意义上被圆通。不仅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体系是如此,孔子、亚里士多德,乃至基督教伦理、佛教伦理、伊斯兰伦理的体系,都是以“德福一致”为基本规律,准确地说为基本信念,虽然它是在某种假设中完成。伦理与自然、义务与现实之间预定的和谐或信念中的统一,这是伦理精神的抽象,是伦理世界观的理性抽象阶段。
抽象复归于具体,必须诉诸现实的伦理行动。在黑格尔的道德世界观中,道德与自然的具体历史的统一,感性具体和理性抽象的扬弃,就是现实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就是义务与现实统一的中介或中项。道德行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性,乃是因为:1)意志行为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意识,即“作为冲动和情欲而出现的感性”,是冲动形态的意识;2)在道德行为中包含了使义务与现实统一的目的性,以及达到这种统一的能力,义务与现实的统一,是行动着的道德自我意识和伦理意识固有的一种和谐。在义务与现实、感性和理性冲突的情况下,精神的真正本质是:“冲突消除,统一出现,而且作为消除冲突的结果的这种统一,并不是由于双方同在一个个体中的那种原始的统一,而是由于知道了两者的对立才产生出来的统一。”[9]这种包含了对立的统一,才是现实的伦理和现实的道德。不过,以义务与现实统一为核心的伦理行为与道德行为,只有透过现实的社会制度,才能具有真正具体和历史的现实性,否则,伦理行为和道德行为同样会造成义务与现实、德性和幸福之间“不相对应和不公正的情况”,对伦理精神来说,会造成“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悖论。因此,伦理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差异,就在于它对行为的社会合理性而非单纯的个体合理性的追求。更有意义的是,在伦理精神中,因为总是存在自然的否定性环节,即伦理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因而伦理与自然、义务与现实之间的和谐,总是处于不断的否定和创造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道德世界观中一样,伦理的完成“是不能实际达到的,而毋宁是只可予以设想的一种绝对任务,即是说,一种永远有待于完成的任务”[10]。可以肯定的是,伦理行为是扬弃感性具体和理性抽象而达到的伦理世界观的辩证复归,是伦理世界观的理性具体阶段。
这样,伦理与自然的原始的独立与对立——伦理与自然在信念中预定的和谐——伦理行为中伦理与自然的统一,便构成伦理世界观的“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结构和生长的辩证过程。
至关重要的是以下两个问题:1)以上三个要素都是伦理世界观的辩证结构中的必要构成,三个环节都是伦理世界观生长的必经阶段,三者的有机复合,才构成伦理世界观的精神体系;2)无论三要素、三环节,还是由它们形成的整体,都必须体现伦理世界观,而不是道德世界观的特质,虽然它们在许多方面与道德世界观具有相通之处。
关于伦理世界观与道德世界观的殊异,有必要作简洁的概括。上文已经指出,伦理世界观与道德世界观在品质方面的最重要的殊异有:第一,它不像道德世界观那样,是个体性的,而是实体性、共体性或社会性的世界观;第二,它以“意识—意志”的双重结构,而不是单一的意识为自己的对象,所以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自我意识,而是社会性的伦理精神。于是,伦理世界观便表现出以下与道德世界观不同的“精神”气质:它不仅是意识或个体的道德自我意识,而且是个体与整体、特殊与普遍相统一的实体性的伦理自我意识;它不仅是意识,而且同时也是意志,不仅是意志,而且是个体意志与整体意志相统一的实体意志或客观意志;它不仅是精神,而且是意识与意志复合、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相统一的具体、现实的伦理精神。
四、“伦理世界观”的两次飞跃
伦理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伦理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但这里的“伦理”与“自然”,与道德世界观中的“道德”与“自然”具有不同的内涵。对“伦理”来说,已经不是个体性的道德自我意识,甚至不是个体道德目的与道德行动的整体,而是个体与整体相统一、意识与意志相整合的“伦理精神”,是实体性的伦理目的与伦理行动。而所谓“自然”,则包括伦理实体或伦理共体的主观自然,即伦理实体的“自然”的冲动与意欲,以及伦理实体所共同面对的客观自然。因为伦理实体的主观自然,必定包括实体内部各个体的主观自然,是个体的主观自然与实体自然的统一,因而伦理所面对的主观自然对实体内部的各个个体来说,又是一种“客观”,不像道德所面对的自然那样,是纯粹主观的、个别性的和偶然的。同时,“伦理”自在的前提,是实体自觉的伦理自我意识,或者说,是伦理实体的真实存在。如果用道德世界观中的“道德”来诠释,那就是,在“伦理”中,道德已经不是以个体的目的和行动的形态存在,而是以实体的或集体共同的道德目的和道德行动的形态存在。所以,伦理世界观就不能只是现象学的研究对象,而必须是现象学与法哲学共同的研究对象。
这样,存在一个真实的伦理实体或伦理世界,并且实体具有自觉的伦理自我意识,即实体意识到自己的伦理本性;这个自觉意识到的伦理实体与它所面对的“自然”,即实体自身的主观自然(上文已经说过,相对于实体内的个体来说,这种“自然”其实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种客观)与客观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伦理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它们彼此独立,相互对峙,又处于一种自觉了的伦理精神的统一体中,便构成伦理世界观的第一种结构和第一个阶段。这个结构和阶段区别于道德世界观的关键在于:实体意识到自己伦理性的存在(而不像道德世界观中那样,是个体意识到自己道德性的存在),在精神中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相对峙的同时,也与实体自身的主观自然,即实体自身的本能冲动相对峙。由于实体自身的主观自然是对它内部的个体的主观自然的扬弃,因而在伦理世界观的起始,就不仅包含意识,而且必定包含意志;于是伦理世界观的本质,在一开始就不是一种个体性的道德自我意识,而是社会性的伦理精神。
个体道德自我意识的产生,在意识与精神的发展中是一个飞跃,但实体或共体的伦理自我意识的产生,却是更有意义和更为巨大的飞跃。后一个飞跃的本质在于,实体是否对自身的共同道德本性,具有自觉的集体意识,在文化传统的意义上,实体对自己的伦理本性,是否有一种“集体记忆”。在第一个阶段,伦理世界观虽然意识到自己的伦理性,但却与自然处于一种独立和对立的状态之中。对立必须扬弃,归于某种统一,于是便进入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伦理与自然只是归于一个抽象的同一体,这个同一体就是义务。这个阶段伦理世界观的特质,是坚持义务的本质性,以伦理义务把握和同一这个分立和对立的伦理世界。这个阶段虽然是抽象的,但却是巨大的进步,因为实体已经意识到自己对“自然”的伦理性义务,并且以此扬弃实体自身主观的自然冲动。伦理世界观在这个阶段与道德世界观的区别在于:它所自觉和固持的,不是个体的义务,而是实体的义务;不是特殊义务,而是普遍义务。在义务的绝对性或“绝对义务”的意义上,伦理世界观与道德世界观在这里相通,但在伦理世界观中,义务扬弃的对象,已经不是个体的主观自然,而是实体的“客观”自然;同时,它坚持实体作为一个整体,对它所面对的客观自然负有义务。因此,这一阶段的进步,是实体对自己以整体形态出现的主观自然的绝对扬弃,以及对客观自然的义务的整体性义务的绝对意识和绝对坚持。
但是,伦理与自然对立的真正扬弃,同一体的真正造就,必须透过实体的伦理行为。行为一方面是一种意志形态,另一方面又内在于意识之中。不过,在伦理世界观中,作为“冲动形态的意识”的伦理行为,却遵循与道德世界观中的道德行为不同的法则,它依照“集体行动的逻辑”,而不是个体行为的法则。而一旦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就不仅要进行个体意识的凝聚,而且必须扬弃个体意志的主观性,达到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统一,确立实体意志和客观意志。这样,现象学的问题就转换为法哲学的问题,世界观就由道德自我意识的现象学进入伦理意志的法哲学,意识和意志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便被统一起来。与道德世界观不同,在第三个阶段,现实地扬弃伦理与自然对立的已经不是个体性的道德行为,而是以实体形态出现的伦理行为,是实体的“个体”道德行为。因此,它不仅面临伦理实体作为一个整体或整个“个体”,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还面临实体内部中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后一种关系的突出表现,是个体与整体、个体至善与整体至善的关系问题。这样,伦理实体内部个体与整体、个体至善与整体至善的关系,就是伦理世界观在现实性与合理性方面所表现出的,与道德世界观不同的独特的或特别重要的内涵。共同的是,在这个阶段,无论是道德世界观还是伦理世界观,意识都向行为转化,都透过行为扬弃对立,达到统一,由抽象复归于具体。藉此,义务与现实便被安置于一个现实的统一体中,进而达到世界观的完成。
可见,伦理世界观的完成,经过了两次飞跃或两个过程。第一次飞跃是由原初的伦理精神中伦理与自然对立的具体,向以义务为本质并以绝对的义务意识为伦理与自然的同一体的伦理精神的抽象;第二次飞跃是由绝对的伦理义务意识,向以伦理行为为中介的伦理与自然整合的辩证复归。伦理世界观在绝对义务与现实、伦理与自然的伦理精神的统一体中具体、现实地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