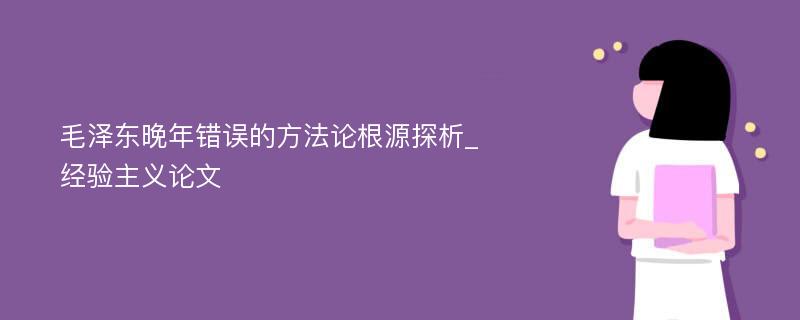
试析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方法论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晚年论文,根源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2)04-0079-04
毛泽东在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毋庸讳言,他晚年探索也存在一些方法论上的罅漏及其运用中的失误,从而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令人痛惜的严重挫折。列宁指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末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1](P449)毛泽东自己也曾总结道:“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2](P311-312)因此,从方法论根源的角度,全面、深入、细致地挖掘和剖析毛泽东晚年失误,吸取经验教训,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验主义对“实事求是”的僭越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的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3](P278)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自己也反复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4](P1308)他还精辟地分析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级发生的东西。”[5](P819)在主观主义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中,他尤其自觉地反对教条主义。应当承认,毛泽东反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运用是较为成功的,“创造了完全没有教条主义的理论。”[6]而且毛泽东晚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思想方法上来看,也正是以批判教条主义、倡导独立思考为理论突破口的。[7]
“然而,只要再向前多走一小步,仿佛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1](P257)毛泽东晚年探索的局限性,相当程度上主要是由于矫枉过正所发生的经验主义偏差所引起的。经验主义所以发生,首先因为马列经典原著对具体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言之甚少,客观上限制了教条主义者“妄宣圣旨”的可能性;其次,随着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毛泽东也开始警惕“以苏为鉴”,这反映了他主观上力图克服教条主义、摆脱“心情不舒畅”的创新精神。在这种主客观情形下,革命经验成了他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思维起点。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在认识一个新事物时,认识主体必然受到认识前结构这一巨大而无形的文化心理场或轻或重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过去已往的经验要素和背景。诚然,对历史经验加以科学地概括总结乃至升华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但是任何经验都有其本身的适用范围,决不能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简单套用,更不能僭越而取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而毛泽东晚年“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旧方法和旧经验,”[8](P37)如从独轮小车推出新中国的历史奇迹中得到“灵感”,发动了大呼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晚年又追忆起革命艰苦时期的淳朴岁月,忽视物质利益原则,试图搞“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从而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犯了严重的经验主义错误。
当然,毛泽东晚年也有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乃至误解的情况,其主观主义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复杂交织。但是仍可清楚地看出,两者不是并列平行,而是以经验主义为主;教条主义是次要的,是为后者服务的。这种带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经验主义貌似正确,具有更大的迷惑性,“积重”更加“难返”。因此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很少自觉地从哲学高度对其经验主义实质作深刻反省。尽管他在“三面红旗”受挫后也曾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但仍未触及思想路线上经验主义的偏差;1961年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因经验主义的残余流毒没有肃清,不久便遭到了更大的干扰和破坏。实践证明,“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9](P606)
二、在群众路线问题上误入了两个歧途
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对于群众路线,我们的工作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凡是遵守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纠正;凡是违背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遇到挫折。”遗憾的是,理论的得出并不意味着实践中一劳永逸的解决,毛泽东晚年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仍然误入了歧途。
首先,群众观点为群众方法相割裂。广义上的群众路线,包括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二个方面。在群众观点上,毛泽东终其一生都笃守了“一切为了群众”、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群众方法上则实际背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从而在决策上演变成了“一言堂”和个人专断。尽管毛泽东在1962有所反思,但终因他对“个人崇拜”的欣赏以及民主制度自身不完善,形势很快再度恶化:民主决策的群众方法遭到了更大践踏,甚至沦落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庸俗形式。
“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10](P218-219)邓小平的这番话,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晚年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背离的症结所在。
其次,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相混淆。毛泽东晚年不仅在实质上抛弃了“一切依靠群众”的民主内涵,而且把它简单曲解为搞一哄而上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否还具有普遍范围的适用性?群众路线是否就等同于群众运动?这个历史性课题摆到了晚年毛泽东的面前。其实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曾指出:“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可以在工人农民当时的觉悟水平上靠提高他们的热情来解决。……但是,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变了。我们要解决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任务了。”[11](P145)
但是1958年以后在毛泽东的眼中,群众运动几乎成了群众路线的同义语。他在视察马钢时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12](P154)由此,理论界掀起了研究“群众运动”的高潮,得出的共识是:“革命时期要大搞群众运动,建设时期更需要大搞群众运动,没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13](P18-22)当时,刘少奇对此曾提出异议,认为“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惟一方式,……显然是不正确的”,它“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14](P404)邓小平也曾强调:“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10](P294-295)但在那个年代里,这种深刻敏锐的眼光毕竟是孤立无援的。到了“文革”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质内容全然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1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这方面的教训说:“我们党的某些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之所以发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运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际上却程度不同地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至于‘文化大革命’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更是根本背离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所导致的恶果。”
三、矛盾分析法上的几处逾矩
毛泽东是一位辩证法大师。其矛盾分析方法,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发挥了摧陷廓清的思想武器作用。在他的晚年,对矛盾分析法的运用更是达到纯熟的程度。但在从心所欲之时,不免也出现了逾矩之处。
第一,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时代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为完备的探讨,”[16]并以此为基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应当肯定,晚年毛泽东仍然关注矛盾的特殊性,尤其体现在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上。但笔者认为,他在注意到国与国空间上的特殊性差异、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却忽视了历史阶段时间上的特殊性区分,犯了盲目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把一些共产主义社会才具备的原则套用到现实中国,大刮“共产风”。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晚年对中国落后的社会状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与认识不足。
而另一方面,毛泽东晚年又过分夸大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各自社会形态的特殊性。一些本来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成果,诸如先进管理经验等,也一概先问姓“资”还是姓“社”,而后再决定取舍;甚至连一些基本生活需要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乖谬地步,捧计划经济为至宝,视商品经济为猛兽。最初那种“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火花,在这般环境的禁锢中终于熄灭了。
第二,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毛泽东在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上,以及建国初期制定“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都成功地运用了抓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法。但晚年却陷入片面性的误区,几乎完全排斥了次要矛盾。诸如“钢铁挂帅”、“以钢为纲”,就严重耽误了农业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则其他一切事业都处于从属的地位。毛泽东晚年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上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已经发生严重失误,而一味孤立地着眼于“抓主要矛盾”,在实践中势必造成更为恶劣的后果。
第三,关于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从《矛盾论》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坚持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统一,但后来却撇开同一性不谈,片面地强调斗争性,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和斗争,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八亿人口,不斗行么?”进而形成一种“斗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哲学依据,朝着谬误方向走得更远了。
第四,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早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指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倡议全党转移工作重心,可见其对形势的分析和把握上是高瞻远瞩的。然而诚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17](P116)问题症结所在,也正如毛泽东后来多次自我批评时所说的那样:在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是因为他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的知识,懂得很少。事实上,正是由此导致他形成了这样的一条思路:只要加速生产关系公有制的发展进程,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注意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是对的,但是过分夸大和片面强调这种作用,试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去解放和促进生产力,这不仅忽视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而且更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
第五,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的条件可以起决定作用[18],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丰富与发展。但其晚年却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视其有条件性,在宣传上沉缅于“要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豪言壮语,甚至滑落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条件论者可以休矣”的唯意志论边缘,从而严重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受到了历史的无情惩罚。
第六,关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二者的结合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阐述,并在批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时,批评了生吞活剥、轻视实践的“唯理论”和具有“反理论倾向”、爬行的“经验论”。[2](P441)但晚年却失于极端化的偏颇,一再拔高直接经验,轻视和贬低理论学习,甚至得出书本知识无用的结论。如1958年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并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列举了许多未读过书或读书甚少的实干家作为人们学习的楷模,而把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学者贬损为徒有虚名的庸碌无能之辈;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论证: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嘉靖以后,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以后,毛泽东忽视理论学习、贬低知识分子思想的流露愈演愈烈。
正如毛泽东在1960年6月《十年总结》中所承认的那样,“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有一些形而上学,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和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陈云在1987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19](P490)这就向全党提出了一个研究方法论的重大任务。“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未竟事业,创造性地构制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在方法论意义上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有效、最强大的科学思想武器。
[收稿日期]200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