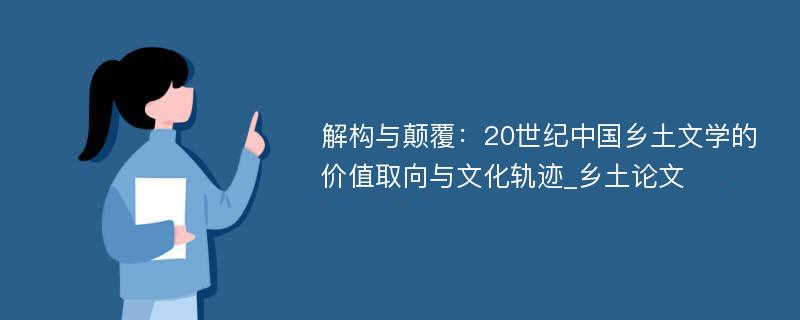
解构与颠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价值取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1)02-0013-05
哲学和文学价值论都证明了,价值观念及其影响、支配下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等具体价值活动是人类生与俱来的基本属性,即从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来讲,它是人类自身所独具的质的规定性,是人所以为人的终极根据或原因,“人的价值存在才是区别人与动物的人类学本体论尺度”[1]。显然,文学也便成为主体在一定的审美价值观念引导、制约下的审美价值创造活动[2]。也就是说,创造主体本身最终形成的审美价值观念及其所包含的爱憎、取舍、抑扬、褒贬等因素,对主体创造活动的价值取向有导向、定向的作用,对具体价值评判有影响、规约作用,文学创作就是在某种价值观念导引下以审美方式表达多样价值取向与价值评判的活动过程。
总体来看,乡土文学以特定乡土地域为客体对象,站立于整个文化人类学高度,用知识者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去打量、审视这一对象并试图揭示其固有价值属性,表达特定价值观念(比如“为人生”)。这里,乡土文学的固有价值属性就是乡土文学独具的质的规定性,即如周作人强调的那样,“乡土艺术”必须”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以充分表现“风土的力”[3](第66页),这种“土气息泥滋味”以及”风土的力”也就是乡土文学内核,是质,是共性,我们不妨称作一种“原乡况味”,即由具体创作展示出来的特定乡土地域的特殊生态景观、风土习俗、文化品格、乡土情感或乡土精神等,它保证了特定乡土地域的自然性存在,也保证乡土文学自身特性不会被消弭。乡土文学的特定价值观念则是流贯在具体创作中创造主体个人的乡村情感、乡土意识、哲学思考和理性批判等,它所体现的是个性,是价值选择多样性。这时,作为客体对象的特定地域已经超越了原先的自然性存在,即不再是原先的物自身,而是具备了一种新的质地的形上式存在,亦即被充分地审美对象化了的存在,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具体考察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价值取向时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与相对静态而稳固的几千年农业社会文明史相比,20世纪中国社会似乎更具一种变动不居的特性,人们再也无法诗意地牺居了。古老的土地正经受着内外危机的双重侵袭,那些躁动不安的灵魂首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继而“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终深化为“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4],并由此而导致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解构,实现了总体价值取向的彻底转型,这种价值取向上不断的否定嬗变成为了循环于世纪内部的主导文化品格,否定或颠覆,是贯穿于世纪的文化主题,乡土文学始终以其成功的艺术实践表述着同一价值诉求。
道德情感式否定——对非人世界与乡土苦难的恶咒和抗议
从最初始的价值层面来看,乡土文学以人本主义思想和人道精神、平民意识为价值尺度,通过“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5]而表达一种情感层次的道德式的悲悯与忧愤情怀,表述着对乡土社会本质的道德式否定。先驱者们早已看出,所谓“仁义道德”的历史实质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6]。后来的文化研究也逻辑地揭示了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7](第83页)。这一伦理——政治型文化形态使主体的丧失成为道德应然,造成了几千年“人”的集体“缺席”(absence),当然,也带来种种人间的病苦。对此,启蒙主义者们“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8]而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叛,并开始在中国“辟人荒”,“从新发现‘入’”[9],具体讲是那些普通的平凡的人,尤其是那些社会最广大的下层平民。由此,文学视点公然转移到“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全力关注“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10],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乡土世界便自然而然地进入文学启蒙者视野,乡间的死生与病苦、悲凉的乡土地上牛马人生的哀吟成为人道主义或平民主义文学思潮的物质依托,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也因此而发生。
最早揭示乡间的苦难,表达上述价值范式的是叶圣陶、杨振声、刘半农、刘大白等。“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5],《渔家》一篇现在看来虽是“较为浅露的速写式的作品”[11](第167页),其对渔民苦情的极力渲染,其作为乡土文学的滥觞,仍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相对而言,叶圣陶的起点就要高些,在《这也是一个人?》(又名《一生》)、《低能儿》(又名《阿菊》)等创作中,乡土世界平凡的小人物的悲苦境遇更多地附着了形而上意义,即在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流露出真挚同情的同时,也流贯着清晰的价值指向:“伊”应该是人,而且本来就是人,但非人的世界使“伊”公然地沦为一只雌性的动物。“伊”甚至连名姓也没有,实际上,在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布景上,“伊”只是一个符号,本来就不应该有名姓,本来就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人的权利与价值问题也在乡土诗歌中得到反映,“平民诗人”刘半农的《瓦釜集》、刘大白的《田主来》、《卖布谣》等,都使人窥见血泪人生的本相,表达了对人间不平的激愤。
更为专注地以乡土地非人的生活遭际为蓝本,表达一种弥漫着浓厚感伤情调的否定性价值评判并体现一定的道德关怀的,是二三十年代由那些“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5]的人们组成的文化群体。他们本来并不单纯为了展览乡村苦难,因此也就构不成所谓“素朴的诗”,而只能是“感伤的诗”,因为他们的本意是为着“用笔写出他的胸臆”[5],本意就为浇自己的块垒。让种感伤是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当初,他们为着反叛而“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2],然而灰暗肮脏、同样透着腐气的都市反而使人更多了一层新的失望与愤懑,更痛切地感到百孔千疮的社会的诸多“不足”,故乡倒反成为排遣内心感伤的去处。而在具体排遣方式上,则大抵有“主观的”、“客观的”和“玩世的”[5]几种。“客观”即写实,是主要方式;“主观”即抒情写意(从价值否定层面讲,是抒写乡土悲苦,表达内心忧愤,此处并不指向牧歌类型);“玩世”则是曲笔,是用“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做‘看破’”[5],或者是如酒神精神一样的“与痛苦相嬉戏”[13],“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5]玩世便蕴含一种深刻。接受着浓厚感伤情绪的蛊惑和驱使,作家们主要展示了悲凉的乡土地上鲜血淋漓的人生惨剧和令人窒息的沉重,表现了乡土社会的衰微现实与弱国子民人权丧失的屈辱卑微。这里充溢着“乡间习俗的冷酷”[5](比如为“菊英”举办冥婚、对乡贼“骆毛”处以水葬之刑、“赌徒吉顺”及“黄胖”等人无奈之中典妻、“环溪村”与“玉湖庄”的械斗等),这里还阴森着宗法制的专横(《水葬》、《他的子民们》等),这里满目萧索,满耳哀鸣,遍地是灾难,到处是匪患,当然,这里也开始涌动起反叛的暗流(象“生人妻”式的个人反抗与“刁佑权”式的自发暴动等)……诚然,作家们“只是站在普泛的人道主义视角上,对苦难和人生的毁灭作常态的描述”[14](第244页),但在形形色色的苦情展览背后,一方面是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闻”一类悯农传统或忧患传统自觉的价值认同,一方面是直指黑暗现实的强烈诅咒与抨击所体现的价值否定,两种情感态度仍然表现着乡土文学的特定价值观念,使我们既看到了“特殊的风土人情”和“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乡土文学固有价值属性),也看到了“在悲壮的背景上”所加上的“美丽”[15](特定价值观念)。
人道主义尺度的再次大规模运用是在历史“新时期”(暂且沿用这一社会政治化术语)。由于诸多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影响),乡土文学自40年代至70年代出现了创作萎缩(有人说是“断层”,亦非确论),人道主义的价值评判相对弱化。随着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全面展开,人道主义旗帜被再度竖起,多灾多难的乡土地再一次成为人们否定极左政治、声讨践踏人性的野蛮行径的特有文化视角。值得往意的是,“新时期”乡土文学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与价值反叛出现了新的变化。与世纪前期对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笼统而情感性的诅咒否定不同,新乡土文学有了更具体、更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指向。如果说用乡土地的种种“伤痕”去否定政治失误的努力还停留在一个较为形而下层次的话,则对极左路线给乡土地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与挞伐就进入了一定的理性层次。极左形态是多样的,其精神实质则是对人的戕害,对价值主体的粗暴践踏,“是用‘虚幻的集体’意识取代具有创造力的个体意识,用整体否定个体,用共性否定个性”[16](第10页)。对此,乡土文学从历史、政治、伦理、人性、心理等不同角度给予了全方位的否定。
情感震撼的能量是巨大的,它代表着价值观念的自觉,体现了认知上的革命性转变,但是,仅仅止于这一层面是远远不够的。道德同情与义愤毕竟缺乏思辩的美丽,缺少哲学理性文化的有力支撑,从这一意义上讲,处于最初价值层面的乡土文学暴露出思想上相对贫乏的意义局限。
文化理性式否定——对荒原遗留与乡土之恶的解剖和鞭笞
这是乡土文学较高层面的价值选择,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乡土文学才真正实现了对历史文化传统中诸多荒原遗留与乡土地一切原生或新生之恶的颠覆性批判。
“实际上鲁迅就是一位最早的乡土文学作家”[17](第4页)。“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18]。即使到了今天,他也仍然是一座难以企及的文化高峰,仍然显示着乡土文学的价值和骄傲。可以说,是鲁迅造就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事实上,不仅仅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作者,尤其是北京的青年们,多数是在鲁迅的扶植下,或者受了他的小说的熏陶才从事写作的”[17](第4页),世纪以来至今的文学都是如此。同时,由以鲁迅式的人格力量、文化情怀与批判理性为主导品格形成的“鲁迅风”给世纪文学,特别是对乡土文学的烛照、影响是全方位的,正是在这类意义上,鲁迅同时又已经超越了或一派别、或一门户的阈限而独具一种巨人的博大深邃,即如有的学者认识的那样,“鲁迅是一个主潮作家,而不是流派作家。……因为他具有过人的,或者说非凡的文化意识或文化器识”[19](第62-63页)。作为大地之子,他与文化的故乡有着无法割裂的精神纠结,而作为思想的巨子,他毅然选择了理性审视,所谓乡土,注定只是一种物质载体,而非终极价值取向。因此,他放逐了乡土之恋,直面惨淡的人生,背负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0]的沉重使命,走进历史文化深层,用他特有的峻切犀利的解剖刀去杀戮一个个腐恶的灵魂。在他的视界内,“乡土”承载的苦难不再停留于物质层面,更多的是封建礼制文化的“吃人”本质、国民的积弱和冥顽不灵的人性丑陋、悲哀等等精神负累与荒原景象。
从审美价值取向看,鲁迅乡土文学(主要是小说)更倾向于将悲悯与忧患上升为凝重的悲剧意识,将平面展示或展览立体化为对产生痛苦的本原的内省与拷问。作为文化先驱者,鲁迅所怀有的是一种大悲悯、大深刻,是无泪的歌哭,是痛定之后的长歌当哭,因而这种悲剧意识透射着理性的凝重冷峻,从《呐喊》到《彷徨》,从精神的病苦到灵魂的震颤,都表述着一种悲剧体验。悲剧来源于痛苦,痛苦来源于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毁灭呈露于社会的历史的人性的各个层面的各类“恶心”,这就是鲁迅乡土小说的一种内在的认知结构。为着强化对这一认知的表达,先生甚至不避“文化偏至”之嫌,不惜采用撕割痛苦、啮噬痛苦、咀嚼痛苦、把玩痛苦的极端方式,其悲剧体验便呈现出庄严与悲壮的总体美学效果。即以《故乡》来讲,记忆中的故乡(文化理念中美的“故乡”范型?)与现实故乡反差如此强烈:“阴晦”“苍黄”的底色,“悲凉”的基调,“萧索”的构图,“冷风”的点染,浓缩为一种深重压抑。为什么会这样?先生的解释是因为“没有什么好心绪”,这一解释在突然间袒露了一颗悲哀的大心——看看那个被民间与王权两头遗弃的孔乙己,看看单四嫂子无望的“明天”,看看“七斤”们对于时代的漠然,看看“祥林嫂”们的满身鬼气……谁还会有什么好心绪!而更具悲壮色彩的是,启蒙者并不惮于前驱,甘愿铁肩担道义,令人寒噤的却是衰亡民族的默无声息与同道难觅的孤独茫然!这种悲壮实质上体现了悲哀与沉重之后强烈的使命意识。有人说阅读鲁迅感觉很累,这大概就是神圣与凡俗的区别吧。不过先生也有让人感觉不累的时候,由“谐谑、“调侃”、“反讽”、“佯谬”等等一类变调处理往往会带来一种貌似“轻松”的快乐效应,悲哀与沉重之中潜流着炽烈的诗情轨迹。实际上,“悲剧包括戏剧类的诗底整个本质,容纳了它的一切因素,因而也有喜剧的因素在内”[21]。读《阿Q正传》、《孔乙己》、《风波》等都能获得由这种喜剧因素引起的审美愉悦。但是,这种“愉悦”、“轻松”的实质是对痛苦的嬉戏,是以乐写哀,因而更具一种酒神式的直面病态社会不幸人生的形而上的悲剧意味,更能见出庄严的否定与批判力量。
以展示乡土苦难见长的乡土写实派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文化批判意向,体现了一定的悲剧精神,像《天二哥》(台静农)、《惨雾》(许杰)、《水葬》(蹇先艾)、《疯妇》、《鼻涕阿二》(许钦文)、《阿长贼骨头》(王鲁彦)、《集应四公》(蒋牧良)、《怂恿》、《活鬼》(彭家煌)等都将艺术视点提升到文化精神的否定层面,但无论是批判的向度还是力度,都远远不及鲁迅的宏廓广大与犀利深邃。这一方面是由于自身文化修养、文化器识的局限,一方面也由于受“为人生”等社会价值论的影响,使他们对鲁迅文化精神作了皮相的模仿,放纵了自己的感伤与同情,因而其眼光只能专注于外部的乡土本然。在稍后的三、四十年代,对乡土历史文化的理性返观渐趋淡薄,其间仅仅零星点缀着李劼人、沙汀、艾青、臧克家、端木蕻良、师陀(芦焚)、萧红、洪深等几处风景,建国后三十年内这一返观则已沦为一条文化“自流河”而消失,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历史、政治影响而导致价值主体在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得他们即便在进行文化反思时也深烙着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政治意识的功利主义印痕。
历史往往在跳跃式地发展。乡土文学进入80年代、90年代,再一次高扬起文化批判大旗,乡土苦难与文化积重再次得到较为充分的理性审视。这一次世纪末的文化批判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回应,而是又一次新的背叛,是在以“传统——现代”这一主题词为核心的时代总体思维构架下对一切已然暴露的乡土之恶与负面文化遗留的反叛、否定、清除。
乡土文学首先所作的努力,是从“昨天——今天”、“原因——结果”的线性角度对极左政治文化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清算,其主要指向是由(昨天)极左文化对主体自觉性的钳制戕害导致的各类精神悲剧。同礼俗社会以道德教化泯灭主体一样,极左政治更坦然地以政治教化收买主体意识、主体尊严和主体权利,规约人们“通过‘内省’、‘克己’的修持,把外在的要求变为主体的心理自觉要求”[22],一旦这种外在教化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便有了公认的专制去泯灭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尽管常常披一件慈善的外衣,或者干脆就是凶神恶煞)。首先站立于这样一种伪民主、非民主的野蛮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人物是“李顺大”。这是一个丧失了个性意识和个人意志的“跟跟派”。几十年来,他省吃俭用,就是巴望着自己能建三间瓦房,而一次次政治运动一次次轰毁了他原本清晰的价值世界,最终只剩下灵魂丧失后的麻木和盲从,再不敢有自己的打算。“李顺大”实际是“陈奂生”的前身,而到了“陈奂生”,主体性丧失则是全方位的,当然这已是另外的话题。“李顺大”的悲剧表明,民主应该是真正的以民为主,而不是替民作主,更不是践踏民主。“李顺大”之后或同时,又出现了“王老大”、“冯么爸”、“胡玉音”、“荒妹”等众多曾经受到心灵虐杀的人物,他们或麻木,或忍受,或扭曲,或斗争,引发了人们广泛深入的历史思考。乡土地上的官僚主义作为一种专制形态,也是乡土文学否定极左文化的一大视点,矫健《老人仓》中的“田仲亭”、张炜《秋天的愤怒》所塑造的“肖万昌”等人物,再也不是梁生宝、刘雨生式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了,他们尖钻浇漓,政治“才干”都用到了谋求一己私利、制造乡间悲剧上面。除了上述型态,现代迷信与政治血统论所孽生的“当代祥林嫂”悲剧、“两条道路的斗争”带来的经济悲剧、“无产阶级专政”制造的各种生活悲剧……也都被摄入了乡土文学的返观视野。
从“凤阳”这块土地上发出的变革现实的呼声,很快席卷而为全方位的社会思潮。乡土文学似乎特别具有一种对“传统——现代“二元悖反思维构架的颖悟力,在应和这一社会思潮的时候,对所有构成现代性掣肘的传统惰性给予了解剖、批判,而在艺术的审美把握上也采用了一种二元方式,将社会文化批判建构在乡村与城市、愚昧与文明、进步与落后、贫穷与富裕、卑贱与高贵等具体的价值二元对立上面。人们再也不会受制于虚妄的“理论”诓骗,再不能无视落后贫穷,再也不能忍受乡土积重,现实的困扰使人们“产生了对故乡的反叛情绪,一种仇恨的审视”[14](第30页),逃离实存意义的乡土(跳出“农”门)成为时代情结,因为城市毕竟是人类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如此看来,已经接受城市文明熏染的“高加林”是注定了无法与“刘巧珍”走到一起的,“巧英”也必定是要离开那个“孙旺泉”的,这不是命定,而是实实在在的价值规律的象征图示,所以,当“高考”、“参军”、“打工”等各类选择为新的价值实现提供可能的时候,人们表现了义无反顾的神情!作为一种“突围”,这本身就是价值否定与新的价值肯定的二元对立,表现这一对立实际上也就隐含了知识者自己的价值认识,“突围”、“逃离”也便具有价值反叛意味。表现价值二元对立中比较典范的个案是贾平凹和高晓声。在《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及“陈奂生系列”等创作中所采用的正是一种清晰的价值二元对立结构,其否定指向明显是那些代表着乡土文化负面精神的乡村人物群。
世纪末期乡土文学所作的文化批判还表现在对地域文化、民族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格渊源中劣质根性的追寻与拷问方面。在一般文化论者眼里,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劣质大抵有“自私自利”、“勤俭”(吝啬)、“爱讲礼貌”(欺伪)、“和平文弱”(中庸)、“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与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7](第22-23页)或“老成温厚”、“超脱老猾”、“知足常乐”之类,“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23](第56-57页)。我们不妨把所有那些在古老农业文明传统基础上生衍积淀下来的劣质文化形态或劣质方面(非优质方面)称为“荒原遗留”,乡土文学自80年代中期以后对此进行了全面丰富的文化“寻根”,并体现了不同程度的否定批判。当然,这里面的情形就显得较为复杂一些。首先,是张炜、韩少功、高晓声、李锐、刘恒、苏童等人在价值判断上体现出了较清晰的否定意向。“《古船》所描述的,果然是深沉厚重悲壮动人的故事,其中关于土改,更不乏惊心动魄的画面。它所具有的悲剧美,令人回肠荡气,感慨良多。……我们有值得自豪、骄傲的光荣历史,也有悲惨、辛酸的民族苦难史,滴着血、流着泪的历史。”[24]“古船”是一种古典辉煌,它究竟能否成为当代生活的烛照呢?张炜通过“洼狸镇”四十年善恶纠缠的历史给予了否定回答。“丙崽”形象也体现出批判意识,其批判坚定地指向传统文化怪圈——那个类似于阴阳二极图式流转弥漫着的神秘荒唐。“丙崽”发育不全,终年流着口涎,一生只会说“爸爸爸”、“×妈妈”两个简单词,这显然是一种隐喻、一个指称和象形,正是这个文化的怪胎在左右着鸡头寨人的灵魂和历史,这样的文化事实真让人不寒而栗!“出国”以后的“陈奂生”也一样是所有那些背负沉重的灵魂的象征。别以为他出国了也就出息了。一方面,他惊异于现代文明的美妙,甚至还能洗盘子挣钱,并试图带点在美国土地上能够茁长的“种子”回陈家村去碰碰运气,但另一方面,传统负累使他终究一事无成:挣的钱到底扔给了美国牙医,那包种子也硬是没能带得回来——别人的文明岂是那么容易就带得回的?带得回来又如何?抑或陈奂生们压根儿就没真想带回来?“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25](第2页)传统农民的固有信条使陈奂生特具一种超稳定性,他永远是那个陈奂生,永远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在“厚土”系列、《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妻妾成群》、《狗儿爷涅槃》等文本中也一样有着清晰的批判指向。与这类清晰的否定情形相反,相当一部分乡土文化“寻根”往往由批判入手,而最终却做了文化“俘虏”,对原始形态或传统人格表现出一种迷醉、留恋,“白嘉轩”与“朱先生”形象就是一个代表。“白嘉轩”是“仁义”“温和”“稳重”等多样价值范型的实体集合,“朱先生”则更多的是一种观念集合,这两个形象互为依存,相得益彰,表现出传统人格上“老犬的狡黠”[23](第19页),这倒的确不是太容易让人一眼识破的,因为没有血,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迷失、偏离,难怪有的论者会尖锐地指出,《白鹿原》“是‘五四’文学的翻案与否定”[26]。同样的情形在郑万隆、马建等人那里也表现得很明显,乡土地的种种“异乡见闻”得到极端形而下的展示,马建甚至在1987年闯下大祸,这都是因为缺乏恰当的价值判断才导致的教训。另外,还有一类情形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的总体批判上表现出价值判断的惶惑与混沌,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他们对乡村历史文化的反思更呈现出一种茫然状态,即一方面是传统的丑陋与物化现实的诱惑,一方面却又是以“破坏”为源头的诸多“文明病”和固有传统的魅力,“其间要穿越的时间和空间,实在是太幽深迷茫了”[27](第1页)。贾平凹曾积极地探索一种形而上的解答,结果仍然只是表达了对现代生存混然无序的无奈。在《土门》中,他试图以“仁厚村”为文化范型去抵御城市扩张与“文明”侵蚀,而这一范型自身无可否认的宗法关系弊端使它怎么也难当此任,其结果仍不过是他以为理想的那个“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28]。长篇《高老庄》也一样时时刻刻寄寓着这种矛盾的纠结与判断,“子路”和“西夏”这两个人物不过是两个文化符号而已。
本时期乡土文学所作的努力也表现在对现实乡土之恶、城市之恶、社会之恶、文明之恶的披露否定方面。处于变革和全面转型时代,乡土地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巨变”,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9](第83页),意识革命乃是更深刻的变革,新的生存哲学与文化观念在引起震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处于这样一个物化与泛商主义时代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价值倾斜与价值失范,乡土地一切原生或新生之恶都得以充分暴露。在朱晓平、田中禾、张宇、何申、关仁山、刘醒龙、谭文峰、李佩甫、阎连科、周大新、莫言、刘恒等人看来,处于这样一个失却诗意、欲望汹涌的年代,乡土运非乐土,是应当背弃、逃离,甚至是应该仇视的。他们恣意张扬乡村之恶,放逐乡土之恋,直接撕破了恶并剥离陈列开来,展示了乡土地令人颤栗的丑陋。80年代乡土苦难与乡土之恶更多传统文化重负的因素,比如朱晓平《桑树坪纪事》、张宇《活鬼》等所批判的还是专制、愚昧,90年代乡土之恶则更多新生因素,比如拜金主义、极端物欲与价值沦丧、个性刁顽等。田中禾《枸桃树》就写到一个农村女子在价值迷惘下出卖肉体的事实,而刘醒龙则展示着乡村“艰难”,何申主要以现实主义方法描摹乡间黑暗(像《穷县》、《穷人》等)与人性刁钻(像“杨光复”、“王大鞭子”等),谭文峰也诅咒着乡间特殊的“生存竞争”(像《乡殇》等),李佩甫以略带感伤的柔板抒写着“乡村蒙太奇”……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这个特殊的物化时代有了既感性而又本质的认识,即对艾略特指出的那个“荒原”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否定作为一个世纪乡土文学的中心话题,其内核只能是哲学意义的,即是扬弃、发展和更新,“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30](第181页)。辩证否定始终包含着肯定因素,也就是保留了有利于新事物发展的积极因素,即以乡土文学本身来讲,其批判否定的主要驱动是关爱,是期待,是价值构建的必要环节,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进入20世纪乡土文学的又一价值世界。
①收稿日期:2001-02-09
标签:乡土论文; 鲁迅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乡土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故乡论文; 反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