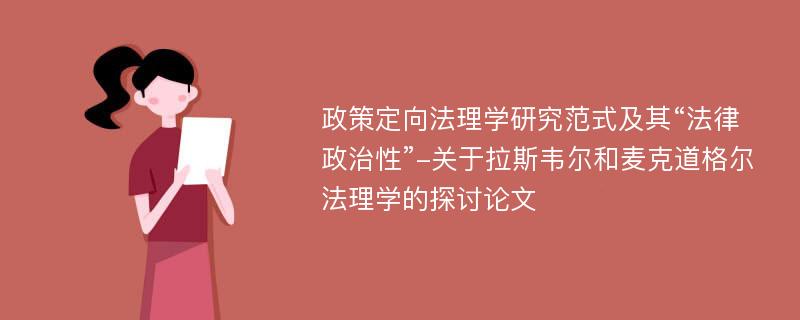
政策定向法理学研究范式 及其“法律政治性”
——关于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法理学的探讨
邹立君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合作创立了“政策定向法理学”。这一跨学科的法学理论提出了一种“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范式,它旨在创造或修改概念工具,即整合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以适用于法律规范的目的、以构建有人类尊严的公共秩序,并且期望这些概念和范畴可以被用来理解和塑造所有语境中的法律。所谓“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经由确定和衡量社会期待的实际模式来确认法律权威;拒绝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区分,以价值决定的方式试图抹平法律推理与政策论辩之间的所有界限;以一种依赖法律基本目的(特别是共享价值)的方式来应用规则和法律程序。“政策定向法理学”以“政策科学”的方式开放出来的“法律政治性”论题绵延至今,依旧是人类智识上的一项重大挑战。
关键词: 政策定向法理学;拉斯韦尔;麦克道格尔;法律政治性
一、政策定向法理学研究范式
(一)政策定向法理学之“法律的政策科学”目标
“政策定向法理学”由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和美国法学家麦克道格尔(Myres Smith McDougal)合作创立,鉴于两位教授的研究主题及方法,也可称为“法律的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 of Law)研究,又因他们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耶鲁大学法学院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小镇纽黑文,还被称为“纽黑文学派”(The New Haven School)。在《自由社会之法学理论》一书中,他们首先表明其研究是一种“关于法律的理论”而不是“法律的理论”(a theory about law not of law)。这一理论在详尽批评主要法理学流派的基础上,包含了对“法理学标准”(criteria for theory about law)的基本预设和对其自身理论内容的再三申明,或至少是以其拟制标准为“政策科学”命题下的法理学研究反复做辩护,即致力于发明一套“法律的政策科学”(a policy-science of the law)研究方式。
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理论首先诊断既有法理学研究的问题。他们认为,标榜为“法理学派”的许多学说,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技术性的法的”理论,它们问题重重或者说缺陷明显,如研究焦点狭隘、研究者立场和目的混乱等等。他们认为,传统的或绝大多数法学思考,虽然依旧对研究和决策发挥重要影响,但它们却是不全面的理论,因其太过狭窄而限制了研究的焦点,并且严重局限了与其相关的智识任务。这些学说通常关注的对象仅限于所谓的法律规则,或是十分不明确的方面,忽略了法律过程的真实运作,缺乏对实证决策或决策的总体流动的清晰聚焦。尤其是从特性上来说,“各种学说较少关注不同社群的权威和控制复杂的相互作用模式,对其进行的现实性描述就更少了。它们只是将可疑的神秘体系投射到‘国内’和‘国际’的利益和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上。在大部分的学说中,所完成的智识任务是逻辑指导方面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有效研究和理性决策所必需的其他任务。”[1]5-6
何谓真正的法理学?更准确地说,何谓“政策科学”命题下的法理学研究?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指出,法理学研究至少牵涉关注决策而非规则、区分权威和控制、聚焦于权威决策过程、从社会形成和分享价值的愿望与成就方面勾勒问题等等。亦即,这种“关于法律的理论”之目标不是为具体的法律行动提供指导,而是详细描述一个概念框架,或者说开发出一套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的概念和范畴,使得对社会过程的研究可以在那一框架(概念和范畴)之下有效展开。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这类研究的基础之上,才可以灵活地选择和运用法律和政策。进而言之,“政策科学”命题之下的法理学研究有其主要标准。
产业集聚在不同的发育程度表现出不同的环境效应,在产业集聚的初期,由于产业间关联疏散、企业之间的网络化协作水平较低,此时产业集聚呈现出较强的负环境效应,表现为污染物排放增加(耿焜,2006)。随着产业集聚水平逐步高级化,产业之间合作逐步深化,通过物质循环、生态效率提高等途径,产业集聚能有效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废弃物排放(Gargava et al.,1996)。当产业集聚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区域资源综合利用网络基本成型,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有效发挥,产业集聚的负面环境效应最弱,污染物排放强度最低(Šlachtová et al.,1998;张攀等,2008)。
1.它必须致力于创造出一整套的概念,以此来构建其理论观念和学术体系,进而来为各项研究提供指引和帮助。[2]3诚如赖斯曼所指出的:“你将注意到他们对范畴和概念的关注。如果法律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一个社群的决策过程,且其目标在于增强这一过程之运转以及人们的参与,从而有助于建立人类尊严之公共秩序,则他们所能够创造或修改的概念工具将异常重要。”[1]3比如“规范”(norm)这一概念,[3]麦克道格尔虽然似乎与哈特共享了对规范本质的概念性理解,但麦克道格尔的方法侧重于“应该”,通过辨识在特定共同体内一般共享的期望或凭经验可识别的权威模式,更可以进行经验性描述。因此,它比哈特的次要规则以及他的“内在”态度概念在进路上更“科学”和更语境化。这决定了麦克道格尔与拉斯韦尔的规范进路超越了仅仅依赖“语词”的含义、正式的文字游戏或单纯依赖过去的行为,有关人际交往的整个范围都被它考虑在内,也包括了可识别的政策、过去的语境、现在和未来的人类语境以及人的需求等等。
正如纽黑文学派的中坚学者赖斯曼所言,“把法律和法律机构当成是政策选择会带来相当不同的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10]1实际上,自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始,该学派一直坚信:找出法律与政策的区别,既不是现实的,也不是适当的和有用的。他们断言:法律即政策,法律中立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4]这至少是因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我的福利无法避免地与其他所有人的福利相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有义务把被称之为‘法律’的机构视为协调政治过程,其中涉及最大限度地分配所有物品和份额的全面政治运作和集体生活中供应短缺的问题,如权力和安全、财富、教化、才能、康乐、情爱、尊重和正直”[10]1。总之,作为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即从权力之形成与分享的社会过程上来研究法律,其主题可以根据某项或某类权威性决策而非既有的或理想的规则和制度来加以表述,借此可以表达沉思性的(抽象的)法律或政治概念的经验基础(可操作性的)。由此来看,政策定向法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传统观念和理论态度的制约,但这并不代表其与既有观念毫无瓜葛。当然,从其方法论上来看,这个问题会更加有意味。
任务实施是学生或小组按照计划逐步完成任务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引入MOOC的知识点讲解,将学生任务中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以线上MOOC的资源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完成学习。再充分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并就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实施步骤形成详细的计划。学生在这个环节要完成的工作主要是进一步收集信息,完成任务或解决问题,汇报PPT、图纸或其他形式的学习成果。
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法理学,不是为现存法律或理想的法律提供正当性论证,而是关注或者说致力于发展一种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本身。该种意义上的法理学,更确切地说,政策定向法理学,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而被使用的。它不是包含对法律学说的详尽阐述即法律应当如何的学说,而是努力建构一套从“为人们所欲求的事物”(desired event)这样一个关于价值的基本预设为出发点的系统性、整体性的概念体系。[5]184
(二)政策定向法理学的研究范式
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认为,一种“政策科学”命题之下的法理学研究,不必排除对“技术性法的”理论的兴趣,但法律科学欲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价值的民主化和致力于创造一个自由而富裕的社会,就应当最大限度地降低技术性法律原则(technical legal doctrine)——它被称为“权威的神话”——的作用。[5]185-186也就是说,从政策定向法理学的视角来看,法理学研究不仅在“权威决策”即法律政策形成过程中扮演创造性角色——在一系列重要性不断变动的事件中作为自我定位的手段——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扮演工具性角色。因此,其研究的主题及意义既不必然是理论性的,也不必然是实践性的;既有操作性(manipulative)观点,也有沉思性(contemplative)观点。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从操作性与沉思性这样两种观点来对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法理学作出综合分析。
3.它必须构建更广泛的相互渗透的参数(变量)体系,以服务于自由社会。这正如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合作之初的宣言那样,法学“教育的一个合法的目的是寻求促进民主社会的主要价值和降低不同意共享民主喜好的道德特立独行者的数量”,“尽管‘目的论法理学’和根据基本政策评估法律结构、原理和程序的必要性大家都在谈论,但是几乎没有有意识的、系统的努力去将它们明确一致地与社会争取实现民主价值的主要问题关联起来”[4]。也就是说,法学教学与研究最大的挑战在于创立一种和建立与维持自由民主的公共秩序相关的法理学。这样一种法理学所要解决的不是和法律定义相关的问题,而是要把权威决策和所要建立的体现人类尊严的公共秩序结合起来,为实现产生和分配人类尊严价值的世界秩序这一目标完善和应用工具。
毋庸置疑,政策定向法理学是对理性决策因素更加具体化的智识任务的程序研究,“其范围从一个基本的社群目标价值的设定,以及通过对与某个特定问题相关的政策的临时性具体说明,从有关价值塑造和分享的事实方面对问题的阐述,到通过运用各种相关智识任务的特殊程序对这种潜在政策进行系统性的检测”[1]223。也就是说,从一种整合性理念来发展一种“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这一理论并存两种不同成分——法律科学的经验建议和法律学说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前者牵涉更多的是沉思性研究,即法律因素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多重思考,或者干脆说,这意味着不可以把法理学研究限制在社会科学的某个领域之内。恰如麦克道格尔所指出的,所有技术性法律原则都有一种不妥当的习惯做法,即“在成对相反的立场上漂移”,概念上的和原则上的自相矛盾是法律特有的,而且法律术语的意义是以这些术语被使用的语境、使用这些术语的人以及运用这些术语的目的来确定的。由此来看,依靠原则并不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并且常常会使被社会认为可欲的目的受到挫折。因此,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建议:应当根据民主生活的目标和重要问题来阐释关键法律术语;法律判决应当被看成是“对社会进程中价值变化的突然事件的回应”;应当对所选择的解决方案给整个社会模式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目标思考”和功能考虑,并用之代替对定义和规则的强调;应当避免对法律与政策等做出明确界分,等等。[5]186
1.它是一套以问题情境为起点的操作性流程研究。政策定向法理学之所以要发明各种新奇的概念,在于决定情境中可供选择的目标,如“研究焦点的确立与分层”“智识任务的确定与程序”“价值的澄清与选择”[1]1-15,并根据通往目标的具体行动阐明该情境中的权威决策到底为何。因此,情境中的各相关要素,须根据它们在“权威决策”形成中的影响而被分析和评价。研究的结果当然就是对这样一种行为方式的权威说明,亦即,情境中的行动者、参与者以这一方式能够提升事件的特定状态出现的可能性:为创造结果Y(或是使Y出现的可能性变大),那么就以方式X行动。[6]3若套用美国学者鲍思特(Jordan J.Paust)的话,它是一种“将法律与一个动态的语境现实——规范从中推导出并且在其中运作——相联系的努力”[3]。因此,政策定向法理学在主题内容上的重要表现,是一系列新奇概念与操作性流程的阐释。典型例如:从对过去关于法的理论之考察中他们断定,法学理论要服务自由社会,并且必须追随研究社会过程的其他领域最先进的现代理论,寻找更加全面和更具穿透力的学说。法律学者目前面临的艰巨挑战就是要创造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有关的法学理论。从以人类为中心和平等主义等角度来看,该挑战不仅仅是通过“定义”解决与法律有关的问题,而是将有关权威决定和公共秩序相联系。[1]14-15总的来说,要从公共秩序大背景中将要最大化的价值的角度来评价一个法律体系。因此,研究的任务是要评估该体系成败的程度,解释导致这些后果的原因要素,明确目标和将来的政策选择。此法学理论必须通过界定一个参照框架来研究法律和社会,通过详细明确智识任务来研究其所揭示的紧迫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将该办法适用之。
从上述内容中推知,政策定向法理学作为一种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包括规划相关过程的概念、技术及方法。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已经反复申明,政策科学命题之下的关于法律的理论研究,类似于文化人类学,须运用一些创造性的调整,以实现任何一个社会过程都可以根据那些参与者的角度进行系统描述,如驱动它们(他们的观点)的主观方面的问题、相互作用的环境、借鉴或依赖的资源(权力基础)以及操纵这些资源的方式(战略)和互动过程的总的结果,即这种法理学研究最终是根据一套完整的价值来构思的。[3]概言之,政策定向法理学的情境论题表明,任何法理学研究若要有助于未来的研究,都必须被限定于明确规定的社会条件上。在实质上,这种研究遵循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学科的原则——“排除情境因素的考虑,不仅不会使命题普遍化,反而会掩盖那些代表我们自身文化的情境的特殊性”[6]9。
2.它以阐述一系列参数、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为重心作沉思性观点研究。在政策科学研究上,所谓沉思性观点并不关注分离目标变量,也不关注被认为具有特定重要性的行动,而是根据各变量对持续展开的研究的重要性来阐述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政策科学命题里,法律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共存关系,可依凭这样的函数表达方式,即形式Y是X的一种函数。这些表达方式可以转换为操作性观点,如果Y是且仅仅是X的一种函数,那么必须以方式X行动才能创造结果Y。[6]3更准确地说,作为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推进法律科学理论的发展,而非法律实践技术的进步(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关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同时这也强调必须与从经验观察和控制中抽象出来的形而上思考相区别。对此,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指出:以政策为导向的法学理论的显著特征,“是利用当代政策科学运动的知识,从而试图将许多不同信息和学科的相关方面的可能性贡献整合成一个系统且审慎的理论和程序,进而来明确公共秩序中关于特殊性问题的社群政策。它所期望的是能够比以往传承的学说在研究上更全面,且在具体参考上更细致。”[1]221该学说承认,在对背景进行规划的过程中,通过重新整合源自道德哲学家和其他规范性专家的价值类别(权力、尊重、教化、福利、财富、技术、情感和操守),并借助文化人类学者的某些“实践”或“制度性”的类别(参与、观点、情形、权力的基础、策略和结果)来寻求全面性和精确性,亦即实现更高的抽象层面和任何必要层面的全面性以及在更低的抽象层面和决定特殊问题所要求的最小细节上的具体化。
由于投入不足,部分工程未开展专业规划设计或设计深度过浅,项目规划布局不够合理,设施配套缺乏,单项工程设计存在明显缺陷或错误,难以为项目建设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不仅影响了工程建设进度、质量及效益发挥,造成资金、资源浪费和闲置,而且部分单项工程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由于投入不足,工程建设施工及建后管护、抚育等各项措施难以保证,导致部分工程施工质量较低,运行不正常,综合效益较差。
由于研究范围较大,辐射距离较长,整段天际线所包含的构成要素数量及形式过多。因此以道路分隔及既有街区为基础,将整段天际线较为均匀地划分为7段样本,每段长度约500~700m。一方面控制样本尺度以便于受访人在之后的调查问卷中进行评价判断,另一方面增加样本数量为后续天际线评价定量化、规律化的探讨提供了基础。
3.它从权力之形成与分享的社会过程上来研究法律。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认为,法律是一种权力价值(power value)的形式,而且“是社会中权力决策的总和”[7]。麦克道格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能使决策同那种保证这些决策得以执行的有效控制结合起来的正式认可的权力,乃是法律过程的实质之所在;正式权力同有效控制的这种结合,产生了一系列决策,而这些决策的目的则在于促进社会价值与社会预期相一致。因此,在整个社会中,法律也被看成是决策的程序而不仅仅是一套规则。[8]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由此所提出的基本建议之一便是社会成员应参与价值的分配和分享,换言之,法律调整和审判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更为广泛地分享价值。而他们所构想的法律控制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世界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以民主方式分配价值的做法得到鼓励和促进,一切资源都得以被最大限度的利用、保护个人的尊严被认为是社会政策的最高目标。[4]简言之,作为一种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其对个人尊严的科学研究,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个人的所有方面加以观察,而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有限需求或利益的化身来研究,如社会学法学家庞德(R.Pound)所做的那样;其对个人尊严的政策研究,珍视的不是非人格化国家的荣誉或社会机制的效率,而是人的尊严和人的能力的实现。这些努力一直以来被纽黑文学派的学者珍视为他们对当代政治法律思想研究的一大贡献。[9]
2.它强调程序性地规划研究内容及过程,在确定研究对象之后,依次明确观察立场、确立关注焦点、设定和阐释相关社会价值、确定智识任务以及指明每项任务的程序等。举个例子,对于国际法庭有效性问题,它通过使用过程模型坚持采纳一种功能性进路,不是假设国际法庭执行相当于美国国内法院执行的那些任务,而是辨识一个具有有效的和权威的结果的持续性决策过程,并审视该法庭对那些结果有何贡献。这必然涉及到认真评估和批评目前的过程、制度与实践。过程模型——其辨识参与者、观点、相互作用的环境、依凭的权力基础、处理权力基础的战略模式、在权力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的结果以及作为其必要条件的其他价值观——允许法律人确定国际法庭有效性的实际程度,而不是简单地假设因为它看起来像一个司法机构,它就必须是某种司法机构。这样就能够检验国际法庭的规定性功能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还会着手提高国际法庭决策过程自身的表现,增强它们的能力,以实现更符合人的尊严的结果。
由大学生对外卖服务的满意情况与对市场未来前景观点的交叉图(见图2)可以看出,随着调查对象满意程度的加强,他们对共享经济在未来发展趋势的乐观度也随之加强.
(1)结构—功能进路。纽黑文学派的中坚学者鲍思特指出,对于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来说,“‘法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活的’过程,它不会离开正在持续的观点(perspective)模式和运作(operation)模式而存在。最相关的观点模式是在既定共同体内普遍共享的法律预期和普遍要求的价值结果;而且‘法律’被视为观点和运作的实际模式之融合。”[3]也就是说,政策定向法理学在其主要内容表述上综合运用了操作性观点和沉思性观点相结合的方法,该种方法与政策科学研究上的结构分析原则是一致的。具体来说,作为“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从操作性观点来看,其功能在于从社会情境来考察法律,亦即提供与内化于社会关系中所实现的价值整合相关的智识,但完全依赖这种观点会因将研究局限于对其方式和手段的思考而减损研究本身的价值;从另一方面而言,纯粹的沉思性观点也无法成功地在既定情境下使研究最大限度地与社会中最可能的和最紧迫的需求相联系。因此,尽管政策定向法理学与许多传统学说一样,也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但它更注重综合运用两种观点,更推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即把法律视为权威性决策,在社会过程的意义上来研究它们,由于这个过程是由情境化的、看得见的行为所构成,所以可以根据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来描述事态与表述概念。
4.它的结构—功能进路和价值进路。“关于法律的理论”之方法,被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用以论证其法理学的可欲性,究其实质,它是被用来对法理学智识标准进行判断的,包括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范围及进路的不同理解。以研究对象为例,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指出,历史上以“规则”的系统和体系来理解法律支配了文明思想数千年。不幸的是,那些强调“规则”的学术研究结果是把这些规则从社群和社会过程中高度孤立和抽象出来,而远离规则的产生、变化和使用等这些影响规则运用的条件。其研究过程往往是:首先找出一些一般性的方法和标准来确定需研究的系统的规则,然后集中精力找出系统中不同规则的内在逻辑联系,并最终把这些规则和决定及社会背景中的其他因素的关系作分别和进一步的研究。“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仍然主要是法律技术,主要的事情仍然是根据权威性神秘体系的模糊概念来界定和安排。集中关注规则的方法是徒劳无益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花费精力在现在的一些泛滥的寻求阐明规则本质的书籍上。”[1]43他们痛斥以“规则”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法理学,认为它们过分专注于“技术性法”而忽略了法理学应是一门聚焦“社会中人的基本问题”、关注权威决策的社会过程、关注搜集数据和提供对特定问题的描述与解释的学科。
(2)价值进路。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进路,“提供了对目标—价值(或法律政策)的探索,经由使用系统探索现行的主观性模式的方法,其超越了哈特的‘假设的人类共同目标’的观念,而且其内在于目标价值能够最合理及客观地进行识别的那些现行模式。‘纯粹的’目标价值是不可能获得的;超验的和语义的引用一点儿也不‘真实’(甚至是‘价值中立的’);以及‘假设的人类共同目标’的部分探索并非如下面的尝试一样有用,即试图绘制出可识别的所有相关的观点,包括实际上持有的、共享的、细节上不同的目标价值。”[3]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明确指出,“政策科学学说的目标就是要提出设计的更好的理论和程序来对权威性决策中独特的复杂性和困难给予适当考虑。……为了对决策的作出给予最高层次的指导,就像其他众多当代国家宪章和一个新兴全球人权法案中所明示的那样,这一学说明确设定而非推导或是假设社群对于人类尊严之历史价值的根本的追求。……整个调查中最重要的目标当然是识别和作出最终达臻对有关直接当事方和他们作为成员的各种社群的、被设定的价值中的共同利益最充分的表达。”[1]274-276为此,对于环境中的某些问题,可能必须要重新表述,并重新组织各方之间交流的结构,来完成所有利益的适当整合。他们指出,为了规则的制定、应用和评价目的,语词或“规则”(这在大多数实证主义方法中其实只是一个语词的组合)必须不断地被解释。他们还指出,单纯的“规则导向”或句法分析不能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或免除人类选择的,无论该努力是多么“纯粹”或“客观”。这就是为什么麦克道格尔和拉斯韦尔的进路寻求近似的“客观性”,然而同时承认必须作出选择。[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关于“法律的政策科学”的结构—功能进路与价值论进路是相融贯的。更确切地说,他们的价值观是追求实现自由社会的公民价值观,但他们并不关注对民主价值的辩护,因为那种辩护与某些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理论研究相关;他们的“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实则十分注重论述有利于建立和维系自由社会的条件,那些论述经由剖析自由社会所赖以实现的制度来培育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富有成效的策略。
在小学英语教学课堂中,老师要学会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但是又不能真正的放手。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中也是这样,老师要让学生们通过小组自行学习,但是又要在这样的模式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这对老师的职业素养也是有着很大的挑战。但是有些老师就没有做好这一点,学生在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时候,老师就安然坐在讲台上,仿佛这个课堂跟自己没关系,这样是不正确的。所以这就要求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积极参与到小组合作中去,在学生讨论的时候,老师要走出自己的区域,走进学生。所以说老师积极参与小组合作中也是优化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重要举措。
在这里,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进路尤其区别于凯尔森(Hans Kelsen)与哈特(H.L.Hart)。凯尔森完全避免论及任何主观性价值,他的“纯粹法理论”完全限定于认识实在法。哈特则一直寻求避免陷入全面的和现实的人类共享的道德观点,而从人性和“理智感”(good sense)中派生出来的、共享且有限的法律与道德的“最低限度的内容”出发。哈特发现“道德之‘最低限度内容’的工作,不涉及在既定的社会中科学探究共享的或根本的道德之实际的‘最低限度’或基本模式。相反,它依赖于一组推定。这种做法似乎不科学也反经验,正如凯尔森通过使用自己的模式化认知逃避持续不断的主观性模式。两者都涉及单纯的偏好”[3]。两者均在处理“社群普遍接受的道德”方面误入歧途。更可取的进路则是一个面向社会过程的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即对合理的、服务于政策的决策,最好的研究方式是探索权威和操作的实际模式,而不是对社会背景的局部调查以及推崇教条式的和必然“不现实的”、反经验的计划。[3]人们应该认识到选择的必要性,阐述可为各种决策者所用的选择类型,并通过检验“所有影响决策的显著变量和决定的替代性选择总体价值后果的理性评估”寻求法律焦点中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所以必须澄清实际上利害攸关的政策,并专注于它们与背景和权威及控制决策的整个持续过程的相互关系,社会共同体正是通过它们塑造和分享其价值。
3M光固化复合树脂FiltekTM Z350;3M TransbondTM光固化黏结剂,自凝树脂,上中切牙整铸网底直丝弓托槽,可见光固化机,858Mini Bionix电子疲劳试验机。
二、政策定向法理学的“法律政治性”评析
对于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法理学,正如学者们所评论的那样:它忠实地反映了美国的政治偏见,大部分的核心工作是全神贯注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它整个的方法论不仅太复杂而且也太耗时费力,诸如语境、过程、价值观和系统评价非国家行为者的作用等等,过于老套和格式化;甚至沙赫特认为,研习它其实就是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对此,韦斯特(Burns H.Weston)辩解说,政策定向法理学作为一种寻求关联法律与社会——同这一联结一样复杂——的方法论和法理学,其本身必然是复杂的。[11]特文宁(William Twining)则将其方法描述为“一个功利主义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混合物,并得到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些洞识的补充,然后将所有内容集合为一个精心制作的术语”[12]385。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政策定向法理学提供了一种关于法律性质的一般视角或分析进路,而这一视角、进路尤其是以“权威决策”为核心且与政策、政治密切相关。换言之,不可否认,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始终主张:政策定向法理学既可以成为法律教育和学术的指引,也引导了政策形成和执行技术的理性化表达摆在法学学科的中心位置。政策定向法理学也可以算作是对“法律的(司法的)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种行动谋划,或者说,对于“法律政治性”论题的一种理论建构。
(一)政策定向法理学的法律权威观念
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主张,通过考量既定社会中全体成员一般分享着的法律期待而作出裁判,他们拒斥根据“权威”而制作司法裁判的法律实证主义方法,[13]并以此来建构其法律权威的观念。遵循实证主义方法的“权威”概念参照的只是官方精英的观点,而不包括共同体成员的观点。但麦克道格尔和拉斯韦尔认为,权威和权威决定并不仅仅涉及到官方精英的观点、喜好或决策的结果,相反,“共同体成员”的观点应该是首要参考。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特定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期待和行为相关模式的组合,亦即规范的有效性和功效(normative validity and efficacy)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这一审查程序,应以政策科学的方式——借助于诸如“期待指数”这种社会科学技术[14]——开展各种目标设定、内容评估等经验性的测量,其目的不仅仅在于选择也在于强调这一事实[13]:审查程序涉及到的不仅是对“法律”的反馈本身,而且也是对原本作为权威性构成的精英选择的反应,亦即选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启动一个规定性的过程,其结果将是一个社会规范。也就是说,政策定向法理学所开放出来的重要论题之一,就是如何确定和衡量社会期待的实际模式,并以此来确认法律权威;对“法律的(司法的)与政治的”关系来讲,重要的问题,不是司法或立法机构等是否最能代表权威,而是在给定的情况下,是否任何一个官方机构的实际规范性选择事实上反映了真正的法律权威。更确切地说,基于此种进路,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避免陷入到司法部门(而不是实际的司法选择)比立法机关(而不是实际的立法选择)更民主的长期和徒劳的纷纭争论之中。[15]在这个意义上,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富有教益的启示:法律不只是作为何为正确的或公正的观念的一种表现,它更重要的是要体现社会期待这一价值,因此它也必须具有行为的有效决定因素;进而,作为权威决策过程的法律,是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它受到在一般的政治工作中运作的因素的影响。
(二)政策定向法理学的政策论辩
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认为,参照普遍共享的法律期待并通过强调权威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可以矫正法学家、政治学家们共有的倾向,即他们仅仅根据权力和利益来理解法律与政治行为。这至少是因为当政策被定义为制定影响价值分配的重要决定时,没有一个处理法律问题的人能够脱离政策。麦克道格尔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中立的法律概念和没有政策内容的法律一样都是一种妄想。具体来说,根据他们的法理学基本信条与原则,作为权威性决定过程而不是作为约束性规则的概念,法律实际上涵盖了涉及权威的视角下的所有社会交往的决定。在这其中,“权威的”决定,与“正确的”或“适当的”决定始终是保持一致的,即术语“权威”“正确”“适当”的含义就是指一系列“符合预期”的决定。它们也不限于官方机构、法院和立法机关的决定。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决定是“控制性的”,它们必须管理行为,即决定具有影响行为之能力的权力元素。因此,法律的过程涉及权威(合法性)和权力两者。虽然它们是有区别的,但也是相互共生的:“权威”如果无效,往往会消失;没有权威的权力,要么成功地受到挑战,要么获得权威。[11]显而易见,他们所谓“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拒绝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区分,以价值决定的方式试图抹平法律推理与政策论辩之间的所有界限。这也与他们的追随者,尤其是新纽黑文学派的主张不同,后者主张从“福利”的视角来对待政策,尽管也主张法律与政策的区别既不现实也无意义。这样,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所不断建构的法理学至少有将法律还原为政治并消除法律的独特规范性质的嫌疑。
(三)政策定向法理学的价值澄清
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法理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从事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人们关于谁、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为了什么目的可以合法作出(社会期待)的“权威性决策”的实际作用与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它提供了发现一个合法的行为或决定的最终检验是“其与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理论和程序。然而,即便根据这一理论,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目标可以通过实证调查发现人们持有的价值观是什么,即便它拒斥关于价值观的“超验推导(transempirical derivation)”进路,正如传统的自然法理论所做的那样。但是,它总是以适用政策或社会目标来凌驾于法律规则、条约等规范性内容之上,也就意味着社会过程中的“价值澄清”总是可能的。正如沙赫特所指出的,政策定向法理学必须要解决[11]:其一,这种“非法律”的考虑可以适当进入法律决定过程的程度问题。其二,麦克道格尔振振有词“世界人民的压倒性多数”希望和平、安全、尊重和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些愿望都被其归结为人类尊严的价值,也出现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表达中,但是,由于它们都是宽泛意义上的政治修辞,它们也兼容于不同机构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它们是否就一定与美国和西欧的所谓自由民主的政治信条联系在一起呢?申言之,政策定向法理学所论及的“法律政治性”,既不是通常法律渊源意义上的政策,也不是通常语境里的法律,而是以一种所谓依赖法律基本目的(特别是共享价值)的方式来应用规则和法律程序。这似乎并不可行,不仅仅是因为价值澄清上的不可能,如到底是谁的价值,而且它似乎以一种破坏既有法律概念的方式来阐释法律学理,让法律服从政策,它的进路无形中消解了规则的约束性,并为伪装成法律的偏见或主观的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总而言之,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法理学以非同一般的法学理论的方式开放出了“法律政治性”论题的规范性内容,如法律权威、权威性决策过程等等。与此同时,该种法理学在赋予权威性决策以规范内容时,其中的所谓共享价值因素,只不过是通过归因于人类的多数目标这些源于道德升华和理想政体的理性观念,而非源于人们实际想要什么的经验发现;因此,既背离了法律现实主义的职业取向,也无视了法律语言的特殊性和自主性。笔者认为,法律过程中优先考虑公共政策,即考虑那些从人类目的之道德反思和理性澄清中产生的愿望是完全适当的,但是若以此为借口并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适用政策来取代法律的约束,即赞成将美国政策作为其所追求的“更高目的”,并隐蔽地依附于美国的政治与法律主张之上,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单边主义霸权思想,因而,也就不会在根本上对法律与政策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提供更具意义与价值的智识力量。
(四)政策定向法理学的“法律政治性”论题倾向
宽泛地讲,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的法理学是以政策定向的,它着力强调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性,以至于存在着将法律还原为政治的趋向。尽管如此,它避免了纯粹视政策为法律(司法)推理(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因素的分析进路,而是将政策泛化并结合社会科学方法对其在社会过程中的表现进行经验性测量,由此,它更专注于行为者(参与者)或大众的接受和期望。一如拉斯韦尔所言,“要成为权威性的就是要被确定为官方的或机构有能力采取的行动;要成为控制性的就是能够塑造结果”,并认为法律是权威性决定的流程,结合权威和控制二要素。这也就是说,重点在于有关沟通的整个过程,即使人们知道法律不会被立法机构单独创制,也是由守法创制的。“政策科学家关心的是在公共秩序的语境下掌握适合于开明决策的技能。……他正在寻找各种技能的最佳综合,这些技能有助于为公共利益提供解决问题的可靠理论和实践。”[16]12-13亦即,政策定向法理学并不是基于一种法律职业者的视角与态度来阐释法律问题的,它更倾向于识别出某一社会共同体及其法律期待,而不是仅仅识别或补充一个规则的规范性内容,因为在根本上它坚持认为规则的功能顶多只能是指导决策者看到问题的相关特征及其背景和适当的政策。
当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以一套迥异于一般法学理论的概念工具、以潜藏的美国政策理念来诠释作为法律的政治科学时,即便是同为判例法系的英国法学也会对他们加以鞭笞。[12]337-387然而,作为法律的政治科学研究,其在认识论上所开放出的“法律政治性”论题,依然值得深究:至少我们应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即将政治权威和权力与社会共同体(甚至于人类共同体)及其期待而非将立法或司法看作是法律的中心,来审视法律与政策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拉斯韦尔,麦克道格尔.自由社会之法学理论:法律、科学和政策的研究[M].王超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William Morison. Myres S. McDougal and Twentieth-Century Jurisprudence: A Comparative Essay [A].Michael Reisman & Burns H. Weston eds. in Toward World Order and Human Dignity: Essays in Honor of Myres S. McDougal [C]. New York: Free Press,1976.
[3]Jordan J. Paust. The Concept of Norm: A Consideration of The Jurisprudential Views of Hart, Kelsen and McDougal-Lasswell[J]. Temple Law Quarterly,1979,(1).
[4]Harold D. Lasswell and Myres S. McDougal. Legal Edu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J]. The Yale Law Journal,1943,(2).
[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6][美]拉斯韦尔,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M].王菲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7]Myres S. McDougal. The Law School of the Future: From Legal Realism to Policy Science in the World Community [J]. Yale Law Journal,1947,(8).
[8]Myres S. McDougal. Law as a Process of Decision: A Policy-Oriented Approach to Legal Study [J]. Natural Law Forum,1956,(1).
[9]Laura A. Dickinson.Toward a “New” New Hav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J].Th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7,(2).
[10]万鄂湘等主编.国际法:领悟与构建——W.迈克尔·赖斯曼论文集[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1]Burns H. Weston, Oscar Schachter, etc. McDougal’s Jurisprudence: Utility, Influence, Controversy,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J].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1985,(1).
[12]William Twining. 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 [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3.
[13]McDougal, Lasswell & Chen. Human Rights and World Public Order: Human Rights in Comprehensive Context [J].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77,(2).
[14]Jordan J. Paust. The Concept of Norm: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tent, Authority,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 [J]. Temple Law Quarterly,1980,(2).
[15][美]伊利.民主与不信任[M].张卓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6]See Harold D. Lasswell. A Pre-view of Policy Sciences [M].New York: American Elsevier Publishing Co., Inc,1971.
中图分类号: DF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533(2019)05-0045-09
DOI :10.13975/j.cnki.gdxz.2019.05.006
收稿日期: 2019—05—08
基金项目: 2018年度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作为司法方法的指导性案例研究》(编号:CLS(2018)D08)。
作者简介: 邹立君(1976—),女,吉林辽源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法哲学、外国法制史。
责任编辑:晏中,曹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