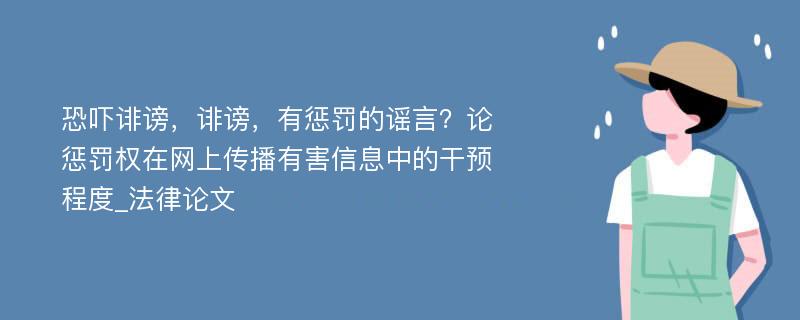
以刑罚威吓诽谤、诋毁、谣言?——论刑罚权对网络有害信息传播的干预程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罚论文,谣言论文,有害论文,信息传播论文,程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2)04-0013-07
一、引言:网络有害信息的界定
毋庸置疑,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信息的传播方式。随着所谓“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方式从“点—面”向“点—点”转变。互联网在大大地促进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的同时,也为各种有害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放大器”。在传统治理模式下,公权力通过对媒体进行有效管理,即可以基本上避免有害信息的大规模传播,因而在前互联网时代,有害信息的传播往往通过“口耳”之间传递为主,只有商业有害信息的传播可以借用有偿广告的方式利用传统媒体的管理“空当”进行传播。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管理模式,有害信息也如脱缰野马开始在虚拟世界恣意传播,并在现实社会中侵害个体性利益,冲击、影响社会秩序。
网络有害信息,是指给某一主体的合法、正当利益带来损害的信息,其形成损害的过程就是其传播过程。①判断信息是否“有害”,并非以某一主体的主观感受为根据,而是以这种信息是否给该主体为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利益,或者虽未被法律规定,但为公序良俗所认可的利益造成可能的或者实际的损害为判断标准。进而言之,“有害”的判断标准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换言之,“有害”与否不是对主体的某种感觉的侵犯,而是对主体的利益的侵犯。对于各种形态的利益,粗略地可以区分为个体性利益和超个体利益。在一个法治状态下,个体性利益总是为法律以权利的形式加以认可,而超个体利益实际上就是安全与秩序,其并非以法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许会认为,超个体利益是所有人应有权利的集合,但如此看法实际上损害了权利的应有内涵,进而会损害具体而合法的权利诉求。
网络有害信息,从不同角度可以做不同的区分。由于法律总是关乎利益的保障与救济,因而从被侵害的利益归属角度,可以将网络有害信息区分为针对公民个人的有害信息,针对公司、企业、团体等单位、组织的有害信息,针对社会的有害信息以及针对政府的有害信息。②针对公民个人的有害信息,从被侵害的权利看,主要是名誉权和隐私权。针对公司等单位的有害信息,直接侵犯的是这些单位的名誉权,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单位而言,最终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损失。这两种有害信息所针对的,就是个体性利益。针对社会的有害信息,表现为对社会安全和秩序的扰乱,其后果最终会造成一定范围内公众的反感、忧虑或者恐慌。针对政府的有害信息,表现为对政府权威和信誉的侵害,由于政府的基本职能在于向社会提供以安全和秩序为内容的公共产品,因而针对政府的有害信息,会影响到政府管控社会安全与秩序的能力。针对社会的有害信息和针对政府的有害信息,其所侵害的利益都是超个体性的。
对个体性利益侵害的制裁与救济,应首先依照民法加以解决,行政法的介入则是其次的,而刑法的干预则是最后性的,即只有当这类行为造成的后果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严重地损害了受害人的正常生活所具有的人际交往条件,需要对行为人进行强烈谴责并通过刑罚进行报应和预防的时候,刑罚权的出现才具有正当性。对于超个体利益侵害的制裁与救济,则无法依照民法寻求救济。虽然在私法上,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成为私法主体,但政府并不具有名誉权,[1]更不具有隐私权。但如此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信誉不受保障,或者可以任意加以侵害,只是说这种利益并不受私法保护,而属于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受行政法律规制。当然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惩罚侵害政府信誉的行为,应保持最大的克制和最为严苛的标准,即只有给政府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干扰并造成社会秩序严重紊乱的情况下,才有予以制裁的必要。
与利用其他类型的媒介或者工具的犯罪一样,以网络为媒介或者工具的犯罪,并不因为使用媒介或者工具的不同,而影响行为性质的判断。不过,虽然与利用传统媒介传播有害信息的行为并无本质不同,但是,通过网络传播有害信息形成的危害要远远超过前者,而且发起和参与传播的样式也更为复杂。利用传统媒介传播有害信息的行为,往往危害性有限,因而利用公法尤其是刑法,予以干预的必要性就相对较小;而利用网络传播有害信息的行为,则危害性很大,而且对危害的影响范围不易控制,因而公法对其干预就大有剑拔弩张、跃跃欲试之势。法治的最大任务恰恰是限制并约束公权力,对于互联网时代所带来这一巨大威胁,一方面,公权力乃至刑罚权有惩治传播网络有害信息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对这样的权力实施必须给予极大的限制,使这种并无恶意的冲动回归到理性而适度的干预状态。
二、刑罚权规制网络有害信息的实质判断根据
运用刑罚权规制某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者作为某种犯罪加以处罚。前者是刑法立法行为,是典型的犯罪化(criminalization);后者是刑事司法行为,在我国由于存在通过刑事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追诉标准或定罪标准的实践,因而从广义上看,后者也被认为是一种犯罪化。[2]虽然这种看法存在争议,③但其也反映了实践中的处理方式,即当出现新型的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时,在以往法律实践并没有予以相应处理的情况下,在不违反罪刑法定的前提下,通过适用既有刑法规范来解决刑事责任问题。当然,这种意义上的“犯罪化”,其性质仍是法律适用问题,而所谓新型的危害行为,可能当然地处于某一刑法规范的评价范围之中,也只有如此,这种意义上的“犯罪化”才可能是正当的;而如果超过刑法规范的可能评价范围,以所谓“司法的犯罪化”的名义行使类推之实,或者以进行所谓实质解释而破坏刑法规范的预测可能性时,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如此也必然是专横而无理地滥用刑罚权。因此,对于运用刑罚权规制网络有害信息传播的行为,一方面,要讨论刑法立法层面的必要性问题,另一方面,则要讨论刑事司法层面的限度问题。而无论在哪个层面讨论,都要首先考虑刑罚权出现的正当性根据问题。④
(一)关于刑罚权出现的正当性根据
刑罚权出现的正当性问题,是比讨论犯罪化正当性问题更为宽泛的、分析有关引起刑罚权实际运作的判断根据和分析工具的理论。刑罚权出现的正当性,包括有关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和司法中刑罚权运用(定罪和量刑)的正当化问题。对于我国而言,讨论后者意义与对前者的讨论同样重要。
关于犯罪化的根据问题,外国学者有较多讨论。英美法主流观点认为,犯罪化的根据在于“损害(harm)”,其基础在于国家将某一行为犯罪化的正当化根据,在于该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或者形成某种不可接受的危险。而这种损害必须是不法(wrongful)行为引起的,即有责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或者“将某人的利益作为满足他人的手段而滥用其利益”。[3]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不法行为中的公共因素和公共不法行为(public wrongs)的情形,后者是指向社会整体的,如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以及税收等。这种观念与德系理论中的法益观念相通。例如,罗克辛即指出:“刑法只允许保护‘法益’。……根据刑法仅仅应当保护确定的预先规定的‘利益’。”[4]12而且,应排除单纯的违反道德行为和违反秩序行为,后者实际上涉及犯罪行为和违反执行行为的分离。在德国学者看来,刑法应当保护预先规定的法益(首先是典型的不依赖于国家的个人权利的基本规范);对于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来说,由于这类规定保护的不是已经存在的财富(Gueter),而是仅仅用于支持维护公共秩序和福利任务的法规,所以应当作为在道德上无色彩的不服从行为,也就是单纯的违法秩序行为,仅仅使用非刑事惩罚的手段加以制裁。[4]13在罗克辛看来,“法益是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者目标设定。”[4]15-17
在我国,刑法理论虽然受德系理论影响日甚一日,然而在对于犯罪化根据问题上的分析,尤其是在刑法立法中,社会危害性理论仍是占主流的根据。例如,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说明》中,阐述醉驾等行为入罪的理由时,即提出“对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建议规定为犯罪”。⑤在一些司法解释中,也将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作为定罪和量刑的实质根据或者根据之一。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有关量刑的指导原则中即规定,量刑要考虑“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而在具体刑事案件的处理中,“社会危害”往往是刑事判决书中阐述判决理由的关键词。虽然有学者也指出,社会危害性在立法层面上考量具有合理性,而在司法层面上不应作为判断根据,[5]但是在学说上,在刑事司法中将社会危害性作为理解犯罪成立,并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认识,仍占据优势地位。⑥
依循不同理论进行判断,在大部分问题的判断上,其结论基本一致,但是如果将不同理论进行简单“换算”或者作“等义”解,则忽视了不同理论出发点上的差异,以及其背后作为支撑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英美法理论中的“损害原则”以及其添附物“冒犯(offense)原则”,[6]与德系理论中“法益理论”,在理论基础上基本相通,其立场是近代法治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其出发点是个体性利益,而犯罪首先且主要的是对个体性利益的侵犯。我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所秉持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前述理论的立场是不同的,它将犯罪看作是一种统治关系(合法化的社会关系)的侵害,即便是针对个体性利益的犯罪,也被认为是对正常的社会关系的破坏,这种理解的立场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性观念。从效果上,简单地将打通法益理论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尝试,在方法论上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由于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立场和出发点的选择,就决定了相应理论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上述三种理论都存在相同的缺陷,这就是三者都存在较强的模糊性,而随着某种需求的增长,无论是对“损害”、“法益”还是对“社会危害性”的理解都存在不断泛化的趋势,这当然也是由于这些概念本身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模糊性有关。对这种模糊性,是需要予以提防的,如果不对所持理论设限,则完全可以作为任意扩张刑罚权的理论根据。为上述理论设限,似乎只能从反面建议限制,正如罗克辛所主张:“专横的刑罚威胁保护的不是法益”、“纯粹的思想性目标设定所保护的不是法益”、“纯粹违反道德行为所侵害的不是法益”。[4]12而考虑我国的刑事法律实践,则必须为社会危害性设定判断标准,不仅要考虑刑法立法层面,还要考虑刑事司法层面,而且在犯罪与部分行政违法行为存在等质性的情况下,则还要考虑“入罪门槛”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危害性在所谓的“量”上的判断问题。
即便不考虑所持立场和出发点,社会危害性理论仍具有很强的论述能力,似乎也契合中国的固有文化。但必须强调的是,比较其他两种理论,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模糊性最强。因此,即便仍将其作为刑罚权出现的正当性根据理论,对其也应作出明确的合理限制。对此,笔者曾提出两条限制原则⑦:一是,任何权利行为都不应视为犯罪;二是,单纯地违反没有利益体现的秩序的行为,不应规定为犯罪。作为补充,有必要提出第三条限制原则:任何社会相当的行为,不应视为犯罪,而对相当性的判断,应从公众承受能力和固有文化上加以考虑。这三条限制原则,可以作为坚持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实质性补充,既应在刑法立法层面予以考虑,也应在刑事司法层面发挥限制作用。此外,在刑事司法中的刑法适用方中,由于实质解释论甚嚣尘上,对解释方法的运用也应进行合理限制。对刑法条文进行“严格解释”,是永远不过时的基本态度。
(二)在干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中刑罚权出现的可能性
从概念的使用上,即已经说明了网络“有害”信息是能够形成某种危害的信息,而传播网络有害信息的行为则会对法律所确定和保护的利益,或者长久以来被认为社会所公认的利益,形成某种危险乃至损害。然而,这种空泛的认识,恰恰可能被用作滥行惩罚的根据。其问题在于:(1)与有形性损害不同,由信息传播而形成的损害是无形的,而针对具体个人或组织无形损害的评价,往往是从受害人的感觉来理解的。但是,能否以受害人的感觉作为唯一或者主要判断根据呢?举个极端的例子,一句无恶意的戏言令一个情绪敏感的人痛苦不堪,能否认为已经形成损害?而这一行为是否就是有害行为呢?(2)社会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性概念,而针对社会的有害信息,谁来代表或者代替社会作出判断?又或者说,对于这种情形,“压根儿”就不需要询问处于特定社会群体中具体人的意见?(3)针对政府的有害信息,能否仅仅由政府作出判断?对于政府而言,是否只要是事后被证明是虚假的信息就是有害信息?对于政府的批评和质疑,乃至无端的指责是否是“有害信息”?对于传播这类信息的行为,是否要求行为人具有恶意?(4)我国刑法对任何犯罪的规定,都设定了“门槛”。这一门槛由《刑法》第13条加以概括性规定,并在具体刑法规范中进一步明确,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来确定这一“门槛”的高度。此外,诸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律也从侧面为具体刑法规范适用设定了“门槛”。换言之,这些行政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所针对行为的最高“门槛”,就是相应的具体刑法规范的最低“门槛”,那么对于传播网络有害信息而言,如果动用刑罚权来加以干预,刑罚权出现的“门槛”在哪里?(5)如果说针对个体性利益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行为,可以通过后果或者损失等来衡量形成危害的程度,那么,对于针对社会或者政府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行为,衡量危害程度的标准是什么?究竟是以传播行为的影响范围来衡量,还是以造成的混乱规模或者以恢复正常秩序所付出的各种成本来衡量?对如上诸多问题的回答,都与合法、正当而合比例地行使刑罚权相关,换言之,刑罚权出现必须“师出有名”,而这个“名”,就是实质的正当性,既然强调这一点,任意而模糊的运用刑罚权显然是不正当的,而以打击有害信息之名行压制言论自由之实,则更是滥用公权力的表现。所以,运用刑罚权干预网络有害信息的传播,必须为“有害”确立明确且可操作的标准。
结合上述对刑罚权出现根据的法理论述,对以上具体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以含糊的“具有社会危害”作为干预网络有害信息的根据,而是要以明确的标准为刑罚权的可能干预铺设“轨道”。
第一个标准就是,判断传播的某种网络信息是否有害,必须从是否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和当下为公众所认可的、事实上存在的利益为根据。任何利益又是客观的,为一般人所认可,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对于针对个体性利益的网络有害信息而言,该标准自不待言;而对于针对超个人利益的网络有害信息而言,则必须从最终后果来考虑这一标准。具体而言,针对社会和政府的网络有害信息,直接表现为对社会赖以存在的,或者政府应加以维护的安全和秩序的危害;但从终极意义上讲,应是对特定社会群体内的一般人的利益以及政府对这种利益的保障产生消极影响乃至严重干扰,这种利益的内容就是对基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依赖。从这个角度看,某种网络信息虽然虚假,但其传播不至于影响到这种依赖时,则不构成作为刑罚权出现前提的“有害”。
第二个标准就是,作为刑罚权干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的前提,“有害”必须到达一定的程度。这一标准的建立,是以刑罚权干预的必要性为基础的,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现有法制现状。对于针对自然人的网络有害信息,只要在一般人看来,通过侮辱、诽谤形式贬低他人人格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对受害人的社会评价、社会形象形成损害,并由此使其正常生活、工作等无法进行的,刑罚权出现才具有必要性;对于针对公司、企业等单位的网络有害信息,如果该单位属于经营性企业的,会因该信息的传播而造成信誉和经营上损失的,以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严重的经营困难作为判断根据;对于针对社会和政府的网络有害信息,则只有对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形成有形的紊乱,且形成较大范围、持续较长时间的,才可以考虑刑罚权干预的可能性,而此时的干预必须有刑法上的根据。
以上两条标准基本上从“正向”建立了刑罚权干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的实质基础。而对于具体案件的处理,动用刑罚权必须具有合法性,即只有在刑法已经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刑罚权。⑧需要注意的是,在刑法条文表述存在模糊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以刑法解释为主要内容的刑法规范适用的正当性,以上提出的两条标准同样也应在相关刑法规范的解释中予以体现,前文提到的三条限制原则也是正当行使刑罚权的保障。
三、遏制网络有害信息与保障言论自由的平衡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第40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当然,任何法律权利的行使都是有边界的,因而《宪法》第51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从该条出发,就网络传播而言,任何人在行使言论权利的同时,也不得通过制造和传播有害信息而损害其他主体的权利和利益。而这一条也提示我们,在规制网络传播方面,要实现遏制有害信息与保障言论自由的平衡;而在刑罚权干预问题上,则应强调这种平衡。当然,这种平衡不是僵化、一成不变的,而是受特定时空环境影响的平衡。从当下情势看,对网络环境的信息传播尤其要重视这种平衡,而这种平衡能否实现,并非是通过“从严(严厉+严格)”治理网络来实现,相反,是通过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来实现的。
网络有害信息传播形式包括文字和音像资料(音频和视频),往往又以言论的形式出现,因而判断其是否有害,尤其用刑罚权加以干预,则还应设立一些反向的、排除性标准来明确加以限定:(1)意见性言论应排除在外。意见性言论,实际上就是个人的看法和主张。有时,这种言论的对象,会因为其影响自己的权威或者声誉而表示反感乃至愤怒,但这种言论不应视为有害信息。当然,发表这类言论时,如果使用侮辱性的语言,则侮辱性语言的使用不是意见性言论。(2)批评性言论应排除在外。在正常人际交往和政治生活中,批评是一种很正常的交流方式,虽然批评会给被批评人形成各种压力,但批评本身无可厚非。尤其是针对公众人物、公益组织和政府的批评,即便使用了比较激烈的语言,即便基于不确切的事实,也不宜诉诸法律手段。(3)合理的推断应排除在外。在信息不全面、不及时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人都可能根据一些相关的、零碎的信息进行推断。只要作为判断根据的信息是真实的,且其推断也是合逻辑或者合常理的,即便推断出的信息与真实情况不符,也不应认为其属于诽谤或者谣言。(4)基于恐慌的言论不属于谣言。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周边民众会产生一定的心理恐慌,如果基于这种心理而误认为某些事实发生或者错误、推断出某些事实已经发生,也不应认为这属于谣言进而惩罚相关人员。(5)单纯的情绪表达不应诉诸惩罚。很多人将公共网络视为宣泄个人情绪的私人场所,常常会出现情绪表达而造成他人情感受害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形,属于社会应予谴责但又要适度容忍的范围,通过社会谴责或者网络技术处理即可,而不应诉诸惩罚。(6)基于公共媒体报道、权威人士发布以及其他具有公信力信源的信息传播行为,不应视为传播谣言的行为,不应诉诸惩罚。由于一般人的信息鉴别能力受制于信息传播环境,因而一般人有理由相信公共媒体、权威人士和其他具有公信力信源给出的信息。在没有更为权威且真实的信息发布之前,其传播由这些信源发布的信息不属于传播谣言的行为。上述排除性标准只是一般性将一些常见情形排除在外,同时,在适用刑法来干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以遏制诋毁、诽谤和谣言行为时,还应从网络有害信息的对象不同而加以区分。
对于针对自然人利益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从现行刑法看,主要是通过侮辱罪和诽谤罪来加以规制的。虽然目前通过网络来诋毁、诽谤他人的事件较多,但绝大多数都是由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护自身的权利。问题在于,《刑法》第246条中“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⑨应如何加以限定。在实践中,与网络有关且为人关注的诽谤刑事案件往往也与此有关。以往数起针对官员的所谓诽谤案件,也是以此为“由头”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此,在刑法立法上对此未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必须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进行限制性解释。对此有学者认为,应限定为两种情形:一是,侮辱、诽谤情节特别严重,引起了被害人自杀身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后果,被害人丧失自诉能力的;二是,侮辱、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交代表等特定对象,既损害他人名誉,又危害国家利益的,对地方机关工作人员的侮辱、诽谤不属于“严重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7]对于前一种情形,该观点已经明显超出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完全不是解释了。⑩对于后一种情形,笔者基本表示赞同,不过还需要进一步限制。具体地说,只有因为侮辱、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导致群体性事件或社会对抗,或者由此严重损害国家声誉的,侮辱、诽谤外国元首、外交代表或者国际组织官员而导致外交纠纷的,则可以归入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范围。
对于针对公司、企业等单位利益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行为,根据现行《刑法》第221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来加以规制。目前,以捏造事实并加以散布为形式通过网络对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损害的现象十分突出,其中两种类型比较突出:一是,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二是,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名行勒索之实。对于前者应根据《刑法》第221条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后者可以考虑以敲诈勒索罪来处理。不过,对于单纯传播有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不应以《刑法》第221条追究刑事责任,将单纯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作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进行处罚已经属于类推,(11)而不是扩大解释。对于其他社会组织,如对公益组织、人民团体等进行名誉权损害的,目前,刑法还未给予调整。至于是否有调整的必要性,笔者持否定态度。
对于针对社会和政府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行为,只有在威胁国家安全和法律秩序的情况下,才可能借助刑法进行处罚,即考虑适用《刑法》第103条第2款煽动分裂国家罪、第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第278条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不过,对于这三个具体犯罪的适用,应掌握严格的适用标准。在实践中,切忌将对政府的激烈批评、质疑、建议等视为反政府的言论,也不能将单纯的思想表达和设想,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若以刑罚权来对待这些行为,则显然滥用了刑罚权,不利于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之,遏制网络有害信息传播与言论自由的平衡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刑罚权的出现,对于遏制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而言,更要十分谨慎和克制,应以有利于保障言论自由为前提。
四、结论
网络有害信息的传播,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并通过法律手段加以治理,这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对此,刑罚权也不应绝对“靠边站”,只是刑罚权的出现应首先考虑其正当性问题,并应保持克制。对于遏制网络有害信息,要充分考虑与言论自由的平衡问题,不能以损害言论自由为代价过度地扩大打击面。对于针对个体性利益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行为,主要应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于针对社会利益和政府利益的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行为,主要通过治安管理处罚的方式予以解决。
当下,网络谣言问题比较突出,政府已经开始整治工作。对于何为“谣言”,必须要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对于不同类型的“谣言”,在处理方式上也应加以区别。早在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他还说:“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8]这段论述为今天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思想上指导。从法治精神出发,在充分保障言论自由的基础上,解决网络谣言问题是为上策。如果不分良莠、不加甄别地“胡子眉毛一把抓”式地加以打击,甚至轻易地用刑罚权加以威吓,则将严重损害言论自由和公民的知情权。
收稿日期:2012-06-09
注释:
①如此是将单纯利用网络进行通谋、策划、指挥等传递信息的行为区分开来。
②针对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等的网络有害信息,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③例如,虚拟财产是一个全新的法律现象,可以被归入到自然意义上的“财物”当中,因而可以作为盗窃罪的对象。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诉孟动、何立康网络盗窃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1期。
④为避免“司法上的犯罪化”提法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混乱,本文以“刑罚权出现”来包括立法上的犯罪化和刑事司法对新型行为的法律适用。
⑤参见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说明》,2010年8月23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⑥参见赵秉志、陈志军:《社会危害性理论之当代中国命运》,载《法学家》2011年第5期。
⑦参见时延安:《刑罚的正当性探究——从权利出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由第一条延伸,如果某一犯罪的规范设置会明显地被滥用进而影响乃至侵犯个人权利的话,那么,这样的犯罪设置就是不妥当的;对于公众基于习惯所实施的行为,不应作为犯罪加以规定。
⑧例如,现行《刑法》第221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实际上仅限定为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保护,而对于非市场经济主体的名誉,即对从事社会公益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而言,并不在该刑法规范的保护范围之内。如果仅就这类组织进行诋毁和诽谤行为,则尚无刑法规范提供保护。
⑨根据《刑法》第246条第2款规定,侮辱罪、诽谤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⑩当然,对于这种情形,不予追究显然是不合正义的。在笔者看来,其法律根据为《刑法》第98条规定。理由在于:这种情形也可以归入到“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之中。
(11)张明楷教授即认为,这种情形可以该罪进行处罚。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