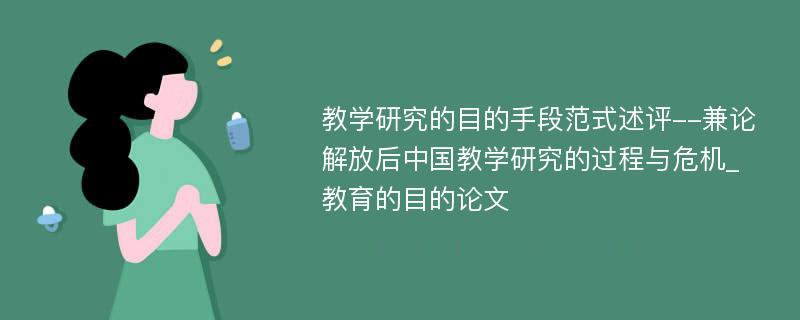
教学研究的目的—手段范式述评——兼论我国解放后教学研究的进程与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研究论文,目的论文,范式论文,述评论文,解放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范式的通则,即问题与问题解决的方式,笔者认为,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是教学研究的目的-手段范式的创始人,在他之前属于教学研究的前范式时期,在他之后,则是教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丰富时期。这里,主要讨论目的-手段范式的确立及其发展轨迹。然后讨论这种范式所面临的危机。
目的-手段范式的确立:赫尔巴特的二元论
教学研究的范式首先始于赫尔巴特,而不是夸美纽斯,这是因为,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并没有提供一种清晰的有关教学的问题-解题方法。他所用的“教学论”(didactics )”一词的涵义比现在对它的意义的理解宽泛得多,例如在他的《大教学论》里不仅谈到狭义的教学,还谈到各种教育: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并且涉及到各个阶段的教育制度:从6岁以前的“母育学校”起, 到18-24岁的专门学院和大学止。因此,确切地说,《大教学论》是“最早的一部‘教育学’,里面有教育原理、教育制度、学校组织、课程、教学法等,相当于现在的‘教育概论’。”(注:林汉达:《西洋教育史讲话》,世界书局1994年版,第111页。)我国翻译出版的《大教学论》, 在“译文序”中称之为“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教育学著作”、“教育学巨著”。
与此相对照的是,赫尔巴特在180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从教育目的演泽出来的普通教育学》(通常称之为《普通教育学》)以及1835年出版的《教育学讲授纲要》,这里的教育学, 德语padagogik, 英语pedagogy,词源于希腊语中的“教仆(pedagogue )”一词, 是由儿童ped,指导者agogue和“……学”的词根-ogy所组成, 它主要是指教学方法和学生管理两方面,并没有后来人们用来替代它的education 的涵义那样广(注:关于pedagogy和education的区别,详见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 教育与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298页。)。因此,他的第一本代表作实际上亦可译为《从教育目的演绎出来的普通教学论》,据此也可以推论,他的教育学体系也就是教学论。他把教育学置于实践哲学(即伦理学)和心理学之上,提出“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明教育的途径、手段与障碍。”(注:[德]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也就是说, 赫尔巴特所构想的教育学“既是一种实践,同时又是一种理论,既是先验思想的、又是经验实证的两相搀半的独特体系。”(注:[日]大河内一男等著,曲程等译:《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这从范式的问题角度来看,赫尔巴特的教学研究体系标志着教学研究二元取向的确立,亦即依目的而言,教育学(教学论)是一种形而上学思辨;依手段而言,它又是一种经验,一种实践。
那第,赫尔巴特如何根据目的-手段来展开他的理论体系的呢?
关于教学目的,赫尔巴特脉承欧洲教育个人道德本位的传统,认为,“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注: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9-260页。)他把道德培养主要集中在“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这样五种道德观念上。他又指出,“教学的最终目的虽然存在于德行这个概念之中,但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教学必须特别包含较近的目的,这个较近的目的可以表达为‘多方面的兴趣’”。(注: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37、12、222页。)在他看来,德行是一种在人身上发展起来的根深蒂固的“内心自由的观念”,反映了认识与意志的关系。也就是说,人只有认识了道德规范,才能产生服从它的意志,并达到自由。教学首先在于培养学生具有多方面的兴趣,使学生具有能正确地决定意志的范围。
此外,他还把教学目的区分为“一种纯粹可能的目的领域和一种完全与此区分开来的必要的目的领域”(注: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37、12、222页。)。前者是为儿童的未来着想,为学生将来作为成年人本身所要确立的目的,也就是说,为成长着的一代将来能从事某种职业实施一定的教育,帮助他们发展兴趣与能力。
关于教学手段,赫尔巴特把教学手段分为管理、教学、训育三部分,其中,管理就是要克服儿童的“不服从的烈性”,以维持教学与教育秩序,为实施教学创造条件。管理的主要措施是威胁、监督、命令、适度的体罚、权威和爱。训育是指“有目的地进行的培养”,目的在于培养“性格的道德力量”。按照作用的不同,他把训育分成“维持的训育”、“起决定作用的训育”、“调节的训育”、“抑制的训育”、“道德的训育”与“提醒的训育”这样6种。 他把训育的措施分成两大类:激发与抑制,其中包括压制与惩罚、赞许与奖励。有些措施与管理相同,但在运用中却有区别,管理主要着眼于当前的作用,而训育注意儿童的未来。
教学是赫尔巴特教育体系的核心概念。他在教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性教学”的概念,把道德教育与学科知识教学统一在同一个教学过程中。他写道:“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样。”(注: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37、12、222页。)他认为要使知识影响道德品质的培养,学生必须对知识发生强烈的兴趣,从而产生坚强的行动意志。这种兴趣还必须是多方面的、平衡的,这样,道德的培养才能是多方面的。在赫尔巴特看来,兴趣既是教学目的,同时又是教学手段。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努力摈弃以往教学中仅仅强调发展学生接受能力的做法,主张给予学生自己活动的自由,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他说“教师在必须确保正在进行的工作能顺利进行下去的范围内,可以给予学生最大限度的自由,这种方式乃是最好的方式”,“仅仅引向死记硬背的学习,会使儿童处于被动状态,因为只要这种学习继续下去,就会排斥儿童通常可能产生的其它思想。”(注: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37、12、222页。)。教学就是“经验与交际的补充”。人通过经验从自然中获得认识,通过交际从社会中获得同情,因此,除了课堂教学,还应重视让儿童进行其它各种活动,主张利用各种力量和场合对儿童开展教育。
赫尔巴特的“手段”观,除了教学的方法、途径之外,还涉及到课程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按两条主线来设置课程,“第一条主线不仅仅包括历史,而且也包括语言常识;第二条主线包括自然科学,而且也包括数学”。他在强调以古典语言、文学、历史为重要教学内容的同时,提出了教授实用内容的主张,建议设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和博物学等。他还指出青少年学习“技术知识”的必要性,“每个青少年应当学习使用木匠最常用的工具,应当象使用直尺与圆规一样出色。使用机械的技巧往往比体操练习有用。前者有利于智力发展,后者对身体有利。”(注: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52-54页。)
对“教学过程”的分析,是赫尔巴特对教学“手段”的本质揭示。赫尔巴特认为,观念是人们认识世界最基本、最简单的要素,它是通过统觉——旧观念对新观念的同化作用而获得的,因此教学过程是观念被统觉从清楚明确的感知、到与旧观念的联系以及扩大到应用的过程,即清楚、联想、系统和方法四个阶段,(注: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52-54页。)俗称“教学四阶段论”。第一阶段既明确地提出教师“教”的具体任务和活动方式,也清楚地规定学生“学”的具体要求和活动范围。尤其是每个教学阶段都围绕着观念心理学的论点,详细划定学生心理活动的范围和内容,使各个教学环节与各种必要的心理活动巧妙地配合,形成严密的教学步骤。如下表所示。
总之,尽管赫尔巴特在追求教育学的科学化时,选定了形而上学和数学作为模式,想把教育作为形而上学的一个部门来考察并以数学的严整性来给它构成一种体系;尽管他试图在“教什么”(实践哲学)和“怎样教”(心理学)的基础上把教育学系统化的构想,反而使他本来所冀求的那种教育学的科学上的独立性落空了,结果,使得其后的教育学导向思辨的伦理学和实证的心理学这两个方向的分裂,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他明确提出了一套问题与解题方法,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正是这种看的方式,至今仍被教学研究共同体所采用,尤其是在前苏联和中国。
表1 赫尔巴特教学形式阶段表
教学阶段清楚联想系统方法
掌握知识环节钻研 理解
观念活动环节静态动态静态动态
兴趣阶段注意期待探求行动
教学方法叙述分析综合应用
目的-手段范式的改造:以前苏联的教学论为例
赫尔巴特范式首先经过他的弟子席勒(T.Ziller)等人的补充与修正,曾经听过赫尔巴特课的席勒信奉赫尔巴特的目的观和兴趣论,但是,就手段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阶段说、中心统合法与五段教学法。他认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与儿童心理发展的程序相当,教学应根据这种理论,并把它作为教材选择与编排的准则,主张要采用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化为中心的教材,来陶冶儿童的情操。中心统合法是关于教材之统合的意见。他还将赫尔巴特四阶段中的“明了”分解为“分析”与“综合”,而成为分析、综合、联合、系统、方法五个阶段,他的学生莱因(W.Rein)继承了赫尔巴特和席勒的思想,但是在教学阶段上,认为席勒所用的名称不适合实际,故改用预备、提示、联合或比较、总括、应用。这就是曾经或继续影响世界各国教师的“五段教学法”。这样,赫尔巴特范式的构成部分经过了第一次的改造或修正。
赫尔巴特范式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继续发展,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经毕业于莱比锡大学与耶拿大学的美国年轻博士的介绍和传播,如德加尔谟(C.Degarmo)的《方法要素》(1989 )以及麦克默里兄弟(C.& F.McMUrry)的《一般方法要素》(1982)的发表, 把美国的赫尔巴特思想研究推向高潮,形成了赫尔巴特学派运动。1895年,成立了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研究会(1910年改名为全国教育研究学会)。以致“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对这个精心建立的体系的兴趣,象浪潮一样,席卷了美国教育界的教师和学生。”(注:F.Eby & F.C.Arrowood,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1934,p.786.) 正如美国教育局在1894年至1895年的报告中指出的:“在今天,美国比德国更为信奉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注:W. F.Connell,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1980,p.61.)到了20 世纪初,“每一个好教师都应该为每一节课准备一份教案,五个形式 阶段都非常明显。”(注:W.H.Kilpatrick,Dewey' s Influence on Education,In:P. A Schilpp (Ed),The Philosophy of JohnDewey.1939,p.465.)后经实用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继承、批判与改造,导致教学研究实证取向的过程-成果范式的产生。(注: 崔允漷:《教学研究的过程-成果范式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4 年第3期。)另一条主线是该范式在前苏联和中国的传播和改造。尽管就其内容而言,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诞生,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下,教学研究共同体对赫尔巴特范式从内容上作了根本的改造,但是就其形式而言,这种范式的问题-解题方式的传统依然予以保留。
在19世纪后半叶,俄国把赫尔巴特学派的许多论著译成了俄文,当时所写的有关教学论的很多著作,或多或少反映了赫尔巴特学派的影响。然而,有关教育和教学的先进思想,主要是在俄国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中真正地发展起来的,其中唯物主义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贡献尤为突出。在谈到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倾向的时候,他说:“这种哲学给科学和思维带来了并且继续带来很多积极的东西,就是教育这种艺术也正应当特别归功于研究工作的唯物主义方向。”(注:[苏]达尼洛夫等著,刘彦等译:《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2页。)他的这种思想在20世纪初继续得到发展。真正使得苏维埃教育学变为“一种在质量上完全新的教育学”的原因是它的理论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苏维埃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1)作为科学一般方法论基础的马列主义哲学, 以及马、恩、列、斯关于文化和教育的学说;(2 )经过批判地改造过了的教育学的历史遗产,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的工作与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俄国进步的教育学对于科学的贡献;(3 )苏联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的现代工作经验,以及家庭教育的经验。”(注:[苏]凯洛夫主编,沈颖等译:《教育学》(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第44—45页。)教学论的伦理学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教学论的认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认识论,心理学基础是建立在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生理学说的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心理学。这样,使得目的-手段的赫巴特范式实现了内容上的根本改造。
从“目的”来看,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指出苏维埃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积极建设者”。(注:凯洛夫主编,沈颖等译:《教育学》(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第58、77、73、73页。)在共产主义方向性原则的指导下,在目的范畴内,提出了“教学目的或任务”,即:“教学是旨在依照共产主义教育的一般目的与具体任务,在学校中有计划地实现下列的工作;以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来武装学生,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有计划地发展他们的智力与道德;在教师领导之下,组织学生的积极活动,以实现这种工作。”(注:凯洛夫主编,沈颖等译:《教育学》(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第58、77、73、73页。)可见,从赫尔巴特到凯洛夫,教育和教学目的从个人道德本位走向以知识为基础并且由此派生的社会道德本位。
从教学的“手段”来看,前苏联教学论丰富并具体化了赫尔巴特的手段观,初步形成了从“手段”展开的教学论体系,“教学法所研究的问题有:关于教学过程的本质及实施教学时所依据的原则,关于教学的内容、方法及组织形式。”(注:凯洛夫主编,沈颖等译:《教育学》(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第58、77、73、73页。)
关于教学过程的本质,依据列宁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把赫尔巴特学派的五阶段改造为6个阶段 (注:瞿葆奎:《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 :(1)授予学生并使他们领会具体的东西,使学生形成观念;(2)理解所学习的客体中的相同点与相异点,本质的、主要的和次要的地方,认清原因与结果、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它各种联系;(3 )形成学生的概念,使他们认识定律、定理、规则、主导思想、规范及其它概括;(4)使学生牢固地领会事实与概括的工作;(5 )技能和熟练技巧的养成和加强;(6)用实践来测验知识, 把知识应用于包括创造性作业在内的各种课业中。这种教学过程的概念是努力建立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上的,与之相对照的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阶段是根据观念心理学来划分的,于是,属于目的- 手段范式的演绎的教学论体系在前苏联已经初步形成,它一直支配着以后的教学论发展,如达尼洛夫等编著的《教学论》(1957)、斯卡特金主编的《中学教学论》(1982)。
目的-手段范式的再改造:中国化的探索
赫尔巴特学说最早传入我国,是在20世纪初。当时正值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之际,由于学校发展迅速,采用班级授课制,对课堂教学的规范化要求非常迫切,一批力图从西方寻找真理、学习西方经验的有识之士,取法日本,那时日本的教育著作都在宣扬赫尔巴特思想和教学方法,他们通过文章、书刊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如1901年《教育世界》出版所《教育丛书》初集第三、四册都介绍了赫尔巴特(原译为海鲁伯尔、费尔巴尔图)的教学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1903年译有《独逸教授法》一册【独逸,即德国(Deutsch)的旧译名】等。 但是,对我国的教学论发展影响最深的还是赫尔巴特范式的“苏联版”,这与解放初期,我国全面引进前苏联教育学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的教师,正如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教师比德国的教师更信奉赫尔巴特一样,比苏联的教师更信奉凯洛夫。直到50年代中期,在反思“中国教育=苏联教育=社会主义教育”这种简单的演绎逻辑时,曾经有学者提出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认为教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注:瞿葆奎:《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 在认真学习马、恩、列、斯、毛关于教育的学说的同时,尝试总结中国教育实践的优秀的经验。这种努力也表现在“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化’探索和教学论水平的代表性之作”——上海师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中,这为“探索教学论中国化的研究方法作了良好的开端”(注:董远骞:《一条曲折的路——教学论发展四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3期。)。80年代初出版的董远骞、张定璋、 裴文敏著的《教学论》,代表了教学论“中国化”探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该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了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批判地总结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学历史经验,注意吸收现代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更能反映我国当前广大优秀教师的丰富的教学经验。该书所揭示的6 条规律是:教学相长;循序渐进;知识技能与认识能力;教学的教育性;教学与学生生理;因材施教。可见,这种探索超越了以前“重视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而重视研究方法尤其是古今中外法(注:徐特立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8—89页。))的转换。教学论“中国化”探索第三阶段的表现是在综合或概括以及理论体系的改造方面。如王策三的《教学论稿》(1985)在“教学论的科学化”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清理和探索”。吴杰的《教学论》(1986)围绕着“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和科学技术在各个发展阶段对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两条主线,对教学理论的知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理。吴也显的《教学论新编》(1991)希望“对原有的教学论从概念到范畴进行必要的调整和突破。”把原先前苏联的教学论框架改造成为五篇:引论,教学过程论,教学构成论,教学实施论,教学艺术论。李秉德的《教学论》(1997)“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我国实际,反映国内外教育研究的新成果,来阐述本门学科的基本理论,使其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该书把教学论分解为“十论”:绪论,过程论,目的论,原则论,主体论,课程论,方法论,环境论,反馈论和余论。由此可见,教学论“中国化”探索第三阶段的重心在于理论体系的改造。不过,尽管我们确实能体会到学者们用心良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仅仅把视界局限在一种范式之内,笔者认为,难以把握教学论“中国化”探索的第三次超越,这从如此众多的学者们所作的不懈努力、付出的巨大的智慧与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似乎值得我们冷静地思考这次超越所面临的挑战。
从人工范式来看,关于目的,由于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占了“隔壁有样”的便利,我国学者几乎就直接搬用凯洛夫的“教学任务”,如,把“教学任务”表述为“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课程中所规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页。)后来, 王策三把我国对“教学目的和任务”的种种表述概括为三句话:“第一,传授和学习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第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学生的智力和体力;第三,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培养学生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道德品质。”(注:王策三:《教学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显然, 这两种称得上“比较好”的表述与凯洛夫的表述只是在语言使用的精炼和准确程度上的差异。近年来, 一些学者强烈呼吁“教学任务必须具体化”, 加上布卢姆(Bloom)等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在中国的全面介绍, “教学目标”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教学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兴趣,并且从不同的年级、学科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
关于手段,在形式上,与前苏联教学论相同之处是,都在讨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效果检查等,但是已经表现出我国学者们在“中国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以上海师大主编的《教育学》为例,该书教学论部分共分三章:课程与教材,教学过程与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与教学形式。以“课程与教材”取代了传统的“教学内容”,这在我国开这种体系之先,又便于与欧美课程理论接轨。近年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波及课堂,因此,“现代化教学手段”这一课题便应运而生,我国的许多研究者对此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并作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对教学方法的探索,更是有一种“遍地开花”的感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6年,在我国公诸报刊的各种新教学方法就有37种之多(注:吴也显主编:《教学论新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1990年有人对“国内教学改革中的新教学方法”作了整理,共为34种。(注:刘舒生主编:《教学法大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虽然这些数字都是不完全或者极不完全的, 但是它说明了“教学手段”研究在中国的深化和扩展。
目的-手段范式的危机:机械论的演绎
若从1806年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问世算起,目的- 手段范式亦有190年的历史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该范式在前苏联和中国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教学研究范式,事实上,民主德国教学论专家克拉因博士1959年出版的《教学论(Didaktik )》(柯新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以及南斯拉夫教学论专家鲍良克1980年出版的《教学论》(叶澜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都属于这种范式。其人工范式一直在改良或修正主义者(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环境中丰富或发展起来的,这些结论代表了这一范式的研究传统或教学论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苏联教学论专家斯卡特金主编的《中学教学论》(1982),以及我国王策三的《教学论稿》(1985)。
目的-手段范式从一开始就是采用哲学的思考, 致力于理论体系的建设(这不同于其它的范式),在它的历史中,已逐渐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也正是这种共识,使得赫尔巴特的体系与凯洛夫的或者可以说王策三的体系都有某种相似之处;也正是这种共识,我们说它的历史是光荣的,它的努力以及对自己目标的追求执著地持续了190年, 而且吸引了如此庞大的研究共同体,在不断地受到批判、责难甚至误解(尤其是杜威为了寻找理智的对立面,把当时美国学校的全部错误做法原原本本地嫁祸于赫尔巴特)之后,它依然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枝独秀”,这本身就说明了和预示着它的生命力。
作为一种范式,“趋同”现象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一旦成为社会-心理上的“情结”,也许就进入误区了,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再多走一步,看来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笔者认为,这一研究共同体似乎已经步入误区,具体表现在:一是“老调重弹”现象,即所有的《教学论》作者几乎都无条件地承认教学论的研究范围是: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教学过程,教学规律和原则,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手段与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的检查(后来加上“教学评价”)等,如此庞大的教学研究共同体如此持久地追求一种理想,这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中是不多见的。有时,一种理论所展开的要素一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理论陈述的具体内容基本上一致那就极不正常了,这就需要进行方法论层次上的反思。笔者认为,“趋同”情结现象的产生,除了钟情于一种范式之外,还与这种范式自身因素有关。目的-手段范式的理论基础是经典认识论,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思辨,思考的方式往往都是演绎推理,这就给滑向机械论的演绎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二是“生搬硬套”现象,如,关于科学认识过程与教学过程的关系,巴拉诺夫批评说,“将列宁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与掌握知识的主要阶段:知觉、理解、巩固、运用联系起来。是一种机械的联系”(注:巴拉诺夫著,赵天译:《论教学本质》,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又如把劳动过程的要素等同于教学过程的要素。三是“……袋”现象,这在我国的教学研究中极为明显,教学理论似乎是一只大口袋,教学研究者扮演着拿来主义的角色,不管合逻辑否、合需要否,都往里装所谓的原则、方法、流派和模式等,以教学原则为例,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 )有5 条; 他总主编的《教育学》(1956)有7条;陈元晖的《教学法原理》(1957)有6条;车文博的《教学原则概论》(1982)列了8条;董远骞等的《教学论》(1984)有7条;王策三的《教学论稿》(1985)有8条,吴杰的《教学论》(1986)有12条;李秉德的《教学论》(1991)有9条, 在这些数字背后存在的问题,就像斯卡特金在批评前苏联教学论中列的教学原则时所说的一样,“教学原则名目繁多,各条原则没有共同的出发点,有些出自教学经验,有些出自哲学,有些出自心理学。”(注:斯卡特金主编,赵维贤等译:《中学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上述例举说明了这一范式已经步入误区,要摆脱这种局面,首先必须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坚持演绎与归纳的统一,坚持证实与证伪的统一;其次必须引进并且从事其它的研究范式,如过程-成果范式、 社会-语言范式,以及近来西方教育文献中讨论较多的一种自我-叙述范式,让不同的研究传统进行平等的对话,以达到新的视界融合,丰富教学论的知识。
标签:教育的目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