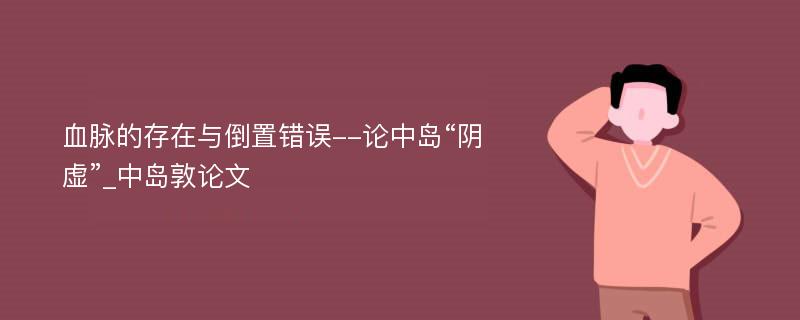
血脉与倒错的存在:中岛敦《盈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血脉论文,倒错论文,盈虚论文,中岛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24(2010)06-0013-05
中岛敦(1909-1942)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出生汉学世家,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中岛敦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不少光耀日本文学史的知名作品。其中,取材于《左传》的短篇小说《盈虚》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盈虚》以春秋时期卫庄公为主人公,其基本故事情节取材于《左传》中散见于定公十四年至哀公十七年间关于卫庄公蒯聩事迹的记载。毫无疑问,中岛敦并不是要依照历史文献来原封不动地塑造蒯聩这个人物形象,而是基于他自己丰厚的汉学素养,以他一以贯之的怀疑主义的思想,给蒯聩这个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人物注入了新的灵魂。如有论者所言:“中岛敦在《盈虚》这一标题下描写出了背负着宿命的人的生死作为、聚散存亡等状况。”[1]也就是说,“中岛敦尝试着将《左传》中生活在遥远过去的人物重新在他的世界中复活过来。但是,这既不单是对过去的再现,也不是死去了的人的重新苏醒过来。既然是在中岛敦的世界中活着,他们就必须是一个经历着崭新生命的人”。[2]像这样,《盈虚》可以视为是中岛敦对于在《左传》中被文字和历史的尘埃所定格的蒯聩这一人物的再解读,其中包含了他对历史,对命运的独到的解释。换句话说,蒯聩在作家的眼里不过是一个风化了的躯壳,是一个被寓言化了的装置,他所指向的内核已远远超越了一个古代中国人的生与死的意义。
在中岛敦所创作的一系列取材于中国古典的作品中,《盈虚》对原典的借用和甄别是最有系统性的,因而情况也较为复杂。本文首先对照《左传》的相关章节来具体检视《盈虚》对它的取舍情况,通过这样的整理来探究中岛敦在这篇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意图。
一、《盈虚》与《左传》的比较
《盈虚》第一段内容讲述的是主人公太子蒯聩在出使齐国途中,路过宋国时听到田野里的农夫在唱歌讽刺自己的继母南子。①太子回国后与刺客戏阳速密谋,企图杀死南子,但由于戏阳速的胆怯而告失败。不得已,蒯聩只好出逃国外。这一段情节依据的是《左传》定公十四年中的如下内容: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彄出奔郑,自郑奔齐。
《盈虚》中第一段的内容和上述引文没有太大的出入,大致情节完全是一致的,作家只是在个别的细节上作了处理。如中岛还将上述引文中出现的农夫所唱山歌的内容做了具体的解释,向不明就里的读者说明歌中的讽刺含义。另外作者在小说中还增加了刺客戏阳速躲在幕布后行刺的情节,这样的想象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让小说的故事情节平添了不少的趣味。《盈虚》中省去了孟彄出逃这一情节,因为它显然与小说整体情节没有任何的干系。
小说《盈虚》第四部分的内容依据的是散落在《左传》哀公十五、六年中的相关记事:
孔悝立庄公。庄公害故政,欲尽去之,先谓司徒瞒成曰:“寡人离病于外久矣,子请亦尝之。”归告褚师比,欲与之伐公,不果。(哀公十五年)
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重酬之,大夫皆有纳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载伯姬于平阳而行,及西门,使贰车反袥于西圃。(哀公十六年)
在这一部分的相关情节上中岛敦作了较大的改动。如按照前引《左传》的说法,蒯聩之所以要将孔悝逐出去是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也就是说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采取的行动。但是,中岛敦有意识地淡化了这样的政治视角,而将蒯聩这样的不义的行为解释为出于他在常年流放生涯中所养成的乖戾、自卑、刻薄等复杂的心理活动。此外,《左传》只是提到将孔悝一人灌醉后放逐了,但中岛敦却将其改成伯姬母子两人都遭到了流放。这样改写的目的无非是想要突出蒯聩暴戾、怪癖得连作为自己恩人的亲姐姐也不放过,读者可以藉此理解蒯聩心理扭曲的程度了。在这个段落里,中岛敦还巧妙地安插进了儿子蒯疾的阴冷、残暴的性格,并指出他这样人格的养成和他从小看惯了人间的阴暗面有关。关于蒯疾这一人物的如此的造型为他后来除掉浑良夫和父亲的举动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总之,在《盈虚》的这一部分中,中岛敦着力展示了登上王位后的蒯聩扭曲的心理。
《盈虚》第八部分依据的是《左传》哀公十七年的下列记事: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与之邑,置之,而逃奔宋。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
在《盈虚》的这个段落中,基本情节的构成与上面引述的《左传》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中岛敦在讲述卫庄公蒯聩在一个秋夜里做噩梦时,加进了一轮赤铜色的月亮这样黯淡、凄凉的景物描写,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一种使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恐怖气氛。这样氛围的营造不仅与蒯聩迎来生命末日的情节相吻合,或许,在作家中岛敦看来,这样黯淡、肃杀的气氛也就是生命之无聊的表征了。中岛敦还写了蒯聩明明通过占卜的方式预知到了马上就要降临的灾难,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任何防御的措施,而是一如既往地沉溺于斗鸡游戏中。蒯聩如此消极地等待死亡,对于灾难束手就擒的态度其实就是中岛敦的虚无、怀疑的生命观的折射,人或许永远也不可能逃脱由一个恶的绝对者加诸自身的命运了。
《盈虚》第九、第十部分主要讲述庄公死亡的经过,依据的是《左传》哀公十七年中的如下内容:
初,公登城以望,见戎州。问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难作。辛己,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阖门而请,弗许。逾于北方而对,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逾从公,戎州人杀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与汝璧。”己氏曰:“杀女,璧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
《盈虚》中这部分内容的基本框架与原典《左传》中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庄公驱赶戎人部落,将己氏之妻的秀发剪掉充作自己宠妃的假发,最后庄公死于己氏之手等都是遵循原典的内容。但是,中岛敦为了契合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同样地对原典中的相关内容做了变更。从上面所引用内容中也可知道,在《左传》中,太子蒯疾是与父亲一道出逃的,在途中为戎人所杀。这样的改写不仅与前面对蒯疾这一人物设定相呼应起来,也将这场子弑父的悲剧推向了最后的高潮,进一步地深化了主题。
二、存在的虚幻
以上花费了较大的篇幅来具体比较了中岛敦的创作小说《盈虚》与中国古典文献《左传》之间的取舍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来:《盈虚》的基本故事框架虽然取材于《左传》,但它并不等同于对于该原典简单的剪辑和串联,而是通过对于原材料的重组、取舍来表达了作者独特思想。总之,《盈虚》是日本现代作家中岛敦创作出来的一部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小说。如何透过古典题材来阅读出隐藏其中的现代思想是读者在阅读《盈虚》时所必须具备的问题意识了。
小说《盈虚》显然存在着表层和深层这样的双重构造。它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古代中国人的悲剧性的一生,而它在深层结构中指涉的则是现代人存在的悲剧性的现实。换句话说,《盈虚》可以当作一个以古喻今的寓言文本来加以读解。中岛敦之所以要将小说的主人公设定为古代中国人,是因为这样的设定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为审视自我提供了有效的距离。也正因为《盈虚》的主人公是中国人,舞台是春秋时代的中国也就越发显示了中岛敦关于人类的存在这一思考的普适性了。
蒯聩作为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公子,在中国封建王位继承制度下,作为太子的他若不出现意外的话,本应很顺利地走向作为绝对者的权利顶峰的。然而就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微不足道的事情使得他成为绝对者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波折。在蒯聩出使齐国的途中,听到宋国农夫唱山歌讽刺他的父亲卫灵公和其宠妃南子的淫乱生活,于是就动了刺杀南子的念头。这场刺杀计划因为刺客戏阳速的临阵胆怯而宣告失败。于是,蒯聩的灾难就降临了。他先是在晋国度过了3年的亡命生活,后来更是在戚地寄人篱下长达十三载,直到在他出逃后的第十七个年头才在姐姐伯姬的帮助下返回故国,并通过宫廷政变取得王位。中岛敦只用了寥寥数语就高度概括了这一人生经历的剧变对蒯聩所带来的伤害:“在成天目睹着黄河水度日的十余年里,曾经的那个任性无常的白面贵公子,不知不觉间已变成了一个刻薄、扭曲的中年苦命人了。”[3]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会导致一个人的存在形态的全面崩溃,这就足见自我与存在的虚妄性了。以此为接点,《盈虚》的主题就和所谓“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一中岛敦文学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连接了起来。中岛敦那带有浓厚怀疑主义色彩的对于存在依据的质疑自从在他的早期作品《过去帐》(《狼疾记》《变色龙日记》)中明确地被表述出来后,这一主题一直以各种形式在他的文学中被复制着,成为了贯穿其全部文学的重低音。可以说小说《盈虚》就是这一重低音的一个变奏了。中岛曾在《狼疾记》中对人的存在本质发出了如此的质疑:“事物必须要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着的理由在哪里呢?应该是与现在的这个样子完全不相同的了。而且像现在的这个样子难道不是可能存在的样态中最最丑陋的了吗?”当然,他这种对于事物的怀疑也会自然地过渡到对于自我的怀疑了。所以,中岛敦借《狼疾记》中的主人公三造之口这样述说道:“就是在想到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他也认为长着那样一双眼睛,长着那样一个嘴巴(中略)以及具备那般全部形象的一个男人为什么就会是自己的父亲呢?凭什么自己一定得要和这个男人之间有着亲近的关系呢?”像这样,在他的自我怀疑中夹杂着自我憎恶的情绪。这样的自我憎恶的情绪是以对父亲的审视为契机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世界当然是特指人的世界,而人的世界是以血脉的形式代代相继的。中岛敦正是在这个维系着人类世界存在的血脉中看出了虚妄性来。血脉承上启下,不知其所来,也不知其所之,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令人战栗不止。《盈虚》中描写了父与子之间的纠葛,继续着《狼疾记》以来的关于阴晦的“血脉”的书写。换个角度来看,以子弑父为题材的《盈虚》可以视为中岛敦要斩断虚妄血脉根源的宣言书了。关于人类所背负的“弑父”宿命的探讨,早就在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故事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就已表现出来。俄狄浦斯从阿波罗的神谕中得知自己将要杀父娶母,他企图从这个命运的魔咒中逃脱出来。但是,他为了逃避命运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反而导致他实现了这个神谕的魔咒,终究未能跳出荒诞命运的怪圈。若说俄狄浦斯讲述的是人类在无意识中犯下弑父行为的悲剧性的话,那么,《盈虚》则是揭露了人类心理意识中潜在的弑父暴力性。两者都是在透过血脉这一视角拷问人的悲剧性的存在。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主人公蒯聩的人生轨迹,中岛敦将这一偶然事件与血脉的偶然性并置起来,凸显了人的存在在本真意义上的荒诞性。
中岛敦在《盈虚》里着力描写了存在于蒯聩父子间的紧张关系。就这么个为所欲为、专横霸道的魔王蒯聩在自己的孩子蒯疾面前总是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显得是战战兢兢、噤若寒蝉的了。小说《盈虚》中有一段这样的内容:
而且,儿时的不幸遭遇,使他看到的尽是人心的阴暗面了。有时候,会在他的身上闪现出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可怕的刻薄相来。由于小时候被过分溺爱的结果,如今一直是儿子不逊,老子忍让。当父亲的也只有在这个儿子的面前才会流露出别人怎么也理解不了的软弱相来。
中岛敦在青少年时期与父亲中岛田人的关系非常紧张,这在他早期作品《在游泳池边》中就有相当露骨的表露。只不过在这篇作品中,中岛还只是泛泛地就事论事,所描写也不过只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与父亲之间的冲撞,并没有太多的深意。尽管如此,透过这篇带有私小说风格的早期习作,可以看出中岛敦在很早的时候就已显露出对于血脉的困惑与思考。这一思考在经过了《狼疾记》等阶段后,最终在《盈虚》中得到了一次总的清算。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游泳池边》还是《狼疾记》都是以孩子的视角为主的,孩子们企图通过对父亲的审视来找到自我存在的依据。但是,在《盈虚》中作者颠倒了以往的视角,从父亲的角度来打量孩子,以图对血脉乃至于存在的根据作出新的思考。一般地说,相对于父亲而言,孩子通常肩负着他者与自我的分身这样的双重角色。从外在的形式上看,父亲与儿子当然是有着独立人格的个体,互为他者。但是,父与子作为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由于血脉的牵连,儿子又可以看作是父亲的分身了。也就是说,做父亲的正是通过对儿子这一分身的审视来完成对自我存在的反观了。《盈虚》中的太子蒯疾是蒯聩在落难岁月中唯一的安慰,两人相依为命。从结果上看,常年流亡生涯中的屈辱体验在这对父子身上打上了同样的烙印。寄人篱下的父亲蒯聩常年都生活在愤懑、憎恶的情绪中。他憎恶代替自己作了卫侯的儿子蒯辄,也憎恶那些冷落了自己的王公大臣,“造成自己流亡的罪魁祸首先君的夫人南子在前几年已经死去了,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憾事了。把那淫妇抓起来,施以百般侮辱后再处以极刑,这是他流亡时代最愉快的梦了”。在这样极端憎恶、愤懑情绪的支配下,蒯聩渐渐地变得尖酸、刻薄起来了。与蒯聩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在儿子蒯疾的“身上闪现出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可怕的刻薄来”。儿子不仅是映照自己扭曲心理的一面镜子,在儿子的血液里还奔流着自身的毒素。渐渐地,蒯聩清晰地感觉到儿子已成为加害自己的一种恶的象征,他也因此看到了血脉所呈现出来的可怖的面孔了。如《盈虚》中所言:“如今一直是儿子不逊,老子忍让。当父亲的也只有在这个儿子的面前才会流露出别人怎么也理解不了的软弱相来。”或许,读者很难理解何以一向为所欲为的父王在面对着自己的儿子时会是如此的战战兢兢的。从表面上看,太子蒯疾曾经当着父亲的面杀死了他的亲信浑良夫,甚至在后来还与大夫石圃一道勾结晋国的反对势力将蒯聩逼上了绝路。但是,这些都不过是表象而已。毋宁说,蒯聩所感到的是一种更为深刻得多的、透彻骨髓的绝望和恐怖了。由一代又一代的血脉勾连而成的存在的长河不过是一个充塞着无限荒诞的黑洞罢了。深秋里的那个噩梦已向蒯聩预示了厄运的来临,但是,蒯聩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防御措施,依旧沉湎在了斗鸡游戏中。他深知反抗的徒劳。
在《盈虚》中,中岛敦通过对作为人类存在表象的血脉关系的透视,再次指出了存在的虚妄性,带着浓厚的怀疑主义的色彩。在中岛敦看来,有一个恶意的超越者高高地凌驾在世界的上头。正如《山月记》中的李征所认为的那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完全不明白其就里。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毫无由头地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命运,稀里糊涂地活下去就是我们生灵的宿命。”李征所抱有的这样无奈的心境与《李陵》中司马迁的绝望是一脉相承的:“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招致这样的结果,最终也只能说是‘太恶’了。可是,是哪里恶呢?究竟是我的哪里?我哪里都不恶。我只做正确的事情。非要说恶的话,那就只有是‘我在’这一事实是恶的了。”有论者像这样评价《盈虚》:
使得弑父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绝对者”,可是,正如文中所写的“是小时候溺爱的结果”那样,公子疾的性格的养成,是和庄公的培养方法的失败有着很大的关联的了。此外,尽管通过梦已经预示了不祥的未来,但庄公只是想“在那灰暗的预言实现之前,尽可能多地享受快乐。”像这样,他的失策也是不能忽视的了。……可是,庄公就因为生了太子疾以及他所拥有的享乐主义的倾向(也因为这个才导致了教育孩子的失败)这两方面的原因而招徕了死亡,比起仅仅是因为性格而导致悲剧的李征来,庄公要回避灾难的难度就大多了。所以,和《山月记》相比较起来,就能明白超越了人的努力和能力的“绝对者”的存在这一事实与小说《盈虚》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了。[4]
这里所谓的“绝对者”就是作为恶意超越者的命运。此外,还有学者是这样谈到《古俗》的:
当然,《古俗》作为一则故事同样是可以归纳出其情节的大要的了。但是,倘若要问,为什么他们(主人公)一定要遭遇到这样的不幸呢?就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了,这当中就包含着单用性格这一托词无法解释得清楚的东西。(中略)如果说人苦恼于很难说清楚内在于自身的性格是《古谭》的主题的话,那么可以说《古俗》是以自己被无可奈何的外界和世界的秩序压得粉碎的历史的必然性(这也许就是世界的恶意的内核了)为主题的了。[5]
这也就是武田泰淳所说的“对于世界苛酷恶意的卑屈的恐惧了”。
像这样,中岛敦通过一个古老的“弑父”故事颠覆了代代相承的血脉的正当性,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拷问了人类存在的确定性。不用说,在他的这一颠覆性的书写行为中,他使用的是他一以贯之的怀疑主义的武器了。
注释:
①本文中《盈虚》的中文均为笔者译自中岛敦《中岛敦全集》,东京:筑摩书房,2002出版,以下不一一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