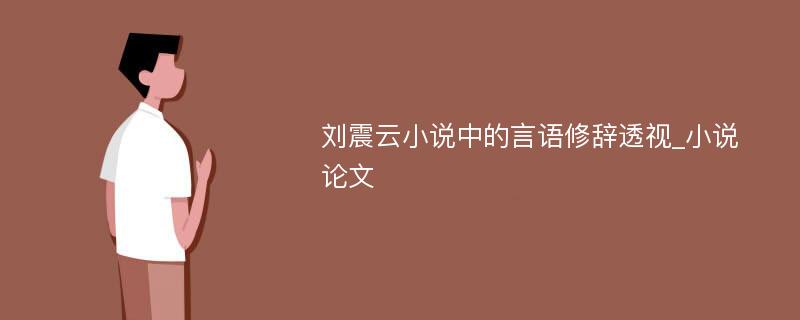
刘震云小说的言语修辞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透视论文,言语论文,小说论文,刘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震云是以一篇《塔铺》走上文坛的。之后,随着《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等中篇的问世和引起的轰动,确定了刘震云在文坛的地位,成为“新写实”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对个人命运浮沉的有距离的冷静观注,对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洞幽察微,以及巧妙的反讽修辞,这一切构成了刘震云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本文试图从语篇修辞角度,按照作者、叙事人、读者和叙事语言,语篇(文本)的结构特征这两个层面,来探讨刘震云的小说。
叙事人与叙事语言的修辞效果
1.叙事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
在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学体裁的言语修辞分析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小说的叙事性和虚构性特征。作者与读者之间在小说中的交际关系是通过作者的委托人——叙事人来实现的。因此,研究小说作者对读者的“控制”,首先应当研究小说中叙事人称的选择和叙事语言运用的技巧。
综观刘震云小说,从《塔铺》到《新兵连》再到《单位》、《一地鸡毛》及至他最新的两个长篇《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我们不难发现其小说叙事人称运用的变化轨迹。
《塔铺》、《新兵连》是第一阶段。刘震云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叙事人“我”是参与情节发展的。故事在“我”的眼中展开,这种叙事把心理描写限制在既是叙事人又是人物“我”的范围之内。
《一地鸡毛》、《官人》、《单位》等则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属于刘震云叙事人称运用的第二阶段。第三人称叙事人属于所谓“虚构世界”的“上帝”。他知道小说里每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和每一事件。在刘震云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中,叙事人严守“不介入”原则,即不直接评论事件或人物,作者的态度只有通过叙事语言的语气来把握。
《故乡相处流传》则属于第三阶段,虽然又采用第一人称,但与第一阶段第一人称不同。这里的叙事人既可以参与情节直接评论人物,同时又能像第三人称叙事那样直接进入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
刘震云叙事人称技法的变化并非“纯技术”的探新,这是和他本人描写重心的变化相吻合的。即针对不同描写对象选择最适合的叙事人称手段。
《塔铺》、《新兵连》的自传色彩很浓,作家在关注“一群”处于命运转机的人的同时,对作为一群人中的“我”则倾注了更多的情感。这时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十分自然。《塔铺》有一个非常“老式”的结尾方式(写景、分离、抒情):
暮色苍茫,西边是最后一抹血红的晚霞。
我走了。
走了二里路,我向回看,爱莲仍站在河堤上看我。她那身影,那被风吹起的衣襟,那身边一棵柳树,在蓝色中透着苍茫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中,犹如一幅纸剪的画影。
《塔铺》是刘震云的成名作。作者在《塔铺》中已显露了叙事语言的机敏,甚至有些刻薄的倾向。但是,他在这篇作品里叙事语言抒情和感伤的一面更值得注意。引文中这样富于诗情画意的叙事语言在小说中仅此一例。《新兵连》也有一个分离性结尾,写到三个月“新兵连”生活结束。排长送我到车站,这是个非常落寞的场面。前面还夹带了一个坏消息:
“信上说,老肥死了”
……
火车已经嗷嗷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两个分离性场面,都呈现一种叙事语言所表现的外倾的情感投注。这在刘震云第二阶段是没有的。因为是第一人称“我”在叙事,所以分离性场面中共同的感伤气氛很自然地在言语中体现出来。
告别《塔铺》、《新兵连》后,刘震云又把重心投向都市机关大楼中大小人物尴尬的生存处境。这时的刘震云完全摒弃了感伤和自恋的自我观照,以一个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视角审视官场、城市文明幕后复杂的关系。这时候我们发现刘使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型”的叙事方法更加得心应手。这个总是“在场”的叙事人聪明、睿智,他不指陈或评论什么,但总是把我们熟视无睹、耳熟能详的事实通过不动声色的叙事语言“原生态”地呈现出来,形成叙事人与读者共同认可的荒诞感以及审视这些荒诞事实的平常心态。
从批评界的态度和读者的反应看,第二阶段是刘震云叙事语言运用最为圆熟的一个时期。《单位》、《一地鸡毛》等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都是产生于这个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刘震云在他最新的一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中又重新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但这和他第一阶段那种视角有限的第一人称叙事又有质的区别。这是一反刘震云以往写实的笔法的。作品的所谓四个历史时期:东汉末年、明初、清代、大跃进时期,人物再生轮回,古代话语与现代话语贯通,叙事语言呈现突梯、滑稽的特色。这种第一人称叙事还不受“我”这个情节参与者的限制,既可以有自己的心理独白,也可以进入别人的心理。这一叙事手法从修辞效果看有两个便利:首先,排除了一般第一人称叙事范围的局限。其次,这种看似荒诞的叙事方法,使叙事语言产生了喜剧效果。“我”随时在叙述时频发“怪论”,而这又是第三人称叙事所不能及的。
刘震云叙事手段的发展过程是和他小说主题和题材相对独立的三个阶段大致吻合的。描写个人经历和情感的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揭示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一类则用第三人称;而反思历史变迁一类的则采用了他独特的“全知型”第一人称。这种变化,显然是作者为了最好地表达自己意图,在修辞上的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故乡相处流传》的叙事方法、叙事语言是否成功,现在定论为时尚早,但作家在修辞上敢于突破自我的尝试应得到肯定。
2.叙事语言产生的情感控制
一篇作品的开头往往能为全篇的叙事语言定下基调,也是叙事人与读者共同进入默契的虚构世界的第一扇门。刘震云所追求的“俗人叙事”话语和平静的叙事语气,可以从他有影响的几个中长篇的开头看出:
到新兵连的第一顿,吃羊排骨。——《新兵连》
“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单位》
小林家一斤豆腐馊了。——《一地鸡毛》
二楼的厕所坏了,有人不自觉,坏了还继续用,弄得下水道反涌。——《官人》
一到延津,曹丞相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的脚气便发作了……——《故乡相处流传》
“羊骨头”“豆腐”“厕所”“梨子”这些俗而又俗的语词使读者既能领悟作者刻意追求的平俗色彩和作者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昭示了叙事人与情感流泄和诗意的绝缘。小说叙事语言所表现出的这种让人时常啼笑皆非的饶舌、唠叨,十分能传达刘震云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家表现凡夫俗子们日常生活困顿、尴尬的创作意图。这里,叙事人首先在语言上取消了自己“比读者高明”的传统叙事人的定位。
这个阶段,刘震云的叙事语言节奏呈现出舒缓而繁简得当的效果。我们以《一地鸡毛》为例:因为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小说就按“豆腐馊了”、“调动工作”、“老家来人”、“女儿入托”依次推进,在琐屑如鸡毛的生活流中,叙事人的语言很自然地脱卸感情色彩和“故事讲述人”的神秘感,只浮现出一层微妙的反讽色彩,很难把握。看似平淡至极的陈述句,十分能凸现作家内敛的无奈悲哀的倾向。“豆腐事件”之后,第一部分这样结尾:
老婆入睡,孩子入睡,保姆入睡,三个人都响起鼾声,小林检查了一下屋里的灯火水电也上床睡觉……小林突然又想起今天那一斤变馊的豆腐,……明天清早老婆起来看到它,说不定又会节外生枝,于是又从床上爬起来,到门厅打开灯,去处理那包馊豆腐。
在这种有节制的唠叨中,在陈述句的明显的拖沓中(开始三个并列的短陈述句,以及后面的细述),读者完全能体会到叙事语言后面的“疲劳”和“冷漠”。
刘震云的叙事语言不仅在一般认为是琐屑的叙事客体上显示“冷漠性”和反讽色彩,即便是传统意义上庄严和重大、乃至悲剧性对象,也坚持使用自己视点的叙事语言。叙事不仅是一种对世界的反映形式,而且成了马丁·华莱士所说的成为“理解生活”的“解释方式”。本应是庄严气派的场面,在刘震云笔下重构之后,失却了我们成规意义上的肃穆感。刘震云在《新兵连》里写了一次军内大检阅,军参谋长、乃至检阅部队的军长,却不过是些“老头”。大家翘首以盼的军长是“胖胖的、脸皮有些耷拉、眼下有两个肉布袋”的人。作家放弃了对场面恢宏的描绘,而是集中笔墨写了个十分真实可信的小失误。老肥反应有些迟钝,但为了“上进”又特别紧张,千万人群中,大家三个音节喊完惟独一人多出一个“苦”字回荡在阅兵场,庄严场面受到影响,喊“苦”字之人自己亦是尴尬,懊悔不已。
这就是刘震云叙事语言提供的新视角,是刘震云独有的叙事语调。
平静叙事不仅贯穿在描写生存尴尬,人性缺失的新写实的中篇,在两部所谓的历史题材的长篇里也很突出。中国的读者在《三国》、《水浒》以及后世的《红旗谱》、《李自成》等历史小说的传统中,已经形成了对厚重、沉稳的“伟大叙事人”的阅读期待。在以往的历史小说中,叙事人始终保持一种对历史事件的尊崇。这在叙事语言的风格上可以得到确证。而刘震云的叙事语言则动摇了读者和作者在这块领域合作的成规。从观念角度论,是和作者试图重构历史话语解释权相一致的,而在语言上,则提供了一种新鲜的审美愉悦。他还是用唠唠叨叨、琐琐屑屑的叙事来还原他眼中遥远和并不遥远的过去,庄严和并不庄严的历史。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天下黄花》中反复出现饥馑、杀戮和死亡的场面。但他的叙事语言并不煽起读者恐惧、憎恶、悲悯等强烈的感情,相反,常常伴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起到了隔离叙事人与叙事客体的情感距离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把读者的情感投入控制在一定程度。
松散的句式和缓慢的语句节奏,及故意游离中心的节外生枝的插叙补叙,这些都是作者叙事语言控制情感投入的突出手段。
3.“作者的声音”并没有消失
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郑重提出了“作者的声音”这一命题。“作者的声音”可以理解为思想和倾向的外显。作者本人当然不能在虚构的世界(fiction)中出现, 因此“作者的声音”只有从叙事人、委托人和叙事语言中捕捉。在对刘震云等为代表的新写实作品的诘难声中,突出的一条就是“作家的集体退隐。”显然,这是有欠公允的,至少从叙事学所体现的修辞关系看不够客观。
在刘震云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叙说”和“显示”的统一,而刘震云特别侧重讲述(叙说)。讲述其实是一种人格化的显示(描写)。他提示我们有人正在反映一个过程或存在。而“显示”(描写)则尽量隐去“是谁在讲”这一因素。在刘震云小说中有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我们称之为“代言性心理描写”,即主要以叙事人的间接引语代替直接引语式的心理描写,在叙事语言上体现了“叙事人”的“在场”和影响。通过叙事人的转述,我们感到了委托人的存在和作者的倾向。如《官场》中有一段描写金全礼的思想活动:
……我们处理问题不妥,讲人情不顾党的原则,把你陆文武拉到这个位置试试。谁不讲人情!不讲人情你能当地委书记,你坚持原则,为什么省委书记来考察就惶惶不可终日,一下准备两套饭局,都是马列主义装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只照别人不要紧,就是害了别人,说不定……
本来这是小说中的一段心理描写。金全礼提拔的事被陆文武黄了。金全礼愤愤不平。细究起来这段描写很符合当事人彼时彼刻的心态。但在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操纵和介入的效果,是一种“叙说”和“显示”的结合。这么有条理和清晰的语言不可能是人物意识活动的纯客观的“显示”。例像是两个人面对面的质问。像“马列主义装电筒”这样的套语的使用,明显地表达了通过叙事人转述后对金全礼的反讽态度。又如《温故一九四二》一段描写更是耐人寻味:
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庐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这是刘震云第一篇历史题材小说。他以一个平民作家独特的眼光追思一九四二年河南旱灾和腐败政治给三百万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其中有一段写到作为政客的蒋介石从集团利益出发,漠视民众的情形。蒋的“思索”语言属于间接引语式描写,巧妙地打上了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色彩,明显具有反讽意味。刘震云并没有就此带住。后面千万灾民的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语义上的急速顿降的修辞格的运用使作家流露出的对蒋的否定更加明显。
这让我们想到罗兰·罗尔特的问题“这里是谁在说话?”(注: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94 页。)这种代言性的心理描写,把人们带入小说世界和人物世界的同时,也让我们分辨出后台“作者的声音”。布思在得出“作者介入是绝对必要”这一前提时指出:“小说的阅读有一种基本要求,读者需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他应站在哪里—— 即需要知道作者要他站在哪里?”(注:W·C·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震云小说中叙事人这种间接引语式的心理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反讽倾向,正是作者介入的一种更巧妙更隐蔽的方式。
《单位》、《一地鸡毛》中都有一个小林,大学毕业分入机关时意气风发,不拘小节,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压力的阴影,逐渐蚕食了他鲜活自由的个性。在叙述这个人物平淡的文字后面,可以寻觅到作家同情和辛酸的声音。
小林是来得最早的一个,来时换了一身破军装,瘦弱的老婆看他换衣服,不由伤心起来说:“小林,你不要去,别这么低三下四的,我看着你心里难受。”
小林说:“我何尝想帮这些王八蛋搬家?可为了咱们家搬家,就得去给别人搬家。”
——《单位》
这一段叙述中,几个词语的选用很能表达作家的态度。写小林换了一身“破军装”,突出了小林这时外在形象和内在心灵共同的凋蔽,以前“静静的”、“眉清目秀”的小林妻,现在成了“瘦弱”的老婆。这些都表达了作家对“破衣”、“瘦妻”的现状的同情的一面。(当然也有反讽的一面)
同样,在《一地鸡毛》中,叙事人对小林的平淡叙述语言中,处处显示出日益尴尬困顿的生活空间对小林的压迫和小林被同化、麻木、顺应的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微妙的批评倾向。
有人批评新写实小说叙事人的冷漠和撤退,其实刘震云往往是以一种表面的平静吐出作者的声音。这种叙事语言的平淡,正是台后作者不平静的心绪的体现。
语篇结构的修辞特征
1.“冬季情节”模式
巴尔特曾说:“行为序列构成了可读性文本或可理解的文本的结构的坚甲,它们提供了既具有顺序性,又具有逻辑性的秩序,于是成为结构分析最势衷研究对象之一。”(注: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06 页。)现代叙事理论认为行为序列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小说的“形态学”特征就是叙事,研究小说文本的结构组成,实际也就是研究情节构成方式。受普罗普关于俄国民间神话情节功能出色的研究成果的启发,结构主义和当代叙事学的研究者也企图寻找小说情节的所谓“普遍的内在结构”。这种努力的动机肇始于这样的公设,即人类喜欢构造有结构的故事,而根据结尾来解释开头的思维方式,一直牢牢存在于我们关于历史、生活和虚构的观念之中。对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形式分析远没有普罗普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结构的功能性分析的结果那样令人鼓舞。但在诸多的情节的理论中,我们愿意采用诺思洛普·弗莱的原型情节或规范情节的理论,来解释刘震云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弗莱的四种叙述类型(mythoi)——春、夏、秋、冬同时又是定型的情节和主题结构或对世界的看法。冬季情节模式,即弗莱所概括的“与罗曼史正好相反,表现的情节呈反讽模式,寻觅以失败告终,社会没有得到改造,主人公懂得了除死亡或发疯外,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出路。”(注:同上书,第329 页。)我们几乎不需费力就把刘震云的小说叙述类型,归入冬季叙事类型。
刘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冬季色彩”。《塔铺》的“复员务农——进高复班——爱情萌芽——高考录取——爱情失落”的情节构架也许可以归入“暖冬”型。
而《新兵连》以后的作品,愈来愈呈现出“冬季”模式,对事件和人物的否定性越来越强。人物的每一次行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及至最后的结局,都显示了作者对他指喻性(refrential)十分清楚的虚构世界(fiction)的价值否定。 比如每篇作品都假设一个相对封闭的“单位”——复习班,新兵连,单位(处、局),延津县。
每篇小说都有一个在社会结构中“向上运动”的趋势——入党、当骨干、考大学、升迁、 抢做皇帝等等, 由这些构成小说的基本框架(setting)和行为模式。谁得谁失,谁浮谁沉并不重要,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所有文本中对“向上运动”的否定。作者自称不是一个观念先行的作家,但他作品中形成的模式和内在统一性,再次确证了文学作品的结构修辞与作家无意识自我的紧密联系。
“向上运动”可以分解为几个“行动”:
A.由于不平衡而行动——B.遭遇挫折——C.行动失败,或上进目的达到,但其成功的意义被否定。
《塔铺》里还有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李爱莲”与“我”。而那些自私自利的同学已经受到否定。到了《新兵连》,除了参与情节的“我”之外,那些原本单纯质朴后又变得扭曲可怜的农村青年皆被否定。到了第三人称叙事阶段,刘震云笔下的人物及其行为皆被否定。如小林的“入俗”“现实”被刘震云否定。《官人》、《官场》中的大小官员们为了升迁和保位,费尽心机的表演,受到不动声色的嘲弄。至于历史题材中,无论是《故乡天下黄花》里数十年里为争夺一个村落的印把子的历史,还是《故乡相处流传》中争夺天下的闹剧,无不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新诠释。因此,我们认为刘震云小说情节模式始终属于一种否定性结构模式。
2.结构上的周期性波浪式推进
可读性(Lisibilite)小说控制和保持我们阅读兴趣建立在两个支点上:第一,我们对一个或一组有开端、展示、高潮、结束这样一个情节周期的期待;第二,我们阅读行为中感受到的意义与我们重新审视这种生活经验的愉悦。前一种就是通常所说的“故事性”;后一种就是“现实性”。刘震云小说是怎样在结构构造中吸引读者的呢?我们以为其结构上的“波浪式”特质和细节叠构的精巧性是其主要的语篇修辞手段。
刘震云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时间跨度短的中篇;另一类是时间跨度大历史性题材的长篇。这两种类型都以各自的波浪形曲线推进。《故乡天下黄花》虽然人物有连续性,但整篇小说分成几个均匀的块段:村长死了,鬼子来了,翻身,文化四个部分。 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倒V字型结构(注: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0页。),A展示,B冲突引进,BC上升活动,C高潮,DC转折。 四个倒V的波浪结构的复叠, 是和刘震云小说“古今一也”的先行的历史观念一致的。同样《故乡相处流传》也是有意切割成四个并不毗邻的历史块段:在曹丞相身边、大槐树下告别爹娘、我杀陈玉成、六○年随姥姥进城。
从情节看,第一部分已经形成一个周期,在语言上第一个周期也最漂亮、有力。二、三、四都是第一个周期的翻版。我们在第一段已经完成了“情节期待”和现实性的指涉性联想。刘震云甚至可以说是有些不知疲倦的再来了三个波浪,究其结构修辞的效果看:三个复叠已经产生了阅读疲劳,但这也许和刘震云先行的历史观相通:历史是一种让人厌倦的重复。连续的复叠正好加深了小说的“否定性”。
同样,刘震云的大部分中篇也呈现出波浪式结构。其波型是:困顿——契机——上进——失败。
人的浮沉得失就在命运(或者说巧合)的捉弄下不断漂移。一直到作者限定的时段叙述结束或者由小周期延续而形成的一个大的倒V 字封闭。《一地鸡毛》在语言和结构上堪称刘震云新写实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此篇中最多地使用了其熟谙的“合情合理”的偶然性联结方式,即运用偶然性来推动情节周期性波动的修辞手段。《一地鸡毛》没有《新兵连》《单位》等有一个明显的“向上运动”的大周期统领,而是由细节串连的,但也就是在似乎是细节连缀的“生活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对情节结构操纵而形成的“周期性”波动。
这种靠“合情合理”的巧合而构成的周期性情节推移,在刘震云其他中篇里也不乏其例。我们常因为被其情节链上的细节指涉的世界所吸引,被“合情合理”的现实感所征服,而忽视了作者在情节结构上的修辞痕迹。
3.通过细节的连缀推动情节发展
所有读过刘震云小说的人,无不为他叠构的细节所折服。细节在刘小说结构中属于“基本功能单位”。通过细节的连缀,情节缓缓推动。反过来,小说的整体框架结构,又是为他一个个精心叠构具有强烈的指喻性和象征性的细节服务的。
细节在小说中具有“指喻性”,它使人感到小说世界的可靠性。而另一类细节的功能,则是其象征性。刘震云小说的细节,往往是“指喻性”和“象征性”的统一。《单位》的开头,从机关分梨始,分梨即是情节开始的一个端点,梨的分法,烂梨的处理等等,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使心领神会的读者自然进入小说世界(指喻功能),同时分梨的每一小段(抢占篓子回家装杂物,抱怨烂梨)过程,又映射了“单位”里人际关系的一个层面(象征功能)。
刘震云小说世界总体上反映出一个共同主题:对社会中“上进的人”,以及由“上进的人”构成的社会的批判。有了这样一个参数,刘震云如此不厌其烦,鸡毛蒜皮而津津乐道地推出密集的细节,都可以在结构功能上得到阐释了。
值得注意的是刘震云不仅在《塔铺》、《单位》等写俗人俗事的作品中靠细节构成情节周期,再由情节周期波动反复来完成叙述框架,而且在所谓的历史小说中,刘还是运用现实指喻性很强的细节完成情节周期。这种细节,叠构构成了语言运作的一种“游戏性”。显然,这种“游戏性”是受他历史小说中“古今一也”的观念支配的。
标签:小说论文; 刘震云论文; 一地鸡毛论文; 新兵连论文; 塔铺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故乡天下黄花论文; 文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故乡论文; 第一人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