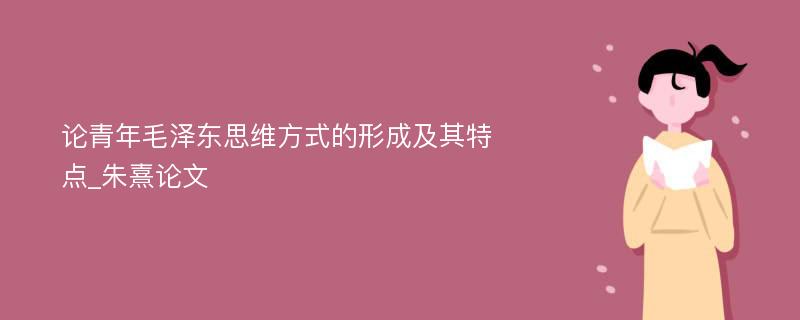
论青年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形成和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特征论文,青年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圈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5)01-0024-09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集中表现为毛泽东思维方式,因此,考察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形成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毛泽东思想,而且对考察唯物辨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及生根,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变革和被超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一考察的前提,是弄清青年毛泽东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为此,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一)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反映现实的方式。它是人们千百万次实践和认识的结果。人的实践活动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逻辑的格,就使这些格获得了公理的意义,也即定型为思维方式。因此,思维方式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实践条件,也就产生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在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形成的,这种环境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既是一种理性思维,又带有深重的非理性色彩。
自然经济是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分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这种生产方式造成人们的生活条件相似,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和各种不同的才能,相互之间也十分隔绝。这种生活和生产环境,也就使人们往往以神学和愚妄等种种非理性思维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在欧洲的中世纪,神学就具有无上权威,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和神学,科学和哲学都处在神学的禁锢中,都是神学的婢女。中国的传统社会,虽无西方那种单一宗教的神学禁锢,但对一切神灵:土地、灶君、玉皇等的崇拜,却表现出了同样的非理性的宗教狂热。中世纪是人类的动物时期。
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虽然使中国传统思维具有非理性特征,但是思维也有其自然发展过程,它则使中国传统思维具有理性的特征。人类学和人类思维发展史已证明,人类脱离了原始社会,就形成了抽象思维能力,虽然这时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但已开始认识世界和人类自己,就像儿童一样,急于问“是什么”和“为什么”。从质上区别客观事物,已成为人类认识当时的主要任务。中华民族早在五千年前就已摆脱了野蛮,进入了文明社会。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有无数的科技发明和创造。这些文明的果实无不渗透着理性的智慧,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其中四大发明等,不仅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直到今天还在造福人类。很显然,缺乏理性的民族,不可能有如此伟大的创造。以春秋战国时期来说,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能力就有了相当发展,作为华夏文化代表的儒、道、墨、法诸学说已富有一定哲理性,它们不仅各自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而且都程度和范围不等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思辨性的哲学范畴和命题。
总之,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思维的自身发展规律,使中国传统思维成为一种既具理性,又带有深重非理性色彩的思维方式。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并存,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围绕这一根本特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派生出一系列特点,如既具逻辑性、分析性,又具直观性、整体性;既是辩证的,又倾向相对主义和调和论;带有强烈的实用倾向等。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这些复杂多重的特征,几乎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支配、统治着中国人的思维。然而到了近代,这种思维方式遇到各方面的冲击,开始发生重大的变革。
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重大冲击的主要力量是新的生产方式——商品经济——的萌芽。我们知道,明清之际,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已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它们的发展虽然十分困难,但已渐渐显示出新生产方式的强大生命力。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借助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直接兴办企业,清政府的一些洋务派大臣和一批买办资本也开始建工厂、办矿山。这些企业虽然带有殖民地性质,但无疑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典型形态,它具有商品经济的一种本质要求:思维的理性。这是因为,商品经济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标志着一定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这种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不仅为人类作为物质实体日益独立于客观世界,而且作为认识主体日益独立于认识客体,直至为与客体彻底分化创造条件。同时,伴随这种独立过程,商品经济还导致个体在社会中的日渐独立。个体的这种独立性,会推进人类理智最终摆脱在自然经济环境中存在着的那种非理性的表象,使每个个体日渐排斥和拒绝集体表象的渗透或影响而进行独立的思考。这是由于,商品经济活动的承担者,基本上是独立的个体,它所有活动依据的应该而且必须基本上是自己的判断。某种共同体自觉和不自觉的强加或渗透给它的种种非理性的表象和认识,基本上已经可能而且必须摆脱。商品经济一方面为推进人类理智彻底摆脱集体表象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与其同生的市场规则,又具有铁一般的性质和残酷性,它要求思维必须明确、理智;非理性的思维,基本上都将受其惩罚。因此,商品经济的洗礼,无论是对整个人类还是独立个体,都提出了思维的理性诉求,它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在此前,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此后“现代哲学”开始产生,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总之,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及其发展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发生变革的主要原因和推动力。
(二)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正处在这样的变革过程当中。这样的社会状况,一方面使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有现实的经济基础,仍然弥漫、统治着整个社会,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人们普遍、习惯的思维方法;另一方面,因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尤其是—些先知先觉者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传统思维方式正发生着近代变革。
青年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并烙上其深深印迹。
如前所说,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思维自身发展规律,使中国传统思维成为一种既具理性,又带有深重非理性色彩的思维方式,即是一种带有深重非理性色彩的实用理性主义。其突出表现为直觉和逻辑的结合、倾向直觉,整体和分析的结合、倾向整体观照,辩证中的相对主义倾向和经学方法(即思维内容的经验性和思维形式的教条性,甚至经典化、神化),主张蒙昧主义等。这些特征,在长期来作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孔孟儒学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和典型。儒学千百年的支配、浸润,使中国人基本上都用这一方式进行思维。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自然也难以摆脱这一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制约。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曾深受以孔孟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传统文化的训导。塾师的教授和父亲的课督,使他熟读儒学经典。当时及后来的一些文稿中,毛泽东推祟和运用儒学及其流变——理学的一些哲学、道德等范畴,充分显露了这种影响的痕迹。
毛泽东当时接受的虽然是封建的正统教育,甚至钦佩、崇拜孔孟,但并非是孔盂的绝对信徒。他在熟读经书的同时,也暗暗阅读了各种“野”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他后来回忆说: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伴随着阅读大量“野”书,他逐渐形成和增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联系自己周围的生活思索一些重要问题。如这些小说里面,为什么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的。这种经历显然对其思维方式理性化的形成具有一定意义。这是因为,经书作为儒学的经典,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不仅汇集和传授着儒学思想,而且集中体现和反映着儒学思维方式的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思维方式的弊端集中地反映在经学方法上,或拘泥章句训诂,或以性命释义理,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实现近代变革。离经从野本身就是对经学方法亦即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倾向的背叛和否定。
毛泽东少年时期思维方式上的这种倾向,促使他更进一步地去接触一些带有理性色彩的历史著作和读书札记等,如《史记》、《日知录》等。他在《讲堂录》中曾写到:“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1]《日知录》是明末清初顾炎武的读书札记,主张实地考察,遇事穷根探源,提倡“经世致用”,以“明道”、“救世”为宗旨。这种力行调查研究的精神和方法深刻地启迪着毛泽东,成为他一生注重调查方法的思想渊源之一。这一时期,他还读了当时维新派的一些书籍,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些书议论时务之得失,阐述改革之必要,不仅具有相当的离经叛道倾向,而且透露出变化是世界之常规的思想。书中的离经叛道和变易的思想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
总之,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一方面接受着儒学的思想教育,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倾向(主要是经学方法)对他有着重大影响,另一方面“野”书中蕴含的反经学倾向,主张实地调查,推崇事物变易等具有理性倾向的思想也对他发生着强大作用。后一种影响与他天生或后天养成的反叛气质、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的结合,成为他日后思想发展的主要基础和方向。
(三)
进入青年时代,在上述思想倾向的基础上,毛泽东与时与世共进,热切地吸取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以及明清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的思想方法,同时,又如饥似渴地接受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变革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从而进一步否定和摆脱了传统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倾向及其影响,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具有近代特征的思维方式。
宋明理学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它主要是以易、道之学的体系为构建自己学说的思想资料,以佛学思辨方法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以传统儒学的人格理论为自己终极目的的一种学说。在思想和认识方法中,它虽有一些合理的、理性主义的成份,但作为整个哲学体系,它则是唯心主义的。在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过程中,它主要继承和强化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非理性的倾向,如它深受象数化的道学和不立文字、直指心性、见性成佛的禅宗以及华严宗的影响。理学大师王阳明在三教合一的发展线索上,会通三家的三性之说,曾折服许多高僧。深受王学影响的李贽甚至削发为僧,使理学陷入佛学。迷信和神学从来是非理性的表现和产物,它是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理学的佛学化,也即表明它的非理性化。
理学也倡导实用化。朱熹曾明确宣扬:“易非学者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朱子语类》卷一○四),所谓“语盂”,就是要使学说政治伦理化,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学说,对於帝王应成为实用的统治工具,对於百姓则应成为“日用”之学,即所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王良:《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文集·答邓石阳》)。理学倡导日用化,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实用倾向的继承和强化,但这种强化,不是推动中华民族的思维具有更强的抽象、推理能力,而是使这种能力凝固甚至退化,以至成为统治术和求生术。
理学还鼓吹经学化。李贽就说:“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于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李贽文集·题孔子像于芝佛院》),认为在封建社会孔子被尊为偶像,是“一犬吠影,众犬吠声”哄抬起来的(《李贽文集·圣教小引》)。
理学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非理性倾向的继承和强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极为深重和恶劣的影响。自此后,陈腐的先圣之言和政治、伦理训条更为严重地充斥世间,成为严密的精神枷锁和罗网,紧箍着人们的头脑,支配着人们的行劲。人们的思维被锁闭在理学规定的框架内,只许信仰,不准怀疑;孔孟之道被奉为绝对真理,视如国定宗教。一切逾越这些“神圣”的东西的思想和行为,都被定为非圣妄法的异端。很显然,这种框架窒息着中国人的思维,一切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难以产生。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在封建社会后期,长期桎梏着人们思想的严密的精致的主要倾向非理性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青年毛泽东在受其深重影响的同时,也发掘和接受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反非理性主义的成分,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的“知行”关系说和“格物致知”说的批判吸收。
“知行”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论先后,知为先”(《朱子语类》)卷五);“问致知涵养先后。曰:须先致知,而后涵养”,“为学者先要知得分晓”(《朱子语类》卷九);认为“如人有此心,去做这事,才成这事。若无此心,如何会成这事?”(《朱子语类》卷七)“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朱子文集》卷五十四)。所以人们应该“事事虽理会知得了,方做得行得” (《论语或问》卷十六)。朱熹的这一思想,青年毛泽东几乎全盘接受。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2]朱熹之所以主张知先行后,是为了强调道德认识的能动性,以提高实践的自觉性,认为做任何事情只有认识其中的道理,才可能自觉地去实行。为此,他特别重视“真知”,即切于自己身心,或“得之于己”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与身心性命直接有关,是一种自觉的认识,只有这种认识才能产生自觉的行动,所谓“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朱子文集》卷七十二)。朱熹特别重视切身经验的思想,毛泽东也全盘接受,他说:“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3];他还强调“其知也,亦系经验而知之”[4]。
朱熹主张“知先行后”,但同时又强调“行重知轻”:所谓“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五),“虽要致知,然不可恃。……功夫全在行上”(《朱子语类》卷十三)。因为他认为,“真知”来自于“行”,所谓“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朱子语类》卷三十二)知的确否、深浅,也都要靠“行”来检验,并在“行”中加深认识。“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朱子语类》卷十四)强调“行”是知的出发点和归宿,“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此理而力行之耳”(《朱子文集》卷五十四)。只有“着意力行,则所学而得者,不为徒知也”(《朱子语类》卷四十六),如果不以“行”为目的去知,或知而不行,只不过是枉知。总之,在“知行”关系上,朱熹又主张“知重行轻”。对于朱熹的这一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学皆起于实践”[5],“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6];他还以语言的形成为例说:“言语在其起原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少之时,即童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7]在《讲堂录》中,他还把“古者为学,重在行事”[8],“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9],“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10]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充分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行”的注重。
“格物致知”是理学认识论最重要的一对范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主要不是为了认识客观世界,获取真正的科学知识,而是通过对“物理”认识,达到对心中“全体大用”的自我认识,即认识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明明德”,“止于至善”。基于此,他一方面把“致知”之“知”解释为主观认识能力及其作用,另一方面又把“知”主要解释为心中固有的道德知识。认为,人心本来具有一切知识,又叫“光明之德”,只是由于主客观的矛盾,这种知识不能实现,要使心中之“知”完全实现而无不尽,就要通过向外求知,即“格物穷理”的方法,而一旦心中之“知”得以实现,就会“豁然贯通”,达到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总之,“格物致知”说的要旨在于推崇主观的思想和道德,把认识、实现心中这种固有的思想和道德,视作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和方法。毛泽东对此充分领会并十分推崇。他一生十分注重哲学和道德,1917年3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指出:“今日变法……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必有本源,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宇宙之真理”在什么地方呢?他认为就在人的心中,“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11],只要把握了这一“本源”,即“宇宙之真理”,世界上便无事不可为。“宇宙之真理”是什么呢?他指出就是思想道德,即“主观之道德律”、“精神之个人主义”。他强调:“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2]而要把握心中的“宇宙真理”,“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认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则沛乎不可御矣!”[13]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手订的“会章”,就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格为宗旨”,把道德品质作为入会的基本的要求。上述言论充分表明,他当时几乎和朱熹一样,推崇主观的思想道德,把实现心中这种固有的道德、思想视作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和方法,只不过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思想,即主观认识能力及其作用就是哲学,更加强调认识、实现心中的固有道德是为了改变世界。朱熹认为,要使心中固有的道德知识得以实现,必须既向内求,也向外求,即一方面向内反思,以求“心中有所觉悟”,达到致知;一方面向外“格物”,以求认知。同时,反思必须经过客观认识的过程,即主体只有在“致知”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我反思。他批评看重反思,认为反思可以脱离“格物”的看法:“若知有未它,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直谓能反求诸身,则不得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成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务求其理,今乃反欲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中庸或问》卷二)毛泽东十分欣赏并接受了朱熹反思必经“格物”、“重行轻知”的思想,提出“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既要有“内省之明”,也要有“外观之识”。他赞同梁启超所说的,要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也表明他主张通过自我反思来达到新的认识和进步。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一方面主张“内省”,认为道德必须建立在自觉意识之上:“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14]另一方面又认为:“主观之道德律”,主要不是在“内省”中、思辨中、修养中实现的,而是应在行为中、活动中、功业中呈现出来。如同他十分重视实践一样,他特别强调向外求识,“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15],提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6]。对于“格物致知”,朱熹还提出要通过积累来达到认识的“贯通”的思想,他反对不顺序渐进,一味“跳踯”的“顿进”之学:“穷理之学,诚不可以顿进。然必穷之,以渐,俟其积累之多,而廓然贯通,乃为识大体者。”(《朱于文集》卷四十九)毛泽东十分赞赏这一“铢累而寸积”的方法。他以“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织。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畜,则终身不得矣”[17]为座右铭。
综上所述很清楚,青年毛泽东曾受理学、尤其是其集大成者的朱熹的深重影响。朱熹理学的唯心主义方面,如推崇思想和道德,把真理看作心中固有之物;朱熹思想方法的唯物主义方面,如重视经验,主张主要向外求知等,都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一方面表明,他当时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倾向,一方面又表明,理性倾向在他思维方式中占据了更大成分。可以说,朱熹思想方法论中的理性成分,使青年毛泽东沿着原有的反经学方向又前进了一步。
(四)
在受朱熹理学深重影响的同时,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王夫之是湖南近代知识界共同崇敬的贤哲,他是我国明末清初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充满了理性光芒。对他倡导的“必以践履为主,不徒讲习讨论可云学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四),“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士文伯论日食》)等“实学”思想,毛泽东十分心服。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经学大师,他开创了对中国近代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乾嘉学派。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毛泽东更是推崇。他敬佩顾“留心当世之故”,注意“经世要务”,对“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以及“足迹半天下”, “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的精神。他还十分称誉颜元、李塨等的习行哲学。在《体育之研究》中,他标举顾、颜、李为一代师表:“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
毛泽东受王夫之、顾炎武等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直接服膺顾、王等人的思想,更深刻之处还在于当时湖南的“湘学”传统和环境。王夫之的实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尤其是在湖南有着巨大影响。晚清道光以降,一大批湘军要员极为钦服王的“言必征实,义必切理”的实学。曾国藩就曾以此思想为据,提出要“重诚”、“求实”。左宗棠则提出“自强为急”、“实事求是”。当时湖南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提出“以实事照实功,以实功程实事。”(《魏源集》)统兵作战的地位和经历,严酷的战争环境,不仅使这些湘军要员在思想上接受实学,而且力行不怠,以此作为经世致用的指导思想,并使首创于王夫之的这种实学思想在当时的湖南蔚然成风,形成“求实”、“求强”的强劲思潮。实事求是作为求学处事、经邦治国的格言,长期风行湖南,形成一种传统。毛泽东一生敬重的先生徐特立,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大门的一块石头上就曾刻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十分景仰“乡贤”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尤其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愚于近入,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8]在将曾与孙中山、袁世凯等比较时,他甚至说:独有曾国藩抓住了世界的“大本大源”。他后来领兵打仗还经常流露出“无湘不成军”的自豪感。至于他后来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更是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影响的深远和深刻。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不仅从顾炎武、王夫之及湘学传统中接受经世致用的思想,从康有为、梁启超处也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康、梁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改革思想的出发点是批判中国传统思想,而其矛头首先指向程朱理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康有为指出,程朱的讲求义理是“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在于“不切于人道”(《论学·来书三》)。考据学把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诱骗到故纸堆中,丧失对专制压迫、民族危机的认识和反抗能力。对于这种阻碍变法图有的学风,康、梁予以痛斥。康有为认为这是“无用”之旧学,责问考据之著再多,“究有何用?”梁说康授课时首先就“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三十年自述》)。康、梁在抨击义理之学和考据学的同时,大力提倡研究学问要致力于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十分崇拜康、梁,梁号任公,他给自己取号为“子任”。
我们知道,青少年时期是人们世界观、思维方式等形成的关键时刻,这一时期接受的知识、思想、方法将基本甚至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品格、素质、思想等。青年毛泽东正好处在一个具有“经世致用”传统的“湘学”环境中,他心目中的圣人顾、王、康、梁等又都竭力宣扬并力行“实学”思想。这种影响的巨大,还在于“实学”、“经世致用”思想与毛泽东当时思想发展的方向极为一致。朱熹理学的看重经验、注重实践,与王的“实学”、顾的“经世致用”,在思想倾向上基本一致。因此经受朱熹理学熏陶后的青年毛泽东接受“实学”,钦佩“经世致用”,十分顺理成章,事出自然,并更进一步、更深刻地强化了他的理性倾向。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当时已基本摆脱经学方法的影响,达到近代思维方式的高度。完全可以说,青年时期接受的这一思想,奠定了毛泽东基本的人生方向和思维方式。
(五)
除了经世致用,康、梁的变易、进化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毛泽东,康、梁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变法,在思想上也就以变易、进化为武器。康发掘、阐述《周易》的变易思想,认为其中的“变易之义”十分深刻,强调“《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郑振铎编:《晚清文选·日本书目志序》);还敏感到变易的趋向是进化,“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在一些文章中还描绘了宇宙间事物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系列。对于这种变易、进化的动因,康还提出了“物必有两”,“有对争而后能进”的观念。梁启超更明确地指出进化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强调“进化者,向一日的上进之谓也,日迈月征,世世不已。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诸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变法通议》)不仅如此,梁还看到,历史的进化不是直线性的,而是螺旋形向前。康、梁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极大地启迪着青年毛泽东。“天下万事,万变不穹”,“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他强调“体育之效”在于动,“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19],由身体之“个别”,他抽象出普遍结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并以此批判朱熹、陆象山等主静之说和佛老“无动为大”、“务求寂静”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所谓“动”就是“抵抗”,就是斗争。“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仑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20]。毛泽东笔记、批注中的这些观点与康、梁显然一脉相承,但这并非说,他关于变易、进化、战争的这些辩证法思想绝对或唯一来自康、梁。由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并渗透在文史哲等各种书籍中,而毛泽东又博览群书,因而不通过康、梁,他也必然会受到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深刻熏陶。只是他作为康、梁的崇拜者更容易接受由康、梁继承和发挥了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这些思想罢了。
毛泽东青年时期,对他有深重影响的还有一位资产阶级维新人士严复。严复是以翻译、介绍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知名于世的。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力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为武器,宣传“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天演论〉导言十八案语》)的进化思想。他以生物进化规律为证,强调社会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指出进化乃“虽圣人无所为力”。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国力富强”、“船坚炮利”,关键在于自然科学发达,而科学技术的发达,又在于运用了新思想方法。“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牛顿——引者注,下同);舟车之神,可推其源于瓦德(瓦特):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哈维)之是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原强》)“所以逻辑者,以如贝根(墙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穆勒名学》),这就是说,逻辑即科学方法是一切科学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接触严复的著作是1912年秋至1913年春,其时他正力图通过自学来提高自己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退学后的文化水平,其中《天演论》他读得较为认真。他后来对这段学习生活曾有深情的回忆:“我正象黄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只顾着了吃!”称这段时期“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这种经历无疑说明严复的著作当时对毛泽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事实也确实如此。1920年11月26日,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的信中曾谈论四种常见的“论理(逻辑)的错误”:以感情论事,以一时概永久,以部分概全体,以主观概客观。他自信地说:“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21]。无疑,这些话反映了他注意从逻辑的角度正误自己的言论。在以后的革命活动尤其是教育干部的著述中,他十分注意形式逻辑问题。对于干部教育,几乎无时不把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摆在首位。至于他强调哲学的方法论功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掌握和运用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表明他对思想方法不是一般的重视,而是提到了根本指导方针和决定革命胜败关键的高度。当然,他对形式逻辑尤其是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并非唯一而且可以说不是主要来自严复的影响,而是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把握和对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然而也无疑与严复的逻辑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思想一脉相承,甚至可以推断,即滥觞于此。
康、梁、严等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不仅宣扬经世致用,主张变易,推重科学的思想方法,而且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的经学传统。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已陷入理学所规范的经学泥坑,经学方法成为当时中国思维方式非理性倾向的集中表现,因此,批判经学传统,冲破经学方法的藩篱,成为当时中国思维方式变革的根本要求和首要任务。维新派闯将梁启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方法是培养奴性的方法:“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官”(《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他愤慨地指出,定孔教于一尊,“强一国人之思想出于一途”,必然导致“学说隘而思想室也”(《新民说·论进步》)。他倡导自由独立,号召摧毁传统,并自求为陈胜吴广(《与严又陵先生书》),要在思想界起义造反。严复也认为这种方法是“循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严复集·救王决论》),甚至痛心疾首地说:“天下之最可哀而令人悲愤者,无过于一国之民,故纸而外,一无所知”(王栻:《严复传》);指出笃信经典,“好古而忽今”、“强物就我”的方法,“其为祸矣,始于学习,终于国家”(《严复集》)。他还尖锐地揭露了作为经学方法产物和制度的制艺八股是“锢智慧、怀心术、滋游手”。康、梁、严等对经学方法的批判,也深刻影响着毛泽东。他当时深切痛恨旧中国之“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它是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提出要发动一场思想和道德领域的革命。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提出的“主观之道德律”、“精神之个人主义”,正是他用以打碎精神枷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的青年学友张昆弟记于1917年的日记中,显露了他还曾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我国国民思想狭隘,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应该有托尔斯泰这样的大思想家来冲冲这种罗网,以真理为归。[22]这些言论,既是对封建道德的抨击,也是对经学方法的批判。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他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将形成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时代,既受到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代表的孔孟经学的严重浸染;也受到既推崇道德,又注重经验的朱熹理学的深重影响,还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理性倾向的主要代表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强烈感染;更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近代变革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行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强烈影响。他热切地吸取了他们关于注重经验、注重实用、主张变易和注重逻辑、注重分析等理性的、辩证的思想方法的思想。由于他主动、大量和反复地吸取这些思想,以及他本身具有的素质和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反叛经历的影响,使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摆脱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倾向即直觉整体、相对主义、经学方法的束缚,而具有理性的特点。这种理性,不仅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理性倾向的继承和发扬,而且带有近代的特点。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毛泽东在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批判、继承的过程中,也基本形成了近代的思维方式。
(六)
虽然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已基本具有近代特点,但他当时并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非理性倾向的影响,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有着悠久历史、深厚基础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倾向的熏染。这不仅因为,作为思维方式,如前所述,它是经过千百次的反复实践才得以形成的,尤其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它已有几千年文化沉积的哺育;更主要的是,作为这一思维方式物质基础的自然经济,当时还以完整的和主要的形态存在,而作为近代思维方式物质基础的商品经济,则力量还很薄弱,还受到封建专制的压制,而且由于物质生产落后,社会没有可能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技术手段去促使人们研究作为近代思维方式生长根基的主要以自然为对象的工业和科学。这种社会、历史状况也就使毛泽东当时完全、彻底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完全确立近代思维方式,缺乏现实的物质条件。这也就决定,这种思维方式的完全变革,只有依赖于先进思想及其方法的观照。正因为如此,青年毛泽东当时还残存着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倾向。这种倾向不仅深入潜意识,而且裸露在表层,其突出的表现是毛泽东当时还存在思辨和相对主义的倾向。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谈到生死等问题时说:“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23]生与死完全等同,否定两者之间有根本界限。又说:“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24];又在一切对立的双方之间划上等号,抹煞它们之间的区别。这种相对主义倾向使他提出了一些根本违背形式逻辑基本原则的论断:“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以为便利言语记忆计也。”[25]这种论断表明他对辩证法的了解不仅仍具有相对主义倾向,而且还具有唯心主义倾向。这种唯心主义倾向也就使他当时的思维方式还不可能完全遵循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而总是不免带有经学的脱离实际的思辨色彩。如他力求从精神方面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表现出对社会实际问题的一定程度的轻视,推崇“人类只有精神生活,而无物质生活”,向往于“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然而无论如何,这些倾向在他整个思维方式结构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只是主导思维方式确立不够成熟、不够彻底的表现。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质已不是传统的,而是近代的。毛泽东青年时期思维方式的近代性质以及他的发展趋向,为他今后接受近现代最科学的思维方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确立了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