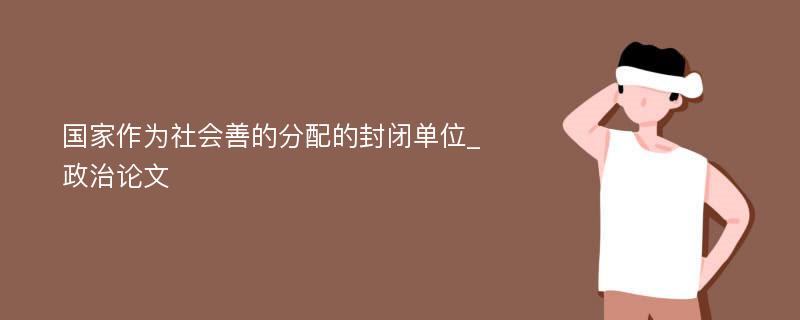
国家作为分配社会善的封闭单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论文,单位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2 自近代主权国家出现以来,国家已经逐步演化成为分配社会善的封闭单位。而且,在当代和可以预见的将来,现代国家仍然是保障一国公民安全与福祉的最为有效和最为经济的途径,现代世界仍将由这样一种基本的单元所构成,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仍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强化和保护,完全开放的自由边界仍遥不可及。对于这里所描绘的这样一个事实,诸多的流行政治哲学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诸理论(大都视封闭特性为敌,故而)采取了一种忽视乃至敌视的态度,因此失去了解释这样一个基本政治现实的能力与机会。要想回答国家何以作为分配社会善的封闭单位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最好的方法,还是需要回到政治现实主义的解释路径中来。 本文借鉴威廉姆斯(他被认为是最近几十年来政治哲学中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的几个重要的理论判断,来重新理解由韦伯(这个政治现实主义大家)在一百年前所做的关于国家的经典定义。通过这种重新理解,我们将有望得到一个比韦伯自己原有的定义更为丰富的理论解释。在这样一个新的解释中,韦伯关于国家定义中所包含的“至上性”、“疆域性”与“正当性”这三个要素将被突出和强化,而且将有效地解释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国家的封闭性问题。对应于这三个要素,一个饱满意义的现代国家将同时满足“足够强大、足够统一、足够规范”这三个标准。 一、为什么是“国家”?何以要选择“现实主义”? 要想回答国家何以以一种封闭形式分配社会善,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善需要由国家来分配?因为本文标题所作出的判断,会让一部分人误以为国家是以一种封闭的形式包揽所有社会善的分配。而事实上,诸多社会善可以通过其他制度与机制来更好地完成分配,比如家庭、友谊、教会、慈善机构、兴趣团体、市场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国家则只是通过选择分工,肩负起它不得不去完成的一些特殊的社会善的分配。 正是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前边的追问也就需要进一步转化为对下述另外一个问题的追问:什么样的社会善不得不由国家来完成?这样一种追问考虑和照顾到了社会善的其他分配形式,但是同时以一种倒逼的形式,将一些“不得不”由国家来完成的社会善的分配形式廓清开来。考虑到国家是政治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化产物,因此,上述问题就可以再进一步后退,变成追问:为什么政治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独立领域?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穷尽了各种可能,却仍然不得不将一些问题纳入到政治领域来考虑?这一追问,已经触及到了“政治的自主性”问题。我们不妨将人类穷尽了所有其他的可能,仍不得不保留“政治”这样一个独立领域的主张,称作关于政治存在的“硬核论”主张。这种主张认为,政治生活所处理的,就是作为一种硬核被保留下来,无法被人类其他制度建制或其他生活形式来加以有效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因其特殊性而被保留下来,我们只能够通过国家这样一种特殊的建制来处理这些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区分开那些“依赖于特殊的政治建制(在本文中,我们特别考虑到通过国家)而进行分配的社会善”和“不依赖于特殊的政治建制而进行分配的社会善”。我们因此也就作出判断,主张国家不就所有的社会善进行分配,但是它仍就相当多的社会善而进行分配。而本文所讨论的,就是那些“不得不”依赖于政治而进行分配的社会善。需要特别交待的是,本文只就这样一种社会善分配得以可能的典型的形式特征即其封闭性展开讨论,而将与此问题相关联的善清单问题,政治的自主性问题等等留待其他合适的地方来加以处理。 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确有不少研究者没有能够意识到社会善的分配具有上述讨论到的多样性。因此,他们经常会拿人类摸索出的其他善分配的形式来否定或诘难政治存在的必要性。比较典型的和为我们所熟悉的就是,人们经常会以市场进行社会善分配的有效性来否认政治存在的必要性。很显然,这两种不同的善分配的形式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并非彻底相互替代的关系。我们有理由优先选择更少社会代价的善分配形式,但是我们也有必要认真面对一个“不得不”被选择的“国家”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形式。 本处需要先交待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本文采纳的是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这样一种立场对以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立场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因为政治现实主义主张政治要考察“权力”以及其规范对应物如“正当性”等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权力以及权力的冲突与竞争,被现实主义认为是政治的本然之意。而回避谈论这样一种本然之物,转而去谈论理性与道德,或者去谈论如何以一种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的方式去消弭权力冲突与权力竞争,在现实主义者看来,都是在用一种“去政治”的方式谈论政治。很显然,政治现实主义持有一种“冲突论”的政治主张,而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则持有一种“和谐论”的政治主张。我们采纳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就是要围绕“权力”及其规范对应物“正当性”来展开对于近代国家的理解。 通过后文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只有采纳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才能够正面去面对和说明国家本身所具有的“疆域性”特征,并且将国家本身同时所具有的“至上性”与“正当性”特征给出一个更为妥善的处理。可以说,近代国家所具有的“封闭性”特征首先需要“疆域性”和“至上性”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说明。而所有的自由主义理论都不愿意面对近代以来国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封闭性”特征。因此,才出现了“疆域性”特征长期不被理论讨论所重视的情况。而且,在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视野中,传统上特别为自由主义所重视的“正当性”特征,也只有在与“疆域性”与“至上性”嵌套在一起进行讨论时,才能够发挥其对现代政治生活更为充分与更为妥当的解释。 二、霍布斯与“至上性”,洛克与“正当性” 威廉姆斯提出“霍布斯问题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这样一个判断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的判断,其目的是要回到谈论政治的本然之物“权力”上来。这样一个判断自然牵涉到复杂的理论争议。我们这里暂时搁置这些争议,径直运用这样一个判断来理解近代国家。我们首先来看,顺着威廉姆斯的这样一种判断,我们可以如何来重新理解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 根据公认的理解,霍布斯问题即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冲突,实现和维护政治秩序的问题。为此,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理论,认为自然状态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为了结束这样一种战争状态,霍布斯提出,需要一个使大家都慑服的“共同权力”。“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霍布斯,第131页)这样一种共同权力,即“至上权力(sovereign power)”,其最终的抽象物,就是我们后来所熟悉的“主权(sovereignty)”。至上权力的基本特点是至大无外,也就是说其威慑能力应该能够覆盖至每一个人。在霍布斯这里,这样一种至上权力的存在,是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的开端条件,但它仅仅是一个条件而不是故事的全部。霍布斯的目的,是要以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条件为前提,强制推行一套规则体系。他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称作“主权者的命令”或“主权者的意志”。我们现代人都知道,他所说的这样一套规则体系,就是一套法律体系。因此,霍布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理论,是要以至上权力为后盾,强制推行一套法律规范。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霍布斯给出的政治理论,其基本特征就是“强制说理”。但是很显然,这样一种解释违反了我们现代人的基本直觉。我们的直觉通常认为:“强制不说理,说理不强制”。但是霍布斯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套可以推行开来的说理规则,必然是以一个具有非理性特征的强力为后盾。因此它可以说是一套政治制度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霍布斯本人甚至认为它是一套政治制度得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很显然,为了能够接受霍布斯意义上的对于政治特性的理解,我们就必然需要修正我们的直觉。 以强力为后盾强制推行一套规则体系,这可以被认为是霍布斯对于政治的基本理解。在这样一种理解中,霍布斯的理论具有两方面的独特贡献:第一,以强力抑制人类激情中可能的破坏力量。在这样一个贡献中,有理论家认为霍布斯需要提供一种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但是也有理论家认为无须这样一种假设。后一种观点最典型地体现在《利维坦》中所阐发的“先发制人”的主张中。按照这样一种主张,不是因为人性的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是由于对他人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个人的恐惧,从而促使每个人不得不预先处于一种防备状态。这样一种主张事关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并不需要预设人性的善恶。“先发制人”源于恐惧,而恐惧的不当指向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防备。而主权(即至上权力)的出现,就是结束个体的人之间的破坏力量涌现的一种改进方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霍布斯的主权学说是对于人类政治面貌的一种深刻的真理性认识,这一学说的出现为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石。主权的出现,使得人类生活即便暂时还没有规则,起码已经可以产生基本的秩序;第二,同样深刻的是,霍布斯的主权理论进一步主张了一种“强制推行的规则体系”的主张。这里所说的强制性,已经相当于我们所处理的“任意性(arbitrary)”,其重心是要说明规则体系与规则推行得以可能的开端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说,以强力为后盾,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得以可能构设与推广。这一主张最终促成了霍布斯的法学思想。法律规范是主权者的意志或主权者的命令,就其开端来说,它是任意的,但它显然又不是随意的。 霍布斯的理论自然是自上而观之,重点考察权力的集中使用(即主权)在形成人类政治生活秩序中的作用。而稍后于霍布斯的洛克,则为我们提供了自下而观之的政治理解,也即考察对于权力集中使用的限制,从而提供了一种关于政治的规范对应物即“正当性”的理解。我们也都承认,基于“正当性”来谈论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是洛克对于政治理论的重要贡献。 洛克主张一种古典意义的自然法思想,认为自然状态是美好的,认为人类在有政治生活之前,存在着社会生活。这些主张都与霍布斯有所差异。但是,洛克也同样主张应该有政府的存在,主张有权力的集中使用即有至上权力的存在。不过,洛克对于权力的集中使用给出了诸多限制,比如说他认为这一政治权力应该用于公共善,尤其是需要得到人们的同意。任何未经同意的权力都是不正当的。因此,“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洛克,第11页)我们可以将洛克所定义的“战争状态”与霍布斯所定义的战争状态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洛克意义的战争状态起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第二,个体公民对政府的战争状态。前一种战争状态与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定义外延一致,且解决这样一种战争状态同样需要诉诸霍布斯意义上的“至上权力”。因此,我们可以对洛克的理论贡献进行紧缩,认为他的主张其贡献是提出了“个体公民对政府的战争状态”,而其解决方案则是“至上权力”的使用需要“正当性”要求。 这里我们要插入威廉姆斯的第二个政治判断:政治正当性是分级的。在威廉姆斯看来,“我们可以接受支持正当性是分级的这样一种主张。在正当/不正当之间作出截然二分,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只能服务于特定的目的。”(Williams,p.10)这个主张将人们对于政治正当性的要求进行分级,认为存在着满足“基本合理的正当性要求”的国家,也存在着满足“充分合理的正当性要求”的国家。无法想象一种政治制度要么是正当的,要么就是不正当的。这样一种截然二分无法解释历史意义上的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同样也无法解释共时意义上的有着不同实际表现的现实的政治制度。而一个合理的政治正当性概念应该是一个可以区分不同等级要求的概念。如果用这样一种思想来反观洛克的主张,我们会说洛克对于近代的政治制度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政治正当性要求”。也就是说,洛克实际上是想说,一个政治制度对于被集中起来的权力的使用起码应该满足“最低限度的政治正当性要求”。我们也可称其为“基本合理的正当性要求”。对应于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有望设想一种“充分合理的正当性要求”。 对于“正当性是分级的”这样一种主张,我们暂时抛开其对于“正当性”概念的考察不论,专门运用其“分级”考察的主张。可以说,这样一种分级考察的观念同样适用于霍布斯结束自然状态的方案。也就是说,当霍布斯提出以“至上权力”为手段结束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时,他也首先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为了分别结束两人所担忧的战争状态,人类政治生活同时需要满足“最低限度的至上权力”与“最低限度的正当性要求”。我们分别将这两个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称作“霍布斯条件”与“洛克条件”。“霍布斯条件”是人类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开端条件,但它同时也是政治生活内部的调整性条件。而“洛克条件”则仅仅是政治生活内部的调整性条件。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主张,“霍布斯条件”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可能具有优先性。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应该相互限制、相互约束。鉴于这两个条件本身的相互限制与相互约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相互牵制特性,因此,如何审慎地在这两个条件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就是一件政治理论家与政治实践家都需要认真处理的技艺性工作。这样一种审慎特性,正是政治现实主义所特别强调的政治美德。 总之,“霍布斯条件”与“洛克条件”相互约束,构成了近代以来国家观念的底线主张。这样一种主张已经基本符合了后来韦伯所定义的国家概念:“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韦伯,第55页)但是,上述分析只是涉及了韦伯国家定义三个基本要素中的一些要素,却仍然明显忽略了另外一些要素。我们有必要在下文中进一步展开讨论。 三、借助“此时此地”主张找回“疆域性” 在韦伯的国家定义中,集中出现了作为现代政治核心特征的三个关键词汇:疆域、正当,以及因暴力垄断使用而形成的主权。这三个词汇对应着韦伯对于现代国家三个关键性要素的强调,也即:A.至上性(Supremacy);B.疆域性(Territoriality);C.正当性(Legitimacy)。 在本文看来,只有分别地与交互地理解了这三个要素的基本含义,才能够对于现代国家的封闭性特征给出一个饱满的、充分的解释。对照这三个要素可以看出,我们上述关于霍布斯与洛克理论的分析分别处理了“至上性”问题与“正当性”问题。也可以说,我们是对韦伯的国家定义中所包含的现代国家应该“足够强大”与“足够规范”这两点作出了一个交待。但是三个要素中的“疆域性”即“足够统一”的问题并不在我们上述的分析中。那么,“疆域性”到哪里去了?我们如何从理论讨论中找回“疆域性”?是什么样的理论预设造成了我们对于“疆域性”特征的忽视乃至回避?如何才能够从理论的讨论中找回被忽视了的“疆域性”?本文认为,我们可以从政治现实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找回“疆域性”。忽视乃至回避“疆域性”,乃是理性主义理论自身缺陷的必然后果。为了找回“疆域性”,我们需要引出威廉姆斯的“此时此地(here and around now)”的主张。 威廉姆斯对当代康德主义者柯斯嘉思想中所包含的“康德时刻”(Kantian moment)(Korsgaard,1996,p.217)的主张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里提到的“康德时刻”,说的是理性主义者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尤其是在思考实践哲学的问题时的一种理论假定。这种假定认为,我们人类都是有理性能力的,即便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还不能够就特殊的问题达成理解,但是在抽去了特定人的特定时期的理解之后,我们能够想象,只要人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那么在某个特定的极限时刻,人们注定会就某些问题达成一致的、无差异的结论。 柯斯嘉曾经提出,我们可以设想,在我们的反思平衡中,或者说在经过了人类的多次博弈选择后,我们有希望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点。在现实的人类选择中,任何人都有可能希望得到起码不低于该平衡点的对待。我们把这个起码不能再低的平衡点要求称作社会公平的观念,也即正义观念。这样一种观念将蕴涵着普遍无差异的道德要求,柯斯嘉把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推理过程而获得理解的理性观念称作“无条件的理性观”。(Korsgaard,2003,p.59)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当我们去考虑“某些人在某些时候还不能够就特殊的问题达成理解”时,我们是在讨论人们“此时此地”的状况和问题。而当我们讨论假想中的“在某个特定的极限时刻,人们注定会就某些问题达成一致的、无差异的结论”时,我们是在诉诸一种“彼时彼地(then and around there)”的观点。 在实际的讨论中,所有的康德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都会最终诉诸“彼时彼地”的观点。当有人提出实际的状况是有的人持有某种终极立场,而有些人就是持有现在这样一种立场时,大部分康德主义者就会说,我们讨论的不是这种实际情况,而是某种可以想象的理想状况。在那种状况下,因为人们拥有理性能力,并且只要我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耐心,让我们多等待他们一会儿,他们早晚都会就这样的一些问题达成一种共同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当代持康德主义立场的人,其立场态度的强弱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的人持一种强立场,坚持认为人类理性活动最终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另外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则在康德立场与所观察到的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之间犹豫,他们注意到人类实践是这样的,而康德主义的处理方式是那样的。依凭直觉,他们也承认人类实践似乎的确有无法完全通过康德主义加以处理的问题。 康德主义者所坚持的这样一种无条件的理性观对于人的假设就是:人是一种理智的动物。紧随着这个假设的第二个假设就是:理智反思的产物要比不经反思而展开的活动更可取。在这样两个假设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就是:未经反思的生活不是好生活。这是一种在人类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传统。正如其名称所体现的那样,它的麻烦就在于,它过于强调了理智在人类生活和理解人类生活过程中的作用,以至于认为所有未经理智审视的生活都不是好生活。并且最终假设,人必有理智,且必然能够通过运用理智达成对于指导人类实践的道德规范与法律和政治规范的根本理解。当然,这种根本理解本身还应该是普遍无差异的。也就是说,从认识者角度来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一种无差异的统一理解。而从规范的角度来说,这种规范最终也会无差异地同等适用于每一个人。非常明显,这样一种观点预设了人在理智生活这件事情上的地位和能力的平等。柏拉图显然是这种传统的代表。当代持有这种立场的人经常私下会说:不诉诸人的理智或理性,我们又能怎么样呢?这种看法的假设就是,无法想象不运用理智来审视的人类状况。 当然,在涉及实践哲学的问题时,理智主义的确还为其他不同立场的持有者留下了讨论的可能基点。这个基点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理智主义者,还基本上都承认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人们的实际认识可能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与其他立场的区别在于,理智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最终加以克服的基本事实。理智主义对于人的这些假设,再加上前边讲到的站在“彼时彼地”立场而坚持的一种“无条件的理性观”,就构成了理性主义者心目中讨论人类道德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期许。这个期许的结果,就是设定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目的王国或政治理想国。在那样一个时刻,在那样一个地方,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认识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的存在,并且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认识到与理想王国得以可能的配套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就是理想王国本身得以可能的基本保证。很显然,(尽管我们在康德那里也看到了关于德福不匹配问题的讨论,不过,在哲学史的讨论中)这种理性主义经常与善良意志论配套运用。它假定人有善良意志,并且假定人们可以通过善良意志的运用达成社会和谐。而人的理性能力则是达成这种社会和谐的另外一种前提保证。 威廉姆斯把与这样一种传统所对应的政治哲学主张称作“柏拉图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柏拉图问题”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被威廉姆斯称作“马基雅维利问题”:“从柏拉图那里继承下来的好人的概念产生了好人根本上如何才能有所作为的问题,而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世界的概念则提出了任何人面对这个世界如何才能有所作为的问题。(‘现实主义’的一个流行含义就是从如下事实中得到了其力量的:即使第一个问题没有答案,但第二个问题是有某些答案的。)”(威廉斯,第96页)威廉姆斯这里所提到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此时此地”的世界。这个世界面对的是具有个体差异的个人,是一个既有理性反思能力,也有情感、意志、气质、禀赋,并且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系统,同时向偶然性洞开的个人。因此,威廉姆斯要处理的是一个并不诉诸理性可达到的极限的、“此时此地”的、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威廉姆斯的主张反对理智主义假设,而且可以说是系统地反对理智主义假设。威廉姆斯认为“马基雅维利问题”才是一种真正的政治问题的开端。因为,假如人类真的都能像理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最终都达成一种理性可及的极限状态,则分歧与差异就都会消失。然而,一个无歧异的理智人的世界不是一个政治世界,而是一个哲学王的理想世界。而政治问题要想可能,政治哲学要想可能,就需要抛弃“彼时彼地”的主张,现实地面对“此时此地”的人及“此时此地”的问题。 “此时此地”的主张,不可避免地要让我们面对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而理性主义的“无条件的理性观”必然主张价值的一元化。或者说,理性主义者可以策略性地接受价值本身的多元存在的局面。但是理性主义的假设必然是,这只是我们开始工作的起点,通过运用人类的理智,我们最终可以达到价值和规范的一元。因此我们可以作出判断说,理性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一元论。 政治现实主义的“此时此地”主张,其思考问题的方法是描述的、视觉的与当下的。当下感意味着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的承认。当下感也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处理一个“是”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处理一个“应当”如何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当下”的事实,提出一个“应当”的要求时,我们就是在同时否定当下,主张一种超越当下的未来状态。这种否定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否定。在时间意义上,“应当”向我们承诺了一个未来,“应当”状态的呈现也只能够在未来得以兑现。因为,现在已经被“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占据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既有状态的否定的方案,注定都只能够是“理想主义”的。“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为我们所承诺的解决方案和可解决方案都注定是“理想主义”的。“这里就是罗德岛,就在这里跳舞吧。”面对现实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嘲讽,理想主义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注定只能够是指向未来的。 因此,当且仅当在接受了一个可以看到的,作为现状而被观察到的对象时,我们才能够把一个单纯理论的问题与人类实践相关联的现实问题结合到一起。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候,才出现了一个需要且只能被政治地加以解决的问题。这样一种对于现状,或者说对于“既定状态”的接受,被人们称作“现实主义”。而当我们“接受了一个可以看到的,作为现状而被观察到的对象”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充分强调被处理对象的“空间性”与“视域化”特征。或者说,当我们强调“此时此地”的主张时,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留驻了被处理对象的“空间性”特征与“视域化”特征。(同样,“他者”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空间性”与“视域化”特征的基本概念。)尽管我们还要加上一句,基于一种审慎的美德,不可过分强调这两个特征的排他性。 “此时此地”的主张在面对国家问题时,必然就会突出主权概念中的“疆域性”。如果不是政治现实主义,我们就不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接受和强调既定状态的主张,也就不可能把“既定状态”作为我们必须严肃面对和接受的政治问题。自由主义不愿意接受“既定状态”,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主张甚至轻率地无视“既定状态”。只有接受了现实主义,我们才能将“既定状态”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存在接受下来,并且进一步将其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加以处理。在这里,我们把“此时此地”的主张视为我们能够理智地接受“国家作为分配社会善的封闭单位”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前所述,“至上性”说明了(在政治意义上的)权力的至大无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至上权力(sovereign power)或主权(sovereignty),落实为规则体系或治理的原则,就是一套融通的、封闭的、对内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与霍布斯以来的政治现实主义主张密切关联,法律实证主义(霍布斯本人就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先驱)对于法律性质的刻画,均是以承认至上权威的存在为基本前提。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眼里,法律体系是封闭的、自主的与自洽的,因而也就表现为对内的普遍一致性。“至上性”体现了现代国家在法理意义上的封闭性。 而“疆域性”则关联于政治现实主义者所特别强调的“既定状态”概念,是在空间意义上和“此时此地”意义上承认一种既有事实。只有至上性本身虽然构成一个规则封闭,但是并不构成一个有形的具体封闭。一个有形的具体封闭观念依赖于我们这里所作的对于政治问题的现实主义方法的植入。这个植入就是把我们在“此时此地”所具体形成的人,以及此时此地具体形成的政治现状加入到我们的考量。只有在接受现状如此时,我们才有了一个可以看到的封闭单元。这个封闭单元才是一个政治的单元,而非一个被窄化后的理性主义的单元。 传统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都忽略了“疆域性”这样一种观念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一直把“疆域性”作为一个不得已而需要提及的底线概念。而在经过我们的解释之后,加上我们对“至上性”相关的一些概念含义(强制说理)特征作出强调说明之后,就可以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有地域限制的、封闭的治理体系,或者说,构成一个“现实的”封闭性概念。 四、国家定义三要素之相互嵌套 在本文看来,在韦伯的国家定义三要素中,“至上性”塑造了现代国家形态,“疆域性”落实了现代国家边界,“正当性”则充实了现代国家观念。或者说,“至上性”提供了现代国家法理意义上的(de jure)封闭性,而“疆域性”则提供了现代国家事实意义上的(de facto)封闭性,这两点合在一起,就已经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实质性封闭。也即既有一套封闭实行的法律规则体系,通过主权者的至上权力为后盾在一个国家内强制推行;同时也有一个完整清晰的疆域概念,通过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不同国家彼此相互承认。并且也通过主权国家的至上权力来确保这样一种事实上的疆域封闭。一个国家只在其内部行使对其公民社会善的再分配。 但是,只有A+B,就只能够说这是一种关于现代国家的消极意义上的封闭性解释。只有当A+B+C之后,才能构成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完满意义上的封闭性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加入“正当性”的考量,我们才能够获得对于国家封闭性的一个好的说明,或者说,我们才能够获得一个充实的封闭性。受到韦伯的启发,我们都承认现代世界进入了一个自我合理化的过程。而与合理性概念相关以后,正当性概念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我们所期望的善清单。这样的善,既与人类欲望的多样性相关,也与价值的多元性相关。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韦伯的“正当性”概念如果与他的“合理性”概念或“合理化”概念结合起来,自身本来就可以构成一种具有动态特性的现代国家概念。但是近代以来的“正当性”概念被不少的自由主义者解释为一种静态的概念,即一种要么正当要么不正当的二分。因此,在这里我们才提出,有必要引入一个威廉姆斯意义上的“正当性是分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主张。 从文献上看,威廉姆斯这一主张并不直接针对韦伯而发,但是威廉姆斯与韦伯的主张关系密切,他对于韦伯见解的赞赏几近于他对尼采的欣赏。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说,威廉姆斯的主张是对韦伯合理性主张的明确化。同时,如果把威廉姆斯关于“评价、价值、规范(性的来源)”以及“有历史的哲学”等主张结合起来考量,我们事实上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关于“合理性分级”的主张。而且,一个更为激进的方案,就是将关于人类实践的评价问题全部化解为关于价值规范的来源问题。从而,所谓实践理性问题,不过就是一种合乎人类规范的“合理性”问题。而公共生活的合理性问题,则其本身就注定是属于特定历史的,因此是分级的和动态变化的。 威廉姆斯的主张不但与韦伯的主张有关联,而且可以强化韦伯所说的“脱魔世界”中的“合理化”主张与价值竞争主张。可以说,威廉姆斯所表现出的对于韦伯的欣赏与接受是无条件的,他们都主张在一个完全世俗化的世界里,谈论一个价值相互竞争(都接受人类竞争与冲突是永恒的),没有外在评判标准存在的人类状况。因此,他们对于近代以来这样一种基于人类自身的制度成果都是接受的。而且,在方法上,他们都是描述的。在结果上,他们都对人类实践合理性这样一种内在化的标准给予充分强调。而正是这样一些特性,决定了他们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加入威廉姆斯“正当性是分级的”这样一种概念主张,是想要说明上述A+B+C是动态的,而如果只有A+B,则这样一种概念通常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静态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威廉姆斯的这些新近主张再次挑明了韦伯主张中“正当性”概念与“合理性”概念的关系。威廉姆斯的贡献就在于,既然合理性概念是依赖于人类价值旨趣的评价性概念,则它必然是历史的和分层级的。一种截然二分的正当性概念不过是一些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一种偷懒。 如果合理性是分级的,从而正当性是分级的,那么近代以来的国家概念就应该可以被理解为,它是一种可以从一种薄版本的国家概念向一种厚版本的国家概念滑动(shift)的过程。这样一种滑动,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国家的更多要求。韦伯之后一百年以来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已经表明我们人类的确对现代国家应该发挥的功能有了更多的要求。自1948年联合国成立以来,联合国大部分的成员国都签署和接受了三个版本的不同的“人权公约”,我们国家更是将“保护人权”写入了宪法。 如果再加入新近为政治理论界所关注和讨论的“失败国家”与“成功国家”的概念,我们就可以发现,失败国家就是自身连基本的政治秩序都无法保证。而且,不但其自身无法完成维护其基本秩序的功能,就是在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完成这样一种基本要求的国家。也就是说,失败国家就是一个无法满足“霍布斯条件”的国家。而一个正常的“成功国家”应该具备韦伯国家定义中的上述基本功能。一个饱满的“成功国家”则进一步成功地发展出了自我创新能力,不但自身能够持续成功,而且能够带动关联国家持续发展。因此,成功国家实现了包括“洛克条件”但不限于“洛克条件”所提出的诸多现代功能。可以说,我们已经为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注入了越来越丰富的内在含义。而正是“正当性”现代含义的不断丰富,才为我们不断撑开了我们自身对于现代国家应该发挥的功能的理解。 以“至上性”和“疆域性”为特征的现代政治主张,是对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实政治所具有特征的一种真理性认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由这两种特征为代表的现代国家将继续表现为一种“封闭的”治理单元。这样一种“封闭性”仍然是对现代政治现实特征的一种真理性认识。相对于这两个特征本身所表现出的事实性特征,“正当性”特征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一种规范性特征。现代国家如果无法满足“正当性”这样一种规范性要求,则其本身一定只能是一种干瘪的,最低限度的底线国家。而只有在不断满足人们对于现代国家的这样一种规范性的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够使得现代国家的内涵变得更加饱满与充实。 我们可以把马基雅维利看作是“疆域性”,即“事实意义上的封闭性”主张的代表,把霍布斯看作是“至上性”即“法理意义上的封闭性”主张的代表,而把洛克看作是正当性即我们后来所说的社会通向善改进主张的代表。只有将这三个基本要素相互嵌套在一起进行理解,我们才能够获得关于现代国家封闭性的充分说明,也才能够理解国家何以通过封闭方式强制分配社会善。 我们提出,现代国家事实上可以从三个方面为我们大家所期望。也就是说,我们期望现代国家应该“足够统一、足够强大、足够规范”[国内学者任剑涛在其近期的论文中注意到了现代国家的这三个标准(参见任剑涛,第189-204页)]。它们分别对应着本文所分析的“疆域性”、“至上性”与“正当性”。一个理想的现代国家,应该是“大政府、大社会”,而不是“大政府、小社会”。大政府不是臃肿,而是应该拥有与其现代功能搭配精当的强大能力。它应该足够强大,足以保证社会秩序与社会规则体系的推行,同时也足以保证既有领土的完整性。但是它也应该足够规范,足以让其疆域内的公民能够更愿意接受其本身疆域内的现有生活模式,而不是采取以脚投票的方式,另寻他们心目中的希望之乡。标签:政治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古典自由主义论文; 至上主义论文; 洛克论文; 哲学家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